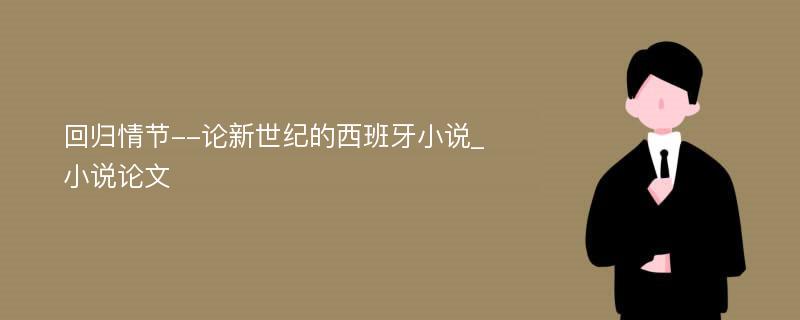
回到情节——新世纪西班牙语小说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班牙语论文,新世纪论文,情节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里士多德把情节当作文学的首要问题,认为它是一切悲剧的根本和“灵魂”。因此 ,在悲剧(或《诗学》)的六大话题——要素——中,情节列第一位,之后依次是性格、 语言、思想、场景和唱词。当然,情节和故事原是不同,情节或可说是经过艺术加工的 故事,但绝对不是脱离故事的观念和技巧。然而,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无论是亚里士多 德的情节崇尚还是以“莎士比亚化”为标志的文学传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挑战。首先 ,浪漫主义文学是比较典型的观念文学。浪漫主义把情节降格为文学内容的某个轮廓, 认为这种轮廓可以离开任何具体作品而存在,而且可以重复使用、互相转换,可以因具 体作者通过对人物、对话或其他因素的发展而获得生命。这基本上把情节降格到了某些 故事套路甚至俗套的地步。即便如此,浪漫主义文学(这里主要指小说和戏剧)并未完全 抛弃情节,有的浪漫主义作品甚至是很有情节的。因此,与现代主义对情节的轻视相比 ,浪漫主义对情节的疏虞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经过现代主义(或者还有后现代主义) 的扫荡,情节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以至于二十世纪的诸多文学词典和百科全书都有意无 意地忽视情节,把情节当作可有可无的文学“盲肠”。
于是,今人似乎普遍不屑于谈论情节,而热衷于观念和技巧了。一方面,文学在形形 色色的观念(有时甚至是赤裸裸的意识形态或反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驱使下愈来愈理 论,愈来愈抽象,愈来愈“哲学”。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也许是这方面的代表人 物,而存在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高大全主义”则无疑也是观念的产物、主题先 行的产物,它们可以说是随着观念和先行的主题走向了极端,即自觉地使文学与其他上 层建筑联姻(至少消解了哲学和文学、政治和文学的界限)。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世纪 批评的繁荣和各种“宏大”理论的自说自话顺应了这种潮流。另一方面,技巧被提到了 至高无上的位置。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到科塔萨尔的《跳房子》,西方文学基本上 把可能的技巧玩了个遍。俄国形式主义、美国新批评、法国叙事学和铺天盖地的符号学 与其说是应运而生的,毋宁说是推波助澜的。于是,热衷于观念的几乎把文学变成了玄 学。借袁可嘉先生的话说,那便是(现代派)片面的深刻性和深刻的片面性。玩弄技巧的 则拼命地炫技,几乎把文学变成了江湖艺人的把式。于是,人们对情节讳莫如深,仿佛 小说的关键只不过是观念和形式的“新”、“奇”、“怪”。当然,观念主义和形式主 义(二者相辅相成)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文学终究是时 代社会的一面有色的、变形的镜子。二十世纪的热战和冷战,社会生活的日新月异和科 学技术的一日千里,无不为观念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甚嚣尘上提供土壤。但所有这些又终 究不能成为小说和戏剧脱离情节、脱离读者大众的全部理由。正因为如此,怀疑和思索 一直存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如芝加哥批评派的罗·克莱恩)就曾不遗余力地希望召 回人们对情节的关注。但正所谓滔滔者天下皆是,克莱恩们的微弱声音基本上没有引起 反响,倒是文学本身的生存危机引起了普遍的关注。而新世纪西班牙语作家回归情节的 走向则无疑是他们化解危机的一种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历史的回归永远不是简单的重复。就像一个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 流,当今西班牙语文学早已是多重混杂的产物。就小说而言,对情节的重视也许只不过 是矫枉过正之后的一种回摆。
一
由于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的原因,西班牙作家没有赶上二战以后席卷西方文坛的解构 风潮,结果倒是轻装上阵,在自己这块处女地上勾勒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这就是说, 相对于其他西方作家而言,西班牙作家少了一些理论包袱;同时,经过近半个世纪的闭 关自守,西班牙对于世界、世界对于西班牙都相对陌生了,于是彼此多了一些新鲜好奇 。
然而,西班牙小说回归情节的道路并非一蹴而就。上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佛朗哥的寿 终正寝,西班牙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首先,西班牙王室和政府对历史问题既往不 咎,几乎使西班牙一夜之间“走向了未来”;其次,由于历史、文化、语言等方面的渊 源和经济、贸易、旅游等方面的联系,西班牙迅速融入欧洲大家庭并全方位地与世界接 轨。相形之下,邻国葡萄牙却显得步履维艰。明证之一是萨拉马戈因为文学创作和政府 信仰而受到了教会与政府的非难,结果却在西班牙受到了保护。
进入八十年代以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西班牙的文学事业也蓬蓬勃勃。文学史 家把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几年的西班牙文学粗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解禁”时期 ,其中的主力军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复出的一代”和“崛起的一代”(单是 这些名词,就不难使人联想到刚刚摆脱文字狱的八十年代中国文坛:一大批老作家被摘 掉帽子,从监狱和牛棚回到自己业已生疏的工作岗位;一大批年轻文人四面逢源,脱颖 而出)。
所谓“复出的一代”是指成名于佛朗哥时代的作家,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到过独裁政权 的迫害。有些作家几乎在监狱里度过了半生。其中的代表人物有塞拉(一九八九年诺贝 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利维斯和托伦特·巴耶斯特尔,他们分别于一九九六、一九九三 和一九八五年获得塞万提斯奖。此外,流亡归来的圣德尔、阿拉亚、罗萨·恰塞尔、圣 普隆、费尔南德斯·桑托斯和玛利亚·希罗内利亚等迅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作家 的特点是生活积累丰厚,对现实有很强的责任感。尤其是那些出生于四五十年代的年富 力强的小说家,如戈伊蒂索洛、贝内特和马尔塞等,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戈伊蒂索 洛同时把笔触伸向了(佛朗哥时代的)两个禁区:性和同性恋问题。贝内特用侦探小说的 形式及普鲁斯特式的长句子,把开放的西班牙社会描绘得犹如迷宫一般。马尔塞几乎是 前两位的有意无意的综合,即把性和敏感的政治捏在了一起。
“崛起的一代”涵盖面更广,像我们的“寻根派”和“先锋派”,至今难有定论。盖 他们实力相当而且一个个既多产又畅销,国内国外声誉极隆。关于这一批作家,首先可 以列出一长串名字:佩雷斯·雷维尔特、里奥斯、米利亚斯、玛利亚·盖尔本苏、玛利 亚·梅里诺、洛佩、蓬波、马里亚斯、甘达拉、门多萨、莫利纳·福伊克斯、巴斯克斯 ·蒙特阿尔班、费雷罗、莫伊克斯、阿桑科特、穆纽斯·莫利纳、马德理、涂斯盖茨、 费尔南德斯·古巴斯、加西亚·莫拉雷斯、蒙特罗等;其次,这些作家的作品可读性明 显强于世纪中叶的“战后小说”。
九十年代,西班牙文学继续繁荣。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开始登上舞台,其回归情 节的倾向更加明显,这直接推动了西班牙小说市场的繁荣兴旺。顺便说一句,文学的繁 荣也促进了影视业的发展。八九十年代西班牙电影之所以成功,首先是因为它拥有一片 丰饶的文学土壤。一如我们第五代导演的成功,当首先归功于“寻根文学”;绍拉、阿 尔莫多瓦等著名导演的出现,也无不受惠于当代西班牙小说。
以上种种,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基本上如乌有之乡。然而,他们对于我们或许比任何 一种文学更具有借鉴意义。因为他们的前面也曾是一片文化沙漠,因为他们的面前也曾 有一个陌生了的世界。与此同时,西班牙的开放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完成的,中间伴随着 社会形态、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颠覆与重构。相比之下,我们的改革可以说是一种渐 进。尽管西班牙与世界(其实主要是欧美)接轨有传统和语言方面的优势,但从百姓的承 受角度看,惊人的变速足以将这些优势消解殆尽。二十多年来,西班牙人的惊喜与惶恐 、欢乐与痛苦、希望与绝望在几代作家的笔下淋淋漓漓地展现出来。这对于同处在变数 中的国人来说,应当说是弥足珍贵、不可多得的参照。
至于情节,女作家罗莎·蒙特罗曾经一言以蔽之,说“回到小说本身,也即回到故事 ,回到讲故事的乐趣”。(注:罗莎·蒙特罗:《在过去,在将来》,载于《回声》, 巴塞罗那,2003年第1期第35页。)此话若在六七十年代,肯定会受到许多人的讥嘲,甚 至会被认为是对“纯文学”的“大不敬”,但在小说惨淡经营的当下,却足以博得许多 人的赞同。然而,问题是好故事难得,讲好故事更非易事。曾几何时,“布老虎丛书” 许下诺言,要以重金购买好看的爱情小说。也许这里面有商业炒作的成分,也许这原本 就是出版家一厢情愿。至于后话嘛,不说也罢。而罗莎·蒙特罗就不同了,她好歹接二 连三地写出了一系列好看的小说,其中最近的一部叫做《地狱中心》(二○○二)。小说 一开始就抛出悬念,然后层层递进,但最终给出的却是一个“太虚幻境”。作品写一个 女记者一早起来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骚扰电话,然后惶惶不可终日,以至于开始了一段 惊心动魄的逃亡。现实的危机和现代人脆弱的心灵在这部丝丝入扣的小说中步步推演, 直至最终包袱抖开:原来主人公所遭遇的一切都是她杞人忧天的想象。
老作家佩雷斯·雷维尔特的小说一直以晦涩难懂著称,但近年来他也改变路数,已出 版多部以情节见长的长篇力作。例如二○○二年出版的《南方的女王》,写一个名叫特 雷莎的女子阴差阳错地混入了大毒枭的队伍,从而引出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故事。
上述作品当然都是反映现实问题的。风气使然,反映历史问题的小说同样愈来愈关注 情节。比如年轻作家哈维埃尔·塞卡斯·梅纳,他的小说基本上是在讲故事,即用一种 “不加修饰”的平和姿态娓娓道来。比如《萨拉米斯士兵》(二○○○)虽然属于历史小 说,以西班牙内战为背景,但故事生动,情节曲折,三年来仅西班牙国内就销售了数十 万册,年前还被搬上了银幕(同名电影先后获戛纳电影节特别奖和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 名)。小说写某报刊记者从作家桑切斯·费尔洛西奥口中得知后者的父亲马萨斯在一九 三九年的一次遭遇。当时,内战已近尾声,长枪党人在德意法西斯的支持下打败了共和 党人。共和党人决定在逃往法国之前枪毙在押的五十名长枪党人。马萨斯趁乱逃脱,被 几个穷追不舍的共和党人捕获。然而,其中一个共和党人居然放过了他这个已经到手的 猎物。尘埃落定以后,死里逃生的马萨斯入阁佛朗哥政府,他知恩图报,千方百计地保 护这几个共和党人。现在轮到记者(即叙述者)穷追不舍了。他不能理解这种亦敌亦友的 心境。于是,他逐个采访了所有证人,惟独找不到那个释放马萨斯的英雄。为了让故事 有一个完满的结局,他只好听信一位作家的忠告:“故事永远比事实更真实”,并杜撰 了一个尾声。于是,那个士兵跨越西法边境,参加法国抵抗运动并随诺曼底登陆的盟军 攻打德国。战争结束后,他隐姓埋名,在法国的一所疗养院里安度晚年。
小说对于真实和虚构的理解几乎回到了塞万提斯时代。
二
拉美当代小说虽然在五六十年代取得了辉煌,但各种探索至今没有停止。回归情节或 可说是其最新趋势之一。众所周知,七十年代,尤其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鲁尔福 、阿斯图里亚斯、卡彭铁尔、博尔赫斯、科塔萨尔等文豪、泰斗的相继去世,拉美文坛 开始显得青黄不接。此间,硕果仅存者也是力不从心,回天乏术(虽不能说加西亚·马 尔克斯、巴尔加斯·略萨、富恩特斯、英方特等江郎才尽,然而他们的创作节奏已明显 减缓,作品也远不如从前厚重)。然而,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拉美文坛迅速复苏。一方 面,老作家如富恩特斯、巴尔加斯·略萨等重整旗鼓,明显放弃了先前的意识形态承诺 。富恩特斯接连发表了三部作品,其中长篇爱情小说《水晶疆界》(一九九七)以及《与 劳拉·迪亚斯在一起的时光》(一九九九)受到普遍好评,被立即译成英、法、德、意等 主要西方文字。和富恩特斯一样,巴尔加斯·略萨近年也有多部力作问世。他的长篇小 说《情爱笔记》(一九九七)被认为是九十年代最有影响的虚构类小说之一。小说主要分 三个层次:人物堂里戈贝托的性爱笔记,堂里戈贝托与妻子、情人的情爱、性爱关系, 堂里戈贝托的儿子与继母的关系以及他充满矛盾的心理活动。由于在作家的前一部小说 《继母颂》中,这些人物“已然出现”(孩子因敌视继母而竭尽手段,最终导致继母与 父亲分手),这部小说就兀自多了一些所指:孩子长大了,对漂亮的继母产生了好感。 这样一来,事情顿时变得复杂起来。作者认为,这是让自己回到另一个青年时代、让小 说“回到另一种本来面目”的勇敢尝试。(注:巴尔加斯·略萨:《回到自己需要勇气 》,载于《文学之友》,墨西哥城,1997年第3期第7页。)卡夫雷拉·英方特是古巴流 亡作家,近年来同样佳作迭出。一九九六年发表《我的极端音乐》,一九九七年出版《 她曾是个民歌手》,二○○四年又有新作问世。巴拉圭老作家巴斯托斯也是笔耕不辍, 佳作不断。
此外,西班牙语美洲作家的政治色彩明显淡化,社会参与意识和代言意识明显消减。 受此影响,爱情小说层出不穷。阿古斯丁的《好人的爱情》、巴斯托斯的《苏夫人》、 埃斯基韦尔的《爱情法则》、马斯特雷特的《爱之恶》、巴尔加斯·略萨的《情爱笔记 》、卡夫雷拉·英方特的《昨日星辰》、富恩特斯的《迪娅娜或孤独的狩猎者》等等, 都是九十年代末拉美和欧洲图书市场看好的长篇小说。
最近几年,情况就更加明朗了。老作家富恩特斯接连有两部情节小说面世。一部是二 ○○一年的《伊内斯的知觉》,另一部是二○○三年的《鹰椅》。前者写一个男人和一 个女人一生当中的三次邂逅。两人的第一次邂逅是在一九四○年的伦敦,当时希特勒的 飞机正在轰炸这座城市。他们的邂逅当然充满了偶然和惊险。但冥冥之中把他们联系在 一起的却是美好的音乐。女主人公天籁般的嗓音使男主人公久久不能忘怀。但是战争的 硝烟和地位的悬殊使男主人公不得不放弃非分之想。多年以后,他们久别重逢,这时男 主人公因为思念女主人公而在一个二流乐队担任指挥;女主人公则已然登上事业的巅峰 ,在乐坛上红得发紫。两人的差距依然存在。最后,到了一九六七年,摇滚乐横扫世界 乐坛,男主人公如鱼得水,红极一时。这时,歌剧光景不再,歌剧女王也已人老珠黄。 三次邂逅。三种情感。男女主人公的爱情真可谓一波三折。富恩特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明确表示要让人类最本真的情感在时间和空间的缝隙中进发出最自然朴素、美丽动人 的火花。小说已经完全放弃了《最明净的地区》或者《阿尔特米奥·克鲁斯之死》的那 种雄心勃勃的所谓多视角、多层次、多声部式的全景观描写。一切都围绕着一个既简单 又复杂的爱情故事展开,充满了偶然和必然、意料之外和情理之中。
富恩特斯的另一部小说《鹰椅》,表现的是他熟稔的权力主题,但情节也相当扣人心 弦。所谓鹰椅,用我们的话说也就是龙椅。富恩特斯在这部篇幅有限(三百八十四页)的 小说中构织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权力网,充斥其中的除了司空见惯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 ,还有企图挣脱阴谋和交易的神圣爱情。小说的情节使我联想到我国的二月河和眼下比 比皆是的清宫戏,只不过富恩特斯把政治比作游乐场中最惊险、刺激的过山车,而鹰椅 便是其中那个人人觑视的“头等舱”。他对墨西哥的社会现实可以说是相当悲观。
同样,去年入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蜂王飞翔》(二○○二)也是一 部相当出色的政治小说。恰恰是因为情节的因素,而今的政治小说已经不是七十年代反 独裁小说。阿根廷作家托马斯·埃洛伊在这部不足二十万字的小说中讲述了一个骇人听 闻的权力故事。小说主人公卡马戈是《布宜诺斯艾利斯日报》的老板。由于他经营有方 ,该报在阿根廷独占鳌头。他以此为阵地,成了阿根廷的“社会良心”和“捍卫民主的 英雄”。他在报社内部却独断专行,比独裁还独裁。一方面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把 第一家族的专断腐败公诸于众,从而直接导致总统下台;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王国 ”内部专横跋扈,干了许多令人发指的勾当。比如,他发现曾经有恩于他的情人不够听 话,便命人对她施暴;最后为了销赃灭口,他甚至亲手杀害了她。正所谓世事乖谬,人 间正道未必总是善恶分明,因此作者有理由下一着险棋:一个反寡头的英雄原来自己也 是一个寡头。
三
在当下西班牙语文坛,类似作品还有很多。如果说上一代拉美作家的使命是创造一部 美洲的《圣经》,那么年轻一代的目标似乎“降低”了许多,因为他们心心念念的似乎 只是恢复小说的“本来面目”。而西班牙语作家是世界文学盛宴的晚到者,几乎已经没 有肆意发挥、“暴殄天物”的余地;因此,回归情节也许不失为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谓予不信,这里不妨举阿尔法瓜拉长篇小说奖为例,其评奖标准的演变多少反映了西 班牙语小说愈来愈重视情节的这样一种现象。阿尔法瓜拉虽然是一家相对年轻的出版社 ,但它名下的“阿尔法瓜拉小说奖”却是当今西班牙语小说各大奖项中的翘楚(有“西 语小说第一奖”之称)。之前声名显耀的“普拉内塔小说奖”和“罗慕洛·加列戈斯奖 ”由于各自局限于西班牙和拉丁美洲,未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西班牙语小说大奖。而塞 万提斯奖和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基本上都是成就奖。近年来,在作家胡安·克鲁斯的领 导下,阿尔法瓜拉出版社后来居上,对西班牙语国家的文学资源,尤其是长篇小说进行 了卓有成效的整合并适时地设立了“阿尔法瓜拉小说奖”。该奖以每部十七万五千美元 的高额奖金和在二十个西班牙语国家同时发行的诱人条件向全世界西语作家悬赏长篇小 说。一九九八年以来,已有八位西班牙语作家获此殊荣。他们是尼加拉瓜作家塞尔西奥 ·拉米雷斯(《玛尔加丽塔,大海多美丽》)、古巴作家埃利塞奥·阿尔贝托(《河蚌》) 、西班牙作家曼努埃尔·维森特(《海韵》)、西班牙作家克拉拉·桑切斯(《天堂的最 后消息》)、墨西哥作家埃莱娜·波尼娅托乌斯卡(《天空的皮肤》)、阿根廷作家托马 斯·埃洛伊·马丁内斯(《蜂王飞翔》)、墨西哥作家哈维埃尔·委拉斯科(《魔鬼使者 》)和哥伦比亚作家劳拉·雷斯特雷波(《梦呓》)。其中,二○○四年获奖小说《梦呓 》是在六百三十五部手稿中脱颖而出的。在这六百三十五部请奖小说中,四百四十四部 来自拉丁美洲,其余来自西班牙及全世界非西班牙语国家的西班牙语作家。诺贝尔文学 奖获得者萨拉马戈任二○○四年阿尔法瓜拉小说奖评奖委员会主任,遴选过程和颁奖仪 式通过广播电视在二十个西班牙语国家及西语人口相对集中的美国、葡萄牙和巴西直播 。
《梦呓》的作者是哥伦比亚《万花筒》杂志的记者,《梦呓》是她的第八部小说。作 品自始至终充满了悬念。主人公是一名中年男子,他因公出差后回到家里,发现妻子竟 然已经疯得不省人事。他完全不知道离家这三天时间发生了什么,可以让一向开朗豁达 的妻子突然神经错乱。在万分的痛苦和无边的绝望中,主人公带着妻子四处求医。医生 认为必须找到太太的致疯原因,否则很难使其恢复理智。于是,他开始了漫无目标的调 查。在此过程中,他像中国寓言中的丢斧人,见了谁都心生怀疑。在现实中经历了许许 多多怀疑和惊险之后,他终于发现,原来导致妻子疯狂的竟是他自己闲来无聊时写下的 一些似是而非的桃色梦呓。评委会的评语是:“《梦呓》是一部非常全面的小说,充满 幽默的情节突出表现了文学的悲剧意识,展示了人类最原始的激情和最崇高的理想、最 残酷的现实和最动人的悲悯。同时,它还是复杂、夸张的现代哥伦比亚社会的真实写照 。”西班牙著名导演对这部“充满了戏剧性”的长篇小说大为赞赏,认为它几乎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电影脚本”。同时进入最后一轮提名的西班牙作品《裸者的未婚妻》和拉 美作品《我的镇长兄弟》也都是可读性极强的长篇小说。前者写一个富有家庭的女管家 。她一直生活得很平静,以为只要兢兢业业地工作,就可以凭借优厚的报酬择婿、结婚 、生子、幸福终生。然而,生活的实际并非如此。一天,她随主人一家外出远游,无意 中发现她的闺阁好友居然一直在背叛她(和她的丈夫有染)。于是,她一气之下离开西班 牙,投入了疯狂的报复。后者写一位相信民主和公正的镇长,在一座以英国伦敦泰晤士 河命名、实际却与世隔绝的小镇上开始了一系列堂吉诃德式令人啼笑皆非的冒险。由于 这个世界上真实和谎言、信义和背叛、仇恨和爱情尚在混淆不清的混沌状态,年轻的镇 长免不了碰得头破血流。然而,叙述者却以桑丘·潘沙式清醒机智和不无嘲讽的口吻, 把“兄弟”的一次次无谓的冒险描写得血泪淋漓。
然而,回头看去,阿尔法瓜拉小说奖并不是一开始就注重小说情节的。创办伊始,该 奖的评委会显然更注重小说的叙事形式。如一九九八年的《玛尔加丽塔,大海多美丽》 是一部探索性较强的作品。作品的故事很简单:一九○七年,尼加拉瓜诗圣鲁文·达里 奥在故乡接受人们的赞美。活动中,一名九岁女孩向他献花,他则即兴赋诗并把崇尚自 由的诗句写在女孩的扇子上作为回赠。五十年后,尼加拉瓜独裁者索莫查途经此地,当 时的女孩已经五十九岁。她居然成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暗杀行动的主谋。一九九九年的《 海韵》同样具有类似的“作文”之嫌:人们在海边发现了一具西装革履的尸体。验尸官 认定他是本镇的尤利西斯。当人们来到尤利西斯家证实这一推断的时候,发现尤利西斯 的太太也已身着盛装死在了床上。小说进入倒叙,谓尤利西斯是古希腊文学教授,爱上 了酒吧老板的女儿。两人婚后相亲相爱。一天,教授突发奇想,决定为太太出海捕鱼, 结果一去就是十年。人们都以为他成了鲨鱼的美餐,太太也耐不住寂寞他嫁别人了。但 十年后尤利西斯回来了,从别人手里要回了太太。这俨然是《尤利西斯》的又一个现代 版本。二○○○年的《天堂的最后消息》几乎是一部典型的“新小说”,写名叫弗朗的 少年在马德里近郊的无聊生活。小说充满了生活的琐碎,而聊作点缀的友情(与同样无 聊的埃杜)与爱情(与同样本能的塔尼娅)在一个叫做阿连的假道学的指引下一点点地变 形、蜕化。二○○一年的《天空的皮肤》是一个转折,尽管向度并不明显。小说写一位 天文学家的遭遇。他的天才被生活的庸常一点点消磨殆尽,以至于工作中麻烦重重,爱 情上更是一筹莫展。
二○○二年的《蜂王飞翔》被认为是一部充满了情节美的长篇杰作。二○○三年的《 魔鬼使者》更是一部情节曲折、高潮迭起的长篇力作。小说一开始就引人入胜:年仅十 五岁的美丽少女维里莱塔心生叛逆。一天,她成功地窃取父母的十万美元后悄无声息地 离家出走了,踏上了她人生的“另一条”不归之路。她辗转来到纽约,住进了高级酒店 ,开始了煞有介事的“富婆生活”。后来,钱花光了,但她的业已开始的生活却无法停 止。于是,她开始变换手法,直至成为有钱男人的附属品和寄生虫。在此期间,她的“ 品质”和“良心”逐渐蜕化、消失,以至于最终不得不闭上眼睛,把自己完全交给“魔 鬼使者”。所谓一失足成千古恨,小说用无数悬念(和巧合)把一个毫无城府的少女一步 步推向了现实的深渊,令人难以释怀。
此外,阿尔法瓜拉近年出版的另一些长篇小说,如豪尔赫·雷维尔特的《边境上的加 维斯》(二○○一)、巴尔加斯·略萨的《天堂的另一个街角》(二○○二)、路易斯·马 特奥·迭斯的《婚礼回音》(二○○三)等,也都明显偏重故事情节。
这里面有物极而反的必然,也有小说重新找回读者的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