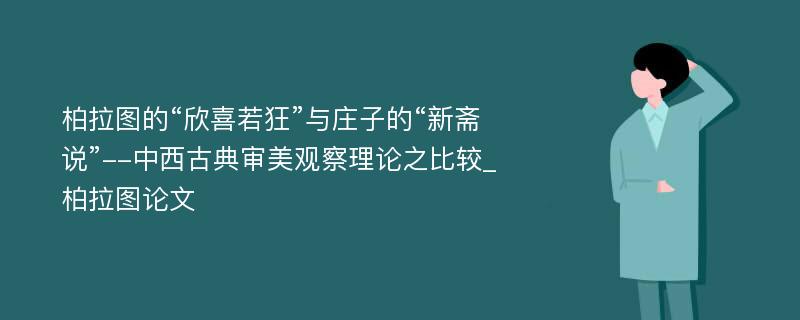
柏拉图的“迷狂说”与庄子的“心斋说”——中西古典审美观照理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柏拉图论文,庄子论文,中西论文,古典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3)10-0097-04
柏拉图与庄子是中西方影响最为深远的古代哲学家和美学家。两人虽相隔万里,却几乎同时提出了关于艺术的审美观照方面的理论,形成了东西方艺术传统的源流。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这是人类两大文明不约而同的“一次深呼吸”的体现。在这次吐故纳新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既呈现出了相同或相近的思想经历,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历史变革。表现在柏拉图与庄子身上,他们的审美观照理论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同时也显现出中西审美观照方式的巨大分野。
考虑到两人著述的庞杂和理论的深邃,为了便于比较起见,仅选最能代表他们审美观照理论的“迷狂说”与“心斋说”,以斑窥豹,探讨他们审美观照理论之异同。
一、柏拉图的“迷狂说”与庄子的“心斋说”理论概述
柏拉图的“迷狂说”的前提是他的“理念论”,他认为“理念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才能代表真理。而人只有依靠“回忆”,进入“迷狂”的状态,才能见到真理。理念论、回忆说和迷狂说形成了柏拉图美学本体论的基本内容。
理念论是柏拉图美学的核心,是我们理解“回忆”说与“迷狂”说的关键。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叙述一下柏拉图的理念论。在理念论中,他设定了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肉体与灵魂、人性与神性等的二元分裂,这成为他的哲学和美学的出发点。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理念与现象两重,理念与可感事物相比具有如下特征:
首先,可感事物是众多的,而理念却是单一的,它是一个自我完善的整体。它们每一个总是其自身,具有同一的自我存在和不变的性质;其次,可感事物总是相对的,美中有丑、善中有恶。而理念则是绝对的,美、善的理念丝毫不含丑、恶的成分或其它杂质;又次,可感事物处于永恒的变动状态中,生灭不已。而理念则是永恒的、不生不灭、不盈不缺的。
既然理念世界不同于可感的现象世界,那么人们就不可能从知觉的内容里认识理念。如何才能达到对理念的认识?知识究竟如何成为可能呢?为此,柏拉图提出了“回忆”说。柏拉图认为,回忆是灵魂对理念世界的渴慕与返回,是人向理性家园重返的中介。
在《会饮篇》里,柏拉图描绘了回忆“美本身”的漫长过程。
先从人世间个别的美的事物开始,逐渐提升到最高境界的美,好象升梯,逐步上进,从一个美形体到两个美形体,从两个美形体到全体的美形体;再从美的形体到美的行为制度,从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再从各种美的学问知识一直到只以美本身为对象的那种学问,彻悟美的本体(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3页。)。
从美的形体到美的灵魂、美的行为制度到美的学问知识,最后到美的本体,这一认识论的过程同时也是价值逐渐升级的过程,是灵魂逐渐返回自身、回到理性家园的过程。所以“美的上升”过程,同时就是一个人渴望生命摆脱肉体和世俗的束缚,让灵魂高飞远举的过程。而迷狂则是灵魂在进行回忆时的一种极端亢奋的心理状态:当人们观照到过去在诸天境界所见到的真实体或美本身的成功仿影时,他先是打了一个寒颤,心里激起一种虔诚;当他继续凝视的时候,寒颤就变成一种从未体验过的高热,浑身发汗,羽翼或灵魂也随之而受滋润,得到温暖,苦痛全消,觉得非常快乐。
这痛喜两种感觉的混合使灵魂不安于它所处的离奇情况,彷徨不知所措,又深恨无法解脱,于是他就陷入迷狂状态,夜不能安寝,日不能安坐,只是带着焦急的神情,到处徘徊,希望可以看到那具有美的人一眼(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8页。)。
据此,柏拉图提出了和他的回忆说相联系的迷狂说。
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因而恢复羽翼,而且新生羽翼,急于高飞远举,可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像一个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把下界一切置之度外,因此被人称为迷狂(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5页。)。
所谓“迷狂”(mania)指的是灵魂的一种神智不清的状态。在古希腊,迷狂往往是和宗教巫术联系在一起的,柏拉图沿用了这一观念,认为神圣的迷狂是一种“神灵的禀赋”。依柏拉图看,灵魂依附肉体,只是暂时现象。它本质上是努力向上的,竭力挣脱肉体,飞升到天上神的世界,即尽善尽美,永恒普遍的“理念”世界。如若它再度依附肉体,投到人世生活时,人世事物就使它依稀回忆到它未投生人世以前在最高境界所见到的景象,见到“理念”世界的美的景象,而且还隐约追忆到生前观照那美的景象时所起的高度喜悦,对这“理念”的影子欣喜若狂,油然起眷恋爱慕的情绪。这就是一种“迷狂”状态。质言之,“迷狂”就是对那曾经拥有而今已失去的,只存在于遥远的天国的理念进行回忆时的一种心灵状态,这是一种高度自由的,摆脱了现象界的尘俗之累的精神境界。
但是,这种境界并不是丧失理智、陷入激情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而恰恰是由于热爱理智而置世俗一切于不顾,才被执著于尘事幸福的人说成是迷狂。实际上,它更多地带有沉思默想、凝神观照、超然物外的性质。因此,这种迷狂本质上是理性的。只有那些具有超常的意志力和才能的人,尤其是哲学家,才能进入迷狂状态,达到绝对的美的境界,最后通过对美的本体的“凝神观照”,实现和美的本体的契合无间:
这时他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于是孕育无数量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如此精力弥满之后,他终于一旦豁然贯通唯一的涵盖一切的学问,以美为对象的学问(注:《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
这里所说的“凝神观照”,正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审美观照”。
在中国美学史上,庄子也把抽象的“道”作为其美学的基本范畴。庄子认为,“道”是一种客观的、普遍的、绝对的美,他在《知北游》中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名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
天地的“大美”就是“道”。圣人“观于天地”也就是观“道”。这是一种静观的观“道”方式,即“圣人无为,大圣不作”。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观照理论,庄子又提出了“心斋”、“坐忘”、“外生”、“见独”等方法,追求主体心境的虚静空明以实现对“道”的观照。
在《人间世》中,庄子提出了“心斋”说:
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耳止于听,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将来舍,而况人乎?
所谓“心斋”,就是空虚的心境。“气”是对这种空虚心境的形容。只有空虚的心境,才能实现对“道”的观照。这种对“道”的观照,排除各种杂念(若“一志”),也排除逻辑的思考(“外于心知”)。这种对“道”的观照,要借助感觉器官(“徇耳目内通”),但从本质上说,它并不是“耳目”的知觉,也不是“心”的逻辑思考。因为“耳目”的知觉和“心”的逻辑思考只能把握有限的事物(“耳止于听,心止于符”)。而“道”是无限的。所以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只有用空虚的心境直观,才能把握无限的“道”。
在《大宗师》中,庄子又提出了“坐忘”的概念: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
所谓“堕肢体”、“离形”,就是从人的生理欲望中解脱出来。“堕肢体”即忘却手足,“黜聪明”即闭目塞听,“离形去知”,意为遗忘整个身体和智慧,即与道相合。
为了说明“同于大通”的过程,《大宗师》提出了由易到难的修养方法,也就是循序渐进地在思想上遗忘外物的几个阶段。第一步“外天下”,即排除对世事的思虑;“第二步外物”,即抛弃贫富得失等各种计较;第三步“外生”,即把生死置之度外。一个人的修养达到了“外生”的阶段,就能“朝彻”,也就是能使自己的心境如初升太阳那样清明洞彻。“朝彻”,就能“见独”,也就是能实现对“道”的观照。到了这一步,遗弃了自然、社会和自己的身体,摈弃了认识、情感,使人心空虚、死寂,从而与道相合。
由此可见,“心斋”与“坐忘”、“外生”、“见独”在本质上是一回事,即从思想上遗弃现实,做到绝对的不动心。这种精神境界,实际上就是艺术和审美的境界。“心斋说”阐明了中国古典审美观照理论的心理状态和精神特征,心斋与坐忘的种种心理流程,也正是美的观照的历程。
二、“迷狂说”和“心斋说”都是受原始思维影响的一种关于世界本体论认识的“诗性智慧”
1.“迷狂说”和“心斋说”中的“诗性智慧”的特征
古希腊哲学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前苏格拉底时期的自然哲学,苏格拉底——柏拉图时期的道德哲学和理念论,亚里士多德时期的形而上学。自然哲学是古希腊哲学的第一个表现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对宇宙、自然进行“终极关怀”。人类对宇宙的终极关怀最初是以具象思维的形式出现的,古希腊神话就是其表现形式之一。神话世界观受原始思维的万物有灵观的影响,它所表现的是一种诗性智慧,是天人合一,主客观尚未分野的产物。处于古希腊哲学发展链条中间环节的柏拉图,不可避免地受到自然哲学观念的影响,再加上和古埃及原始宗教的渊源关系,他的哲学呈现出一种原始性与思辨性、具象性与抽象性、人性与神性、哲学性与神性相缠绕的复杂状况。
柏拉图的“迷狂说”具有浓重的神秘色彩,与宗教神学难解难分,是以古希腊传统的灵魂不朽的观念为基础的。古希腊最早提出“灵魂轮回说”的是毕达哥拉斯,而毕达哥拉斯则是从埃及祭司那里学来的,他把灵魂不灭、轮回说带回了希腊,与希腊原有的奥尔弗斯教神秘学说结合了起来。在柏拉图的“迷狂说”中,柏拉图也是从原始的“气息”角度来解释灵魂的性质的,原始宗教的余体尚温。
从柏拉图的“理念”说中我们已经看到,理念构成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独立世界,即本体世界,这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到于我们的感官所接触到的具体事物所构成的世界,是不真实的虚幻的世界。于是,就形成了“本体世界”与“现象世界”二元对立。由此可知,柏拉图时代的逻辑抽象能力还很有限,他们还没有完全弄清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即一般和共性只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从一方面来说,柏拉图已意识到了一般和共性与个别事物的差别,企图从具体事物、即个别之中寻找一般和共性。从另一方面来讲,他又受传统思维的支配,把事物的一般和共性绝对化,使他们成为脱离具体事物并且先于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把猜想的概念理解为可以单独存在的个别体,这是原始思维具体性特征的一种突出表现。
而在如何从一般个别事物达到对普遍共性的认识过程中,柏拉图则放弃了逻辑论证方式,直接用神话来表示他的理解。在“迷狂说”中,柏拉图认为人的灵魂带有羽翼;因为羽翼能帮助灵魂向高飞升,升到神的境界。这种看法,很可能受到原始宗教把灵魂看作飞鸟的习俗影响。
柏拉图的“迷狂说”是对西方文化精神中的“诗性思维”作的第一次系统表述,借“迷狂”这一诗性的智慧或思维方式来超越和克服现象界与本体界的分裂和矛盾,来完成人的诗意的生成。
中国进入文明的时间很早,但发展变化却非常缓慢。这种近似于停滞的缓慢发展的古老文明,曾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之为“活化石”。古代人类早期的社会结构、思维方法、伦理习俗、宗教信仰、生产生活方式、审美趣味、艺术表现等,在很大程度上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直至老庄时代,原始思维的痕迹在他们的艺术思维中还深深的存在。叶舒宪在《中国古代文化》一书中指出,诗性智慧是《庄子》一书的最大特色。所谓“诗性的智慧”不同于一般的哲理、教义、信条,难以用常规的语言形式去传达和教授,只能通过特殊的间接语言形式去激发和启导。庄子拒绝用概念化的方法表达思维,反而转向一种诗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大量运用寓言的形式。使那些抽象概念、思想范畴、精神境界,以具有感性的形象的样式出现。在《庄子》中,作为最高的、世界总体和根源的理性范畴“道”,就常是以“真君”(“真宰”)、“造物者”(“造化”)、“宗师”等具有形象性、人格性的名词来表达;相应地也以人类的行为特征来描述“道”的这种根本性质。《庄子》写道:
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而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齐物论》)
今之大冶铸金,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大宗师》)
显然,这些文字出现的具有“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的形象—真君(真宰)、造化(大冶),它们实际上都是“道者,万物之所由也”(《渔父》),庄子的作为宇宙最后根源的“道”这一抽象的理性概念或范畴,以一种具有鲜明具体的感性内容的规定,形象地被表述出来。
对“体道”过程的表达也是如此。《庄子》写道: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希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逃乎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知北游》)
在这个既有认识特质又有实践因素的精神活动中,凝聚着个人的独特的思想经历和生活经验,因而是一种难以用理论语言表述的、无固定逻辑轨迹可循的精神过程。《庄子》正是借助一些寓言故事和形象,展现和说明了人类心灵中的这一深邃的、然而是完全真实的精神现象的。
2.“迷狂说”与“心斋说”共同的审美心理特征
正是受原始思维模式的影响,“迷狂说”和“心斋说”才具备某些同质的因素,具有一些共同的审美心理特征。
第一,它们都强调彻底打破人的生理常态,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使心从欲望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才能实现一种高超的生命体验。无论是“迷狂”还是“心斋”,其目的都是达到澄明空虚的心境,以实现对“理念”和“道”的彻底观照。柏拉图描述的“美的上升”过程和庄子描述的养身的各个阶段,其实质都是使生命摆脱肉体和世俗的束缚,让灵魂高飞远举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就是与道相合的过程,亦即由人间升入天国的过程。离物远一分,对道就近一分,彻底抛弃了物,也就彻底入了道。《大宗师》说的“入于不死不生”,正是自我与道完全相合的状态。
第二,它们都注重主体(灵魂)对对象采取的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因为欲望消解了,“实用”的观念便无处安放,精神便得到自由。柏拉图要求摆脱肉体的拖累,洗净心灵的污垢,去掉一切尘世的欲念,专注于对象的本质,亦即真实本体本身。
庄子的“心斋”说,其核心思想就是要人们从自己内心彻底排除功利观念。如果观照者不能摆脱实用的考虑,就不能发现审美的自然,就不能从具体有限的物理世界中把握宇宙无限的意味,就不能得到审美的愉悦。以审美创造来说,如果创造者不能从利害得失的观念中超脱出来,他的创造力就会受到束缚,他就不能得到创造的自由和乐趣。这既是审美主体的一种要求,也是自我摆脱身体的束缚,达到精神绝对自由的必由之路。
第三,它们都突出审美观照过程中主体(自我意识)的作用。柏拉图认为主体或者说灵魂、心灵在“凝神”中不要旁骛他物,将下界的一切置之度外,像鸟儿一样昂首向高处凝望。这种主体对对象采取的一种积极注意状态,类似于庄子所说的“用志不分,乃凝于神”。
对于主体精神的强调,是古希腊哲学的一大变革。古希腊自然哲学否定自身,向前发展的契机是在公元前5世纪,此时古希腊的经济、政治和人的观念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时期人们放弃了对自然的研究,哲学家们把注意力转向政治科学和有益于人类美德的问题。”希腊哲学和科学“走向了人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意志力”(注:汪子嵩:《希腊哲学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47页。)。处于转型时期的柏拉图,其理论具有了由自然向人的心灵转向的时代特征,即由面对可感世界的意见状态转向以理念世界为对象的理性状态。
同柏拉图相似,庄子也认为最高最美的“道”,是看不见,听不见,只能靠心灵去感受。于是对“道”的追求只能“向内转”,只有依靠人类的精神世界。《庄子》中许多关于“神”的描述,如“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操舟若神”,“器之凝神”,“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即是指在技艺上所达到的一种神化的境界,也是主体心灵完成审美超越的过程,是心灵对超验的本体世界的一种“彻悟”、“豁然贯通”,是心灵从经验世界到本体世界的一次“飞跃”。
三、“迷狂说”和“心斋说”在审美观照途径上的巨大差异
以柏拉图和庄子的审美思想作比,主要表现为在审美观照途径上存在巨大差异:
1.理智与情感
尽管抽象的理念与道同是柏拉图和庄子审美理论的逻辑起点,但如何去观照它,两人却存在着巨大的分歧。柏拉图认为,只有理性才能达到对理念的认识。柏拉图的“凝神观照”,由形体到行为制度,由行为制度到学问知识,最后从各种学问知识一直到美的主体,其态度是极其冷静客观和理智的。这一过程虽起源于具体事物,并由具体物象上升到对理念的观照,但实际上它一方面强调对事物进行直接感悟和观照,另一方面又抽去了这其中任何感性具体的内容。
柏拉图的“迷狂”说虽有某种审美心理内涵,但总体上还是一种哲学本体意义上的理性直观,它忽视或者排除了情感在观照中的作用,以致于亚里士多德批评他的老师过于忽视“情感”的因素。
庄子的“道”则是以人的精神自由为出发点,以现实的人生体验区别于柏拉图的宇宙论倾向,不作形而上的纯哲学思辨,从而使“道”的哲学人情化、审美化了。庄子不依靠理性的思辨和逻辑的语言来认知或表达道,而以审美的、心理体验的方式通向道,突出了情感和想象在审美观照中的意义。
2.间离与融合:二元对立与天人合一
柏拉图的“迷狂说”,要求把审美主体和对象间离开来,以主体绝对自由心灵直观美的本体,达到对理念的一种“静观”,“凭临美的汪洋大海,凝神观照,心中起无限欣喜”。西方的静观审美,无论是柏拉图的“凝神观照”、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还是海德格尔的“澄明”说,本质上是一种理性直觉与领悟,它是主体凭借对象的提升而产生美的欣喜,而没有主体与对象的心灵契合与交融。
庄子的“心斋说”,则强调主体与对象的亲密交会与融合,一种主体全身心地潜于对象的情感体验。主体客体原是一体,其间没有隔阂与鸿沟。我即是道,道即是我。世界的必然性就是我的意志,我的意志也就是世界的必然性。庄周著名的“蝴蝶梦”,就是主体与客体相互转换的一个例证。
3.推理与直觉
正是基于柏拉图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他的审美观照理论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方法展现出来。“迷狂说”把知识的源泉从外部对象转移到心灵自身,它试图解答世界的本原问题,并提出“返身内求”的探索方式,为西方理性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迷狂说”的逻辑推理过程,表现为它是一个漫长的认识对象的过程:它既使观照者的内心激起“无限欣喜”的情感,又使他孕育出无数的“优美崇高的道理”,得到丰富的“哲学收获”。
庄子则排斥分列、辨别等理智手段,也摈弃目视、耳闻、口尝等感知途径,保持直觉的心境,通过移情共感,用虚豁宁静的心境把握“道”。所谓直觉,就是在大量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思维飞跃和爆炸性的创造性感悟,它的基本显现形式为:无法言述的敏锐的预感、突发其想的冲动、刹那间的透彻的理解等等。
四、“迷狂说”和“心斋说”对后世的影响
如何看待“迷狂说”和“心斋说”,并了解它们的异同,这对确定中西方审美理论的发展走向是至关重要的。在西方美学与诗学历程中,后来的哲学家们都直接或间接地讨论过“迷狂”的问题,并且都将其置于其诗学理论的核心。维柯说,迷狂是一种植根于肉体,从肉体中吸取力量的能力,是诗之本源;海德格尔更加明确,他说,怀疑是诗的源和根,迷狂就是回过头来反思过去的东西,就是告别尘嚣,回归到心灵空间的最幽隐的不可见上去。虽然说法各有不同,但在迷狂与诗、迷狂与人性神性化的关系这点上,他们与柏拉图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柏拉图可谓是这一理论的先驱。
庄子的“心斋说”,阐述的是一种空明澄净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正通向艺术创造的自由。这个思想对中国古典审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刘勰后来发挥了这个思想,“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脏,澡雪精神”(《文心雕龙·神思》)。到陆机的“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张彦远的“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两望,离形去智”,以及郭熙的“林泉之心”,均是“心斋说”的一脉相承。
总之,两种学说均开启了不同文化的艺术之源,既是各自艺术审美理论的奠基石,又是东西方审美理论的分水岭。
标签:柏拉图论文; 庄子论文; 审美观论文; 柏拉图文艺对话集论文; 文化论文; 古希腊哲学论文; 大宗师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