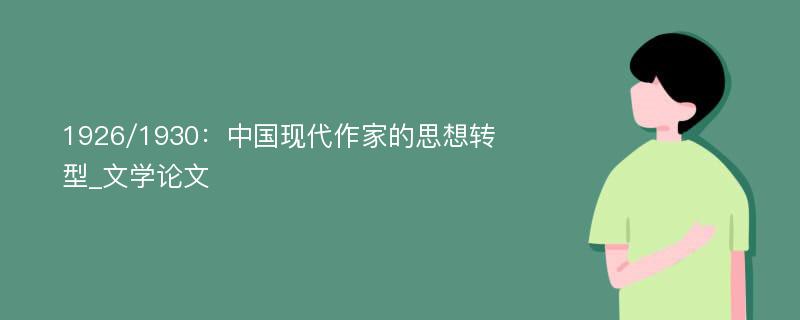
1926~1930: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作家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529(2002)05-0097-07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1926年至1930年是中国现代作家思想的转型期。因为随 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退潮和中国社会形势的变化,新文学作家几乎是以思维意识的 群体连动行为,强烈表达了他们的思想集体“左”转的主观愿望,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现 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彻底转换。如果仔细分析一下这一时期中国作家的思想状况,我们发 现用集体主义的精神理念去取代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完全是他们的一种自觉自愿的社 会行为。因为从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到“五四”的新文学运动,虽然使中国文学告别了 古典主义的历史时代,但却并没有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文学价值观念体系;所以 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短暂辉煌之后,“五四”新文学作家都表现出了一种精神苦闷和思 想困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以及“左联”社团组织的 成立,无疑是对已经步入了现实困境的“五四”新文学运动,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拯救— —它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信仰,全面规范整合了中国现代作家自由涣散的思想状态; 同时也以强烈的时代社会责任感,牢固地奠定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对 于这一问题没有足够而清醒的理性认识,那么我们将无法从本质上去研究论证中国现代 文学发展过程的历史独特性。
一、嬗变前夜的躁动:“五四”新文学后期作家思想心态的抽样分析
谈到“五四”新文学作家思想的集体“左”转,首先我们应该充分注意到他们的这种 社会行为,并不是由外界压力的驱使所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内在的思想动因所引发的 。换一种说法,“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其发展过程中,本身就客观存在着一种思想“左 ”转的潜在动能。
从历史发展的宏观角度来加以分析,晚清与“五四”时期的文学变革运动受西方现代 人文精神的影响,在其逐渐地走出了古典主义的愚昧时代之后,都明确地表现出启迪民 众觉悟、传播西方思想的高度社会使命感。中国近现代作家这种主观上的思想倾向性, 无疑是有所寄托的,他们是希望能够像西方社会的现代转型期那样,以文化启蒙的软性 浸透方式,去开启中国人的现代意识。只要我们稍加回顾一下“五四”前后中国文坛上 思想解放与个性解放社会呼声的热烈高涨,就不难发现中国作家无论是钟情于何种表现 风格或何种表现形式,他们的价值追求和精神渴望却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即:对 于传统文化群体理性意识的深刻反省,以及对于西方的主体性价值观的强烈认同。所以 ,从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呼唤国魂开通民智[1]、“欲新一国之民”的文学主张,到“五 四”文学革命运动“以为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3](P511)的创作宗旨, 其实际上所产生出来的客观社会效果,也是思想文化方面的意义明显要大于文学本体方 面的意义。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无论是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还是“五四”的新文学思潮 ,它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启动和新文学初期创作的繁荣,的确都曾做出过不可磨 灭的巨大的历史贡献。
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对思想文化启蒙长期性的认识不足,“五四”前后的文 学革命与新的思想文化运动,都没有延续多长时间便沦为沉寂;启蒙者反抗叛逆的时代 呐喊,也随之转变为悲愤凄凉的痛苦呻吟。为什么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思想启蒙运动 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便出现这种大起大落极不稳定的社会躁动现象呢!追根溯源, 是因为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缺少一个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长达500年之久的思想 过渡期。再加上中国人急功近利文化传统的内在影响,错误地将思想启蒙与社会革命混 为一谈,所以面对苦难深重黑暗依旧的中国社会现状,无论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还是 “五四”新文学精英群体,他们很快便对自己所曾经信仰过的、以个性解放思想为核心 内容的西方现代人文主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与动摇。经历了两次思想启蒙运动的鲁迅, 后来在总结“五四”文学革命失败的历史原因时,便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非常清晰地 表述了自己当时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说:“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 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找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 际的黑暗……他们是要歌唱的,而听者却有的睡眠,有的槁死,有的流散,眼前只剩下 一片茫茫白地,于是只好在风尘洞中,悲哀孤寂的放下他们的箜篌了。”[4](P244)对 手鲁迅的这段话,研究者多有引用且各有心解。但我个人则认为,鲁迅这段颇为凄楚苍 凉的叙述话语中的“歌唱”,意思当然是指新文学创作中所反映出来的人文主义启蒙意 识,而“听者”自然就是指思想愚昧不思醒悟的落后国民群体。当“五四”新文学的启 蒙主义并没有取得原先主观预想的实际效果时,放下“箜篌”也就暗示着新文学作家对 其最初所选择的西方人文主义价值理念的绝望和放弃。这决不是刻意的曲解或夸大其词 。“五四”新文学后期的创作实践,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现出了这种思想倾向性。比如鲁 迅的《彷徨》和《野草》、郭沫若的《星空》、闻一多的《死水》、叶圣陶的《倪焕之 》、茅盾的《蚀》和《虹》、丁玲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男女主人 公面对苦难的现实人生所表现出来的困惑与焦虑,已不仅仅是新文学作家对于当时社会 上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苦闷的一种艺术描述,而且是新文学作家群体借助并通 过自己笔下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真实而生动地展示了他们本人灵魂深处内在的思想矛盾 和情感磨难。诚如“五四”新文学另一位巨子郭沫若在其狂热激情严重受挫后所哀鸣的 那样:“我们内部的要求和外部的条件不能一致,我们失却了路标。”[5]从坚定地信 仰西方人文主义的启蒙精神到“失却了路标”,“五四”知识分子精英群体思想理念的 极不稳定性,就其本质意义而言,实际上已向社会发出了新文学价值观正面临着重新选 择的暗示信号。由于受20世纪中国文学与中国政治一体化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关系所决 定,随着席卷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迅猛崛起与发展,必然会导致无产阶级意识形 态价值观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全方位介入。而这种全新价值观的介入,无疑是成功地拯 救了当时正处在停滞状态并失去了前进方向的新文学运动。
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价值观与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之间错综复杂的结盟关系,我个人始 终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必然性。如果我们从时间概念的角度来 做一分析,1926年前后,中国新文学运动出现了一种带有普遍性质的社会现象,十分值 得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与深刻思考。当时那些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新文学代表性作家 ,他们在其逐步放弃了先前的思想信仰并开始自我深刻反省时,几乎都对文学崇高而神 圣的思想启蒙使命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五四”精神 自我矛盾的思想裂变现象)。与此同时,在急功近利传统文化观念的支配之下,他们对 于文学本质与功能的认知态度,也一步一步地走向了非理性的情感偏执——即:从文学 “决定论”走向了文学“无用论”。比如,一向被研究者所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 退潮后,仍然坚定地厮守着人文主义启蒙精神的文学巨人鲁迅,此时他却主动放弃了对 文学创作的原有激情(事实已经证明,1926年以后,鲁迅基本上脱离了文学创作的具体 实践,其主要精力基本转向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斗争),愤然发力向社会大声疾 呼道:“文学文学,是最不中用的,没有力量的人讲的”;“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 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6](P417-423)。 又如,先前一直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并一再声明将艺术视为是生命惟一的郭沫若, 此时也逃离了象牙之塔的艺术宫殿(无独有偶,郭沫若也是从这个时候起终止了他对缪 斯的青睐,目的明确地加入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政治斗争。他40年代的历史剧创作 ,也多是出自于政治斗争的实际需要,而并非是出自于真正自觉的艺术追求),并公开 改变了以前对于文学的神圣信念,他斩钉截铁的认为:“要解决人类的痛苦,那不是姑 息的手段可以成功的”,使用文学的方式根本不可能发生任何效率,最终只能“用武力 来从事解决”[7]。众所周知,鲁迅与郭沫若的人生观和艺术观,客观上都存在着很大 的差异性,但是到1926年前后,他们对于文学功用的认识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前途命运的 思考,却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应该说,他们对于文学自主意识的全然放弃,是因为 他们已清醒地意识到了文学缺乏改造社会现实的直接效应;而他们对于政治革命和武力 崇拜的自觉认同,则从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反映出了他们对于“五四”人文主义启蒙精神 的潜在否定。“无产阶级”这一新生社会政治力量的出现与存在,他们在苏俄社会主义 革命取得成功的具体实例的感召下,纷纷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对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理 解和向往。不仅鲁迅与郭沫若反复地在他们的文章里阐述了见解相同的上述观念,茅盾 也在此时对“为人生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发生了质疑,他强调“在我们这时代,中产阶 级快要走完了他们的历史的路程,新鲜的无产阶级精神将开辟一新时代,我们的文学者 应该认明了他们的新使命,好好的负荷起来”[8]。而诗人气质颇浓、个性意识极强的 郁达夫,虽然对中国社会现状大为不满,但他对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预测则说得更为大 胆而直率:“我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抬头,是绝对承认的。所以将来的天下,是无产阶 级的天下,将来的文学,也必然是无产阶级的文学。”[9](P63)无论以鲁迅等人为代表 的新文学作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理解程 度如何,但是他们所自觉萌生的这种内在思想情感的倾向性,其本身就已经向世人表明 了他们有对此深表认同的主观要求。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鲁迅、郭沫若、茅盾、 郁达夫等人在“五四”中国文坛上,客观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和精神号召力; 他们思想的急剧变化,必然会波及到整个新文学阵营,并使之迅速转变成为一种新文学 作家的社会群体行为。否则仅仅凭着“创造社”与“太阳社”的几个热血青年,运用从 国外贩来的一些抽象理论概念在那里尽情地加以鼓吹,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决 不可能“自此就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潮”[10]。对此我们不必加以怀疑。
二、碰撞中的交流对话:“革命文学”口号之争历史内涵的重新诠释
在“五四”新文学作家思想整体转向的过程中,发生于1928年的那场“革命文学”口 号之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事件。“革命文学”的倡导者与“五四”文学精英通过 一场大规模的思想碰撞交流,彻底摧毁了新文学作家的个人主义思想信仰,并顺利实现 了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全面转型。
谈到“革命文学”口号之争,我个人有些与众不同的看法。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 那段最为艰难的时间里,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的一些成员,他们率先高举起了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醒目大旗,并以革命时代急先锋的身份亮相于中国现代文坛。他们 中间绝大多数人都是二十多岁的热血青年,青春期的情感躁动结合于浪漫主义的政治理 想,使他们强调文学创作的主观战斗精神和直接作用于社会革命的政治功利目的;反抗 叛逆的时代情绪借助于一种全新的政治理念,又使他们表现出了比“五四”新文学更为 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他们将除郭沫若以外的所有“五四”新文学作家,全都视为是历史 变革时期的思想落伍者,并以讥笑和嘲讽的狂妄语言,对“五四”人文精神作了虚无主 义的全盘否定。总而言之,他们就是要以一种脱胎换骨的激进形式,凭借自己彻底清除 现代文坛沉闷气氛的主观意志,去刻意营造一个狂飙突进的革命浪漫主义的文学时代。 用现在的眼光来看,他们当时的思想行为不免有些幼稚和莽撞,但却正是由于这些年轻 人幼稚与莽撞的大胆举动,才为已经陷入了困境的“五四”新文学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至于为什么他们会同鲁迅等新文学主将发生激烈地思想冲突,我认为这绝不是一个简单 的“意气用事”或“门户之见”的个人成见问题,而是一个对于现代文明意识思想见解 完全不同的认识角度问题。“五四”新文学作家主张以纯粹“客观”的人生写实态度, 去真实地描写主体人性的思想情感,进而通过对个体事例的艺术再现,去生动地反映中 国社会的真实现状;而“革命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则强调说,任何所谓的“客观”性, 其实都只不过是一种创作主体主观意志的集中表现,所以他们主张以无产阶级集体主义 的政治革命理想,去深刻地分析中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反映劳苦大众的革命要求,并通 过对阶级意识与阶级斗争的艺术写意性,去生动揭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美好前景。我 们不妨先去听听“革命文学”口号的倡导者,他们本人对于这场论争的原始表述:
中国社会革命的潮流已经到了极高涨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无处不表现着新旧的冲 突。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是如此的现象,因之在表现社会的文学上,也不得不起了分化 。一般先进的分子及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因为要走向自由的路上去,不得不起来反抗旧 的势力。因之我们很显然地看出革命与反革命的争斗。同时,在我们文坛上,一股激进 的文学青年,为着要执行文学对于时代任务,为着要转变文学的方向,所以也不得不提 出革命文学的要求,而向表现旧社会生活的作家加以攻击,这一种现象,在表面上观之 ,似乎只是文坛上的论争,似乎只是新旧作家的个人问题,其实这种现象自有其很深沉 的社会的背景,若抛开社会的背景于不问,而空淡什么革命文学,那是毫无意义的事情 。[11]
从“创造社”与“太阳社”成员的所有理论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他们提出 “革命文学”口号的主观意图,就是要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信仰,去统一中国现代文 坛上的思想混乱局面;以革命理想主义的艺术追求,去规范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无政府主 义个体行为。正是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革命文学”口号的倡导者对于“五四”新文 学自由涣散的精神状态大表不满。他们指出:“五四”新文学作为“中国的资产阶级的 文化革命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狂热追求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一切种种资 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完全是落后时代的精神产物。[12](P22-23)而 作为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言人,新文学作家“他们历史的任务,不外一个忧愁的小 丑”[13]。他们的创作无一例外都因其思想意识的灰暗性,而根本“没有现代的意味” 。[14]比如他们称叶圣陶“是一个静观人生的作家,他只描写个人——当然是很寂寞的 有教养的一个知识阶级和守旧的封建社会,他方面和新兴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隔膜’。他是中华民国的最典型的厌世作家,他的笔尖只涂抹灰色的‘幻灭的悲哀’。”而“鲁迅这位老先生——若许我用文学的表现——是常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他的小说创作,“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话”[13]。他们甚至还把鲁迅的文学创作,统统视为是小资产阶级灰色人生观的消极产物,并强调说它只具有作为旧社会挽歌的存在意义,而无法给人指出理想和希望。“鲁迅所以陷入这样的状态之中,我们可以说完全是所谓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的结果只有徘徊,所谓自由思想在这个世界上只是一个骗人的名词,鲁迅便是被骗的一个。”[14]无论人们如何去评价这段历史公案,但有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那就是这场论战的客观效果,无疑加快了鲁迅等“五四”文学精英思想“左”转的时间进程
“革命文学”口号的倡导者们,都是沐浴着“五四”人文精神的阳光雨露成长起来的 年轻一代,但他们却都以对“五四”精神的彻底背叛而昭示着他们对于前人的大胆超越 。所以谈及“革命文学”口号之争,我的兴趣点并不是鲁迅等人思想“左”转的事实本 身,而是那些热血青年是如何促使鲁迅等新文学巨匠毫无条件地接受了他们全新的革命 文学理想,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如果我们进 一步去分析研究“革命文学”口号倡导者的原始理论主张,便能够发现他们是以马克思 主义的现代革命哲学为武器,用强大的政治理论攻势无情地摧毁了鲁迅等“五四”人文 主义作家所做的无谓抵抗。首先,“革命文学”口号的倡导者根据中国社会形势的新变 化,他们敏感地意识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到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 历史时代。那么在这个新时代里,“革命文学,不要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是由 历史的内在的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15]。其次,他们认 定现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价值理念,已经发生了“由个人主义趋向到集体主义”的根本性 变化,那么中国现代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历史使命,就应“是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 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作为现代 政治意识形态附属品的现代文学,它同样应该以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创作上表现出 崇尚集体主义、反对个人主义的鲜明政治态度。再者,革命文学因其具有了无产阶级的 政治属性,因此它必须“完成他主体阶级的历史使命,不是以关照的——表现的态度, 而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产生出来一种斗争的文学”。这就要求“我们的文学家,应 该同时是一个革命家。他不仅在关照地‘表现社会生活’,且实践地变革‘社会生活’。他的‘艺术的武器’同时就是无产阶级的‘武器的艺术’”[11]。再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宗旨是要描写“中国的被压迫群众对于帝国主义的反抗”和“旧社会制度的反抗”,“它的主人翁应当是群众,而不是个人主义”。“革命文学的任务,是要在此斗争的生活中,表现出群众的力量,暗示人们以集体主义的倾向。”[11]“文学革命”的倡导者正是以他们政治革命理论的严密逻辑性,将鲁迅等“五四”文学精英无情地推到了严酷的阶级斗争现实面前,并明确地告诉他们现在“摆在每一个人底面前的,只有二条路径:走革命的大道呢?否则,就陷落在反革命的泥坑之中”[16];究竟是赞成革命并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集体主义精神的立场上,还是不赞成革命并站在与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为敌的立场上?鲁迅等人实际上已无可选择。当鲁迅等人在这场论战的过程中,被逼无奈不得不去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时,实际上已预示着这场论战的结束和“革命文学”理念对于“五四”新文学人文精神的彻底胜利。
需特别强调的是,鲁迅和其他“五四”文学精英对于“革命文学”基本理论的最后无 条件的接受与认同,还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中介因素我们不能加以忽视:从“五四”新 文学的崇尚文化功利主义,到“革命文学”的崇尚政治功利主义,从新文学的“文艺为 人生”主张,到“革命文学”的文艺为劳苦大众服务宗旨,新文学作家的认识转变其实 并没有遇到什么根本性的思想障碍,这中间只不过是文学实用对象而不是文学实用目的 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的客观结局,无非是使文学实用主义的目的与对象都变得更加 具体化了。所以“革命文学”的倡导者用他们青春的理想与叛逆的勇气,不仅没有将鲁 迅等人排除出“革命文学”的阵营,反而却重新激活了他们参与变革现实社会的巨大政 治热情。当鲁迅等人与“革命文学”口号的倡导者握手言和,并联合其他进步作家共同 于1930年3月2日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时,它即宣告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 史终结,同时也宣告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开始。
三、规范整合的完结:中国现代文学主流价值观的最后确立与定型
鲁迅等“五四”文学精英加入了“左联”,与“左联”接纳鲁迅等“五四”文学精英 ,应该说这是一个双赢的结局。因为鲁迅等新文学作家借加入“左联”的机会,彻底摆 脱了后期的精神苦闷,并寻找到了新的思想增长点;而“左联”则因鲁迅等人的加盟, 使得自己完全获得了精英文化的社会表现形态。两者合二而一的最后结局,是使中国现 代进步作家以一个强大的群体声音,形成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话语时代。
“左联”并不是一个纯粹文学意义上的社团组织,而是中国无产阶级在文学领域中传 播自己政治意识形态的一个“斗争机关”[17]。当它的成员初步完成了思想意识的规范 整合之后,“左联”内部在涉及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都达成了 基本一致的思想共识。“左联”组织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向社会公开宣称自己政治功利 主义的文学主张:“我们——普罗列塔利亚——的队伍正向着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进攻 !我们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政权,我们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生产机关!我们更要把这 些实际的斗争和我们阶级的意识反映到艺术上去,摧毁资产阶级的艺术!”[18]当然, “左联”成员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斗争,是流血的斗争。我们的生命,是冒着极 大的危险。”[19]从这些铿锵有力且火药味十足的文字词汇中,我们所感受到的不仅是 左翼革命作家对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理想的虔诚信念,而且也十分直率地表露出了他们 渴求参与现实“战斗”的主观愿望和创作冲动。如果我们以平和的阅读心态去进入30年 代左翼革命文学的话语体系,仅凭直观感觉便能发现在文学从属于政治观念的支配下, 左翼作家所使用的关键性词语都发生了观念上的明显变化:“阶级性”淘汰了“人性” ,“我们”取代了“我”——个体形象的阶级群体化特征和艺术典型化意义,直接构成 了左翼革命文学与“五四”新文学完全不同的审美价值取向。正是从关注社会大多数人 的人性(主要体现为是被剥削与被压迫者的政治权利和生存权利)立场出发,左翼作家坚 信“阶级性”是“人性”的合理发展,是“人性”的最高体现与千古永恒的价值准则; 因此他们以前所未有过的政治激情与极度亢奋的精神状态,由衷地表达他们“与人奋斗 ”的政治理想和奋发向上的乐观情绪。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政治信仰,“左联”组织还 要求它的成员,必须以深刻的政治眼光和正确的阶级立场,去真实地反映中国现实社会 生活的本质特征——不但要揭示“资本主义的崩溃”与“地主阶级的崩溃”的历史必然 趋势,同时还“必须描写农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以及工农革命运动的兴起;[20]不仅 要生动而艺术地再现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而且还要 形象化地描述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未来美好前景。在左翼革命作家的艺术思维中,文学 的社会价值只有经过现实阶级斗争“血与火”的洗礼才会得以实现,艺术创作的生命乐 趣也只有在充满着政治理想主义的青春激情中才会具有实际的人生意义。正是基于这样 一种艺术思维方式,3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渐渐褪去了个人主义的喜怒哀乐情调,逐渐 加重了它时代政治使命感的主观战斗色彩。从此以后,中国现代作家已不再是作为文学 创作上独立自为的个体存在,而是集体转变成了被剥削者、被压迫者的意识形态代表以 及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锋战士。
左翼革命作家主观战斗精神的获得,使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警觉性,随时准备去应付各 种各样自由主义文学思想的公然挑战。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左联”时期发生的 文艺论战次数最多,既有外部的,也有内部的,论争的焦点则都是所谓的文学自由问题 。由于左翼革命作家思想的规范整合刚刚完成,“左联”的基础还比较脆弱,再加上国 民党执政当局的政治绞杀,因此左翼革命文学运动所面临的形势也非常严峻。这不能不 使左翼革命作家以极其强硬甚至于有些武断的态度,去面对一切危及自身生存的社会异 己力量。尤其是当“新月派”、“第三种人”和“自由人”试图用个性自由意识同“左 联”所倡导的集体主义精神相抗衡,并对其进行纯粹文学意义上的理论解构时,“左联 ”文学阵营为了维护自己价值观念的正确性和权威性,势必要以思想斗争的强硬姿态做 出群体的回应。一场大规模的理论交锋也就因此而再所难免。综观这几次大的思想论战 ,左翼革命作家几乎是以前所未有过的思想一致性,向“左联”组织内外一切资产阶级 自由化的文学观念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他们的共同理论见解是: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他 所客观隶属的阶级群体面独立存在,个人只不过是不同阶级群体中的一分子。强调抽象 的个体“人性”,无非就是要将作家个人的狭隘利益凌驾于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之上, 这无疑是同无产阶级集体主义价值观相对立的。因此他们主张“批判一切个人主义,人 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类的腐化的意识”[11]。牢固树立无产阶级革命的人生观与价值观 ;并要求广大作家充分认识到民族群体的全面解放乃是个人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民族 现代意识的全面确立乃是独立人格健康发展的必要保障。如果仅仅关注个人的精神痛苦 而忽略了社会群体的公众利益,那是典型的没落腐朽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在这一次次的 思想论争过程中,左翼革命作家向社会显示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话语霸权意识:无产阶级 革命文学“所要的是全盘,不是一角的地位”[21](P208)。由此可以看出,“左联”正 是以其外向扩张的战斗姿态,不仅捍卫了自己政治理想的神圣尊严,而且也扩大了自己 的政治影响。毫无疑问,“左联”时期所有文艺论战的层面意义,都直接体现为无产阶 级集体主义精神对于“五四”人文精神的批判和取代;但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由于批判与取代者(如鲁迅等人)大多都曾是“五四”人文精神的传播者或信仰者, 所以论战的本质意义又间接地体现为“五四”人文精神的传播载体,在新的历史形势下 对“五四”人文精神的自我否定。“左联”以其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全面压倒了一切 反对者的微弱呼声,并在进一步巩固了“革命文学”口号之争已取得的胜利成果的基础 上,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全面无产阶级意识化,扫清了最后的思想障碍。
左翼革命作家思想的规范与整合,使得他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主题与创作方 法,也形成了相对统一的看法。从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大局的前提出发,“左联” 在其组织决议中,明确要求它的成员应以广阔的艺术视角去反映大的革命时代背景:既 要表现“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旧世界,因为内部矛盾日益发展,经济危机加速的深化,现 在无处不是饥饿,杀戮,镣铐,无处没有斗争,愤懑,革命,一切惨淡残酷黑暗的光景 证实资本主义第三时期的腐败崩溃的特质”;同时也应表现“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日益 显著,广大劳苦群众的生活,日益向上改善,充满着和平,建设,协力,幸福,热心和 一切光明的要素”[17]。为此,“左联”还特地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题材,做出 了以下5个方面的硬性规定:
(1)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的题材——描写帝国主义对于中国劳苦民众残酷压迫和剥 削,分析帝国主义和中国农村经济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分析帝国主义和封建势 力,军阀地主资本家的政权,以及各派资产阶级的利害关系。分析各帝国主义在中国的 利害冲突。暴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以中国作军事根据地进攻苏联的阴谋,中国民众反 帝国主义的各种英勇的斗争,等等;(2)作家必须抓取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 阀混战的题材——分析这些和帝国主义的关系,分析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描写广大群 众的数重的被压迫和被剥削的痛苦情形,广大的饥饿,巨大的灾祸,描写军阀混战的超 过一切大灾祸也造成一切大灾祸的战祸,描写农民和士兵对于军阀混战的憎恶及其反抗 的斗争和兵变,等等;(3)作家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苏维埃治下的民众生 活、红军及工农群众的英勇的战斗的伟大的题材;(4)作家必须描写白色军队“剿共” 的杀人放火,飞机轰炸,毒瓦斯,到处不留一鸡一犬的大屠杀;(5)作家还必须描写农 村经济的动摇和变化,描写地主对于农民的剥削及地主阶级的崩溃,描写民族资产阶级 的形成和没落,描写工人对于资本家的斗争,描写广大的失业,描写广大的贫民。[28]
“左联”对其成员所提出的具体创作要求,无论是描写现实斗争还是展示未来理想, 字里行间都充斥着强烈的主观战斗精神。而左翼革命作家也以高度自觉的组织原则,忠 实地执行了“左联”关于革命文学创作的组织决议:他们以“无产阶级的观点,从无产 阶级的世界观”出发,[22]“在文艺上表现中国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23],深刻地反 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以及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千 丝万缕的错综复杂关系(如茅盾的《子夜》);以一个纯粹农民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农村, 揭示“那边郁积着要爆发的感情”[24]。“真实”而艺术地生动再现了中国工农民众阶 级意识的空前觉醒和奋起反抗(如蒋光慈的《短裤党》、胡也频的《光明在我们的前面 》、茅盾的《春蚕》、叶紫的《丰收》、洪琛的“农村三部曲”等);以“辩证法为工 具,去从繁复的社会现象中分析出它的动律和动向”,并“从这些现象中指示出未来的 途径”[17],用革命的理想主义去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革命斗志以及增强他们的革命 信心(如胡也频的《同居》、华汉的《尘影》、洪灵菲的《前线》、欧阳山的《竹尺与 铁锤》等)。左翼革命文学的创作实践,以乐观向上的革命浪漫主义情调,强劲支撑着 左翼革命文学的政治理想,并由此而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学革命英雄主义的红色经典时代 。
全面回顾中国现代作家思想转型的历史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 入主中国现代文学运动,乃是一种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人们是以什么样的眼光去 看待这段历史,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客观事实:解放区文学与新中国文学的理论架构与 创作模式,几乎都能从这里找到它最初的思想源头。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1926年至 1930年,仅仅四年多时间中国现代作家的思想律动,便凝聚了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子 。
收稿日期:2002-05-12
标签: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作家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群体行为论文; 个人价值观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读书论文; 个人主义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