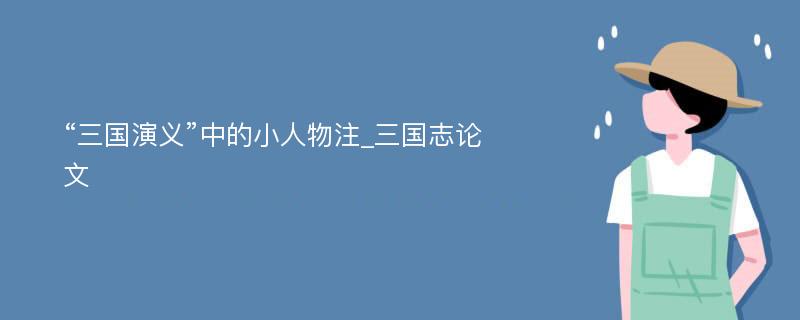
论《三国演义》的小字注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字论文,演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是《三国演义》研究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围绕嘉靖本小字注的作者、作注的时间、小字注的价值等问题,学术界曾经开展过有益的探讨。早在197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出版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出版说明”中,就尝试用“地名注”解释小说的成书年代问题。1980年,章培恒先生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前言”中,再次利用“今地名”小字注去探求《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肯定小字注是罗贯中原作,并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以前。袁世硕先生在《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注:袁世硕《明嘉靖刊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东岳论丛》1980年3期。)一文中,也肯定小字注是小说作者所加,并从地名注与元代地理名称相符入手,证明嘉靖本成书于元代。但是,章先生说除“偶尔误用宋代地名外”系元代地名,袁先生说“除了儿个笔误之外”与元代之行政区名称相符,这些例外不是“误用”或“笔误”所能解释的。正是这些例外说明了“今地名”注不完全反映某一朝代的地理情况。欧阳健先生考察了嘉靖本的“今地名”小字注,认识到“书中的‘今地名’,远至汉晋,下迄明代,确实比较复杂”,但他同意章、袁二先生“小字注出自罗贯中之手”的说法,也以“误用”去解释“今地名”反映不同朝代地理情况的矛盾现象,并对小说成书时间得出了不同的看法:“全书初稿的完成,当在1371年以后”。(注: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同样利用“今地名”作为证据,得出小说成书年代的结论却相去甚远,看来仅用地名注去推求小说的成书年代是行不通的;把小字注定为罗贯中所作更会碰到无法解决的矛盾。
与章、袁、欧阳等先生不同,王长友先生认为小字注不是《演义》小说作者所作,(注:王长友《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是作者手笔吗?》,载《武汉师院学报》(哲社版)1983年2期。 )这个前提是对的,但是对于小字注的来源却没有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且王先生认为作注的时间“远在小说刊行之后”,更与事实相去甚远。张国光先生则认为:嘉靖本小字注是“该书作者抄录旧籍时随手所加”,只是他认为小说作者是庸愚子蒋大器,并据此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注:张国光《〈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于明中叶辨——与王利器、周村、章培恒等同志商榷,兼论此书小字注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版。)笔者不敢苟同《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是蒋大器的观点,但赞同张先生“抄录旧籍”的说法,问题在于:是谁在什么时候“抄录旧籍”并另加小字注?近年来,有的论者从不同侧面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李伟实先生认为:《演义》的夹注及诗文论赞是修髯子张尚德所加(注:李伟实《〈三国志通俗演义〉夹注及诗文论赞何人所加》,《社会科学战线》1989年2期。); 张志合先生认为:给嘉靖本作整理加工和增订注文工作的是张尚德,但作注的还有别人。(注:张志合《〈三国演义〉的小字注非一人一时所加》,《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6期。)
遗憾的是,上述争论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小字注问题最后被作为悬案搁置起来。笔者认为,嘉靖本小字注的问题之所以悬而未决,主要原因是:第一,只盯着嘉靖本的小字注,对别的明刊本中的小字注却视而不见。缺乏不同版本的参照与比较,因而阻碍了研究向纵深发展。嘉靖本固然是《三国》一个很重要的版本,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刊本,但是还有别的二十多种明刊本存在,它们的重要性不容忽视;第二,只基于嘉靖本小字注中的某一部分(比如地名注)立论,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其结论难免以偏概全。
本文试图通过全面地考察嘉靖本的小字注,并参考其他明刊本相关的小字注,对《三国演义》的小字注问题作比较全面的分析,就教于专家及同好。
一、从一条可疑的小字注谈起
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下文简称标点本)卷二十二《司马懿父子秉政》一则写到司马懿杀死曹爽,大权在握,下有一段文字:
懿忽然想起:“曹爽全家虽诛,尚有夏侯玄守备雍州等处,系爽亲族,倘思骨肉之情,骤然作乱,如何提备?必当处置。”即下诏遣使,往雍州取征西大将军夏侯玄赴洛阳议事。玄乃曹爽外弟。此时夏侯霸正在雍州守把隘口,听知司马懿取夏侯玄【其后有小字注云:玄乃霸之侄】,霸大骇惊惧,心中忧疑,慌引兵三千出城哨探。
标点本的底本应是据涵芬楼藏本影印的商务印书馆本(以下简称商务本),或者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上海图书馆藏本为底本并配以甘肃图书馆藏本的影印本(下文简称人文本)(注:商务本与人文本虽统称为嘉靖本,但二者有初刻本和覆刻本之分,人文本是初刻本,而商务本是覆刻本,详细的考证可见刘世德著《夜话三国》,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但是商务本“玄乃霸之侄”一句却以正文的形式出现,又查人文本,“玄乃霸之侄”一句亦是正文,不知标点本这条小字注何所据。可能是标点整理者从上下文考虑,认为“玄乃霸之侄”一句改为小字注更加合适一些吧?果如是,则说明该小字注出自今人之手;既然今天的标点者能“作”小字注,则当时嘉靖本的编订者更是可以“作”的。以此推想,嘉靖本小字注是《三国演义》小说作者手笔的说法就大可怀疑了。
其实,在嘉靖本中,“玄乃霸之侄”一句,无论是作为正文或作为小字注,这句话的出现都非常突兀,它与小说另外相关的内容抵触,造成了前后人物关系的混乱。请看卷二十二第四则“姜维大战牛头山”有关叙述:司马懿只忧曹氏、夏侯氏这两枝宗党。日夜不安。令人取征西将军夏侯玄赴洛阳议事。玄叔夏侯霸听知大惊,引本部三千军造反。……霸亦骂曰:“吾祖父于国家多建勤劳,今司马懿何等匹夫,灭吾兄曹爽等弟兄,夷其三族,却乃父子三人掌握朝纲,又来取吾,必有逆心篡位。吾今仗义讨贼,汝赶来,何也?”
既然上文言明夏侯霸是玄之叔,而又言玄乃曹爽外弟,则霸应为曹爽叔辈,这里夏侯霸称曹爽为兄,显然不对。如果“玄乃霸之侄”是作者所加,恐怕说不过去。出现这种讹误只有一种可能,即它出自别人所加。因为不是小说作者手笔,所以与其他内容矛盾。
司马氏召夏侯玄赴洛阳议事,看来他还是听命去了,引兵三千出城哨探并造反的是他的叔叔夏侯霸。(注:《三国志·魏书》卷九载:“爽诛,征玄为大鸿肪胪,数年迁太常。玄以爽抑绌,内不得意。中书令李丰虽宿为大将军司马景王所亲待,然私心在玄,遂结皇后父光禄大夫张缉,谋欲以玄辅政。”《三国志》裴注引《魏略》云:“霸字仲权。渊为蜀所害,故霸常切齿,欲有报蜀意。……至正始中,代夏侯儒为征蜀护军,统属征西。……及司马宣王诛曹爽,遂召玄,玄来东,霸闻曹爽被就而玄又征,以为祸必转相及,心既内恐;又霸先与雍州刺史郭淮不知,而淮代玄为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
夏侯玄应诏赴洛阳后,出现在嘉靖本卷二十二第七则“司马师废主立君”之中,其时司马氏专权,曹芳成了孤君,有一次,他向曹芳奏道:“臣兄夏侯霸非反,因惧司马师弟兄而投西蜀。今若剿除此贼,臣兄必回也。臣乃国家旧戚,安敢坐视奸贼也。”口口声声称呼夏侯霸为“臣兄”,又与“玄乃霸之侄”一句明显矛盾。加这句话的人只是依据史书,指出夏侯霸与夏侯玄为叔侄关系,夏侯玄与曹爽乃表兄弟,却没有顾及小说正文之中夏侯霸称曹爽为兄,夏侯玄称霸为兄的描写。
可见,“玄乃霸之侄”一句来路不明,那么它究竟出自何人之手呢?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即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原稿最初是以抄本的形式流传的,诚如蒋大器所说:“书成,士君子之好事者,争相誊录,以便观览,则三国之盛衰治乱,人物之出处臧否,一开卷,千百载之事,豁然于心胸矣。”(注: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庸愚子蒋大器所作《序》。)很难保证这些“好事”的“士君子”在“争相誊录”的过程中不有所作为,兴之所至则随手批注一二有何不可?直接参与嘉靖本刊刻工作的庸愚子蒋大器就是“好事者”之一,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中,他特别提到读书要有自己之所得:“予谓诵其诗,读其书,不识其人,可乎?读书例曰:若读到古人忠处,便思自己忠不忠;孝处,便思自己孝与不孝。至于善恶可否,皆当如此,方是有益。若只读过,而不身体力行,又未为读书也。”所谓“身体力行”,对“士君子”而言,添加史料或把读书所得写下批注是重要的一环。这些东西到了嘉靖本中就是今见的小字注。
目前为止,还不能确定小说从抄本到刻本的流传过程具体有多长时间,不过,今见《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最早刻本嘉靖本刊行于嘉靖元年(1522),(注:不排除存在过早于嘉靖本刻本的可能性,但在最早的刻本之前,《三国志通俗演义》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了很久是毋庸置疑的。)而罗贯中大体生活于14世纪,那么至少这一过程持续了百年之久,其间罗氏原稿历经辗转抄录,到它正式刊刻之时,与原稿相比已是面目大变,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嘉靖序刻本增加了四百多条小字注。以前的研究者在讨论小字注的问题时,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传抄的过程,而问题恰恰就出在其间。
二、嘉靖本大量音注不是罗贯中所加
嘉靖本共有四百余条小字注,其构成成分斑驳杂乱,其中注音释义的一百七八十条,增补叙事内容的一百多条,介绍人名、表字、品评人物的一百多条,地名注四十来条,诗文及《论》、《赞》、《评》的注解二十多条,还有少数几条点明材料出处的注语。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小字注的添加非常随意,没有整体规划,看得出来非一人一时所加,而是传抄过程中不同人的手笔。
以音注为例,洋洋近九十万言的巨著,应该注音的难字何止上百,凭什么只选这一百多字进行音释呢?有许多字是习见常用的,根本不必作注,而许多生僻的难字又不加音释,这不仅说明注释出自多人之手,也说明了作注者文化素养的参差不齐。作注者基本采用“直音法”注音,即用习见的常用字去训生僻的难字,比如“揲蓍”注为“音舌尸”,“谗阋”的“阋”注为“音隙”等等。如果这些注音是作者一人所加,按理前后应该比较一致,但是不然,有几处地方同一字却用了不同的字作注。像“妆奁”的“奁”字在卷二之六和卷四之七分别注为“音连”和“音廉”,“揲蓍”的“蓍”在卷八之四和卷十六之二分别注为“音尸”和“音诗”。因此有理由假定这些音注出自不同人之手。
另外我们注意到,嘉靖本一百七十余条音注中,只有两条采用了反切法注音。其一是,第一卷之三“张飞安喜鞭督邮”中“径揪到县前马柳上缚住”一句后注云:柳,鱼浪切,系马桩也。(上海古籍出版社标点嘉靖本误“马柳”为“马柳”)其二是,第八卷之九“献荆州粲说刘琮”中“岂其负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一句后注云:园,即刓字,五丸反,谓刓团无棱角也。每,贪也。下文将要论及,第二条音释是抄袭《东汉详节》为孔融之死所写《论》中附带的,不是小说作者所加;剩下唯一一条用反切法注音的小字注需要在此多说几句。《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载:“先主(注:“安喜鞭督邮”的主人公原本是刘备,罗贯中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时采用他惯用的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备的故事说成张飞所为。)……除安喜尉。督邮以公事到县,先主求谒,不通,直入缚督邮,杖二百,解绶系其颈着马柳。”裴松之在“马柳”后注云:“五葬反”。但是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没有采用裴松之的这条音注,而是改“五葬反”为“鱼浪切”,且加了释义。姑不论罗贯中在别处从没有采用裴松之的音注(我们知道《三国志》裴注的音释是很多的),就算他偶尔采用裴注的音释,他为何不直接援引,却偏偏要作“五葬反”为“鱼浪切”这样无谓的改动呢?为了佐证这一点,再举一个罗氏不用裴注音释的例子:《三国志·魏书》卷一《武帝操》载:“黑山贼于毒、白绕、眭固等【后有裴注:眭,申随反】十余万众略魏郡,东郡王肱不能御,太祖引兵入东郡,击白绕于濮阳,破之。”而嘉靖本卷四之八“白门曹操斩吕布”中“却被张杨部将眭固杀之,……”“眭固”后注云:“眭,音锥,姓也。”裴注用的是反切法,而嘉靖本采用的是直音法,说明了罗贯中并不采用《三国志》的音注,改动或添加嘉靖本音释小字注的只可能是传抄者或刊行者。
下面再来看一看几种闽刊本对“马柳”一词的处理:
藜光堂本:“被张飞扯到县前马柳上缚住”一句后有小字注云:柳,音昂,系马桩也。
联辉堂本、双峰堂本:“被张飞……径揪到县前马柳树上缚住”一句后有正文:“柳,即今系马桩是也。”
乔山堂本、朱鼎臣辑本:“被张飞揪到县前缚在柳树上”一句后既无小字注亦无正文。
汤宾尹本此处小字注残缺,仅剩“系马桩也”四字,不知是否有注音。
如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嘉靖本标点本一样,许多闽刊本将“马柳”误作“马柳”,难得的是藜光堂本没有致误,仍写作“马柳”,但是其音释小字注却改成了直音法,这说明藜光堂本并没采用嘉靖本的这条音释小字注,而是另有所出。无独有偶,同属嘉靖本系统的夏振宇刊本也没有采用嘉靖本的这条音释小字注,而是与藜光堂本一样,在“马柳”后注为:“柳,音昂,系马桩也。”
嘉靖本和其他明刊本对同一个词的音释小注均异于史书的注音,说明依据史书创作《演义》祖本的罗贯中没有采用史书的注释;嘉靖本和闽刊本同一个词音小注不同,又说明《三国演义》祖本的作者也没有添加这些音注。那么嘉靖本和闽刊本中这些音释小字注的来历就很明显了,它们或者是传抄者在传抄过程中随手所加,或者是刊刻时编订者所为,都不是罗贯中的手笔。《三国演义》不同版本系统同一内容小字注歧异的事实,证明《三国演义》的小字注在小说传抄刊刻的过程中曾屡遭改易。
另外,有人从音韵学角度探讨了嘉靖本中的音释小注的作注时间,据分析,发现嘉靖本的音释小字注有三个特点:其一,入声已消失;其二,无闭口韵;其三,近代汉语的庚清韵部与钟东韵部合流。据此三项推断,“音释的时代远在《中原音韵》、《洪武正韵》之后,而距万历不远,或许是正德、嘉靖年间。”(注:参见李伟实《〈三国志通俗演义〉夹注及诗文论赞何人所加》一文引宁继福先生的有关论述。)这与笔者的结论吻合,也证明元末明初的罗贯中不可能是嘉靖本音释小字注的作者。
三、老生常谈“地名注”
嘉靖本的地名注也一样,完全没有统一的体例,成千上万个地名,为何只给这四十来个地名加注?该注的不注,不该注的却又注了,有许多地名后只注“地名”二字,纯属多余。也有同一地名几次加注却前后不一的情况。比如:卷十三提到“绵竹”,后注云:“今县名”,但卷二十四再次提到“绵竹”时,却注为:“今雒城”,若是作者一人加注,既然前文已注明绵竹是“今县名”,为何过了不久就成了需要重新加注的非“今县名”了?更令人生疑的是同卷提到雒城,却又注云:“今涪城”(而且卷十三出现“雒城”时,并没有加注;只在“雒县”后注云;古县名,今之江州也)看来“雒城”又成了非“今地名”,我们不禁要问:到底绵竹、雒城(雒县?)与涪城三者是否是一个地方,若是,哪一个是“今地名”?欧阳健先生虽然发现了其中的矛盾,但在揭示产生矛盾原因的时候,却认为它揭示了罗贯中写作的时限,并“假定罗贯中1371年以后写到第二十四卷”云云,未免牵强附会(注:见欧阳健《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年代》,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罗贯中生活于元明易代之时,同一地方也许有过名称的更迭,但显然不会如此变化多端,而况他创作《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时候,彼时的“今地名”是相对稳定的,他脑子里关于某一地方的概念也是固定的,绝不会忽此忽彼,对同一地名乱注一气。
但如果说嘉靖本的地名注是在小说传抄过程中和刊刻时由不同的人杂采旧籍时插入的,那么地名注混杂不清的原因就迎刃而解了。我们知道,不同的地理和历史旧籍给三国时的地名加注时是不一样的,汉晋人给某地加注“今时”何地说明汉晋的地理情况,宋元的人加注“今时”何地反映宋元的地理情况,明初的人加注“今时”何地反映明初的地理情况,而传抄者只知杂采旧籍,搬录前人旧注,故而汉唐宋元旧籍中之“今时某地”全成了嘉靖本中的“今时某地”小字注。比如卷二十“陆逊石亭破曹休”,于皖城后注云:今之浔阳也;卷六“曹操官渡战袁绍”提到官渡,后注云:官渡在郑州中牟县北,二者都反映唐代的地理情况,其中“官渡”注是抄袭《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其他如卷九“夏口”注为“今时鄂县”、卷十一“武陵郡”注为“今属鼎州”、卷十一“桂阳郡”注为“今属郴州”等都跟南宋郭居仁《蜀鉴》之地名注基本相同。
当然,对于加注者自己比较熟悉的地名,他们也不一定迷信旧籍,比如书中出现的几条符合元代地理情况的“今地名”注,就不像是抄录旧籍的注释,而是作注者尽自己所知随手添加,因为作注者本来是元明间人,所以他们添加的“今地名”合于元明间的地理情况,据此大体可以说元末明初即有《演义》的抄本流传并有人加注。
四、“已详见上节”与“已上见详节”
翻检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二之七“王允授计诛董卓”,在有关董卓的论赞之后有小注云:“祲,音侵,已详见上节。”“已详见上节”不知何意。经查涵芬楼影印本,此小字注为“已上见详节”,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上海图书馆藏嘉靖本也作“已上见详节”,看来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时把“已上见详节”误作“已详见上节”,令人无法理解。这条小字注特别值得引起重视。
《详节》当指《十七史详节》中的《东汉详节》和《三国志详节》,据周兆新先生考证:“嘉靖本的《论》、《赞》、《评》直接引自《详节》,而非直接引自《后汉书》和《三国志》。”(对此,周先生举了很有说服力的一个例证:即《详节》引用《三国志·蜀书·后主传》之《评》,抄脱“传、曰、信、矣、哉、焉”六个字。而嘉靖本卷二十四写刘禅降魏,引用此《评》,抄脱了同样的六个字。)“罗贯中编撰的《演义》原本,并没有引用范晔的《论》、《赞》和陈寿的《评》。”“在罗贯中之后,嘉靖元年即公元一五二二年以前,有人对罗贯中的原作进行修订。修订者仅仅依据《详节》,把《论》、《赞》、《评》增入小说,因而亦步亦趋地重犯了《详节》的错误。”(注:见周兆新著《三国演义考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这证明了笔者上文的论述:在“争相誊录”罗氏原稿的过程中直至小说付梓,有“好事者”(即周兆新先生所言之“修订者”)做了手脚——增入《详节》的《论》、《赞》、《评》及其小字注(注:嘉靖本增插尹直《名相赞》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可为“好事者”修订罗氏原稿的又一铁证。)。另外,在闽刊本中找不到下列嘉靖本来自《详节》的《论》、《赞》、《评》,当然更别说有《论》、《赞》、《评》附带的小字注了,这也说明罗氏原稿没有采用《详节》的《论》、《赞》、《评》及其小字注,因为如果罗氏原稿就有,那么总会在闽刊本中保留一二的,闽刊本不会单单删掉来自《详节》的《论》、《赞》、《评》。
据初步统计,嘉靖本中来自《详节》的《论》、《赞》、《评》本身附带的小字注共有二十条左右,它们是:
卷一“董卓议立陈留王”写何进之死所引《论》中一条:“《传》曰:‘天之废商久矣,君将兴之。’斯宋襄公所以败于泓也。”句后注云:楚伐宋,宋公将战。子鱼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公将兴之?不同”。公不从,与楚战,大败于泓。
卷二“王允授计诛董卓”所引之《论》中两条:1.“然犹折意缙绅”后注云:折,屈也,谓忍性屈情,擢用郑泰、蔡邕、何颙、荀爽等。2.“残寇”后注云:残寇,谓傕、汜等。(《论》中另有不见于《详节》的音注三条)
卷二之七“李傕郭汜寇长安”写王允被杀所引之《赞》两条:1.“子师国难,晦心倾节”句后注云:屈意于卓。2.“时有隆夷, 事亦工拙”句后注云:诛卓后被杀焉。(另有不见于《详节》的音注一条)
卷五“青梅煮酒论英雄”写公孙瓒之死所引之《论》中一条:“若虞、瓒无间,同情共力,纠人完聚蓄”后注云:贡父曰:“按文‘人’下少一字不成文,理当有一‘众’字。”
卷八之九“献荆州粲说刘琮”写孔融之死所引之《论》中五条:1.“是以孔父正色, 不容杀虐之谋”后注云:《公羊传》曰:孔父正色立朝,则人不敢过。而致难于君者,可谓义形于色也。2.“平仲立朝,有纡盗齐之望。”后注云:纡,音舒,解也。盗齐,谓田常也。一旦齐杀君,而盗其国。3.“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人存”后注云:“移鼎”,谓迁汉之鼎。“人存”,谓曹操在,不待篡位也。4.“代终之规,启机于身后也”后注云:“代终”,谓代汉祚之终也。“身后”,谓曹丕受禅也。5.“岂其负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后注云:园,即刓字,五丸反,谓刓团无菱角也。每,贪也。
卷八之九“献荆州粲说刘琮”写董卓之死所引之《评》中两条:1.“董卓狠戾残忍,暴虐不仁,自书契以来,殆未之有者也。 ”后注云:《英雄记》:大人见临洮铜人,铸临洮生卓,而铜人毁。世有卓而大乱作,而卓身灭,抑有以也。2.“袁术以奢淫放肆,荣不终己,自取之也。”后注云:臣松之以桀、纣无道,秦、莽纵虐,多历年所。董卓自窃威权,至于陨毙,未盈三周,残恶之性实豺狼之不若。袁术无豪芒之功,纤芥之善,而得狂妄自尊立,固义夫之振腕,人鬼之共疾,但云色淫不终,未见大恶。
卷十三“曹操兴兵下江南”写荀爽之死所引之《论》、《赞》中六条:1.“荀君乃越河、冀,间关以从曹氏”后注云:间关,由展也。 2.“夫以卫赐之贤,一说而毙两国”后注云:两国,谓齐与吴也。 赐至吴,请夫差伐齐。之晋,说以兵待吴伐齐之弊。吴既胜齐,与吴争强,晋果败吴也。3.“功高势强,则神器自移矣”后注云:谓魏太祖功业大而神器自归矣。4.“权诡时逼”后注云:谓辞对卓。5.“音情顿挫”后注云:尤抑扬也。6.“直辔安归”后注云:直道也。(内中另有不见于《详节》的音注两条)
《后汉书》和《三国志》中《论》、《赞》、《评》的注释数量极大,《详节》只摘选了极少的一部分,而上举出现在嘉靖本《论》、《赞》、《评》中的全部小字注刚好是《详节》筛选出来的那部分小字注,这雄辩地说明了嘉靖本《论》、《赞》、《评》的小字注是《详节》本身附带的,后人增插《详节》的《论》、《赞》、《评》时把小字注也一并插入。除了《详节》本身的二十来条注释,增插者还另加了六条不见于《详节》的音注,这六条音注与《详节》本身的音注截然不同,《详节》的音注有注音和释义两部分,采用直音法或反切法两种方法注音;但这六条音注只用直音法注音,而且不加释义,如同上文已经分析的那样,系传抄者或刊行者所为。
至于“已上见详节”这条小字注本身,则可能是加入《详节》内容的传抄者所为,也可能是后来的传抄者或是嘉靖本的刊行者所为,然其绝非出自《演义》作者罗氏之手却是一定的。类似“已上见详节”这样点明材料出处的注文还有两条:卷三之一“刘玄德北海解围”写糜竺一段轶事后注云:事出《搜神记》;卷十九之一“孔明秋夜祭泸水”写孔明以“馒头”代人头祭泸水,有注云:“传至今日。出《事物纪原》。”此等画蛇添足注语同“已上见详节”一样,也不可能出自小说作者罗贯中之手。《三国志通俗演义》取材广泛,罗贯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一一点明其选用素材的出处,比如他选用加工《搜神记》的有关记载,除了糜竺的故事,还有于吉、左慈和管辂等三人的故事,为何在这三人的故事后不加注呢?
嘉靖本还有以下五条小字注是引自王幼学(1254~1346)所著《资治通鉴纲目集览》:
卷一之二《刘玄德斩寇立功》“操年幼时,好飞鹰走犬,喜歌舞吹弹。少机警,有权数”后注云:机警,谓有机关而警醒。权数,谓权谋术数。引自《集览》中平元年(注:参见《四库全书》本《御批资治通鉴纲目》12下。)。
卷二之八《李傕郭汜寇长安》“掖门”后注云:韦昭曰:“宫中小门,在正门之傍者,谓左右掖门。”;“宣平门”下注云:《三辅黄图》云:“长安都城十二门,东出北头第一门曰宣平,民间所谓东都也。”引自《集览》初平三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12下】
卷二之九《李傕郭汜杀樊稠》“节钺”下小注,引自《集览》初平三年和嘉平六年两处。【《御批资治通鉴纲目》12下】
卷二之十《曹操兴兵报父仇》“琅琊”下注云:“琅琊,今益都路沂州,本汉琅琊国。《括地志》云:今兖州、沂州、密州,皆故琅琊地也。”引自《集览》初平四年。【《御批资治通鉴纲目》12下】
卷四之八《白门曹操斩吕布》“操颔之”后注云:颔,音含,首肯也。操点头而允之。大体引自《集览》建安三年“《索隐》曰‘颔之,谓首肯也’。”【《御批资治通鉴纲目》13】
罗贯中有可能参考《集览》并引用其中的注释,但是上引五条小注只见于嘉靖本而不见于闽刊本,说明了它们不是罗氏所引,因为闽刊本保留了嘉靖本别的许多小字注,不可能仅仅删掉引自《集览》的这几条注释,所以这五条注释应该是嘉靖本的刊刻者所加。
综上,嘉靖本中诗文及《论》、《赞》、《评》中的小字注是传抄者和刊行者增插《十七史详节》等史书时附带加入的,另有少数小字注则系他们采自《资治通鉴纲目集览》等史书,它们均不见于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原稿。
五、“旧本书作板”之“旧本”系指抄本
我们已然证明了占《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注绝大多数的音注、地名注、诗文及《论》、《赞》、《评》附带的注释不是小说作者所加,下文将举几条特殊的小字注进一步说明嘉靖本的小字注是传抄者和刊行者继续加上去的。
嘉靖本第十二卷第九则《张永年反难杨修》中写到,曹操得知张松读一遍《孟德新书》,即能背诵,并称该书为战国时无名氏所作后,曹操“遂令扯碎其书烧之。”其后有一条小字注:
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书”作“板”差矣。今《孙武子》只有魏武帝注。
此注显然不是小说作者所加。如果是作者最初写作时不慎用了“破板焚之”一类的话,他自己后来发觉不妥,修订时改为“扯碎其书烧之”,他犯不着加注予以说明,更不会将自己的原稿称为“旧本”,且批评为“差矣”。那么,有没有加注者批评的“旧本”存在呢?
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刊刻以前被辗转抄录的那些抄本中的一种,而且这种抄本的“扯碎其书烧之”被写作“破板焚之”之类的话。有人认为“旧本”系指早于嘉靖本的刻本,我以为在没有发现或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有早于嘉靖本的刻本之前,说“旧本”是抄本中的一种比较稳妥。嘉靖本出现上述小字注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传抄的过程中,有人发现了所据底本(“旧本”)“书”作“板”这一破绽,遂修改并作注说明之,嘉靖本刊刻时予以采纳;二是嘉靖本的刊行者在刊刻时改正并加注。不管是传抄还是刊行者,他们依据的底本都是抄本,嘉靖本这条小字注中所说的“旧本”应该是他们依据的这种抄本。
我认为第一种可能性较大,即是传抄过程中有人加注。关于这一点,与嘉靖本接近的夏振宇本透露了某种迹象,该本在“遂令扯碎其书烧之”后有小字注云:“《孟德新书》不可考,今《孙子兵法》有魏武帝注,疑即此书。至柴世宗时方刊板,旧本《三国志》……”这条小字注没有写完,但它不仅彻底否定了“旧本书作板”是指“原来写作板”的说法,而且比嘉靖本在语义上更加清楚,显然夏振宇在作注时还参考了别的抄本,也就是他说的“旧本《三国志》”。
虽然嘉靖本和夏振宇本称为“旧本”的抄本没有流传下来,但是闽刊本为“旧本”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附带说明一点:闽刊本较嘉靖本晚出,但其依据的底本并不仅是嘉靖本,已经有学者指出闽刊本的内容不全出自嘉靖本,我也将另有专文论及,兹不赘述。起码闽刊本将“书”作“板”是符合“旧本”的条件的。案闽刊本系列的郑少垣联辉堂本、刘龙田乔山堂本、余象斗双峰堂本、藜光楼刘荣吾本、汤宾尹校正本等版本均作“扯碎其书烧之”为“破板焚之”(各本文字稍异),闽刊本沿袭“旧本”而来,保留了“旧本”以“书”作“板”的原貌。也许有人会问:晚出的闽刊本有可能见到嘉靖本的小字注,但是为什么没有改“板”为“书”呢?试想,如果闽刊本的校梓者见到了嘉靖本,他们何不原样搬用?之所以固执地采用“破板焚之”,是因为他们依据的底本是不同于嘉靖本的“旧本”罢了。退一步说,即使闽刊本的刊行者见到了嘉靖本这条注语,唯利是图的书坊主也不见得会自找麻烦去作改动的。
六、“九伐中原”与“九犯中原”
在嘉靖本卷二十二第四、第七、第十则,卷二十三第一、第四、第六、第八、第九、第十则的标题之后,分别有从“一犯中原”直到“九犯中原”的四字小字注。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回目总体的风格来看,“×犯中原”的小字注就很令人生疑,前面的“×气周瑜”、“×出祁山”、“×擒孟获”等都是直接以回目正文的形式出现,为何只有“×犯中原”作小字注呢?此其一;其二,在闽刊本的分则标题之后,也有这些小字注,不过有的闽刊本的“犯”字改作了“伐”字,李卓吾评本也作“×伐中原”,后来的毛评本卷首一再提及的“九伐中原”,其来源应是闽刊本或李评本。
不可小瞧这一字之改!改动中透露出来的“正统”观念的原则之争或许能帮助我们解释“×犯中原”小字注的出处。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学术界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它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非正统,嘉靖本全书的总体倾向也确实如此,小说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地书写蜀汉一方“兴复汉室”、“北定中原”的壮举。以“匡扶汉室”为己任的蜀汉一方征讨“篡逆”的曹魏集团,在《演义》的作者看来自然是正义之举,如果小说作者要加小字注,也应该加“×伐中原”,而不会加带贬义的“×犯中原”字样。嘉靖本的“×犯中原”的小字注只能是传抄过程中外人所加,或者是编订它的书商所为,他们脑子里存有以曹魏为正统的观念,所以视姜维的攻打中原为“进犯”和“侵犯”的非正义之战。
同样是闽刊本,不同的书坊主对待姜维进兵中原的态度也不一样,这种差异表现在相关的分则标题之下,加的小字注却不同,如乔山堂本、蔡光堂本、朱鼎臣辑本作“×犯中原”,而双峰堂本、联辉堂本、汤宾尹本作“×伐中原”。
毛评本承袭了朱熹的封建正统论,强化了南宋以来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读三国志法》开篇即云:“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接着又说:“是以前则书刘备起兵徐州讨曹操,后则书汉丞相诸葛亮出师伐魏,而大义昭然,揭于千古矣”。“讨”、“伐”二字可谓爱憎分明,《读三国志法》后来又多次提及“九伐中原”。比如:《三国》一书,有横云断岭、横桥锁溪之妙,文有宜于连者,有宜于断者。如五关斩将、三顾草庐、七擒孟获,此文之妙于连者也。如三气周瑜、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此文之妙于断者也。又如:《三国》一书,有隔年下种、先时伏着之妙。善奕者下一闲着于数十着之前,而其应在数十着之后。文章叙事之法犹是已。……姜维九伐中原在一百五回之后,而武侯之收姜维,早于初出祁山时伏下一笔。既然蜀汉就是“正统”,那么出兵中原在毛氏父子眼中完全是讨伐“僭国”者的正义之举。
可见,在谁是“正统”这样的原则问题上,所有的人都立场鲜明,《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者更是不会含糊的,罗贯中怎么会加“×犯中原”之类违背全书思想倾向的小字注呢?
与“九伐中原”或“九犯中原”小字注相联系,嘉靖本还有一条小字注颇为引人注目。卷二十写陈式(《三国志》作者陈寿之父)乃是诸葛亮的部下,四出祁山后,因违背军令,私入箕谷口,结果大败。他为了推脱己责,竟将责任推给魏延,不想被诸葛亮识破而被斩首。后有小字注云:“后陈式之子陈寿为晋平阳侯,编《三国志》,将魏延为证,绝言孔明入寇中原”,思之再三,终不明白这句话的确切含义,既然陈寿与以诸葛亮为代表的蜀汉一方有杀父之仇,那么如何解释“绝言孔明入寇中原”呢?“将魏延为证”一句更是文理不通,因此,有人猜测这段小字注中的“延”、“证”、“绝”三字是“廷”、“正”、“统”三字的形讹,整段话应该是“后陈式之子陈寿为晋平阳侯,编《三国志》,将魏廷为正统,言孔明入寇中原”。查闽刊本,果然有“以魏为正统”一类的话。比如汤宾尹本,在陈式被斩之后的小字注为:“后陈式之孙(案,闽刊本误,应为陈式之子)陈寿作《三国志》,故以魏为正统,以孔明入冠中原”,联辉堂本、郑世容本后有小字注云:“后陈式孙陈寿作《三国志》,将魏为正统,言孔明入寇中原。”而乔山堂本相关内容以正文出现:“后来陈式孙陈寿作《三国志》,将魏为正统,孔明入寇中原,此见史官亦有私也。”朱鼎臣辑本“此见史官亦有私也”一句作小字注,其余内容同乔山堂本,也以正文出现。嘉靖本和闽刊本都保留了上述内容,可见它们是《三国演义》的早期抄本中就有的,但是比较而言,嘉靖本所据的抄本却出现了形讹,而闽刊本的文字更符合情理,可能也更接近罗氏原稿。
七、嘉靖本小字注和其他明刊本小字注之异同
小字注并非嘉靖本独有,在其他明刊本中也保留了大量小字注。这些刊本中的小字注有与嘉靖本重复的,也有嘉靖本没有的。比如周曰校本和夏振宇刊本虽然正文基本与嘉靖本相同,但是其小字注比比皆是,数量远远多于嘉靖本,它们的注文之前,一般都标明【释义】、【音释】、【考证】、【补注】、【评论】等等字样,汤宾尹校正本《三国志传》在注文前也标明【参考】、【补遗】、【补正】、【发明】等字样,它们显然是书商在翻检重刻过程中所为。诚如周曰校本封面识语所说:辄购求古本,敦请名士,按鉴参考,再三雠校,俾句读有圈点,难字有注音,地理有释义,典故有考证。它的书名作《新刊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所谓“校正”、“音释”就是通过小字注的形式来完成的。大多数闽刊本的书名中都有“增补”、“校正”、“音释”、“补遗”、“按鉴”、“评林”等字样,这一方面是为了故意显其与众不同,借以招徕读者;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出版界风行评释校补通俗小说《三国演义》。
也许正因为其他明刊本的小字注太过庞杂,反而遭到研究者的轻视,但是细加分析不难发现,这些明刊本小字注与嘉靖本小字注的异同却是解决《三国演义》小字注问题的一把钥匙,对此有必要再作进一步的申说。
就笔者手头掌握的几种闽刊本而言,嘉靖本小字注的内容在闽刊本中多数以正文出现,小字注极少。比如,乔山堂本只有两条小字注:一、卷十八“姜维大战牛头山”回目后注云:“一犯中原”;二、卷十九“姜维长城战邓艾”回目后注云:“五犯中原”;双峰堂本完整保留了九条“×伐中原”的小字注,除此以外只有下面一条小字注与嘉靖本一样:卷二十《凿山岭邓艾袭川》一则中,写邓艾率军过了摩天岭,忽见道旁有一石碣,上刻“诸葛武侯亲题”。其文云:二火初兴,有人越此。二士争衡,不久自死。四句话后分别有小字注:“二火初兴”,乃蜀改炎兴也;“有人越此”,已知艾过;“二士争衡”,乃钟、邓也;艾字士载,会字仕孝(“士季”之误),不久自死,皆应此言也。
嘉靖本中的音注、地名注以及诗文、《论》、《赞》、《评》附带的小字注在闽刊本中都见不到。而嘉靖本其他内容的一些小字注在闽刊本中以正文形式出现。比如嘉靖本卷二之七有一段文字:“卓裹甲不入(后有小字注云:裹甲者,披甲于内,而加衣于甲上。原来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铠甲两副。)伤臂堕车,卓大呼曰:吕布何在?”其中,除“原来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铠甲两副”一句外,悉引自《资治通鉴》卷60。可是,乔山堂本、郑世容本等闽刊本省略了“裹甲者,披甲于内,而加衣于甲上”,而把“原来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铠甲两副”改为正文。很可能“原来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铠甲两副”是罗贯中原稿就有的正文,所以以乔山堂本为代表的闽刊本保留了原貌,而嘉靖本的编订者在补充《资治通鉴》的“裹甲者,披甲于内,而加衣于甲上”一句时,顺便把正文“原来董卓恐人暗算,常披掩心铠甲两副”也降为了小字注。
闽刊本中只有藜光堂本仍以小字注的形式保留了多数嘉靖本的小字注,嘉靖本的小字注在别的闽刊本中大多以正文的形式出现,这一方面是因为闽刊本的刊行者避免刻写双行小字注所致,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嘉靖本小字注的内容在闽刊本的底本中本来就是正文。
与嘉靖本同属一个版本系统的周曰校本、夏振宇刊本的小字注也与嘉靖本有很大的不同。上文已指出: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小字注的数量几倍于嘉靖本,而且夹注之处有【补注】、【释义】、【参考】等等醒目的字样,它们的刊行者倒比嘉靖本的刊行者来得爽快,敢作敢当,不像嘉靖本的编订者加了注又不言明,颇费后人的猜测和探考。
八、几点结论
通过上文的分析,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1.罗贯中创作的小说《三国演义》以抄本的形式流传了很长时间,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和其他明刊本《三国志传》所据底本是不同的抄本,当然《志传》系统的本子可能受到了嘉靖本的影响。
2.嘉靖本的小字注是传抄过程中或刊刻时由不同的人增插进去,或是将罗氏正文降为注文,绝大多数不是罗贯中的手笔,因此以嘉靖本的小字注去考察《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是靠不住的。但是少数小字注的作者是元末明初人,又大致可以说明《演义》成书的年代。
3.嘉靖本和其他明刊本小字注的存在,为我们考察《三国演义》版本的早期流传与演变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尤其是闽刊本小字注和嘉靖本小字注的差异,从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闽刊本所据底本比嘉靖本更接近罗贯中小说的原稿。
标签:三国志论文; 罗贯中论文; 三国论文; 三国演义论文; 演义论文; 嘉靖论文; 夏侯玄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明朝论文; 地理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