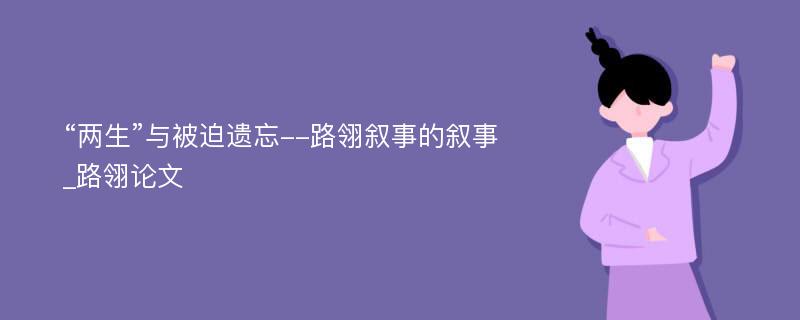
“一生两世”与强制遗忘——关于“路翎叙述”的叙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一生两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路翎(1923.1—1994.2)的生平事迹和文学活动情况,虽然迄今为止仍有诸多疑点尚待澄清,也并无任何一种详备的年谱或传记资料可资放心引据[①a],但总的说来,不论在普通知识界抑或专门研究领域,人们对他似乎都并不陌生,相反,此前经由各种渠道传播开去的关于他的知识和信息是那样的多而一致,以至人们早已形成了某种定见,一提起这个名字,差不多总会在自己脑海里迅速组织起一套大同小异的“路翎叙述”。此种“叙述”的经典表述形式,来自路翎生前的文学伙伴和“反革命”难友之一的冀汸先生,道是:
1955年那场“非人化的灾难”,将你一个人变成了一生两世:第一个路翎虽然只活了三十二岁(1923—1955),却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是一位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第二个路翎尽管活了三十九岁(1955—1994),但艺术生命已销磨殆尽,几近于零,是一位衰弱苍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患者。[②a]
路翎早慧,根据他自己的回忆,他的创作活动始于1937年,处女作是一篇题为《在古城上》的散文[③a],但研究者一般都根据现存资料将1938年发表在《弹花》杂志上的另一篇散文《一片血痕与泪迹》视为其创作起点[①b];他正式踏上文学道路的标志,是1939年因投稿结识胡风[②b]。如所周知,正是因为与胡风之间切磋砥砺、互为助益的长期深厚友谊,才使得他出众的创作潜能得以有效调动、规范和激发,迅速成长为四十年代国统区以迄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声誉卓著的“天才”作家,也才使得他不可避免地与胡风等人一同沦为“共和国第一大文祸”的主要受害者。1955年5月“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发之前,路翎实际上早已被迫搁笔,他在自己前半生的文学活动中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是写于1954年11月的长篇创作申诉《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冀汸先生的“第一个路翎……有十五年的艺术生命”之说,推算起来大约是以路翎1940年5月首次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上露面为起点的[③b]。此说尽管与其实际创作历程略有出入,但泛泛说来亦无大碍。因为前期路翎的重要作品的确都是在此一期间创作的。所以,冀汸先生对“第一个路翎”的界说应许基本准确。由于入狱和出狱之后的路翎的确发生了十分显著的变化,“一生两世”的区分,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相信不会有人对此持有异议。那么,在以冀汸先生此说为经典表述形式、几成定论的“路翎叙述”中,值得推考的就只剩下一个细节了,即,“第二个路翎”的“艺术生命”是否确实已经“销磨殆尽,几近于零”?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确乎是要令人感觉到“真正的恐怖”的。[④b]
路翎于1955年5月16日即《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一批材料》公布后的第三天被隔离审查[⑤b],几天后被移至另一处关押时曾有人见过他一面:“目光匆匆相遇,我忽地发现几天不见的路翎竟垂下了一绺白发。这一绺白发几十年来都使我惊怖而战栗!”[⑥b]足见路翎因此一变故而遭受的心理创伤之深巨。入狱后的路翎被单独关押着,与他咫尺天涯的同案难友们除隔墙听音外,不可能对他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常常听到路翎在房间里困兽一般发出几声叫声,或者无可奈何的叹息声”[⑦b];在他们中,绿原开始攻读德语和法语,徐放练习翻旧体诗,谢韬、严望也已经定下神来,做好长期打算,“唯有住在隔壁的路翎最不安宁,经常大声吼叫,立即被制止,鸦雀无声。不久复又大声吼叫,骂人,他已精神分裂。”[⑧b]
“精神分裂”!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这是一个过于触目惊心、令人谈虎色变的词汇。但是且慢,还是让我们先看一看吧。
由于路翎本人出狱后一直对自己的狱中生涯持克制慎言态度,在不能不有所交代的情况下,往往也只是大略说明动向,比如被从某处移至某处,“因与看管者冲突、吵架”而“被捆绑起来关入角屋”[⑨b]。措辞客观冷淡,基本不带感情色彩,也不涉及当时情绪、心理、想法之类,这就终不免使其此一阶段的真实生命状态形貌模糊,难窥其详。好在,经研究者多方努力,路翎狱中经历的大致线索是清楚的,即,他曾于1961年被从监狱移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至1964年1月被“保外就医”释放回家;在家中曾多次上书中央自我申诉(总共写了三十多封信),1965年11月事发后复被收监,并随即转往精神病院继续治疗;1966年10月被遣回监狱,直至1973年,才被正式宣判犯有“集团”案和“攻击党中央”的双重“反革命罪”,处有期徒刑二十年(从1955年起算);此后,他在一间监狱工厂和一间农场各劳改过一段时间,1975年6月19日刑满释放。在漫长的牢狱生涯中,路翎自己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有着明确的作为动机和足够的自省能力吗?他自己是怎样看待这一阶段的生活的?
针对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本身即是一种“疯狂”举动。但我们还是不要忙于下结论吧。——尽管在笔者见及的资料中,绝大多数作者都十分肯定地将路翎在狱中所患的精神疾患称之为“精神分裂”,但这似乎并非路翎自己乐意接受的一个说法,相反,在经他校订过的张以英所编的《路翎年谱简编》中,对此给出的说法是“精神受挫”,此一说法后来亦为慎重的研究者所沿用[①c]。但“精神受挫”含混其辞,看起来像是一种刻意的文饰,此地无银三百两,越发令人狐疑。事实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看来惟有去路翎当年曾经就诊的医院查阅档案,才可望揭开谜底了。在谜底揭开之前,我们所能做的依然只是文字追索而已。以我所见,惟有一人曾将路翎的病指实为“心因性精神病”[②c]。倘此说可靠,则路翎与胡风在狱中所患的是同一种病。胡风病状多见载记,主要是“幻视幻听”,路翎的病状是否即是众所周知的间歇性“长嚎”、吵闹之类,不得而知。
在这一问题上细加纠缠是没有意思的,而我所以还要说一说,是因为它或多或少可以为十分难得的路翎的狱中生活自述提供一点阅读参照。下面一段引文,取自路翎晚年的未刊文稿《喷水与喷烟》,其中加括号的部分,是原稿中拟于删除的:
我作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一九五五年夏季起被囚,于“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因个人猛烈反抗案被移动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监狱,与前一度的监狱在同一乡间;这中间曾因病住院及被保释回家医病。我在这监狱中维持着我度岁月的方法:每日回忆往事,其余的时间便对将我判为反革命的,伤害、侮辱我的人们和形势进行抗议,我的抗议活动有说道理,叫骂,包括大声唱歌。监狱荒凉,(有时押下楼劳动,在院子里拔草,觉得隔绝了人间,——监狱墙外是荒凉的旷野,不知亲人与友人在何处。)荒凉的痛楚的感觉中也想到,中国似乎在沉静地进展,于是更愤慨地呐喊与高声唱歌。(我想到,我也是爱国的人,却被认为反革命囚在这里。对于田野和远处的城镇、城市的人间的想象使我更愤慨地抗议、呐喊与高声唱歌。)这使我几次被从原来囚室押出去,关押到走廊角落里的小的窄的幽暗的囚室里去。
——路翎在说些什么?难道他那些几乎被所有人毫不犹豫地视为“精神分裂”征象的狱中异动,竟然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自觉“反抗”行为?难道他的疯狂只是“佯狂”?难道他在借“佯狂”舒泄内心的“痛楚”和“愤慨”时,还曾非常仔细地注意着将自己的“猛烈反抗”行为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以不造成对他人和“国家财产”的破坏为目的?
这些疑问都可以留待另文去做结论,此处需要肯定下来的其实只有一点,即:上引路翎的狱中生活自述是否可以算作一种有效表达?我想,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吧。倘是,那就意味着,就算路翎的的确确是一个“疯子”,恐怕也与普通的疯子有些不同,在于他即使疯狂了,也仍然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赋予一种“疯狂的逻辑”,并且努力依此过活,将它贯彻到自己的劫后余生之中去。强调一遍:在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疯子”固然无需认真对待,可以轻而易举、轻描淡写、毫不犹疑地被打发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另册”之中去,不予理睬,(天哪,我在崇洋媚外!这些难道不是米歇尔·福柯一直在说的事情吗?)但是,“逻辑”就不同了,那是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加以尊重的东西。
一生两世。路翎在狱中“走”过了他的“人生的中途”,重回人间两世为人时,已经年过半百(五十二岁),步入晚景了。当他“穿着监牢犯的衣裤”,回到“离别二十年的北京,离别二十年的家”时,除了仍旧背负着“双重反革命”的社会身份,必须为自己的“公民权”奋斗之外,还面临着一个家已不家,首先“必须谋生”的局面[①d]。他在当时栖居的北京芳草地街道做了四年半扫地工,才等到1979年11月的个人“反革命罪”案平反,恢复公民身份。他的另一项“反革命罪”是在一年之后的1980年11月才初步平反的。据他自己说,“平反后我最初见到的友人是曾卓与绿原”[②d]。曾卓先生于1982年追述见面情形时写道:
我两年多前见到他时,他已是那样苍老了,虽然还只五十六岁。在他身上,已很难想象当年英俊的身影。更使我感叹的是他的精神状态,显得冷漠,迟钝,健忘。他抽着烟,眼神漠漠地望着窗外,谈到过去的遭遇和谈到一些老朋友时,他都用的是平淡的语气,而且话语是极其简短的。他还能够写作么?坐在他面前,我不禁这样悲痛地怀疑。[③d]
十年后,曾卓先生对此次见面(1979年9月)作过更详尽的记述,其中可与上引文互为参证的,是以下一段话:
路翎见到我丝毫没有激动,一如我们昨天才分手。问到他的情况,他三言两语就带过去了,只是向我打听胡风和别的几个朋友的消息,我告诉他胡风已出狱,现住在成都,并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朋友的情况告诉了他,说现在政治形势已好转,问题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的。他也并没有表示出欣喜。他说话很有条理,看不出任何精神病兆。但他有时沉默不语,两眼茫然地凝望空间,无意识地移动着下颚的样子,却使我心酸直至心悸。[④d]
但是在此之前,其实已经另有朋友见过他。牛汉先生所记述的他在1978年初冬见到的路翎,是这样一幅形象:
……我透过窗玻璃朝里仔细望望,屋里地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门,一动不动,背有点驼……我喊了几声“路翎,路翎……”,我的嗓门很大,可是那黑憧憧的站立的人,并不应声转过身来……我几乎哭喊地叫起来,“路翎,你怎么不答应我?”同时伸手臂环抱他的肩头。想不到路翎异常平静而清醒地对我说,“你不是牛汉吗?我从第一声就听出是你的声音。”“哦,我的好朋友,你还没有忘记我的声音。那你为什么不答应呢?”他说,“余明英教我买两毛钱的肉,我把它忘了。”回答的莫名其妙。他刚才呆呆地立在那里,原来是想着忘了买两毛钱的肉的事。我的心酸痛起来。[①e]
看来,为“两世为人”的路翎与他的普遍有着“起死人而肉白骨”(绿原用语)的强烈再生之感的故人和难友们劫后重逢时,他不仅曾以其外观形象上的巨大变化使他们惊为异人,而且,在他与他们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情感和精神状态上的巨大反差。“他还能够写作么?”当他们悲痛地发出这样的疑问时,一个潜在的结论向度事实上就已经开始生成,单写路翎以他的实际行动来予以应答、调校、扭转或催生了。
当我们今天来就晚年路翎的写作能力、活动成就和“艺术生命”作结论时,我们必须面对的前提条件是:从1981年3月重新执笔为文到谢世,晚年路翎写下了总字数不低于五百五十万的诗歌、散文、小说和回忆录[②e]。尽管迄今为止,其中占总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长篇小说仍然未能公开发表,亦即不能为我们所置身的当代文化环境中的文学体制的“正常”动作所吸纳和接收,但我想,在对此一巨大的文本和精神存在作出全面检视之前,任何先期结论恐怕都是要暂且存疑的。
回头来看前引冀汸先生的结论,他的结论依据便不能不首先受到质疑。他据以对晚年路翎的“艺术生命”作出“几近于零”的悲观估价的事实依据究竟何在呢?从其长篇(两万余字)路翎追述中可察,那仅仅是他们劫后四次重逢所得的外观感性印象,他零星接触到的路翎晚年已刊作品和他亲手处理过的两篇“最后还是没被采用”的中篇小说手稿;而且,在谈到他对晚年路翎未刊文稿的“失望”时,他也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艺术分析,而只是感叹说:“你的艺术创造力可惊地萎缩了,你的审美力也同样可惊地衰退了,我更痛惜的是你的思绪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方寸之地的稿纸上随意东窜西突,留下来的只是一片混乱的蹄痕。”
很遗憾,在冀汸先生的表述中,我见到的只是过多的自我情感倾注,过少的“异在”事实揭显。他显然是在以己度人、以关于“第一个路翎”的记忆衡量和要求“第二个路翎”,他简单而不情愿地接受了路翎已经发生变化的事实,同样简单而不情愿(不甘心)地将导致变化的原因归结为“非人化的灾难”之下的“精神分裂”,以至事实上拒绝了对晚年路翎所拥有的自己的情感和精神逻辑的深入了解和思考,失却了对他依据此一逻辑创造出的一种首先属于他自己,其次也深深牵系着某种群体状况的文本和精神事实的充分尊重和把握。以我陋见,“衰弱苍老神情恍惚的精神分裂患者”的概括即使是一种经得起推敲的事实陈述,所陈述的也不过是一种外在形象,与“艺术生命”的内在存活并没有铁定不移的联系;而且,将此一说法与“挺拔英俊才华超群的作家”对举,适足以说明“第一个路翎”在冀汸先生的情感记忆里所据有的位置太过雄大和显要,以至“第二个路翎”无论出以何种形象,只要不足以与之相匹配,都可能会遭到前者的本能抵拒。
我因此明白,以冀汸先生的“一生两世”说为经典表述形式的“路翎叙述”之所以会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早期路翎的文学表现过于卓特,使得大多数人都自觉不自觉地在向晚年路翎要求着同一样式的卓特表现,倘若他做不到,或者变化太大,便难免要令人失望,乃至打入另册(“疯子”),“强制遗忘”。
至少迄于目前,关于晚年路翎的人生和文学形象认证的诸多“正面”信息是被我们所处的当代社会文化环境“强制遗忘”了。
比如,关于晚年路翎的人生形象,前引曾卓先生的“他说话很有条理,看不出任何精神病兆”的记述便几乎从来不曾为人注意过,人们津津乐道的,总是他的诸种“病态”表现。
谈到晚年路翎的文学表现,人们不惮词费地加以强调的总是他以多么大的“毅力”写出了多么大量的“不能发表”的“残品或者废品”,偶或提及那些发表出来的作品,也差不多总要名之曰“小诗”、“短文”,在措辞周到地评价说“令人欣慰”之后,再更为周到地找补一句:四十年代的那个路翎是已经永远逝去了……
诗就是诗,文就是文,我搞不懂它们为什么非要被压榨得又短又小地来谈论;从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许多人红脸唱完唱白脸,翻来倒去不知变幻了多少副嘴脸,大家似乎并不觉得多么奇怪,这就更加令我搞不懂,一个遭遇那么悲惨的路翎,付出了那么巨大的努力,想做的不过是重塑一回自己的文学形象,为什么就那么难以被接受,以至总要被与他的注定追不回来的过去绑在一起被谈论,而始终得不到就事论事的认真对待?
晚年路翎的文学表现真的就那么糟糕吗?
早在路翎刚刚“重返文坛”,在《诗刊》1981年10月号和《青海湖》1982年1月号上相继发表了《果树林中》、《刚考取小学一年级的女学生》等五首晚年诗作之后,曾卓先生即怀着欣喜的心情对路翎写作能力的“恢复”作出了热情洋溢的肯定:“这里没有任何伤感,他歌唱的是今天的生活。这里没有矫揉造作,他朴实地歌唱着在生活中的感受。这里没有感情上的浮夸,他的歌声是真挚、诚恳的……”曾卓先生说:“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诗,这是需要热爱生活的心灵。能够将平凡的生活提升到诗的境界,这是需要敏锐的感受力和高度的表现力。”又说:“这是真正令人惊奇和欣喜的。”还说:“我喜欢这几首诗,而且通过这几首诗所说明的和预示的东西也使我喜悦。”[①f]
我们看到,曾卓先生同时也在表达他的个人情感,但与别人有所不同的是,他是将他的个人情感和审美判断建立在对作品的具体而细致的分析了解基础之上的:“这里展开了平凡的生活场景……”“语言是清新的,而又有着一种朴素的美。跳跃性比较大……但融合着生活的脉流的是作者情绪的脉流;情绪的节奏融合在生活的节奏中间……”
其实,就在曾卓先生撰文勾勒晚年路翎的第一幅文学形象的同一时期,路翎还在《光明日报》、香港《新晚报》、兰州《雪莲》上发表了另外五首诗,而且其中刊载在《雪莲》1982年1月号上的《黎明》一首,今天看来当与《刚考取小学一年级的女学生》并居为路翎晚年创作初始阶段的“杰作”,只可惜曾卓先生当时没能读到;阴差阳错,倒是刊载在《新晚报》上的两首并不优秀的诗作《阳光灿烂》、《鹏程万里》立即在香港引来好评:“前者歌颂中国现时代的灿烂……,后者则纵情唱出‘青年一代成长,壮年一代稳重,年老一代威严’的歌声,并且试图勾画出一幅‘鹏程万里,雄鹰飞翔’的壮丽景象”。论者称:“对于一位脑病患者来说,堪称难能可贵。”[②f]经过这样的出口加工转内销,附加在这两首诗上的对于“脑病患者”的作品的“鼓励性好评”从此大畅其道,渐渐变演成事实上不利于路翎的对其晚年文学形象加以评估的一个基本模式。
此后,晚年路翎的文学努力虽然并非不受关注和肯定,如冀汸先生在上引长文中所记述的,《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上发表了他的小说新作《钢琴学生》后,“读者高兴,朋友们更高兴。汪曾祺同志就在《人民日报》副刊上撰文表达了他的喜悦心情”[①g];对于他在《诗刊》上发表的诗,“唐HT5,7〗读后就说过:‘这才像现代派的诗……’”如此等等。但总的说来,反响既不热烈,评价也并不高,大多数人的持论倾向近于冀汸先生:“总体说来,都只是火星一闪,并没燃烧起来……”甚或更为悲观[②g]。直到1996年9月,我们才终于见到了李辉先生针对路翎晚年诗作和散文所作出的一种近于曾卓先生的充分肯定性的评价:
……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种诗意。痛苦日子的生活,在晚年路翎那里,竟然酿出如此宁静与清新的诗句。这是真正的诗。……它们表明,他内心中仍然以一种特殊方式潜藏着艺术激情和才华。……在沉默的时刻,在给人一种近乎于呆滞印象的时刻其实他的灵魂正在飞翔。[③g]
行了,我耗费在别人对晚年路翎的人生和文学形象认证上的精力和笔墨已经够多,回头看看,却还有若干尖锐的问题不曾触及。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暂且打住吧。但在结束本文之前,我还想做一件事,即请求本文的读者现在尽可能将此前已经获得的关于晚年路翎的诸种“干扰信息”统统抛开,以便以自己的洁净之躯和明净的眼睛感受和注视晚年路翎灵魂深处巨大的诗性存在——以下是完整抄引的一首路翎晚年诗作,请您自己来作一个判断吧:
《红果树》
干枯的红果树在昼与夜静默着/别的树都长了树叶了/羞惭的红果树/用它的魂魄在挣扎着/风吹过/用关切的声音喊着:杭唷/泥土屏息着/也在喊着号子:杭唷
杨树和枣树/长了很茂盛的树叶了/那些树叶似乎是被春风带来/落在树干上的/仿佛是魔法似地/从膨胀的风和膨胀的泥土/膨胀的树浆……/这些树也觉得一种羞惭/红果树沉默着
太阳照耀得很欢快/发出金色的箭簇/夜晚有有力的风/红果树听见自己枝干内/有顽强的声音又中断了/它发出痛楚的叹息/周围的树木替它/喊着鼓舞的号子:/杭唷/房屋内睡着的儿童/也似乎在替它喊着号子/而诚实的泥土用很大的/元气充沛的声音喊着/而在夜间发芽的小草也喊着/而在夜间月光下开放的花也喊着/而在夜间幸运地孕育着果实的桃树也喊着/而在夜间未睡着的蜜蜂也喊着/而远处的江流也喊着/而在城市边缘鼓动着的/旋转着的车轮也喊着
红果树被一些亲爱之情围绕/泥土在它的根须下嗞嗞发响/它的树干内又起颤动了/它用它的魂魄奋斗着/它的树叶的脉胳在树浆里形成了/它的树叶的绿色/又得到泥土的补充了/它的新的树浆灌满树干了/它的花的形态在激动里形成/而果实还连着果核的形态/连着对下一代的预想/含着爱情痉挛着形成/泥土高喊着:杭唷/红果树在一夜之间长出树叶/树木群中/林荫路上/楼房旁侧/不缺红果树
这棵“被一些亲爱之情围绕”、“用它的魂魄奋斗着”的“红果树”是否感动了你?需要说明的是,这首写于1986年4月23日的路翎晚年杰作并非未刊秘笈,而曾公开发表过;刊载它的杂志也并不冷僻,是重庆出版的大型文学双月刊《红岩》,1986年第6期。
同等优秀的路翎晚年诗作当然并非仅此一首。我可以负责地说,晚年路翎首先是一位诗人。今后各种辞书和文学史论著在谈到路翎时,看来是有必要在他早经获得的小说家、剧作家、文论家[①h]等头衔之外,再为他添置一项诗人头衔的。
1997.3.9—15复旦
注释:
①a 迄1997年3月,笔者见及的路翎年谱和传记资料计有如下数种:
沈永宝,乔长森:《路翎传略及其创作》、《路翎生平及其创作的若干考订》、《路翎作品系年目录》,均载南京《文教资料简报》1985、4;
张以英:《路翎的生平、小说和书信》、《路翎年谱简编》,均见《路翎书信集》,漓江出版社,1989;
杨义:《路翎传略》,见《路翎研究资料》,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
未具名:《路翎著作年表》、《路翎著作目录》,同上;
朱珩青:《路翎年谱简编》,见《中国现代作家选集·路翎》,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4;
朱珩青:《路翎早期的文学活动》,《新文学史料》1995、1。
以上数种就可靠程度而言各有长处,但详备程度均未如人意,总的来说侧重于前期路翎(1955年之前)资料梳理,后期路翎(1955年之后)资料基本付阙,可以参考的成果仅有张以英和朱珩青各自的《年谱简编》,但都十分简略,且多错讹。
②a 冀汸:《哀路翎》,《新文学史料》1995、1。
③a 《关于自己生平和创作的一些说明——路翎致本刊编者信(摘要)》:“我是1937年开始写作,投稿赵清阁主编的《弹花》,题为《在古城上》散文一篇……”,《文教资料简报》1985、4,45页,但此文迄未发现。
①b 《弹花》2卷2期,1938年12月6日出版。朱珩青《路翎年谱简编》将此文的写作年份系定于1937年,未具名之《路翎著作年表》亦将此文列于表首。
②b 现存最早的路翎致胡风书信写于1939年4月24日,见晓风编《胡风路翎文学书简》,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
③b 《“要塞”退出以后——一个年轻“经纪人”的遭遇》(短篇小说),《七月》五集三期。此文写于1939年。参见②,尤其是作为该书《代序》的路翎回忆录《我与胡风》。
④b 钱理群:《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说〈路翎——未完成的天才〉》,《读书》1996、8。
⑤b 余明英:《路翎与我》,未刊,已收入张业松、徐朗编:《像是要飞翔起来——路翎晚年作品集》,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即出)。以下引用文献凡属未刊稿,均见该书,不另说明。
⑥b 杜高:《一个受难者的灵魂——为〈路翎剧作选〉出版而作》、《路翎剧作选》,427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
⑦b 李辉:《胡风集团兔案始末》,308页,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
⑧b 涂光群:《严望——一个角色》,收入涂著《中国三代作家纪实》,313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
⑨b 张以英:《路翎年谱简编》,1955—1975部分。此年谱曾经路翎修订,但亦每有错讹。
①c 朱珩青所编《路翎年谱简编》中便沿用了这一说法,见前举书392页。
②c 邹霆:《路翎和他的家人》,原载1982年1月12日香港《新晚报》,收入《路翎研究资料》,13页。此文同时也曾将路翎的病称为“精神分裂症”。
①d 路翎:《错案二十年徒刑期满后,我当扫地工》,原载《香港文学》1992、1,已收入《路翎晚年作品集》。以下所引路翎晚年已刊稿同此,只注原刊出处。
②d 路翎:《一起共患难的友人和导师——我与胡风》(即前举《胡风路翎文学书简代序》),收入晓风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工人回忆》,50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
③d 曾卓:《读路翎的几首诗》,收入《曾卓文集》第三卷,14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4。
④d 曾卓:《重读路翎》,《曾卓文集》第二卷,497页。
①e 牛汉:《重逢第一篇:路翎》,收入牛著《萤火集》,86—87页,中国华侨出版社,1994。
②e 这一文体区分是按《路翎晚年作品集》的编排体例作出的。
①f 曾卓:《读路翎的几首诗》,《曾卓文集》第三卷,150页。
②f 邹霆:《路翎和他的家人》,见《路翎研究资料》,15—16页。
①g 汪曾祺先生此文笔者未见。但事实上,当初读到过《钢琴学生》的人恐怕并不多。如罗飞先生所指出的,这期刊物“因为一篇什么作品闯了祸,刊物被收回了,连他这篇……好不容易发表了的小说,也等于没有发表。”参见罗飞:《悼路翎》,收入邵燕,祥林贤治编《散文与人》第4集,18页,花城出版社,1994年。《人民文学》1987年1—2期合刊上“闯祸”的作品是马建的小说《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
②g 如罗飞:“路翎从写‘疯人’、‘半疯人’,到自己成为疯人、半疯人,到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作家的全部智慧和灵气。”同上引文,25页。在这篇文章中,罗飞先生还引用了一封路翎致他的短信,以印证晚年路翎思维混乱、文句不通,显例如“现问你问题,便之。”一句,读来与上下文毫无关系。但其实是有关系的。根据笔者对路翎晚年手迹的了解,猜想起来,在这个句子中罗飞先生可能至少认错了两个字:第一个“问”字应为“因”字,“题”应为“起”。但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因我未见原件,不敢遽断。错处也可能是路翎笔误所致。此事虽小,所关实巨,不可不察。引文出处同上,17页。
③g 李辉:《灵魂在飞翔——〈像是要飞翔起来——路翎晚年作品集〉序》。此文曾以《像是要飞翔起来》为题,先期删节发表于1996年9月18日上海《新民晚报》。
①h 路翎前半生曾写下为数不少的文论,介入当时的文学论战,晚年又写出了大量理论性的文学回忆录。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和贡献,迄未引起研究界充分注意。现经笔者与人合作搜集整理,已结集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路翎文论集》(鲁贞银、张业松编),交付珠海出版社出版。有关论说请见张业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文艺理论研究》199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