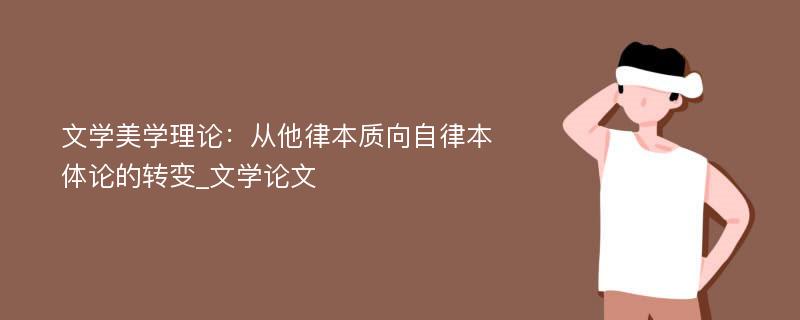
文学审美论:他律本质论向自律本体论的转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本质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的文学审美论,是在主体论文艺学力图摆脱哲学认识论的制约、争取文艺的主体性地位的整体努力中被催醒和发展的。审美文论的倡导者们以主体的“自由”学说作为学术立足点,去寻证认识论视域之外独立的“审美本体”的存在。尽管后来这种审美的自由超越由于逐渐迷失了文艺关怀人生、介入现实的维度,而终于陷入偏狭甚至虚妄,但它对文艺的特殊规律的探讨和对文艺内在特质的深入发掘,则是在本世纪以来中国文艺学发展历程中所鲜见的。
由文学认识论到审美反映论
——审美的自觉和发展
从审美的角度出发把握和评价文艺现象,80年代初开始成为许多学者的自觉追求。伴随着新时期文学中人的主体地位的恢复,以及文学创作的中心由客观外部生活向人的主观内心情感的转移,许多文艺理论家意识到:文艺自身本属于“情感的领域”、“美的领域”,只是长期以来,文艺理论与批评没有在意文艺的“情感性”,特别是没有重视、甚至蔑视文艺的审美性质;一些文艺评论著作和文章常常以政治判断和社会分析代替审美评价,因而“不能很切实地指导文学创作的文学欣赏”。80年代的文艺学研究与以往的显著不同在于:对文学的审美特性的强调,带来了文学研究主视角的变化。愈来愈多的文论家自觉地把审美当作把握文学自身性质和价值的基本范畴,把美学的方法当作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强调“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只就其精神掌握方式而言,是能动地反映世界的审美掌握”(注:胡经之:《文艺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看来,文艺学研究“只有以审美为核心,多元检视文艺的性质和特点,才能建立起真正科学的文艺学”;而文艺学的出路也就在于:以审美论为基础建立和发展“文艺的审美社会学”“文艺的审美实践论”“文艺的审美心理学”(注:杜书瀛:《文艺与审美及其他》,《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2期。); “审美”应当是制约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主视角”(注:童庆炳:《文学研究的主视角》,《批评家》1988年第2期。)。或许可以这样说:80年代文艺学研究中审美论的自觉,标志着文艺学研究的理论视角和价值取向由“他律论”向“自律论”的转变,标志着文学的特殊性质和审美价值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文论家关注的中心、驰骋思辨才能的天地。
在80年代的中国文论界,“审美文论”最初是以对传统的“文学反映论”和“文学意识形态论”体系的“修正”、“改良”和“更新”的形态出场的。也就是说,许多理论家开始并不想打破认识论的框架,而是在“文学反映论”和“文学意识形态论”的“文学—现实”“文学—意识形态”单向关系中加入一个双向互动的中介因素——“审美”,从而将审美与反映相统一、将审美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相融合,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新命题(注:这派理论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钱中文、童庆炳、王元骧。他们有关“审美反映”和“审美意识形态”问题的著作和文章写得很有功力,论述得扎实而充分。如钱中文的《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 童庆炳的《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王元骧的《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4期)以及他发表在《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上的一系列有关文章。)。可不要小看了“审美”这个中介因素的意义,正是由于“审美”的介入,突出强调文学是“审美反映”和“审美意识形态”,强调文学认识(反映)的特殊性,强调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特殊性,才使我们的文艺学研究在对文学特质的把握上跃进了一步、深入了一层。同时,“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作为对以往“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的纠偏,也发生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必须说明,以往的“反映论”和“意识形态论”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说即是“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但由于以往的“文学反映论”和“文学意识形态论”没有紧紧抓住文学区别于其他“认识活动”和其他“意识形态活动”的特质,将文学的特殊的反映混同于哲学的一般的反映,将文学的特殊的意识形态性混同于哲学的一般的意识形态性,这就给了“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在文艺学领域滋生和肆虐以可乘之机。“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强调:文学的特质在于审美,在于主体对客体即对外在世界的全身心投入的“实践—精神”(马克思语)的审美把握;文学是通过艺术家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的中介来反映生活的,因而文学是不同于科学认识活动的“审美反映”,是不同于哲学、道德、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审美意识形态”。因此,艺术家和生活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文学认识论和文学意识形态论所认定的那种直接的、“镜映”式的、单向的关系,艺术家不再是简单地去反映和复制生活,而是作为审美主体以整个心灵去拥抱生活;艺术家不再仅仅是单向地接受生活的信息,而是还要将自己的个性情感投射给审美对象,构成主客体双向的相互作用相互交融的审美关系。关于“审美反映”的总体特征,钱中文的下面一段话表述得充分而有代表性:“审美反映是一种感性活动,又是一种理性活动;是一种感性的具象活动,同时也渗透着理性的思考;是一种感情活动,感情的愉悦活动,也是显示着哲学、政治、道德观念形态的认识活动,意志活动,实践的功能性活动。这是一种上述各种活动的综合。当然,在以具象的、显形的感情形态为存在的语言形式的构架中,隐形的艺术思想,始终是它的血肉。可以这样说,审美反映既类似于对世界的一种精神把握,又是一种接近于对世界的实践把握,即马克思说的对世界的实践—精神的把握。总之,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决定了艺术反映中感情和思想的融合,感性和理性的相互渗透,认识和评价,感受形式和语言、形式统一的审美本质特征“(注: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
“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以上述这种文学的“审美本质特征”去纠正以往的“文学认识论”和“文学意识形态论”所常常表现出来的片面性,显示了这一时期审美论者鲜明的精神意向。更有论者特别突出以往认识论文艺学重视不够的情感因素,系统地论述了审美反映作为一种情感反映在对象、目的、内容、方式上的特征。如童庆炳在《文学概论》(注:童庆炳:《文学概论》,红旗出版社1984年版。)和其他一系列著作和文章中,就对文学的情感特征作了比较充分的论述,强调情感在文学的审美反映中的重要作用。王元骧也对文学的审美反映的情感特点作了具体分析:就反映对象而言,情感反映的是“主体性的事实”,是以主体自身的存在,以及对象与主体之间所建立的关系的发展、变化为转移的,也就是说情感反映的对象不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情感反映的内容而言,由于情感对感知所具有的选择和调节作用,及情感对审美感受的支配作用的存在,使得艺术的反映成为评价与创作的统一,反映与创造的融合;就方式而言,由于受到主体的价值观念、性格、气质、兴趣、爱好以及心境、情绪的影响和制约,情感反映是以崇敬、赞美、爱悦、同情、哀怜、忧愤、鄙薄等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的。情感来源于生活对艺术家的感动,同时又反过来支配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注:参见王元骧:《审美反映与艺术创造》,《文艺理论与批评》1989年第4期。)。因此,情感性成为艺术的生命之所系,艺术的审美特性之所系。
“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者不但突出强调审美反映的情感性,而且还特别强调审美反映过程中主体“心理意识”(“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的中介形态及其重要作用。他们认为,审美反映是一种“心理层面”的反映。现实生活是反映的源泉;但现实生活一旦进入审美反映,很快就会发生形态的变异,其变异序列是:现实生活——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注:参见钱中文:《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是最丰富的——审美反映的创造性本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4期。)。这样,在审美反映中, 客观的现实生活就不再像在以往的文学认识论中那样直接成为艺术内容,而是首先转换成“心理现实”、“审美心理现实”,即由外在的客观的现实转换成内在的主观的“心理意识”,然后才变成艺术内容、艺术形象。
相对于以往的“文学反映论”、“文学意识形态论”,“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中的理性维度虽未隐去,但已失去了以往那种压倒性的主导地位。“审美反映”、“审美意识形态”逐步将情感的东西、感性的东西,充满个性的虚构、夸张、幻想、想象等因素推上了艺术创作的主体地位,使其能量得以开掘和释放。随着审美主客体之间的审美关系的确立,审美过程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超实用功利性。审美主体的情感、感觉、表象、联想、想象将其带入虚静、超脱的心理体验当中,暂时忘却现世的纷扰。主体心理世界的被打开,使艺术家面前的对象世界变得广阔和丰富起来,创造性思维由此挣脱了现实时空的拘囿而获得了无限的驰骋天地。于是,“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不再像以往“文学认识论”、“文学意识形态论”那样仅仅是关于如何把握现实世界的学说,而开始转化为如何领会人自身的学说;文艺创作也不再仅仅是对外部世界的精确的确定不变的复现,而成为充满主体心灵意味的变化着的诗化世界。由客体论到主体论再到本体论,标志着文艺学由他律到自律、由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到探求文学的“本体位置”的逻辑历程,而“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正是从主体的情感、感受、体验、想象等创造性心理因素的引入中推动着文艺学研究向着其本体论方向迈进了一大步。
然而,“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仍然是在哲学认识论的控制之下完成自己的各项动作,就象孙悟空虽然一个跟头可以跳十万八千里,却终究跳不出如来佛的掌心。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
如果说“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还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所进行的对它的“修正”、“改良”和“更新”,那么,“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则是从对文学主体性的强调出发,力图打破和挣脱认识论的束缚去展开其艺术本体思考的。在“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看来,“审美反映论”对于主体审美心理中介的强调仍然不足以回答“文艺是什么”的艺术本体问题,因为它仍未完全摆脱外界参照而把目光凝聚于人类本体自身、艺术本体自身。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是审美文论步入艺术本体论殿堂的又一关节点。人类学本体论理论的倡导者们认为,所谓本体,指事物内部的根本属性及本源,或称终极的存在。所谓本体论也就是对本体进行描述的理论。本体论与认识论不同,它是自我相关的,它并不凭借外界的事物尺度来说明自身,而是以自身的整体的不断发展的存在为依据,去探求其存在的本然处境,追问其生存的终极意义和根基。因此,人类学本体论只能是探向人类自身的本然处境,描述人的生存意义及终极价值的理论。在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看来,艺术正是人类生存本体自身的诗化,是人类的重要的本体活动形式之一。正如苏珊·朗格在她的《艺术问题》中所言:“真正能够使我们直接感受到人类生命的方式便是艺术方式。”(注: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6页。)在这里,人类本体即艺术本体,人类学本体论与艺术本体论合二为一。于是,审美文论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性质,即自身完美,以自身为目的的本体性质。它既不同于认识论美学对他律的文艺本质的探讨,也不同于主体论美学那种源于一种“外在于艺术的哲学理论”的对于主体之文学地位的强调,而是直接将艺术活动与人类生命活动同一,将人类本体论直接演化为艺术本体论,从人的生命活动入手去释读艺术自律的奥秘。因此,艺术乃人的生存,从人的生存出发,必然走向艺术;从人的艺术出发,不得不深入到人的生存……这成为了8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论家们的一种颇为时髦的思路。
较早提出“人类学本体论美学”命题的是李泽厚(注:参见李泽厚:《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论纲》(《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关于主体性的补充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等。); 而对这种新的审美文论形态作出比较系统而明确的表述的则是他的学生们(注:参见彭富春、扬子江:《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1期; 彭富春:《生命之诗——人类学美学或自由美学》,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这两位青年学者的文章和著作写得过于思辨、抽象,甚至虚空。他们常常只是提出一系列的判断,而缺乏具体的、有说服力的、以大量资料为基础的论证。)。他们从把握人类生存与人类艺术、文艺本体与人类本体的关系入手,将“更完整、更深刻地显示了我们的生存之根”的艺术与人类自身的生成及超越联系起来,认为:艺术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乃是生存自身的创造,这种创造是从无到有的生成,是从虚无到存在的跳跃,是从无生命到有生命的转化。人在创造中生成着,又在自身的生成中创造着艺术;同时,艺术还拥有人类生存的超越性质,它试图回答过去、现在、未来的神秘性,向人们显示着存在之谜,将人们引向未来,因而它是理想的世界、是梦境和乌托邦;而艺术作为生存的超越,又是基于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对幸福的渴望和在有限中获得无限,于瞬间中获得永恒,达到存在的最高和最高的存在的欲望,艺术及审美作为生命的自由运动,必然成为这种人类的生存超越的现代形式。显然,在他们看来,艺术审美具有着无可质疑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审美既作为人类生存的动因,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目的;既作为人类生存的起点,又作为人类生存的终点。而艺术作为一种审美超越活动,不仅是人的存在在符号上的显现,而且成为人类生命活动的自我拯救和自我希求。于是,人的生存史与人的审美史重合,审美成为衡量人生意义和人的历史进步程度的唯一标尺。
此外,其他学者也对人类本体论文艺美学进行过论述。如杜书瀛在《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的特征》一文中提出:“作为审美活动的文艺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类生活,是生产和创造人的审美生命的生活”;“凡是真正表现出人的本质的生活活动,都是人的自由的生命活动,这也就是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注:杜书瀛:《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的特征》,《文论报》1989年7月25日。)。在《文学原理——创作论》中,他再次论述文学作为审美活动的人类本体论地位。他在引述了马克思的话“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作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弥尔顿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的表现”之后,说:“作为审美活动的文学创作,根本就不应该是另外一种什么东西的附属物,而是人的本性之一,是人的‘天性’(社会本性和社会‘天性’)之一,是社会的人自身存在的方式之一,是人之作为人不能不如此的生活形式、生存形式之一。”(注:杜书瀛:《文学原理——创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
还有的学者提出,人在审美活动中达到了最高度的自主性,审美已成为人的最高存在方式。以这样的人类学本体论去考察艺术作品将顺乎逻辑地将艺术的任务界定为“创造一种自由性的实体即艺术作品,以使之成为普遍的和永恒的存在”,艺术把“那在审美体验中对人现象的呈现出来的东西固定在自主的实体形式中,并且在存在的这种深度中获得一种不可替代和不可穷尽的意义”(注:陈燕谷:《审美·艺术·存在——美学本体论大纲》,《当代文艺思潮》1987年第4期。)。 在这里,文艺最终体现了它与人类生存的同一及对人类生存的创造和超越,实现了文本与人本的统一。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超越了审美反映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对哲学认识论的归根到底的依赖性,站在了认识论之外,并且进一步又站在了认识论的对立面、站在了认识论的否定者、排斥者的立场上来探求文艺的审美本体,但由此它也就走上了极端,走上了片面。
片面之一:它完全割断了文艺、审美同认识的联系。在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看来,艺术不是认识,而且似乎艺术同认识没有任何联系;艺术离认识越远越好,只有隔断了艺术同认识的联系,才能显出艺术的本性。事实上这是办不到的,也是不合理的。我们认为,把艺术等同于认识是片面的,反过来,把艺术同认识绝对对立起来同样是片面的。摆脱对认识论的依赖性并不等于要同认识论绝交。审美—艺术活动是同认识—思维活动性质不同而又密切联系的精神活动形式和方式。审美—艺术活动虽然并不必然依赖于认识,但审美—艺术活动从来就不排斥认识。审美—艺术同认识是可以成为朋友甚至密友的,这已为审美—艺术史上的无数事实所证明。
片面之二:它完全泯灭了审美—艺术同人的生活—生命活动的界限。在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看来,审美—艺术即人的生存—生活,人的生存—生活即审美—艺术,“艺术是人类的生活本身”。“艺术不再是作为生活的一部分,而是作为整个生活整体。因而,生活本身将成为舞蹈、音乐、绘画和诗”。“因而,我们看到人就是艺术家。作为分工而出现的艺术家的概念和现实也许会消亡,取而代之的将是我是艺术家,你是艺术家,他是艺术家,人是艺术家”(注:彭富春:《生命之诗——人类学美学或自由美学》,花山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显然,这种论断既不合于审美—生活,人的生存—生活也离不开艺术。但是,生活并不就是艺术;艺术也不就是生活。假如艺术与生活等同,那么,观看《白毛女》演出的战士向舞台上的黄世仁开枪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审美体验论
人类学本体论文艺美学不再将文艺的本质追问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而是把文艺活动中审美与生命合一的令人陶醉的人生体验之一种——审美体验推到了前台,从中探讨文艺活动的人类学本体意味,同时也为当代文艺美学由认识论向体验论的过渡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点。而文艺的人类学本体观本身也在此过渡中凝结为一种存在论或生命论的文艺本体观。
审美体验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新时期审美文论的关注点由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到对人生之美的体会和体验的转移,以及中国古典美学感兴论和体验论的当代复兴。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儒释道美学中的感兴论与体验论思想,将审美与艺术看作是人的生命直觉或体验的结晶,强调要“体味”人生真谛、生命气韵,要以诗以画以书以舞以乐去表现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生命体验,而且认为艺术的精粹之处就在于善于表现那种蕴涵着“生命体验”的“言外之意”和“韵外之致”。宗白华就特别强调中国艺术对生命律动和人生体验的表现。《美学散步》引用了王船山下面一段话:“唯此窅窅摇摇之中,有一切真情在内,可兴可观,可群可怨,是以有取于诗。然因此而诗则又往往缘景缘事,缘以往缘未来,经年苦吟,而不能自道。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宗白华强调:“‘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这两句话表现出中国艺术的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注: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1页。)“为什么它是“中国艺术的最后的理想和最高的成就”呢?就因为“通天尽人之怀”最可宝贵的人生体验,是生命真谛。而表现了这种人生体验、生命真谛,就达到了艺术的至境。中国美学的这种感兴论和体验论思想,这种生命诗化的特征,得到了西方现代生命哲学、表现主义和存在主义美学的认同和呼应(注:宗白华的学生刘小枫的《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一书,就比较系统地论述了西方美学中与中国体验论美学相通或相近的理论思想。)。进入新时期以后,文学艺术对人的精神内宇宙的日益丰富的开掘以及认识论美学应对能力的日益减弱,都为审美体验论的复苏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于是,宗白华、王朝闻等老一辈文论家、美学家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学传统,在重“逻辑”“分析”的认识论美学之外,重建和发展重“体味”“意会”的体验论、感兴论美学,将审美体验作为美学的中心问题,从人生感悟的角度、从“活生生的感性”的角度去探讨审美这种复杂的生命直觉现象。宗白华的《美学散步》风靡学界,王朝闻的《论凤姐》、《不到顶点》等表现着体验论感兴论美学特点的论著、文章也颇受欢迎。一批中青年文艺学研究者也敏锐地作出了反映,刘小枫、王一川、王岳川等相继发表著述,展示出超越认识论的理性逻辑规范的诗化理论的特征。他们对审美体验的内涵作了界定,认为“审美体验是一种精神的、总体的情感体验,不像日常生活或科学体验是功利的、单维的情感体验。审美体验往往由对对象形式美的愉悦进入到对人生、未来的感悟,并能直接进入人的潜意识深层领域,是照亮人格心灵内海之光”;“审美体验是一种心理震撼的强效应,深度审美体验,可以唤醒蒙蔽的自我意识,达到一定高度的精神自觉”;“审美体验过程始终伴随着一种心理愉悦,并在意象纷呈中获得审美享受”(注:王岳川:《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4页。)。他们还对照西方的有关美学思想对“体验与生活的共生性”和“体验的内在性”(注:刘小枫:《诗化哲学》,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进行了论述。
由于“审美体验”中感性感受和心理直觉等发挥着重要作用,因而由“审美体验”又引发了文论家、美学家们对审美活动中的“活生生的感性”及“审美直觉”现象的特别关注。他们发现认识论美学对美的追问表现出“对理性能力的过分信赖和对感性能力的过分轻视,以及为着思辨理论的体系性而忽视对具体的现实存在境遇的认真关注”;而“理性总会有局限的,无法单独把握审美这种复杂的直觉现象;相反,应该充分依赖活生生的感性,因为它更切近审美本身”(注:王一川:《走向修辞论美学——90年代中国美学的修辞论转向》,《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在审美体验论的倡导者看来, 只有追寻体验的难以言喻的感性直觉特征,才能求得对于现实人生的有限性的超越之途。
与艺术的感性本位相并生的是对个体本位的强调。“审美体验”不但突出了“感性”、“直觉”,而且突出了“个体”的主体性,即“个体”的人格独立和个性自由。在“审美体验”中,艺术审美的意义就在于它给予了感性个体以在其他活动中所不曾有过的自主地位,它使每个个体自身期盼着的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权利得以实现,而艺术审美正是这种实现的特殊方式。当然,多数的审美体验论者是在个体与整体的统一中给予个体以更加显明的地位的。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契所言,“审美体验是以个体和个人命运的形式来说明人类”(注:卢卡契:《审美特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48页。)。审美体验实际上是为个人的心理体验与人类精神的贯通提供了一个媒介体。王一川的《审美体验论》(注:王一川:《审美体验论》,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就直接将美的本质界定为:人类活动的总体远景在个体体验中的显现。而王岳川在他的《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注:王岳川:《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一书中则将个体审美体验的这种整合性渲染得更加神奇:“个人审美体验在时间上,短仅需一瞬则可体味人生执着追求和自然的终古之美”,“审美体验的深化是个体心理不断地‘同化’和‘顺应’的过程……是一种体合宇宙精神、把握人生境界、渗透自然之气、讲求灵肉内修的过程”。在这些青年文论者看来,审美体验中的主体正是从个体的人生境遇出发,通过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人类精神内宇宙的感悟,去体味人类心灵的深层领域的丰富蕴含,从而使个体得以传达总体,实现对人类生命本体的直观表达。审美体验的个体性到了刘晓波那里,则被张扬为对抗群体理性的一面鲜艳的旗帜,个体与群体裂变为壁垒分明、尖锐对立的两种力量。他强调以追求人格独立和生命自由的自觉个体为本位,反抗压抑个体自由发展的“社会本位”对人的奴化。由文化哲学上的“感性—个体本位”观念,推出艺术美学上的“冲突为美”的命题。刘晓波认为,“在审美上,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个性与共性的统一,只要有这种统一,就是共性对个性的无情阉割”,因此,审美体验的主体不再是人类精神的个性载体,而是审美者“独特生命的形式化”;审美活动不是在个体与整体的和谐统一中完成,而是个体与整体的势不两立,以及在特殊的生命与历史、大众和社会的统一模式的圣战中实现。而在这种审美活动中个体所体验到的则是“人类童年时代的最本真的原始生命力”,即感性强力挣脱功利性世俗和思辨性逻辑而达到的人类生命的自由之境(注:参见刘晓波:《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142页。)。于是,个体与感性共同被提纯为最纯粹的性灵之真,而在这种本真原始的迷人情致中,历史文化对人之心智的影响,以及感性直觉之中的理性渗透被认真地过滤掉了,文艺被轻抛给自由审美的太空,成为远离现实人生、社会文化制约的天外孤星。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极端化的理论也就把审美艺术推进了死胡同。
从审美反映论到审美体验论,审美形式愈来愈受到文论者的关注,审美体验“将他人称为‘形式’的东西看成是内容”,“由对对象的形式美的愉悦进入对人生、未来的感悟”(注:王岳川:《文化话语与意义踪迹》,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于是, 形式本身的意味日益变得丰厚和悠远。审美体验论在张扬感性、拒斥理性的同时,把作为艺术“审美外观”的形式推到了前台。在审美反映论中,对文艺本质的穷究导致了对艺术内容的强调,而形式则作为内容的附从和陪衬被理论家疏忽和淡忘,“为内容牺牲形式”、“为思想丢弃语言”往往成为反映论之理性述说的题中应有之义。审美体验论的复苏使得那些召唤着深层人生体验的审美形式获得了足以取代审美内容的品格和价值。正如王一川所言:“使形式从属于内容本体,内容的形式化意味着把内容视为形式,当作形式,动用形式分析技巧去加以研究。这并不是要以形式取消、代替内容,而是把内容镶嵌在形式框架中。换言之,当我们把内容看作形式时,就能从形式中更清晰地瞥见内容的面貌。”(注:王一川:《修辞论美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0页。)审美体验论以对形式魅力的关注取代对本质内容的形而上追问,明显受到了英国著名视觉艺术理论家克莱夫·贝尔的艺术定义的启发。贝尔在1913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深得中国当代审美文论家的青睐。贝尔认为,意味就在形式之中,离开形式而作无边的联想不是意味,用说理的方式传达思想也不是意味。那么究竟“意味”是什么呢?贝尔认为是一种能够唤起我们的审美情感的在艺术品中存在的某种性质,“离开它,艺术品不能作为艺术品而存在;有了它,任何作品至少不会一点价值也没有”(注:克莱夫·贝尔:《艺术》,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 那么艺术品中能够唤起审美情感的是什么呢?贝尔并没有说得很清楚,只是说它是一种与人的无意识心灵相对应的东西。然而正是这种含糊诱导出了人们对于形式本体的“终极实在”的思考,使人们发现了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的创造性形式的某种内在、先验的联系。审美体验者正是从这里,从人的审美心灵与艺术形式的这种内在的神秘联系出发,在两者的情感生命的交融中去寻求形式美的意味之所在,开始了对艺术形式的独立价值的发掘。审美体验作为一个独立于认识的自主性概念带来了文艺学的“内部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文艺的形式本体论研究也由此发生并逐步蔚成景观。
标签:文学论文; 本体论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理性与感性论文; 艺术论文; 人生哲学论文; 文化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文艺理论研究论文; 美学散步论文; 文艺美学论文; 文学概论论文; 美学论文; 生命本质论文; 认识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