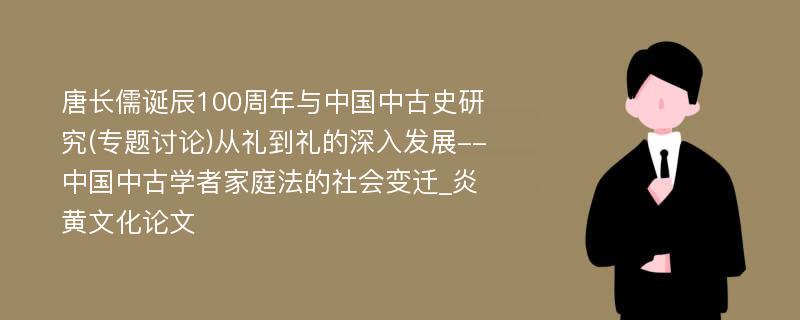
唐长孺百年诞辰与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深化发展(专题讨论)——从礼容到礼教:中国中古士族家法的社会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古论文,中国论文,士族论文,家法论文,专题讨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1)03-0036-17
以往讲宋明理学的起源,几乎都要追述到韩愈“辟佛”。但余英时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却把理学放在北宋儒学运动及两宋政治环境中来观察,以为理学的产生寻找更丰富也是更“切近”的原因。笔者认为,宋明理学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主流意识形态,至今仍在影响着国人的心灵与伦理,因此绝对不仅是政治的产物,也不能仅被看成是少数思想家的孤明先发。宋明理学的产生,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它的产生与所造成的影响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本文所谈中古士大夫风操即是上述长时段问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风操”一词,源于《颜氏家训》:
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喏,执烛沃盥,皆有节度,亦为至矣。但既残缺,非复全书。其有所不载,及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故世号士大夫风操。然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视而见之,耳能听而闻之,蓬生麻中,不劳翰墨。汝曹生于戎马之间,视听之所不晓,故聊记录,以传子孙[1](卷2,《风操第六》)。
颜之推早年生活在南朝,后来定居在北方,对公元6世纪南北迥异的文化氛围深有感触。他认为,风操的来源有两个,首先是《礼经》中设定的生活细节规范,体现了圣人的精神,但《礼经》残缺不详,故士大夫又根据现实需要自行创造并加以传承了一些礼仪规范,二者结合便成为所谓“士大夫风操”。
一、礼经·礼容·礼教
十三经中的《仪礼》、《礼记》与《周礼》被并称为“三礼”。现在所知道的上古礼制大多是士礼,如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士丧礼等,主要保存在《仪礼》之中,但还有一部分保存在《礼记·曲礼》中。比如,著名的戒条“食不言,寝不语”等。春秋时期的子产认为,礼是“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2](《召公二十五年》)。即礼当然的有其超越性的价值核心,但必须行之于一套严整的仪式,体现为具体的行为规范。《礼记》认为,礼主要在八个方面展现,即冠、昏、丧、祭、射、乡、朝、聘[3]《礼运》),其实便是八类主要的仪式与规范。但这些具体的仪式与规范是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的,所谓周因殷礼、殷因夏礼,代有沿革损益。《汉书》云:
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备,周监于二代,礼文尤具,事为之制,曲为之防,故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及其衰也,诸侯逾越法度,恶礼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灭学,遂以乱亡[4](卷22,《礼乐志》)。
上引文献中出现了“威仪”一词,《左传》对该词汇有下述阐释:
卫侯问:“何谓威仪?”对曰:“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有威仪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爱,进退可度,周旋可则,容止可观,作事可法,德行可象,声气可乐,动作有文,言语有章,以临其下谓之有威仪也。”[2](《襄公三十一年》)
这里的“威仪”,并非公共性的仪式,而是涉及个人言行举止的具体行为规范,因此较之经典正文必然是复杂烦琐,正如前引《汉书》所说“礼经三百,威仪三千”。后来,“威仪”一词也出现在中国佛教典籍中,如有所谓“沙弥威仪”的说法,其内涵与之类似,皆指对于个体生活状态的一种规定。值得注意的是,《礼记》中则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说法[3](《礼器》)。这说明,曲礼就是威仪,《礼记·曲礼》正是集中保存了生活细节方面的种种礼仪规范,可以看做是颜之推所说“士大夫风操”的滥觞。
“威仪”还有一个较为通行的称谓,即“礼容”。中国古代贵族对礼容有专门的教育,也就是所谓仪容、辞令、揖让之学,并由专门的职官“保氏”负责传授。《礼记》中有“君子九容”的说法,即“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声容静,头容直,气容肃,立容德,色容庄”[3](《玉藻》),这已经与后世士大夫风操所涉及的言谈举止相当类似了。《礼记》至迟于汉初即已成书,彼时贾谊《新书》中亦设有《容经》一章,专讲“威仪”或“礼容”方面的问题。从汉代开始,“威仪”或“礼容”已不仅仅是贵族阶层成员的个人修养问题,而是构成更加深刻的社会文化现象“礼教”的一部分。
先秦时代,与礼相关的一系列社会文化现象皆以宗法制度为核心。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希望人在这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中各安其分,承担各自不同的责任,礼在其中起到的就是标明与稳定社会等级的作用。春秋战国以来,宗法制逐渐瓦解,固有的社会结构遭到破坏。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焚书坑儒、以吏为师。但他对礼乐文化的破坏并不利于稳固统治。看到秦始皇出巡,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也”,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连为人佣耕的陈涉也说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千古名言。人人不安其位,都想取而代之,这是秦始皇文化专制政策造成的后果。汉朝立国之初,以黄老治国,通过实行休养生息政策使经济获得明显恢复,但社会问题却依然严峻。贾谊作长沙王傅时上书认为,自秦商鞅变法以来,社会秩序混乱,人心失驭。他用了一个生动事例来说明风气败坏,即“借父耰锄,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父亲问儿子借农具,儿子以施恩的心情借给父亲;婆婆向媳妇借笤帚簸箕扫地,媳妇站着辱骂婆婆。贾谊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商鞅“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的政策密切相关。此外,他还列举种种社会病态,如人民的嫌贫爱富、官吏的假公济私,种种丑恶,不一而足。贾谊引用《管子》中的名言“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指出重建意识形态与社会道德体系已经是统治者刻不容缓的任务[4](卷48,《贾谊传》)。
汉代意识形态与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很复杂,简而言之可归为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是在秦焚书之后对儒家经典的重建,这为其他方面的重建提供了根本的价值标准,由此导致了汉代经学的全面繁荣,对经典的解释成为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制度的逐渐儒家化,从叔孙通开始,各种国家礼仪制度被逐渐恢复,官员选拔制度也与道德伦理重建相结合,对“孝廉”的察举就是明证。再者是郡县教化职能的赋予与基层社会秩序的重建,其中“礼”的作用被凸显,这便是“礼教”。按照儒家的基本观点,礼的精神根植于人天生的情感,但礼所包含的各种仪式与规范对人的行为又有规范与塑造作用,因此可以用来教化。在礼的各组成部分中,“礼容”有着重要作用。《史记》载:
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索隐:汉书作“颂”,亦音容也。)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太守。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5](卷121,《儒林传》)。
《士礼》十七篇是由高堂生传的,但另有一位徐生因“善为容”而做到礼官大夫。“善为容”是指他知道在《礼经》指导下表现出一副怎样的做派,其实就是在展现“礼容”方面很有些功夫。其孙徐襄不通经文,但因继承了这套做派,依然获得官爵,此后对礼的解释和表达都出自徐氏。
在汉代意识形态与社会道德体系的重建中,礼容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是礼的重要外在形式,是一种伦理道德的示范形态。关于礼的各种义理性问题,尚有《礼经》残本可作讨论与传承的基础,而礼容因为具有表演性质,非经过“身教”不可,因为多种多样的细节是无法用文字表达清楚的。汉代全面复礼,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职官体制,除前面所出现的礼官大夫外,各个郡国都有专门从事礼容研究的官员,叫容史。容史遇到不懂的问题时,就到儒学大本营鲁地去学习。具体而言,礼容包括的动作要件有:拱,用手表达恭敬的礼容;揖,表示辞让谦退的礼容;肃,外貌恭敬而内心肃敬的礼容;拜,表示敬服的礼节。此外,礼容还包括表情神态,“临丧则必有哀色,执绋不笑;临乐不叹;介胄则有不可犯之色”,以达到《礼记·曲礼》中“君子戒慎,不失色于人”的要求。
君子礼容会影响大众,全国百姓均渐渐认可为人处世应该遵守这样一些礼。中古士族是讲究礼容的。阮籍《咏怀诗》云:“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粮。外厉贞素谈,户内减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可为明证。
由此可见,颜之推所谓的士大夫风操,其源头之一就是包含在《仪礼》和《礼记·曲礼》等“礼经”之中,以“礼容”为中心的一系列内容体现着“礼教”的具体原则。当然,这里的礼经、礼容、礼教是经过汉代重建而形成的。然而,士大夫风操并非后人对礼容的简单承袭或模仿。时移世易,士大夫形成了自身“家法”,这是士大夫风操的另外一个现实渊源。
二、“家法”的演变
“家法”之“家”,大致可以解释为学派。自东汉,儒家经典开始以家族为主要传承方式,经术与仕宦的结合使东汉以来出现了世代公卿、世代传经的家族。城南杜氏有杜预,清河和博陵崔氏有崔骃、崔寔,范阳卢氏有卢植,均为著名学者或经学大师。其子孙便遵循祖上对经典的诠释,这时其所秉承的“家法”之“家”就有了家族之意。这些家族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发展为士族。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中谈到:“所谓士族者,其初并不专用其先代之高官厚禄为其唯一之表征,而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钱穆明确指出:“当时极重家教门风,孝弟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6](P309)这表明,在家族中传承的儒家经学与家庭伦理有直接关系。士大夫家族世代学习经学,这些道理逐渐内化为士族特有的家学礼法,其本质是他们在传承经典之中自我体悟出来的伦理规范,由此构成了士大夫风操的另一个来源。
士大夫风操包括两部分:一是言行举止方面的各种做派;二是内在的伦理标准。前者从礼容改造而来,后者系由经学衍化而来。《宋书》载有一条典型史料:
诸儒各为章句之说,既明不独达,所见不同,或师资相传,共枝别干。故闻人、二戴,俱事后苍,俄巳分异,卢植、郑玄,偕学马融,人各名家。又后之学者,未逮曩时,而问难星繁,充斥兼两,美文列锦,焕烂可观,然而五服之本或差,哀敬之制舛杂,国典未一于四海,家法参驳于缙绅,诚宜考详远虑,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7](卷55,《傅隆传》)。
从这条史料可以清楚看出,儒家章句之典礼如何向国家和士大夫应该遵行的礼法转化。这里主要强调分歧来自对于经典理解和遵从上的差异。如在婚礼及丧服制度上,对于经传理解的不同“家法”就会影响到实际的士族之家采用不同的礼仪形式。因此,颜之推所谓“家门颇有不同,所见互称长短”即起源于此。
家法虽立足于对儒学经典的阐释,但很多士族的家法又不是完全依据《礼经》,而是颇有损益。例如,东晋中郎卢谌著有《祭法》,所用祭品“皆晋时常食,不复纯用礼经旧文”[8](卷703,《服用部·香炉》)。北朝崔浩“作家祭法,次序五宗,蒸尝之礼,丰俭之节,义理可观”[9](卷21,《崔浩传》。在更多情形下,士族家法是向着个性化方向发展的。《礼经》中有庙见之礼,王暾的妻子已经去世,其子结婚时就要求新媳妇去祭扫婆婆之墓,这是王家特有的家法[10](卷45,《王暾传》)。
南北朝时期,士族家法的文本化迅速发展。例如,琅琊王氏家族的王彪之“博闻多识,练悉朝仪”,并谙江左旧事,有“王氏青箱学”家世相传[7](卷24《王淮之传》)。王弘“明敏有思致,既以民望所宗,造次必存礼法,凡动止施为,及书翰仪体,后人皆依仿之,谓为‘王太保家法’”[7](卷42,《王弘传》)。无论是王太保家法,还是前面提到的卢谌《祭法》,都说明士族家法在文本方面的发展。考《隋书》,收仪注类作品“五十九部,二千二十九卷。通计亡书,合六十九部,三千九十四卷”[11](卷33,《经籍二》)。那些从“吉、凶、军、宾、嘉”五礼之外逸出的日常生活类仪注,具有相对独立的价值,因而被颜之推名为“士大夫风操”。有研究者指出,中古时代流行的“书仪”受到世族特别是东晋南朝士大夫的影响。笔者认为,书仪其实就是以南朝为主的士大夫家法的记录,是其所谓“士大夫风操”或“士大夫风范”的普及本形式。
三、士大夫风操与社会变迁
在颜之推时代,“士大夫”一词专指士族,这与其在后世之意有很大不同。中古士族有着特定内涵,一般文人官僚并非士族。士族之所以看不起庶族,是因为士族有士大夫风操,而庶族没有。北魏公孙睿之妻为崔浩侄女,其堂兄公孙邃的母亲是雁门李氏,地望悬隔。崔氏与李氏一为大士族,一为庶族,遇到婚丧嫁娶家族集会时,两兄弟做派完全不同。故时人说:“士大夫当需好婚亲。”[12](卷23,《公孙表传》)言下之意,母亲或妻子出身决定了其修养、文化能否应付吉凶集会这样复杂的程序,而这对丈夫或儿子的声誉、对整个家族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
由汉至唐,这些复杂的礼仪与日常生活中的风操为世家大族所垄断,成为其特有的文化资本与身份符号。士族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都表现出文化上的优越性。儒家伦理从经典演变成行为规范,是由士族阶层推动完成的。
然而,到了唐代,士族在文化方面的优越地位开始受到挑战。唐太宗对于士族特别是山东士族一贯采取打击态度,最明显的做法是重修《氏族志》与《姓氏录》时试图完全以现实政治地位来排定族性地位,不承认士族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优势。《贞观政要》记载了唐太宗与房玄龄的一段对话:
比有山东崔、卢、李、郑四姓,虽累叶凌迟,犹恃其旧地,好自矜大,称为士大夫。每嫁女他族,必广所聘财,以多为贵,论数定约,同于市贾,甚损风俗,有紊《礼经》,既轻重失宜,理需改革[13](卷7,《礼乐》)。
唐太宗发难的理由恰恰在于士族买卖婚姻的行为“有违《礼经》”,而士族所标榜的家法、风操即便多有自己创造的成分,但绝不敢否认与《礼经》的渊源,唐太宗所提出的理由也有釜底抽薪的意味。
唐代有不少制度被认为是反对士族的,但在事实上,士族仍顽强地保持了其固有的影响力。如在婚姻方面,唐太宗刻意不与士族通婚,两百年以后,唐文宗、唐宣宗在为公主安排婚姻时却都倾向于士族子弟。但士族们却不愿与皇家联姻,因为公主不仅目无礼法、骄悍难治,生活作风也不检点,以至于唐文宗曾对宰相感叹:“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14](卷172,《杜中立传》)针对这种情况,唐宣宗屡屡要求公主遵循礼法。《幽闲鼓吹》曾记载一事云:
驸马郑尚书之弟觊尝危疾,上使讯之。使回,上问:“公主视疾否?”曰:“无。”“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戏场。”上大怒,且叹曰:“我怪士大夫不欲与我为亲,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辇至,则立于阶下,不视。久之,主大惧,涕泣辞谢。上责曰:“岂有小郎病,乃亲看他处乎?”立遣归宅。毕宣宗之世妇礼以修[15]。
更有甚者,永福公主原已许婚士族,后因其盛怒中折断用餐的筷子,从而被唐宣宗勒令停嫁,而以性情温顺、谙习礼法的广德公主代之[14](卷83,《诸帝公主传》)。上述事实充分表明,唐太宗对于山东士族不遵《礼经》的批评并未能阻止唐皇室在文化方面向士族靠拢。
唐代士族的礼法与风操得到全社会仰慕,原来为士族所垄断的各种家法开始普及,并在普及过程中走向统一。《新五代史》云:“弘宣患士庶人家祭无定仪,乃合十二家法,损益其当,次以为书。”[16](卷197,《卢弘宣传》)又云,郑余庆也“采唐士庶吉凶书疏之式,杂以当时家人之礼”[16](卷55,《刘岳传》)。士大夫风操的出现亦使国家礼仪日常化,到了唐代则因印刷术的发明与教育的相对发展而进一步平民化,士族的礼仪文化通过书仪等形式传播到大众。因此,士大夫风操逐渐由一个阶层的规范变为全社会的法式,礼法文化发生了下移。敦煌文书中保存有一本面向大众的《太公家教》,其中云:“其父出行,子须从后;路逢尊者,齐脚敛手。尊者赐酒,必须拜受;尊者赐肉,骨不予狗。尊者赐果,怀核在手,勿得弃之,违礼大丑。对客之前,不得叱狗;对食之前,不得唾地,亦不得漱口。忆而莫忘,终身无咎。”这些内容,已经与当年颜之推所谓士大夫风操别无二致。正因为这种文化资本不再为士族所垄断,故士族的独特性被消解。到了宋代,“士大夫”一词成为官僚、绅士乃至一般读书人的泛指,其独特的门阀内涵已经完全消失了。
最后,附带谈一下中古礼法文化下移中佛教扮演的角色。佛教在社会伦理与个人行为规范方面与儒家结合,对中古社会起到了巨大的塑造作用,《二十四孝》的出现就是儒佛互动的结果。佛教讲究戒律,其对信徒的生活细节有具体规定,如《四分律》中的戒条涉及僧尼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中古时期,大众笃信佛教的情况非常兴盛,因此佛教的这些戒律、威仪也很深入人心,逐渐变为大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敦煌文书中发现的许多启蒙读物中浸润着佛教伦理及其日常规范,其影响甚为深远。
综上所述,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礼法名教,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中的一家。汉代通过独尊儒术,把经学变成官方意识形态。东汉末年,世代读经、世代做官的名士世家逐渐成为士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家法和门风,儒家经典被内化为士大夫风操,士族之家各有家法。到了唐代,士族开始与官爵脱钩,礼法文化也为更多的社会阶层所接受。因此,士族衰落与礼法下移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化的佛教扮演了重要角色。
至于随后兴起的理学,则是针对业已下移普及的礼法文化完成了一次理论化重建。在某种意义上,宋明理学不过是为士大夫风操这套东西寻找到了一个超越性源头,正是通过这样的演变,儒家伦理完成了从经典(经学)向社会和个人伦理规范(道学)的转变,并且由于佛教的影响,使它具有禁欲主义的宗教色彩。中华文化本身的一次阶段性变化,由此而得到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