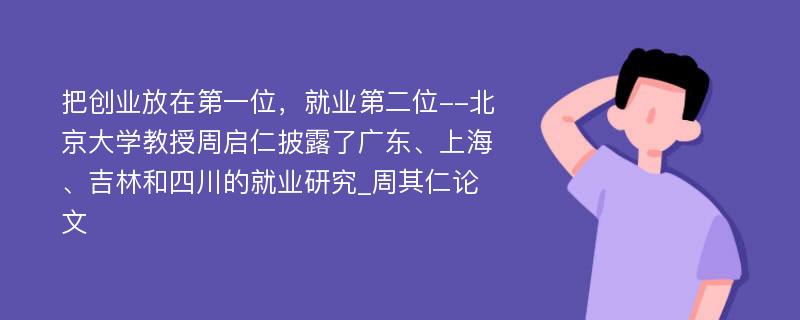
把创业放到第一位来,把就业放到第二位去——北大周其仁教授披露广东、上海、吉林、四川就业调研情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吉林论文,广东论文,上海论文,北大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周其仁,前不久在成都召开的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披露了外界尚不清楚的我国就业方面的情况,现将其讲话录音整理如下,供读者参考:
就业问题现在成了国家经济生活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1997年立题的时候,还没有估计到情况会变得那么严重。当时一个非常直接的想法是,当时农村劳动力还在往城里走,这是解决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的出路。这也是我们1994年到1996年期间与劳动部合作的一个课题得出的结论。乡镇企业能够带来的就业相当有限,下一步就是国民经济结构、城乡结构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才能吸纳中国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这个势头刚刚一起来就碰到城市国营企业的改革,城市大规模工人的下岗。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农民要进城,城里国营企业工人要下岗。到底会发生什么?这是1997年夏天我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当时我们试图解决的一个问题,或者试图去验证的一个东西,就是希望农村劳动力更加市场化,它没有那么多的福利,希望把这个力量引到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业系统、城市系统来,以至我们国家的整个工业产品、商业服务和其它领域的产品和服务更加具有竞争力。当时以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城市工人下岗,城市工人原来是不能动,现在是可以动,希望这里头有一个市场化的过程,把原来在身份上分开的两个劳动力市场变成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我们是根据这么一个主要的线索去作工作的。调查下来的情况呢,跟原来想像的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各地的地方政府,在遇到下岗压力的时候,基本上的趋势是把原来已经开放的城门再统统关闭起来。不是说让农村工人跟城里工人很好地竞争,而是首先把农村工人从城里驱逐出去。我们已经收集到几十个城市的法规或者临时立法,就是明确的(有些是带有数量指标的)把农民工这个岗位空出来让给下岗工人。
我今天讲中国的失业问题、就业问题是一个非常地方化的问题。我的看法是恐怕不能单靠什么中央的宏观政策就可以解决。它必须靠地方政府根据各地的情况去有针对性的解决。首先,地区之间就业压力的差别非常大,我们观察到对付就业压力的方式,各地的差别也非常大,这一点我觉得值得引起下一步作政策讨论时的注意。这样的信息,完全集中到北京让中央政府来处理,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先讲讲我们调查过的几个城市的一些有趣的现象。
首先,我们在广东选了中山市,因为这代表广东发展模式,特别珠江三角洲发展模式。它的模式是本地劳动力很少,大量的引进外资,然后大量的雇佣外地民工。民工的流动性非常高。流动性非常高,它老是保持了新的劳动力进来,然后成本就非常低。现在你到中山去,每月到当地工作的工人的工资,可能还有500块钱一个月,在深圳还有600元钱一个月,除此之外就没有其它福利。那么,像这样的工资价格,你要拿全国国有工业的工资成本来比,它有极大的竞争力。所以它一方面就吸引港台的资本进来,另一方面就把全国各地主要是湖北、四川、安徽、江西、湖南农村劳动力往这里吸引,它形成这样一个发展模式。我看广东过去多少年的竞争跟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但在1997年我们调查的时候发现,就是这样的地区也遇到问题。遇到什么问题呢?这当然是在香港、亚洲金融危机刚刚爆发时作的调查,当地出现劳动力短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找不到工人,很多投资进来,大的鞋厂一下子要招两万工人(我们在中山市已经看到过所谓劳动力密集型的工厂,一个工厂有几万工人,象一支军队一样,几个月以前还全都是农民,经过短期训练后就变成产业工人了,做鞋呀,出口……)。结果就找不到工人。找不到工人的原因,就是因为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一起来以后,导致了发达地区劳动部门收入的提高,因为它有管理费。我们调查一个镇劳动管理部门一年的收入,大概是在四百几十万人民币,有很多地方,内地一个县剩余的财力都没有这么多。这样就刺激了内地劳动部门的压力,因为都是劳动部门嘛,所以它就开始管理劳动力市场,对流出的劳动人口征收费用,征收中间费用,并且派人跟着到广东来收费。这个结果呢,导致劳动力在移动中的成本急剧上升,上升到他们来不划算。这是我们在广东看到的一个非常吃惊的事情。整个中山市,当时是说缺五万工人,你马上来五万工人,都可以解决。 过去是内地劳动力到广东来求职,1997年的时候已经是广东劳动部门去招,招不来人。非常显著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有序工程”,就是劳动部推出的劳动力流动有序工程,有双证,双卡,然后每月交费,每年交费,各种各样的中间费用上升很快。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把它一般化了看,这是目前造成中国就业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根源。政府在市场里面抽取了过多的税和费。抽取过多了,导致了本来还有利可图的生意告吹,市场萎缩,这样导致了两头都不好。广东就开始资本密集,用机器替代工人,内地还是很多工人找不到工作。那么,梗阻就梗阻在非常具体的体制因素上,这是我们在广东看到的故事。在当地,中山市整个劳动力大概45%是外来人口,这个供给量它是靠源源不断的增加新流量。广东的技术含量并不高,附加价值也不高,它就是靠流动的农村人口压低工资价格,维持竞争力。这个模式为什么在1996年、1997年就受到梗阻,就是我们这个政府部门。如果市场经济过程中对政府部门的行为没有有效的扼制机制,什么市场最后都会变成乱的,最后这个市场就会垮下去。这是我们在广东看到的事情,这个问题可能跟其它地方就不同。
第二个我们研究了上海,上海的情况也非常独特。一方面有大约三百万人口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流入了上海,三百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上海就业。另一方面,上海工业的竞争能力在全国市场上急速下降,庞大的工业产品都开始卖不出去。所以我们1997年、1998年在这里调查,它累积的国营系统下岗工人我们当时报告的人数是一百一十万人,这件事情也积累了重要的经验。因为原来中国的国营工人是不能动的,那么在市场竞争的形势面前,它开始大量的下岗。上海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上海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看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正面的东西,就是它开始引导一个所谓的再就业机制,就是把下岗工人全部拖出来离开公司,由这个行业成立再就业中心来托管。这个托管,它设定了一个时间,不是无限地管下去。这个政策后来基本上就变成了国务院的政策。就给设定两年,这两年由上海市政府拿出三分之一的钱,由所在的行业贫富调济,还有赢利的公司补贴亏损的公司,整个行业拿三分之一的钱,还有三分之一的钱,就是我讲的负面因素,向整个进城的农民工去提取,每个农民工提取一笔钱拿来补贴城市下岗工人。他用这三笔钱建立那个叫再就业的基金,扶持下岗工人,给他两年的时间,让他找到新的机会,培训时期,大概第一年每个月发236元, 第二年递减,发219元,第三年不管了。那么,上海就创造了这么个经验。 另外我们在上海的调查中看到,它对工人采取分流的政策,其中非常重要的分流就是对1984年以后的新的合同工,完全就是走市场化的路线,你如果累积工龄12个月,那么你如果离开工作岗位,给你补贴一个月的工资,相应的就是失业保险,就是走正规的失业保险这条路线,就不再是传统的国营工人了,国家、工人、工厂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完的一辈子的关系,就变成一个contract,就变成一个合同的关系。但是老的工人不行,因为老的工人在年轻的时候国家只付给他们非常低的工资,国家等于对他们负有债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他们就用了三家出钱来抬一个再就业中心。这是我们在上海看到的。上海看到负面的东西就是市政府列出了文件,确定了哪些行业不准招农民工,哪些行业把农民工驱逐出去。资金呢,全市要按年度减,累计每年减15%的外来就业给城市的下岗工人腾职位,那么这个政策实际上执行当中遇到了市场很大的抵抗,因为企业要挣利润,它就要请相对来说最合算的工人。那这就形成了有一点像美国的打黑工的制度。名义上不合法,但是很多雇的都是农民工。这是我们在上海看到的情况,上海这么大的工业城市,特别是国营企业的规模比较大,那么它解决它的失业和农民再就业之间就找了这么一种组合的模式。当然,上海的这个经验很特别,因为上海还是有很多外资流入,有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很多新的机会。另外,上海的服务业原来很落后,所以这样就吸纳了很多下岗的产业工人,所以上海总的来说是平稳的,一百多万产业工人离开了原来的公司没有遇到很大的社会震动。
但是绵阳很例外,它有一个全国著名的长虹。长虹的经验很简单,就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加上市场机制的工人。长虹大量请的是合同工、农民工,因此工资是非常低,管理极其严格,所以它有很高的理论。在绵阳市,它就给市财政交了一大笔钱。市财政就用来安置这个城市其它的将近十万的下岗工人。所以绵阳变成这么一个循环机制,等于是优秀的企业去利用农村劳动力,农村劳动力有竞争力的labour,形成了利润,上交给财政,财政获得一个资源来安置其它没有竞争力的国营工人。这是绵阳我们看到的一个模式。
那么总的说来呢,上海和绵阳基本上都是国营体制转型当中还有路可走的,但是如果我们转到了东北,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严重,你像吉林市,吉林市大概整个下岗正式失业的工人占整个职工正式编制的25%,实际情况大概比这个统计数据还要高。也就是25%—30%的工人完全没有工作,完全没有收入。而且当地很少有新兴民营企业,也没有类似长虹这样的优势企业。所以那里的困难就直接转化成一种社会的紧张,工人不愿意下岗。下岗,让我去领那个百把块钱呀,把过去国家对我的债务,等于都给免掉了,他不干啦!所以我们管它叫发生了一种粘连现象,工厂开不了工资,也没有钱发,工人还就是不走。他觉得唯一可靠的是国家过去对我欠的那个债你还得认帐,最后就潜在的把这个经济问题转化为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东北非常象苏联,所以可以理解俄罗斯那种情况。因为它国营比例到了这个程度以后,没有任何其他空间可以走。这是我们在吉林市看到的东北的情况。
那么,就业情况最好的可能是温州,是浙江的温州。温州官方统计的失业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我们在那里调查的时候,全国登记的失业率是3%,它登记的失业率是4.7%,就高1.7个百分点。 但实际上这个城市没有感到有任何就业的压力。因为所有国营工人、国营企业,大概在十年前就开始转型,所以它很多问题在十年前就已经解决了。也就是大量的私营工厂、民营企业起来,很多下岗工人后来都变成了民营企业的老板。所以在温州,我们就得出了一个概念,非常重要。就是创业要比就业重要,政府不要光研究就业问题,因为实际上政府是不可能提供这么多就业机会的。你一定要通过企业家,他去开发市场,形成有吸收就业的能力,你这个就业问题才能解决。温州我们去调查的时候劳动局跟我们讲,说三年来大概只有一个人跑到劳动局来找工作,全市只有一个人!这个人还被人说是脑筋有问题,其他人都到市场里去找机会,没有人留恋你原来的那个国营的铁饭碗。温州是个大流动的格局,七百万人口有一百万在全国各地经商,同时它吸纳全国一百万的流入的劳动力,另外它内部七个市、县,在七个市、县内流动的据统计也有一百万人。所以它七百万里头有三百万不是出去就是进来。它是一个高度流动靠市场为主的。那么这个城市最重要的问题,是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建立对劳动力的保障体制,劳动力就业的介绍、工人的福利、工人的必要权益,这些东西是这个城市面临的一个新的问题。不要落入原来的国家来承担福利,但是必须要有相应的工人的福利保障。否则对这个labour,长期对自己的投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都是不利的。
另外一个城市是南京,南京的情况有一点跟吉林市的相仿,经济结构没有很大的改变,工人靠这个国营靠得非常的紧。
那么我这些东西出来以后可以概括出什么东西呢?一条就是中国就业虽然是个全国性的问题,但是解决就业问题不能单单只靠中央政府的所谓宏观政策,要靠地方政府,我的看法主要靠体制政策。这个体制政策里头中心点是要把就业问题放到第二位去,要把创业问题放到第一位来。你这个政府如果你不给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提供空间,提供市场的可准入的机会,你这个就业问题就解决不了。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处在这个十字路口。就业很严重,到底怎么去解决它?一个思路就是政府直接面对工人,政府承担越来越重的义务,开各种各样的支票,或者走入福利国家的这条路线。还有一条路线,政府提供体制改革的环境,让更多有竞争力的企业产生,把更多原来垄断不准进入的行业对市场开放,让这个市场产生更多的机会。让我们不断形成的劳动力在这里获得收入,变成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最后应该讲一句话,就是这个时间并不长。因为这几年你看劳动力的这个供给数字,这几年都是低峰。因为这几年有一个人口的大的周期,三年自然灾害以后那个人口大爆炸,其中第一代大概应该成为劳动力。1963年生的孩子,成为劳动力应该在十八、十九年以后。他们再结婚,再生孩子,现在大概再有两三年后,我们估计是2001年,中国会有一个新的劳动力供给的一个峰。这两年都是在低谷里,所以labour在低谷上我们的就业已经严重到这个程度,我的判断,如果这个体制,特别是依靠地方政府以经济体制政策为主导的这个就业政策如果再不形成,那就会酿成很大的全国性的经济问题。这是一个判断,到底怎么样可密切观察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