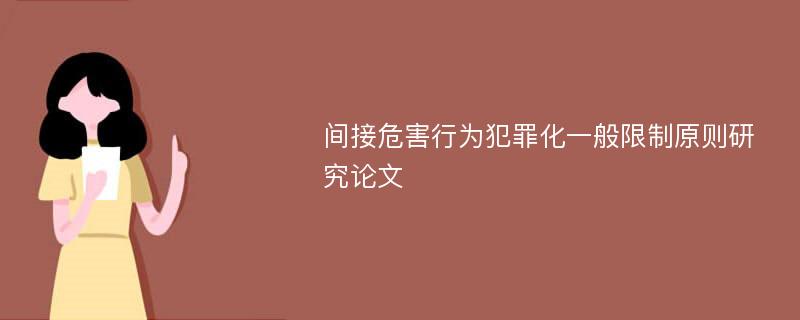
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一般限制原则研究
姜 敏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重庆401120)
摘要: 积极预防性立法以先发制人之策略,把与严重实害结果有距离的间接危害行为予以犯罪化。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虽突破了传统刑法理念,但其能严密实体刑法法网,对安全维护具有积极意义。其若不受限制和约束,会导致刑法无原则膨胀,继而诱发不公平归责和法治危机。立法机关将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其实质是让该行为人分担部分实害结果犯罪之刑事责任。立意于此的责任分配,不能违背刑事责任公平分配原则。因此,间接危害行为分担的责任,应是其本身应当承担的。尽管三大类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必须直面的问题不同,但基于公平归责和法治精神,其犯罪化均应受到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行为本身具有不法性、预防的必须是重大危害和与拟阻止的严重犯罪具有规范性联系等一般原则的限制。
关键词: 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规范联系;公平归责
我国刑法学界通常以风险行为、风险刑法等术语,分析没有实害结果的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但因风险行为术语本身并非一个纯正的刑法概念,而且其具有有益和有害的两面性,这决定了反对论和支持论似乎均有道理的局面。在英美法系国家,立法者以标准危害原则为根据,建立了刑法的核心犯罪体系。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于危险驾驶行为和持有行为等没有实害结果的行为,英美法系学者创造了间接危害行为的概念。① 参见姜敏:《英美刑法中的“危害原则”研究——兼与“社会危害性”比较》,《比较法研究》2016年第4期。 有学者认为,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是对危害原则的挑战,也有学者认为其是对危害原则的发展。无论哪一方,都是围绕着间接危害这一纯正的刑法概念探讨的,所以争点更为集中。从风险行为和间接危害行为自身的概念及对两者进行的比较来看,间接危害行为不具有两面性,并与危害原则紧密联系。因此,本文尝试引入间接危害行为这一概念,分析对没有实害结果且距离实害结果有一定距离之行为的犯罪化,这也许能消解风险行为、风险刑法理论的诸多分歧。
一、间接危害行为概念及其与关联概念的区别
要真正明白间接危害行为诱发的法治危机,其关键必须从间接危害行为的概念界定入手。提出或使用间接危害行为的英美法系学者,对其进行了界定。另外,如前所述,基于当代风险社会背景和风险刑法观,在研讨惩罚没有造成实害结果行为之犯罪化时,是以风险行为或危险行为为切入点的。因此,还有必要对间接危害行为与风险行为或危险行为予以区别,据此进一步研判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限制,才更具有针对性。
探伤中发现某一缺陷波,它所反射的声压值只能人为地与某一标准长横孔相比较[3-5],而决不是说这个缺陷的实际尺寸就是这样大,而它只能说相当于多大直径的长横孔[6-9].所谓当量缺陷的大小乃是相当于标准反射体的尺寸的大小,而并非缺陷的实际尺寸的大小.
(一)间接危害行为概念界定
1.安德鲁·阿什沃斯的“机会创设论”
安德鲁·阿什沃斯认为:“间接危害行为是指本身不具有过错和危害,但为最终导致严重危害结果创造了机会的行为。”② Andrew Ashworth,Principles of Criminal Law 49(5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根据阿什沃斯的“机会创设论”,间接危害行为为最终实害结果的出现创造了机会。因此,考察某些持有枪支和毒品的行为,虽然持有行为本身没有危害,而且行为人也没有征表出将要实施犯罪的主观心态,但持有这些物品的行为却为实施严重犯罪提供了机会或平台。同样,某些中立的帮助行为等,也为犯罪提供了机会。虽然中立的帮助行为人本身没有要实施严重犯罪的动机或主观心态,但其帮助行为属于间接危害行为。从阿什沃斯的该界定看,没有明确阐述间接危害行为就是风险行为。
其次,目前磁共振设备硬件和开发的软件技术仍有一定限度,需要不断开发如磁场补偿匀场,采用自旋回波序列,脊柱前方空间饱和,呼吸及心电门控,相位编码方向改变,运动补偿梯度等用来减少运动伪影及改善成像质量[13-14]。使用较低的扩散加权及较短的回波时间(TE)的优势,因此增加信噪比,较高的b值(>1 000 s/mm2)为区分受限扩散的程度提供了更高的灵敏度,但仍需要在扩散敏感度和信噪比之间找到平衡。
安德鲁·冯·赫希的定义则明确认为间接危害行为就是风险行为:“间接危害行为是涉及多种偶然性因素的风险行为。”③ Andrew Von Hirsch,Extending the Harm Principle:“Remote”Harms and Fair Imputation,in A.P.Simester&A.T.H.Smith(ed)Harm and Culpability,1996,P.263. 间接危害(remote harm)中的remote本意是指距离实害结果有一定时空距离,但赫希认为当把remote和harm联系起来时,remote不是指时空距离。之所以认为remote是间接的,是从其可能导致实害结果发生的角度分析的。④ Andrew Von Hirsch,Extending the Harm Principle:“Remote”Harms and Fair Imputation,in A.P.Simester&A.T.H.Smith(ed)Harm and Culpability,1996,P.263. 很显然,赫希认为间接危害就是风险行为,其持“风险行为”论。
3.丹尼斯·贝克的“诱因论”
丹尼斯·贝克对间接危害行为的界定是:“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具有危害,但事实上诱使其他独立主体实施具有危害性的犯罪行为,则该行为是间接危害行为。”⑤ Dennis J.Baker.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New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2007(03),P.370. 从该定义分析看,贝克虽然认为间接危害行为不具有实害,但把间接危害行为视为实害结果的诱因行为。贝克对间接危害行为的定义进行界定后,还举例进行了阐述:当X这一无害行为导致Y决定实施犯罪行为时,X便是间接危害行为;X与直接的(主要的)危害之间只是存在间接的联系,因为对其引起的而由Y独立选择实施犯罪的决定而言,只是偶然因素。其还举例:当X给Y一张传单,Y基于自己独立的选择将该传单扔到大街上而污染了环境。X的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就是间接危害,因为对环境污染这种直接危害的导致,是取决于Y随意丢弃垃圾的自由选择,但X的派发传单本身是无害的。⑥ Dennis J.Baker.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New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2007(03),P.372.
设置抽象危险犯把某种危险行为予以犯罪化,就面临这种质疑。以危险驾驶行为入罪为例,一般而言,某些危险驾驶行为确实会导致严重危害后果,且其本身也具有高度危险性。因此,从宏观上看,把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然而,具体到某个犯罪,则并不必然如此。比如,虽然行为人十分清楚街道上空寂无人,喝酒之后在该空无一人的街道上驾车,或者行为人自己酒量特别好,喝酒之后仍然如同正常人一样开车,但是根据刑法规定,行为人的行为还是会受到惩罚。设置抽象危险犯的立法,担心的是风险,且这种风险通常并没有规定在法条中。换言之,法律只规定禁止达到特定血液酒精浓度的驾驶员的驾车行为,并推定其具有应被禁止的风险,无需在法条中明文规定是否具有某种风险。也就是说,有些国家的立法机关在设置抽象危险犯时,会把刑事责任施加于一些可能不具有危险的行为,由于某些行为人实施该类行为可能危及他人,因此,立法机关仍然把该类行为予以禁止。冯·赫希以瑞典为例,对此进行了阐述:瑞典对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相当低的驾车行为予以禁止(即0.2 pro mil或以上),大多数人在这种酒精浓度下仍然能够非常安全地驾驶,只有极少数酒量不好的人不能正常驾驶,但是,为了避免少数人不致危及他人,该国立法机关还是设置此罪,禁止公民从事这种危险程度相当低的行为。⑤ Andrew Von Hirsch,Extending the Harm Principle:“Remote”Harms and Fair Imputation,in A.P.Simester&A.T.H.Smith(ed)Harm and Culpability,1996,P.263~264. 一旦该类犯罪被设置,则适用于所有人,即使某些人实施这些行为根本不会产生任何危险,但也予以禁止。对于这些人,刑罚的施加就是殃及无辜。因此,对于这种行为的犯罪化,必须有足够的理由证成其正当性,否则也是对法治精神的侵害。
(二)间接危害行为与风险行为及危险行为的区别
间接危害行为被一些学者界定为没有造成实害结果的风险行为,但并不意味着间接危害行为和风险行为可以等同。⑦ 参见姜敏:《危险驾驶行为犯罪化研究——从间接危害行为的视角》,《现代法学》2016年第6期。 间接危害(remote harm)中的“harm”的英文含义是:“injury,loss,damage,material or tangible detriment(伤害、损失、毁坏,物质的或具体的毁坏)。”⑧ Bryan A.Garner(ed),Black’s Law Dictionary(9th edition),Thomason Business,1999,P.784. 从解释看,其都带有恶害性。权威的汉语词典对“危害”的解释是:“损害,使受破坏。”⑨ 《新华汉语词典》编委会:《新华汉语词典》(第1版),湖北长江出版集团崇文书局2006年版,第911页。 所以从翻译的中文意思看,也带有恶害性。因此,无论是“harm principle”(危害原则)和“remote harm”(间接危害)中的“harm”(危害),还是翻译的“危害”,其基本含义都是“使受破坏,损害”。因此,间接危害行为不具有两面性,没有“利”的一面,其中的“危害”不具有可容忍性。风险行为中的“风险”,在英语中的表达是“risk”。无论是中文“风险”还是英文“risk”,都仅仅意味着可能性。如权威汉语词典对“风险”的解释是:“有可能发生的危险。”⑩ 同上注,第246页。 权威的英语词典对“risk”的解释是:“the uncertainty of a result,happening,or loss;the chance of injury,damage,or loss(某种结果、发生或损失的不确定;伤害、损害或损失的机会)。”① Bryan A.Garner(ed),Black’s Law Dictionary(9th edition),Thomason Business,1999,P.144. 因此,风险意味着某种结果的可能性,当然也包括某种伤害、破坏或损失的可能性。这也就意味着风险行为有两面性——损害的一面和无损害的一面。其无损害的这一面还意味着其可能是有“利”的一面。既然风险行为具有两面性,那么有些风险行为就具有可容忍性。特别是作为概率或者可能性的风险与利益关联时,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容许其存在。
从立法实践看,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的典型情况包括的事实有:(1)被犯罪化的当前行为是V行为——间接危害行为;(2)立法机关推断或以经验判断,V行为能创设或者帮助创设某种可能导致最终严重危害后果的不可接受风险;(3)刑法规定的主观罪过仅是行为人针对当前实施的V行为的故意,行为人对V行为是否可能会引起最终实害结果,可能不明知;(4)行为V与最终实害结果犯罪有一段“距离”;(5)行为V与实害结果并不必然具有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会被切断。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对上述情况的包含,就会引发质疑:(1)没有实害结果的V行为,为什么被犯罪化?其被犯罪化的正当根据是什么?(2)立法机关的推断和检验判断是否可靠?并且,多大危险才可入刑?(3)行为人为什么应对其无意识的实害结果分担责任?(4)其中的“距离”到底应是多远?立法可以无限延展吗?(5)因果关系如果切断,则行为人不应对后续结果承担责任,但立法依然把行为人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则意味着必然被分担责任。因果关系切断还被分配责任,是否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间接危害与风险行为两者的范围大小有区别。间接危害行为是具有“害”这一面的风险行为,其“害”的内涵便是“危险性”。换言之,风险行为的范围大于间接危害行为的范围,后者只是具有高度“危险性”的风险行为。“危险是一种根据科学视角和社会大众的一般生活经验认为刑法所保护的法益处于负面的、可能会遭到破坏的危急状态。”② 胡彦涛:《风险刑法的理论错位》,《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 正因为这个缘故,刑法将其犯罪化从而打击和抑制其“危险性”。当某种行为被视为具有“危险性”时,则意味着该行为不具有“利”的价值而只有负价值。比如,站在陡壁悬崖上的行为,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这种行为只有“害”并无“利”。因此缘故,有学者在区分危险行为与风险行为时,把危险行为视为没有“社会利益盈余”的风险行为。③ 参见梁宾:《危险驾驶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风险行为仅是具有“害”之可能性的行为,但其本身并不一定就具有“危险性”。比如经济领域的投资行为,可被视为风险行为,但其本身并不必然具有“危险性”,因其还具有“利”的性质或说是有“社会利益盈余”的行为。因此,正当的投资行为显然不应考虑是否应被纳入刑法规制的问题,把其称为危险行为也难以接受。换言之,某行为是风险行为,不意味着该行为就应入罪。甚至从某种意义看,风险行为具有高价值,比如前述提及的商业投资行为,所以有学者认为风险行为并非人们谈之色变的恶魔,恰恰相反,风险是获取更高安全标准的钥匙。④ 同前注②,胡彦涛文。 简言之,间接危害行为是风险行为中的仅剩下“危险性”且没有“社会利益盈余”的那部分行为,其范围小于风险行为。
2.安德鲁·冯·赫希的“风险行为”论
风险行为与间接危害行为虽有联系,但不宜互相替用。在刑法学界,因“风险刑法”概念的出现,使风险行为几乎成了学者们的口头语,无处不在,随时可用,甚至到了滥用或混用的境地。日本有学者分析了“风险”的一般使用场合:“如果检索日语中的报刊用语,会发现‘风险’一词经常在经济与商务(金融、投资、保险等)中使用。并且在表示企业及个人的经济的危害可能性方面占据了绝大多数,但在环境问题上基本不采用该词。”⑤ 甲斐克则:《刑法におけるリスクと危険性の区別》,法政理論,2013(第4号)。 从这个现象看,风险一词多用于经济领域。所以如前所述,投资可视为风险行为,但一般很难接受把站在险崖峭壁的行为称为风险行为。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间接危害行为和风险行为是有联系的。从时间上看,风险行为分为风险创设行为和风险现实化行为。因此,如果某种风险行为不是“有利”可能性的风险行为,而是“有害”可能性的风险行为,则其“害”之实现并不总是一步到位,而是有个发展过程,即从风险到实害的发展过程。从这个过程看,间接危害行为是具有“害”之风险行为的“害”的进一步现实化行为。据此,间接危害行为和风险行为的联系可以更精确地表述为:间接危害行为是有害风险的现实化行为,即风险已转变为危险。所以可以说风险是概率性概念,而间接危害是有害风险的现实化概念。只不过这种现实化程度,与实质危害对行为之风险的现实化相比,具有程度上的区别。亦正因为如此,间接危害行为和风险行为虽然具有联系,但仍有巨大差别。
如前所述,间接危害行为是具有危险性的那部分风险行为,因此,还需要追问:当把间接危害行为视为危险性行为时,是否可用危险性行为替代间接危害行为?毫无疑问,危险性是间接危害行为的特征,如要将两者互相替代就不是很妥当。首先,间接危害行为是英美学者,比如冯.赫希等,提出的一个学术概念,而危险行为仅是这类行为的特征,不应用概念的特征替代概念。其次,间接危害行为衍生于危害原则,从渊源上看,用“危害”(harm)比用“危险”(danger)更能体现其与危害原则(harm principle)的渊源关系。最后,间接危害(remote/indirect harm)中的“remote/indirect”是与标准危害原则中的直接危害(direct harm)或最终危害(ultimate harm)相对应,其直观且形象地描述了该类仅具有危险性的行为与最终实害结果的距离、与最终实害结果的关系以及对最终实害结果的加功的大小。总之,不宜用危险性行为代替间接危害行为。
“我们的策略就是熬,有风险的产品不敢碰,高投入的行业都不做。”张华说,公司处于半停半开的状态,有了流动资金才敢考虑开工投入下一批项目。
二、间接危害行为的类型及各自犯罪化应直面的问题
间接危害行为虽然是没有实害结果的行为,但不同的间接危害行为有不同的特点,且有较大差异。比如,前述提及的危险驾驶行为和持有行为,就属于不同的类型,同时,不同类型的间接危害行为,其犯罪化会直面不同的问题和质疑。
(一)间接危害行为的类型
冯·赫希对间接危害行为的分类,具有代表性。对于第一种情况,赫希仅把其限于抽象危险行为。实际上,具体危险行为也是没有实际危害的高危险行为,也是间接危害行为。因此,笔者认为,第一类间接危害行为应扩大至危险行为。从立法实践看,立法把没有造成实害结果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大致可以归入上述三类情况。比如,我国刑法中的危险驾驶罪,就属于第一种情况。持有型犯罪、预备型犯罪、帮助型犯罪和成员身份型犯罪等,属于第二种情况。德国《刑法》第324条第1款规定的“水污染犯罪”和我国《刑法》第338条规定的污染环境罪,属于第三种情况。虽然累积犯一般是在生态环境犯罪中存在,但学者对累积犯的适用范围做出了实质性拓展。特别是德国学者黑芬戴尔(Hefendehl),主张把累积犯适用于对制度信赖法益的保护。因此,某些保护制度信赖法益的犯罪,比如,保障货币的流通功能与公共信用的伪造货币罪以及保护资本市场正常运行的内幕交易罪,都是累积犯,⑧ 参见张志钢:《论累积犯的法理——以污染环境罪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2期。 也属于第三种情况。无论上述三类间接危害行为有何区别,其犯罪化对于控制风险和维护安全,均具有积极意义。
安德鲁·冯·赫希不仅对间接危害行为进行了界定,同时还进一步列举了间接危害行为的类型。⑥ See Andrew Von Hirsch,Extending the Harm Principle:“Remote”Harms and Fair Imputation,in A.P.Simester&A.T.H.Smith(ed)Harm and Culpability,1996,PP.263~265. 具体而言,间接危害行为大致包括以下三类。第一类是抽象危险行为(抽象危险犯),如醉酒驾驶行为。第二类是需要进一步介入性行为才会创设危险或严重后果的行为。基于对严重危害后果风险的担忧,立法者认为某些行为本身不会产生危害后果,但被会通过行为人自身或第三者的进一步行为,诱发或导致严重危害或危害风险,比如持有行为。第三类是联结型/累积型危害行为。该类行为在英语中的表达有两种,即联结型危害(conjunctive harm)和累积型危害(accumulative harm)。该两种表达均是赫希在不同的著述中使用的术语,且指的是同一内容。⑦ Andrew Von Hirsch,Extending the Harm Principle:“Remote”Harms and Fair Imputation,in A.P.Simester&A.T.H.Smith(ed)Harm and Culpability,1996,P.265;A.P.Simester&Andrew Von Hirsch,crimes,harms,and wrongs—on the principles of criminalization,Hart Publishing,2011,P.59. 无论用语如何有差异,均指的是某些风险只有与其他人的类似行为相结合或累积时,该行为才会造成令人担心的严重危害。比如,向河流中倾倒生活垃圾,被视为会对健康造成危害的风险行为,但只有当许多其他人也这样做的时候,该行为才会实际上危害健康。在这种情况下,被禁止的行为只是累积性危害行为的一个代表。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谋划了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宏伟蓝图,开启了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江苏教育系统将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大会部署要求,坚持改革创新,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努力写好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奋进之笔”。
(二)基于公平归责,三类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必须直面的问题
哀莫大于心死,孟导现在眼里全然没有了桌上那堆‘乾隆通宝’,就像是看到不成器的大儿子一样视而不见。他一边用手把‘乾隆通宝’们拨到桌子的另一侧,一边把目光集中到“次子”——数量更多的一堆古钱币。
在立法实践中,虽然有必要且应把某些间接危害行为予以犯罪化,但因上述问题和质疑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而诱发了下文论及的法治危机。当然,尽管前述三类间接危害行为都是没有实害结果的行为,但除此共性外,它们还是有极大差别的,因此,它们各自直面的问题也不同。无论是哪种类型,其犯罪化均是为了避免严重危害后果,如果其他问题的解决能使其避免法治危机,则上述第二类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具有正当性。除此之外,对于第一类行为,危险行为的犯罪化还包括了上述第二类事实。因此,该类行为的犯罪化,必须准确回答多大危险的行为才应入罪,以及立法机关的推定或经验判断是否可靠?也就是说,这类情况不会引起因果关系或罪责自负等原则的检视。对于该类情况所涉及的问题,如下文论及的,通过危害原则标准分析,就可以限缩其犯罪化,保证其正当性。第二类情况和第三类情况,则几乎包括典型情况中的所有事实要素,因此,如果不受到限制,则会引起更多理论讨伐,比如违背刑法谦抑原则和罪责自负原则等。该两类行为的犯罪化,除了直面第一类行为犯罪化必须直面的问题外,还应直面因果关系问题、规范问题和罪责自负问题等。对于该两类情况,单凭危害原则标准分析方式难以解决,还必须寻找其他路径,保证其分配责任的公正性。概言之,在实然层面上,正因为当前很多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没有遵循刑法原则对其进行指导和限制,所以也就没有解决上述论及的这些问题,导致其犯罪化不符合法治精神。
三、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对于传统刑法的改变
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立法,是积极预防观的体现,虽有前述的问题等待解决,但在司法实践中,其已在实然上突破了传统刑法的格局,并导致刑法理念的转变。为了更好地理解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也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是如何诱发法治危机的,有必要梳理其犯罪化对刑法的改变。
为更好地立体化宣贯,行动开展以来,广东海事局各分支局积极履职,营造良好的宣传氛围。佛山海事局牵头编制了《西江流域风险防控手册》,实现西江沿江六局风险防控标准化。肇庆海事局牵头编制并印发了《西江船舶污染物处置须知手册》5000余册,大力开展水上防污知识宣传教育,防止船舶污染西江。江门海事局牵头编制了《船舶附属艇安全管理指南》,及时向航运公司和船员大力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对附属艇驾乘人员随艇降落、不穿救生衣等违反安全规定行为进行提醒。中山海事局牵头编制了《西江水域船舶安全航行指南》,研究西江船舶通航环境、规章制度,梳理西江流域通航要素,为船员提供安全航行指引。
(一)改变了刑法的打击目标,使设置的罪名没有实害结果
传统刑法立法是把实害结果和行为联结在一起的,但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立法,导致“刑罚的干预包含了距离实害结果较为遥远的侵害行为,使得‘行为’与‘危害结果’间出现了分离”。⑨ Bernard E.Harcout,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90 J.Crim.L.&Criminology,1999,p.109. 其直接的后果就是:间接危害行为成为刑法的打击目标。间接危害行为成为刑法的打击目标,征表的是要在尽可能多的情形下,监控和控制犯罪风险,事前切断危害结果发生的路径。正是这种超前预防,重塑了潜存于刑法体系下的打击目标,⑩ 参见姜敏:《刑法反恐立法的边界研究》,《政法论坛》2017年第5期。 即惩罚的对象不是实害结果行为,而是可能导致或诱发实害结果的行为,比如持有行为和危险行为等。虽然其逻辑根据是犯罪的暴力和无序是通过可预测的、不断发生的行为实现的,但这种行为的发生是与社会性的、精神的甚至生物的诱发性变量因素有关联的。不仅如此,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理论和立法认为微小危害或风险行为,甚至无害行为,也能反映个体的危险性格,因此,为了阻止严重后果发生,立法者便把这些行为予以禁止。立法的这种逻辑根据,意味着立法者重视人类行为与某种事态的关联性,期冀通过对某种行为的禁止而切断某种事态发生的路径。由此产生的结果就是:设置的罪名没有实害结果。这样,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突破了传统刑法惩罚实害结果的范式。
(二)侧重推定或经验预测风险有无,弱化或消弭针对实害结果的主观要件
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产生的罪名,不仅没有实害结果,而且弱化或消弭了针对实害结果的主观要件。积极预防立法观是一种事前预防观,侧重于对客观世界的保护,对严重后果的避免。这种立法重在塑造个体的行为,阻止个体实施可能会引起严重后果的行为,同时,又因为其认知的风险或危险是推定的或经验上的,立法就缺乏对行为人针对实害结果的主观罪过的关注。因此,如前所述,在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中,并不关心行为人对实害结果是否有认识,只考证行为人对间接危害行为是否有罪过。与之相反,传统刑法秉承消极预防观,侧重事后预防,且一般是以刑罚的当罚、报应和道德罪责为基础的,且借助于心理强制,寄希望于刑罚威慑阻止犯罪人再犯或潜在的犯罪人重蹈覆辙。因此,其更关注行为人的道德可罚性,关注行为人针对实害结果的主观罪过。基于此转变,实施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后的立法设置的罪名,其道德可罚性轻于传统刑法的核心犯罪。
课的最后,介绍了各种量角工具,甚至是有别于量角工具但又与角有关的经纬度,意在给学生开拓眼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被惩罚之行为的不法程度降低甚至缺乏
因传统刑法立法侧重报应,故其不仅重视实害结果和行为人对实害结果的主观罪过,而且重视行为本身的不法。不仅如此,传统刑法惩罚的行为之不法性还非常严重。比如,故意杀人行为和抢劫行为,其行为的不法性程度就非常严重。以间接危害行为之名进行犯罪化时,立法者以推定或经验上的风险为根据,把某些不具有不法但被立法者视为可能诱发某种犯罪风险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比如,贝克列举的某些国家对被动乞讨行为的犯罪化,① Dennis J.Baker.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New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2007(03),P.370. 就是这种情况。基于“破窗理论”,立法者认为被动乞讨行为会诱发社会混乱或其他犯罪,所以其应被犯罪化。然而从实质看,被动乞讨行为仅可被列为不文明行为,不具有不法性。同样,越轨行为、禁忌行为、日常生活行为、“微害”较小的行为,甚至“无害”行为,被视为是风险行为或更严重犯罪的逻辑先导,从而被犯罪化。因此,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如果不受限制,就会导致刑法无限扩张,并使其惩罚之行为的不法性极低或缺乏。
12月24日,国旅公告拟将全资子公司国旅总社100%股权转给控股股东中国旅游集团,转让价格18.3亿元,以现金形式一次性付清。中国国旅目前免税和旅行社双线并行,此次剥离旅行社业务有助公司和集团理清资产,解决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让上市公司聚焦免税主业,同时集团取得旅行社资产后也有助于做大做强,与免税业务相互引流。
(四)赋予刑法新功能并改变刑法预防犯罪的实现方式
犯罪化间接危害行为,既征表社会生态演化语境下危害原则面临的挑战,② 参见前注①,姜敏文。 又征表社会的发展赋予了刑法新功能。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是对内在于工业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的回应,因此,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虽导致了刑法制度设计的转变,但也是社会外部环境与刑法知识形态互动的结果。实际上,这种制度设计的转变,赋予了刑法风险管理这一新功能,并让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③ 参见周光权:《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 在传统刑法理念中,刑法应通过事后打击的方式威慑犯罪,然而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重构了刑法目的之实现方式,即由威慑转向超前预防。虽然威慑实质也是传统刑法中的预防理论模型,但超前切断实害结果出现的预防理论模型,与之有巨大差异。超前预防犯罪理论模型,是企图在尽可能多的情形下监控和控制犯罪风险,事前切断危害结果发生的路径,所以,这种预防犯罪的理论模型,侧重的是事前防御。
从唯物主义立场看,刑法的存在、发展和演化必然依附于一段具体的历史时空和特定的社会结构,同时,社会变迁铸就某种历史图景,历史图景铸就的语境也影响刑法立法及刑法的发展。因此,任何刑法理论、理念或原则均要受到社会发展和变化的影响,并随之发展且与之相适应。风险社会与犯罪高频发生的迭加,迫使刑法犯罪化间接危害行为,以期维护安全。任何事情均会过犹不及,同样,如果刑法立法把距离实害结果极为遥远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则会陷入法治危机。
四、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诱发的法治困境
任何一个国家、社会或个体,均希望预防犯罪,因此,从宏观角度看,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的初衷并不应被诟病。然而,从具体设罪的微观维度看,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把设罪规范位置移到最终实害结果行为之前,甚至更远的位置,导致对刑事责任分配不公或不当,使其被质疑和诟病。
经研究,矿区矿(化)体矿化富集具有一定规律性:(构造)蚀变石英脉型钼矿(化)体矿化相对较好、钼品位较高。浸染状矿化不均匀,矿化主要集中于薄石英脉及与围岩接触带上,钼矿品位相对较低。同一矿(化)体中,黄铁矿化较强的部位,一般钼矿化较好、钼品位较高,反之则钼品位相对低。沿矿体走向,矿(化)体迅速膨大部位,一般钼矿化就好,钼品位相对较高。沿矿体倾向,矿(化)体产状发生扭曲部位,易形成钼富矿段。在构造交汇叠加位置,易形成钼富矿段。
(一)轻微不法,不文明的行为或日常生活行为被惩罚
刑法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刑罚的施加也仅能针对具有严重不法行为或严重后果的情况,因此,轻微不法或日常生活行为入刑法,违背刑法的最后手段原则和谦抑原则。如前所述,该行为是否具有风险,是由立法机关予以推定的。基于防范风险,立法者如格外保守,则会把诸多行为推定为风险行为,进而把其犯罪化。贝克教授在举例反对某些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时,就举到了轻微不文明的“被动乞讨行为”犯罪化的例子。根据“破窗理论”,立法者把被动乞讨行为视为诱发更多严重犯罪的先兆——被动乞讨的行为给其他不法分子传递该被破坏的领域是无人监管的领域的讯息,从而使之更容易成为犯罪的目标。因此,为了防止其他独立主体在该被破坏的领域实施犯罪,被动行乞行为被犯罪化。④ Dennis J.Baker,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New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2007(03),P.370. 一般而言,被动乞讨行为仅是轻微不文明行为,甚至不具有不法性。在某些情况下,被动乞讨行为甚至是公民唯一的谋生行为。因此,不应被犯罪化。同样,我国刑法修正案将“缠访”行为入罪,也与此类同。“缠访”行为本身并没有直接危害后果,仅是轻微不法行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缠访”行为是权利被侵犯公民走投无路的表现,它是一种正当的维权行为。然而立法者基于“破窗理论”的潜在思维,害怕该类行为会酿成重大的管理秩序混乱局面,因而将其入罪。对于“缠访”行为,无需动用刑法——改善公民权利受到侵害后获得救助的机制,增加公民维权的方式,提高司法等裁判机制的公信力等,就可解决公民的“缠访”问题。对于贝克论及的被动乞讨行为而言,其仅是主流社会所谓的不文明行为,本身并不具有不法性,本身就不应被刑法规制。因此,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如果不受限制,就会导致其违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和谦抑原则。
(二)设罪不当而致惩罚过度,殃及无辜行为
从上述界定看,学者对间接危害行为的界定是有区别的。然而,无论学者的界定有何区别,有一个共识却不容置疑,即间接危害行为是没有实害结果的行为。根据间接危害行为概念、共识性特征以及实践中的犯罪化情况看,间接危害行为确实有不同样态。正因为其样态不同,离实害结果的距离不同等,导致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后生成的罪名不同,因此,其诱发的法治危机也不同。
(三)让初始行为者对自己或第三人将来之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冯·赫希分类中的第二类,即“需要进一步介入性行为才会创设危险或严重后果的行为之犯罪化”就属于这种情况。持有型犯罪是其中的典型,比如,某人为了防身而持有枪支,自身并没有犯罪的故意,也没有为第三人提供枪支予以犯罪的故意。就其持有枪支本身的现状而言,仅可能是为自己或他人将来使用枪支犯罪,无意识地构建了一个“平台”。根据现有刑法规定,其仍然会被惩罚。实际上,立法机关之所以将这种行为予以犯罪化,是担心随后的介入因素导致严重犯罪。然而,随后的介入性因素,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可能发生。比如,大多数持有枪支的人不会滥用枪支,行为人自身并不必然会有进一步介入性行为。同样,第三者是否会有进一步的介入性行为,也并不确定。从实践经验看,介入性因素确实会偶然发生。因此,立法者基于预防将来发生严重后果,便把持有枪支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实际上,这是让持有者对自己或第三者将来的行为分担刑事责任。然而,当行为人并没有后续实施犯罪或者为第三者提供帮助的故意时,该责任并不应由行为人承担,因后续的行为才是实害结果产生的决定性因素,其切断了因果关系。因此,这类犯罪化违背罪责自负原则。
(四)累积犯立法无法在各个累积危害行为之间划清道德界限
对累积危害行为的犯罪化,产生的是累积犯。从前述冯·赫希对累积危害行为的描述看,单独的累积危害行为不会产生实质危害,也不具有造成实质危害结果的可能。比如,单独的公民个体向河流倾倒一次污水的行为,并不会导致河流被污染的严重后果。如果不禁止该类行为,公众却又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现实中有诸多类似的行为,其累积会对河流造成严重的污染。因此,立法者基于避免河流被严重污染,对这类行为予以犯罪化。这种行为之所以被犯罪化,主要在于其与其他人的类似行为累积,便会产生累积效应,即产生严重实害后果。从立法现状看,累积犯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式,并不是刑法立法设置的常态犯罪。一般而言,“累积犯集中于环境犯罪和经济犯罪领域。”⑥ 同前注⑧,张志钢文。 累积行为犯罪化,是刑法最为极端的扩张形式。⑦ 参见黎宏:《法益论的研究现状和展望》,《人民检察》2013年第7期。 因此,累积行为的犯罪化饱受质疑。比如,有学者认为处罚累积犯的“理论基础是脆弱的”。⑧ 姚贝、王拓:《法益保护前置化问题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1期。 也有学者认为对累积犯的惩罚,是集体责任的体现,违背罪责自负原则。⑨ 参见王永茜:《论现代刑法扩张的新手段——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和刑事处罚的前置化》,《法学杂志》2013年第6期。 姑且不论其是否属于集体责任,但就累积危害行为犯罪化而言,确实使行为人无法在自己的行为与促成该实质危害的其他人行为之间,划清道德界线。还需要澄清的一点是,该种情况必须有行为人自己或第三人的介入性行为,实质危害结果才会发生,与风险行为的犯罪化情况不同,对于后者,行为本身是不具有危害或危害风险的,其仍然被犯罪化主要是因为其被推测可能会引起或诱发自己或第三者实施进一步的危害行为;在累积性风险行为中,被犯罪化的行为本身具有一定的风险,但程度较轻,只有与其他人的类似行为结合,才可能产生实质性结果,因此,两者引发的主要问题也是不同的。
因存在上述法治困境,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遭遇反对和质疑。比如,丹尼斯·贝克质疑其“违背了公平和罪责自负原则的要求”。⑩ Dennis J.Baker.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New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2007(03),P.370. 伯纳德·E·哈考特对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也表示了担忧:“当危害原则的适用范围被扩大至包含更加间接的危害行为时,事情就改变了——因为我们所为的各种表面上看来清白无辜的行为,可能最终均会引起危害性后果。”① Bernard E.Harcourt,The Collapse of the Harm Principle,90 J.Crim.L.&Criminology,1999,p.105. 换言之,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会导致惩罚范畴无限扩大,殃及无辜。冯·赫希等对此也极为担忧:“当涉及到更加间接的风险时,使行为人对可能的有害结果承担责任,就变得更成问题。”② A.P.Simester&Andrew Von Hirsch,crimes,harms,and wrongs—on the principles of criminalization,Hart Publishing,2011,P.54. 无论理论如何质疑和担忧,立法实践是谨慎而义无反顾地把诸多间接危害行为予以了犯罪化。因此,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是成熟的犯罪化理论必须重视的客观事实,甚至其本身已是成熟的犯罪化理论的重要内容。实质上,学者担心的并不是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本身,也不是质疑其犯罪化的必要性,而是担心由此而产生的不公正。因此,真正具有实际意义的,便是探寻保证其犯罪化符合法治精神的路径,将其犯罪化限制在公平与法治的框架内。
五、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一般限制原则
任何行为的犯罪化,都必须有根据、守“规矩”,否则,启动刑罚权的犯罪化决策便会变得肆意而狂傲。这意味着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也必须受到限制,保证给其分配的刑事责任是其该当的。至少,应通过一般限制原则,把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限制在合理的框架内,避免其对法治精神的践踏。
(一)坚守“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
间接危害行为衍生于危害原则,其应践行危害原则的法哲学意义。要践行危害原则的法哲学意义,就必须铭记危害原则是划分刑法合理范畴的限制自由原则。为了使刑法对危害行为(包括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具有正当性,学者提出了“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实际上就是“范伯格范式”,其主要针对的是危害原则在面对某些棘手或疑难问题时,如何进行选择和决策。在范伯格的话语体系中,除了论及实害行为犯罪化外,也关涉到危害原则在实践中必须面对的一些反例,比如轻微危害、可能危害、合理及不合理危害风险、综合危害、可以阻止却须以过分损害其他利益为代价的危害、结构性冲突的危害、累积危害、模拟危害等情形——其中已包含间接危害行为。范伯格清醒地认识到,如果要让危害原则解决这些棘手和疑难问题,就必须借助于其他补充性原则对危害原则予以完善。范伯格以“调和准则”作为概括性术语,指代这些完善和补充危害原则的参考因素。③ 乔尔·范伯格:《刑法的道德限制》,方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10~211页。 “调和准则”主要包括危害的大小、危害发生的可能性、整体性危害、统计歧视与危害净减、危害的相对重要性、自由利益在天平上的位置等因素。④ 参见上注,乔尔·范伯格书,第210~239页。 因此,“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就是“危害原则+调和准则”范式。间接危害行为的论及者,均坚守了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冯·赫希在论及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时,把该标准分析范式分解为三步:“第一步考虑最终危害的严重程度及其可能性。严重程度与可能性越大,其犯罪化的可能性就越大。第二步权衡和评估没有犯罪化前行为的社会价值以及犯罪化将对行为人自由选择的侵犯程度。行为的社会价值越高,或者犯罪化产生的刑法禁令对自由的限制越大,则不应犯罪化的理由就越充分。第三步考量某些将会阻却犯罪化的边际约束。例如,禁令不应该侵犯隐私权或自由表达权。”⑤ A.P.Simester&Andrew Von Hirsch,crimes,harms,and wrongs—on the principles of criminalization,Hart Publishing,2011,P.55. 依靠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能解决某些类型的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问题,特别是危险行为的犯罪化问题。对于部分累积型危害行为是否应予以犯罪化的问题,根据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也能获得答案。比如,在公共场所高声吹唢呐的行为,如果汇聚人数众多,会造成公共秩序的混乱。其虽属于累积危害行为,但与向河流倾倒污水的行为不同。从经验和常识看,前者发生的危害结果可能性和频率均很低,后者却很高。因此,前者不应犯罪化,后者应被犯罪化。
除冯·赫希外,米歇尔·M·登普西在主张附条件地犯罪化间接危害行为时,也首先坚持了危害原则的标准分析范式。比如,登普西把教唆嫖娼视为间接危害行为,主张应附条件地将其犯罪化,并指出应首先遵循危害原则的标准分析范式,其次才以其他原则予以补充。⑥ Michelle M.Dempsey,Rethinking Wolfenden:Prostitute Use,Criminal Law,and Remote Harm,2005 Crim.L.R.449. 确实,附加了“调和准则”的危害原则及其内涵,不仅能解决实害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也能解决部分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问题。然而,危害原则及其“调和准则”主要是针对实害结果行为及部分危险或风险行为的犯罪化,并不是直接针对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因此,其并不能解决所有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问题。比如,“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难以解决持有行为的犯罪化问题,尤其是在面对为什么犯罪化持有枪支的行为,而不犯罪化持有刀具等行为的诘问时,更加显得捉襟见肘。具体言之,对如冯·赫希论及的“介入干预型”犯罪和某些累积型犯罪,单凭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是无法圆满解决问题的,还必须寻找其他的限制路径。
(二)被禁止的行为本身应具有不法性
被禁止的行为本身应具有不法性,源于刑法固有的可责罚性特征。刑法是一种复杂的、权威的和谴责性的手段,其通过犯罪化宣示某种行为是应受责备的不法行为。立法者将某行为犯罪化,就是对该行为不法的质的评价。⑦ 参见严明华、张少林、赵宁:《刑法分则条文罪状的理解与相应法定刑配置关系研究》,《政治与法律》2010年第12期。 然而行为之不法的质是指行为人有罪过地实施某行为,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从表现看,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客观上有危害或有危险,不应被容忍,而行为人主观上也具有罪过,应被责罚。因此,根据不法性要件,行为人无意中实施的某个风险行为,虽引起了严重后果,但不能把这种风险行为犯罪化。同样,从客观上看,行为人的行为本身是合法行为,或是可容忍行为,虽然具有诱发严重犯罪的可能,但亦不宜犯罪化。比如,销售菜刀的行为,如果销售者知道购买者购买菜刀之目的是为了杀人,仍然把菜刀销售给购买者,因销售菜刀是合法行为,即使把菜刀销售给购买者会助力于杀人行为,也不宜予以犯罪化。当然,在实践中,某些行为在客观方面的不法,并不是立即就征表出来的。其不法是在一定的过程中慢慢展现的。对于这种情况,就需要等到行为已征表出不法时,才应予以犯罪化。一般而言,客观行为要征表出不法性,行为人要有朝向实害结果的实质步骤,即只有行为人的主观意思和实施的行为已具有实质意义,导致行为人将来的选择不再对危害结果是否发生具有决定作用时,才可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具有不法。比如对持有菜刀、石头和木棒的行为,是否具有不法的判断就是如此。很显然,仅对这些物品持有本身,无论是从行为人主观视角看,还是从行为的危险性角度看,均不具备不法性,同时,这些行为本身并不能决定严重后果必然发生,相反,是行为人将来进一步的行为决定严重后果是否发生。因此,就当前的持有状态看,严重后果是否会发生具有极大的偶然性,对于这种状态下的对普通物品的持有,还不具有不法性,不应予以犯罪化。
同样是持有行为,为什么持有枪支的行为被犯罪化了,且在一定的文化语境下,还具有极高的认同度呢?持有枪支的行为,虽然也属于需要进一步的介入因素才可能导致严重后果的行为,行为人也没有征表出实施犯罪的故意和朝向严重危害的实质步骤,但与持有前述物品的行为相比,还是有不同。对于持有枪支这种行为,范伯格是把其放入“整体性危害”予以论证。按照经验推定,该类行为确实会产生有害结果,但实际本身还是无害的。在这种情况下,一律禁止尽管(可能)会消除或减少一般性损害,却要以阻止无害或有益行为作为代价。⑧ 参见前注③,乔尔·范伯格书,第217页。 其之所以在整体上被认为是有危险的,是因为有少数人会滥用某种自由。⑨ 参见前注③,乔尔·范伯格书,第221页。 持有枪支行为本身并不一定就有损害或损害风险,有些人可能会用持有的枪支实施犯罪,有些人持有枪支则是为了防身。因此,对于持有枪支到底是否予以刑法禁止,就会处于进退维谷中。最终其仍被犯罪化,是因持有枪支行为具有内在危险性,这种内在危险性使其具有不法性。从现实经验看,一把装有子弹的手枪确实很容易走火,且会让人身权利遭受严重侵害。对此情况,范伯格主张对具有内在危险性的行为“应予以禁止,而只对值得信任且有特殊需要的少数人予以特许”,即刑法以禁止或特许证的方式规制这种情况。⑩ 参见前注③,乔尔·范伯格书,第221页。 换言之,不一律允许,也不一律予以刑法禁止。即对于普通公民持有枪支的行为,因其具有内在危险性,予以刑法禁止,而对于特殊人群,比如猎人等,采用许可证的方式予以允许。
(三)阻止的最终危害必须是重大危害
刑法要把某类间接危害行为予以犯罪化,必然会限制行为人的部分自由。以限制自由的方式早期化干预公民没有实害结果的行为,阻止的最终危害必须是重大危害,才能使这种早期化干预具有正当性。该限制原则其实已包含在“危害原则标准分析范式”中,但当专门论述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时,有必要把其单独作为一个一般限制原理提出来,突出在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中,其具有重要性。很多学者在论及犯罪化时,均认为刑法阻止的最终危害应是重大危害。胡萨克认为国家让公民承担刑事责任,其原因必须在于阻止重大危害,且把该要件视为犯罪化的内部限制原则。① 参见胡萨克:《过罪化及刑法的限制》,姜敏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189页。 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是把不具有实害结果的行为予以犯罪化,因此,更应是为了阻止重大危害,才能使其犯罪化具有正当性。登普西在分析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时,也认为应考虑危害的严重性。其把引诱嫖娼行为视为间接危害行为,并认为其应被犯罪化,首先的原因便是其可能导致强奸罪的发生,而强奸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并且传统上刑法都将强奸的危害视为最严重的危害之一。因此,把引诱嫖娼行为犯罪化,符合阻止重大危害的旨意。基于此原理考察,把恐怖犯罪领域、公共安全犯罪领域、食品安全犯罪领域和国家安全犯罪领域的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也是有根据的。
(四)被禁止的间接危害行为,应与拟阻止的严重犯罪具有规范性联系
现代法治国家一般均应秉承罪责自负的原则,这要求应把刑事责任分配给应该承担之人。在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中,立法的旨意明显是因要避免最终危害结果,才将其犯罪化。因此,从实质意义上看,其分担的是最终实害结果行为的刑事责任。然而,间接危害行为为何应分担不是自己本身造成的最终实害结果的刑事责任呢?根据罪责自负原则,间接危害行为不应分担和其自身毫无关联的最终实害结果的刑事责任。即使要给某些间接危害行为分配刑事责任,其承担的也应是其本身就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即承担的是其自身对严重犯罪的“加功”作用所对应部分的刑事责任。这样的责任分配才是公平的,冯·赫希就认为:“应以行为人在危害风险创设中扮演的角色为根据,对行为人公平分配合作义务。”② Andrew Von Hirsch,Extending the Harm Principle:“Remote”Harms and Fair Imputation,in A.P.Simester&A.T.H.Smith(ed)Harm and Culpability,1996,P.269. 贝克也认为:“因为其他人的行为而被犯罪化,这在道德上是没有正当理由的,因为这忽略了每个人作为一个承担责任的、自主性的个体,具有的独立性。”③ Dennis J.Baker.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New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2007(03),P.372~373. 因此,对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还必须将其限于与后续严重犯罪具有牵连的情形之中。
然而,该牵连关系不是任何牵连关系,是规范性卷入关联关系。贝克明确提出,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必须符合规范性卷入要件,“只有当某人与其他人的犯罪行为,具有规范卷入关联关系时,才应该对其他人的犯罪行为承担责任”。④ Dennis J.Baker.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New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2007(03),P.370. 如前所述,虽贝克认为被动乞讨行为是间接危害行为,但反对其犯罪化,原因在于其与“破窗效应”没有规范性卷入关联关系,因此不应被犯罪化。有的学者则认为:“与破窗理论相反,轻微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与抢劫以外的犯罪行为之间,不存在必然的联系。”⑤ Robert J.Sampson,Stephen W.Raudenbush,&Felton Earls,Neighborhood and Violent Crime: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277 Sci.918(1997);Robert J.Sampson&Stephen W.Raudenbush,Systematic Social Observation of Public Spaces:A New Look at Disorder in Urban Neighborhoods,105 Am.J.Soc.603(1999). 贝克还通过剖析犯罪发生的原因,否定被动乞讨行为与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犯罪之间的经验因果关系,进一步否定规范性卷入关系的存在。“促使犯罪发生的因素,是社会结构的缺陷和集体效应的弱化,而不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⑥ Robert J.Sampson,Stephen W.Raudenbush,&Felton Earls,Neighborhood and Violent Crime:A Multilevel Study of Collective Efficacy,277 Sci.918(1997);Robert J.Sampson&Stephen W.Raudenbush,Systematic Social Observation of Public Spaces:A New Look at Disorder in Urban Neighborhoods,105 Am.J.Soc.638(1999). 贝克认为:“行为人实施的间接危害行为,只有在对直接实施犯罪者的后续犯罪选择,具有相当的归咎于他的谴责理由时,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⑦ Dennis J.Baker.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New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2007(03),P.372. “相当的归责理由”,当然包括规范性卷入这一要件。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明显体现的是功利主义,其被立法实践采纳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犯罪化可以降低整体的犯罪率。亦正因为其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所以受到理论界质疑。然而,贝克认为:“如果有足够的规范性理由,对该类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以追求功利,也是可容许的。”⑧ Dennis J.Baker.The moral limits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s,New Criminal Law Review(Summer),2007(03),P.373,note 6. 贝克支持的原因在于,当间接危害行为与最终严重后果犯罪有规范联系,那么对其归责便是公平的。换言之,某种间接危害行为与最终实害结果具有规范性卷入关联,意味着间接危害行为犯罪化的功利目的,是以报应为基础的——行为人对最终实害犯罪,具有指使、实施、预谋、计划或者积极鼓励的行为受到归责。因此,对其归责是该当的。
只是朝敏万万没想到,儿子也感染了周暄一身的江湖痞气,才小学四年级就经常在学校里欺负人,看谁不顺眼就捉弄谁,老师为了这事好几次来家访,希望他们能多多管教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规范性卷入关联关系,仅是一个概括性概念。就实践而言,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时,不同的间接危害行为类型,对最终实害的加功作用力或说因果力不同,且距离远近也不同,甚至主观罪责程度也不同,因此,其与最终实害结果的规范联系、方式和程度等也不同。然而,无论类型如何不同,规范性卷入关联关系,始终包括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因素。前者如“帮助”、“教唆”、“计划”和“鼓励”等行为,后者如“明知”和格伦威尔·威廉姆斯提出的“特定目的论”等。⑨ Glanville L.Williams,Complicity,Purpose and the Draft Code—1,1990 Crim.L.R.4,10(1990). 一般而言,在“帮助”、“煽动”或“教唆”他人实施犯罪中,如果要把“帮助”、“煽动”或“教唆”予以犯罪化,则行为人主观上应具有“明知”。在研判某些其他间接危害行为是否应予以犯罪化时,行为人在实施间接危害行为时,仅有明知是不充分的。比如,某种间接危害行为的发生,仅可能会“影响”后续的某些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行为人仅有“明知”是不够的。针对此种情况,威廉姆斯提出了“特定目的论”,即“在‘影响犯罪’的情形下,具有‘特定目的’是建立规范联系的非常重要的决定因素。仅仅因为行为人应当‘预见’其合法的间接行为对主要危害产生有影响,而对其进行谴责是不符合道德法则的。”⑩ Glanville L.Williams,Complicity,Purpose and the Draft Code—1,1990 Crim.L.R.4,10(1990). 贝克论证的被动乞讨行为,也属于这种情况。被动乞讨行为对他人犯罪有“影响”意义,但如果行为人在主观上仅仅只有“明知”,还不足以与他人犯罪建立规范上的联系。从被动乞讨者本身看,其不具有“特定目的”,其与后续可能的严重犯罪不能建立规范联系,不能予以犯罪化。当然,针对不同的间接危害行为,还有其他的规范卷入判断标准。这需要立法机关在把间接危害行为予以犯罪化时,找出恰当的规范卷入因素,把间接危害行为的犯罪化限制在公平归责的要求内。
On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Limiting Criminalization of Remote Harmful Acts
Jiang Min
Abstract: The positively preventive legislation,by taking the strategy of striking first to gain the initiative,criminalizes remote harmful acts that are distant from serious real harm.Although the criminalization of remote harmful acts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criminal law,it can enlarge the coverage of substantive criminal law,thus enjoying a positive significance in security maintenance.But if it is not limited and restrained,the criminal law will be expanded in an unprincipled manner,thus bringing out unfair imputation and a crisis of the rule of law.The essence of criminalizing remote harmful acts by the legislator is to let such actors undertake part of the criminal liability for the crime with real harm.The liability allocation based on this should not violate the principle of fair allocation of criminal liability.Therefore,the liability undertaken for remote harmful acts should be based on its own merits.Al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t issues confronted in criminalization of three categories of remote harm acts,on basis of fair imputation and the spirit of rule of law,such criminalization shall be limited by general principles such as the standard analysis model of the principle of harm,the illegality of the act itself,the seriousness of harm prevented,and the normative connection with the serious crimes to be prevented.
Keywords: Remote Harmful Acts;Criminalization;Normative Connection;Fair Imputation
中图分类号: DF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512(2019)05-0096-13
作者简介: 姜敏,西南政法大学外国与比较刑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法学博士。
(责任编辑:杜小丽)
标签:间接危害行为论文; 犯罪化论文; 规范联系论文; 公平归责论文;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