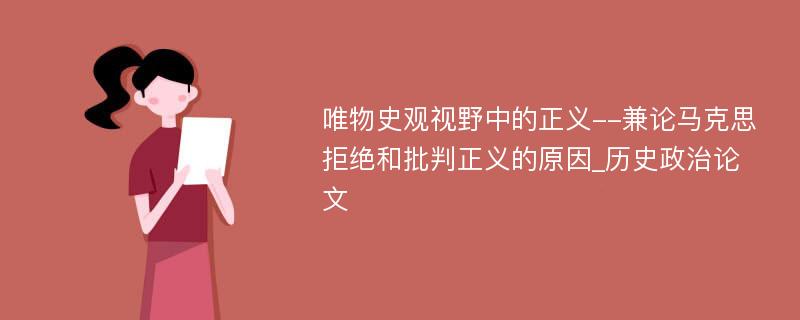
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的正义观——兼谈马克思何以拒斥、批判正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义论文,马克思论文,历史唯物主义论文,视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般而言,正义都会被当作具有积极意义或者说是某种体现为善的价值理想。然而正义在马克思成熟时期的作品中,却有着与这种流行观点几乎不同的境遇:正义并不是马克思诉求的对象,而是马克思拒斥、批判的对象。[1](P566);[2](P309);[3](P188);[4](P281)以伍德(Allen Wood)的说法是,“在他的著作中找不到任何清楚地阐述积极的权利或正义思想的真正努力”。[5](P390)对于这一事实,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解释,以波普的说法就是,马克思是心怀正义但又苦于“正义”为人所滥用的缘故才忌讳使用“正义”的。[6](P310、319)但是,如果考虑到马克思是一位严肃的学者,是“审慎”地对待正义,[5](P390)而不是出于一种情感的偏激和理论的“猎奇”的话,就有必要考虑马克思拒斥、批判正义极有可能是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到了正义的限度。而这一点正是笔者在此所要探讨的。
一、社会的真正基础和动力不是正义,而是社会的经济发展
在关于社会的真正基础和动力的认识上面,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论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在正义论者看来,正义是合乎人性的,是引导和提升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并且具有超越社会、历史的永恒价值,因而,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就在于倡导正义,推行正义。[1](P566);[7](P161)但对于马克思来说,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的要求,是从属于社会的经济发展的,社会进步的真正基础并不是正义,而是社会经济的发展。马克思认为,特定社会的经济状况往往规定了特定社会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作为社会经济状况的基本因素的社会生产更是具有基础性意义。生产既是人把自己与动物区分开来的标志,[1](P24)又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1](P30-32)正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在实质上是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表述的内容归根到底无非是对物质生产的反映。[1](P30)实际的情形往往是特定的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特定的生产方式,特定的生产方式的选择往往体现为特定的经济制度,而任何经济制度都是一种利益格局的安排。正义观所反映的内容,既表现为对特定经济制度的适应,也表现为对特定的利益格局的呼唤。因此,正义就其产生和内容上来说,都是具有从属和派生的意义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揭示的就是包括正义在内的社会意识与人的物质生活之间的本来关系。[1](P30);[8](P8)正义论者之所以会把正义看为人类社会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动力,就在于他们漠视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对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念的决定作用,仅是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从正义观念出发。这使得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关系落在他们的视野之外,而落入他们眼帘之中的就只是正义观念,因此,历史呈现在他们眼下的就是一幅正义观念的画卷。[1](P44)而在这一画卷中,得到充分展现的也无非就是各个历史时期中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正义观念,因为在每一时代中占统治地位且能流传于世的也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主要是该时代的统治阶级的正义观念。[1](P52)同时,历史上的正义观念也确实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而且往往是越往后的正义观越具有真理性的意义。如果割裂这种演进背后的根本动因,就容易把后期的正义观念看成前期正义观念演进的目的。[1](P51)因此,历史的演进就成了向他们所掌握的正义理念演进的过程。
二、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决定了正义的范式及其实质
虽然历史上有过不同的正义形态,但是,作为正义,它们都传承着这条一个共同的范式:各得其所应得。从表面来看,正义的这一范式似乎不为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所左右,但实质上却烙下了物质生产、社会经济发展和分工的印记。透过这一范式,我们能够发现它传达出这样的一些信息:(1)“各”隐含着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界分;(2)存在着一种所得关系或所有关系;(3)包含着一种衡量“所得”是否为“各”所应得的尺度或参照。其中,(1)、(2)两点所包含的关系恰好与人们在社会生产和在特定经济制度中所形成的关系一一对应。这不是巧合,而是表明正义这一范式是与社会生产以及特定的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依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要生存必须进行两方面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的生命生产。但是,“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9](P24)都必然发生着人与人的关系和人对自然的占有关系。[1](P33)因此,正义范式所透露出来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对物的所有关系就只不过是生产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而正义观念之所以突显“分”的意义,又与人类的社会生产受制于分工这一事实息息相关。在早期的人类社会生产中,人类个体力量的微弱决定了合作的必要性,[1](P35)以便获取一种联合起来的力量去征服威力无比的大自然。在这一过程中,人类自发地产生了依据各种自然条件基础上的分工倾向,合作往往是自发分工的合作。与此相应,他们也以其特定的方式,分享着他们的劳动所得。后来,随着人们的生产发展到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分离的阶段,[1](P35)分工具有了全新的历史意义。从事精神活动的生产者,就会在他们的观念世界中重构人类进行物质生产这一过程,而在他们的观念世界中,分工-合作-分享所得将是他们无法摆脱的观念和需要肯定的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毕竟是人类进行物质生产的经验总结。另外,分工的观念之所以得到肯定和不断的强化,也在于分工在文明社会中,在事实上已成为具体人生的一种“宿命”。因为当分工产生之后,一方面意味着人类通过分工合作的过程获取了一种整体的力量,即获取了“扩大了的生产力”;[1](P38)另一方面,分工也导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分立和依赖,并且具有某种遗传性发展的性质,因而越来越成为人们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人们也因之使自己的活动固定化。因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1](P37)因此,人们基于分工所从事的活动就成了人们彼此相互区分的一种标识,一种“身份”。或者说,人们是以自身无法选择的分工规定了的方式参与社会生产的。因此,人类的生产在其开始之初就烙下了“分”的印记。
人们在参与生产时,烙下了分的印记,必然使人们在分享其劳动所得时,也遵循着分的逻辑。马克思指出,“分工和所有制是两个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1](P37)因此,人们以何种分工方式参与生产,将意味着有相应的方式分享其所得,就会被认为是合理的。从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正义即是对‘分’的修饰和支持。”[10]
但是,任何劳动成果的获取,就其性质上来看,都是社会合作的产物,是人们的共同劳动所得,要分配共同劳动所得,就必须有分配标准。由于人们参与劳动的方式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从各自的维度看,就意味着在分配所得上存在着不同标准,存在着不同主张的冲突。由此产生了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协调各方的利益主张,分配其各所应得?这意味着必须要有一个普遍认可或者不得不认可的标准来进行分配。显然,不同标准体现出不同的利益格局。在不同标准的可能博弈中,依据于特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所有制起着绝对支配的作用。因此,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标准。在所有者关系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群体或阶级也必将在这种分配标准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这种分配标准与所有制关系的直接联系,使得正义打上了各个时代的烙印,并从根本上体现了不同时代的强势集团或占支配地位阶级的利益要求,因此,正义在其实质上无非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利益的表现。正是作为对历史上的正义形成的总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十分中肯地指出:“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11](P379)显然,这并非马克思对自己的正义标准的论述,而是对历史上的正义观实质的揭示,也是对把正义的价值永恒化和中立化的否定。
三、物质生产的发展决定了正义内容的演变
正义形态曾经历了由古代正义到近代正义的发展。这种发展如果撇开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似乎可以看为文化自身演变的结果。然而,一旦从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发展的维度来看,就会发现,这种演变之所以可能并成为现实,就在于物质生产和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提供了绵绵不断的动力。正义在其实质上无非就是在生产上处于支配地位的阶级意志和利益的表现。在古代,不论是奴隶主还是封建贵族或地主要实现自己的利益,都必须在国家的框架之下才有可能。这是因为这些阶级支配生产是通过支配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才得以实现的,离开了这些要素,特别是土地,就难以实现。因此,要支配土地和劳动力就只有在拥有国家分给的土地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即至少必须成为国家公民一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此,人被看为“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9](P21、526)也即“天然就是政治动物”。但是,此一“天然”也只有在人们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必须通过政治的方式才能够达到的条件下才是“天然”的。而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以及伴随而来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商品生产者要实现自己的利益不再需要借助国家就能实现,国家就由属于人的内在必然性跌落为人的外在的必然性。[9](P21)此时,追逐自己的私人利益就直接被看为人的“天然属性”。
与人的“天然属性”的变迁相对应的是,正义也由古代的强调人的责任转向近代的强调人的权利。古代正义之所以强调人的责任,就在于古代的人们必须成为国家的一员,才能实现自己的利益,拥有国家的政治特权是获取利益的保证。而在商品经济盛行的近代,人们试图拥有的就是保护自己财产和进行商品自由贸易以及平等地从事一切所谓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活动的权利。[12](P324)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代正义何以强调人的责任,近代正义何以强调人的自由、平等等人权。[9](P190-203)
进一步说,古代正义何以显得崇高,近代正义何以显得卑微或世俗,也与政治由人的内在必然性跌落为人的外在必然性密切相关。古代正义的崇高之处,在于个人要实现自己的利益,就必须先成为政治社会中的一员,而政治社会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在此一社会之中,不同的等级拥有不同等的特权,意味着能够实现不同的利益。因此,在这一金字塔式的政治社会中,人们所向往和仰慕的就是位居金字塔顶端的王者的特权,只有在这一位置上,才能拥有最大的利益。但近代正义所对应的商品经济社会中,人们无需成为政治国家中的一员,只要拥有生产资料,就可以实现对劳动力的支配,金钱无疑是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世俗君主,谁拥有它,也就能实现自己的利益,实现自己的正义。这样一来,古代正义就似乎显得崇高,而近代正义就似乎显得世俗和卑微。这一切如从归根结底的意义来看,可以说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正义的普遍性诉求虽然在正义产生之日起就已存在,但却只有在商品经济盛行的近代才真正地“普遍”起来,因为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必然要求突破地区与地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政治限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从而实现资本的增殖。而全球正义和万民法所蕴涵的也无非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全球化在观念上的反映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并不存在所谓的自然正义,而只存在随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变更的正义。
四、正义是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正义不仅不是自然的,而且不是永恒的。因为正义赖以存在的主客观条件并不是人类的“永恒事实”,而是生产力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足的“历史事件”。
首先,从正义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来看,正义只能存在于资源中度匮乏的环境。在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分工还不发达,物质资源极度匮乏的境遇下,生产没有剩余,没有产品可以私人占有,不存在占有观念,正义无法产生。[13](P38);[3](P22-23)这一历史事实我们可以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看到,也可以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看到对这一事实的考据,而马克思对梅恩《古代法》的批判之一也在于梅恩把所有权设想为人类的永恒事实。在生产力充分发展,资源无限丰富的环境中,是无需提出“各得其所应得”正义要求的。[13](P34-36);[14](P670)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3](P23)因此,以马克思的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在此一社会中,正义将成为人类历史的遗迹。[14](P670)因此,正义的存在只是社会生产有所发展但又发展不充分的产物。从分工的角度来看,正义的产生只是人类发展到出现社会分工,但又无法自主支配分工的产物。
其次,从正义赖以产生的主观条件来看,正义的产生离不开自我意识的生成。以正义论者自己的表述,正义是自我意识的一个运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自我意识并不是人天生就具有的,而是在社会生产中“生成”的结果。“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1](P29)当人开始对其所处的生存世界有所意识时,人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分化和冲突关系也刻印在人的意识之中,而正义观念正是在肯定这种分化和冲突状态中的一种思考。因此,正义是在冲突中寻求协调,在紧张之中寻求和解。从这一点来看,正义的存在也是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作为前提的,一旦消解了这种紧张关系和冲突,正义也就不复存在。而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以及“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已得到真正解决。[15](P120)
五、是生产决定分配,而不是正义决定分配
从最为宽泛的意义上说,正义内含着分配正义。因为正义具有着双面的诉求:一面指向它的价值追求——人道,[16](P508)一面指向它赖以产生的世界——物质世界。因此,正义从其具有人道的指引和追求来说,它具有一股“形而上”的向往;从它试图对物质世界进行规范、谋划、界分和评价,以至于摆脱不了物质的纠缠这一点来说,正义充满了一种“形而下”的欲望和指向。而分配正义正是这种形而下指向的具体表现。因此,正如“分工和私有制是两个同义语”一样,[1](P37)正义和分配正义也是属于相等的表达方式,只不过分配正义强调的是要对形而下的东西进行规范、谋划、界分和评价。由于正义内含着分配正义,因此,在马克思批判正义之时,也已经包含了马克思对分配正义的批判,也就可以不必再行追问马克思何以拒斥、批判分配正义。但是,这里为了突显马克思批判分配正义的深刻性,也不妨再次探问马克思何以批判分配正义。
从马克思所拒斥、批判的分配正义主张来看,当时的分配正义者一方面对私有财产所引起的社会不平等表示一种道德上的不满或情感上的愤慨,另一方面又未能看到社会不平等的深刻根源;即一方面认为这个社会是“有病”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未能对当时的社会进行科学诊断,因而,开出的“药方”不是医治人性的堕落,[1](P618、619)就是要求从人道或正义出发调节私有财产,[2](P351)甚至是取消私有财产,如蒲鲁东。[15](P117)
但是,对于分配正义论者的这些“善良的努力”,马克思指出分配正义论者并不了解他们所谈论的对象。[2](P309、313);[17](P35)由于不了解他们所谈论的对象,他们不是把社会的症结归结在人性的堕落上,就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3](P23)他们认为问题的症结在于离开特定的生产方式,以某种所谓的正义观念来“随心所欲”地进行分配,[3](P323);[9](P24)这是极为荒谬的。因为,不论是生产条件本身的分配,还是消费资料的分配,都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分配的,都是受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马克思认为,就生产过程来看,分配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生产条件的分配和生产成果的分配。就前者来看,它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3](P23)是“生产的条件和前提”,它们构成了“生产的要素”;[9](P34)而就后者来看,它“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3](P23)因此,分配在实质上是由生产方式规定的。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有什么样的生产结构就会有什么样的分配结构。如,在资本主义分配关系中,“工资以雇佣劳动为前提,利润以资本为前提,”[18](P997)地租以土地私有权为前提。“个人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因此,“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9](P32)
既然如此,正义论者所看到的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不正义的问题就不可能在分配领域得到根本解决。要解决正义论者所看到的资本主义分配不正义的问题,只能挖掉它赖以存在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才有可能根本地解决问题。[2](P480)因为,“认为公道和公平的东西,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就在于:一定的生产制度所必需的和不可避免的东西是什么?”[19](P76)也是基于这样的理解,马克思才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哥达纲领》的“公平分配”提出了这样的反讽:“什麽是‘公平的’分配呢?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由经济关系来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3](P18-19)
以上几点是从正义论自身所存在的限度,寻找马克思拒斥和批判正义的尝试。但以此还不足以探讨马克思何以要拒斥和批判正义,因为一种理论即使有其限度或缺陷,假如只是停留在理论之中,或封闭在个人的私人领域,对现实没有指涉或实践作用的话,也可以不必理会。但是,正义论者却是试图把他们的正义观念运用在具体的社会实践上。因此,马克思对正义的拒斥、批判也是着落在其“正义实践”对社会的误导或破坏上面。这些误导作用如做一简要的归结,主要有:(1)从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基础和动力出发,认为要推动社会进步就必须改变人们的正义观念。[20](P30)这样就把变革社会现实引向无谓的观念之争和词句之争,[1](P22)在实质上是与现实的影子作斗争。(2)既然认为正义是人类社会的真正基础和动力,就必然把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落在“生产”正义的学者、思想家和能够实施正义的统治阶级身上,[21](P354)至于从事物质生产的广大人民大众只不过是应该去怜悯,和应该给以改造、拯救的对象。[22](P452)(3)与以上两点相呼应的,必然认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在于自上而下的改良,而不是自下而上的革命。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个结论性的说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成的生产力和由它创立的财富分配制度,已经和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发生激烈的矛盾,而且矛盾达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于如果要避免整个现代社会灭亡,就必须使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发生一个会消除一切阶级差别的变革。现代社会主义必获胜利的信心,正是基于这个以或多或少清楚的形式和不可抗拒的必然性印入被剥削的无产者的头脑之中、可以感触到的物质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一个蛰居书斋的学者的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观念。”[14](P1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