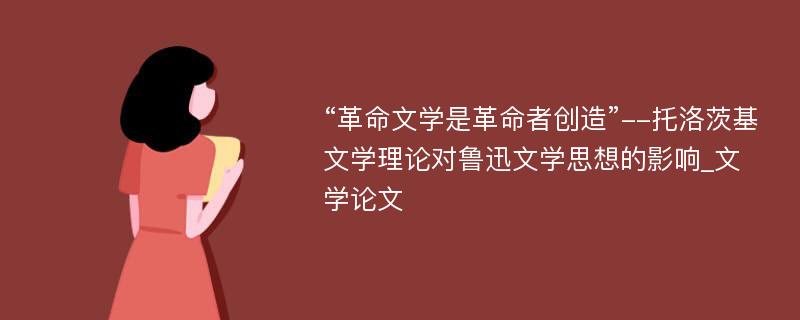
“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托洛茨基论文,鲁迅论文,文论论文,才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应首先宏观地将二者视为两个完整体系,进而分析双方核心观念的影响关系,这应该是一个立足于细致辨析的整体性比较,而不是仅仅寻找鲁迅使用过的文论术语的词源。但是,学界目前普遍集中于探讨鲁迅对几个名词概念的接受情况,最主要的是鲁迅对“同路人”概念的接受,但是,综观鲁迅的所有文章会发现一个现象,凡是涉及“同路人”概念的部分,几乎都是借用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例子,并没有深入阐述和发挥,更没有进一步提出自己新的观点和认识,这意味着这一概念只是被鲁迅认可,但没有真正与自身的文学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日本学者长堀佑造在其论文《鲁迅“革命人”的提出——鲁迅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之一》中讨论了鲁迅对托洛茨基“革命人”思想的接受,但是,且不论他所采用的简单的“数学公式”式的等价替换论述方法是否可信,也不论其出发点是否偏离了文学领域,单就其结论来看,就不符合鲁迅的文学思想。他的结论是:鲁迅从托洛茨基文论中借用了“革命人”术语,结合自己对国民革命运动的现实思考,得出了“革命者写的东西不管主题如何都是革命文学”的认识,该认识换用他文中的另一句话解释,即“‘革命人’如写东西,什么都是‘革命文学’”①,这就既没有看到鲁迅在托洛茨基文论影响下对作品艺术价值的要求,也没有看到他在这一影响下对作为创作主体的“革命人”应有特征的思考。托洛茨基和鲁迅要求“革命文学”的作者是革命人,但并非认为所有革命人都可以成为创作主体,而且他们更要求作品是艺术品,并非长堀佑造所说的“什么都是‘革命文学’”。长堀佑造对鲁迅接受“革命人”思想的论述,实际与学界普遍关注的鲁迅接受“同路人”思想犯有同一个错误:只在字面上寻找词源,而没有对两个文学思想体系进行宏观把握和细致辨析。这就导致不仅没有进入鲁迅文学思想的核心和“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文学思想的影响”这一问题的核心,而且偏离了鲁迅文学思想,从而更不会看到鲁迅在托洛茨基文论影响下形成的文学思想如何影响了他对当时文坛的批评。 就托洛茨基文论体系整体而言,“只有革命的艺术家才能创作革命文学”是其核心观念,综合鲁迅关于“革命文学”的全部论述和相关文献来看,他在此影响下,形成了“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的认识,并主导了他的“革命文学”观,这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讨论,即创作主体必须是“革命人”和“革命文学”必须坚持艺术应有的独立审美品格。本文选取的托洛茨基文论作品只有1928年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十二个》汉译本前言和1930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文艺政策》里收录的托洛茨基讲话,这是基于以下考虑:鲁迅虽然接触过多种《文学与革命》版本,但是从笔者阅读能力和行文方便等等各方面考虑,只能选择汉译本,在鲁迅接触过的两种汉译本中,1928年未名社出版的《文学与革命》根据俄文原文本翻译出来,是与鲁迅最熟悉的人——李霁野和韦素园——翻译的,也是鲁迅亲自指导翻译的,从这些方面来考虑,应该比傅东华的译本更贴近鲁迅;《十二个》汉译本前言和1930年水沫书店出版的《文艺政策》里收录的托洛茨基讲话都是鲁迅亲自翻译的,必然深受影响;目前来看,鲁迅只接触过这三种托洛茨基文论资料。 关于“同路人”的论述是《革命与文学》一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托洛茨基以大量篇幅对克留耶夫、叶遂宁、“舍拉皮翁兄弟”派和皮涅克等等“十月革命底文学‘同路人’”逐一进行点评,通过分析他们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思想,指出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有何偏差,在此基础上说明为什么称他们为“同路人”。然而,如果这部分内容只有这么简单,就没必要以接近全书三分之一的笔墨来写作,托洛茨基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在对“同路人”的论述中隐含着对一个观念的阐释——“只有革命的艺术家才能创作革命文学”,这是其“革命文学”创作论的核心观点,也是其整个文学思想体系的主干。 所谓“革命的艺术家”,就是指能“沉没在革命中”“溶解在革命中以领悟革命”“不仅拿革命当一种元素的力,也当作一种有目的的进程去领悟它”②的人。这个观念无法以具体的作家作品来正面论述,因为在托洛茨基看来,革命的艺术家和革命文学都尚未诞生,当时仅有一种“介于在反覆或沉默中消逝的资产阶级的艺术,与尚未诞生的新艺术之间”的“过渡的艺术”,也就是“同路人”的艺术,“它多少和革命有机地相连,但同时又不是革命地艺术”③,因此可以从这一差异之处入手采取侧面论述的策略。从书中的内容来看,所有关于“同路人”的论述都间接或直接指向了“只有革命的艺术家才能创作革命文学”这一观念。比如“克留耶夫接受革命,因为他解放了农民,他并且对它吟咏了他底许多歌。但是他底革命既没有政治的动力,也没有历史的观念。对于克留耶夫,革命好像是一个市场或华丽的婚礼,人从各处来到那里聚集,以酒与歌,拥抱与跳舞沉醉,于是各自回到自己家里……他允着经过革命的天国,但这个天国不过是夸大的,修饰的,农民的王国,一个小麦与蜂蜜的天国而已。”④又如“时常皮涅克恭敬地从共产党旁过去,有一点冷然,有时甚至带着同情,但是他从他旁边过去了。你不大在皮涅克中找到一个革命的劳动者,更重要的是,作者不用并且也不能用后者底眼睛,去看发生着的事情。……红军对于1918-1921年的这个艺术家是不存在的。……都会的革命的赤卫队在1917年末与1918年初,在谋自存的战争中,成队成营的出发到前线上去,皮涅克对这不加注意。对于他,红军是不存在的。此其所以1919年对于他是空光的。”⑤当然,以上两例还不太明显,需要仔细体会,以下两例则表达得更加直接:“不可见的中枢应当是革命底自身,绕着它旋转的,应当是全盘不安稳的,混乱的,在重行建造着的生活。但是要想叫读者觉得这中枢,作者自己必得曾经觉得过,同时并必得把它思索过。”⑥“只有学着从全部中理会革命,把它底后退看为走向胜利的步骤,透入到后退底策略中的人,和能在退潮时代的积极的势力预备中,见到革命底不死的至情与诗的人,才能够变成革命底诗人。十月革命是澈底地民族的。但它并不仅是一种民族的元素——它是一个民族的学院。革命底艺术一定要经过这个学院。而且这是一种很难的课程。”⑦ 托洛茨基阐述的文论,实际是作为政治家面对文学的发言,这必然决定了其文学思想受其政治主张的制约,是其政治主张的外延。“不断革命论”是托洛茨基的根本政治主张,他认为,无产阶级必须掌握革命的领导权,领导和帮助软弱的资产阶级达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然后继续革命以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中间不能有停顿和间歇,这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它将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一个无阶级、无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基于此,他认为十月革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应该而且“已经开始在文学中申述自己,指挥文学而且管理文学,并且不仅在行政的意义上,在较深的意义上也是如此”⑧,文学只有正面面对并充分表现十月革命及其开启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才有价值,因为这是一场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革命,所以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艺术家才能自觉的“沉没在革命中”“溶解在革命中”以“领悟革命”⑨,进而创作出符合“十月底观点”的作品,托洛茨基由此出发,进一步对“同路人”进行了分析和批评,指出了他们在文学领域的过渡性质。另外,托洛茨基认为正是由于无产阶级革命者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中,并对革命进程和意义有深刻理解,要实现一个无阶级、每个人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将忙于革命,无产阶级文学将不会出现,只会出现一种从革命中走出的“革命文学”,同时,革命的艺术家会“摆脱掉卑下的党派的恶意”⑩ ,“对于各种正真诚地努力行近革命,并且这样助成革命底艺术的造成的艺术团体,能够而且必须另加以信任”(11),由此实现一个以“革命文学”为主导方向的自由多元的艺术领域,进而推动“革命文学”的大发展,这些都是非“革命艺术家”们无法做到的。可见,整个托洛茨基文论,无论是文学的阶级分析论还是自由多元的艺术观,都是以“只有革命的艺术家才能创作革命文学”这一观念为中心的。 对于这一托洛茨基文学思想体系的主干,鲁迅肯定非常熟悉,首先因为他曾接触过多种版本的《文学与革命》,根据目前能看到的鲁迅日记、书信以及其他相关材料进行统计可知,1925年8月26日,他买到了这本书的日译本;1927年3月到4月之间在《中央副刊》上读到了傅东华的汉译本;1927年9月11日买到了英译本;1928年2月23日又买了一次日译本;1928年3月16日收到韦素园、李霁野合译本,另外,韦素园为了翻译这本书,曾从苏联人铁捷克那里得到了俄文原文本(12),这个版本或许也被鲁迅见到过。其次,鲁迅对托洛茨基的文论了如指掌。鲁迅文章中关于“革命文学”的内容几乎都能找到《文学与革命》的影子,比如《革命时代的文学》对“大革命与文学有什么影响”这一问题的论述,以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中对“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的论述,主要观点几乎全部脱胎于《文学与革命》第一章“十月革命以前的文学”和第六章“无产阶级的文化与无产阶级的艺术”;在《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对“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的简短论述中,也能看到托洛茨基评论“同路人”文学时的一些观点;在《〈竖琴〉前记》中表达的对“同路人”文学的理解和评价也基本符合《文学与革命》的内容;鲁迅还把《文学与革命》的第三章完整翻译过来作为勃洛克《十二个》汉译本的序言。鲁迅曾在《马上日记之二》《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等多篇文章中对托洛茨基的一些文学观点表示赞同,在他看来,托洛茨基是一位“深解文艺的批评者”(13)。 在托洛茨基“只有革命的艺术家才能创作革命文学”观点的影响下,鲁迅形成了“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的认识,他关于革命文学创作主体的思考、对革命文学作品应达到的艺术高度的要求以及对当时文坛的批评,几乎都是围绕这一认识展开的,可以说,这一认识成为了鲁迅的“革命文学”观的主导思想。 鲁迅对托洛茨基的一个观点非常赞同:“托洛斯基曾经说明过什么是革命艺术。是:即使主题不谈革命,而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者是;否则,即使以革命为主题,也不是革命艺术。”(14)在托洛茨基本人看来,要“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作者本人就必须全身心投入到革命之中,“假如人不在革命底全部中,即作为革命主力底标的那种客观的历史的工作中去看革命,那是不能够了解革命,也不能接受或绘画革命的,甚至就连部分地也不能够。假如这个弄错了,那末中枢与革命就都吹了。革命就分裂成枝叶与奇谭,这些既不是英雄的,也不是罪恶的。要是如此,画一点儿怪乖巧的图画还可能,重新创造革命是不可能的,和革命和谐一致自然是不可能的了。”(15)对此,鲁迅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所以革命文学家,至少是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的。”(16)只要作家是这样的“革命人”“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17)然而在鲁迅看来,“以革命文学自命的,一定不是革命文学”(18),“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19),因此,这样的“革命人”应该是“希有”的,他们必须具备两个特质。 第一,必须主动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对革命的实际情形有深刻的了解。鲁迅经常以叶遂宁为例,说明“对于革命抱着浪漫谛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进行,便容易失望”(20),他们不是“革命人”,只是革命的“同路人”,这正是《革命与文学》一书中对叶遂宁的评价,鲁迅还用托洛茨基的观点说明什么是“同路人”:“讬罗兹基也是支持者之一,称之为‘同路人’。同路人者,谓因革命中所含有的英雄主义而接受革命,一同前行,但并无彻底为革命而斗争,虽死不惜的信念,仅是一时同道的伴侣罢了。”(21)由此可见,鲁迅接受了托洛茨基的看法,认为“同路人”对于革命的向往,并不是建立在一种理性认识的基础上,而是基于英雄主义的浪漫幻想,他们也曾对革命表示过呼唤与支持,但对革命过程中血与火的残酷现实并不清楚,也并不关心,因此,当革命真正到来之后,他们的行为无法与历史进程合拍,最终被历史所淘汰,他们的作品虽然可能因其较高的艺术水平不会被淘汰,但终究无法做到“有从革命所发生的新事物藏在里面的意识一贯着”,不能作为革命文学流传于世。鲁迅常常从俄国的叶遂宁等“同路人”联想到中国的“南社”,作为“希望革命的文人,革命一到,反而沉默下去的例子”(22),进而联想到中国革命与革命文学,根据上述认识,他提出,作为“革命人”的革命文学家必须主动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对革命的实际情形有深刻的了解,这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有集中阐释:“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房子里,最容易高谈彻底的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者,毫不足靠。”“倘不明白革命的实际情形,也容易变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秽和血,决不是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现实的事,需要各种卑贱的,麻烦的工作,决不如诗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当然有破坏,然而更需要建设,破坏是痛快的,但建设却是麻烦的事。”(23) 第二,作为“革命人”的革命文学家在接触和深刻了解革命实际情形的基础上,还必须是一位“战斗者”,他要认清整个革命局势以有的放矢地去斗争,也就是“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要写文学作品也一样,不但应该知道革命的实际,也必须深知敌人的情形,现在的各方面的状况,再去断定革命的前途。惟有明白旧的,看到新的,了解过去,推断将来,我们的文学的发展才有希望”(24),这正是托洛茨基所谓的“每个大时代,不论是宗教改革也罢,文艺复兴也罢,革命也罢,必得整个地被接受,不是成段地或分为小部地。”(25)更重要的是,还要具备一位“战斗者”应有的“韧”的精神,“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门一敲进,砖就可拋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26),就是“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27),这也与《文学与革命》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极为相似:“革命底至情与诗。是在于下面的事实中:一个新的革命的阶级,变成了这一切战具底主人,而且以去充实人并造成新人的新理想底名,它继续着与旧世界的斗争,兴起衰落,直到最后的胜利的瞬间。”(28) 但是,鲁迅并不认为这种作为“革命人”的革命文学家应该马上出现,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演讲中直陈:“诸君是实际的战争者,是革命的战士,我以为现在还是不要佩服文学的好。”这不仅因为“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止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而且因为他始终坚持“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29),“做文学的人总得闲定一点,正在革命中,那有功夫做文学”(30)。这实际就是托洛茨基在演讲中所说的:“一直先前,就有老话的:剑戟一发声,诗人便沉默。要文学的复活,休息是必要的。”(31) 在文学创作方面,托洛茨基始终坚持艺术应该具有自身独立的审美品格,并认为“麻疤的艺术不是艺术”(32),鲁迅也有同样的观点,他说:“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的意义的。”(33)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鲁迅认为在具备了作者是“革命人”这一条件的基础上,还必须满足另一个条件,即革命人做出的东西必须是“艺术品”,才能称为“革命文学”。在托洛茨基看来,革命文学作品要成为艺术品,具有艺术价值,必须在内容中展现出言说革命的强烈欲望,有革命意识浑融的充斥其间,而不是简单的拼凑革命词语,同时还要学习运用艺术技巧,这可以用鲁迅的一句话进行概括:“当先求内容的充实和技巧的上达,不必忙于挂招牌。”(34) 托洛茨基在《文学与革命》第三章对亚历山大·勃洛克及其诗作《十二个》进行了评价,认为“《十二个》也一毫不差不是一首革命诗”,原因在于,虽然“勃洛克抓住了革命底车轮”,但这首诗“是被革命占有了的个人主义艺术底鸿鹄歌”“他在革命底最粗俗的形式中,而且仅在粗俗的形式中,看取革命”,而所描写的貌似革命的事实其实都与革命无关,诗中出现的基督“无论如何不是属于革命,不过是属于勃洛克底过去的”。(35)鲁迅将这一章翻译过来作为《十二个》汉译本序言之后,又写了一篇后记,对托洛茨基的判断表示认可:“如讬罗兹基言,因为他‘向着我们这边突进了。突进而受伤了。’”接下来还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句引文进行了阐释:“人多是‘生命之川’之中的一滴,承着过去,向着未来,倘不是真的特出到异乎寻常的,便都不免并含着向前和反顾。诗《十二个》里就可以看见这样的心:他向前,所以向革命突进了,然而反顾,于是受伤。”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鲁迅得出结论:“呼唤血和火的,咏叹酒和女人的,赏味幽林和秋月的,都要真的神往的心,否则一样是空洞。”(36)这里所谓的“真的神往的心”,用托洛茨基的话来说,就是“说革命的大欲望”(37),没有这种欲望,作品内容就是空洞的,即使主题反映革命,也不成其为“革命文学”,而只要具备这种“真的神往的心”,即使主题并不与革命相连,其内容也会“澈底地为革命所煊染”“被由革命而生的新意识着了色”(38),这样的作品就是内容充实的革命文学作品。由此出发,鲁迅进一步认识到:“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杀,杀’,或‘血,血’的。”(39)因为这两类作品“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对于失败者的革命并不是革命,其中并没有对革命真的神往的心贯穿着,“‘打,打’,‘杀,杀’,听去诚然是英勇的,但不过是一面鼓。即使是鼙鼓,倘若前面无敌军,后面无我军,终于不过是一面鼓而已”,作品内容仍然是空洞的,鲁迅还以唐朝人做富贵诗进行类比,真会写富贵景象的,根本不用“金”“玉”“锦”“绮”等字眼,但作品内容却是被富贵着了色的、更加充实的。(40) 做到了“内容的充实”还不够,“技巧的上达”也是必须的。托洛茨基认为:“光是文学技术底研究就是一种必需的层序……对于许多年青的无产阶级作家,人可以十分公道地说,不是他们是技术底主人,确实技术是他们底主人。对于更有天才者,这不过是一种生长病。但是拒绝学习技术者,将要成为‘不自然的’,模仿的,甚至小丑似的。”(41)鲁迅也重视“技巧”的学习,他在《文艺与革命》一文中对这一点进行了简短阐述,其行文逻辑与托洛茨基非常接近,托洛茨基在说明学习“文学技术”很重要后,就批评了“拒绝学习技术者”,指出他们的作品“将要成为‘不自然的’,模仿的,甚至小丑似的”,鲁迅同样在说明“技巧”的重要性后批评了“革命文学家是又要讨厌的”,指出他们的作品将会流于非文艺的宣传品。不仅如此,他们这种主张的动因也是一样的,也就是将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不把它视为某种东西的附庸。比如,鲁迅在《文艺与革命》中阐述技巧重要性的一段最后一句话说道:“革命之所以于口号,标语,布告,电报,教科书……之外,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42)从此处可知,鲁迅视文艺为革命过程中区别于口号、标语、布告等等的一种独立的宣传形式,独特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需要运用艺术技巧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又如,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鲁迅根据“讬罗兹基曾以对于‘死之恐怖’为古今人所共同,来说明文学中有不带阶级性的分子”,表达了自己对文学的阶级性的看法:“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经济’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着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43)这同样也是认同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主张文学应该具有自己独立的地位,不能因为革命而成为阶级的附庸。总而言之,无论是把文艺看作区别于口号、标语等等的一种独特宣传形式,还是反对文学成为阶级的附庸,鲁迅的这两个观点都可以用托洛茨基的一句话予以概括:“艺术必须开辟自己的道路,并且用自己的方法。”(44) “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的认识影响了鲁迅对当时文坛的看法。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的部分成员与鲁迅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论争,从这一年开始,他经常在杂文中对一些革命文学家和革命文学口号提出批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他看来,这些革命文学家并不是真正的“革命人”,他们所讨论和创作的作品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文学作品。 鲁迅认为,之所以“上海的文界今年是恭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沸沸扬扬”,是因为很多人觉得“文艺家的眼光要超时代,所以到否虽不可知,也须先行拥篲清道,或者伛偻奉迎”,并不是真的基于对革命的体验和关怀,于是对于无产阶级文学使者,他们“在大屋子里寻,在客店里寻,在洋人家里寻,在书铺子里寻,在咖啡馆里寻……”(45)鲁迅这样写明显是在讽刺他们,因为“大屋子”“洋人家”“咖啡馆”等等场所一般来说是与革命、无产阶级无关的,另外,鲁迅对“超时代”也有定义:“超时代其实就是逃避,倘自己没有正视现实的勇气,又要挂革命的招牌,便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必然地要走入那一条路的。”(46)也就是说,他认为在革命风潮即将到来的现实状况之下,上海文学界的普遍风气只不过是在忙着挂招牌,其目的是为自己寻找一个出路:“于是做人便难起来,口头不说‘无产’便是‘非革命’,还好;‘非革命’即是‘反革命’,可就险了。这真要没有出路。”(47)而对于需要革命的社会现实以及马上到来的革命风潮,没有人了解实际情况,更没有人表示热切的渴望并去主动迎接,“招牌是挂了,却只是吹嘘同伙的文章,而对于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视”(48)。不仅如此,鲁迅后来更发现了叶灵凤、向培良等等很多所谓的“革命文学者”缺乏“韧”的战斗精神,他在《上海文艺之一瞥》中写道:“但有些‘革命文学者’的本身里,还藏着容易犯到的病根。‘革命’和‘文学’,若断若续,好像两只靠近的船,一只是‘革命’,一只是‘文学’,而作者的每一只脚就站在每一只船上面。当环境较好的时候,作者就在革命这一只船上踏得重一分,分明是革命者,待到革命一被压迫,则在文学的船上踏得重一点,他变了不过是文学家了。”(49)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做法绝不是一位坚韧的战斗者所为,因此,无论他们讲“革命文学”还是后来更“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学”,都是含混的,加之毫无革命生活体验,他们根本不是鲁迅所谓的“革命人”,在鲁迅看来,这最终导致他们“要有革命者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于是不但笑啼俱伪,并且左右不同,连叶灵凤所抄袭来的‘阴阳脸’,也还不足以淋漓尽致地为他们自己写照”(50)。 既然不是“革命人”,就无法在作品中融入“真的神往的心”,作品内容便不免“空洞”,鲁迅认为“创造社所提倡的,更彻底的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学,自然更不过是一个题目”(51),是将文学变成“阶级性”的附庸和某种斗争工具:“索性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但无须无产者自己来写;无论出身是什么阶级,无论所处是什么环境,只要‘以无产阶级的意识,产生出来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直截爽快得多了。”(52)这里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就是指“阶级性”,鲁迅在《文学的阶级性》一文中就讽刺了这种“住洋房,喝咖啡,却道‘唯我把握住了无产阶级意识,所以我是真的无产者’的革命文学者”(53);这里的“一种的斗争的文学”就是把文学视为斗争工具,也就是李初梨所谓的“由艺术的武器到武器的艺术”、成仿吾的“十万两无烟火药”。无论是把文学视为“阶级性”的附庸还是某种斗争工具,其着眼点都不在文学本身,没有把革命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品来看待,这就无法成为“被说革命的大欲望所充满的艺术”(54),也就与鲁迅所主张的“内容的充实”相去甚远了。内容尚且不充实,艺术技巧就更无从谈起了,鲁迅对于“现在的广东,是非革命文学不能算做文学的,是非‘打打打,杀杀杀,革革革,命命命’,不能算做革命文学的”(55)现象非常不满,认为这些字眼“不过是一面鼓”“‘赋得革命,五言八韵’,是只能骗骗盲试官的”(56),“作品虽然也有些发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连报章记事都不如”(57)。 “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思想的形成是托洛茨基文论对鲁迅文学思想的主要影响。鲁迅根据自己所读的《文学与革命》、自己所翻译的这本书的第三章和《文艺政策》等资料,在对托洛茨基文论有全面、深入的理解的基础上,抓住了托洛茨基文学思想体系的主干,认识到革命文学的作者必须是一位“革命人”,要主动接触并深刻了解实际的社会斗争情况,并具有“韧”的战斗精神,是一位战斗者,另一方面,革命文学作品必须是一件艺术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内容要充实,技巧要上达。这些思想直接影响了鲁迅对于当时中国文坛的看法,成为其“革命文学”观的主导,他认为文艺界缺乏真正的“革命人”,故而不会有对革命“真的神往的心”,这使不断出现的作品在内容方面并不充实,更谈不上艺术技巧,因此,不能算作真正的革命文学作品。 ①[日]长堀佑造:《鲁迅“革命人”的提出——鲁迅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之一》,《鲁迅研究月刊》2002年第10期。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11)(15)(25)(28)(32)(35)(37)(38)(41)(44)(54)[俄]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未名社出版部1928年版,第117、67、77-78、105-106、100、133、21、117、292、288、116、100、127、270、155-161、302、301、270、288、302页。 (12)李霁野:《鲁迅先生与未明社》,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 (13)(36)鲁迅:《后记》,载《十二个》,北新书局1926年版,第73、70-71页。 (14)鲁迅:《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第306页。 (16)(24)(49)鲁迅:《上海文艺之一瞥》,《鲁迅全集》第4卷,第307、308、305页。 (17)(19)(39)(40)(56)鲁迅:《革命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568、568、567、567-568、568页。 (18)(30)(55)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全集》第7卷,第121、119、119页。 (20)(23)(26)(27)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第239、238-239、242、240页。 (21)鲁迅:《〈竖琴〉前记》,《鲁迅全集》第4卷,第445页。 (22)(51)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第137、138页。 (29)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第441-442页。 (31)《关于对文艺的党的政策——关于文艺政策的评议会的议事速记录》,载《文艺政策》,水沫书店1930年版,第123页。 (33)鲁迅:《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鲁迅全集》第4卷,第376页。 (34)(42)(46)(48)(57)鲁迅:《文艺与革命》,《鲁迅全集》第4卷,第84-85、85、84、85、85页。 (43)(53)鲁迅:《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128、128页。 (45)(47)鲁迅:《路》,《鲁迅全集》第4卷,第90、90页。 (50)鲁迅:《文坛的掌故》,《鲁迅全集》第4卷,第123-124页。 (52)鲁迅:《“醉眼”中的朦胧》,《鲁迅全集》第4卷,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