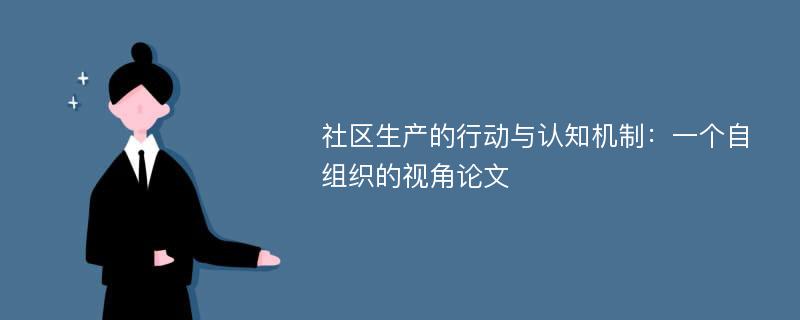
社区生产的行动与认知机制:一个自组织的视角
文/郑中玉
摘要: 社区研究倾向于将“社区”的存在视为自然而然,忽视了分析社区的生产问题。目前围绕着社区的生产存在两种方案:维权或都市运动和社区营造。前者忽视了非反抗的、日常生活行动所具有的意义,而后者则主要寄托于学者和社会组织的干预。同时,两种方案都忽视了社区行动者自发自组织过程生产社区的可能性。一个社区网的实践展示出社区生产的自组织行动和认知机制:社区行动者自发自组织过程产生独特的社区传统和社区精神,促进社区认同的形成;空间与社会的隔离以及社区行动者内部团结等因素,进一步促进社区的想象。
关键词: 社区网;自组织;社区的生产;想象的社区
一 社区生产的三种方案
从滕尼斯开始,社会学一直在思考着面对现代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力量,社区将遭遇什么命运或未来,[1]都试图思考社区如何受到现代社会结构力量的压迫,导致某种“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2]强调应该去发现和服从社会变革和创造历史的力量或者普遍的历史规律。经典社区理论倾向于具有历史决定论和线性进化论的立场,坚信社区在朝向某种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3]习惯于总体化地理解理性化结构趋势下的现代日常生活。[4]这些总体化的本质主义理论立场线性地分析工业化、城市化和官僚化发展的结构性力量对于社区的影响,似乎社区只能接受一种终极的命运,一种单一的结局。但是,实际上社区研究还存在另外一种视角,即关注在结构性的、非人化的社会力量压力之下,行动者所上演的重要的人类剧目(human dramas)。研究者需要关注行动者如何形成与大众社会不同的互动模式,可以借此超越结构局限。[5]这种“行动”或“实践的视角”重点关注,在结构约束下,行动者如何创造性地实践社区。[6]当然,大多数研究习惯于停留在结构研究维度上,忽视在行动者维度上社区实践的复杂性和主体能动性。但是,就像我们在“保卫”社会之前首先要去“生产”社会[7]一样,无论是社区的管理还是治理,前提应该是社区的“生产”。关于“社区的生产”,目前有政治性的集体行动和专业化的社区营造两种行动方案。
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方案关注行动者围绕着产权的斗争,通过“行动”来打造“社会”和“公民”,[8]通过大量社区维权和集体行动促进公民参与网络、信任和互惠规范等社区“社会资本”的形成,[9]这种对显性的、有组织集体行动的理论偏爱非常普遍。学术界在研究阶级关系和阶级冲突的时候,就倾向于关注显性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阶级行动,比如说革命和暴动等等,容易忽视基于“安全第一”的伦理,农民倾向于避免公开反抗的集体风险,[10]因此更多的阶级冲突不是革命,而是那些“非正式的”“隐蔽的”“日常形式”的反抗。[11]都市生活中的集体维权必然会遇到各种权力和资本的压制,需要维权者具有“公民的勇气”[12]和“公民的毅力”。[13]换个角度来说,维权以及都市运动都无法代表社区日常生活。同时,从长期看来,类似业委会等社区组织具有维权的工具性特征,只是在短期内可能与社群主义的组织形式发生偶合,在长期的共同体发育过程中并不必然有利于建构社群。[14]
社区营造(community building)是一种由专家和社区精英共同合作推动的“社会学干预”。在亚洲,社区营造运动由20世纪60年代日本市民运动推动起来,[15]90年代以后,逐渐在台湾地区的政务、学术界和市民运动领域得到了新的反应。[16]21世纪以来,中国内地也逐渐引入了社区营造的思想和实践,将其融入社区治理体系的实践与创新之中。[17]但是,社区营造作为一种图海纳意义上的“社会学干预”实践,一方面确实可能推动社区治理和社区建设转向“自组织治理”,[18]但是无论采取“强干预”还是“弱干预”,[19]都可能存在外部驱动造成社区自组织缺乏持续性的问题。
总体上看,两种社区生产方案对行动者的想象都具有精英主义的问题,容易忽视日常生活视野下行动者自组织过程对于社区生产的重要意义。实际上,还存在着第三种方案,即社区居民作为行动者,从日常生活意义上自组织社区生活的社区生产路径——本世纪初开始,B市北部五环外的一个大型经济适用房小区的社区生产过程就体现了这种可能性。本文将从“行动”和“认知”两个维度尝试分析自组织的社区生产机制:首先,社区居民自发建立社区网,通过自组织方式发起各种虚拟社区和物理社区的日常活动,形成大量社区纽带和传统,最终将一个陌生人的居住区转化成“我们的”“社区”;其次,与外部环境的空间与社会区隔以及促进内部团结的因素促进了“社区的想象”。
二 通过“行动”打造社区
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强调功能分区。H社区所在区域最初主要被规划为居住区,大多数的居民都是在主城区工作。城市空间功能的单一化使得H社区成为局外人眼里的“睡城”。这种观察实际上忽略了信息时代社区空间的复杂性,忽视了在虚拟社区上稠密的交往和关系建构的意义。虚拟空间和物理空间的交织塑造了日常生活“行动”,进而促进“社区”的生产。
(一)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自组织治理
社区网是一个基于日常社区生活的虚拟社区,参与者主要是业主和租户。区别于其他虚拟社区的是,它更具有促进本地社区重新组织的“再地方化”趋向。社区网最早是2000年由网名为“班长”的购房者建立,最初只是一个网页,后来慢慢发展成单独注册域名的虚拟社区。大家可以在这里交流购房和装修经验。随着注册网友的增加,根据网友建议和社区生活需求,慢慢围绕着小区和网友兴趣形成共计近60多个论坛,还增加了一些类似“集采”“团购”“资讯”和“社区服务”等虚拟空间,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社区生活所需。所以,网友们戏称之为“万能的社区网”。
当然,传统的发明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在每一代人那里不断被更新、调整和重构”,[24]根据新的形势可能会利用与改造“旧材料”,有时候也会发生“连续性中的断裂”。[25]H社区的传统也在经历变迁,既有延续也有重构。一些传统延续下来了,比如周年庆典、春节晚会、“超级H声”、足球联赛等等;一些传统活动因为各种原因而停办,但是以其他形式继续存在,比如新年音乐会后来就演变成春节晚会;一些传统活动随着网友年龄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变化而悄然改变,比如2015年开始,足球联赛开始增加青少年和“老猪”的附加联赛,形成中年、青年和少年不同年龄段的完整赛制。与此同时,社区也在不断产生新的传统。2010年以来,最初一批网友们的孩子逐渐成长,“亲子小屋”论坛陆续组织“圣诞老人到我家”(2013年以来)、少儿春节联欢晚会(2014年以来)、“亲子嘉年华”(2012年至今)等围绕孩子和家庭的传统活动。网友的下一代也开始成为新的社区网使用者。2014年12月,社区网成立了小记者团,确定了正式小记者10名、预备小记者15名。一年后,举行了第三批小记者加入仪式,小记者团已经共计有40名在册记者。“小野猪”们开始以各种形式登上社区网,参与传统活动,持续建构社区和社区网的历史,开始形成新一代网友自己的集体记忆和“连续性”。
几十个论坛和经由社区网组织的活动都是网友自组织管理。社区网结构上是一种扁平化“网络”而非等级制垂直结构。虽然,网站存在“站长”“副站长”和论坛“版主”的层级结构,但是在具体操作上,版主基本上是自荐和推荐,再经网友们认可选出;版主负责论坛日常秩序维护,站长和副站长只有当网站出现巨大纠纷或者出现重大问题才会以协调人的身份出现。大多数情况下,社区网的活动和社团都是网友自组织建立,与站方没有直接关系。
(5)区块链自身的安全问题。区块链在为IoT提供安全防护的同时,自身也面临着一些安全威胁,如eclipse攻击、路由劫持攻击、51%攻击、智能合约漏洞等,这同样为2种技术的融合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
社区网的自组织过程具有赋权社区的作用。尽管社区网是一个虚拟社区,但是它在组织日常活动的时候必然要处理与相关组织的关系问题。因此,不能脱离组织环境而谈“自组织”,而是应该从嵌入性情境出发分析自组织的具体过程。[20]社区自组织始终发生在与地方政治与社会组织的相互作用之中,不能二元论式地将国家与社会或者社区自组织和政府部门对立起来,[21]而是需要从社区、权力和市场的复杂交织和角力之中理解社区自组织的发生情境、过程和自组织能力的培育。一方面,网友有普遍的倾向试图排除街道办事处的介入;另一方面,社区网在组织活动时又需要从街道办事处获得政策意义上的“合法性”支持,以及经济和社会资源的供给。对于后者而言,作为原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他们缺乏足够能力组织和动员普遍接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群体。庆幸的是,社区网填补了这个社区治理的空缺,它几乎以自组织的方式将大量社区居民连接起来。许多社区网的活动获得中外媒体广泛报道,取得了广泛的社会知名度。无论是从社会控制还是业绩的需求上看,街道办事处都有强烈意愿参与到社区网的组织中。而社区网的精英则要直面自组织和政府组织之间充满紧张的“双重运动”。
虚宁寺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静。虽然靠近昆明市区,但是虚宁寺仍然给人几分闹中取静的直观感受。由于地处昆明北市区,长虫山东麓的半坡上,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许多人都喜欢到此一带登山、郊游,中途顺便到寺里休憩,吃顿素食,行人零散却也是络绎不绝。
社区网精英作为网友和政府部门之间的纽带和缓冲,策略性地参与政府部门的组织和要求,努力减少后者对自组织的干预,疏解网友的不满和对抗情绪。幸运的是,街道办事处也比较好地尝试在获得业绩与控制的同时,将更多的社区活动组织与动员交给社区网及其自组织群体。双方在争议、冲突和协商中互相学习与适应。社区网网友不断积累保持自主性、减少对抗的“实践知识”,在“合作”和“协调”中动员政府的资源为网友服务;不断了解社区服务的政策,积累组织和沟通经验。对于H社区而言,在这种纠结中成长是一个赋权的过程,进而也是一个打造“社区”的过程。
(二)社区传统的发明和再发明
霍布斯鲍姆等学者强调,很多貌似古老的传统实际上都是当代人“发明”出来的。被发明的传统具有“仪式”特性,通过“重复”受规则控制的实践活动,表现与过去的“延续性”。[22]这种“重复”使得它具有了一种神圣感和历史感,有助于促进民族认同和归属。传统的发明通常在社会剧烈变迁的时期更为频繁。发生转变的社会团体、环境和社会背景呼唤新的发明,以确保或表达社会凝聚力和认同,并建构社会关系;变化中的社会也要求新的统治方法或建立忠诚纽带的新方法。[23]
传统可以区分为官方的非官方的,它们在行动主体和组织性程度上有所不同。官方发明的传统是“国家或有组织的社会与政治运动”形成的;非官方发明的传统则形成于不那么正式的社会团体中,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的”传统。前者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实践,而后者则来自草根的或“社会的”自发性实践。H社区传统的发明属于这种“社会的”传统范畴,来自于居民自发自组织的、分散的、没有非常明确意图的发明和创造。
[13]高云红、郑中玉:《基于嵌入性的社区自组织》,《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H社区所在位置原来是几个村庄,因此现在的居民都是非本地的“外来人”。它并没有遥远的“过去”,进而也就缺乏所谓的“社区传统”。但是,在社区网的凝聚下,H社区正在形成自己的“传统”和历史。这种历史不是试图和遥远的“过去”建立一种“连续性”,而是重新制造一种属于自身的“过去”及其“连续性”。从最初形成一直到现在近20年间,这种连续性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网站的周年庆典(至今举办了18届),社区趣味运动会,社区足球联赛(至今举办了15届),新年音乐会(后来改成春节晚会,至今举办了9届)等等。人们对H地区历史了解很少,但是对社区传统活动却了解甚多。在传统活动创意的协商、组织和广泛参与过程中,网友们走出虚拟网络,开始重构地域性社区的历史。社区网的传统和历史逐渐被等同为社区的传统和历史。在社区传统的生产与实践过程中,社区认同以及个体对于社区成员身份的自我意识也被生产出来。
无线充电的基本原理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电磁感应,另一个是感应电动势。电磁感应的基本原理如图1所示,当在送电线圈输入直流电流时,送电线圈和受电线圈中就会产生磁场,在受电端,通过闭合电路在磁场里做切割磁场运动从而产生感应电动势,感应电动势在受电端的闭合回路中驱动电子形成电流。通过这个原理,当送电线圈的磁场量不断变化时,送电线圈与受电线圈之间的磁场会产生变化,从而带来受电线圈中的磁通量不断改变,达到改变受电回路电流的大小,提供不同功率的电势,再将这部分电流整合为直流为设备充电。[2,3]
(三)社区精神的锻造
[8]郭于华、沈原:《居住的政治》,《开放时代》2012年第2期。
首先,社区网自组织本身具有民主和自愿的特性。网站的组织结构倾向于是平面化的“网络”而非等级化的结构。各论坛由网友自发组织和协调日常秩序。通过社区网所组织的各种团体和活动以自愿和协商为主,各种组织规则也是在协商、冲突和妥协之中不断确立起来。2006年以前,网站还有一个“社区猪大”,即当版主无法解决论坛里的事务,可以向这个代表大会提交提案,然后代表进行投票。最多一年(2002)的提案有28次。而站长个人的提案则若干次被否决。用“班长”的话就是,社区网上“没有谁去管着谁”。网站也没有权力施加单方面的任何决定。各种传统活动的倡议大多是网友们的创意,再由网友志愿组织和参与。甚至,在一些活动的组织过程中,站长和组织者会直接受到网友的批评。
其次,社区网有非常普遍的互助精神。一个非常典型的社区网场景是,网友们遇到疑难都会到论坛求助,从买房、装修到购买一应物品和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许多论坛的网友搜集了各种大家需要的电话和地址等信息,为其他人提供方便。这些信息基本上是网友们在自发汇聚的基础上积累而成,甚至在网友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状况下,各种社区内外信息都可以在虚拟网络中传播。
社区网也提供了一种情感支持网。比如在“亲子小屋”论坛里,围绕着家庭关系、情感和孩子抚养等问题,形成了大量的交流和社会支持网络。一些富有声望的明星妈妈经常会给年轻的妈妈网友提供人生的建议,互相开解,纾解怨气。“亲子小屋”的网友们还自发组织成立了一个“亲子图书馆”,将大家募集的儿童书籍汇集,通过网友志愿者日常管理,免费供社区的孩子们借阅。至今,这个图书馆已经经营了十几年,设立了3个分馆。
在制作教学课件过程中,应避免页面中文字过多,教师要发挥创意思维,运用各种形状、点、线、面等修饰内容,让教学内容简捷易懂,以最优美的方式呈现。教学内容的布局没有固定的模式,但也有一些常用的布局方式,如图4所示,竖向、横向、错位、阶梯等列表排列方式,教师还可以创作出更好看的排列方式。
最后,社区网具有深入人心的慈善和志愿精神。网友自发组织慈善活动是社区网非常普遍的场景。几乎每个月都会有网友发布慈善号召,也经常有社区外的人到社区网寻求帮助。不完全统计,2006年社区网慈善活动就有儿童运动会募捐、为烫伤女婴义卖玉米、帮残疾人艺术家义卖、为半瘫少年集善款、组织车友远赴外地支教等不下10余次。2007年下半年,仅仅是当时研究者所了解的慈善活动就不下6次,帮助网友寻找母亲、为兔唇和白血病的孩子募捐、为西藏和内蒙古边缘地区的孩子们捐衣物,以及为盲童捐助挂历等等。由于活动太多,最后促使社区网“慈善法案”的形成,建立了一个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协会,试图规范社区网上的慈善活动,保护网友们的公益热情。这种慈善热情一个直观表现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网友通过社区网上的号召和商议,迅速在社区设置志愿者和捐助地点,在两天内募集了40多万元的捐款。
三 多元的“想象的社区”(imagined communities):社区生产的认知机制
社区网自组织过程推动了社区传统的形成,通过社区传统的重复实践建构社区历史的“连续性”,也同时锻造了社区网的民主、互助和慈善精神。这些传统和精神建构了社区认同,很多网友都因此为自己的社区而骄傲。一个陌生人的居住区通过这些自组织行动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当然,人们如何将一些与自己没有直接关系的人们视为“我们”的一部分,如何将一个诺大的生活空间视为自己的“社区”,这其中还包含一个认知的过程。
H社区有独特的生活方式,网友们通过社区网来建立社会网络以及组织日常生活。社区网的产生和发展与虚拟社区和互联网在21世纪初于中国的发展是同步的。虚拟社区的匿名性、开放和自由精神同步融入H社区内部交往和生活方式,也同时形成H社区与同一时期其他类型社区的区别。社区网日常活动号召、动员和组织,平等和志愿精神都体现了虚拟社区的交往规则。这不仅仅体现在网络语言对日常交往的影响,也体现在日常组织中参与者都仍然保持着虚拟社区的身份(比如网名)。社区网友即有共同体的“亲密”,也保持着彼此尊重的“社会距离”;可以保持网友关系的自由,也可以避免常规社会关系的亲密所带来的隐私性问题。社会关系的形成不是简单基于共同归属的地方,而是基于个体的“选择”或反思性监控。人们可以反思性操控彼此关系的距离和关系中潜藏的义务。
外向性问题行为指在课堂上比较容易被发现的问题行为,包括一些对抗性行为,如课堂上争吵、挑衅、和老师对着干等;还有一些扰乱课堂秩序的行为,如随意说话、发出怪声、模仿老师说话、吃东西等;也有一些诸如玩手机、写别的作业、看课外书等行为。调查显示,外向性行为是中职生比较普遍的课堂问题行为。大多数学生无论学习好坏都表示自己或多或少存在外向性问题行为,只是轻重程度不同。
安德森将民族视为一个“想象的社区”,而社区的“想象”关键就是如何建立一种“相互联结的意象”。一切社区都需要这种“想象”,区别在于“被想象的方式”。[27]总体上看,一个能够“穿越时空的、稳定的、坚实的同时性概念”是成员想象自己是共同体一员的基础。它会在空间上彼此分割的成员之间建立一种想象的连带。在这种意义上,甚至消费也可能有助于形成这种“想象的连带”,促进社区的想象。[28]在波德里亚看来,消费就像语言一样,作为一种“沟通行为”而存在。消费者之间建立一种虚拟的联系,同时保持一种与“他群体”的“区分”。比如,“阅读”行为就扮演着联络符号的角色,是在和某个抽象的共同体,和所有潜在的集体进行联络。[29]
不同的共同体可能还有各自促进想象的社会条件。安德森具体分析了不同阶段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制度化因素。制度所造成的隔离和歧视造成了群体的边界,形成对共同命运的认知。比如,美洲民族主义和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民族主义的形成中,一种“被束缚的朝圣之旅”[30]就发挥了重要作用。美洲殖民地人民接受和母国相似的教育和拥有共同的语言,亚非殖民地的土著精英无论在语言和文化上如何与殖民地母国保持一致,他们都同样无法进入母国政治体系。这使得殖民地精英日益形成一种内部的“连带”,意识到一种“共同的宿命”。对于H社区的想象而言,符号的关联、社会隔离和内部团结等因素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首先,H社区从社区网建立开始就形成了独特的符号体系与生活方式。安德森强调,无论是神圣语言之与宗教共同体,还是19世纪地方方言和印刷语言之与欧洲语言民族主义形成,语言都有助于形成一种“符号的共同体”。19世纪的欧洲,在方言和印刷语言基础上,形成了各种类型组合的“阅读联盟”,“以方言想象出来的共同体”。随着识字率的上升,知识分子和资本主义企业家结合起来,推动了这种“阅读联盟”的形成,唤起民众支持。H社区居民也具有符号意义上想象社区的能力。社区网有自己的语言符号。他们称“业主”为“野猪”,将社区网上的老资历网友称为“老猪”,男性网友是“蓝猪”,女性网友称为“粉猪”,称他们的孩子是“小野猪”。此外,他们也有一些自己具有网络风格的语言习惯,比如“CP”(串啤,即肉串儿加啤酒)、“LD”(即领导,对家里女主人的称呼)、ZZ(即猪猪,对业主的称呼)和“腐败”(即AA制聚会)等等。网友们自发设计了社区网的标识,一个野猪的卡通形象。很多网友将这个图标印制在私家车、各种社团乃至店面的标识上。这些独特的符号系统只有内部社区成员才能理解,借此建立成员之间的虚拟关联,发挥着建立群体边界的作用。
山羊乳100 kg→65℃预热→6~8 MPa均质→85℃杀菌15 min→冷却至45℃→接种发酵剂→灌装→发酵→冷藏→成品
用网友FL的话来说:“我们并不是网友,其他的朋友是通过电话联系,而我们是通过网络。只是以网友的形式存在,但是关系要比网友亲近多了。”当然,由于有共同归属的地方作为根基,社区网的关系比一般虚拟社区的关系更加具有“真实性”的基础。一方面,共同物理空间的约束会给在线行为施加一定道德约束,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社区网上关系确立的可靠性。这种在所谓“真实和虚幻”之间的交替,虚拟社区与现实空间的交错成为H社区独特的生活形态和日常生活场景,不断凸显与其他社区的区别,巩固内部“一体”的想象。
其次,空间与社会的隔离有助于促进内部共同性的形成,造成交往的内卷化。H社区具有非常独特的形成过程和生态学上的特殊性。大多数网友是B市最早的经济适用房购买者,拥有共同的身份和集体利益诉求。每一次经济适用房政策调整及其传言都会引起整个社区网的持续热议。这也使得他们共同的身份得以持续具体化和清晰化。他们都倾向于是由于学习和工作原因移民到城市,具有“外乡人”或“农村人”的相似出身;在职业和教育上具有很大相似性,普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以从事IT和教育行业为主。相似的生活和教育经历,相似的与城市的关系,相似的居住状况等造成“共享的”城市身份和观念。
H社区和主城区有巨大的空间隔离。居住区位于城市北部,距离城区约15公里。2000年最早的三个小区入住时,地铁还没有通车,只有一两条公交线路,生活设施也严重缺乏。这种物理“距离”自然地形成网友与城市以及原有社会网络的隔离。有网友称之为“孤岛”。这种社会和生态学条件加强了社区的边界,同时也造成社区交往的“内卷化”倾向,即在空间隔离造成日常生活和交往的压力之下,一种向内寻求归属、支持和认同的倾向。[31]当社区网提供有效的沟通媒介时,网友们就可以在这个陌生人居住空间寻求认同和建构新的关系网络,也驱动了一系列打造社区传统的行动,最终形成日常自组织秩序。
最后,虚拟社区空间也使得人们超越邻里空间与物理距离限制建立一种存在的“同时性”和“在一起”的感受。很多网友反复提到一个典型的H社区人的一天:早晨到了办公室,打开社区网,登录喜欢的论坛,一边工作,一边聊感兴趣的话题;在论坛上,与工作地相近的网友相约共进午餐;临近下班,相约晚上回到小区的“腐败”活动。每一天,人们在社区网“旁观”到无数人登录社区网,在线讨论,发布活动消息。即使大多数网友彼此并不相识,但是都“见证”和“旁观”他人以及网络的存在。这种生活方式成为网友的日常仪式,恰似安德森所说的“群众仪式”,产生着一种“同时性”的感觉,建立一种虚拟的“连带”。
2.整合。课程整合是超越不同知识体系,以关注共同要素的方式安排学习的课程开发活动,目的是减少知识的分割和学科间的隔离,把受教育者所需要的不同知识体系统一联合起来,传授对人类和环境的连贯一致的看法。课程整合的方法有开发关联课程和跨学科课程两种。教学中,笔者主要采用了开发跨学科课程。如周杰伦的《青花瓷》就可以与相关美术、语文内容整合,通过美术作品感受青花瓷的曼妙和美丽,通过语文朗读以及理解感受歌词的魅力和意境。
“仪式”最重要的功能在于“群体被集合起来”,“使心理倾向于兴奋起来”。[32]社区传统活动年复一年的“重复”,一方面建构了社区历史的“连续性”,同时也与日常虚拟空间中的仪式性生活方式共同作用衍生出一种“共在感”。它将人们联系起来,反复确证彼此之间的“连带”。不同网友对社区传统活动的参与和偏好不同,但是传统所带来的感受和认同感却仍然相似。和其他大多数女性网友一样,单身时期的FL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她日常主要参与“亲子小屋”和“单身乐园”论坛以及论坛所组织的活动。尽管并不喜欢足球,但是通过网友、足球联赛的活动信息和传统媒体对社区足球联赛的报道,她对足球联赛也有所了解,每当和居住在其他区域的朋友说起自己社区的足球联赛,总是会“感到非常骄傲”。
当然,社区的想象并不是“总体化”,而是一种多元的。我们总是习惯于将社区视为一个实体,好像它以“一体化”的方式存在。[33]实际上,作为“想象的社区”,社区存在不同的行动者,他们有不同的社区想象,同时社区认同也是“流动的和短暂的”,充满了争议、论证和协商。[34]对于网友而言,这种多元的想象可能包括几种方式:有的网友对社区的想象是基于为社区网上的“人情味”和“互惠”所感动;由于大量社区传统和社区精神获得公众的认可而骄傲,最终在彼此之间形成某种“集体意识”;基于具体的关系网络或“圈子”实现对社区的想象。除此之外,部分并不积极参与社区网的人仅仅是“旁观”社区网的集体欢腾就可能产生一定的社区意识,认为这里“很好”;而其他“身居”社区网之外的人们可能基于个人关系网络而想象自己的社区,呈现一种“脱嵌的”社区解放论所描述的状态。
4)怕积涝。大樱桃园长期积水容易导致根系缺氧,呼吸困难,甚至产生厌氧呼吸,根系中毒,吸收根死亡,叶片萎蔫变褐,失去光合能力,出现死树现象。
四 简要结论与讨论
如上分析,大多数社区研究倾向于结构主义立场,习惯于假定“社区”的存在,继而讨论社区管理和治理问题。实际上,甚至像民族这样的“社区”或“共同体”也不是一个自然的单位,而是一个“区分和分离”活动的结果,需要通过行动建构而成。[35]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社区”之形成也是如此。区别于强调政治性集体行动生产社区和作为“社会学干预”的社会精英发动的社区营造两种方案,本文尝试揭示出一种社区成员通过日常生活意义上的自发自组织过程打造“社区”和想象“社区”的路径:社区的生产是一个持续行动的结果,行动者自发的社区自组织行为创造了社区传统,锻造了社区精神。正是这些反复的集体实践打造了社区。另一方面,社区的生产也包含一种认知机制。空间与社会隔离造成了交往的内卷化,各种产生内部团结的因素以及虚拟社区作为交往的社会空间形塑了“同时性”和“在一起”的时空认知共同促进了对社区的想象。
网站发展也缺乏整体规划。副站长LNN表示,网站的成功恰恰来自于“目的性不是很强”,一开始“就是想要买房,搞个网站大家在这里交流吧。一步一步就起来了。这是一个挺重要的因素”。正是因为缺乏“目的性”和缺乏“管理”,依靠网友自发组织塑造了社区网的巨大繁荣与活力。社区网常规的活动都是来自于网友的创意与自发动员,主要包含组织性的和非组织性活动两种类型。“非组织性”活动具有随意性,没有确定的组织结构,没有固定组织成员和组织者,比如旅游、文化沙龙和集体采购等活动。实际上,社区网上大多数活动都是“非组织性”的。“组织性活动”则具有比较规范的组织结构和规范,固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比如足球、篮球、羽毛球、排球、网球等体育运动俱乐部。其中像足球运动甚至组织起非常规范、成规模的联赛体制,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网友们在自发活动中通过协商、冲突和妥协最终形成组织与活动规则。
当然,尽管我们呼吁不要将“社区”的存在视作“自然而然”,应该转向对社区生产过程与机制的研究,但是也应该意识到社区的生产并没有一种普适机制,进一步研究需要关注社区情境的特殊性以及不同行动主体社区实践的复杂性。比如,不同的集体记忆和共有的历史,或者面对共同的外部困境进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客观需要,这些不同的资源是否产生社区生产的不同可能性?社区生产的自组织路径和都市运动以及社区营造的专业化行动如何相互作用,社区营造和都市运动如何形成一般的社区社会资本以及如何促进社区自组织?最后,也要关注社区的非本质主义以及社区生产的过程性。社区不是总体化的、不变的生活世界。从一种“流动的现代性”视角出发,一方面,所有“社区”都是“跨越边界的”,即关系和社会空间的去边界化;另一方面,它们也都是“流动的”,即社区行动者的变动不居以及由此造成社区生产具有动态的过程性。它需要不断经历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绝非一劳永逸的建构。这就要求研究者持续关注行动者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发现日常生活空间中生产社区的诸多可能路径。
注释:
[1]Barry Wellman,“The Community Question: The Intimate Networks of East Yorker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5(1979).
[2]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晚期癌症病人最为常见的症状之一就是疼痛,由于受到疼痛的折磨,病人的生活质量显著下降的同时还会伴有恐惧、焦虑、悲观、厌世等负面情绪,正是这些负面情绪可再次增加对疼痛的反应。所以,针对晚期癌症病人采用疼痛护理是十分有必要的。作为一个关键而且重要的护理措施,如何来减轻病人的疼痛等级,改善病人的情绪反应,提升病人的生活质量这一问题得到了医务人员的关注。
[3]郑中玉、梁本龙:《非线性视角下的社区实践与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期。
[4]郑中玉:《社区性质与发展趋势的争议》,《河北学刊》2016年第6期。
[5]Maurice Stein,The Eclipse of Communit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0,p.303.
[6]郑中玉:《选择性关系与反思性社区》,《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7]沈原:《社会的生产》,《社会》2007年第2期。
“历史”以及所谓“传统”是行动合法性的依据和团体一致的黏合剂。[26]通过行为的“重复”、广泛的参与来建立与“过去”的“连续性”,进而产生增强团体凝聚力、促进社会动员和认同、保持群体差异的效应。霍布斯鲍姆强调,“传统”就是通过“重复”来灌输某种“价值观”或精神。社区传统虽然在“仪式性”和“象征”属性方面比较单薄,是为了社区生活和动员的需要而被发明的实践,也没有系统的具有完整规划的组织过程,但是传统的作用却是相似的。在网友们的交往和传统的实践中确实凝聚着独特的充满魅力的社区精神。
[9]陈鹏:《从“产权”走向“公民权”:当代中国业主维权研究》,《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陈海萍:《社会资本与拆迁户维权行动》,《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石发勇:《社会资本的属性及其在集体行动中的运作逻辑》,《学海》2008年第3期。
[10]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11]詹姆斯·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39页。
[12]沈原:《社会的生产》,《社会》2007年第2期。
1.3.2 考试成绩比较。1)理论知识考核:包括主观题(血液与肿瘤疾病病例分析60分)和客观题(血液与肿瘤疾病基础知识40分);2)实践技能考核:病例分析,学生针对一名血液疾病SP进行病史询问、体格检查给出初步诊断、诊断依据及治疗方案等(50分);对学生的临床沟通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随机应变能力打分(20分);血液与肿瘤疾病常见检查操作考核(血常规检查、血细胞涂片、骨髓穿刺操作、骨髓片的结果分析等)(30分)。
5. 论文标题:X射线荧光光谱法测定白云石、石灰石中氧化钙、氧化镁和二氧化硅;文献来源:冶金分析,2014,34(1):75-78;作者:乔蓉,郭钢;机构:涟源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4]吴晓林、谢伊云:《房权意识何以外溢到城市治理?》,《江汉论坛》2018年第1期。
[15]彭澎:《日本“社区营造”论》,《日本学刊》2013年第3期。
[16]河口充勇等:《社区营造与民间团体的功能》,《中国第三部门研究》2013年第2期。
[17]李培林:《当前社区研究的三个面向》,《清华社会学评论》2017年第七辑;吴海红、郭圣莉:《从社区建设到社区营造:十八大以来社区治理创新的制度逻辑和话语变迁》,《深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18]罗家德、帅满:《社会管理创新的真义与社区营造实践》,《社会科学家》2013年第8期。
森林高火险预警期,所有扑火队员保持24h通信畅通,整装待命,全员处于临战戒备状态,一旦发现有火情,根据森林防火应急预案,以最快速度出击,快速扑救,确保实现“打早、打小、打了”。扑火队员到有关乡、镇、场扑救的,队员必须服从上级指挥官指挥。
[19]沈原:《“强干预”与“弱干预”:社会学干预方法的两条途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5期。
[20]高云红、郑中玉:《基于嵌入性的社区自组织》,《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
[21]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社会》2007年第6期。
[22]E.霍布斯鲍姆、T.兰格主编:《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2页。
[23]E.霍布斯鲍姆、T.兰格主编:《传统的发明》,第338页。
[24]Paul Kennedy and Victor Roudometof,“Transnationlism In A Global Age”,Paul Kennedy and Victor Roudometot eds., Communities across Borders: New Immigrants and Transnational Cultures, New York: Routledge,2002,p.9.
[25]E.霍布斯鲍姆、T.兰格主编:《传统的发明》,第6-9页。
随着微创技术的发展,不断追求更小的创伤、更好更快的康复及更满意的美容效果是外科医生与患者共同的目标。经脐单孔腹腔镜技术比传统腹腔镜技术更加微创,是腹腔镜技术不断向微创方向发展的大势所趋。改良式经脐单孔腹腔镜技术乃是通过脐部这一天然入路进行手术操作,因脐部皮肤原有的皱褶可以遮盖切口,实现“无瘢痕手术”的目的,故而具有更好的美容效果[2]。
[26]E.霍布斯鲍姆、T.兰格主编:《传统的发明》,第5页。
[27]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第6页。
[28]于文洁、郑中玉:《基于消费构建想象的社区》,《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1期。
[29]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30]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第56页。
[31]郑中玉:《选择性关系与反思性社区》,《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
[32]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6页。
[33]W.H.Isbell,“What We Should Be Studying: The ‘Imagined Community’ and the ‘Natural Community’”,Marcello A.Canuto and Jason Yaeger eds., The Archaeology of Communities: A New World Perspectiv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2000,pp.245-252.
[34]Mark Varien and James Potter,“The Social Production of Communities: Structure,Agency,and Identity”,Mark Varien and James Potter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ies ,AltaMira Press,2008,p.4,p.16.
[35]齐格蒙特·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
中图分类号: C9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38(2019)05-0064-0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区治理研究”(12CSH03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HIT.HSS.201854)
作者简介: 郑中玉,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博士,哈尔滨市,150001。
责任编辑 刘秀秀
标签:社区网论文; 自组织论文; 社区的生产论文; 想象的社区论文; 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