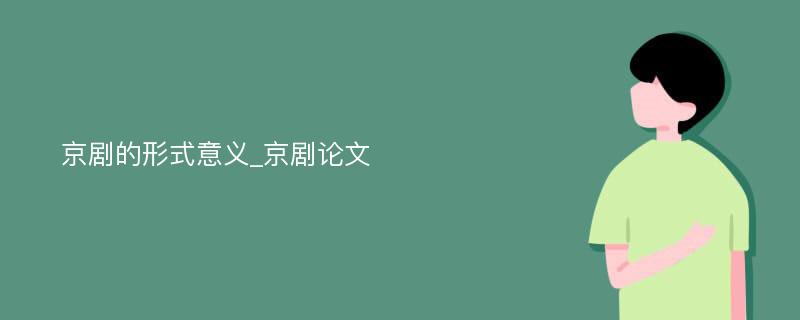
京剧的形式意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剧论文,意味论文,形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意味的形式”,这个克莱夫·贝尔的著名美学命题,换做中国话说,不妨视作是关于形神关系的一种西方表述:所谓“意味”,就是“神”;“有意味的形式”,就是“形神兼备”。“兼备”自然是最佳之结果,但这并不等于“形神”便可以等量齐观。古人说:“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①]又说“以神为主者,形从而利;以形为制者,神从而害。”[②]这就是说,“兼备”的主要方面在于神而非形。我们说过,形式大于内容;从这里的分析看,则神须胜形,也就是说,意味大于形式。由“形式大于内容”之“大”,到“意味大于形式”之“大”,应该说是层层推进,而最终达于庄子的“大美”之境。这是我们对于内容、形式、意味之间关系的一个概括认识。下面仅从京剧的歌、舞及其内涵之精神三个方面对此作些讨论。
一、“大音希声”
王元化先生在谈到京剧的词句与腔调的关系时,曾指出这么个较为独特的现象,即京剧“在遣词用语上显得十分粗糙,但在音调韵味上是极为精致的,目前尚无出其右者”;而“用俚俗不雅,甚至文理不通的词句,竟能唱出感人肺腑的腔调,这似乎不可思议,但事实确实如此。”[③]然而,这个“事实”正如王先生所说,却是“京剧中最引起争议的”——岂止是“争议”,而且是一些人否定京剧的依据。对此,王先生的认识是:
但必须注意,京剧唱词大都是老艺人根据表演经验的积累,以音调韵味为标的去寻找适当的字眼来调整,只要对运腔使调有用,词句是文是俚,通或不通则在其次,因为京剧讲究的是“挂味儿”……这就是说,把词句当作激发情感或情绪的一种媒介或诱因,使音调韵韵成为感人的主要力量。[④]
首先,我们注意到,这种求韵味而不讲词句的现象在京剧中是较为典型的。其所以出现,一是文化水平不高的演员的参予。二是因经名家唱成“定局”而不易更改。谭派研究家陈彦衡就说过谭鑫培改《武家坡》和《汾河湾》的旧词,“殊不若旧词之恰合剧情也”,也就是说,他改的词不合剧情,可“演此二剧者,大半皆本谭词,不但不肯改易,且目此段为全剧精华。盖其声调佳妙,久已脍炙人口,虽欲割爱,有所不能。古人谓声音之道入人最深,岂不信哉。”[⑤]可见这“脍炙人口”的力量。三是如秋文(叶秀山)所说,“反映了中国戏曲中音乐性与文学性之间的矛盾”,而演员们在这种矛盾面前,竟常常迁就音乐性,所以后来即使有些演员文化修养并不差,但对某些词句明显不通处,也并无改动。譬如《珠帘寨》中‘哗啦啦打罢了×通鼓’,曾被认为不通,[⑥]因为鼓并无‘哗啦啦’之声,但因情绪气氛关系,演员宁可词句不通,也不愿改唱‘咚咚咚’……”[⑦]所以出现这种“迁就”,其原因大概也如秋文所说,“中国古典京剧本质上是一种古典的歌剧”,“对它应作歌剧观”。[⑧]启功也说:“听皮黄戏词中的‘抬头看见老爹尊’、‘翻身上了马能行’等句,曾经失笑:爹当然尊,安能爹卑?马当然要能行的,不能行的,又安能骑?后来明白歌词受曲调的制约,出现削足适履、狗尾续貂的现象,可以原谅。”[⑨]
由此而说到其次:这种现象有否合理性?换言之,其根据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须先置一词的是,如此求答,并非是鼓吹京剧文理不通,无论怎么说,“不通”总是不好的;不过,这里讨论的是已有的“存在”,就有一个如何认识这种现象的问题。还是王元化先生说得好:“在京剧中,音调与词句俱佳,自然最好,倘不能至,我认为,正如作文不能以词害意,京剧也同样不能为了追求唱词的完美而任意伤害音调韵味。”[⑩]这就是说,在音调词句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是只能“削”词句之“足”,而“适”音调之“履”的——这不是典型的形式意味大于内容吗?
或谓,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怎么就不能反过来“削”音调之“足”而去“适”词句之“履”,那不就是内容大于形式了吗?如此反诘,似不无道理;问题在于,这种谁大于谁,不是任意的,其中确乎存有合理性。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人唱着某个唱段时,他可以只哼腔而去词,却断无只念词而不要腔的;“戏考”一类唱词的印制也主要是为便于人学唱,而不是供人阅读的。苏珊·朗格说,“音乐是‘有意味的形式’,它的意味就是符号的意味,是高度结合的感觉对象的意味。音乐能够通过自己动态结构的特长,来表现生命经验的形式,而这点是极难用语言来传达的。情感、生命、运动和情绪,组成了音乐的意义。”[(11)]这就是为什么在艺术的世界里,会有“无标题音乐”,因为它大于文字的语言;那些“言不尽意”的“意”,常常是可以在音乐中得到“尽”的。所以汪曾祺说裘盛戎演《姚期》,“他的唱腔具有很大的暗示性,唱出了比唱词字面丰 富得多的内容。”[(12)]音乐鉴赏家辛丰年更说:“我一直觉得,既像‘宣叙调’又似‘咏叹调’,简单之中包含了丰富的变化可能性,不古不今,又可古可今的京剧唱腔,恐怕是世界音乐文化中非常奇妙的现象。”[(13)]我们说,在京剧中形式意味大于词句的内容不是任意的,其合理性就在于此。
国学大师钱穆于此也有说法,其论可以说是与王元化先生之论相为呼应的:
有人说,中国戏剧有一个缺点,即是唱词太粗俗了。其实,此亦不为病。中国戏剧所重,本不在文字上。此乃京剧与昆曲之相异点,实已超越过文字而另到达一新境界。[(14)]钱氏所说的新境界,可以作多种解;而我们这里联想到的是老子的“大音希声”,并有我们的读解:“声”在这里,是较为确定的内容,而当“音”的旋律达于“至美”而具某种境界,亦即构成“大音”时,“声”的内容便稀释了,变得不那么要紧了,变得可听可不听了(老子:“听之不闻,名曰希。”),而至于最后成为“大音”的一种“导(或“载”)体”,使人们在“恍兮惚兮”中去领略那如“兰田日暖,良玉生烟”般的“大音”,即矇眬难测、意味不尽的境界。由此,我们说,王元化先生所指出的京剧“把词句当作激发情感或情绪的一种媒介或诱因,使音调韵韵成为感人的主要力量”的这样一种客观实存,其见解是十分透辟、深刻的。在这里,形式决定内容的艺术现象得到了集中而鲜明的体现。
海德格尔说:
道出的从不在所云
被道出的尽在不言中。[(15)]
沿着海氏这“诗意的”“运思”,也许我们可以说:
道出的从不在词句
被道出的尽在韵味中。
二、“大象无形”
上文说的是京剧中“歌”的因素,我们以为是“大音希声”;这里要讨论的是京剧中“舞”的因素,我们则以为可以概括为“大象无形”。
前面说过,京剧的程式动作既有生活依据,同时又经过了抽象变形。这种抽象变形的程(幅)度是有高低大小之别的,于是,我们便看到了舞台上的两种形态的“舞”:
一种是离生活原形虽有一定的距离,但还在人们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尽管要经过一定的想象和联想。比如,《秋江》中船上的许多动作,《拾玉镯》中喂鸡、做针线活的动作等,均是。
一种是与生活原形已经基本脱离了的,人们对之难以作出判断,想象和联想机制也起不了什么作用,总之,是不经人作出解释便无从理解。比如,“起霸”、“走边”以及前举的“挡袖”一类程式等,均是。
上述两种形态的程式动作,前者因属较为直接摹拟生活动作而表现为有形(生活之形),不妨称作“形”的动作。后者因抽象变形程度高而显得模糊、浑沌,而具象征性,不妨称作“象”的程式。下面,我们从三个方面就二者作些比较,以见出形式意味之所在。
第一,说“意味”,自然离不开“意”;而“意”与“象”之关系尤大。《周易·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故“圣人立象以尽意”。《周易》这里指说的“象”,是卦象之象;为什么要“立象”呢?为的是“以尽意”,可见“象”之于“意”的重要。而之所以要“立象以尽意”,则是因为“言不尽意”。确实,比诸“象”,“言”一旦说出,便有了限定。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一类的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而比诸“言”,“象”则具有模糊、不定的多义特征(故《周易大传》才有那么多的释解),正因为此,“象”才更具有接近“尽意”的功能。下面我们据此来说说京剧中的“象”的程式。
这里以“起霸”为例。从总体上说,我们知道它是古时大将出征前“整装待发”的准备活动;但从构成这一套完整的程式舞蹈的每一个具体动作及相应的组合单元来看,你很难说出一个“云手”,一个“跨腿”,一个“抖靠旗”究竟表现了生活中的什么。所以,那些初接触京剧的人,看到这些,常常莫名其妙,不知演员抬手投足之所指——唯其没有具体所指,只具象征意义,它才可能充满“意味”而味道无穷。
反观“形”的动作,由于它是对生活的某个形态的直接模仿,而让人们一目了然,比如《拾玉镯》中的喂鸡,虽然也是虚拟的、夸张的,但谁也不会看不明白;而一旦这一组动作完成,它所要“演”之“意”也就表达完了,很难说还有什么更多的“意味”蕴藉其间。这里至多只有摹拟表演的优、劣之别。说到表演,“象”的程式倒有个能否接近“尽意”的问题,这就不能不涉及演员的修养。有的演员一个“霸”“起”下来,该做的都做到了,可是让人觉得没什么味道;有的演员技巧不错,难度不小,来得花里胡哨,挺能唬住人,可以说是“尽象”了,却没有“意”。而那些修养高、造诣深的演员,也许抬手投足之间,并未到位,然其意味十足,让人玩味不已,如书法中之所谓,是“意到笔不到”,“笔不周意周”。而这一点在“形”的动作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它要的恰恰是“笔”要“到”,“意”到与否,倒无所谓,不然,模拟的像与不像便成问题了。可见,在形式的意味这一点上,“象”是大于“形”的。
第二,说到像不像的问题,“象”与“形”之间又有了差异。先说“形”的动作。仍由于其是直接模仿生活形态的,在演者就有了一个仿真的摹拟环节,而在观者则有了一个比较的观照环节。比如《秋江》这出戏,有许多船行江上的表演动作,扮演老艄公和陈妙常的两个演员就须密切配合,通过娴熟的表演而让观者有身临其境之感;观者也会因其维妙维肖的“形”的动作而由衷的赞誉一句“真像”。反之,一个蹩脚的演员因蹩脚的表演,也会遭到观者“一点也不像”的批评。可见,在“形”的动作这里,“像”与“不像”是居第一位的,也就是说,观者在这里首先作出的是认识判断。
再说“象”的程式。我们前面说过,因这些程式在艺术实践的不断抽象中,早已无法“还出娘家”,而于观者也就从根本上剔出了“真像”的认识判断;然而,这又从根本上保证了观者只能作出“真美”(或“不美”)的审美判断。当然,一个好的“形”的动作,同样也是可以博得“真美”的称誉的;但它毕竟是附着于“真像”的,也就是说,连“像”都说不上,是谈不上“美”的。这就使得其在“美”的程度上不及“象”的程式来得纯粹。可见,在形式的美这一点上,“象”又是大于“形”的。
第三,说到“纯粹”与否的问题,“象”与“形”在审美接受的范围里又有了差异。在“象”那里,能指就是一切,而不论所指,这就带来了对能指的理解问题;在“形”那里,因能指有所指的显现,也就一目了然。是故,我们才看到这么一种现象:一些不太懂戏的观众,他们能看“懂”“形”的动作,并发生兴趣;而出访演出的也多为《秋江》、《拾玉镯》这些主要为“形”的动作表演的剧目,外国人也看得如醉如痴。而对“起霸”这一类“象”的程式他们就因难以看懂而难以接受了。反之,那些懂行的观众,更为热衷的却是“象”的程式。也许如《周易·系辞上》所言,他们是要“观其象而玩其辞”,所以常常津津乐道于一招一式之间。他们非但不以“观象”为难,而且是要在“难”中咀嚼、品味、把玩,以觅得“象”中之意味而获得审美愉悦。所以他们能为一个“象”的精采表演而大喝其采,却很少为一个“形”的展示鼓掌叫好。可见,在接受的难、易程度上,“象”也是大于“形”的。
由以上三点之比较分析,可以见出,在“舞”的范畴内,京剧的形式意味主要是蕴涵在“象”中;“象”所以能得此蕴涵,又在于它脱出了对生活之“形”的直接模仿。是故,我们说“大象无形”。附带说一点,由于“象”的较难理解,出于让观众看“懂”的良好愿望,一些人对“象”似乎总不大看好,比如“起霸”的时遭非议(以至非难),即一显例。这实在是他们不知“象”中之意味,不懂“大象无形”的道理。当然,有意味之“霸”,眼下能“起”者,是日见稀少,这也就不能全怨人家了。
三、人生共相
有人说京剧剧目中很少哲理,是否如是,这里不作辨析;但我们可以说,京剧的形式意味中蕴含着哲理。余秋雨在谈到中国戏剧文化在艺术形式上有更多可以留存并发扬光大的因素时,曾明确提出:“作为一种艺术语汇,作为一种有魅力的符号,虚拟动作和程式也会大大地突破原有功能,而起到深层象征和隐喻的作用,从而提高中国戏剧文化的哲理素质。”[(16)]显然,在余秋雨看来,虚拟动作、程式这些形式因素,是可以具有哲理素质的,只不过他以为这是“突破原有功能”之后的事。事实上,戏曲,特别是京剧形式,其“原有功能”中即已蕴蓄有哲理,已具有“深层象征和隐喻的作用”。我们且看钱穆是如何说的:
中国戏剧之长处,正在能纯粹运用艺术技巧来表现人生,表现人生之内心深处,来直接获得观者听者之同情。一切如唱工、身段、脸谱、台步,无不超脱凌空,不落现实。[(17)]以为艺术技巧能表现人生,已是一大发现,且冠以“纯粹”二字,尤可见形式因中的哲理感之强。这还不说,甚至锣鼓在钱氏看来也含有哲理:
又如京剧中有锣鼓,其中也有特别深趣。戏台无布景,只是一个空荡荡的世界,锣鼓声则表示在此世界中之一片喧嚷。有时表示得悲怆凄咽,有时表示得欢乐和谐。这正是一个人生背景,把人生情调即在一片锣鼓喧嚷中象征表出……因此,中国戏的演出可说是在空荡荡的舞台上,在一片喧嚷声中作表现。这正是人生之大共相,不仅有甚深诗意,亦复有甚深哲理,使人沉浸其中,有此感而无此觉,忘乎其所宜忘,而得乎其所愿得。[(18)]这真是见人之所难见,发人之所未发。不要说有些人,以为京剧锣鼓只有喧嚷而一无它用,即使是我们的一些行家,也只限于对打击乐能打出时间、地点、环境、气氛、人物感情等这样一些认识;而钱氏却在这一片喧嚷声中听出了含有“甚深哲理”的“人生之大共相”。锣鼓尚且有此深意,就更不用说唱念做打等形式因了。总之,在钱氏看来,“京剧在有规律的严肃的表演中,有其深厚的感情。但看来又觉极轻松,因为它载歌载舞,亦庄亦谐。这种艺术运用,同时也即是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了。”[(19)]
这就是说,京剧,作为一门含诗、歌、舞的写意、表情艺术,其本身就体现(亦复体验)着人生之态度、方法、情趣。中国人的处世,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艺术人生。儒家“乐感文化”思想其中即有艺术人生的涵容。这里再就道家思想多说几句。庄子的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逍遥论中。有人批评庄子之主张是“游戏人生”。游戏人生可以有两个层次,一者形而上,一则形而下;下者系官能的、功利的,上者是艺术的、审美的。庄子实是形而上的,故其所谓“游戏人生”,亦即“艺术人生”,“审美人生”。庄子主张“逍遥游”,从根本上说,是对一种精神自由的追求。庄子要“游乎四海之外”“游乎尘垢之外”(《齐物论》),“以游无穷”等(《逍遥游》),并非是身之游,而是心之游,即所谓“且夫乘物以游心”(《人间世》)。如果说在庄子的时代,他的“游心”于“尘垢之外”的精神自由的追求,还只能是个人的一种精神体验而近乎于虚幻之境,那么,我们今天则可以寄寓于身外之“物”去体验这种精神的自由,这就是艺术(不妨称作“且夫乘艺术以游心”),接着我们的话题,便是京剧艺术,是审美的京剧艺术。从我们前面分析到的作为演者的余叔岩和作为观者的马叙伦来看,就在一个“演”、一个“观”的那一刻,因“外天下”、“外物”、“外生”(《大宗师》),亦即忘怀一切,便也就同时体验到了那种精神的自由。而这种精神自由的获取,正是通过形式因的意味、美感而得到的。
对艺术,人们有这样的划分,一是“为人生的艺术”,一是“为艺术的艺术”,后者是常常被批评的。因京剧被划为后者,故也屡遭批评,其中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指斥一些人只在一字一板、一招一式之间玩味。其实,这一字一板、一招一式之间何尝没有人生?只不过其人生不是浅直的、当下的、急功近利的;而是“有此感无此觉”的,“存神过化”的(钱穆语),“润物细无声”的。不然,以研究人生哲学著称的张中行何以能在老生腔中听出人生、听出天道呢?[(20)]张先生确乎悟透人生而于“戏”别有会心,我们就以他的一首绝句来结束这部分的讨论:
闻道浮生戏一场,
雕龙逐鹿为谁忙?
何当坐忘升沉事,
点检歌喉入票房。[(21)]
注释:
① ② 分别见于《淮南鸿烈》《诠言训》和《原道训》。引自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第4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7月版。
③ ④ ⑩ 《京剧与戏改》。见《思辨随笔》第299页,299页,301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⑤ 《旧剧丛谈》。见《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下册)第86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⑥ 持此论者为齐如山(《中国戏剧之变迁》),秋文就此以《法场换子》中有“催命鼓响咚咚”句为例,说“可见并非演员不知道鼓声‘咚咚’,而是照顾到当时的感情心境作出的选择。”(引见同注⑦)王元化也认为齐的这种批评“是苛论”。他说:“固然真实的鼓声不是‘哗啦啦’,但他没有从写意的角度去衡量。一旦走上这条什么都要求像真的形似路子,那么作为写意型的表演体系也就不存在了。”(引见同注③)事实上,“哗啦啦”、“响咚咚”的不同处理,还受制于腔调的不同设计。
⑦ ⑧ 《古中国的歌—京剧演唱艺术赏析》第75、76页,第76页。宝文堂书店,1988年5月版。
⑨ 《有关汉语现象的一些思考》。见《文史知识》1992年第7期第5页。
(11) 《情感与形式》第4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版。
(12) 《艺术和人品》。见《读书》1990年第3期第64页。
(13) 《乐中史史中乐》。见《读书》1990年第8期第45页。
(14) (17) (18) (19) 《中国京剧中文学之文学意味》。见《中国文学讲演集》第128页,第127页,第128页,第129页。巴蜀书社,1987年8月版。
(15) 引自赵越胜《语言就是语言》。见《读书》1987年第7期第133页。
(16) 《中国戏剧文化史述》第497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20) 《余派遗音》。见《负暄琐话》第18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
(21) 《戏缘鳞爪》。见《负暄三话》第19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