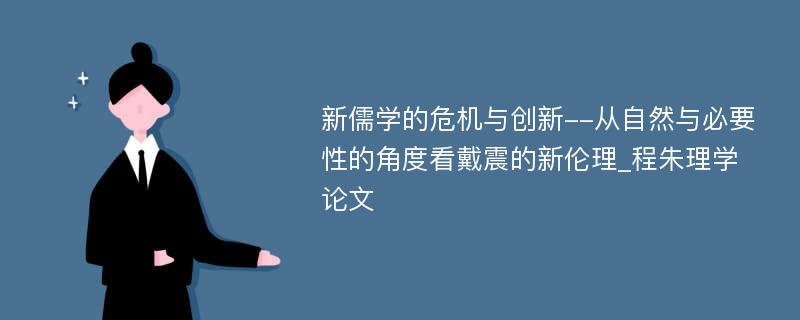
理学的危机与创新——从自然、必然的视角看戴震的新伦理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学论文,伦理论文,视角论文,危机论文,自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天崩地解”的剧烈变革,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们的理论与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巨大波澜,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启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运动的曙光。然而,明清之际这股昭示着学术自由、思想解放、人性复苏的社会进步思潮随着清王朝闭关锁国政策的实施、文化专制主义制度的加强以及对广大知识分子思想言论的钳制,渐渐成为历史的回忆。乾嘉考据学随之兴盛起来,成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又一里程碑。然乾嘉考据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治学之方法和目的,于明末清初之经世致用思想和民族忧患意识则鲜有深究和关注。惟有乾嘉考据大师戴震,发时贤所未发,超越前人,振臂疾呼,以复兴原始儒家思想为己任,遥承明清思想之余绪,在猛烈抨击宋明程朱理学及释、老思想的同时,提出了一种与传统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不同的新伦理观。本文仅就戴震新伦理观思想的一个侧面——自然、必然思想,做一简要评述。
一
十八世纪的中国思想界,虽考据学成为社会主流思潮,但程朱理学作为影响中国社会达八百年之久的官方意识形态,尽管已遭到明中叶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不同思想家、不同学术派别的猛烈抨击而日呈衰颓之势,但在社会日常生活及人们的价值观念中,程朱理学仍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戴震提出的关于自然、必然关系的伦理思想,正是与程朱理学宣扬的“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存天理,灭人欲”、“人欲净尽,天理流行”等观念针锋相对的。程朱理学以“天理”作为衡量、评判一切思想行为的价值标准,从根本上限制了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发展。戴震坚决反对这种荒谬的观点。他指出,人欲与天理问题,实际上就是自然与必然的问题。欲、理之极致便是自然、必然。人的自然情欲是人们从事其他一切活动的最基本前提。脱离了人的自然情欲,一切将无所归依,宋儒所谓“理”也便无存在之基础。戴震指出:“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孟子字义疏证·理》下简称疏证)。可以看出,戴震继承了明末清初以来注重个性自由与解放,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的思想,把人欲抬到高于一切的程度,并使之成为评判人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在乾嘉时代众多考据学者埋首于音韵、文字、训诂、校勘、金石等领域并以此为终身目的的时候,戴震的不同凡响之处表现在他只是仅仅把它们作为“闻道”、“明道”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其目的就是恢复被宋儒、释、老曲解了的原始儒学之本来面目,“以六经、孔孟之旨还之六经、孔孟”,把握和弘扬原始孔孟儒学之真精神,从而真正达到明义理的目的。戴震提出的新伦理观,正是其明义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震新伦理观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注重人性、人的自然情欲。那么,人性、人的自然情欲是如何产生的呢?对于这个中国思想史上争论不休的老问题,戴震仍援用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予以解释。他指出,人之为人,人性之为人性,不是悬于空中的天理赋予的,而是本之于阴阳五行。他说:“性者,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人物莫不区以别焉是也”(《疏证·性》),“言分于阴阳五行以有人物,而人物各限于所分以成其性”(《疏证·性》),还说:“血气心知者,分于阴阳五行而成性者也”(《疏证·诚》),“耳目百体之欲,求其故,本天道以成性者也”(《原善》卷上)。在戴震看来,“阴阳五行”是“道之实体”,分于道,就是分于阴阳五行。因此,他为“性”下的定义是:“性者,分于阴阳五行以为血气心知,品物区以别焉”(《疏证·性》),而性的实体是指“血气心知”。血气心知是从阴阳五行剥离分化出来的,在人性的来源这一点上,戴震坚持了性一元论的观点,而与宋儒主张的性分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的性二元论思想相对立。
二
自然、必然是戴震哲学思想体系中两个极为重要的范畴,是戴震气化流行之自然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戴震在对人的自然欲望作出本体论解释后,便对人的“自然”情欲进行了剖析。戴震所谓的“自然”,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人或物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状态;二是指人或物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戴震在其不同时期的著作中曾多次使用过“血气之自然”、“心知之自然”、“气化之自然”等话语,这些话语之表述虽字句不完全相同,但要表达的基本思想却是完全一致的。他试图向人们证明:就每一个个体生命而言,人性、人欲本身就是自然。他说:“性,其自然也”(《疏证·道》)。他有时称之为“性之自然”。戴震认为,从人的本性萌发出来的好利恶害之欲,怀生畏死之情,都是人欲的自然体现及合理要求,是与天地间生生不息、生化流行的宇宙规律相协调的。“自然者,天地之顺”(《原善》卷上),“其自然则协天地之顺”(《戴东原集·读孟子论性》)。就整个社会群体而论,戴震认为,社会中一切人物庶物,日用人伦,同样也是“自然”的体现。“实体实事,罔非自然”(《疏证·理》),“自然者,散之普为日用百事”(《原善》卷上)。具有本能情欲的生命个体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而成的社会群体,扩展了“自然”的外延,而其质的规定性却保持不变。一方面,“自然”的社会群体是“自然”的生命个体合乎逻辑的扩延和投射;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之“能够”存在,正是以人之本能情欲及血气心知为其建构基础,即所谓“日用百为,皆由性起”(《疏证·道》),“人伦日用,皆血气心知所有事”(《疏证·诚》)。因此,戴震所阐述的“自然”,是个体情欲与社会群体辨证关系的总称,“个体”与“群体”构成了“自然”关系中两个密不可分的侧面,二者之有机结合,恰好构成了“自然”的完整含义。
戴震对“必然”的阐释具有更为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批判意义。他所谓的“必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事物当然之条理,“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疏证·理》)。二是指人之行为的当然准则,所谓“尽乎人之理非他,人伦日用尽乎其必然而已矣”(《疏证·理》)。按照戴震的理解,“必然”对于“自然”的意义,只在于前者是对后者的最为详尽的概括,而不在于将“自然”的本质归之于“必然”,所以,戴震指出:“归于必然适全其自然,此之谓自然之极致”(《原善》卷上)。从自然之极致所把握的“必然”,并不具有本体论层面的含义,“推而极于不可易之为必然,乃语其至,非原其本”(《疏证·理》)。戴震回避探讨和穷究事物背后的“所以然”,是与他否认程朱理学以“无形无迹者为实有”(《疏证·天道》)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因而他主张,对事物的追寻,应有一定的限度,这个限度就是止于阴阳五行,“由人物溯而上之,至是止矣”(《疏证·天道》)。这里所说的“是”,便是称谓“阴阳五行”。前面说过,戴震所说的“必然”,实际就是指“理”,自然与必然,无非是戴震理、欲关系的一种具体展开和表述。“理非他,盖其必然也”(《绪言》卷上)。“必然”不是孤立悬搁的,它始终与“自然”融合为一体,是人的自然情欲的合理发挥和适当调制,即“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无过情无不及情之谓理”(《疏证·理》)。因此,从戴震的理论路径来看,人的“自然”情欲满足的过程,就是“必然”之“理”逐步确立并得以实现的过程,二者具有相辅相成、同步发展的性质。但是,“必然”不是无节制的,它对人的情欲具有规范和约束作用。戴震把人的情欲概括为欲、情、知三个层面,并指出“唯有欲、有情、有知,然后欲得遂也,情得达也天下之事,使欲之得遂,情之得达,斯已矣”(《疏证·才》)。戴震倡导“体情遂欲”,但不是纵欲主义者,他主张合理引导人的情欲,使人的情欲合乎中正之“必然”,若放纵情欲,不加以正确引导,人固有之善性就会丧失,就会出现“私”、“偏”、“蔽”之弊端。他说:“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情之失为偏,偏则乖戾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疏证·才》)。“必然”之于“自然”,其内在逻辑关系十分明显,是完整有机的统一整体。戴震认为,“必然”萌生于“自然”之上,没有“自然”,“必然”则无所依附,他说:“由血气心知而语于智、仁、勇,非血气心知之外别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伦日用而语于仁,语于礼义,舍人伦日用,无所谓仁、所谓义、所谓礼也”(《疏证·理》)。戴震还把二者的关系比喻为物、则关系,他说:“就事物而言,非事物之外别有礼义也”(《疏证·才》)。若离“情”而求“理”,离“自然”而求“必然”,那么,此“理”此“必然”只能是个人主观之意见。“必然”是“自然”发展的终极结果和当然准则。“自然之于必然,非二事也。就其自然,明之尽而无几微失焉,是其必然也。如是而无后憾,如是而后安,是乃自然之极则,若任其自然而流于失,转丧其自然,而非自然也;故归于必然,适完其自然”(《疏证·理》)。
三
戴震以自然、必然为视角构建的伦理观是超越乾嘉时期普遍道德伦理的一种新型伦理观,是代表社会进步思潮的突出表现。戴震是现实主义思想家,他的新伦理思想是通过对程朱理学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无情批判而得以阐释的。这一方面表现了戴震新伦理观的进步意义;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戴震新伦理观的现实价值。戴震以恢复先秦儒学为己任,以矫正世人之心为天职。正是基于这种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趋向,他对历史的或现实的所谓“异端”逐一进行了批驳。
戴震认为,在历史上,老庄释氏“徒见于自然,故以神为已足”。他们把人的形体看作产生有害情欲的外壳,因而主张摒弃人的物质形体,“绝圣去智”,以“无欲无为”的“神”为其最高原则和目标。他说:“告子、老聃、庄周、释氏之说,贵其自然,同人于禽兽也。圣人之学,使人明于必然”(《绪言》);“老庄、释氏见常人任其血气之自然之不可,而静以养其心知之自然,于心知之自然谓之性,血气之自然谓之欲,说虽巧变,要不过分血气心知为而本”(《疏证·理》)。老、庄、释氏主张听任自然,反对人的认识活动及所作所为,从而否认认识事物客观规律的必要性。而事实是,人不同于动物之最根本点之一就在于“物循乎自然,人能明于自然,此人物之异”(《绪言》)。用现代语言表述就是:动物只是听任自然,而人则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掌握从而改造自然。用恩格斯的话说就是:“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做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换言之,“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383-384页。)在这里,戴震虽然还不了解人的社会属性与人改造自然、改造世界的重要意义,但他对老、庄、释氏的揭示和批判却一语中的,指出他们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把精神和形体割裂为两个毫不相关的实体。因此,他们虽主张无情无欲,但丝毫不能证明其无私,其目的无非是妄使自己“长生久视”、“不生不灭”,是“以无欲成其自私者也”,因而他们是最大的不仁不义。戴震指出,作为“圣贤之道”,无私并不是说无欲,重要的是对欲进行节制,使“欲出于正”。他说:“有是身,故有声、色、臭、味之欲”(《疏证》);“是故君子亦无私而矣,不贵无欲。君子使欲出于正,不出于邪,”(《疏证》)。圣贤之士并不提倡绝情灭欲,而主张通过无私以“通天下之情,遂天下之欲”。
对于先秦著名思想家荀子,戴震认为他所说的“常人之性,学然后知礼义”,即一般人的本性通过后天的“修习积为”可以把握礼义规范的原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戴震不同意荀子关于人的情欲必然导致邪恶的结论。他说:“荀子见于圣人生而神明者,不可概之人人,其下皆学而后善,顺其自然则流于恶,故以恶加之,此论似偏”(《疏证·理》)。就是说,荀子只知礼义是为圣人之教,而不知礼义也是出自人的本性;只知礼义为明于其必然,而不知必然乃“自然”之“极则”,乃“自然”之完成。因而戴震得出结论说,荀子尽管理论宏富,以礼义相标榜,但究其实质仍不得“礼义之本”。
对当时社会上盛行一时的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戴震在早年和中年时期曾经历了一个由信奉到怀疑的痛苦过程。但到晚年,则充分认识了其杂老庄、释氏以为学的本质及殃祸斯民的恶劣影响,用心血撰著了其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一部“正人心之要”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对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给予了无情的抨击和严厉的批判。戴震认为,陆王心学与老庄释氏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致其毁訾仁义者,以为自然全乎仁义,巧于伸其说者也”(《疏证·理》)。程朱则信守“天理人欲,不容并立”之信条,“辨乎理欲之分,谓不出于理则出于欲,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舍情欲而求空漠虚无之理,把一般人饥寒呼号、男女哀怨,以至于垂死冀生之类,皆视为人欲横流的表现,断然否定人的情欲所具有的必然合理性因素;这样,便导致“小之一人受其祸,大之天下国家受其祸”。对于天下大事,程朱也以自己主观之理“强断行之”,而对于事物自身的“原委隐曲”却丝毫不予查明。戴震愤怒地发出了“此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杀人之具”的呐喊,他并把宋儒之所谓“理”与酷吏之所谓“法”相提并论,把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凝炼为一句千古名言——“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并对此做了振聋发聩的诠释,“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这一批判精神发生在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清中叶,既表现了戴震不畏权威、无所畏惧的人格魅力,也表现了戴震对程朱理学批判的进步性及超时代性;同时也表现了戴震对垂死冀生劳苦民众的深深关切;戴震的这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是在对封建社会的深刻批判和自觉反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过程中极其重要和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借鉴和批判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