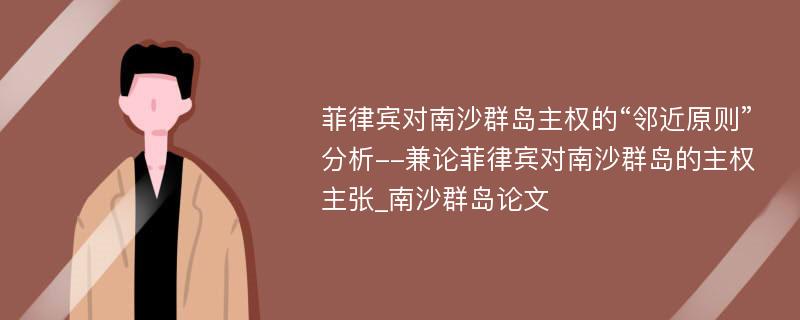
解析菲律宾在南沙群岛主权归属上的“邻近原则”——评菲律宾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主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沙群岛论文,菲律宾论文,主权论文,原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菲律宾政府在其解释对南沙群岛主权主张的法理原则时,提出了许多法理支持,如“安全原则”、“发现原则”、“占领原则”、“历史原则”、“大陆架原则”、“群岛原则”、“地理原则”等。在这些法理支持中,最先提出的和影响较大的就是所谓的“邻近(Proximity)原则”。虽然现在菲律宾政府已经很少有人再提起这一法理支持,但从其目前一直坚持的“安全原则”、“大陆架原则”、“群岛原则”、“地理原则”,甚至于“历史原则”来看,“邻近原则”其实还是其主张拥有南沙群岛部分主权的法理基础之一。故而在笔者正在进行的研究中,首先对其进行必要的法理分析,用现行国际法的准则去评判其合理性,推论其实践的可行性,以期能较全面地研究论述菲律宾政府在南沙群岛问题上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行为。
一、菲律宾政府“邻近原则”的出台及其理论外延
从笔者所见资料来看,一般认为最早以政府官员身份提出“邻近原则”的是菲律宾总统季里诺。1950年5月17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在国际法之下,团沙群岛(按:即我们所说的南沙群岛)应属于最接近之国家菲律宾。”(注:《南侨日报》,1950年5月18日。)虽然季里诺没有明确提到“邻近原则”这个词,但言辞之中的相同或相近含义是再明显不过了。只是因为当时主要当事国中国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是准备全力解放台湾,二是朝鲜问题随之而来,加上季里诺的表态基本上还限于外交姿态,并无实际行为,所以没有引起大的外交反应。但从时间上来讲,这应是菲律宾官方人士最早提出以“邻近原则”主张南沙群岛主权的言论。
真正引起外交反应的是菲律宾副总统兼外长加西亚(Carlos Garcia)在南沙问题上的明确表态。1956年5月19日,加西亚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南中国海上包括太平岛和南威岛在内的一群岛,‘理应’属于菲律宾,理由是它们距离菲律宾最近”。(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不容侵犯》,《人民日报》1956年5月29日。)加西亚的这次讲话引起了主要当事国中国政府的关注,中国政府很快发出反驳意见。5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对菲律宾政府在南沙群岛的行为和主张发表了专门声明。声明说:“南中国海上的上述太平岛和南威岛,以及它们附近的一些小岛,统称南沙群岛。这些岛屿向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合法主权。……菲律宾政府为了企图侵占中国的领土南沙群岛而提出的借口,是根本站不住的。”声明还说:“中国对于南沙群岛的合法主权,绝不允许任何国家以任何借口和采取任何方式加以侵犯。”(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中国南沙群岛的主权不容侵犯》,《人民日报》1956年5月29日。)
加西亚的讲话之所以立即引起中国政府的外交反应,背景原因之一就是在此之前不久有一名叫托马斯·克洛玛(Tomas Cloma)的菲律宾“探险家”开始在南沙群岛地区活动。他在5月11日,率先进入南沙群岛,并在所到岛屿上插上菲律宾国旗,宣布对其“正式拥有”,还将南沙群岛更名为“卡拉延群岛”(Kaldyaan),意即“自由地之地”。5月15日,克洛玛向加西亚致送信函,声称以“发现—占领之权利”向世人宣布“卡拉延群岛”是“自由之群岛”。该群岛位于“菲律宾海域之外,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之内”。(注:陈鸿瑜:《南海诸岛主权与国际冲突》,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83页。)5月17日,克洛玛向菲律宾政府报告其在南沙群岛的行动。值得指出的是,加西亚与克洛玛的私人关系非同一般。他们都来自菲律宾的务匆省,加西亚还亲自出席克洛玛为其起程赴南沙群岛“探险”而特意举行(3月1日)的晚宴,其中寓意不言自明。以加西亚这样的身份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发表这样的讲话,当然会引起中国政府迅速、强烈的反应。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菲律宾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特别是当时菲律宾在外交上常被“视为美国国务院的尾巴”,(注:陈烈甫:《菲律宾对外关系》,正中书局1974年版,第138页。)一直奉行非常强硬的反共立场。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并没有使菲律宾政府改变其在南沙问题上的政策。同年12月,加西亚在正式参加克洛玛的聚会时再次表示:“从这些包括自由地在内的群岛的小岛的地理位置来看,它们除了鱼产、瑚珊、海产和磷酸肥等经济潜力外,因其接近菲律宾西边的疆界,与菲律宾群岛有历史和地理关系,对我国国防和安全有重大战略价值,所以只要菲国国民依法行事的话,菲政府不会不关心他们在这些无人居住和未被占领的岛群上的经济开发和徙居的问题。”(注:Marwyn S.Samuels.Contest for the Couth China Ses.Methuen,New Youk andLondon Methuen & Co.1982,pp.82-83.)在加西亚提出“邻近原则”后不久,1957年2月19日,同样是来自务匆省的菲律宾众议员加芒芒在众议院中公开主张菲律宾应该拥有南沙群岛的主权。他说:“自由岛并不包括于南沙群岛。既便如此,南沙群岛与菲律宾的距离即可构成后者对南沙群岛行使主权。”(注:《华商日报》(马尼拉),1957年2月20日。)1974年2月5日,菲律宾外长罗慕洛(Carlos P.Ronulo)在给越南西贡政权的大使杨煌成的抗议照会中说:由菲律宾占领的南中国海岛屿(马欢岛、费信岛、西月岛、北子礁、中亚岛)位于“南沙群岛东北部,距离有200英里之远。它们距离位在东边的巴拉望首府普林塞萨港(Puerto Prrincesa)有250英里,距‘中华民国’直线距离950英里,它们距越南海岸线有350英里。”(注:Marwyn S.Samuels,Contest forthe South China Sea.Methuen,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 Co.,1982,p.104.)虽然罗慕洛没有再提“邻近原则”,但“邻近”的理论指向则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菲律宾政府人士提出拥有南沙群岛主权的主张在许多年前就有了,只不过它不是以官方的正式渠道表现出来的,没有一个准确的表达方式,没有一个法理依据支持,特别是当时菲律宾的国际地位尚不明确,故而没有引起有关国家的普遍重视。如1933年8月,美国菲律宾殖民地前议员雷耶斯(Isabeol de los Reyes)对法国出兵占领南海9个岛一事向美国驻菲律宾总督墨菲(Frank Murphy)提出,按《巴黎和约》的规定,该地区应属菲律宾所有。但雷耶斯的意见未被采纳。因为当时美国驻菲律宾海岸测量人员认为,这些小岛是在离海岸线200海里以外,按《巴黎和约》不应是菲律宾领土。(注:参见《时事新报》(上海),1933年8月13日。)菲律宾总统季里诺自称其在1934年任美国菲律宾殖民地内务部长时,就“曾提出要求拥有该岛,惟美国国务院当时未批准”。(注:《南侨日报》,1950年5月18日。)1938年,菲律宾自治领政府总统奎松(Manuel Quezon)曾游说日本政府与其联合占领南沙群岛,未果。(注:参见陈鸿瑜:《南海诸岛主权与国际冲突》,第83页。)1946年7月23日,菲律宾外长奎林诺宣称,菲律宾政府拟将南沙群岛“合并于国防范围之内”。(注:《大公报》(上海),1946年7月24日。)菲律宾国会曾专门讨论过南沙群岛的主权问题。据《华商侨报》报道:季里诺总统曾下令国防部部长江良转饬菲海防司令安达那上校前往南沙群岛视察,但立即被外交部副部长礼尼劝阻。礼尼获悉巴拉望岛的菲律宾渔民时常前往南沙群岛海域捕鱼,遂向季里诺总统建议劝诱这些渔民移居南沙群岛,以备在菲律宾国防安全需要的时候,能将南沙群岛吞并。(注:参见《华商侨报》,1949年4月13日。)1950年5月13日,菲律宾《马尼拉论坛报》声称应立刻占领南沙。5月17日,季里诺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南沙群岛若为“敌人”所占,将“威胁我们的国家安全”。(注:《南侨日报》,1950年5月18日。)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人马顿·米兹(Morton F.Meads)曾宣布在南沙建立了一个"Kingdom ofHumanity/Republic of Morac-Songhreti-Meads"政权,1951年菲律宾总统麦格塞塞(Roman Magsaysay)曾试与其取得联系,因始终未能找到其所谓政府所在地而作罢。(注:参见Marwyn S.Samuels,Contest forthe South China Sea.Mithuen,New York and London Methuen &Co.1982,p.81。)
可见,菲律宾政府图谋拥有南沙群岛主权已有很长时间了,只是因为客观因素未公开化、程序化、行为化、法律化。南沙群岛自古属于中国,这是历史也是现实,并得到世界公认。菲律宾政府想介入这一地区的事务,必须要寻找到法理支持。这个时期他们提供的法理支持就是“邻近原则”,所以该时期的菲律宾政府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的主张,以“邻近原则”为基础。英国伦敦的《南方》月刊在评论菲律宾政府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上的行为时说:“菲律宾采取的新战略是以‘邻近’的逻辑——这些岛屿距离菲律宾的边界比离他们提出要求的国家要近一些——和发展为依据”。(注:[英]金·戈登贝茨:《在亚洲成堆的海洋》,《南方》(伦敦)1988年6月。)这就十分准确地道出了菲律宾政府的基本理论基础。泰国《民意报》亦说,菲律宾声称南沙群岛东南地区的一部分岛屿是菲律宾人发现的,而且位于菲律宾领土附近地区。(注:参见张水荣编译:《南沙群岛争端及其对泰国的影响》,《东南亚研究》1993年第4期。)
那么,从现代国际法理论原理角度研究,菲律宾政府在南沙群岛主权问题上所主张的“邻近原则”是否有效,是否真的给菲律宾政府提供了拥有南沙群岛的法理支持呢?
二、“邻近原则”不是现代国际法承认的拥有领土主权的基本原则
现代国家采取的国际行为必须符合现代国际规则,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那么,什么是现代国际法?从学术上讲,“现代国际法是在现代国家相互交往中产生的,表现这些国家的协调意志,调整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由它们单独或集体采取强制措施保障实施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注:朱奇武:《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也就是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各个现代国家之间在不断的相互交往之中,需要一个基本的行为规范来界定其行为,以保证其行为具有公认的合理性,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所以,各个国家政权既有权利享受这些行为规范给自己带来的利益保护,也有义务用这些行为规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这种行为规范本身应该具有某种强制性,而其强制特征是通过单独或集体的实施来实现的。现代国际法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下去,就是植根于现代国际社会的整体需要。
国家领土主权是现代国际法首先要保护的国家权利,也是现代国际组织赖以存在的基础。《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二条第四款明确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注:联合国新闻处编:《联合国手册》,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724页。)国际法理论同样认为,“侵犯国家的领土完整和领土主权,就是侵犯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是现代国际法着重禁止的,构成严重的非法行为”。(注:朱奇武:《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第102页。)国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这是无可置疑的。现代国际法同时要求,国家领土的获取方式必须是符合现代国际法承认的方式。只有有效的领土获取,才能获得有效的现代国际法保护。相反,非法的领土取得,不仅不能享受现代国际法的保护,而且是现代国际法明令禁止并谴责的。
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领土获取方式,总结起来有五种,即先占、添附、割让、征服和时效。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一些传统的领土获取方式已经逐渐被人们否定,现代国际法也不已不予承认。如强制割让和征服行为,因为具有明显的武力强制性而被现代国际法彻底否定。时效原则因含有非法和武力因素,其应用也受到限制。先占原则亦因现代人类知识的扩展和行为的扩张,可应用的范围也越来越少。目前看来,只有“自愿割让”(利益割让)和“自然添附”两个原则得到继续承认,并在实践中继续使用。很显然“邻近原则”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领土获取方式。根据笔者的观点,对于“邻近原则”至少有下列问题可以进讨论:
其一,关于“邻近原则”的定义。现代国际法从来没有给“邻近原则”下过具体定义,也从来没有认为它是领土争端双方必须遵守的强制原则。就连主张“邻近原则”的菲律宾政府也没有给“邻近原则”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们只能从他们发表的言论和主张中体会其定义。从各种资料看,菲律宾用来确定是否“邻近”的唯一标准就是地表的直线距离。我们从季里诺所说的“最接近”、加西亚所说的“最近”和“接近”、加芒芒主张的“距离即可构成”主权、罗慕洛所进行的公里数计算等等行为表现上看只能这么理解。笔者认为地表的直线距离“邻近”不等于主权“拥有”。从历史的角度上讲,它只是曾经为“拥有”提供一个地理便利条件而已,并不等同已经“拥有”;从现代地质学的角度来讲,地表直线距离相近也并不一定表明两地间地质意义上的“邻近”。地质学上的“邻近”可以分为形态学和地质学两种不同的定义,而这两者在个案分析上是有很大不同的。(注:参见《国际法律资料》1981年第4期,第814页。)从现代国际法角度来讲,没有一个规定主张“邻近”即“拥有”。“邻近”仅是表明一方利益的要点之一,却不是双方必须遵守的原则。况且,南沙群岛在地质学意义上是与菲律宾分割的,是不“邻近”的,标志就是东南亚地质板块结构以及由此形成的存在于菲律宾与南沙群岛之间的“马尼拉海沟”。我们知道,有争端的领土一般来说总是具有距离“邻近”的特点,主权问题以是否“邻近”来判断是十分不规范的主张和行为。而且“邻近”本身就是一个相对模糊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背景认识,可能有极为不同的解释。这样就极易被不断扩展的技术和知识无限制地扩大和利用。如果广泛地使用“邻近原则”来审视领土争端的是非,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二,“邻近原则”的行为对象。任何国家或政权在主张新的领土主权的时候,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不可忽视的前提,那就是这个被主张的地区(包括所谓的“邻近”地区)首先应该是处于无主的状态或者原本就处于自己的主权范围之内(这是针对“自然添附”而言的)。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讲,我们都不能对那些早已归属别国的领土实施单方面主权主张,更不能擅自实施武力占领。正如希腊代表在加拉斯加国际法会议上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人能够处理他不拥有的东西”。(注:赵理海:《海洋法的新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1975年国际法院在关于西撒哈拉法律地位的咨询意见中也明确指出:“凡住有土著部落或人群具有一定社会政治组织的地方就不能认为是无主土地。”(注:L·C·格林:《国际法案例》,第441页,转引自朱奇武:《中国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第112页。)南沙群岛显然不属于菲律宾能够主张领土主权的地区。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开始对南沙群岛实行行政管理,而且一直延续到现在,所以它不是无主地。菲律宾的国土主权范围是在数个国家实际普遍承认的国际条约中明确划定的,如1898年美国与西班牙签订《巴黎和约》、1900年美国与西班牙的条约、1930年美国与英国的协定以及1932年美国与英国的条约都明确将南沙群岛划在其主权之外。甚至菲律宾公布的共和国第3046号令、1961年6月17日菲律宾发布的第3046号共和国法案《菲律宾领海基线订定法》和1968年9月18日菲律宾参、众两院通过的第5446号法案,以及“1940年菲律宾调查统计委员会出版的多卷本《菲律宾调查统计地图》,1950年出版的《菲律宾地图》,1969年马尼拉调查委员会海岸和大地测量局出版的《地图集》都未将南沙群岛划入其版图”。(注:杨翠柏、唐磊:《从地图在解决边界争端中的作用看我国对南沙群岛的主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2期。)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菲律宾当然不是南沙群岛的主权国。
其三,“邻近原则”,在理论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在国家间的领土谈判中,“邻近原则”确实是可以用来表述某一方利益的因素,但却不是另一方必须遵守的强制原则。我们知道,所谓“邻近原则”背后其实隐含着许多潜台词,如“国家安全问题”、“交通便利问题”、“资源结构问题”等等,但这所有一切都不能构成领土所有权,而只是谈判过程中表明某一方利益所在的思考因素。要想维持现代世界和平,使现代社会能够有序的持续发展,“历史拥有原则”才是国家间领土争端首先考虑的原则。只有在充分尊重历史的背景下,才能保障未来。国家领土基本上就是一个历史继承过程,为了某种短暂利益去否定历史的连续,将会带来无数的问题,事情也只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说白了,这不是解决问题,而是在制造问题。
世界上有些国家是主张“邻近原则”的,但这并不能说明“邻近原则”就具有普遍的合理性或合法性。如1947年6月23日和8月1日,智利和秘鲁分别宣布其国家主权扩展到“邻近”其国家大陆和岛屿的全部大陆架,而不论其水深是多少。从条文上看,它们在强调大陆架为基础的同时,似乎更重视地理“邻近”(即地表的直线距离)这个概念。1950年9月萨尔瓦多通过的新宪法第七条宣称,其领土“包括自最低潮线起距离为二百海里的邻近海域及其相应的领空、底土和大陆架”。(注:《公海制度的法律规章》第1卷,第300页。)这些拉美国家之所以提出如此主张并付诸实施,一方面是因为它们几乎都是大陆架极为狭窄的国家,使用大陆架原则将会使它们一无所获,而200海里“邻近”区的划分就能体现其利益。更重要的是它们几乎都是直接连接公海的,基本不存在与相向国划界问题,也就是说基本没有与他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对现代国际法理论和国际社会来说,“大陆架原则”和“邻近原则”既互有矛盾但又可以相互补充,前提是不侵犯他国利益。既便如此,现实中的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主张仍是有争论和保留的,理由是不利于对公海利益的保护。
其四,“邻近原则”在解决国家间领土争端实践过程中是不可行的。我们知道,目前各个国家领土现状的形成是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结果。在表象上千姿百态,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果用“邻近原则”来审理领土争端必将带来一系列的问题,甚至导致有关国家领土“大洗牌”。如英国的海峡群岛(Channel Islands)离法国仅20海里,而离英国85海里。其中的泽西岛(Jersey I.)离法国瑟堡半岛(Cherbourg)甚至只有14海里。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位于与瑞典相望的一个岛上,其最突出部分的埃尔西诺尔(Elsinore),离瑞典仅3海里。位于波罗的海中的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离瑞典22海里,离德国60海里,离丹麦的西美兰岛95海里,离日德兰半岛更是远达219海里,但却被认为是丹麦的领土。法罗群岛(Faroe Islands)离丹麦650海里,离苏格兰240海里,离冰岛300海里,但它同样是丹麦的岛屿。阿留申群岛(Aleutian Islands)最西端离阿拉斯加300海里,却是美国领土。法国的圣矣尔岛(St.Pierre)和密克隆岛(Miguelon)位于离续芬海岸仅12海里的地方。如果实行“邻近原则”来判断这些领土的归属的话,世界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就是主张以“邻近原则”来划定领土主权的菲律宾也面临相同问题。菲律宾的苏禄群岛(Sulu Archipelago)中许多孤立的小岛离马来西亚的加里曼丹岛仅3至5海里,离菲律宾却远在这个数字的十倍以上,马来西亚可以按“邻近原则”主张对这些岛屿拥有领土主权吗?还有,位于巴士海峡中的一些菲律宾岛屿在直线距离上与我国的台湾较近,而离菲律宾本岛则较远,难道中国也可以主张对这些岛屿享有主权吗?我们知道,现代国际法是努力建立在“公平”原则之上的,适用于此的原则,同样应该适用于彼。这个推理结果,恐怕菲律宾政府是绝对不会接受的。正是基于维持世界现行秩序稳定的目的,1967年2月20日,国际法院在审理“西德、丹麦、荷兰三国北海区域主权案”时认为,“如果某水下区域是不构成某沿海国陆地领土的自然的延伸,那么,即使它距离这个沿海国比距离其他任何邻国都近,也不能被认为是该国的一部分”。国际法院还进一步指出,显然不能将邻近原则与自然延伸原则混为一谈,否则将会导致一国领土的自然延伸区域被另一国领有。(注:参见国际法院报告:《北海大陆案判决书》,第32页,转引自张克宁:《大陆架划分与国际习惯法》,文载赵树理主编《当代海洋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页。)国际法院在1984年10月12日对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缅因湾海洋边界划分案”做出的判决第103段是这样说的:“说国际法将邻近的大陆架或邻近海岸的海洋区域的法律权利给予沿海国,是正确的,但是要说国际法承认由于大陆架或海洋区域的邻近而赋予该国权利,好像邻近这个自然事实就能产生法律后果,则是不正确的。”第106段还说,不能接受等距离已是国际法所赞成的一个概念,因为这种说法的目的是不管什么,如果离一国海岸较另一国海岸为近,就应自动隶属该国。因此法庭承认等距离是一种划界的实际方法,而不是一项法律规则。(注:张鸿增:《缅因湾海洋边界划分案例介绍》,《当代海洋法的理论与实践》,第191页。)很明显,现代国际法的理论和实践都认为,“邻近原则”在领土划分时可以是一个参考因素,并不是主张领土拥有的必要法理依据。众所周知,在菲律宾群岛与南沙群岛之间有一个世界上最深的马尼拉海沟,从地质结构上将两者完全隔断,所以,从地理“自然延伸”这个角度上讲,菲律宾是没有任何主权法理基础的。
其五,如果将“邻近原则”用于现代国际法的审理实践中,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其中不仅有大量的现实的领土冲突问题,还会面临许多法理理论问题。如前所述,目前我们所面对的国家领土状况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是各种矛盾不断平衡的结果。如果我们现在人为地去打破这个平衡,必将带来无数的混乱,甚至灾难。“邻近”是一个相对概念,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而不断扩展的概念。早期人类概念中的“邻近”可能仅仅是那些直接关系到自己生存的地区,而现代科学技术的极端发展,已使这种“邻近”概念早被变换了内涵。地理上的阻碍早已不是主要的问题了,真正的阻碍源自人类社会本身。就目前而言,大国与小国的“邻近”概念不同,强国与弱国的“邻近”概念不同,高科技国家与较落后国家的“邻近”概念又有不同,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论证、去实践呢?从现实来看,“邻近原则”的实施只会给大国、强国、高科技国家以更多、更大的发展扩张空间,而小国、弱国、较落后的国家只能看着别人分享利益,甚至任人宰割。以菲律宾目前的国家实力而言,恐怕是很难在这种“竞争”氛围中取得真正益处的。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菲律宾政府在南沙群岛问题上主张的“邻近原则”在理论上是违背现行国际法原理的,在实践上是不符合“防止且消除对于和平之威胁,制止侵略行为或其它和平之破坏”(注:联合国新闻处编:《联合国手册》,第723页。)的联合国基本宗旨的。它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说仅仅为了菲律宾政府一时之需,是实用主义的产物,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危险的,同时也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拥护正义的人民所反对的。
标签:南沙群岛论文; 国际法论文; 菲律宾共和国国旗论文; 菲律宾南海论文; 菲律宾总统论文; 美国领土论文; 美国史论文; 大陆架论文; 岛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