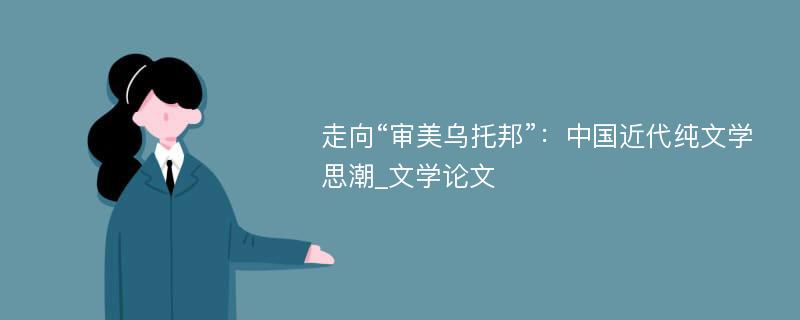
走向“审美乌托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乌托邦论文,纯文学论文,思潮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3)03-0096-05
文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活动,审美活动具有非功利的性质,这一种具有鲜明的外来色彩的观点,在现代中国因知识界对传统儒家文学观的不满而得到迅速传播,成为纯文学思潮兴起和发展的理论依据,同时也实现了中国文学观念的现代性转型。但现代中国对审美非功利性的理解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依据理解的差异,我们可以把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分为三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纯文学”有不同的对立面,也有不同的文学理想。
一
第一阶段从20世纪初延续到20年代,是纯文学思潮的萌芽期。在这一阶段,“纯文学”的意识刚刚确立,其主要目的是反省和批判儒家文学思想的政教功利主义,改变文学的附庸状态,把对功利性的剥离和超越视为文学的神圣性之所在,从而建立信奉文学之独立价值的现代性文学观念。这时,”纯文学”的对立面是混淆了审美与实用性,混淆了文学文体与非文学文体的杂文学传统。所以,这一时期“纯文学”的倡导者大多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传统。早在1905年,王国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美术之无独立价值也久矣,此无怪历代诗人,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以自解免,而纯粹美术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迫害而无人为之昭雪者也”(注: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见姚淦铭、王燕编《王国维文集》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7页。)。为了表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决裂,王国维使用了“纯文学”与“纯粹美术”两个新术语,其中的“纯”和“纯粹”,就是区别于掺入了政教功利与个人名利的实用主义文学观的突出标志。王国维的美学文学思想有清晰的德国知识背景,康德、席勒排除实用功利性的美学观,叔本华把欲望视为痛苦之源的悲观主义哲学,都使在现实人生中挣扎于俗务而欲罢不能的王国维顿生知音之感,他把后者视为知己,把前者奉为理想,表达了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相当彻底的非功利思想。王国维的彻底性多少有点偶然,似乎是不世出的天才,敏感的个性,率先接受新知识的机遇与不幸的个人生活四者相遇才会有的产物,但对实用主义的文学传统发起批判却并非偶然。在王国维之外,至少还可以举出鲁迅、周作人、徐念慈、黄人、吕思勉等人的名字。1907年,鲁迅作《摩罗诗力说》,明确提出“纯文学”概念,并对之有一个初步的定义:“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文章为美术之一,质当亦然,与个人暨邦国之存,无所系属,实利离尽,究理弗存。”(注:鲁迅:《坟》,《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65页。)这一定义包含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基本要素,一是把文学视为美的艺术,从而美学就取代了其它理论成为讨论文学的第一前提;二是文学作为一种审美活动,审美快感应是它追求的第一价值,由于这种快感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因此与“个人暨邦国之存”的实际功利无关,亦与理性和逻辑无关。也就在同一篇文章中,鲁迅还揭示了文学“无用之大用”的文化价值。至此,鲁迅几乎全面涉及了康德美学的基本思想:非功利、非概念、审美愉悦、无目的之合目的性。次年,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使用了“纯文章”一词,并与“杂文章”对举,同样显示了追求文学独立性的现代意识,并更为尖锐地把批判矛头直指孔子,认为其删诗定礼的举动正是功利性文学观的渊源。由此可见,现代中国最早的“纯文学”观念直接来源于德国美学,并由此发现本土传统的缺陷,因而“纯文学”一词进入汉语就标志着新型文学理想的诞生,即认为文学应该是除审美之外别无其它主观目的的精神活动。
但“纯文学”在理论上固然可以推向极致,在实践中,非功利的态度却未免有些模糊,“纯”与“杂”的边界也未必那么泾渭分明。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否因为痛感彻底性的不可实现,固然已无法追索,但周氏兄弟却有后来的转变可以证实他们对彻底性的放弃。就在同一篇《摩罗诗力说》中,鲁迅以文学为启蒙的思想已很显明,他弃医从文,力求改造国民性的用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更是赫赫有名。周作人“五四”时期提倡“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在领一时风气之先的同时终止了对文学功利性的排斥。从历史的角度讲,担当启蒙的任务是时代对中国新文学的必然要求,而从理论上看,“无目的之合目的性”、“无用之大用”,本来也为某种宽泛的功利性留有余地。
“五四”前后,知识界对待传统文学的态度与十数年前一样仍是批判,但批判的内容已悄然转换。王国维痛心疾首的是“载道”剥夺了文学的独立与自由,新文化先驱们对“载道”的不满则是所载之道的具体内容,而不是这种思维方式。甚至,在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另一痼疾——“消闲”——的批判中还强化了“载道”意识。于是,新文学对“纯文学”的理解不再是坚持审美的纯粹性,不再是对功利性的严密防范,而是追求文学的严肃性,这种严肃性出自对社会人生的良知和责任感。当然,新文学对严肃性的追求,并不等于回到传统功利性文学的老路。毕竟所载之道的具体内容不同了,儒家的经世致用、道德教化被现代性的政治、经济、文化内容所取代。在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在这一阶段与政治经济的现代进程是一致的,它要求文学对后者起推动作用而不是制衡监督的作用。
在中国现代纯文学思潮的萌芽期,知识界关于“纯文学”的理解已经出现了两种路向,一是针对传统杂文学观念下模糊的文体意识和以文学为政教工具的功利主义,要求建立以审美为基本特征和最高价值的新型文学观念;二是针对旧文学中无处不在的封建意识形态,要求用现代内容来置换已成为文化惰性的传统,从而通过新文学的建立来塑造和张扬新的文化精神。显然,在这两种路向之间存在着矛盾,但由于共同的对传统的反省和批判,共同的对西方文学、文化的借鉴,共同的对新型文化的憧憬,使得这一矛盾暂时隐而不现。看似各执一端的“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争论,事实上并不那么泾渭分明,而且很快就因双方都有成员在文学观上发生转化而不了了之,远不如后来新月派与左翼文学的论争那样针锋相对。
二
带着隐藏的却难于调和的矛盾,随着世易时移,这两种路向各自的发展都渐趋于极端,矛盾也日益明显化。前一种路向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下把“唯美”推向极致,后一种路向则因过于强调文学的社会责任而放弃了对文学自身的严肃态度,复活了传统文学观的功利主义和工具主义并使之变本加厉。于是,“纯文学”意识淡出后一阵营,而向前一阵营集结,其主要对立面也由传统的儒家文学观转向新兴的“革命文学”。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进入了第二阶段,在时间跨度上大约从2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是中国纯文学思潮的发展期。总体而言,这一阶段从两个方面推进了纯文学的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一是继续上一阶段的任务,坚守文学价值与现实功利的距离,发展审美批评;二是侧重对现代文学形式的探索,发展本体批评。对立面是只有“白话”没有“诗”的模糊文体意识和只重宣传放弃艺术的功利主义文学观,但发展到极端,未免走向虚无、轻薄的“趣味主义”和颓废的唯美主义。同时,由于现代商业意识的发展,出版业的繁荣和现代市民社会的兴起,以利润为文学目的的商业功利性极大地带动了以市民趣味为主的“消闲”文学的发达,成为“纯文学”必须面对的另一个障碍。
纯文学思潮对以“教化”、“新民”、“启蒙”、“革命”等一切形式出现的政教功利性文学观的抵制,既是对“五四”新文化反传统的延续,也是出于对新文学本身的反思和调整。当胡适掀起“白话文”浪潮的时候,首要任务是论证和宣扬白话文作为文学语言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因而,对“白话诗”的提倡,其着重点在“白话”的使用而不是在“诗”的经营,于是,“白话”的成功却不幸以“诗”的丧失为代价,文学语言革命的成功却不幸以审美的丧失为代价。当新文学以启蒙文学自期的时候,其着重点在“启蒙”的达成而不在“文学”的完成,于是,文学启蒙的成功却不幸以“文学”,自身作为牺牲。“纯诗”理论和“美文”运动,正是对上述弊端的反动,也是中国现代纯文学思潮在第二阶段的主要内容和重要成就。
“美文”于1921年首倡于周作人,他把“艺术性”作为“美文”的本质(注:周作人:《美文》,《晨报副刊》1921年6月8日。),最初的目的就是希望把白话文章写得美一些。这篇短文预示了周作人从“五四”启蒙文学的先驱向“唯美”方向的转变,也引发了日后一系列关于散文、小品文的讨论以及二三十年代散文写作的繁荣,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促成了现代文学散文在文体上的确立和成熟。这场“美文”运动有两个内容,也从两个方面体现了二三十年代的“纯文学”理想。首先,它从语言雅化的角度强调文章之美,是对初期白话文学忽视语言艺术性的纠偏。对文学语言的重视为新文学的真正确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使白话文学最终能取代文言文学,实现了胡适建立“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倡议,所以胡适当时就对此给予首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第二,“美文”以及稍后的“小品文”,都要求作者在文章内容和写作心态上适当保持与现实社会人生的疏离,这是对过于直接、过于强烈的功利主义的纠偏。对此又是周作人起到了先驱的作用,1922年他就提出“艺术的要点”在于“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晨报副镌》1922年1月22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美文”、“小品文”、“絮语散文”等名目出现的散文,实际上吸取了传统和西方两方面的文学资源。中国古典散文尤其是晚明小品的潇洒随意、飘逸灵动,是从周作人到林语堂等“小品文”倡导者都一直心仪、模仿的对象;而英法散文中的essay一体,又以其优雅亲切的笔触,幽默开朗的风度以及充满哲思的智慧,折服了一批有欧美知识背景的现代文人,成为他们在经营现代散文时重要的参照。无论是晚明小品还是西方essay,都具有精英趣味,散发着精致文化的气息,所以极易与本身即具有精英气质的现代文人获得共鸣,成为他们心目中“纯文学”的一种典范。
如果说20年代初期的“美文”主张是新文学自身的调整,那么在20年代中后期以来,面对愈演愈烈的把文学视为宣传工具的风气,对“美文”的坚持就成为对文学独立性的坚持,在此,纯文学思潮对功利主义文学观的批判从传统转向了现实。这样,同样出自于文学现代性追求的两种倾向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在这样的对立中,双方都容易走向极端和偏颇。就“美文”运动而言,它的确很快就蜕化为象牙塔里絮絮叨叨的呓语,对唯美的追求滑向享乐与颓废,对趣味的欣赏成为逃避沉重的借口,对智慧的冶炼掩饰着心灵深处的荒芜。如果说这在太平盛世还无伤大雅的话,在二三十年代中国“风沙扑面”(鲁迅语)的社会现实中却难以找到为之辩护的空间。所以,“美文”、“小品文”不仅遭到来自左翼文学的批判,也受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指责和规劝。而且,“雅到俗不可耐”(朱光潜语),洒脱到轻薄,非功利到虚无,这样一种严肃性的丧失对“纯文学”自身的发展来讲也决不是福音。30年代中期,此种文学风气即受到来自纯文学思潮内部的批评,这也标志着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进入了第三阶段。
“纯诗”理论的兴起与“美文”运动有大致相似的背景。出于“使白话新诗成为诗”的艺术本位意识,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诗歌从各自的角度共同推进了新诗的艺术追求,也丰富了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想。新月派诗论的意义,首先在于理直气壮地追求诗歌的形式之美。我们的古典诗歌是一种把形式美发挥到淋漓尽致的诗歌,但在诗歌理论和诗歌观念上,形式美却始终不能获得本体上的意义,而必欲把一切对形式的追求归结为“尽善尽美”、“文质彬彬”而后快。所以新月派的格律化不仅仅是对“五四”白话诗过于散文化的纠正,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对形式美的正名。当然,新月派诗论的意义还在于对功利性文学观的防范。不用说他们所倡导的新诗格律化本身即是对只重“白话”不重“诗”,只重“启蒙”不重“文学”的抗议,而且他们也曾明确提出过“美是艺术的核心”、“艺术家为美的原则而牺牲”等“纯文学”主张。大约与新月派同时出现的象征派,同样不满于“五四”新诗的过分直白和透明,更多地从西方象征主义中吸取所谓“诗的思维术”和“诗的逻辑学”(注:穆木天:《谭诗》,《创造月刊》第1卷,1926年第1期。),以营造模糊、晦涩、神秘而又具有无穷的意义生发性的艺术氛围。他们同时也从西方象征主义那里接受了唯美的艺术观,把对功利性文学观的敌视表达得比新月派更为极端,中国象征诗派的鼻祖李金发就曾这样说:“艺术是不顾道德,也与社会不是共同的世界。艺术上唯一的目的,就是创造美;艺术家唯一的工作,就是忠实表现自己的世界。所以他的美的世界,是创造在艺术上,不是建设在社会上。”(注:李金发:《烈火》,《美育》创刊号,1928年10月。)此后,现代派总结了新月派与象征派各自的优势与缺陷,力图融汇中西诗艺,创造真正民族的和现代的“纯诗”。尽管这三种诗派在创作和理论上都各有侧重,但在对“纯诗”的追求上却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共同在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中写下了重要一页。
然而,“纯诗”理论与“美文”运动具有相似的缺陷,即在与极度功利性的文学主张的对峙中自身也难免片面和偏执。但这些互不相让的文学主张在二三十年代的并存,从整个文学史的发展来看还是起到了相互制衡的作用,就在30年代中期,纯文学思潮已经从内部开始了调整和综合,重新思索了审美与功利性、艺术追求与社会关怀的关系。此外,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步伐的艰难迈进,知识界也越来越多地意识到现代性本身的负面因素,于是,在第三阶段的纯文学思潮中,对功利主义的批判进一步由传统儒家文学观转向了现实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商业功利主义,并由具体转向抽象,即从批判具体的功利性转向批判这种功利性给精神带来的戕害。当然,“纯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也就开始与政治、经济的现代性内容日益疏离,把审美放进了精神乌托邦的殿堂,使之成为审视现代性进程之负面影响的一个独特视角。
三
从30年代中期开始,纯文学思潮进入了自我反思、自我调整、走向综合的阶段,京派和九叶诗派是其中的主要力量。
像一切“纯文学”主张一样,京派也仍然坚持文学艺术的本质是超越现实功利的审美活动,但此时的审美已不是唯美,此时的“纯文学”理想已不是“为艺术而艺术”,超功利也不是拒绝现实关怀,而是以自由精神为核心构建的文化理想。或者说,审美在此时具有了精神乌托邦的意义,“纯文学”也日益意识到自身的文化责任感。但京派有感于当时文坛口号理论满天飞却缺乏佳作精品的现状,致力于以创作实绩来证实自己的理论主张,更有意避免介入当时的文坛纷争,因而京派见诸文字的理论并不多见。京派在理论上比较突出的是沈从文和朱光潜。
1933年10月,沈从文引发京、海派论争的《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表达了对浮华文风的不满,提倡“厚重”、“诚实”的严肃态度,希望扭转文坛风气。此后,沈从文又发表了《论“海派”》、《关于海派》、《新文人与新文学》、《谈谈上海的刊物》等一系列相关文章,批评的范围也从浮华文风扩展到追逐政治功利性或商业功利性的文学倾向。其中,首倡于周作人而在当时风头正健的小品文也是其矛头所指,如果说这还是对小品文经“海派”之手而流于时尚和轻薄的指责,那么沈从文在《论冯文炳》(注:此文写于1933年沈从文到北平以前,收入《沫沫集》,于1934年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一文中对周作人、俞平伯、废名(冯文炳)等人的“趣味”、“绅士有闲心情”的微辞,则预示着京派文学观内部的重组以及对“纯文学”一味追求“唯美”的反思。正是在京、海派论争和京派对自身的反思中,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发展到第三阶段,并一直持续到40年代末,而“严肃”也成为这一时期“纯文学”新的理想。与萌芽期不同的是,此时的“严肃”不仅出自于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也强调对文学本身的严肃态度。
沈从文在京派中显得有些“特别”,他的批评时有把复杂现象简单化、以偏概全的缺点,不足以代表京派的全部,这一时期京派的核心人物朱光潜就没有沈从文那么尖锐偏激,但在批判小品文的轻薄,批判充斥着商业气息、政治欲望的文坛风气,提倡严肃的文学态度,要求知识阶层的负起文化责任等大方向上,朱光潜或者整个京派,与沈从文并无分歧。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是京派的重要刊物,也是京派为树立“健康纯正的文学风气”而作的一次真诚努力,虽然仅出四期即因抗战爆发而停刊,但仍不失为京派文学成就和理论主张的代表。朱光潜在发刊辞《我对于本刊的希望》中表达了自己的,同时也是京派同人的文学观(注:此文载于《文学杂志》创刊号,由朱光潜起草,经编委会讨论定稿,实际代表京派核心成员的集体意见。),一方面,一如既往地反对各种功利主义文学观,把“为大众”、“为革命”、“为阶级意识”、“为国防”,都视为“文以载道”的“新奇的花样”;另一方面,又同时声明“十九世纪所盛行的‘为文艺而文艺’的主张是一种不健全的文艺观”(注:朱光潜:《我对于本刊的希望》,《文学杂志》1937年5月1日。)。朱光潜反对简单的“为艺术而艺术”,也不满于传统文学中的名士风度和隐逸气味,“认为中国文学最大的缺陷就是缺少‘严肃’,极力主张对于传统文士的‘潇洒’,以及因感于‘浮生若梦’的那种风流佚荡的气质加以约束和纠正。他看重的是一种雄浑坚实的文学”(注: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可见,京派的文学理想和审美追求不是与现实的疏离,而是对现实的介入和批判,当然,这些介入和批判都仅限于文化领域。
京派随着战火的蔓延而风流云散,纯文学思潮在风雨飘摇的民族危难中似乎也不合时宜,但一个民族的文化追求不会因为时势艰难就荡然无存。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学需要担当更多文学以外的责任,但纯文学思潮并没有就此消歇。在诗歌领域,40年代的九叶派与京派同样体现了纯文学思潮自我调整的趋势。九叶派与30年代的现代派诗歌有直接的历史联系,但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九叶诗人拒绝沉湎于象牙塔内唯美、唯情的浅吟低唱或纯智性的上下求索,变更了与现实疏离的诗学主张。但九叶诗派与同时期的延安诗派和七月诗派仍有明显不同,它并不要求诗歌直接地宣传什么、鼓动什么和反映什么,也从未放弃对艺术独立性的认同,而是认为一个真诚而严肃的艺术家不应该对血与火的现实视而不见,它把对艺术的守护与对现实的投入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九叶诗派的“平衡”美学观追求政治与文学的平衡、现实与艺术的平衡,对于前期纯文学思想尤其是“纯诗”理论矫枉过正的偏颇进行了有效的调整。追求知性与感性的平衡,使智识与理性进入了一向以抒情感兴为主的诗歌领域,为纯文学的审美追求注入更多哲思,更具形而上色彩,这其中自然有西方文学思潮的知识背景,但九叶诗人的智性追求又与他们对民族现实的思考息息相关、血肉相连。
因此,到40年代,现代中国的纯文学思潮已经出现了综合趋势,一方面仍然防范功利主义(政治的和商业的)对文学独立性的侵蚀,坚持艺术的审美本质,同时也反省“唯美主义”、“趣味主义”的缺陷,重新思考了审美与现实的关系,重新思考了“纯文学”在文化中的位置。这些反思,最终把审美定格于“精神乌托邦”的位置。审美不再是对现实的疏离和回避,不再坚持文学与现实各行其是,也不再是个人高蹈远引,追求精神解脱的法宝,而是引导艺术对不合理的现实执行否定功能,“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引导人类精神永远追求高尚和神圣。所以,以“审美乌托邦”为内核的纯文学思潮更具哲学意味,也更具现代意识。它靠近了西方现代美学的文化功能,也融入了传统文化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气质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这固然是时代使然,但纯文学思潮自身演进的规律性也不可忽视。综合是一种理论成熟的前提,但也仅仅是前提,40年代关于“纯文学”的思考毕竟没有得到充分展开就戛然而止,它仍然是一种未完成的思考。
中国现代纯文学思潮在50年中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从早期在对杂文学传统的批判中认识到功利主义文学观的弊端,初步确立起“纯文学”意识,到二三十年代在与声势浩大的功利主义思潮的对立中把审美的纯粹性推向极端,再到三四十年代在综合趋势中走向“严肃”的审美,把“纯文学”理想定格于艺术追求、人生关怀和社会良知的统一。这一历程,实际上是从单纯追求文学独立性走向建构“审美乌托邦”的过程,也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求相始终:“纯文学”意识的出现,本身就是现代性的标志,但文学与美学的现代性,最终要体现于它从精神上与物质主义、强权政治的抗衡,体现于它对人类社会现代性进程的监督和约束。
审美之所以能够成为精神乌托邦,具有形而上意义,就在于它是以批判现实来达到超越现实。人们虚构了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点石成金,得道飞升,菩萨显灵,体现的是懦弱心态和投机心理,而把与物欲横流、强权专制抗衡的审美精神作为乌托邦,则展示了人类理性的批判意识和永不失望的坚韧。但“审美乌托邦”毕竟只是一种制衡,如过分夸大其意义,无疑会陷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潭。同样,无论是杜绝功利性的“纯文学”,还是追求“审美乌托邦”的“纯文学”,都只是人们对于文学的一种理想和信仰,作为对文学现象的理论解释,它有本质的缺陷,它把文学的一个特征扩大为文学的全部,而无视文学的无穷丰富性。何况,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纯文学思潮还是一种发展很不完善、很不充分的理论。这是我们今天评论中国现代纯文学思潮不能遗忘的前提。我们对前辈的尊敬和理解,不应该成为冷静反思历史的障碍;我们对“纯文学”理想的认同或向往,也不应该成为理性分析文学现象的障碍。
标签:文学论文; 纯文学论文; 朱光潜论文; 功利主义论文; 现代性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王国维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