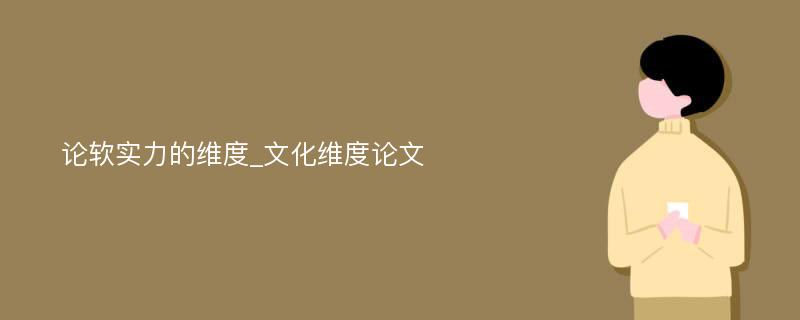
论软权力的维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权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07-07-25]
【中图分类号】 D8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9550(2007)09-0016-07
冷战后的世界政治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变化,即国家权力的可转换性、强制性和有形性不断下降,软权力的重要性开始上升。① 约瑟夫·奈(Joseph Nye)提出了“软权力(soft power)”的概念,他认为“软权力”是一个国家运用吸引力而非强制力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并使其他国家按照与它的偏好和利益相一致的方式界定自身的偏好和利益。②“软权力”与主要依靠军事力量的“硬权力”不同,它是通过诱导和说服,使对方接受和认可某种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制度安排。约瑟夫·奈虽然提出了软权力的概念,但他只是笼统地论述了软权力的特性和影响,缺少对软权力的系统分析,使软权力的研究过于零散,不利于理论和知识上的积累。本文依据软权力的来源将其划分为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和同化性权力三种维度,分别对应一国主导制度的权力、通过取得别国对其领导者身份的认可而拥有的权力以及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探讨这三种软权力的维度将有助于软权力研究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一 制度性权力
自从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的概念后,软权力大都被看做是一种文化和价值观的感召力,例如,强调美国流行文化(如好莱坞的电影和流行音乐)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美国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推广。这些当然都是软权力的重要内容,但绝不是它的全部内容。软权力之所以成为一种权力,关键在于能够让其他国家自觉自愿而不是被迫地接受一国所倡导的制度安排和国际秩序。文化吸引力固然是软权力的体现,但主导国际制度的能力(即制度性权力)也是软权力的重要维度。
制度是权力的来源,改变和建立制度都应被纳入权力分析之中,这是一种隐性的、间接的权力。③ 制度性权力是一种重要的结构性权力(structural power)。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提出,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有两种权力——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relational power)。联系性权力(按照现实主义者的解释)是指让别人做他们原本不愿做的事;结构性权力是决定全球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中包含对国际制度的规则和惯例的设定,但不限于此。④ 斯特兰奇进一步解释了结构性权力的四个来源(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的控制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1)存在于能够控制人们的安全(即威胁人们的安全或保护人们的安全,特别是保护人们免受暴力的侵犯)的人那里;(2)存在于决定和支配商品和劳务生产(这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方式的人那里;(3)存在于(至少是发达国家)能够控制信贷供应和分配的人那里;(4)存在于能全部地或局部地限制或决定获得知识的人那里。
四种结构性权力通常碰到的情况是,权力拥有者能够改变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又不明显地直接对他们施加压力要求其做出某个决定或选择。按照国际关系中现实主义学派的观点,在其他方法都失败之后,作为最后一招,军事实力和利用强制力量迫使别国就范的能力必定会占上风,不过按照结构性权力的概念,在许多时候、许多地方,决定是在强制力量没有发挥全部作用的情况下做出的。
约瑟夫·奈认为:“如果国家能使其力量在其他人眼中合法化,它们所遭遇的有违其意愿的阻力就要小得多……如果一个国家能塑造国际规则并使之与本国的利益和价值观相一致,其行为在别国的眼中就更具合法性。如果一个国家借助机构和规则来鼓励别的国家按照它喜欢的方式来行事或者自制,那么它就用不着太多昂贵的胡萝卜和大棒。”⑤ 他还指出:“国际政治性质的变化常常使无形的权力变得更加重要。国家凝聚力、普世性文化、国际制度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⑥ 因此,制度性权力是国家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约翰·鲁杰(John Ruggie)认为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regime)是被一些国家所接受的一系列相互预期、规则与法规、计划、组织实体和财政承诺。⑦ 这种机制的特点是形成了各种层次的制度。邓肯·斯奈德(Duncan Snidal)认为,对于同一问题,不同类型的机制可能会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⑧ 国际制度涉及不同的问题领域,如国防、贸易、货币和法律等。后来,国际制度被定义为在一个既定的问题领域内使各行为体预期趋于一致的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⑨ 从本质上讲,机制可能是正式的安排,也可能是非正式的安排。机制可能源于自愿协作或合作,也可能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的意志为基础。奥兰·扬(Oran Young)对协商型机制和强加型机制进行了区分。前者以参与者明确同意为特征,而后者是由居于主导地位的行为体精心建立的,即主导者综合利用增强凝聚力、推进合作和刺激利诱等手段,使其他参与者服从规则的要求。⑩ 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发展了机制的概念。他认为主导大国在机制的建立和维持中发挥领导作用,该机制既服务于主导大国的利益,也能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因为对于主导大国来说,通过建立国际制度可以掩盖其利己的实质,增强其行为的合法性。与武力威胁相比,国际制度对霸权国而言是一种极其有效的工具,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不是直接控制而是间接诱压。基欧汉承认,在一个以利己主义为行为原则的个体所组成的世界中,其决策往往导致集体利益的受损,或者即使它们之间存在共同的利益,往往也很难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而由霸权国家来主动承担并领导其他个体实现这些共同利益,则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在基欧汉看来,实现这些共同利益的工具就是主导国际制度的创设。(11)
此外,大国在维护公共物品方面还担负着重要责任。约瑟夫·奈认为,国际秩序和国际社会的发展是公共物品——人人可以消费而又不会阻碍别人获取此种物品。如果一项公共物品最大的受益者(比如说美国)不愿意率先垂范,为公共物品的供应耗费更多的资源,那么较小的受益者就更难以提供这种公共物品。因为当较多成员介入之时,组织集体行动变得相当困难。最大受益者的责任经常使得其他国家“免费搭车”。应该把国际社会的发展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因为它也是一件重要的全球公共物品。在世界上绝大多数的贫困地区中,有许多地方正处于混乱状态,深陷于疾病、贫穷和政治动荡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12)
大国在机制建立过程中的这种影响力是软权力的一种重要维度。基辛格指出:“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个世纪似乎总是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企图根据其自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13) 正是这样的大国决定了国际制度的框架并主导了国际格局的走向。美国在主导国际制度的创立方面是全方位的。通过制定规则和建立组织,美国获得了日益增长的“结构性权力”。(14) 美国不但在金融、贸易等领域创建国际制度,而且还倡议主导建立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和联合国,通过这些国际组织表达美国的意志,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在美国帮助下建立起来的国际机构,不仅影响了其他国家谋求利益的方式,而且也影响了它们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以及对国家利益的确定……这类体制并非建立在强制性的基础之上,其之所以能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利用了它们来达到其他国家也试图达到的目的。”(15) 有学者指出:“所有的霸权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基础、以强制方法实现自己的海外利益的,美国与以往霸权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完全依靠军事实力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而是想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制度性霸权体系。”(16)
除了主导联合国的创立之外,美国的影响还表现在与制度有关的三个领域。第一,设计一个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以促进国际贸易和金融的自由流通。这意味着美国必须以一种负责的态度来管理国际货币体系,提供充足而非过度的国际资本流动。美国采取的措施是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1944年通过的《联合国家和联盟国家货币金融会议最后议定书》、《国际货币基金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诞生,也确立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第二,提供开放的市场。美国积极地采取措施削减关税,并且在消除歧视性限制条件上走在前列,它也容忍欧洲国家采取地区性歧视措施,并容许欧洲在美元短缺时期保持暂时的各种壁垒。作为美国推行其贸易政策的产物,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从一个仅仅为签署国提供“共同行动”的多边协定变为新的国际贸易机制的中心。美国的实力和二战后其与欧洲相一致的意识形态对关贸总协定的建立产生了巨大的作用。(17) 第三,保持石油价格的稳定。美国早期曾设想在石油领域建立国际机制。例如,1944~1945年间,美国曾试图建立一个以它为资深成员国、英国为初级成员国的政府间石油卡特尔,但由于美国国内的反对而未能成功。由此可见,从美国获得霸主地位起,就着力在世界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建立国际制度,最终创立了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制度体系,在制度性权力方面表现了美国的软权力。
二 认同性权力
软权力的第二种维度就是认同性权力。认同性权力的概念受到建构主义“认同”概念的启示。“认同”是指某行为体所具有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建构主义认为利益依赖于认同,行为体之间认同和利益一直是处于互动的进程中,行为体通过教导他者和自身学会合作,就会逐步减少行为体之间的“异质”,促进自身内在化新的认同。(18) 建构主义的认同是指行为体由于有着共有知识,使它们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信任。这样,世界就被分成了两部分,与自己具有相互认同的、拥有共有知识的行为体被认为是可信赖的,而与自己没有认同的行为体,双方之间依旧会陷入安全困境。
而软权力中的认同性权力与建构主义的认同不完全一致。认同性权力主要是指国际关系中的主导国家通过使得其他行为体认同其主导国身份而具有的权力。当然,对于没有共有知识的“异质”行为体,主导国家的认同性权力无论如何也难以发挥其效力。如果说建构主义的认同是行为体之间的相互认同,那么软权力中的认同性权力则是主导国家依靠自身的影响,获得具有共有知识的行为体的认同,在这些行为体中获得领导地位,从而主导正式的联盟。主导国家获得认同性权力的最重要的条件是:(1)要有远远超出其他行为体的强大实力;(2)作为同盟的领导者,要给其他行为体以利益,从而引导它们自觉地追随自己。
国际体系中的领导者要有推广关于政治秩序的观念和原则的能力,并能够塑造其他国家的利益和行动,使之用新的方式理解自身的利益和政策目标。(19) 二战后,美国积极在全球建立联盟体系,代表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围堵社会主义苏联和中国,看起来是意识形态色彩极为强烈的行动,但如果从霸主国家的角度看,这也是美国遏制挑战者、维护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的必然举措。美国发挥认同性权力来维系联盟体系,实际上具有双重作用:第一,利用意识形态上与美国相近的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恐惧和对防务的需求,与之建立同盟关系,扩大美国所能支配的国家范围,使其在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获得更大的影响力。第二,通过建立在意识形态外衣掩护下的同盟关系,渗透到过去的霸主国家英国和其他强国掌控的地区,例如,通过建立“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控制了过去法国掌控的中南半岛;通过推动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渗透到历史上英国和法国掌控的中东地区;通过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主导了欧洲列强争霸的欧洲大陆。二战后,美国之所以能够通过和平方式以“美国治下的和平”取代“英国治下的和平”,除了英国已经无力遏制美国的崛起这一因素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新的霸主国家美国不是仅仅依靠军事、经济的硬力量,通过战争的方式来对抗原有的霸主国家,而是依靠认同性权力这样的软性力量以逐步渗透的方式挤入英国等强国的势力范围。
二战后,美国在国际上推动建立的联盟体系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值得人们思考的是,美国是如何让这些加入同盟的国家心甘情愿地接受其领导的呢?也就是说,美国是如何拥有和运用其认同性权力的呢?回顾美国构建联盟体系的历史,可以总结出如下原因:
首先,始终高举“道德”大旗。同盟理论认为,同盟能够凝聚在一起的首要前提是形成同盟意识形态。同盟意识形态的功能是为同盟提供例行的思考方式。(20) 还有人用同盟实体愿意为意识形态做出承诺或其意识形态相容来解释同盟形成的原因。换句话说,民主国家愿意同民主国家结盟。大多数北约成员都认同西方文明的价值观,如以代议制政府为基础的政治体制。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结盟。(21) 美国在二战后凭借战胜法西斯势力而获得的巨大威望,高举道德大旗,在全球推广它所信奉的民主体制。1947年出台的“杜鲁门主义”提出了美国捍卫自由的“道德”追求,描述了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第一种生活方式的基础是多数人的意志,特征是自由体制、代议政府、自由选举、保障个人自由、言论与信仰自由,而且有免于政治压迫的自由。第二种生活方式的基础却是以少数人的意志强加在多数人身上。它依恃的是恐怖和压制,控制着报章和电台,操纵选举,并且压制人身自由。”(22) 杜鲁门把他的主张称为“美国支持自由人抵抗武装的少数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23)
美国在战败国推行的政策也体现了类似的特点。二战后,在日本担任盟军最高司令官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以“联合国军”的名义,在“非军事化”和“民主化”的口号下,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教育等各项基本制度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推行农地改革、解散财阀、劳资关系民主化等经济民主化政策;确保思想、宗教、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妇女参政权、地方自治制度改革等措施,促进了整个社会民主化的改革。日本人对麦克阿瑟的友好态度一度达到高峰,日本国会还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感谢麦克阿瑟的决议。日本民众向麦克阿瑟元帅表达友好的信函就多达50多万封。(24) 运用认同性权力的前提是认同,美国的这些做法非常有利于获得苏联阵营以外的国家(包括被美国打败的国家)民众的认同,并由此产生了软权力。
其次,提供安全保障。二战后,美国和苏联两国由于意识形态不同、目标不同而形成尖锐对立的东西方两个阵营。美国所追求的目标是构建世界秩序,而苏联追求的目标是具体的,即占领领土。苏联一直寻求获得与西方之间的战略缓冲空间。在这样的情况下,威胁的临近经常影响国家对威胁的认知。西欧国家和日本不与苏联结盟而与美国结盟,除了与美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认同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感受到威胁的临近,“苏联经常被指责为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和革命国家,而不是一个满足现状的国家。苏联也倾向于追求具体目标或占有目标,比如领土扩张,而美国则倾向于追求抽象或环境目标——构建国际政治大环境”。(25) 在欧洲和日本看来,苏联的威胁是紧迫的,而美国则离它们很远。美国正是利用了苏联毗邻国家对苏联的恐惧,为这些国家提供安全保障,从而获得了这些国家的认同。
最后,给同盟者以利益。美国在二战后积极构建联盟体系,先后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巴格达条约组织以及美日、美菲、美韩同盟。加入同盟的这些国家之所以能够认可美国的认同性权力,而美国也能够始终处于联盟体系中心,其原因在于:美国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对与它结盟的国家或地区给予大量援助,比如,“马歇尔计划”试图通过经济援助并在获得认同的基础上组建反苏同盟,以使美国有一个“更具内聚力的势力范围”。(26) 另外,对战败国在战争赔偿方面施行“仁慈”的政策。为了扶持日本对抗苏联和中国,美国劝诱其他国家减少对日索赔数额,使日本支付了远远小于《对日和约》规定的赔偿数额。(27) 除此之外,美国还为全球盟国分担安全成本,如二战后的日美同盟使得日本免除了军备负担,经济得以稳定发展。也就是说,同盟的主导国家美国能够给同盟者以实实在在的利益,这样就获得了这些盟国政府和人民的广泛认同。与美国结盟的国家需要付出的成本则是本国在国际社会中丧失自主性或失去独立行动能力,其所获得的收益是安全得到保障、军备开支减少、使本国安全成本降低、获得可观的经济援助、有助于本国的经济复苏和发展。
三 同化性权力
同化性权力是软权力的第三种维度。目前,学界讨论最多的即是这种软权力。约瑟夫·奈认为,软性的同化性权力(co-optive power)与硬性的命令性权力(command power)同样重要。如果一个国家能使其他国家认可其权力的合法性,那么它所期望的目标将甚少受到他国的抵制。如果其文化与意识形态有吸引力,其他国家将更愿意追随其后。如果该国能够建立与其社会相一致的国际规范,那么它无须被迫改变。如果有一种能让别国按照自己的预期采取行动或限制其行为的制度,那么它就无须以高昂代价运用硬权力。(28) 命令性权力主要依靠诱惑或威胁,而同化性权力主要靠国家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29) 约瑟夫·奈所说的软权力完全等同于同化性权力,而本文所述的同化性权力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一种基于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吸引力的软权力,是软权力的一个重要维度。
作为软权力之一的同化性权力,它虽与文化有关联,但是文化的特性使我们不太容易将文化统称为软权力,因为文化至今没有统一的概念界定,甚至在很多时候同文明相混淆。一般来说,文化指的是人类的精神产品及其相应载体,它同物质活动及其产品相对应。文化和物质产品一样,并不必然包含着权力。权力意味着控制,是使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因此,权力只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文化只有在进入与他者关系之后,才可能带有权力的属性。(30)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称为软权力,关键在于能否对其他国家的行为产生导向性。哪些文化可以称之为软权力呢?如果从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来看,也即符合同化性权力的概念,应该在文化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力方面来考虑,即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其一,文化的传播能够对他国的政策制定者和国民产生感召力。其二,文化的传播能够使他国愿意效仿。而这两个条件又与运用软权力的国家的三个文化特色相关联:第一,拥有吸引人的文化和普世性的价值观。第二,具有适宜社会繁荣发展和社会财富积累的政治制度。第三,具有强大的新闻传播能力,能够将本国的普世性文化和体制特色转化为良好的国家形象。
文化的感召力是同化性权力的基础。感召力即意味着让他人接受自己国家的思维、价值观等,从而具有与自己相似的观念。感召力的基础是主导者自身的文化先进,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一国所独有的。一个国家的文化之所以能够吸引别的国家,关键在于这种文化蕴涵着符合一定时代潮流的进步性。例如,自1776年以来,美国《独立宣言》中所体现的平等原则就一直为世人所传诵。当初,美国的改革家们不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无论是为了废除奴隶制,还是禁止种族隔离,或是要提高妇女的权利。都要向公众提到“人人生而平等”。(31) 美国的民主观念也曾产生强大的感召力。美国立国之初和在早期的发展中体现的对人类正义事业的追求、对民主的践行,曾经感召了世界上无数的人们。那时,法国的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于1831年专程赴美考察九个月后,写成学术名著《论美国的民主》,推崇美国的民主观念是建立新世界的理论基础。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于1892年赴美担任纽约国家音乐学院院长,他为美国平等、自由、奋发向上的社会风貌所感染,创作了交响曲《自新大陆》,将美国社会所体现出来的清新之风吹向全世界。二战以后,美国的流行文化风靡全世界,除了这些文化形式为人们喜闻乐见外,最主要的是这种文化形式所承载的精神内涵。它“以其自由意志和平等主义的潮流,统治了电影、电视和电子通信……信息和美国流行文化已经逐渐增加了世界对于美国观念和价值的关注和开放程度”。(32)
美国文化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感召力,能够产生同化性权力,而一旦美国文化丢掉了这种普世性的内涵,转为意识形态掩盖下的对美国利益的狭隘追求,美国文化很快就会丧失它的感召力。美国的同化性权力正在经历这样的蜕变过程。美国独立智库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朱莉娅·斯韦格(Julia Sweig)对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说,在20世纪,美国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无形资产,即当全世界各国对美国的意图存有疑问的时候,宁愿相信美国的善意,但现在美国正在失去这种信任。如果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将是反美的世纪。(33)
美国奉行单边主义的代价是高昂的:在一味地按照美国的偏好和选择处理世界事务时,尽管可能在国内获得支持,但在国际上往往被视为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行为。(34) 美国为了推行民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不尊重别国的国情,直接导致了反美主义的盛行。美国抛开联合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拒绝签署防止全球气候变暖的《京都议定书》,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批准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美国通过这种傲慢的方式展现了自己的力量,表明了自己的实力,但同时也在国内外失去了权威和影响力。
推广自己的政治体制是同化性权力的另一个重要内容,目的是吸引他国仿效自己的政治制度。如果只有一个政治体制的榜样,而没有推而广之的政策相辅助,那就与同化性权力即软权力无关。正如前面所述,权力意味着控制,是使他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的能力,因此,权力只存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无论是文化还是物质产品,只有在进入与他者关系之后,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政治体制的推广是同样的道理。以美国为例,美国率先将洛克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设想变为现实,人民主权原则在美国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使其人口、领土和财富不断增加。当时的欧洲正遭受革命所带来的动乱,而在美国,个人权利和财产得到了保护。(35) 美国从建国之初就有一个理想,将美国的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推向全世界,建立美国领导下的自由世界大家庭,美国将其作为国家战略,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动。这种观点也体现在托克维尔的思想中,他认为,“平等的逐渐发展,是事所必至,天意使然,这种发展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普遍的和持久的,它每时每刻都能摆脱人力的阻挠,所有的事和所有的人都在帮助它前进”。(36)
从美国200多年来稳定发展的过程看,美国的政治制度是适合其国情的制度。但是,当美国不考虑各国的政治、文化背景,以一种宗教般的狂热态度在世界上推行这种制度时,也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这种狂热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内在的扩张和掠夺特性。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更助长了美国在世界上推行民主体制的宗教般的狂热。苏联解体后,美国又在拉美、非洲极力推广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这些地区的国家中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危机。如果从极端狭隘的国家利益着眼,以掌控者的姿态强制性地推介本国的政治体制和偏好,那么这样的同化性权力也会变成破坏性的力量。
如果说制度性权力和认同性权力是依靠构建国际制度和国际同盟来展示软权力,而同化性权力则主要依靠国内的普世性文化和良好的政治制度的感召力。同化性权力的运用必须要借助一定工具,这种工具就是公众外交和强大的对外传播的媒体力量。美国政府将公众外交作为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投入数万人员和每年数亿美元的财政拨款。(37) 美国新闻署曾经是美国公众外交的核心机构,其主要职责是推行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即向世界其他国家解释和宣传美国政府的政策,与其他国家在教育、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的交流与对话,介绍美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文化,宣扬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念。新闻署并入国务院后,不再作为独立的政府部门存在,但其多数活动仍在继续进行。(38) 美国公众外交的突出成果就是:“其他国家了解美国要胜过美国人了解其他国家,甚至要胜过美国人了解自己的国家。”(39) 如果说美国的公众外交反映的是美国政府在推介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为,而美国传媒的全球影响力则反映了美国社会在推介美国形象和施展同化性权力方面的作为。美国是一个大众传媒的超级大国,美国传媒在世界上推介美国的国家形象、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影响全球舆论。美国以电影和电视为龙头的大众传播与文化出口,成为美国潜移默化影响世界公众思想的重要手段。
四 结语
作为分析软权力的框架,对软权力的维度进行划分和详细阐述是必要的,但这不意味着三种软权力是相互分离和独立的。运用同化性权力易于形成认同,在认同的基础上运用认同性权力易于结成同盟,在形成同盟的基础上便于建立国际制度,行使制度性权力。实际上,国家也都是综合地运用这三种软权力。无论是制度性权力、认同性权力还是同化性权力,都与国家的硬权力密不可分,拥有强大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国家也往往拥有较强的软权力,有能力主导和控制制度安排,能够获得其他国家对其地位的认同,同时也更容易产生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吸引力。三种软权力都无法在短期内获得和累积,而是需要长期的维护和培育。在运用三种软权力的过程中,国家有必要在关注自身利益的同时考虑其他国家的利益,滥用军事权力和以经济实力作为打压别国的砝码都将使国家的软权力遭到削弱。
注释:
①[美]约瑟夫·奈著,何小东、盖玉云等译:《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165页。
②Joseph S.Nye,"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Issue 80,Fall 1990,pp.165-168.
③Stefano Guzzini," Structural Power:The Limits of Neorealist Power Analysi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7,No.3,1993,p.452.
④Susan Strange,States and Markets,2nd edition,London:Pinter,1994,pp.24-25.
⑤[美]约瑟夫·奈著,吴晓辉、钱程译:《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
⑥Joseph S.Nye," Soft Power," pp.153-171.
⑦John Gerard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29,No.3,1975,p.570.
⑧Duncan Snidal," Coordination versus Prisoners' ,Dilemma:Implications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m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79,No.4,1985,pp.923-924.
⑨Stephen D.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s: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 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Ithaca,N.Y.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1.
⑩Oran R.Young," Regime Dynamics:The Rise and Fall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Stephen D.Krasner,ed.,International Regimes,p.100.
(11)苏长和:《解读“霸权之后”——基欧汉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12)Joseph S.Nye,Jr.,"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78,No.2,2002,pp.233-244.
(13)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 Publishers,1994,p.17.
(14)Aaron L.Friedberg,"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1.109,No.1.1994,p.9.
(15)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第159页。
(16)阎学通:《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7)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174~179页。
(18)[美]亚历山大·文特:《国际政治中认同和结构变化》,载 [美]约瑟夫·拉彼德、[德]弗里德里希·克拉托赫维尔主编,金烨译:《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69~91页。
(19)G.John Ikenberry,"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1.111,No.3,1996,p.388.
(20)[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年版,第573页。
(21)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580页。
(22)Henry Kissinger,Diplomacy,p.452.
(23)Henry Kissinger,Diplomacy,P.453.
(24)[日]寺岛实郎著,徐静波、沈中琦译:《呼吸历史——对亚太区域的人文思考》,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9页。
(25)参见[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88页。
(26)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62页、第65页。
(27)周斌:《战后日本的崛起——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政治考察》,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28)Joseph S.Nye," Soft Power," pp.153-171.
(29)Joseph S.Nye," 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and Science Quarterly,Vol.105,No.2,1990,p.181.
(30)陈玉聃:《论文化软权力的边界》,载《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期,第57页。
(31)[美]戴安娜·拉维奇编,林本椿等译:《美国读本:感动过一个国家的文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8页。
(32)Robert O.Keohane and Joseph S.Nye,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Vol.77,No.5,1998,p.87.
(33)Dejin Su,The Anti-American Century,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en/topic.cfm? topicid+53.
(34)Ralph G.Carter," Leadership at Risk:The Perils of Unilateralism," 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36,No.1,2003,p.18.
(35)[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页。
(36)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第85页。
(37)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5页。
(38)关于公众外交和美国新闻署的情况,参见韩召颖:《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公众外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39)Fitzhugh Green,American Propaganda Abroad,New York:Hippocrene Books,1988,p.198,转引自李智:《文化外交:一种传播学的解读》,第10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