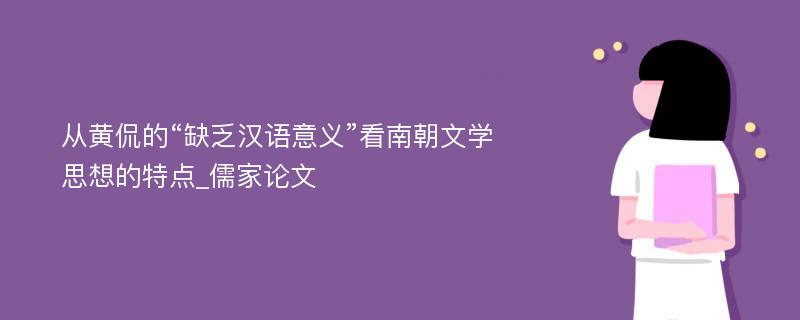
從皇侃《論語義疏》看南朝文學觀念之特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朝论文,從皇侃论文,論語義疏论文,文學觀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漫長的中國學術史上,現代學科意義上的文史哲分科並不明顯,而是體現出各門學術史的互相滲透與融合的態勢,這種特點,在魏晋南北朝的學術史上看得很清楚。在古人心目中,無論是任何學問,都是精神活動,因而這種精神活動是互相融會,互相促進的。《文心雕龍·宗經》中提出:“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者也。”也就是說,經典的效用不僅可以參天地,效鬼神,而且可以洞察人性的奧秘,窮盡文章的神髓。 在儒家經典中,《論語》獨具風采。清代學者唐晏論曰:“《論語》之爲經,乃群經之鎖鑰,百代之權衡。七十子學孔子而各得其性之所近,孔子既没,乃各徵所聞以志弗諼。故二十篇不必出諸一人也。”①《論語》是記載孔子與弟子言行的重要儒家經典。孔子的文學思想與範疇,比如興觀群怨、思無邪、文質觀念、美善合一等思想,在《論語》中得到直接的顯現,奠定了儒家文學批評的基礎,《論語》在漢魏以來,隨著孔子地位的變化與時代精神的變遷,不斷得到闡釋與傳播,獲得提升。梁代皇侃的《論語義疏》不僅在《論語》注疏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且延及文學思想的變化與發展。彰顯了南朝文學批評思想的變化特點。迄今爲止,對於皇侃《論語義疏》的經學上的作用與地位的研究著論不絕如縷,但是對於它在文學理論構建上的作用與貢獻,相關的研究論著極少,本文擬就此空白作一些補苴。 一、性情之辨與文學創作 皇侃《論語義疏》對於文學觀念的構建作用,首先是從性情之辨的角度去著眼的。這顯然是與他的經學家的獨特視野直接相關的。 梁武帝時期是南朝士族群體與文化達到鼎盛的時期,也是學術文化繼魏晋的動蕩分化之後進行重新組合的時期。梁武帝禪齊後,開始復興儒學,《梁書·武帝本紀中》記載:“七年春正月乙酉朔,詔曰:‘建國君民,立教爲首。不學將落,嘉植靡由。朕肇基明命,光宅區宇,雖耕耘雅業,傍闡藝文,而成器未廣,志本猶闕,非所以熔範貴游,納諸軌度。思欲式敦讓齒,自家刑國。今聲訓所漸,戎夏同風,宜大啓庠斅,博延胄子,務彼十倫,弘此三德,使陶鈞遠被,微言載表。’”梁武帝多次下詔修禮作樂,他在《訪百僚古樂詔》中提出:“夫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所以移風易俗,明貴辨賤。而《韶》、《濩》之稱空傳,《咸》、《英》之實靡托,魏晋以來,陵替滋甚,遂使雅、鄭混淆,鐘、石斯謬”。②梁武帝繼承了漢代《詩大序》的“聲音之道與政通”的觀點,高度重視文學“移風易俗,明辯貴賤”的作用。他的兒子簡文帝蕭綱也倡導儒家“詩教說”,在《請尚書左丞賀琛奉述制旨毛詩義表》中明確提出:“臣聞樂由陽來,性情之本,《詩》以言志,政教之基。故能使天地咸亨,人倫敦序。”③强調文學對百姓的教化作用,推重《詩》的政教地位。 皇侃是梁代經學的代表人物。據《梁書·儒林傳》記載:“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侃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起家兼國子助教,於學講說,聽者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秘閣。頃之,召入壽光殿講《禮記義》,高祖善之,拜員外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遍,以擬《觀世音經》。丁母憂,解職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侃既至,因感心疾,大同十一年,卒於夏首,時年五十八。所撰《論語義》十卷,與《禮記義》並見重於世,學者傳焉。”④皇侃乃魏時著名學者皇象的九世孫,有家學淵源,他本人以孝聞名於世,精通《三禮》、《孝經》與《論語》等經典,但最擅長的是《論語義疏》。 皇侃《論語義疏》對於南朝文學觀念的建樹,表現在人性論的重構上面。自先秦諸子以來,對於文學觀念的看法,總是同人性問題相聯繫的。無論是孔孟還是老莊,都認爲文學活動是人性的彰顯與詠嘆。“詩言志”,“興觀群怨”,“以意逆志”等文學命題的提出,即表明了這一點。魏晋以來,“文以氣爲主”的文學思想發展了先秦兩漢的“詩言志”觀念,成爲抒發士人性情的觀念。經學對於文學的影響,在南朝得到了延伸。而皇侃《論語義疏》中的觀念即是表徵。它汲取了三國時魏國哲學家王弼的玄學,對於與文學觀念相關的性情之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皇侃《論語義疏》的顯著特點是調和儒玄。這一點也與當時的風氣有關。《顏氏家訓·勉學》中記載:“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弃之度外……洎於梁世,茲風複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爲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⑤所以皇侃受到當時風氣的影響也是很自然的。 何晏的《論語集解》融合漢代至魏的經學家注釋而撰成,創意並不多。⑥皇侃的《論語義疏》融匯漢魏以來王弼、何晏等人的注疏成果,將玄學與經學融會貫通。但是這本書在以往評價並不高,《隋書·經籍志》雖然著録有皇侃《論語義疏》十卷,但是在敘録中並没有給予特別的提示,而是褒揚何晏的《論語集解》。⑦有的研究者認爲:“皇疏雖一度盛行,但因它以道家思想解經,且多依傍前人,較少創獲,又‘時有鄙近’,頗爲後世學人不滿。隨著時代的變遷和政治傾向、學術思想風氣的轉變,至北宋咸平二年(九九九),朝廷便命邢昺等人改作新疏。”⑧邢昺代表著北宋的崇儒觀念,他在注《論語》時,有意删削皇侃注疏。以後因邢昺的注疏適應北宋之後的儒學觀念,於是皇侃注疏衰落而邢昺的注疏成爲正宗。但皇侃注疏卻在日本等地廣爲傳播,其中的思想光彩,並没有被消解。這本書對於文學觀念的潜移默化,既凝聚了魏晋以來的思想成果,又拓展了思維的空間與方法的多樣化,體現出南朝思想文化的多元互動之魅力。 性情之辨是魏晋以來經學的重要問題,涉及文學創作的根本。性指人之爲人的本體,情是指性與環境接觸後的意志心理表現,與文學創作直接相關。西漢的《淮南子·天文訓》中指出:“道始於虛霩,虛霩生宇宙,宇宙生氣,氣有涯垠。清陽者薄靡而爲天,重濁者凝滯而爲地。清妙之合專易,重濁之凝竭難,故天先成而地後定。”⑨這樣,清濁又進入了元氣的範疇,用來闡明宇宙生成論問題。東漢王充《論衡》中廣泛採用清濁之氣來論人的道德操行與志向。在《命禄篇》中指出:“故夫臨事知愚,操行清濁,性與才也。”⑩《逢遇篇》中指出:“道有精粗,志有清濁也。”(11)王充關於清濁之氣與人性養成,命運遭際的論述,既是先秦兩漢元氣說的總結,也對六朝思想影響甚大。三國時劉劭《人物志·九徵》中指出:“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爲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12)皇侃認爲,人的性情由於秉氣而形成不同的品質,清濁二氣是個體秉受天地之氣的道德素養,聖人與小人之分便以氣而論。皇侃《論語義疏·陽貨》在注孔子“唯上知與下愚不移”話語時指出: 夫人不生則已,若有生之始。便稟天地陰陽氛氳之氣。氣有清濁,若稟得淳清者,則爲聖人;若得淳濁者,則爲愚人。愚人淳濁,雖澄亦不清;聖人淳清,攪之不濁。故上聖遇昏亂之世,不能撓其真。下愚值重堯疊舜,不能變其惡。故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也。而上智以下,下愚以上,二者中間,顏、閔以下,一善以上,其中亦多清少濁,或多濁少清,或半清半濁,澄之則清,攪之則濁。如此之徒,以隨世變改,若遇善則清升,逢惡則滓淪,所以別云“性相近習相遠”也。(13) 皇侃强調清濁之氣的秉賦是聖愚之性的決定因素。而文藝則是這種氣對於人類的感染,曹丕《典論·論文》的“文以氣爲主”思想基於此種元氣說而獲得論證。葛洪《抱朴子·尚博》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作家創作個性與文辭風格的內在聯繫,提出:“清濁參差,所稟有主,朗昧不同科,强弱各殊氣。而俗士唯見能染毫畫紙者,便概之一例。斯伯牙所以永思鍾子,郢人所以格斤不運也。”葛洪認爲作者稟氣不同,個性有异,藝術風貌也不同。他在另一個地方也談到:“夫才有清濁,思有修短,雖並屬文,參差萬品。或浩瀁而不淵潭,或得事情而辭鈍,違物理而文工。蓋偏長之一致,非兼通之才也。”(《抱朴子·辭義》)這是强調文學創作要因材使氣,不要强力爲之。南朝梁代鍾嶸《詩品序》提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詩品序》强調氣是貫通與啓動人與天地之間的生命感興,這些文論家繼承了先秦兩漢以來的這些以氣論性情清濁的論點,並加以發揮。 皇侃《論語義疏》中的性情觀,明顯地受到三國時魏國玄學家王弼的《論語釋義》的影響。《禮記·大學》中提出:“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儒家認爲,人性的本體是秉承天命而生成的,天命乃是生來俱有的道德秉性,而情則是後天習染的,魏晋玄學則試圖將性情說成是後天生成的自然之道,無善無惡的道體,王弼稀釋了性情中的道德因素,而代之以精神本體“無”的概念,强調性與道的結合。聖人體無,是自然之道的人格表現,理想人格的本體即是“無”與道的表現。從現存的《論語》與《史記·孔子世家》等文獻資料來看,孔子是一位性情中人。他自言不諱地提出:“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皇侃注疏:“夫仁人不佞。故能言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人也。”(《論語義疏·里仁》)也就是說,真正的仁者應是憎愛分明的性情中人。《論語·陽貨》中記載:“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皇侃義疏: 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然性無善惡,而有濃薄。情是有欲之心,而有邪正。性既是全生,而有未涉乎用,非唯不可名爲惡,亦不可目爲善,故性無善惡也。所以知然者,夫善惡之名,恒就事而顯,故老子曰:“天下以知美之爲美,斯惡已。以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此皆據事而談。情有邪正者,情既是事,若逐欲流遷,其事則邪,若欲當於理,其事則正,故情不得不有邪有正也。故易曰:“利貞者,性情也。”(14) 漢代的儒學性情觀,一般尊性貶情,認爲性尊情卑,性善情惡,猶陽尊陰卑一樣,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即持此種觀念。以陰陽定性情,反映了漢代今文經學的人性論的基本路徑,而魏晋玄學的情性論則不然,認爲性也好,情也好,都是人性自然之道的顯現,性是天然生成的,由人秉受陰陽二氣而獲得,而性與外界事物接觸則自然生成了情感,情感是性不得不外化的自然產物,雖是聖人也難免。因此,性與情都是中性的範疇,不存在善惡的價值屬性。皇侃强調性情由於外界事物與人所接觸的善惡習染而生成的。他又指出: 王弼曰:“不性其情,焉能久行其正?”此是情之正也。若心好流蕩失眞,此是情之邪也。若以情近性,故云性其情。情近性者,何妨是有欲?若逐欲遷,故云“遠”也。若欲而不遷,故曰“近”。但近性者正,而即性非正,雖即性非正。而能使之正。譬如近火者熱,而即火非熱,雖即火非熱,而能使之熱。能使之熱者何?氣也,熱也。能使之正者何?儀也,静也。又知其有濃薄者。孔子曰“性相近也”,若全同也。 王弼的所謂“性其情”,也即是魏晋玄學中的聖人理想人格。他們能够感物而不爲物所困惑,而並不是無情無欲。皇侃引用王弼的話,說明他是贊同王弼的性情觀的。 在魏正始年代,玄學家們曾說情性之辨發表過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學說。王弼與何晏在性情觀上實不相同。《三國志·魏書·鍾會傳》附何劭《王弼傳》云:“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15)何晏否認理想人格聖人存在著現實的情欲,聖人無喜怒哀樂。何晏《論語集解》中注“性與天道”云:“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聞也。”王弼與何晏的觀點明顯不同。他强調聖人應物而無累於物,精神的高尚與世俗的享受兩不相妨。這一觀點使兩漢儒家的情性觀得到修正。它對於六朝文學理論中的緣情感物,超越世俗的文學思想有著直接的啓示。皇侃《論語義疏》接受王弼的觀點,强調聖人應物而無累於物的性情觀。 《三國志·魏書·鍾會傳》附何劭《王弼傳》還記載:“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逾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16)王弼在與荀融對話中,借題發揮,意爲你的觀點雖然明足以察微,然而不能去掉人的自然之性。王弼還提出,即使孔子這樣的聖人,雖然對於顏回的在心目中的份量很瞭解,但是在顏回死後,悲不自勝,哀嘆“天喪予,天喪予”,可見聖人也是有情感的,過去自己常常以爲聖人不能免俗,未能以情從理,現在纔知道自然之情是不能革除的。 皇侃心目中的孔子也是這樣一位“應物而無累於物者”的聖人,他在《論語義疏自序》中提出: 但聖師孔子符應頹周,生魯長宋,游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删詩定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十有二。但聖人雖异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情既同,則朽没之期亦等。故嘆發吾衰,悲因逝水,托夢兩楹,寄歌頹壞。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背之後,過隙區駐。(17) 皇侃刻畫的孔子形象正是這樣一位聖人。顯然,他直接用王弼的性情論來解讀孔子形象,從而使孔子形象從兩漢神學化的模式中解放出來,變成富有情懷的一位世俗聖賢。而孔子的文學觀念自然也就具有了凡俗與超越相結合的特點。聖人尚且應物而無累於物,至於芸芸衆生,更是應物而感的族類,只不過他們不能像聖人那樣超凡入聖,擺脫情感的役使。皇侃提出,個體的人都秉受元氣而生,這就是性的自然本質,但是由於後天習染,也就是社會環境的不同,接觸的人各各不同,緣此而造成善惡不同,“性者生也。情者成也。性是生而有之。故曰生也。情是起欲動彰事。故曰成也”,皇侃這樣的解釋雖無大的創見,但也說明了性與情的不同,是由動静造成的,而與善惡無關,客觀上也爲情感正名。 同時,皇侃强調,情雖無善惡之分,但卻有邪正之辨,關鍵在於性其情,即用性的天生而静的本體克制與化解情的過於膨脹的欲望。《論語·雍也》中記載:“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皇侃義疏云:“此舉顏淵好學分滿所得之功也。凡夫識昧,有所瞋怒,不當道理,唯顏回學至庶幾,而行藏同於孔子,故識照以道,怒不乖中,故云‘不遷’。遷,猶移也。怒必是理不遷移也。”云“顏淵任道,怒不過分”者,“過猶失也。顏子道同行舍,不自任己,故曰‘任道’也。以道照物,物豈逃形?應可怒者皆得其實,故無失分也”。(18)皇侃强調,顏回不遷怒,不貳過,體現出那種任情適得其分的秉賦。 這種以性制情的觀念,我們在魏晋名士的文學觀念中可以經常看到。《文選》卷五十五選録了陸機《演連珠五十首》,其中强調:“臣聞烟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姻微,性充則情約。”李善注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19)“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李善注曰:“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文心雕龍·明詩》提出: 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聖謨所析,義已明矣。是以“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舒文載實,其在茲乎!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爲訓,有符焉爾。 劉勰的觀點,也是基於儒家性情觀念而提出的。 皇侃《論語義疏》中論性情,特別重視自然之道在性情範疇中的運用。儒家强調孝悌爲仁之體,而仁則是一切道德的出發點。皇侃在注疏《論語》中孔子弟子有子所言“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時引用道:“王弼曰: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也。”可見王弼的自然之道是皇侃闡釋儒家孝悌之道時的重要依據。《論語·泰伯》中提出:“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皇侃義疏: 王弼曰:言有爲政之次序也。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采謠以知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矯俗檢刑,民心未化,故又感以聲樂以和神也。若不采民詩,則無以觀風,風乖俗异,則禮無所立;禮若不設,則樂無所樂;樂非禮,則功無所濟。故三體相扶,而用有先後也。侃案:輔嗣之言可思也。且案內則明學次第:十三舞勺,十五舞象,二十始學禮,惇行孝悌,是先學樂,後乃學禮也。若欲申此注,則當云先學舞勺舞象,皆是舞詩耳,至二十學禮,後備聽八音之樂,和之以終身成性,故後云樂也。(20) 孔子這三句話的主旨是描述的君子成長之路的特點,王弼提出“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皇侃在引用王弼的話之後,强調王弼的話可以採納。禮樂刑政出於自然,統治者應當順應民情采詩觀風,無爲而治。從個體人生成長來說,詩樂俱是人在兒童與少年時代學習的課目內容,至年二十學禮,漸次成長。這亦是自然生長的過程,符合人的教育特點。 漢魏以來,隨著社會結構的轉變,以及道德價值觀念的變化,人們在重視道德倫理的同時,也看重文章中的才情與才性。在六朝名士中,吟詠情性成了時代風氣與文學理念,構建成當時的審美精神與趣味。裴子野《雕論》中批評當時的風氣:“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尚,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游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詠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裴子野思想比較保守,他指責魏晋以來,由於皇帝的嗜好與提倡,吟詠情性形成風氣,造成經學章句衰落,文學活動興盛。不過,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風尚的變遷。 綜觀魏晋以來的性情之辨與文學關係的觀點,大體說來,有這樣幾類:一、正面倡導性情乃文學之本體,自然之符契。如劉勰《文心雕龍》中指出:“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鍾嶸《詩品序》指出:“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萬有,靈祗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二、强調性情乃文學的審美特性,也是詩歌與其他文體的區別所在。陸機《文賦》指出:“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鍾嶸《詩品序》中提出:“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梁簡文帝蕭綱《與湘東王書》:“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這些性情之辨影響到當時的所謂“文筆之辨”。三、對情性二者關係的辨析,一方面是漢代詩學的“發乎情止乎禮義”觀念仍然保留;另一方面,情性並舉,無分軒輊。兩漢倡導性尊情卑,六朝則提倡人當道情。《世說新語·排調》記載:“王北中郎不爲林公所知,乃著論沙門不得爲高士論,大略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反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世說新語·傷逝》記載:“王戎喪兒萬子,山簡往省之,王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王曰:“聖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范曄《獄中與諸甥侄書以自序》:“常謂情志所托,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這些文獻資料,都記載了六朝人在情性觀念上的看法,已經不同於兩漢時代,呈現出更加開放的態勢,切中文學審美活動的肯綮,而皇侃的《論語義疏》正反映了這種時代精神。 二、理想人格與詩學精神 皇侃《論語義疏》的思想成就,還表現在對於秦漢與魏晋以來的經學與文學中的根本問題,也就是人格養成問題進行了融會貫通,拓展了文學研究與經學的空間,與劉勰《文心雕龍》中經學與文學關係的構建,完全可以互補。 人格問題是孔孟之道的根本問題,以君子人格作爲教化與養成的始點也終點。强調“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可以說是孔孟學說的核心觀念。但是對於人格的內涵,以及人格的養成,在先秦時代,孔孟强調的內省式與自我修養的路徑,迄至秦漢之際,形成了《禮記大學》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再到修齊治平的路徑,而老莊爲代表的道家則反對禮樂對於人心的桎梏,主張“道法自然”,“任其性命之情”。 漢魏以來,社會陷於無序與動亂之中,國家分治,南北分裂,民不聊生,而社會中堅力量的士人與官僚也被生命悲劇所困擾。傳統的注不破經,疏不破注的經學,便不得不爲解答現實問題的玄學所取代。何晏的《論語集解》雖然以彙集漢魏以來的學術家的注集爲編修體例,與王弼《周易注》與《論語釋疑》的大言發微不同,但是它的採納重點所在,是關心與討論人格養成與現實問題之關係,彰顯出魏晋玄學的關注所在。 皇侃《論語義疏》看到了以往儒學人格論的缺失在於過分拘泥於現實情境,而老莊與王弼、郭象的玄學,推崇性命之情與自然之道,融入孔孟的人格論,恰恰可以啓動其中的生命底蘊,使生命與人格得到一種本體論上的自我意識。理想人格過於沉迷於現實情境與修身養性,克己復禮,便無法獲得自我超越,而老莊的逍遙游思想可以裨補儒家人格論的拘束。王弼的《周易注》與《老子注》與《論語釋疑》正是有鑑於此而加以重釋。 皇侃心目中的君子人格,既有傳統的成份,更有玄學的理想人格因素。孔子曾經對於堯這樣的上古聖賢大加讚美,認爲他們彰顯了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境界。《論語·泰伯》中記載:“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也!”皇侃在義疏中加以發揮: 王弼曰:聖人有則天之德,所以稱“唯堯則之”者,唯堯於時全則天之道也。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傾,而名分形焉。若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任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21) 皇侃援用孔子的話來嘆美堯的人格偉大在於行不言之美,“則天成化,道同自然”,這樣的自然無爲之境界順從天道,用來施政,便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顯然,這裏面融入了道家“道法自然”的理念,是典型的調和儒道的經學思想與方法。 皇侃認爲,孔子自己的人格理想也浸染著這樣的意境。《論語·陽貨》中記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皇侃在注這段話時發揮: 孔子既以有言無益,遂欲不言,而子貢怨若遂不言則門徒無述,故孔子遂曰:天亦不言,而四時遞行,百物互生,此豈是天之有言使之然乎?故云“天何言哉”也。天既不言而事行,故我亦欲不言而教行,是欲則天以行化也。王弼云:“子欲無言,蓋欲明本,舉本統末,而示物於極者也。夫立言垂教,將以通性,而弊至於淫;寄旨傳辭,將以正邪,而勢至於繁。既求道中,不可勝禦,是以修本廢言,則天而行化。以淳而觀,則天地之心見於不言;寒暑代序,則不言之令行乎四時。天豈諄諄者乎?”(22) 孔子認爲,天道中蘊含的性命之情與智慧,是人類無法完全體認的,因此,最高的智慧便是不言之言,不說之說。而子貢不能明白這一點,所以孔子再三用天道來啓悟,也隱含著自己以天道爲人格楷模的思想。皇侃在注釋中,引用王弼的思想來解釋這段話,並且强調天道與人道是本末體用之關係,聖人的人格以天爲榜樣,政治也以天道無言爲法則。 儒家的人格精神以陽剛爲美。《易傳》中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對於孔子人格的剛健强悍,皇侃《論語義疏》加以充分肯定,因爲儒家人格思想的基本出發點是有爲,甚至“知其不可而爲之”,歷史上許多儒家思想薰陶下的仁人志士,都以這種悲劇人格精神來激勵自己,屈原投江自沉,東漢末年黨錮之禍中就義的士人,以及後來的嵇康、韓愈、文天祥等人皆是。《論語·八佾》中記載:“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皇侃解釋道: 言今無道將興,故用孔子爲木鐸以宣令聞也……孫綽曰:“達哉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觀大聖,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玄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23) “天將以夫子爲木鐸”是後世儒家一直津津樂道的名言,木鐸精神可以說是儒家代天立言的表徵,一直到今人樂道的北宋張載的“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即是這種精神的發展與弘揚。皇侃對此的解釋,既立足於傳統的經學,又融入了知天命的思想。强調孔子“深明於興廢。明道內足”的自我意識。皇侃引用了玄學家孫綽的注釋,指出孔子的藝術精神與藝術作品,就是這種木鐸精神的表現,“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玄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瞻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這樣就將孔子的藝術精神與人格精神融會貫通,影響後人。 在魏晋文學思想中,將自然與教化融會貫通,是許多重要的文論家的思想理念與方法。比如,西晋時陸機《文賦》提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未泯。”與皇侃同時代的劉勰在《文心雕龍·序志》中提出: 夫宇宙綿邈,黎獻紛雜,拔萃出類,智術而已。歲月飄忽,性靈不居,騰聲飛實,製作而已。夫人肖貌天地,稟性五才,擬耳目於日月,方聲氣乎風雷,其超出萬物,亦已靈矣。形同草木之脆,名逾金石之堅,是以君子處世,樹德建言。豈好辯哉?不得已也! 劉勰將孔子的木鐸精神作爲自己的寫作精神,自叔創作《文心雕龍》是爲了繼承孔子與孟子的憂患精神。 孔子對於人生的使命,提倡以理想人格來擔當,這是儒家思想的特點。《論語·子罕》中記載:“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皇侃注疏: 此欲明君子德性與小人异也,故以松柏匹於君子,衆木偶乎小人矣。言君子小人若同居聖世,君子性本自善,小人服從教化,是君子小人並不爲惡。故堯舜之民,比屋可封,如松柏與衆木同處春夏。松柏有心,故本蓊鬱。衆木從時,亦盡其茂美者也。若至無道之主,君子秉性無過,故不爲惡;而小人無復忌憚,即隨世變改。桀紂之民,比屋可誅,譬如松柏衆木同在秋冬,松柏不改柯易葉,衆木枯零先盡。(24) 建安七子之一的劉楨《贈從弟》詩云:“豈不罹嚴寒,松柏有本性?”勉勵從弟在動亂中保持人格的堅貞純潔。皇侃對於儒家知其不可而爲之的人格精神是堅持認同的。但同時他與接受了玄學的自然之道思想,採用自然之道來充實命運論。 皇侃的《論語義疏》既肯定了孔子殉道精神,同時又用道家與玄學的命運觀念來解釋之。《論語·衛靈公》中記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本義是强調君子人格中的擔當精神與勇氣。這裏的道顯然是指儒家的社會倫理之道,包括仁義禮智信等因數。但皇侃在解釋這段話時,引入了道家自然之道的因素: 道者,通物之妙也。通物之法,本通於可通,不通於不可通。若人才大,則道隨之而大,是人能弘道也。若人才小,則道小,不能使大,是非道弘人也。故蔡謨云:“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云‘非道弘人’之也。”(25) 用通物之妙來解釋道的基本內涵,可謂聰明之極,通物便是不滯於物,與物消息。而對於道“行之由人”,皇侃認爲,聖人既要弘道揚義,勇於擔當,又要承認天命,儒家的知其不可而爲之道,與道家的“道法自然”,可以統一在人格精神之中。在注《論語·子罕》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一句時,皇侃發揮道: 逝,往去之辭也。孔子在川水之上,見川流迅邁,未嘗停止,故嘆人年往去,亦復如此。向我非今我,故云“逝者如斯夫”也。斯,此也。夫,語助也。日月不居,有如流水,故云“不舍晝夜”也。江熙云:“言人非南山,立德立功,俛仰時過,臨流興懷,能不慨然乎?聖人以百姓心爲心也。”孫綽云:“川流不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而道猶不興,所以憂嘆也。”(26) 此段重在强調逝者如斯,不舍晝夜中的人生哲學。時間無限而人生有限,要在有限的人生中窮盡無限的事業,注定是悲劇,故而孔子有逝川之嘆。這也是一種命定。在這段注釋與發揮中,我們是不難從而考見王羲之《蘭亭序》那樣的“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的人生感喟的。《論語·堯曰》中還記載: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皇侃解釋道:“命,謂窮通夭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强求,則不成爲君子之德,故云‘無以爲君子也’。窮謂貧賤,達謂富貴,並稟之於天,如天之見命爲之者也。”(27)皇侃對於命的看法,顯然是融進了老窮的命運觀,帶有知天命任自然的思想。魏晋時阮籍的《通老論》與《通易論》中闡發了這種調和名教與自然的觀念。比如阮籍在《通老論》中曾經指出:“聖人明於天人之理,達於自然之分,通於治化之體,審於大慎之訓,故君臣垂拱,完太素之樸;百姓熙怡,保性命之和。”“道者,法自然而爲化,侯王能守之,萬物將自化。《易》謂之太極,《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而皇侃對於《論語》的這些看法,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與兩漢對於《論語》的解釋明顯不同。 推崇自然的人格理想,是皇侃《論語義疏》中吸收老莊與王弼哲學形成的思想觀念。這一思想與魏晋至南朝的文論批評一脉相承,相得益彰。《論語·學而》中記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皇侃注疏: 巧言者,便僻其言語也。令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爲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28) 老子云:“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皇侃認爲,人們雖然有時難免有假,但是當時社會普遍存在著巧僞,因此,也就仁義之心漸消,形成爲一種社會風氣就很壞了。導致人心的變壞。皇侃認爲,禮樂教化,移風易俗,是社會文明的必須的環節,而外在的藝術則是要從內在的的心靈需要出發。如果没有這種內在的需要,那麽一切禮樂也就成了擺設,還不如拋弃之。 《論語·陽貨》記載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皇侃注疏:“孔子重言‘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明樂之所云不在鐘鼓也。王弼云:禮以敬爲主,玉帛者,敬之用飾。樂主於和,鐘鼓者,樂之器也。於時所謂禮樂者,厚贄幣而所簡於敬。盛鐘鼓而不合雅、頌,故正言其義也。繆播曰:玉帛,禮之用,非禮之本。鐘鼓者,樂之器,非樂之主。假玉帛以達禮,禮達則玉帛可忘。借鐘鼓以顯樂,樂顯則鐘鼓可遺。以禮假玉帛於求禮,非深乎禮者也。以樂托鐘鼓於求樂。非通乎樂者也。苟能禮正,則無持於玉帛,而上安民治矣。苟能暢和。則無借於鐘鼓,而移風易俗也。”(29)皇侃引用王弼的話,强調禮樂以仁心爲本體,而玉帛與鐘鼓則是禮樂的表現,如果不能崇本舉末,則外在的禮樂不足爲訓。反而成爲巧僞的器具。 皇侃提出,禮之用和爲貴的本體在於樂教之和。而樂之的來自於內心的和敬,發乎自然,心靈是禮樂的本體。阮籍《樂論》指出:“乾坤易簡,故雅樂不煩;道德平淡,故無聲無味。不煩則陰陽自通,無味則百物自樂。日遷善成化而不自知,風俗移易而同於是樂。此自然之道,樂之所始也。”(30)嵇康《聲無哀樂論》中也持這樣的觀點。嵇康反對儒家的樂教,倡導無聲之樂,他提出:“和心足於內,和氣見於外。故歌以叔志,舞以宣情。然後文以采章,照之以風雅,播之以八音,感之乙太和。導其神氣,養而就之,迎其情性,致而明之,使心與理相順,氣與聲相應。”(31)這種以自然樂教爲上的觀點,同皇侃的思想是一致的。皇侃的樂教自然論,明顯地受到魏晋思想的影響。 《論語·憲問》中記載:“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皇侃注“有德者必有言”時提出:“既有德,則其言語必中,故必有言也。”在注“有言者不必有德”時指出: 人必多言,故不必有德也。殷仲堪云:修理蹈道,德之義也。由德有言,言則末矣。末可矯而本無假,故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李充曰: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敷陳成敗,合連縱橫者,說客之言也;淩誇之談,多方論者,辯士之言也;德音高合,發爲明訓,聲滿天下,若出全,有德之言也。故有德必有言。有言不必有德也。(32) 皇侃在注這段話時,專門引用了李充的話語,强調有德者之言內容與語辭一致,而能言善辯之徒往往没有道德,“甘辭利口似是而非者。佞巧之言也”。《論語·衛靈公》中記載:“子曰:辭,達而已矣。”皇侃注疏:“言語之法,使辭足宜達其事而已,不須美奇其言以過事實也。”(33)《論語·雍也》中還記載:“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皇侃注疏:“謂凡行禮及言語之儀也。質,實也。勝,多也。文,華也。言實多而文飾少則如野人,野人,鄙略大樸也。史,記書史也。史書多虛華無實,妄語欺詐,言人若爲事多飾少實,則如書史也。彬彬,文質相半也。若文與質等半,則爲會時之君子也。”(34)從這些來看,皇侃對於表裏不一,虛飾過度的僞君子是很反感的。 六朝的文論家,最反對的是虛僞造造的寫作態度。劉勰《文心雕龍·情采篇》慨嘆:“昔詩人什篇,爲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爲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馳誇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真,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采濫忽真,遠弃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制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泛詠皋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夫桃李不言而成蹊,有實存也;男子樹蘭而不芳,無其情也。夫以草木之微,依情待實;況乎文章,述志爲本,言與志反,文豈足徵?”劉勰總結了兩種文學創作態度,一種是有感而作,一種是無病呻吟。有感而作的作品自然真誠,無病呻吟則文辭淫麗煩濫,不足以道。劉勰與皇侃都是經學造詣極高的學者,但他們同爲梁代士人,在推崇經學與文學觀念的互滲互動上,可以互相印證。 南朝梁代是儒學復興的年代。經學與文學的結合,不僅對於《文心雕龍》與《詩品》等文學理論著作產生了直接的影響,而且《論語》等儒家經典對於文學觀念的構建方面,也有所滲透。皇侃的《論語義疏》融合儒道,其對於儒家經典與人生奧秘進行的闡釋,反映出南朝經學的特點,與當時的文學精神可以互證。從這一維度去開掘其對於古代文論的啓示與互通,是我們從事古代文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①唐晏:《兩漢三國學案》,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495頁。 ②《答何佟之等請修五禮詔》,嚴可均輯:《全梁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15頁。 ③《全梁文》,第100頁。 ④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472頁。 ⑤王利器:《顏氏家訓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226頁。 ⑥參見高華平校釋:《論語集解校釋》,瀋陽:遼海出版社,2011年。 ⑦《隋書·經籍志》記載:“《論語》者,孔子弟子所録。孔子既叔六經,講於洙、泗之上,門徒三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於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没,遂緝而論之。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其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魯人傳者,二十篇。齊則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宗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魯則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韋丞相節侯父子、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並名其學。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當世重之。周氏、包氏爲之章句,馬融又爲之訓。又有古《論語》,與《古文尚書》同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异,唯分《子張》爲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孔安國爲之傳。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魏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爲義說。吏部尚書何晏,又爲集解。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古《論》先無師說,梁、陳之時,唯鄭玄、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其《孔叢》、《家語》,並孔氏所傳仲尼之旨。《爾雅》諸書,解古今之意,並五經總義,附於此篇。”魏徵、令狐德棻:《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939頁。 ⑧皇侃撰,高尚榘校點:《論語義疏》,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頁。 ⑨障廣忠譯注:《淮南子》,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第103頁。 ⑩丕充著,張宗祥校注,鄭紹昌標點:《論衡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頁。 (11)同上,第3頁。 (12)伏俊璉:《人物志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2頁。 (13)《論語義疏》,第446頁。 (14)《論語義疏》,第445頁。 (15)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795頁。 (16)同上,1959年,第796頁。 (17)《論語義疏》,第1頁。 (18)同上,第127頁。 (19)蕭統編,李善注:《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397頁。 (20)《論語義疏》,第193頁。 (21)《論語義疏》,第199頁。 (22)同上,第463~464頁。 (23)《論語義疏》,第79頁。 (24)同上,第229~230頁。 (25)同上,第409頁。 (26)同上,第224頁。 (27)《論語義疏》,第524頁。 (28)同上,第6~7頁。 (29)同上,第458頁。 (30)嚴可均輯:《全三國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第483頁。 (31)同上,第516頁。 (32)《論語義疏》,第351頁。 (33)同上,第415頁。 (34)同上,第14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