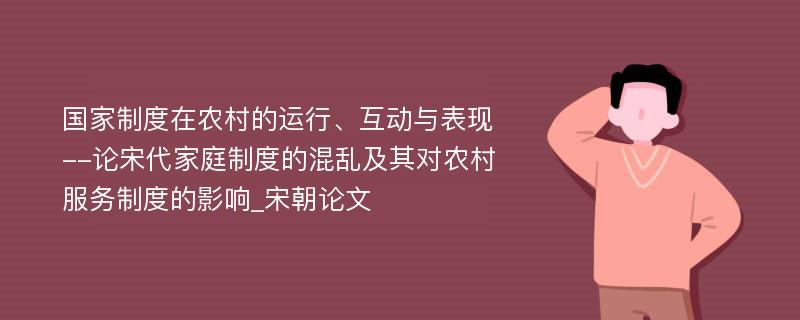
乡村中国家制度的运作、互动与绩效——试论两宋户等制的紊乱及其对乡役制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紊乱论文,其对论文,绩效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22x(2006)03-0010-11
对编户齐民的有效控制和及时征收到足额的赋税,是中国历代王朝建立正常社会秩序,确立统治的基础。建立户籍、户等制度,则是国家控制广土众民的具体形式。宋王朝沿用了北齐以来的户等制度,并有所变革。职役是宋代徭役之一,按照服役地点的不同,又分为州、县役和乡役;征税派役和治安管理、维护乡村社会秩序是乡役的主要职责。乡役差派的根据,主要依据民户户等的高低,户等簿籍又由主要的乡役人负责攒造,二者紧密相关。对于宋代户等制,中外学者均多有研究;对于户等制与乡役制的关系,学者也有所涉及①。但是,立足于历时性的角度,对两宋社会发展过程中户等制与乡役制具体实行、运作和互动,这两项乡村管理制度的最后绩效,还缺乏系统细致的探讨。对此,在学习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习作试做一补阙的努力,以期综合前贤而稍有寸进,藉以观察宋代国家制度在乡间实行的实态,并进而申述传统中国乡村社会中一些普遍性现象。
一、宋代户等、乡役制度与差充乡役的户等规定
按照居住地的不同,宋王朝将广大民户分为坊郭户和乡村户。对于乡村户,则又依据有无资产,将乡村民户分为主户和客户。② 对于主户的户等划分,除了在王安石变法时出现了短暂的细分现象外,一般说来,两宋大致沿用了五等户制。历仕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的张方平指出“本朝经国之制,县乡版籍,分户五等”③。宋人有时称第一、二等户为上户,第三等为中户,第四、五等为下户;也有时称第一、二、三等户为上户,第四、五等户为下户。“州县上户常少,中下之户常多”④;“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户少”⑤,则大致反映出两宋乡村户等实况。宋代户等制的作用极为广泛,主要涉及差役、夫役、乡兵、两税、役钱、和买、和籴、青苗、义仓、科配、购买和租佃官田、赈贷等,关涉到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⑥ 宋政府规定,五等户簿每逢闰年要重新攒造一次,由耆长、户长和乡书手合作完成。划分户第的主要依据是民户资产和人丁的多少,但以何作为评定资产的标准,各地并不一致。这正如北宋吕陶所说:“天下郡县所定板(版)籍,随其风俗,或以税钱贯佰,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钱,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⑦ 大致说来,北宋时期,北方各州县一般用家业钱,南方则多数州县用税钱。南宋时期,南方大部分州县则改用家业钱作为划分户等的标准⑧。民户资产多少不等,土地转移频繁,致使家产变动不居,户等高下自然也就难以恒定不变。
两宋期间,乡役制度前后变化很大。《宋史·食货志·役法上》载:宋初,循唐五代之旧制,在乡村中设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设耆长⑨、壮丁“逐捕盗贼”,都是轮流差派(即所谓差役)上、中等主户承担。开宝七年(974),诏令“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⑩。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四月,诏令废除里正。王安石推出的募役法(或称雇役法、免役法)和保甲法,在熙丰后期却逐渐与乡役法混同为一了。这主要表现为以都副保正、承帖人取代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以大小保长或催税甲头取代户长等负责催纳赋税。由此,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也相应地转化为乡役人。总体看来,虽然乡役制因时因地而有所差异,但是,北宋后期直至南宋时期,就大多数地区而言,或是在役名上差派原来的户长、耆长等(乡书手则于元丰前后上升为县役),或是以都副保正、大小保长、承帖人及催税甲头轮充乡役。虽期间又有元祐改制、绍述之变等反复,但是,北宋晚期和南宋时期,各地多以后者为主,名募实差是元祐之后役制的主要内容。此外,在南宋一些地方(如福建路)还有“兼差”制等(11)。
中国历代王朝大都任用家景富裕、人丁众多、富有才干的民户担任乡官里吏,藉以监控、管理乡村,征派赋役。唐代出现了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轮派乡吏的规定。宋朝虽在称谓上改为“乡村职役”,但是对于上述原则,大致未变,并规定各种乡役“以乡户等第差充”(12),要求按照民户的“物力高下,人丁多寡,歇役久近”,而“参酌定差”(13),同样延续了前代的制度精神。
对于何等民户差充何种乡役,宋代役制有着具体的规定。我们谨依据史料,对其一一对应的关系,具体加以考察。
先看充差里正、户长的户等规定。据《文献通考·职役一》记载,各种乡役自“国初”即“循旧制”,“各以乡户等第差充”。但是,由于史料残缺,自北朝以来的户等制与乡官里吏是如何一种对应关系,宋初是怎样的具体规定,以及所循旧制究竟是哪一时期的制度,已难以一一查考。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是宋太宗淳化五年(994)的诏令:“两京、诸道州府军监管内县,自今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不得冒名应役。”(14) 《宋史·食货上五》亦载此事,则将《长编》中的“自今”二字改为“始令”。后一资料表明,此后应役里正、户长的具体户等才制度化。至和二年诏废里正,户长一役则主督赋税,以第二等户充役。熙宁推行募役制时,规定应募户长役者须是第四等以上民户“有人丁物力者”;(15) 元丰八年(1085),经过一番反复更革重行募役时,户长一役仍规定以第四等以上民户应募。(16) 元祐后重新推行差役制,沿用熙宁前的制度,以第二等乡村民户轮差户长。此后,虽然乡役制屡经演变,但凡以户长催税,大致沿用这一规定。
再看关于耆长、壮丁的户等规定。据《嘉定赤城志》卷17和《淳熙三山志》卷14,耆长“以第一、第二等户差”,壮丁从属耆长“于第四、第五等差”。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乞伏矩奏云“况第一、第二等户充耆长、里正……”(17) 易言之,宋初以来一直以第一或第二等乡村主户轮差耆长,以第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按规定,只有在狭乡户少的地区,耆长方可轮差至第三等户。(18) 熙宁募役法关于充募耆长的户等规定,也可从元丰八年(1085)朝廷再次下诏恢复耆壮之法中找到依据,即允许募第三等以下民户充应。(19) 元祐之后,复更为差役制,耆长、壮丁的应役户等则一如熙宁前旧制,此后也大致沿用下来。
熙丰后期,保甲制混同于乡役制,宋政府对于充担保正、保长、甲头、承帖人等乡役的民户,亦有具体规定。熙宁三年(1070)初行保甲制时,朝廷对保正、保长的户等规定较为含混,即充任小保长须是主户中“有才干、心力者”,充任大保长须是主户中“最有心力及物力最高者”,充任保正副者须是主户中的“最有行止、心力材勇为众所伏及物力最高者”(20),并未言及具体的户等。倘若依五等户制下的民户而言,充任大保长和都副保正须是第一等户,因为只有第一等户才是“物力最高”。由此还可看出,初设保甲时,对于充任保正长者不但有资产的要求,还有对其能力的要求。保甲制应用于乡役制后,政府规定充役的户等,并非与乡役那样明确,但仍就贯穿着“以物力高下定差”(21) 的原则,并强调“在法:保正副系于都保内通选有行止、材勇,物力最高者二人充应”(22);或说“在法:差募保正长,通选物力最高人充应”(23)。南宋林季仲引述绍兴二年(1132)和四年(1134)的臣僚上奏,称他们要求轮派差役,“欲不拘甲分,总以一乡物力次第选差,非第一等[户]不得为都[保]正,非第二等不得为保长……”(24) 另据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知忠州张德远反映:川峡四路“差至第三等末人户充保正”(25)。于是,有臣僚上奏反映,如此差派,“物力不均,望依绍兴免役令,选差物力最高之人”(26)。朝廷允奏。从上引两则记载可以看出,以第三等户充任保正长是与国家制度不符的,那么,所谓的“物力最高之人”,也就只能指五等户制中的第一、第二等户。承帖人则一直以下等民户充任。
甲头之役,早在熙宁三年(1070)二月,从判大名府韩琦的奏疏中即可发现,政府强调负责散敛青苗钱的甲头,须是乡村“有物力”(27) 的第三等以上民户。熙宁七年(1074)十月,司农寺奏请以甲头主催赋税,取代户长,元祐时又改回熙宁以前旧制,复经崇宁之变,南宋时期或以甲头代户长,或以户长兼任甲头,但凡轮差甲头催税,每甲三十户(或稍少于三十户),只要家有三丁,则一般是“自高至下,依次而差”(28)。在两浙路,绍兴初规定,将资产相近的人户三十家归为一甲,以形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淳熙十六年(1189),又改行“流水甲首制”(29),即不分户等高下,依次轮差。然而,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朝廷又同意权发遣江南东路转运副使魏安行的奏章,以“甲内税高者为[甲]头催理”赋税(30)。“税高”之家,当然是指上中等户。
综上所述,大致而言,两宋政府一直贯彻着以乡村中较富裕(一般指第三等以上的主户)的民户充任里正、户长、耆长、都副保正、大小保长、甲头等乡役的制度,并凭藉这些较富裕的乡役人,来实现中央政府“以民治民”职役模式下对于乡村社会的控制和有效管理。
二、两宋户等制的混乱与实际充差乡役的民户
宋朝五等户制在实行中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南宋时期还出现了形式化的趋势,使得户等簿籍并不能准确反映民户家产变动的实况,而五等户制是摊差派役的主要依据,户等制出现弊病,也自然就影响到职役的轮差,并直接导致了乡役制的紊乱。结合已有研究,我们对此再稍加考述。
(一)两宋户等制中的弊病及其原因
两宋户等制的混乱,主要原因在于诡名挟户现象的出现,其次也与户等制自身制定的繁难以及缺乏有效的地方行政监督有关。
首先,豪强形势户的欺瞒隐漏,以及他们与当职官吏违法舞弊,致使户等制滋生弊病,一直是两宋社会中一大不能根除的痼瘤。宋朝役法规定:形势户中的官户,女户、单丁户、寺观户,与得解举人、太学生都可以免除部分赋役。宋仁宗朝后,由于国家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赋税征收中存在名目翻新,不断增益的趋势。户等高下是政府征税派役的依据,为了逃避日益沉重的赋役负担,许多豪强形势户想尽千方百计,或伪冒官户等特殊户,或隐瞒家产,降低户等,甚至改为客户,以规避赋役。史载“命官、形势户占田无限,皆得复役”,故许多“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也有民户“窜名浮图籍,号为出家”,以避差役,北宋时赵州一地就有这样的诡名者一千馀人。(31) 按照国家法制,官户也承担部分赋役,但是,显而易知,占有大量土地,拥有丰厚资产的官户是不会自愿按政府规定承担全部赋役的,他们更会凭其各种资源和优势,逃避、转嫁部分负担。宋高宗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一月,权尚书礼部侍郎辛次膺言:“有官户多立户名,编民冒作官户,及祖父母、父母在而私立别户者。”(32) 道出了一些官户以多立户头,降低户等来逃避赋役现象的存在。由于豪强形势户的干扰,导致户等簿混乱,对社会带来诸多危害,直接的危害到乡役不能公平摊派。
宋代不法民户避身于“官户”名下,逃避赋役负担的史例很多。如,北宋时期,长安有一“大姓”范伟,以其祖母冒为某官户“继室”的欺诈手段,竟“不徭役者五十年”(33)。宋神宗时期,由于“宗室租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予官”的规定,所以一些地方出现了“民争市婚为官户”的现象。对此,杜纯指出:“人赀得承务郎以上犹不为官户,盖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34)《名公书判清明集》一书记载了南宋中后期一些有关乡役案例的判决情况,其中多有官户限田免役和不法民户伪冒官户的事例。(35)
利用基层胥吏,豪强形势户在户等簿攒造过程中违法舞弊,也是导致户等制混乱的一个主要原因。宝元初,婺州浦江县“俗有幸民以赀自豪,市奸吏为期谩以避徭役”(36)。杜范曾经反映乡村的情况说:“贵家豪户所纳常赋,重赂乡吏,或指为坍江逃阁,或诡寄外县名籍,虽田连阡陌,输纳既少,役且不及。”(37) 换言之,许多形势户都是通过与基层公吏的私下交易,才得以逃避某些赋役。绍兴三年(1133)二月二十六日,提举淮南东路茶盐公事郭揖奏:“差役之法,比年以来,吏缘为奸,并不依法[以]五家相比者为一小保,却以五上户为一小保,于法数内选一名充小保长,其馀四上户尽挟在保丁内。若大保长阙,合于小保长内选差;保正副阙,合于大保长内选差。其上户挟在保丁内者,皆不著差役。”(38) 南宋陈耆卿也曾指出,户等制“—岁遇攒造,不过以往年陈籍沿袭抄转而已,升降出没既莫能详,乡胥、里豪始得株连奸伪,以为牢不可破之计。故有一户化为数十户者,有本无寸产而为富室承抱立户者,有虚为名籍以避敷敛”(39)。参与户等簿编造的保正副“私受人户钱物”,导致户等“升排不公”的现象是较普遍的。(40) 由于“隅保吏胥”的“飞走卖弄,听其自为需求”,以致出现了胥吏们“如志,则以上等之户降而为下等;贿赂不至,则以十金之产增而为百金,牒诉纷然,一不受理,遂使冤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今日聚众围保正之家,明日聚众撤户长之屋”(41),导致社会秩序混乱。
依据人丁和资产划定户等,就资产而言,有形和无形的资产是难以准确评定的。如所周知,中唐以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42),或说“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43) 的新税制的出现,即由税丁到税产的变化,对国家基层管理方式影响很大。我们知道,相比而言,税丁的方式简单而易行;履产而税,这就需要乡村税收人员在履定税额时,既要走遍所辖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核定山田、平地、水田的边边角角,勘验田亩多少、贫腴成色,又要到农户家中逐一检察各种各样的家产,以便最后计算乡户的资产总数,评定户等,征税派役。有形而易于估算的资产尚好以为凭据,但是,无形的或轻便小巧的贵重资产则不易被外人发现而列入评估对象,资产的增值部分也不易被评估。(44) 中唐入宋后,乡村赋役摊派方式主要有:按田地多寡肥瘠、人丁、乡村主户的户等、按家业钱和税钱等划分乡村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这四种方式往往重叠,又派生出多种摊派方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45) 乡役人的工作日趋繁难和复杂化了,工作量也明显增加了。
另一方面,战争的破坏也是造成户等簿混乱的原因之一。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北宋时期宋辽、宋夏、宋金邻接地区,南宋时期的两淮、湖北等宋金接壤地区,蒙(元)宋战争中遭到破坏的一些地区,以及北方大量移民南迁给社会造成的混乱。自北宋徽宗时始,南宋绍兴、嘉定、开禧等各个时段,金军不断南侵,宋民少有宁日。端平之后,蒙古铁骑大批南下,给南宋政府以毁灭性打击。兵火所过,人民死伤逃移,城乡萧条冷落。历经丧乱之后,不但政府的许多簿籍文引丢失散落,而且,乡村户等簿籍也同样遭到破坏。绍兴二十八年(1158)正月,直秘阁、湖北转运判官罗孝芬言:“湖北州县比岁残破,亡失版籍,乃有以丁增税者,每一丁受种七斗,或丁多田少,或有丁无田,概责其人,甚为民患。况奸猾之民,以隐匿而获轻免,贫懦之家,以无赀而受实害”(47),诸如此类议论,指的就是战争给户等制度带来的混乱。
州县政府的行政不作为,未能督促乡役人按时攒造、修订簿书,也是五等户簿出现混乱的原因之一。我们先看南宋庆元六年(1200)六月时一位官员的论说:
国家立法,三岁一推排,盖欲均贫富也。使占籍于乡者,富而进产则在所升,{穷}而退产则在所降,截然不紊,皆合公议,则州县之间,差役自然公平,输纳自然均一,此国家之良法也。(47)
在国家设定的理念中,户等制每隔三年攒造一次,既可以及时反映民户的家产变动,也有利于差役的公平轮派。然而,两宋都有未按时攒造户等簿的现象。王安石变法时,就有官员为多征收免役钱,而随意升降民户户等的现象,致使户等制趋于混乱。乾道元年(1165)正月,朝廷赦书云:“州县差役,自有条法指挥,往往当职官吏不躬亲检照簿籍户口,物力高下,致轮差不均。有力者夤缘幸免,下户复致频并,互有纠论,更不纠实,枝蔓追呼,淹延不决。公吏恣行诛求。”(48) 此后,这种现象还时常发生,如南宋时期“江东州县因循不举者十六年,版籍浑肴(淆),贫富易位”(49)。淳熙五年(1178)二月四日,有臣僚言及有些地方户等簿甚至“兼有十数年不曾推排处”。两年后,吏部尚书王希吕反映“远方县邑有一二十年未尝推排者”(50)。南宋晚期的王柏也指出“婺都二十年不过割矣”(51)。由此可见,因为国家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当职官吏的行政不作为,导致户等簿不能按时攒造,乡村民户的资产变动,也就不能及时准确地得到反映,由此给户等簿的攒造带来诸多弊病,从而也就影响到乡役公平的差派。
(二)两宋实际充任乡役的民户户等
在任何时代,当乡官里吏之役有油水可捞,能享受到较多的特权时,不但乡村富户,而且连一些退闲乡居、无阙甚或在职的官绅士大夫阶层(部分形势户),也想方设法承担;而一旦所谓的“职役”没有多少油水可捞,享受特权极少,尤其是负担较重时,那些乡村上户和官绅阶层等便避之惟恐不及。即便政府明令规定去充任“职役”,他们也会设法逃避或转嫁给其他民户。趋利避害,人之常情。两宋时期,也不例外。史载“乡户之役于州县者,优则久留,劳则欲速去,赂吏辄不以时代”(52)。国家的相关制度,则如北宋张方平所说,“至于五等版籍,万户之邑,大约三等以上户不满千,此旧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户不啻九千,此旧制不任差役者也”(53)。然而,由于诡名挟户等诸因素,实际充任乡役的乡户与宋国家制度的规定之间,有着一定的差距。文献中所见“下户半曾差作役”(54),“差徭例及于贫民”(55),“官吏贪浊,差募之际,富者以贿赂幸免,贫者以诛求受害”(56) 的现象,虽难免有夸饰的成分,但也恐非一时一地偶尔有之。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分别从各个色役入手,逐一考察,再作阐述。
北宋前期,里正、户长和乡书手一起督催赋税,享有较多的职权,故应役民户都乐于承担。里正先是主催赋税,并参与县司中的差派徭役,“号为脂膏”(57)。天禧前后,里正则只是用来准备应差重难衙前,充差民户不胜其苦。宋代役制规定,里正“用第一等户”,而在陕西路“乡狭户少者至差第三等充”(58)。在河东路“却差下等义勇人户充州县重难里正或衙前等差役”,甚至“往往将第三、第四等人差充第一等色役,亦有主户小(少)处,差稍有家活客户充役勾当”(59)。在朝臣的纷纷反对下,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朝廷终于下诏废里正衙前之役,作为乡役之一的里正也随之废除。
耆长、壮丁“逐捕盗贼”,主管乡村治安,北宋时也曾被视为“轻役”(60)。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开封畿县试行的募役法规定:“耆长于第一、第二等户轮充,一年一替……如本村上等人户数少,即更于第三等内以上轮充。”(61) 元丰八年(1085),诏令耆长以第三等以上户应募,同时又有“如元充保正、户长、保丁,愿不妨本保应募者听”的规定。李焘在此条记事下注云:“按此时保甲固在,保正长亦未尝废。”(62) 换言之,在保甲正长等与户长、耆长等并存的情况下,朝廷允许原来充差保正者应募耆长。然而这种所谓的应募,其中弊端很多。王岩叟在元祐元年(1086)正月时的一份奏疏中指出:“近日指挥许雇募户长,其耆长须得雇第三等以上人户,则朝廷知浮浪之人实不愿于受雇也;不愿则必阳为雇名而阴用差法,此郡县必然之理也。谓之为差则与雇钱,谓之为雇则用差法,臣以谓不若明为差法之为便也。况三等以下自当为耆长,耆长又无所陪(赔)费,枉于下户敛钱以与之。”(63) 随后又恢复为轮差法。(64)
南宋大体沿用元丰八年和元祐元年的差役制,应差充任保正者,按规定依然是通选乡民中家赀丰厚、人丁较多且有一定能力者,然在实际推行中却出现以下各种情况:其一“州县差募之际,不体照法意,致上户百端规避,却令中下户差役频并”(65)。究竟是哪些人从中违法舞弊呢?是“当职官不切究心,乡司与役案人吏通同作弊,故意越等先差不合着役之人,致令纠论,乘时乞觅,百端搔扰,方始改差实合着役之人”(66),“致保正之役多及下户”(67)。其二,两宋之际的士大夫杨时认为,即使朝廷役法规定耆长要募雇民户承担,但“岂有上户肯利若干钱而愿役于官乎?上户不愿,则其势须至强使为之,是名募而实差也”(68)。豪强上户便转嫁差役给中下民户,实际充差服役的却是乡村贫乏下户。王曾瑜先生曾对宋代官户与乡村上户的诡名挟户现象进行了研究,其中就包括这些逃避、转嫁赋役负担的方式,此不赘述。(69)
再看户长、保长和甲头的轮差与户等的对应。宋初役制规定,户长以第二等民户充任,严禁“冒名应役”(70)。北宋前期户长主督赋税,还负责编造户等簿等,有一些职权。熙宁二年(1069)推行募役法,则规定户长募民户充任,至元丰八年(1085)时则明令以“第四等以上民户应募”(71)。此后,户长或募或废,或以保长、甲头代之。南宋庆元五年(1199)二月,时任右谏议大夫兼侍讲的张奎言:由于诡名挟户之弊,致使“为户长者,率是五等贫乏小民”,这些充役的贫民下户“卖产陪(赔)偿,卖产不足,则有逃徙而去尔”(72),显现出户等不实导致了户长轮差不公。
关于承担保正长等乡役者的户等规定,如绍兴五年(1135)金安节所说:都保正副“若依法选差,自不及下户”(73)。绍兴二十六年(1156)十二月,朝廷诏书再次重申:“诸县保正长并将上户斟酌定差,下户止轮充太(大)保长。”(74) 但此后乃至南宋,却出现了许多诸如“诸县纵容案吏、乡司受上户计嘱,抑勒贫乏之家充催税保长”(75) 的现象。这些“贫乏之家”,“率是四等、五等下户”,由于乡村“多有豪右、官户倚势不输”赋税。面对县司紧迫催逼,充任催税保长的贫下民户被迫代替缴纳,长此以往,保长的困苦可想而知,乃至有“鞭笞责挞,至有缘此鬻产陪(赔)纳破家”(76) 者。绍兴三十一年(1161)九月,知忠州张德远言:在川峡四路,差派逐都保正不仅未曾遵行绍圣、绍兴的免役令,而且“妄引未行免役之前”的皇祐敕条,“次第轮流,差至第三等末人户充保正”,“致保正之役多及下户”。他还指出,“都保内家业物力有及一万贯者,歇役或致二十年不差,却差至第三等家业三百贯文人户”。对于这种种与朝廷役法大段背离的现象,他感叹:“贫富相远,力役何由均平?”(77) 宋宁宗时的一道南郊赦书称:“诸县所差保长催税,率是四等五等下户。往往乡村多有豪右、官户倚势不输”(78),使得充任保长的乡村下户代其赔纳,甚至于因此倾家荡产。上面已述,根据宋代役法规定,都副保正、大保长“二者必以物力之高,人丁之多者为之”。然而“法久而弊,人伪日滋”,以致出现了——
富而与贫为伍,预知差役之必至也,乃赂乡佐,求于富者为伍焉!于是,富与富为伍,物力虽钜万而幸免;贫与贫为伍,物力虽数千而必差,盖由猾胥造弊于排甲之初,致使下户受弊,于被差之后,征求之频,追呼之扰,以身则鞭捶而无全肤,以家则破荡而无馀产,思所以脱此者,而不可得时,则有老母在堂,抑令出嫁者;兄弟服阙,不敢同居者,指己生之子为他人之子者,寄本户之产为他户之产者,或尽室逃移,或全户典卖,或强逼子弟出为僧道,或毁伤肢体规为废疾。习俗至此,何止可为恸哭而已哉!(79)
乾道八年(1172)八月,有臣僚奏陈:充任保正等差役者“率中下之户”(80)。绍熙二年(1191)八月,太常少卿张叔椿指出:“差役之法,以物力高下定为流水通差立法……保正副之数少,则上中户为之而有馀,保长之数多,则中下户为之而不足,州县之间始以保正副之歇役者俾充保长,不理役次,固有朝解保长之役,而暮受保正之帖者,而上中户俱受其困矣。”(81) 屡有臣僚的奏疏,朝廷也多有敕书行下,那么,这样看来,南宋统治者明确知道,在乡役的差派过程中因户等不实出现了诸多弊病。
要而言之,由于各种原因,两宋以户等高下而轮差乡役的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较大的差异。而这些制度内外的漏洞所带来的苦难,无疑大都由中下民户,甚而部分客户承担。由于户等簿的混乱,依据五等户簿所差派的役法,也就不能以实定差,宋政府依靠富足上户控制乡村的制度,其实际推行的效果,就不能不受到影响。这种情况主要表现为,在所差派的民户中,以中下等户充任上等户应担差役的情况为多,即“中下之产,役次频并”(82)。此外,还有许多士大夫都指出了差役推行过程中的不均现象。绍兴三十一年(1161)二月,又有臣僚在奏疏中说:“近因宣州一乡上户绝少,下户极多,守臣奏请,本欲不候歇役六年即再差上户。有司看详,误将歇役六年旨挥便行冲改,遂致上户却称朝廷改法,是以鼠尾流水差役,必欲差遍白脚,始肯再充;当差之际,纷纭争讼,下户畏避,多致流徙。盖上户税钱有与下户相去百十倍者,必俟差遍下户,则富家经隔数十年方再执役”(83)。
上面引述不同时间段的史料都说明了同一问题,那就是,在实际的乡役差派过程中,许多上户并不充役,中下等民户频并在役的现象在两宋时期是普遍存在的。乡村社会的诸多事务必须按时完成,以保证整个政府的财政开支和乡村社会的稳定,然而,贫乏下户又实在无力完成,执政者无可奈何,只好“更改”(新酒旧瓶)役制,再重新以另一种役名轮差乡户充任乡役。绍兴十三年(1143)十月,广西路提刑兼提举常平司言:轮差甲头“自高至下,依次而差,至今已经七年。每甲共差过一十四户,今已轮至下户。如一甲内不下三五户系逃移,壹半系贫乏,设若轮差甲头尽是上户之家,壮丁佃客委是催科不行,若再差上户,即又不免词诉。今来若复用户长,实为利便”。朝廷允之(84)。就是说的这一情况。
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国家的乡役制度在乡村实际执行中,虽然多有中下等民户充当乡役的史料,显而易见,这是一种非常态的社会现象;但是,相当多的资料也显示出上、中等民户在充差职役,还有豪强形势户隐身其中,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实际上充当着这样或那样的职役,抑或其他社会精英,在乡村中起着中下等民户所不能起到的社会控制作用。历史上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或非现有文献所能一一毕现;依据现有资料,下户、上中户哪个群体充役者较多,也是无法准确判断的。以此而言,前人所论,宋朝职役究竟是否能够一言以蔽之,是地主阶级当权派的职权,是富豪民户侵剥贫民的制度的说法,是值得再行斟酌的。
由上述可见,户等制需要里正等主要乡役人负责攒造,而乡役的轮差又是依据户等的高下,二者紧密相关。乡役制本身前后变革不一,乡役人和县司公吏的营私舞弊,导致了户等的不实;随着户等制的紊乱,乡役就难以依据民户资产的实际而据实轮差。这两者的互动关系,是显而易见的。
三、相关思考
近年来,有关中国历史上基层社会问题的研究日益深入,而对于古代国家制度在实行过程中与制度本身的差距,以及如何正确审视历史上的制度运作等问题,均引起学者们极大的兴致,并已取得可喜的成果(85)。那么,如何审视传统社会中国家制度在基层乡村中的实行,考察距离中央政府较遥远的乡村是怎样执行国家制度的,制度与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和实际绩效如何;国家借助于怎样的一个管理体系,从而达到既节省管理广土众民的政治和经济资源(治理成本),又能对于编户齐民相对有效控制;承担着向国家完税纳粮义务的民户,在上述制度的约束和管辖之下,有无能力、会不会、又是怎样与政府互动等等,并对这些问题加以研究,似可更加深入地透视中国传统社会的某些普遍性特点,抑或可为今日乡村治理的借鉴。
进而言之,国家制定户等制和乡役制的目的在于,掌控民户的贫富变化情况,征收赋税,并藉以维护社会秩序。这是国家制度制订者的理念所在。但是,由于国家过于强调赋税征收和治安管理的重要性,对已经推出的制度缺乏有效地约束机制;社会变化之后,一些制度本应因时制宜作相应改动,而国家却一味强调制度产生的最后绩效(民户按时足额地完税纳粮,以应对中央和地方日渐困窘的财政收支;面对内外交困的国势,强化地方治安管理,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安定),而忽视了顺时应变,所以,我们发现,这些有关乡村治理的制度在实行之中,不但制度自身紊乱(并有国家制度地域化的现象),而且,随着一种制度的紊乱及其效用的减弱,另一种制度也相应受到影响,也随而变动和紊乱,甚至难以继续推行下去,更难以达到制度制定者最初的治理理念和效果。再者,由于传统中国强国家、弱社会的传统根深蒂固,基层社会根本不具有与国家平等对话的资格和能力,地方乡族势力在实行国家制度时,发现问题却不能得到国家的认可而适时应变。为了一地或一己私利,就只好采取各种方法,将国家的制度加以变通。久而久之,即便原本良好的制度也会成为空文。
通过上面的考察,我们发现,宋中央政府对于基层乡村的管理、控制是松弛的,国家权力渗透乡村的力度虽较前代或有所加强,但还是有限的。原因何在?浅陋认知有以下内容:
一、国家治理乡村的成本太高。特别是两宋国家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窘境,中央政府根本不具备直接管理广土众民的能力。甚至为了应对国家财政,还不断剥夺作为其“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既得利益——王安石变法时,原用于支付役人报酬的免役钱,北宋末到南宋一直照征不误。然而,募役其名,差役其实的役制下,却并不支付乡役人任何薪水。国家为了控制乡村,不得不采取以民治民的办法,以地方胥吏、部分形势户、家族、宗族等乡族势力、乡村能人作为国家和乡村社会的中间层,利用他们在乡间的社会网络和各种资源,起到填补县乡之间“权力空隙”的目的。但是,乡族势力是融合有地缘性和血缘性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作为国家政权(公)的“神经末梢”而出现在普通民众面前的;而另一方面,他们同时还是地方上“私”的利益的代表者,为了自己的私利和乡土亲邻的利益,而与官方做着这样或那样融通的事情(86)。魏晋以来的世卿世禄传承,隋唐时逐渐被打破,而以科举取代;中唐以降,土地转移频仍,贫富、贵贱转化也较之前代更显迅猛。读书应举者多,中举入仕兼有实阙者少,所以,许多士人乡族既感受到社会中向上发展的空间,又有向下流动的强烈压力。社会流动的加速,也就使得这一社会群体更加自觉地关注自身命运,关注与自家发展密切相连的地方社会事务。(87) 在乡民心目中,兼有豪横和长者两者或更多的立体形象,是他们在社会中实有的常态。(88)
二、国家之于控制乡村的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兼而国家大政是以防弊之政,为立国之法,却在许多方面矫枉过正(89),导致地方行政管理机能的不足——行政官员相对有限,难以处理辖区内广土众民的诸多事务;避籍制和迁转法又往往使得他们多不熟悉地方实情,一旦稍微熟悉后,却面临着调转岗位甚至无阙休闲。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行政对于乡村的管理,也不得不主要依靠乡族势力。故而,宋代乡族势力在乡间的影响力呈现出上升趋势,在诸多事务上左右着地方行政和基层社会,其上下交融的实际状况,又使得他们更多为自家和地方利益着想(90)。
中唐以降至于两宋,国家权力下移乡村的努力一直不减,特别是保甲法的推行及其与乡役制的混同为一,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国家权威渗透乡村的力度。我们认为,在宋代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都极端窘困的情况下,国家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为数众多的乡役人的报酬。财力不足,也是天水一朝极力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的动因所在——加大赋税征收的力度,将乡民牢固控制起来。但是,这一渗透也是有限度的。我们认为,在宋代,处于县、乡衔接点上的乡村职役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效用,一如投石于静水后产生的涟漪,距离投石落水点越远,涟漪也就越加微弱。由于乡村距离中央政府过于遥远,国家政权的权威在此产生的力量也就越是微弱,基层也就越是容易改变国家的法令和制度。(91) 帝制政权凭藉乡族势力等将国家权威完全渗透乡间的治理理念,并不能达到其理想的控制效果。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中国学者的研究回顾,请参见刁培俊《当代中国学者关于宋朝职役制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原载《汉学研究通讯》总第87期,增订后转载中国宋史研究会主办《宋史研究通讯》2004年第1期。宋晞先生《宋代役法与户等的关系》(原载《华冈文科学报》第12期,1980年,今据台湾宋史座谈会编《宋史研究集》第13辑,台北:国立编译馆1980年),黄繁光先生《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80年。承蒙黄教授惠赠大作,谨此鸣谢),日本学者柳田节子教授《宋元乡村制的研究》(尤其是第一、第三编诸文,东京:创文社1986年)等论著,也都涉及到这一问题。但统观上述诸作,户等与乡役一一对应的研究,尚显薄弱;其间的社会内涵,亦鲜有论及。
②《嘉靖惠安县志》卷6《户口》:“宋太平兴国初立县时,版籍仍伪闽及留陈之旧。至道元年,始造户口版籍,至元丰八年,又分主、客户,以丁力多寡科差,兼论资产,遂为一代之制。”(《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初编,上海书店1981年影印本)。直至元丰时期,主、客始得两分,究竟是惠安一地之事,抑或是全境如此,我们倾向于后者。前人或过于坚信这则史料,恐非。
③张方平:《乐全先生文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并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版(本文首次标注版本,如无特殊标注,后出同于首次列出者)。
④刘挚:《忠肃集》卷5《论役法疏》,中华书局2002年点校本。
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新版)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丑载宋神宗语,又见卷313,元丰四年六月己巳。梁太济先生认为,五等下户在宋代主户中所占比例,一般为60—70%,局部地区高达80%以上,见其《五等下户的经济地位和所占比例》,载《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⑥参见王曾瑜先生《从北朝的九等户到宋朝的五等户》,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2期。
⑦《宋会要辑稿》(下简称《宋会要》)食货13之24,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
⑧参见王曾瑜先生《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载《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并梁太济先生《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载《宋辽金史论丛》第二辑,中华书局1991年。
⑨《五代会要》卷25《团貌》条载:“周显德五年十月诏:‘诸道州府令团并乡村,大率以百户为一团,选三大户为耆长,凡民家之有奸盗者,三大户察之;民田之有耗登者,三大户均之。仍每及三载,即一如是。’”今按:当时及宋初三大户确实是由乡村中资产较多的民户三家承担,参见《程子遗书》卷21上:“程子过成都,时转运判官韩宗道议减役,至三大户亦减一人焉,子曰:‘只闻有三大户,不闻两也。’宗道曰:‘三亦可,两亦可。三之名不从天降地出也。’子曰:‘乃从天降地出也。古者朝有三公,国有三老。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三人行则必得我师焉。若止二大户,则一人以为是,一人以为非,何从而决?三则从二人之言矣。虽然近年诸县有使之分治者,亦失此意也。’”由此可知,三大户即由乡户中较富有的三家承担耆长之职。
⑩《宋会要》职官48之25。
(11)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17《吏役门》,中华书局1990年“宋元方志丛刊”影印本;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转对论役法札子》,四部丛刊初编本。有关“兼差制”,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35《与闽帅梁丞相论耆长壮丁事》、真德秀《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29《福建罢差保长条令本末序》有明确揭示。并参Brian E.Mcknight(马伯良)所著Village and Bureaucracy in Southern Sung China(《中国南宋乡村职役》,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之第4章。另外,如刘克庄所说:“今天下皆行熙丰条贯,独海外四州犹用元祐之旧,民亦便之。”(《后村先生大全文集》卷100《安溪县义役规约》,四部丛刊初编本。海外四州为琼州、万安、昌化、朱崖军,又见《宋会要辑稿》食货65之24)。勾勒上述役法变化的论著,主要有前揭黄繁光先生《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先师漆侠先生《宋代经济史》(第11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
(1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2《职役一》,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
(13)《宋会要》食货66之75。
(14)《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戊辰。其实早在建隆初年,程能奏疏中已经显现出富者当役,贫者免役的役法精神,见《宋史》卷177《食货上五》,中华书局1985年点校本;《长编》卷21也载有此事。梁太济先生认为,两宋史籍中明确记载按五等户制科派差役,是在乾兴元年十二月,参其《两宋的户等划分》,《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5)《止斋先生文集》卷2《转对论役法札子》。另《宋史》卷177《食货上五》载耆户长等须募三等以上户。
(16)《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
(17)《长编》卷73。
(18)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转对论役法札子》。
(19)《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申,又见卷364,元祐元年正月王岩叟言。
(20)《长编》卷218;《宋会要》兵2之5引司农寺《畿县保甲条制》。
(21)《宋会要》食货65之86载绍兴十六年十一月南郊赦。
(22)《宋会要》食货66之82。
(23)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简称《系年要录》)卷189,绍兴三十年三月庚子户部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简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6年。
(24)林季仲:《竹轩杂著》卷3《论役法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宋会要》食货66之84。
(26)《系年要录》卷192,绍兴三一年九月癸巳。
(27)《宋会要》食货4之19。
(28)《宋会要》食货65之85。
(29)《宋会要》食货65之82至83,66之76,14之37;《嘉定赤城志》卷17《吏役门》。
(30)《宋会要》食货65之92,66之83。
(31)《宋史》卷177《食货上五》。
(32)《宋会要》食货66之81。
(33)《三朝名臣言行录》4之4《集贤学士刘公(刘敞)》,四部丛刊本。
(34)晁补之:《鸡肋集》卷62《朝散郎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杜公(杜纯)行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3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赋役门》,中华书局1987年版2002年新印本;请参阅黄繁光先生《南宋中晚期的役法实况——以〈名公书判清明集〉为考察中心》,《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并前揭梁太济先生《两宋的户等划分》。
(36)邹浩:《道乡集》卷34《杨都曹(处厚)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7)杜范:《杜清献集》卷8《便民五事奏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8)《宋会要》食货14之20,65之78至79同。
(39)陈耆卿:《簧窗集》卷4《奏请正簿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0)《宋会要》食货11之21。
(41)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12《申将前知建康府溧阳县尉王棠镌降事》(嘉定八年九月),四部丛刊本。
(42)刘昫:《旧唐书》卷118《杨炎传》;同书卷48《食货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421、2093页。
(43)陆贽:《陆宣公翰苑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四部丛刊初编本。
(44)参看陈明光先生《汉唐之际的国家权力、乡族势力与“据资定税”》,原载《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三卷,中华书局2001年版,今据师著《汉唐财政史论》,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92页。
(45)《陆宣公翰苑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第一条《论两税之弊须有釐革》:“……曾不悟资产之中,事情不一。有藏于襟怀囊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有积于场圃囤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已大致反映出两税法之后计算民户资产、评定户等的繁难。类似论说,宋人尤多。参前揭梁太济先生《宋代家业钱的估算内容及其演变》。另参阅前揭王曾瑜先生《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并《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载《晋阳学刊》1987年第1期。
(46)《系年要录》卷179。这类记载很多,恕不一一。
(47)《宋会要》食货70之100。
(48)《宋会要》食货14之40。
(49)真德秀:《真文忠公文集》卷12《申将前知建康府溧阳县尉王棠镌降事》。
(50)《宋会要》食货70之73,69之31。
(51)王柏:《王鲁斋集》卷17《答季伯韶》,四部丛刊本。
(52)《长编》卷197,嘉祐七年十一月辛未。
(53)张方平:《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
(54)《李觏集》卷37《往山舍道中作》,中华书局1981年点校本。
(55)李光:《庄简集》卷12《应诏论盗贼事宜状》,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6)《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朝廷诏书。
(57)韩琦:《安阳集》卷13《家传》,《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58)文彦博:《潞公文集》卷17《奏里正衙前事》(至和二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9)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15《河东奉使奏草》卷上《义勇指挥使代贫民差役奏状》,四部丛刊初编本。
(60)《宋会要》食货65之6,杨绘奏称。而沈括根据他在两浙路的见闻,却认为耆长是“州县重役”,见《宋会要》食货65之17。
(61)陈傅良:《止斋先生文集》卷2《转对论役法札子》。
(62)《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戌。
(63)《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64)《宋会要》食货13之24载元祐元年四月二十八日吕陶疏论成都府路之时,曾说:“天下郡县所定板籍,随其风俗……就其五等而言,颇有不均。……亦为第一等中差耆长,则税钱一贯与十贯者并须二年一替。是贫者常迫急,富者常侥幸。”事又见《长编》卷376。
(65)《宋会要》食货66之79,李若谷言。
(66)《宋会要》食货65之86,南郊赦。
(67)《宋会要》食货66之83至84,张德忠言。
(68)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3,四部丛刊续编本。
(69)参见王曾瑜先生《宋朝的诡名挟户》,载《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4—5期。
(70)《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戊辰。
(71)《长编》卷360,元丰八年十月丙申。
(72)《宋会要》食货66之28。
(73)《系年要录》卷179。
(74)《系年要录》卷175。
(75)《宋会要》食货66之24。
(76)《宋会要》食货66之31。
(77)《宋会要》食货65之93。
(78)《宋会要》食货70之106。
(79)林季仲:《竹轩杂著》卷3《论役法状》,此绍兴五年四月间事;又见《系年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己未记事。
(80)《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51《孝宗皇帝十一》,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宋会要》食货65之95至96大致同。
(81)《宋会要》食货66之26。
(82)《宋会要》食货66之83。
(83)洪适:《盘洲文集》卷41《论人户差役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会要》食货65之93。
(84)《宋会要》食货65之85。
(85)近年宋史研究中,以包伟民先生《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和邓小南师《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载《浙江学刊》2003年第3期)及其相关的研究为代表。杨宇勋博士《取民与养民:南宋的财政收支与官民互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专刊之三十一,2003年。承蒙作者惠赠大作,谨此鸣谢),陈雯怡博士《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等,都是富有创新意义的论著。
(86)参见傅衣凌先生《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
(87)参阅李弘祺先生《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中译本,第234-263页;其中,和下文中的韩明诗一样,他也有这些乡族势力地方化的论断。邓小南师《“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宋》,参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238页,第261-263页。
(88)参阅梁庚尧先生《豪横与长者:南宋官户与士人居乡的两种形象》,载《新史学》第四卷第四期,1993年12月。刁培俊《宋代的富民与乡村治理》,节略载《河北学刊》2005年第2期。
(89)参阅邓广铭先生《北宋的募兵制度及其与当时积贫积弱和农业生产的关系》,载《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90)学者研究认为,北宋中期以后,尤其是南宋时期,士大夫已开始越来越多地经营与自己利益密切联系的地方事务了。参见[美]Robert P.Hymes(韩明诗).Statesmen and gentlemen,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si,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官宦与士绅:两宋江西抚州的地方精英》,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但是,是否南宋较之北宋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尚难令人认同。当考虑文献存世状况等诸多综合性因素。近年来,两岸宋史学界对于地方家族的研究中,也多有乡族势力经营地方事务的事例。可见梁庚尧先生《家族合作、社会声望与地方公益:宋元四明乡曲义田的源起与演变》,载《中国近世家族与社会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中研院史语所1998年版;《南宋的社仓》,原载《史学评论》第四期,1982年7月,今见氏著《宋代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黄宽重先生《科举、经济与家族兴衰:以宋代德兴张氏家族为例》,载《第二届宋史学术探讨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6年版,等等。
(91)参见周振鹤先生《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载《复旦学报》1993年第3—4期)。王家范先生《中国历史通论》(前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也有类似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