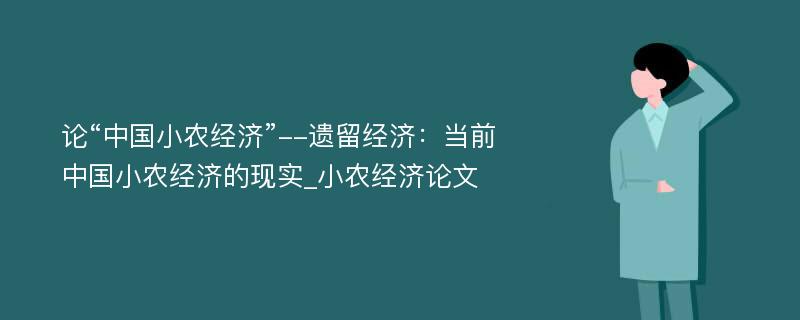
笔谈:关于“中国式小农经济”——留守经济:当前中国式小农经济的现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农经济论文,笔谈论文,现实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大量中青年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入城市谋求生计,他们或暂时或永久地离开了农村,使得农村成为了“三留守群体”(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栖息之地。同时,留守群体也成为现阶段农村经济的主要从业人员,当前的小农经济呈现出既异于经典理论表述的小农经济,又异于资本主义式农业的经营模式,而是表现为基于小农家庭的性别与代际分工而形成的妇女种田、老人农业,以及打短工、搞副业等方式的以“留守群体”为主力的经济形态。本文试图以“留守经济”来概括当前农村经济的现象。“留守经济”的形成在中国现阶段的农业与农村发展中是必然的,“留守群体”因自身的劳动力质量以及市场机会缺乏而无法实现城市化,因而留守在村庄来完成农民家庭再生产以及农村劳动力的再生产,“留守群体”属于城市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劳动力,但却是农村经济中的主力,“留守群体”颇具创造力和主动性地发展出多种农村经济方式,支撑着农村经济的稳定性。“留守经济”构成了当前中国经济二元结构的重要维度,为中国经济转型塑造了“蓄水池”和“稳定器”的功能,这也使得中国农业发展道路以及城镇化模式呈现出异于西方经典理论所预言的形态,是中国式小农经济的“特色模式”。
一、“留守经济”的概念释义
“留守经济”是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经济的形态与特征的总汇。中国的转型包含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等过程,共同的内涵是将农业劳动力转化为工商业劳动力,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农村经济实现资本化与规模化。然而现实却是,虽然农村外出劳动人口由20世纪80年代的不足200万人发展到2012年的2.6亿人①(相当于全部农业人口的四分之一),但在农村却普遍出现了“留守群体”,妇女、老人和儿童则由于各种客观或主观因素滞留农村,无法进入城市非农行业从事高工资收入。
农村在社会层面表现为“留守群体”,在经济上表现为“留守经济”。留守群体虽被称为辅助(或边缘)劳动力,但却能充分利用农村资源开展多样经营、创新农业种植模式、开拓家庭生计来源,使得农村主要劳动力流出后农村经济不至凋敝,反而为家庭生计作出重要贡献。农户的劳动力在城镇化过程中自动进行了重组,由留守人群来承担农村种田任务和幼年劳动力的教养、老年人的赡养和照料,中青壮年劳动力进城打工获得较高货币化收入,两者共同相互扶持支撑一个完整家庭的生活所需和家庭的再生产。
二、留守经济的多种形态
从最简单的含义上看,“留守经济”的突出特征表现为从业者主体属于“留守群体”。农村主要劳动力流出后,妇女种田、老人农业、中农经营等形态成为主粮种植中的主要模式,有的在耕作之外开展特色种植或养殖,部分劳动力尚强的老人与妇女,寻找机会“找零活”赚钱,农忙种田,闲时在乡镇打短工;甚或是从事家庭化作业的手工加工。“留守群体”在城镇经济中或可被称为边缘劳动力,但在农村经济中却成为绝对主力。
从农业经营上看,当前“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家庭经营形态仍长久存在,农民家庭劳动力的配置维系了贺雪峰描述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老人农业”是指年轻子女外出打工,留守在家的父母的务农活动;“妇女农业”则是以基于市场要素配置的性别分工而形成的丈夫外出从事工商行业,妻子在家务农,照顾老人、小孩,承担家务劳动。这是中西部的主粮种植结构地区的“留守经济”的主要模式。妇女农业仍是延续传统的性别分工所演化形成的“男工女耕”,“老人农业”则是基于中国传统的代际伦理所贯穿的“父代相传,子孙相连”的家庭再生产而实现的。中国这种独特的代际伦理和代际交换模式使得当前的农村家庭普遍呈现年轻人外出打工,老人种田带孙子的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形态。
除此之外,我们常在村庄看到多个兄弟的家庭,只留守一个在家种田。笔者在繁昌调研时发现每个家族几乎都有一户在家种田,或者是种兄弟、堂兄弟的田,或者是老人种儿子或者侄子的田。无论是父代子耕型抑或是兄弟代耕型,这些“家族留守成员”成为村庄的主要务农群体。与家族留守成员相类似的便是中农群体,他们也是耕种亲邻好友的农地获得规模效益而成为村庄的活力阶层,更重要的是他们也是村庄公益活动的主要群体。
农村中青年劳动力的大量外出,会使得留守在家的成员根据家庭收入和劳动力状况调整生计结构,发展一些特色种植或养殖。农民在自家的承包地里除了种植主粮作物之外,还会依据市场发展特色经济活动。例如在陕西安康形成的桑蚕模式。农民除了种植口粮田的水稻之外,多数用来种植桑树养蚕获取副业收入。在江西安远,农民除了种植水稻之外,也会发展脐橙。在河北易县,小麦种植大面积缩减,农民转向高价值的核桃和柿子。依据家庭劳动力和市场行情,调整生产结构,发展部分特色种植获取高额的货币化收入也是“留守经济”的重要形态。
生活在郊区或有乡村工业的村庄,乡村初级工厂的低工资对于青壮年劳动力是没有吸引力的,多数从业者是没有市场机会的中老年群体。在湖北黄冈调查时,村里附近的粮食加工厂、炼油厂和塑胶厂80%的工人都是五六十岁的老年妇女和男性劳动力。他们会种植口粮和蔬菜。由于农业固有的季节特性和时间的弹性,农作周期使得工厂作业时间会有农闲和农忙之分,勤劳的老人早起在自家田里忙2个小时,8点到油厂去上班,下午4点下班后,再在农田劳动2小时,既照顾了自家的农田,又不耽误雇工收入。“留守群体”会以农业为基础,自由配置其他类型的劳动和经济活动,他们会跨越农业,从事多种劳动,包括到规模化农场中雇工、从事家庭副业等,合理安排自己的农闲。在江西安远看到,留守妇女和儿童在家为工厂加工计件产品,农闲时间或是假期时间,他们会大量地接手灯泡厂的灯泡加工,根据计件数量获取额外收入。小城镇的房地产开发也使得村里的五六十岁的“小老人”有机会在本地及附近工地上做小工。近几年来,在农村调查的一个直接的感受便是,虽然都是“留守群体”,但每一个人都很忙,不再有以往的农闲、农忙之分,每一个人都会在农村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活计。
这些多种类型、多样内容的农村经济形态已经超出了“小农经济”的原有概念,具有“非正规”经济的内涵,也因其繁杂性而无法被纳入现有的分析概念。本文从从业者特征的角度,用“留守经济”来概括当前农村经济的复杂内容,可以看到,“留守经济”是农村留守群体自主实践、辛勤创造的产物,是农村转型时期不可忽视的客观现实。
三、留守经济的形成机制
(1)城镇化的阶段性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吸纳了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城镇化的质量仍处于低级阶段,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都未能全部稳定地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生活,务工仍然无法给他们提供稳定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如此庞大的青壮年劳动力尚且无法稳定的留在城市,更遑论近9亿的庞大农村人口如何在短时间内转移到城市。城镇化的阶段性特点使得大量的“留守群体”仍将需要长期生活在农村,依靠在农村劳动来维持生计,支撑家庭再生产。
(2)中国特有的地权制度和城乡二元制。中国式小农经济建立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足十亩”且地块分散的农地结构上,当今的货币化压力不断增强,农民仅仅依靠农田种植根本无法满足家庭消费,更别谈完成家庭再生产。进城务工群体因城乡二元分治的历史传统和制度障碍无法获得如城市工人一样的工资,在远低于城市工人工资的同时,他们还面临着随时可能发生的失业,高度不稳定性和低度安全感使得他们必须安排家庭成员留守农村。恰恰中国的地权设置为他们的回乡作了必要的缓冲,因而“留守群体”在村庄探索了多样化、多种内容的经营方式,使得外出者在回乡—进城间能够来去自如,在流动—留守的生活中过得紧张而又从容。
(3)家庭内部的性别与代际分工。如今小农家庭为了主动适应其生存环境的变化,就需要使家庭资源要素追随市场的货币化价格进行调配和重新安排,其结果就是自发形成的家庭内性别分工,形成了农业女性化,没有市场机会的中老年人父母在家种地导致了老人农业,具有市场优势的中青年劳动力则外出打工。农村家庭的打工和务农的“两手抓”,共同目标是为了增加全家收入和提高家庭福利。农民家庭也并非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存型目标,现阶段的农村家庭均是为了追求自我积累的发展型目标,即俗话“日子过得比过去好”。在外出打工过程中,面对超时的工作、歧视性的眼光、远低于城市工人的工资,他们也能够坚持、忍耐,因为他们的参照点是自己家的历史状况,与自己家过去相比,而不是和城里人相比。留守在家的劳动成员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最大化地开发劳动能力和劳动潜力,不辞辛劳,最大化地赚取货币收入。
(4)劳动力的自我剥削。“留守经济”成为可能的关键机制是,被称为辅助、边缘劳动力的留守群体广泛寻找、从事各种劳动机会,增加劳动强度,这体现了农村留守群体的“自我剥削”机制,货币化的压力使得小农家庭只有最大程度地自我开发劳动潜力,才能扩展生计源。上述笔者所列出的诸种留守经济的形态都彰显了农民劳动过程中的自我剥削。笔者在农村调查中,据村里的老人自己估算,在当今机械化和轻简便农业技术的推广下,使得农村老人的劳动时间延长了3.5年,甚至10年。除此之外,农民的农闲时间也被多种生计活动所占据,他们无论是在主动还是被动的情况下均安排了他们休闲时间的劳作活动。正因为是他们的不辞劳苦,探索出各种各样的生计类型,才使得留守经济和打工经济一起支撑了农村家庭的生计稳定。
四、留守经济与中国小农经济的现实
虽然近几年来,在政府的鼓励和推动下,中国的农业道路也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农业产业化在逐步加速,用资本积累推动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但是在诸多的农村调查发现,农业企业化经营或是大规模的农场经营均以亏损或失败而告终。据宏观数据分析,企业公司和雇工经营的大家庭农场今天仅占到全部农业劳动投入的3%,小家庭农场则占到将近97%②。根本原因则是小农家庭农场的强韧的竞争力。无论是过去的农业+副业,还是今天的非农业+农业组合,都展示出规模化雇工农场所不具备的竞争力。小农家庭能够同时依赖两种收入(务农和打工)自我维持,依靠代际分工所形成的半工半耕模式③来支撑其家庭生产。小农家庭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形成的打工+留守的运作模式具有先天的优势,也是长期的客观现实。无论是从城镇化的阶段性特点以及农民在城市所从事的非正规行业的不稳定性和低收入来看,留守经济都将是中国式小农经济当前重要的社会现实。
“留守经济”的生成具有客观性,无法实现城镇化的农村留守群体在当今的货币化压力生活中需要为家庭寻找更多生计来源,当前的农地结构为“留守经济”提供了基础,城镇化带来的就业机会为留守群体提供了部分劳动空间,农户的创造性劳动为“留守经济”提供了可能。在当前城镇化的阶段中,“留守经济”不仅具有合理性,而且为中国式城镇化发展模式长期作出了隐性贡献,对中国农村经济与社会稳定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小农家庭用自主创造力和生存智慧为中国小农经济制造了韧性,“留守经济”成为小农经济的阶段性现实,也将伴随着在城镇化的未完进程而长期存在。
注释:
①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12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②黄宗智,高原,彭玉生.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中国农业的发展[J].开放时代,2012(3)。
③贺雪峰.小农立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1-5。
标签:小农经济论文; 农民论文; 经济论文; 留守妇女论文; 留守老人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三农论文; 农村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