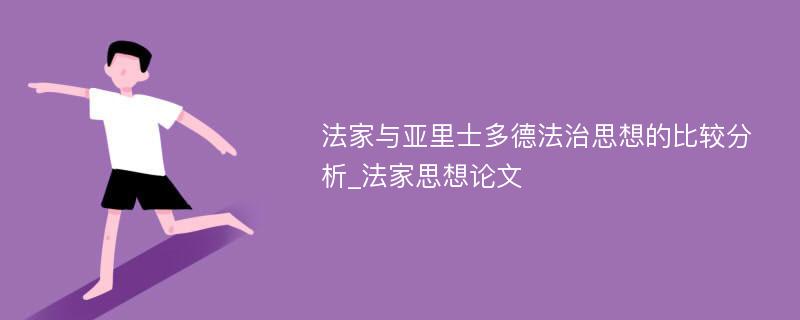
法家与亚里士多德——法治思想之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亚里士多德论文,法家论文,法治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与希腊是两个较早形成系统的法治理论的国家,而且,法治理论产生的时代也大体相当。战国时代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代表,而古希腊的法治思想的典范则是亚里士多德。在法家与亚里士多德身后,留下了两种不同的法哲学传统。法家与亚里士多德对于法律与法治的不同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与西方国家法治实践的走向。因此,深入分析法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各自的特点及其成因,是深入理解中国与西方国家两种不同的法哲学传统的前提,对于我们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也不无裨益。
一
法家和亚里士多德所生活的时代,制度文明都已经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也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空前繁荣的历史时代,法家学派与亚里士多德在各自的国度创立的法治理论,代表了那个历史时代人们对于法律最深刻的理解。他们都深刻地认识到了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实行法治的必要性。法家的代表人物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为治而欲去法令,犹欲无饥而去食也,欲无寒而去衣也,欲东而西行也”(注:《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外内》、《商君书·修权》、《商君书·农战》、《商君书·说民》、《商君书·说民》。)。在法家看来,法律之所以是社会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关键在于法律有两个方面的功能,其一是“定分”,即能够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财产界限和政治等级差别,“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贪盗不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且皆如鹜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贫、盗不取”(注:《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外内》、《商君书·修权》、《商君书·农战》、《商君书·说民》、《商君书·说民》。)。在能够确定财产分界的诸要素中,法家认为只有法律才最为可靠。其二是法律能够约束民众的行为,从而收到富国强兵的良效。“欲战其民者,必以重法,赏则必多,威则必严”(注:《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外内》、《商君书·修权》、《商君书·农战》、《商君书·说民》、《商君书·说民》。)。对于法律的功能,亚里士多德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要使事物合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的一个中道的权衡”(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9页。)。所以,城邦虽然是由一定的公务团体管理的,但是,城邦的最后裁决权却应该属于法律,即城邦治权的所有者必须按照法律的精神治理城邦。
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后的中国与希腊,思想界都曾经有过一场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论争,而法家与亚里士多德都旗帜鲜明地主张法治而反对人治。在希腊,一些持人治思想主张的人认为,对于城邦的管理来说,法律只能制定一些通则,当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具体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法律并不能发布政令,所以,“完全按照成文法律统治的政体不会是最优良的政体。”(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2-163页。)针对这一观点,亚里士多德指出,法律虽然在处理某些它所涉及不到的政治事务的时候无能为力,但是,必须注意到,在任何一个统治者的心中实际上都是存在着通则的,城邦的统治者总是按照一定的通则治理国家的。在某些时候,那些凭感情因素治理城邦的统治者虽然可以处理一些偶然性的事件,但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而法律恰恰是全没有感情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3页。)因此,即使是在以一人为治的君主政体下,城邦的一切政治事务都应该以法律为准绳。在中国,也曾有一些思想家认为:“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注:《荀子·君道》),而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法分明,则贤不得夺不肖,强不得侵弱,众不得暴寡,托天下于尧之法,则贞十不失分,奸不徼幸”(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之所以主张法治,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对于人的本性都没有作出乐观的评价。韩非认为,人性好利与计利而行是每个人基本的行动法则,“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不免于欲利之心”,(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由于人的道德品质是不可相信的,所以,治理国家只能依赖于法律而不能依赖于人。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人在本质上包含着兽性的成份,每个人都不可能完全消除野兽的欲望,即使是贤良的人也是如此,如果不依据法律治理国家,而是把国家交给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9页。)法律虽然不能使人变得良善,但是却可以抑制人的本性。
历史上一切主张实行人治而反对法治的思想家,其近乎一致的观点是,法律在任何时候都是要由人来执行的,因此,人的智慧比法律更为重要,“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注:《荀子·君道》)。对于这样的观点,法家与亚里士多德作出了十分明确的回答,在他们看来,在人与法之间,人的智慧并不可靠,“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去规距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短长,王尔不能半点中。使中主守法术,拙匠执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而亚里士多德则更加明确地说,法律确实在遇到某些具体事件时因为法律本身的内容没有涉及而无能为力,在这时,需要统治者个人的才智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个人的才智只能是作为法律的一种补充,而且个人才智的运用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违反法律的基本精神。同时,亚里士多德又指出,对于某些事例,法律虽然规定得不周详,无法作出决断,但是,在遇到这些事例的时候,个人的才智也未必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统治者只有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才能对法律所没有周详的事例做出公正的处理和裁决。
法律是历史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过程中,法律也经历了一个由不成文法向成文法的转变过程,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主张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所强调的法治,都是在成文法的基础上实现的法治。先秦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亚里士多德虽然曾经说过,“积习所成的不成文法比成文法实际上还更有权威”(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9-170页。),但是,在另一处,他却着重指出,城邦“最后的裁决权力应该寄托于正式订定的法律”(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47页。)。“正式订定的法律”与韩非对于法律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都认识到,要实行法治,就必须维护法律的权威,“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91-192页。)如果没有法律的权威,就不会有优良的社会生荤会生活。法家学派也提出了与此十分相似的主张,他们认为,法律高于一切臣民的利益,任何人都不得枉法,“法之所加,知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世,赏善不遗匹夫。”(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法律的权威,最终只能体现在社会成员对于法律的服从,所以,亚里士多德期冀“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99页。)而商鞅的说法则更为严厉:“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注:《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外内》、《商君书·修权》、《商君书·农战》、《商君书·说民》、《商君书·说民》。)虽然二者的旨意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在强调社会成员知法守法这一点上并无二致。
实行法治的前提之一,就是法律本身应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亚里士多德极其反对轻易地变更法律,他指出:“人们倘使习惯于轻率的变革,这不是社会的幸福,要是变革所得的利益不大,则法律和政府方面所包含的一些缺点还是姑且让它沿袭的好。”(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81页。)亚里士多德显然不赞同一个国家颇繁地进行法律方面的变革,在他看来,“法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须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81页。)与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十分相近,法家学派也有“法莫如一而固”的说法,韩非在评论申不害在韩国执政期间的得失时指出,申不害相韩十七年,没有使韩国成为霸主的原因,就是频繁地变更法令,“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使法律失去了相应的稳定性。法律不固,民众也就无法可守。如此可见,在如何实行法治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与法家学派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
二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思想有着诸多的相同或相近之处,但是,我们又不能不看到,在他们的身后,是两种有着本质差别的法治传统。深入理解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理论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比认识其共同点更为重要。
法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善德与正义是亚里士多德理解法律的出发点,而法家是用非道德的观点理解法律。
人们常说,法律不承认道德,但是,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法律与道德之间的联系却又是无法割断的。尽管二者只是在各自的领域里才有意义,但法律意义的合法与道德意义上的正义总不能相去太远。因此,在倡导人们服从法律的同时,思想家也必须解决另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用纯粹法律的观点去理解,只要是法律就必须服从,但是,在道德的立场上,人们只能服从善法。当亚里士多德在论及法律应该获得广泛的社会服从的时候,他随之又为这一论点附加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即“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99页。)至于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亚里士多德也做出了回答,“相应于城邦政体的好坏,法律也有好坏,或者是合乎正义或者是不合于正义”,(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48页。)从亚里士多德的这段话不难推断,在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中,善法就一定是合于正义的法律。同时,亚里士多德又说,“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48页。),可见,所谓“政治学上的善”与道德的善实际上是一致的,亚里士多德对于法律与法治的理解,并没有离开苏格拉底以来的哲学家所坚持的道德的善和正义的理念,总之,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中,优良的社会生活所需要的一切美德是法治的基础。
法家学派站在极端的立场上体认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家的政治学说在本质上是一种非道德的政治学说,在法家看来,仁义忠信等一切美德都是不可靠的,要实行法治,就不能讲道德,“今世皆曰,尊主安国者,必以仁义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国者之必以仁义智能也。故有道之主,远仁义,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誉广而名威,民治而国安”(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由于法家不承认道德的善或“正义”,因此,什么是善法,什么是恶法,也就成为一个无须讨论的问题。人们只需讨论如何实行法治,而无需为制定善法而努力。
由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主张也就有了不同的境界。亚里士多德说,城邦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优良的社会生活”,“凡订有良法而有志于实行善政的城邦就得操心全邦人民生活中的一切善德和恶行。所以,要不是徒有虚名,而真正无愧为一城邦者,必须以促进善德为目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37-138页。)。也就是说,法治的目的是实现优良的社会生活,而优良的社会就是道德的良善。
就法家的政治学说而言,我们没有理由断定法家没有对于优良的社会生活的追求,但可以断定,法家所追求的优良的社会生活决不是道德的良善。战国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了法家浓重的功利主义思想倾向,他们认识到,在列国之间愈演愈烈的兼并战争中,富国强兵是决定每一个国家兴废存亡的首务,并且清醒地认识到,农与战是富国强兵的根本途径,“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注:《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外内》、《商君书·修权》、《商君书·农战》、《商君书·说民》、《商君书·说民》。),于是,富国强兵便成为法家法治思想主张最直接的目的。应该说,富国强兵确实是战国时代的社会主题,但是,当法家把法律与法治简捷地理解为实现这一主题的途径的时候,“法治”也就失去了许多不该失去的东西。
第二,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中,法律是公共的规范,而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中,法律却是为专制君主所有的工具。
由于亚里士多德用“公共的利益”解释政治学上的善和正义,这决定了他必然用公共的观念理解法律。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法律是公共利益的体现,一个最高的社会权威,因而,亚里士多德在讨论执政者对于城邦的管理行为时,每每强调执政者应该“依法为政”或“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律为依归”(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3页。),即使是法律规定得不周详之处,执政者也只能是“遵从法律的原来精神,公正地加以处理和裁决”(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8页。)。执政官的权力只不过是“法律监护官的权力”(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8页。),而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但是,中国古代的法家却是用“所有”的观念理解法律,由于中国古代特定的历史环境,法家对于现实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高度的认同,在法家看来,国家、权力都不过是君主的私有财产,“国者,君之车也,势者,君之马也”(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法律也不过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管子·任法》在谈到君主与法律之间的关系时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法律是由君主制定、由臣下执行、约束民众行为的工具,这是法家学派对于法律的基本理解。
由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法家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律在内容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法家所说的法律,主要是指刑法,在某些时候,刑就是法的代名词,而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律,则是涉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规范和准则,这样,法家所说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法治便有了不同的意义,在法家的政治学说中,法治是“以法治国”,而在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说中,法治则是“依法治国”。
以法治国与依法治国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虽然也认为“全权君主”是“政体的一式,”但同时,他又指出,在平等的人民所组成的城邦中,君主用个人的智虑执行全邦一切公务,“以一人高高凌驾于全邦人民之上是不合乎自然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7页。),这意味着,法治不承认高高在上的权力。在法家的法治理论中,虽然也有“法不阿贵”的原则,可是这一原则只是适用于卿相将军下至于庶人这一范围,法家从来没有说过君主的行为应该受法律的约束。在有些时候法家也主张君主应该“守法术”,“守法术”的本意并不是遵守法律,而是如何用法律治理国家。法律对于君主来说,依然是工具而不是规范。确切地说,法家所主张的法治,虽然不是儒家所主张的人治,但也绝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法治。
第三,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强调公民的权利,而法家的法治思想则重视臣民的义务。
亚里士多德认为:“凡自然而平等的人,既然人人具有同等价值,应当分配给同等权利:所以,对平等的人给予不平等的——或相反地,对不平等的人给予平等的——名位,有如对体质不等的人们分配给同量的——或对同等的给予不同量的——衣食一样,这在大家想来总是有害(恶劣)的”(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7页。)。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自然而平等的人,是指自由的公民,公民平等是亚里士多德理解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基本的出发点。因为每一个公民都拥有不可侵夺的权利,法律必须成为“毫无偏私的权衡”,法治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基于这样的认识,亚里士多德主张“同等的人交互做统治者也做被统治者”,并且建立公民轮番做统治者的法律,(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67页。)主张“一邦之内所在同样而平等的人们也就一样地参与公务”(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71页。),通过公民议事机构制定法律。不难看出,强调公民服从法律仅仅是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的一个方面,而法律必须体现公民的意志、保护公民的权利则是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
法家不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也不承认民众的权利,当法家论及法律与民众的关系的时候,他们只是把民众设计为法律制裁的对象,把民众与法律置于完全对立的位置上,甚至认为,民众与法律之间无非是谁战胜谁的问题,“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注:《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外内》、《商君书·修权》、《商君书·农战》、《商君书·说民》、《商君书·说民》。),从法胜民需要出发,法家建议统治者首先把民众假定为奸民,“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强”(注:《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定分》、《商君书·外内》、《商君书·修权》、《商君书·农战》、《商君书·说民》、《商君书·说民》。)。在法家的法治理论中,民众所能做的只能是知法守法,能否尽守法的义务,是否对专制统治有益,是判别好的民众与不好的民众的唯一的尺度,如“学道立方”者被视为“离法之民”,“寡闻从令”者被称为“全法之民”(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在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中,法律只是规定了民众无尽的义务。
当然,亚里士多德关于平等与权利的认识也不是没有局限性,就像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自由的意识虽然首先产生于希腊人中间,但是,“希腊人不仅蓄奴,……而且他们自己的自由既局限于狭隘的范围,同时也局限于人的……残酷奴役状态”(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第18页,转引自(美)列奥·施特劳斯等:《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第883页。)。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等与权利,仅只是雅典人之间的平等和雅典人的权利,并不是普遍意义的人的平等与人的权利,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奴隶和野兽一样都不具备自由意志,所以,亚里士多德观念中的法治,不可能给予奴隶以平等和公正。不过,应该说明的是,亚里士多德法治理论的这一局限性,是社会历史的局限,而不是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的局限。
第四,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包含着权力制衡的因素,而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与集权专制的统治模式却是有机的统一体。
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建立政体的正当方法的时候,尤为注重法律与政体之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三者之一为有关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部分);其二为行政机能部分……其三为审判(司法)机能”(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215页。),并且指出,一个优良的立法家在创制时,必须考虑到怎样才能使法律适合于其所构成的政体。不难看出,近代思想家所倡导的三权分立原则,实际上来自于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曾经讨论过各种类型的议事机构,无论是平民政体还是寡头政体,其共同的特点都是议事机构具有最高权力,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制定和通过法律。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理论中,立法权属于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议事会,而不属于城邦的行政长官,因此,城邦的执政官只能成为法律的监护官。
但是,法家所主张的法治却是与君主专制的集权统治互为一体的,法家认为,国家不能存在二元的权力结构,“两则争,杂则相伤”(注:《慎子·德立》),国家的立法权与行政权必须集中在君主一人手中,“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由此看来,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以高度集中的权力为前提的。
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思想家不知道法律与法治的重要,因此,是否主张法治,并不是唯一的评价标准。关键在于,在思想家的政治设计中,法律是与什么样的权力结构结合在一起的。由于亚里士多德与法家对于国家的权力结构的不同理解,其法治思想也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
第五,亚里士多德主张严明的法治与贤人政治相结合,而法家则完全否定人在法治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在任何历史时代,即使是最好的法律,也是由一定的人来执行的,执法者的素质如何,必然影响法治实践的质量,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因此,就社会政治生活的全部内容来说,一方面需要一部善法,另一方面,也需要由贤良的人治理国家,事实上,人类社会生活质量的提高,与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是分不开的。亚里士多德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在他主张城邦的政治以法律为依归的同时,他又指出:“最优良的政体就该是由最优良的人们为之治理的政体”(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73页。)。以最好的法律为依归,由最好的人来执政,是亚里士多德的主观心理追求。
法家的认识恰与亚里士多德相左,在法家看来,或者任法,或者任人,在法与人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于是,法家在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同时,绝对否定了人在法治实践中的作用。他们或者说“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则万不失矣”,或者说“上(尚)法不上(尚)贤”(注:《韩非子·守道》、《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守道》、《韩非子·难三》、《韩非子·有度》、《韩非子·定法》、《韩非子·说疑》、《韩非子·外诸说右上》、《韩非子·六反》、《韩非子·二柄》、《韩非子·忠孝》。)。社会需要法治,但法治不应允许庸才治国。法家在人与法的关系上的认识局限是不言自明的。
标签:法家思想论文; 政治学理论论文; 君主制度论文; 法治国家论文; 韩非论文; 商君书论文; 法律论文; 中国法制史论文; 哲学家论文; 君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