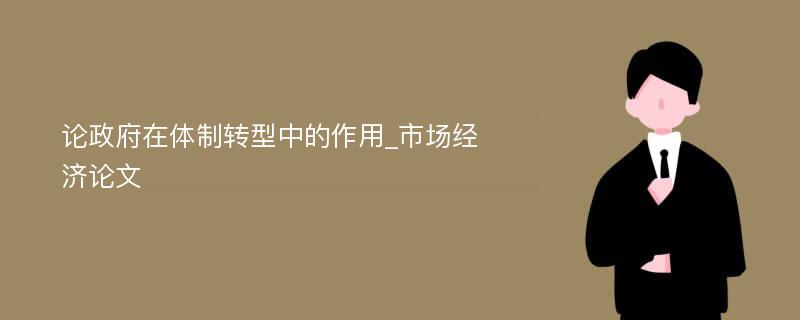
试论政府在体制转轨中的作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体制论文,作用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什么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合适活动范围,本来就是一件争议很多,很不容易正确地加以确定的事情。转轨期间的情况更为复杂。自从中国的改革开始以来,如何正确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始终是一个很费斟酌的问题。
1.集中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往往是所谓“全能政府”。由于计划经济体制意味着由国家的有形组织——政府通过计划集中地配置资源,在这种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形成的政治体制,必然带有政府对全部社会生活进行控制的特点。在中国传统体制下,包括按其性质来说只能由个人决策的领域,如职业选择和消费选择,也在很大程度上由政府包办。因此,传统体制下的中国经济在70年代的比较经济学中曾经被称作“动员型的命令经济”。市场经济建立在独立的经济行为者之间的自主交易活动之上。市场经济按照定义,意味着由市场力量通过按照供求关系形成的价格配置资源。向市场经济转轨,自然也就意味着政府活动范围的缩小和所谓民间社会的壮大。政府放弃某些支配经济资源的权力,就成为经济转轨题中应有之义了。在这个意义上,“大政府”与“小政府”之争反映了转轨过程的本质。
由于改革前占统治地位的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和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利益格局,政府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向市场交出不该由它行使的权力,必然地受到在命令经济中有既得利益和具有保守思想的人们的反对。这在改革初期,突出地表现为“放”与“不放”的矛盾。这种矛盾与冲突,一直延续到现在。虽然形式有了改变,但实际上内容依旧。
2.不过在讨论政府在转轨过程中的作用时,人们有时也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把政府在转轨期间要做的事情简单地归结为“放权”,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管的事情愈少愈好;在转轨的过程中,只要政府放手不管,市场的自发力量会自然而然地把事情安排得井然有序(或者通过一个混乱的、乃至“相互欺骗”的过程,使人们认识到通过订立合约建立秩序的必要性,从而把市场规则建立起来)。
然而中国改革的实践表明,上述想法是不一定恰当的。它接近于所谓“曼彻斯特资本主义”或斯密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并不适合于现代市场经济。例如本世纪初期就已提出了所谓“福利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的概念。凯恩斯以后的主流经济学更积极地主张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由政府发挥作用来加以弥补。即使是80年代盛行一时的新自由主义,也并不完全否认政府发挥作用的必要,只不过认为政府的作用范围应当严格地加以约束,因为政府也会失灵,需要在两种失灵之间进行权衡。战后时期,根据亚洲一些绩效良好的经济经验,经济学界相当一部分人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有更为正面的评价,对东亚表现良好的经济中的政府职能作出了“市场亲和”、“市场增进”等性质规定。当然,在最老的市场经济国家如英国,市场制度的发育成熟大体上是自发地进行的。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从18、19世纪极不规范的市场到现代的比较规范的市场,花费了一、二百年的时间,中国不能等待那么久。而且需要注意到这样的演变趋势:本世纪以来各发达国家政府在推动市场成长中的作用趋于主动。虽然其间有波动和反复,但政府参与市场发育(特别是在设定市场规则方面)对于现代市场经济成长上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单以1929年大危机以后美国证券市场的成长为例就可以看到,如果没有美国国会1933年和1934年的证券和证券交易立法,如果没有罗斯福行政当局对当时刚刚建立的证监会(SEC)的全力支持,就根本不可能克服那些操纵市场和进行内幕交易、愚弄广大股民的大金融资本的反抗,使美国的证券市场走向规范,证券交易走向有序。中国当前存在的情况是,由于对市场的规制和监管远落后于市场放开的进程,常常导致严重的混乱(如证券市场)。据此,我们应当充分吸收上述观点演进的成果,对于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职能作出更准确的界定。也许问题的要点并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而在于政府作用的性质和它同市场关系的“好”、“坏”,即在于它对市场有效性的提高是起了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
3.为了减少阻力、增加助力,中国在改革一开始曾采取了两项做法:第一,中央政府向下级政府下放自己的权力,包括干预企业微观经济活动的权力;第二,允许乃至鼓励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下海”经商。这种做法,有效地减轻了来自政府内部的对改革的抗拒,但是,也由此形成了一种不利于市场健康发展的格局。
由第一种做法形成的经济体制,在中国被界定为“行政性分权”(在前南斯拉夫则被称为“多中心国家主义”)。与这种做法相适应,甚至形成了一种普遍流行的观念,以为从中央向地方下放权利就是改革。其实真实的情况未必如此。如果下级政府持有一种“把你的权拿到我的手里来行使;过去你怎么管理经济,今后我也怎么管”的想法,权和利的下放也不意味着市场取向的改革。事实上,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行政性分权的结果势必导致市场分割(所谓“切块、切条、切丝、切末”)和地区保护主义,极不利于统一市场的形成。
由第二种做法形成的,是一种“工农兵学商,一齐来经商”、“官商不分”、“权力揽买卖”的格局。在这种体制下,利用行政权力“寻租”的条件广泛存在,因而使腐败行为在干部队伍中迅速蔓延,而且促成了一种力图阻碍寻租环境消失的社会力量的成长,因而不利于旨在建立健全的市场环境的改革的进行。例如早在1984年,中共中央全面规划市场取向改革的第一个决议,即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就已正确地指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成败的关键”。在1985年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又明确规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是预定在1990年建立起基本框架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个基本环节。虽然根据这些决定中国政府试图在这方面的改革上有所作为,但是直到90年代上半期,并没有太多的建树。不要说要素价格和要素市场的放开迟迟没有到位,即使就商品(货物和服务)价格而论,政府多次计划采取的主动行动也是以取消告终。究其原因,除技术上的困难和配套条件的不具备,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来自价格“双轨制”的利益和代表这种利益的社会力量的反对。这种反对使领导人不敢在价格改革上采敢果断行动,以致中国的商品价格改革只得以被动的方式进行。虽然到90年代初期我国的大部分货物价格已经放开,但是这种被动式改革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是很大的。
4.中国经济目前仍然处在转轨的过程中,健全的市场制度尚未初步形成。看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具有较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更多的职能。这主要是:
(1)消除对市场取向改革的阻力。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意味着利益格局的巨大变动。这种变动自然会遇到来自既得利益的反对。从中国的情况看,改革遇到的既得利益阻力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与计划经济(“命令经济”)相联系的既得利益;一是与转轨过程中的不规范的经济关系相联系的既得利益。在中国改革前15年采取“增量改革”战略的条件下,利用价格、汇率、利率等的“双轨制”寻求租金,变成一些有可能接近行政权力的人发财致富的捷径。从这种利益出发,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虽然支持前期的改革,却极力阻碍进一步的改革,因为市场制度的真正确立,会使寻租环境遭到破坏。面对着以上两种社会力量的阻碍和反抗,如果政府不能依靠群众并运用自己的力量来消除障碍,进一步的改革就会步履维艰,难于迈步。对于前一种阻碍改革的社会力量,人们保持着比较高的警惕。而后一种力量,由于他们在改革初期的确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力量,而且由于他们在阻碍进一步改革时打着“保护改革成果”、“选择符合中国实际的改革方式”等旗号,往往对于人们有较大的迷惑力,甚至被误认为最坚定彻底的“改革派”。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过来自力图保持双轨定价制度的社会力量的阻力使中国的价格改革迟滞的情况。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也有过相反的经验。当1993年秋季中国政府决定1994年1月1日实现汇率“并轨”,向经常帐户下人民币自由兑换过渡时,在双重汇率制下获既得利益的人们广泛进行“公关”活动,宣传汇率“并轨”将引起巨大混乱和本币急剧贬值,甚至导致人民币的崩溃。可是在中国政府顶住了这种压力如期实行“并轨”以后,虽然由于准备工作做得不好而有过短时期小的混乱,但是顺利实现了有限制的自由兑换而没有出现大的乱子。现在人们不能不承认,总的结果是好的。
(2)设定并执行市场活动的“竞技规则”, 市场的有效性建立在公正竞争的竞技规则的确立上。在最初形成的市场经济如英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中,竞技规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几百年的漫长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后起的市场经济国家大大地缩短了竞技规则确立的过程,原因就在于汲取了先行国家的历史成果,用政府的力量来确立规则。在我看来,这也许是格申克隆所说的“后发性优势”的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吴庆瑞博士在一次和我的谈话中指出:英国殖民统治对新加坡造成了许多消极影响,但他们也做了一件好事,这就是留下了一个比较好的法律框架。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从这里得益不少。这的确是经验之谈。中国缺乏法治传统,政府在设定规则方面的任务就更加艰巨繁重。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M·布鲁诺1996 年夏天在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的一次讲话中指出,中国今后应当把改革工作的重点放到设定竞技规则方面去。我很同意他的这个意见。
5.发挥政府的作用以促进转轨的进行,也会带来一些问题。从中国的经验看,这主要是:(1 )由于改革是在原有的政府机构的领导下进行的,而政府工作人员中的一部分人会由于在计划经济中习惯的思维定式或在计划经济中获得的既得利益而倾向于守住自己的权力不放,阻碍改革。(2)由于政府机构被赋予了较大的权力, 有些政府工作人员就会利用这种权力与寻租者勾结,从后者那里收取贿赂。这样一来,腐败就会盛行。更有甚者,一些人还会在改革过程中进行“设租”活动,以便创造更多的寻租可能性。这就使立意很好的改革措施遭到扭曲,走偏方向。1992-1993年期间“国有土地批租”改革的扭曲,就是一个突出的事例。一些地方本来有着很好的发展形势,但是由于纵容肆无忌惮的寻租活动和鼓励不动产投机,结果不但由于地价飞涨妨碍投资者进入而断送了大好的发展前景,还使大批干部陷入贪污犯罪的泥坑。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代价都是十分沉重的。面对这种情况,政府必须按照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使自身健全起来。除了坚定地推进改革以便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在执行自己的职能时采取“市场增进”的做法之外,它应当对政府人员进行市场取向的政治思想教育;加强法治,清明吏治和肃贪反腐;同时,推进政治改革,扩大民主,把政府机构和政府工作人员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转轨过程中有效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