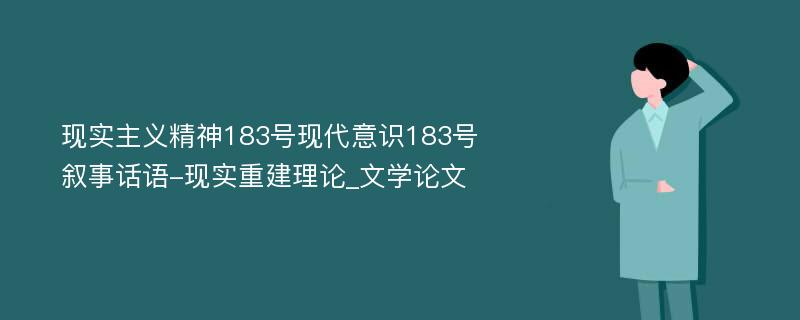
现实精神#183;现代意识#183;叙述话语——现实主义重构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重构论文,话语论文,意识论文,现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两个世纪的交接点。在世纪之交的特殊历史背景下,思考文学的发展道路,提出对文学发展有意义的理论命题是值得重视的。《作家报》与《时代文学》主张对现实主义这一在本世纪产生广泛影响的创作方法进行一些新的思考,以期拓宽文学的发展道路,我以为是一件很有意义和富有实践价值的想法。
从整个二十世纪文学的发展过程来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现实主义文学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五四时期的现实主义与40年代、50年代、80年代的现实主义相比较,显然有着各自的特点,叙述话语、艺术精神等都有所不同,于是“现实主义”这一被运用得颇为广泛的批评术语,有时就显得空洞而不着边际。也许理论批评界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分析不同时期的文学创作时,便在“现实主义”之前加上了种种限制词,譬如:批判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等等,以便用这种方式区分出各种与“现实主义”相关的文学现象的特点,不能说这种区分毫无道理,但在一些基本的概念上则是模糊和不清晰的。这一点秦兆阳先生在50年代发表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一文中已经指明了这一点,他认为现实主义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对于客观和对于艺术本身的根本态度和方法,不是指人的世界观,而是指人们在艺术创作的整个过程中,以无限广阔的客观现实为对象、为依据、为源泉,并以影响现实为目的。这是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大前提,离开了这一根本的性质考虑一些具体的问题,所谓现实主义的意义就模糊和狭小了。在今天提出重构现实主义这一问题,秦兆阳先生的这一观点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也是我们思考的基本出发点。
一、现实精神:现实主义文学的内核
现实主义既然是指人们在文学艺术实践中对于客观和对于艺术本身的根本态度和方法,那么,我们以为这个根本态度的核心问题就是对于“现实精神”的深刻思考和艺术地真实呈现。
“现实精神”是一切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所必具有的特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现实精神是有误解的,我们往往把现实精神理解为生活的本质,又把“本质”与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等同在一起,从而导致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化”“观念化”倾向;二是因为在近几年的文学创作中,现实精神演化为琐碎的生活情趣,作品境界趋于一隅,缺少博大、深邃的景观。自从89年以来,源于一种非常复杂的原因,人们提出了“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后新时期”、“后现代”“后殖民”等等口号。这些问题的提出自然是有一定意义的,与其相关的一些作品也表现出了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的心理状态和生存状态,但是在这追“新”逐“后”的过程中,我们的确变得有点媚俗和浮躁,在“削平深度”“消解主流话语”的喧哗声中,我们的文学作品走向平面,表现“现象”,拘于一隅,远离现实,“现实精神”走向衰微。面对这样的文学背景,重提“现实精神”显然是有意义的。
“观念”不是现实精神,正如思想不等于现实;“现象”也不是现实精神,正如衣服不等于人一样。虽然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思想离不开现实,衣服也代表着一个人的气质和审美情趣,但两者终究不是一回事。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由“观念化”走向“现象化”,虽然纠正了文学创作中的某些偏差,但仅仅呈现“现象”也不是够的,目前的文学作品缺少有深度的力作,缺少激情和理想就说明了这一问题。那么,现实精神是什么?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而言现实精神就是作家对人生现实的深切关注和对现实人生的理性审视。两者相辅相承,在作家与现实生活的相互联系中,呈现出生动、丰富、深刻的内容。
深切关注人生现实就是关注人生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仅就这一点来讲,近年来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新写实”“新体验”“新状态”等文学作品还是有意义的。当“新写实”以“还原生活本相”表现人的“原生态”为宗旨,力求客观地完整地再现生活中的一切,返归到生活本身和人生存本身,追求原色的生活魅力时,它的确开拓了文学创作的空间,但是在新写实通过超然于作品人物之外的叙述角度和对生活流程的重视而传达生活的原色魅力过程中,由于忽视了人的理性的意义和价值,也就是说缺少对现实人生的理性审视,而使其作品显得琐碎、凌乱,他们在尊重现实的一切存在时,却把自我淹没在了喧嚣的尘世生活中,而难以看到精神的光芒。“新体验”小说可能是为了纠正新写实小说的弱点,从而强调作家的“亲历性”,要求作家写出对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感受,从作品中见出人的精神和情感的力量。这种追求无疑是有着良好的美学愿望的,但就我所读过的一些作品来看,却普遍呈现出作品境界狭窄的倾向,“亲历性”成为宣泄自己内心情感的代名词,身边琐事被一己的情感牵引,失去了与广阔现实人生的多层次联系,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成为对一己人生的独自咀嚼,这一点在“新状态”小说中也有所表现。“新状态”是含糊不清的一个概念,抛开概念本身不谈,仅就其所推出的一些作品来看,显然缺少现实人生的深度和人生现实的博大,男欢女爱的痛苦与绝望在“性”的操作中显出人性的龌龊和生存的无意义,当然这些作品对人的潜意识及人的生存意义的思考是有意义的,但是这种思考如果不是与具体的现实人生相联系,不是与人们所能理解的生活方式相联系,就显得空洞和缺乏现实感。
目前的这种文学状况显然是不尽人意的,特别是在“先锋文学”落潮,人们对文学渴望的目光转向“关注现实的文学”时,我们这些强调“关注人的当下存在状态”的作品却存在着如上问题就更加令人失望。我们也承认这些作品在某一方面有所探索和深化,但绝不能走向偏狭的路途,应该关注现实、关注人生,走向博大和宏阔,把新的审美经验、博大的理性精神及广阔丰富的生活内容结合起来。因此,在我们重构现实主义时,就不能不把“现实精神”与人的灵魂相联系,而强调在作品中见出灵魂的重要性。见出“灵魂”在此有两层意思:①是在作品中见出人物灵魂的深度,见出在多种社会关系纠缠下“灵魂”的复杂性,见出现实生活的深层意蕴;②是在作品中看出作者真诚、深刻、独立、直面人生的灵魂。
从作家创作主体的角度,现实精神表现为深切关注现实和理性审视人生;从现实生活角度而言,现实精神又是与无限丰富的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的,是蕴含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历史力量,具有某种客观性特征,它具体体现于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所生活的外部世界中。在此我们重点强调人的“精神世界的现实内容”,因为对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究与思考与作品中“见出灵魂”的艺术追求是密切相关的。新时期以来所出现的“先锋文学”对于当代文学的重要贡献就是对于人的“生命”的重视。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拓宽了文学的表现领域,使我们对于人自身存在的焦灼、危机感、苦闷、烦躁等等情感、欲望的内容有了新的认识。在我们重构现实主义时,我们理应把这种“生命的内涵”纳入我们的理论中,由此去深入地思考和发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性。这一点在50年代和新时期初期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是被忽略了的,在那些作品中,人主要所扮演的是一个被人们所认可的社会性角色,人的七情六欲难以有表现的机会。作为社会历史生活中的“核心”——人,其精神世界缺少深度和广度,也就难以见出“现实精神”的深度和广度。
强调“人的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并不等于忽略“人所生存的外部世界”,现实主义的文学要求把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人放置于丰富的、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把人放置于动态社会系统中,表现人的精神和灵魂,使人物形象在内与外的相互联系中变得更加立体和丰富。
“现实精神”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文学的活力之源。虽然现实精神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内容:五四时期的现实精神与我们今天的现实精神不同,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也有区别,但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都是写出了时代的个性精神特征,深刻地把握和表现了其时代的现实精神风貌。实际上一切优秀的作品都离不开现实,即使宣称“为自己而写作”的西方现代派文学——萨特、加缪、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也深切地表现了人被异化的精神痛苦和荒凉的生存景观,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中“现实精神”的重要性,离开了现实精神,文学作品就会失去生命力。
二、现代意识:通向“现实精神”之桥
现实精神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核心,它从创作主体的角度表现为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注和对人生现实的理性审视,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而言,现实精神又蕴含于人的内部精神世界和人所生活的外部世界之中,那么文学作品如何才能深刻地呈现“现实精神”呢?也就是说作家的“关注”和“理性”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达到对现实精神的把握的呢?
在不同的时代,作家的这种“理性内容”是有所区别和不同的,在目前我们认为这种理性内容换句话说就是现代意识应是对人类的未来、现在、过去有着深刻、清醒的认识,而不被外在的既定观念、时尚所左右,具体一点说,就是爱的激情、批判精神、理想精神。——如果缺乏这种强健的现代意识,就无法在作品中见出现实精神和灵魂的深度。我们近几年文学创作缺乏现实感、境界狭窄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新写实”陷于琐碎,“新体验”拘于一己,“新状态”缺少丰富,就是未能在创作中用这种现代意识的眼光来审视生活,把现时的生活放在人类生存的长河中思考其价值和意义。
爱是什么?爱就是关心人,关心人类终极存在的命运,这一点在目前似乎有许多作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仅仅意识到是不够的,要把这种理性的思考灌注于创作中才是有意义的。关心人类的终极存在意义似乎是一个很抽象、虚幻的命题,然而又是一个很现实、具体的问题,人类的终极与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过程也就无所谓终极,因此关注终极首先要关注现实的具体。我们目前的文学创作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是在关注现实具体时,忘却了对终极之光的追寻,使现实生活形态变得狭窄和琐碎;另一方面则是在追寻“终极”时,忽略了具体的生活内容而成为观念的图解。这都造成了作品理性不强、生活境界低俗的弱点。
批判精神就是对人类及现实生活中的弊端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由于近几年的文学作品大多沉溺于平凡的生活氛围中,为普通人的生活情趣所陶醉,作家也就未能以超越现实之上的理性眼光,在人类生存的历史过程中审视我们生活中应有的和不应有的一切,也就难以深刻地挖掘人在历史流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丑陋品质,于是在近几年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陷于琐碎生活中的苦恼,读到了人归于家庭后的温情与欣慰,也读到了人飘泊无定的孤独感和绝望情绪,可就是读不到对于人和社会的种种问题所发出的严厉拷问,体验不到那种对人生悲凉的感悟和悲悯。这是幸与不幸?难道我们的现实与人生真的消失了值得我们批判的理由?还是由于作家对于艺术和生活的态度出了问题?如果是属于后者,我们就应该重新纠正我们的态度,而让理性的批判精神重新回到心中。
理想精神并不是虚幻的乌托邦,虽然它也是一种虚设的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理想与以往现实主义文学所强调的理想有着很大的不同,它不是廉价的对于“明天”的歌颂,它也不是所谓的“光明”的尾巴,更不是意识形态话语所提供给我们的那一观念性的世界,而是立足于现实,对于一种强健的理性人格精神和对于人类精神的一种永恒渴望。这一点在目前的文学创作中显然极为薄弱,穿越俗世的障碍,把人的美好的精神情怀和永恒的渴望贯穿在创作中,使精神呈现出抗争现实的超然魅力的作品在目前的确是太少了。
爱、批判精神、理想精神是我们所要重构的现实主义极为重要的三个内容,这三者共同构成了作家对于生活和艺术的基本态度,它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如果爱和理想精神淡化,仅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其作品可能会呈现出以往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品格;如果批判精神淡化,爱与理想精神政治化,其作品可能会呈现出我们建国之后的“现实主义”作品的风貌;如果在作品中消失了我们所说的“爱”的精神,亦即对人类终极意义的关怀,这类作品可能就会陷于琐碎,而近似于“新体验小说”,显出偏狭;如果在作品中淡化了理想,就会把自我淹没在喧嚣的尘世中,疲惫、无奈的“新写实”风格就是其必然的归宿。由此可以说爱、批判精神、理想精神是“现实主义”在经历了历史的坎坷之后,在今天所必然出现的一种境界,是作家所必具有的一种现代意识。
我们所要倡导的这种“现实主义文学”,显然渗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在当今世界各种文学潮流都被我们所了解的文学背景下,回避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精华内容显然是不明智的。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一般都被认为是“非理性”的产物,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如果仔细想一下现代主义文学所提倡的“非理性”创作原则中所包含的仍然是一种理性,只不过这种理性的内涵与现实主义作家所说的理性有很大的不同,现实主义作家所强调的理性原则是明晰的,真善美在世界中是存在并且可以创造的;而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世界是偶然、非理性的,对真善美能否在世界中必然有意义持怀疑态度。由此可以说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世界都有一种明确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理性认识的结果,如果这种态度也是非理性的,就无法表述他们对世界及人的看法。我觉得现代派文学最为激动人心的一点就是他们在残酷、充满绝望的世界上,仍然关注着人类的终极存在意义,对人类的生存图景有着不满于现状的永恒追求,即使绝望和死亡已经来临,他们的心也是指向人类的未来的。我们在重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时,强调作家对于生活和艺术要具有爱和理想的态度,就是在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思考中提出的,这一点也是以往的现实主义文学所缺少的。在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中能够达到这种思想境界的作家,恐怕只有鲁迅堪称典范,他拒绝现实的挤压、困顿于精神的荒凉,他对中国人的思考以及强烈的爱和理想向往,演化为对现实人生的无情批判,而使其作品具有了永恒的魅力。
我们的文学理应有这种品格。这也是我们在世纪之交的历史背景下,对于未来文学前景的一种思考,因为我们的现实和人们的审美经验,决定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生命活力,这一点已被文学史的实践经验所证明,在此就不作论述了。
三、叙述话语:现实主义的表述特征
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作为具有自己美学个性和审美规范的一种文学形态,它应该具有自己独特的叙述话语。如果说现实精神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基本内核,现代意识表明了现实主义艺术家对生活和艺术所取的情感思想趋向,那么叙述话语则力求说明在其创作过程中区别于其它创作方法的特点。
叙述语言对小说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艺术态度,并且往往受着表现内容的制约。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所面对的是现实人生,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与社会、大众对话,因此,我们强调其叙述语言的当代性和大众性特点。当代性表明了现实主义艺术家使用语言的能力和区别于以往时期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语言特点。譬如说在我们所倡导的这种具有新的特点的现实主义文学中,其语言就不会如“新写实”那样事无巨细、琐碎唠叨,也不会如建国初期的“现实主义”那样,作家的话语完全纳入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系统中,缺少独特的个性色彩,也不会如古典现实主义那样主要在现实层面上叙述,而缺少对人的心灵世界的探究。这种具有当代性的语言应该符合当代人心灵世界的内容,具有创造性和表现力。我们强调语言的大众性,不是走向通俗,大众性也不能等同于大众化,大众性是相对于宣称“为自己写作”的现代主义而言,应该是社会群体所能接受的语言。
叙述方式的客观性是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又一特点。强调“客观”,不是要作家进入“零度”情感状态,而是把情感包容于对现实、人生事件及人物心理的叙述过程中。这个“客观”是相对于表现主观的浪漫型艺术和现代艺术的主观性而言,它强调了文学作品与现实之间的亲和、依附关系。
强调客观性原则是否就意味着叙述语言必须恪守具体的真实性呢?也就是说每一句话必须是有据可证的呢?这又牵涉到“艺术的变形”问题,我们不妨在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的联系中作一简单说明。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是强调真实、具体、形象的,而现代主义的文学艺术则是变形、抽象、象征的。象征使作品的主题趋于深刻和涵盖面广泛,能够使人从多个侧面去理解作品的意义。在当今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现实主义是否还要恪守细节的真实性原则是值得考虑的。如果我们也看到了世界存在的某种荒诞性,把现代主义的“变形”方法纳入到创作过程中是能够加强作品的深度和力度的。意识到世界的荒诞,并把荒诞升华为一种艺术境界,应该说也是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只不过现实主义文学艺术不能把“变形”作为自己的主导性原则,否则就不是现实主义了。
现实主义文学艺术的叙述话语是开放的系统。由于它贴近现实的特点也就决定了它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人为地界定其特点是费力不讨好、也是徒劳的事,只能就其主要方面做如上简单说明。
如上我们重构的现实主义理论是针对目前的文学创作所提出的一些想法,也是一种文学理想,我们期待着理论的进一步完善,也期待着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和博大、深邃的艺术作品的出现。
最后值得进一步说明的是我们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绝不意味着对其它各种创作方法的排斥,实质上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在中国的发展是在与其它各种创作方法的联系中发展的。鲁迅的现实主义就不仅与浪漫主义相联系,同时也渗透着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一些优秀之作,也都带有外来文学的各种有益内容。因此,我们在倡导现实主义文学的同时,也不应忽视那些具有探索性内容的文学作品。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只有在与世界各种文学的联系中,在开放的文化背景中,才能确立自己应有的当代性品格。
另外,中国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所处的文化背景是极为特殊的,即一方面背倚着中国古典现实主义的传统,一方面又与西方的现实主义和西方发展至今的各种文学流派相联系,在这种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所倡导的现实主义文学,就必然在整体风格和审美经验上与其它各个时期的现实主义文学有所不同,同时也给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是既不能固步自封,无视世界文学的发展趋向,又不能食洋不化,把现实主义搞成不伦不类的大杂烩,既不能忽视传统的审美趣味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又不能陷于传统不能创造更新。这些都是原则性的提法,说多了也无用,还是寄希望于文学创作的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