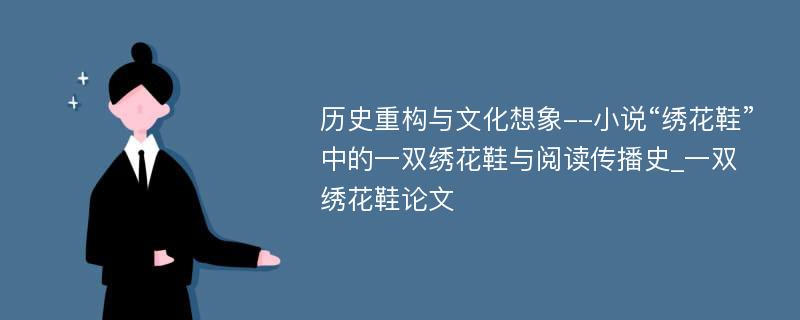
历史重构与文化想象——小说《一双绣花鞋》及其阅读传播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绣花鞋论文,重构论文,文化论文,历史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原刊主持人语:在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和访问学者一起做“重返八十年代”的研究七年后,我们意识到八十年代文学的边界应该上溯到七十年代初前后。也就是说,八十年代文学的“起源性”因素在七十年代,或者六十年代就存在了。也就是说,八十年代的启蒙,七十年代的“文革”,与六十年代最为激进和多重的青年政治运动之间,并不是相互脱节的历史链条,而是一种相互质疑又相互连接的关系结构。因此在我看来,从一个方面看,八十年代文学中的思想启蒙表面上是以与七十年代“文革”的断裂为前提的,然而这种启蒙思潮,早在七十年代一部分大城市的“读书小组”和“知青圈子”中已处在萌动、酝酿和发展的状态;另一方面,如果不关注七十年代公开发表的小说,不真正了解那个年代人们精神扭曲的状况,也就无法对八十年代的兴起拥有一个更为宽阔和全面的历史视野。但是,由于这一时期历史的复杂性,我们对问题的判断又不能过于大而化之,和过于武断,而应该以具体小说的分析为立足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探寻,在全面深入地研究了许多问题之后,我们对八十年代文学的理解也就建立起来了。“七十年代小说研究”,是“重返八十年代”的延续和向纵深的发展。
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明确要求“坚决纠正此前的镇反运动中出现的‘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以完成彻底清除国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历史重任。重庆市从1950年第四季度起,到1951年上半年先后展开了三次镇压、清除反革命分子的大批捕运动。其中涉及面最广、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三·一三”大批捕,一晚上抓了4000多人。①被称为“文革地下文学”第一书的中篇小说《一双绣花鞋》的创作灵感即来自于作者况浩文亲身经历的“三·一三”大批捕事件。
《一双绣花鞋》写于提倡群众写作的1958年,最初名为《在茫茫的夜色后面》。1964年况浩文应峨眉电影制片厂导演张波之约,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同年秋天,小说开始在重庆地区广泛流传,同时书名也被著名评书艺人徐勃改为《一双绣花鞋》。然而,令作者做梦可能也难以预料的厄运也紧接着降临到他的头上。电影未及上映即胎死腹中,在梦魇般的“文革”浩劫中,况浩文因为倒霉的“绣花鞋”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但在他为自己的身份焦灼、纠结的同时,小说《一双绣花鞋》通过大串联的红卫兵和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以手抄本形式在祖国大江南北被疯狂传抄。
也正是经由况浩文响应主流文化创作的故事到“文革”期间地下不断秘密地手抄、口传,《一双绣花鞋》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十七年”、“文革”主流文学的政治话语运作方式,挣脱了“文革”期间在“夹缝”中生存的种种禁忌、束缚,获得了来自民间大众的那种自由而绵长的生命力,成为“在文化沙漠中煎熬的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株绿草。”②小说也因此勾起了几代重庆山城儿女这个特殊“种族”的集体记忆与文化想象,重塑了他们当年“那有时有点像本城的雨季般阴郁,比本码头的坡坡坎坎还陡峭的心灵史。”③由小说到手抄本,况浩文以及一大批匿名的读者、传抄者把自己关于“反特”、“文学”的想象不断地投射和附加到《一双绣花鞋》上,最终形成了对“三·一三”大批捕这一历史事件的复杂同时又隙缝丛生的文学重构与文化想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尝试把《一双绣花鞋》尽量放在一个复杂的视域和语境中,考察它是如何以文学化的方式重构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具有重大意义的镇反事件?文学叙事对历史想象作出了哪些特殊回应?作为通俗文学,《一双绣花鞋》何以能够产生如此大的冲击波与轰动效应?作为“文革”手抄本小说的代表,它有没有政治之外的文化意义?
一、由“镇反”运动到“反特”小说
新政权刚诞生之际,维护国家人民和财产的安全,巩固发展基础是一个国家经济建设的首要任务之一。在美国支持下,1950年代初,蒋介石把西南地区作为撤离大陆后的最后据点。国民党军警宪特匪在那里的人数之多、活动之活跃,令人惊讶。据作者况浩文回忆:“当时光军警宪特匪就有8万人,他们还吆喝了些土匪武装,组成‘反共保民军’、‘反共抗俄军’,国民党武装号称达到一百万人”④。1950年3月,西南局向中央发出一份紧急报告:“近一个时期以来,西南川、康、云、贵各省,连续有土匪在各地发动大规模武装暴动……二月份以来,各地土匪又围攻并占领了包括温江、崇庆、郫县、金堂、新繁及川东之秀山等多座县城。邛崃城遭匪万人之围攻,壁山军分区一夜之间八个区政权遭匪袭击而全部丢失。”⑤由此可看出当时国内形势的严峻性。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国际环境,1950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在大陆上基本结束,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已先后成立。但在某些地区特别是有些新解放地区,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仍在采取武装暴乱和潜伏暗害等活动方式,组织特务土匪,勾结地主恶霸,或煽动一部分落后分子,不断地从事反对人民政府及各种反革命活动,以破坏社会治安,危害人民与国家利益。因此,领导人民坚决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⑥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十七年”文学创作中以“反特防奸”为题材的小说应运而生。“反特”小说虽然在“文革”初期一度出现停滞、萧条阶段,但是“文革”中后期再度复苏并延续到新时期文学创作中。
“十七年”的“反特”小说创作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初期以白桦的《无铃的马帮》、公刘的《国境一条街》、文达的《奇怪的数目字》等为代表,主要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复杂、严酷的斗争环境中,我国公安保卫人员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机智、勇敢地清剿敌特的反特壮歌。后期反特小说在题材上得以横向拓展,大致呈现出军队题材反特小说、城市工农业题材反特小说、农村题材反特小说、边防海疆题材反特小说四种走向。⑦由于受政治意识形态的规约以及主流文学创作模式的约束,“十七年”的“反特”小说形成了公式化、概念化的基本创作模式:“公安部门得知潜伏的阶级敌人或国外派遣的特务将要窃取某一机密文件、图纸,或引爆全国性庆典、国际交流会等会场,或是破坏某项大型工程等,于是侦察员跟踪追击,最后顺藤摸瓜,将特务一网打尽。”⑧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在十七年文学创作中成长起来的作家被剥夺了创作权利,这期间公开出版的反特小说数量寥寥。同时由于迎合、适应当时的政治形势,“文革”期间公开发表的“反特”小说与“十七年”“反特”小说相比,政治色彩更加强烈,人物脸谱化、情节模式化、冲突简单化、情感直露化的弊病更加凸显。如龚成的长篇小说《红石口》、周肖的长篇小说《霞岛》、李良杰与俞云泉合著的长篇小说《较量》等“文革”期间出现的几部比较有代表性的“反特小说”,也被一些学者称为在夹缝中生存的“夹缝文艺”⑨,都表现出艺术粗糙、政治色彩浓郁的创作倾向。汤哲声即指出这类作品“都显得粗劣雷同、形象呆板、语言干巴。这类作品对极‘左’思潮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是特殊政治条件下的文学的畸形产物。”⑩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中后期,远离政治、讲述悬疑惊险故事的反特侦探小说被疯狂传抄,代表作有《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梅花党》《火葬场的秘密》等。其中尤以况浩文创作的《一双绣花鞋》最为出名,在民间广泛流传甚至传播到了国外。
就《一双绣花鞋》的题材而言,它来自作者况浩文的一段亲身经历:1951年3月12日晚八点到第二天凌晨六点,当时在重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下属的边防保卫处工作的他,率领一支由16人组成的抓捕小组,参加“三·一三”大批捕行动,搜捕反革命分子。当晚全城戒严,口令是“镇反”,答不出来就是敌人。他们负责抓捕11人,抓捕工作进展很顺利。在抓捕完一个一贯道点传师(11)例行搜查其房间时,作者况浩文在屋角带有穿衣镜的衣柜下发现一双绣花鞋动了一下。这一幕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以至于他日后回忆起还心有余悸:“恐怕我看那双绣花鞋就两三秒钟,但这两三秒钟给我的冲击太强烈了。”(12)为了配合镇反运动要特别注意对群众的教育作用的要求,(13)此次大规模抓捕行动结束后,重庆《大公报》《新华日报》等报纸以及当地广播对清匪反霸消息进行了“长篇累牍”的宣传。这一做法引起了中央的警惕,毛泽东曾经为此事找来罗瑞卿命令召开全国公安会议,部署全面收缩,同时电告西南局等地的负责人,注意防止地方镇反扩大化倾向。(14)1958年“大跃进”,提倡群众创作。时任重庆市第二工业局(即后来的化工局)党组秘书的况浩文根据这段历史记忆挑灯夜战,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创作出了后来引起巨大反响的小说《一双绣花鞋》。
我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详地叙述《一双绣花鞋》的题材来源,是为了把它放在一个相对复杂的历史环境中考察作者是如何在艺术的真实性与虚构性之间精心构思,在“十七年”那个所谓“一体化”的特定时期,提供一套既能满足读者阅读需求又能获得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叙事方案。而如何把“三·一三”大批捕这一历史事件叙述成符合“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反特”小说,是况浩文必须解决的问题。很显然,如果完全照搬原先的故事,尽管其中不乏惊险、刺激的抓捕情节,但除了能够激起当年的情感记忆,一定会让读者感觉到单调、乏味。同时,这种故事也不可能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接纳。因为,如果完全照搬原先的故事,实际上是在暴露新中国成立初我国国内形势的严峻、恶劣,暴露我党在处理反革命分子时出现的“左”倾盲动倾向。这样处理的结果,一方面因过多描写敌对阶级的残暴、猖獗而使读者产生“心灰意懒”的恐惧心理;一方面过度渲染描写大批捕行动会让人认为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错误地判断了形势。众所周知,在“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如《红日》《红岩》《红旗谱》《保卫延安》《林海雪原》等中,作者都是把作品中的反面人物作为不同阶级、不同阵营的敌对分子而尽情丑化与暴露的。因此,既要使群众受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安全教育”,不触犯“注意防止地方镇反扩大化倾向”的政治禁忌;又要使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趣,作者就需小心操作,对原先故事有意无意地做出一些加工、改造,把抓捕行动这一政治性历史事件处理成“反特”故事。同时,对“反特”故事产生的历史背景、人物形象等重新进行大规模的建构,既使故事更“复杂”、“曲折”、“紧张”,又使小说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而取得文学合法性。
首先,根据况浩文的回忆,1951年3月12日晚八点至第二天凌晨六点在重庆市南岸区龙门浩进行的“三·一三”大批捕是一场覆盖面极大,旨在清除潜伏在该地区的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镇反运动。这样一个事件可以讲出完全不同的故事:可以叙述成新中国成立初期公安战士捣毁非法教会组织的故事;也可以严格按照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原则,讲述地方镇反大批捕运动;还可以写成披露新中国成立初西南地区特务活动猖獗的故事。可是,《一双绣花鞋》改变了故事发生的历史背景,叙述了侦察科长沈兰凭着自己的才智与胆略和我公安战士密切配合、并肩作战,在广大群众的帮助下,两次使国民党特务企图炸毁峦城实现其反攻大陆的C-3计划破灭的故事。通过改写,作者把新中国成立初期发生在西南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批捕、清剿运动,演绎成了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反特”小说,把一场进展顺利的抓捕历史反革命分子的镇反运动,叙述成我公安战线保护国家人民与财产安全、防止敌特蓄意破坏的敌我斗争。这一情节模式的营构显然属于“十七年”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工农兵”小说题材范畴。“抓特务”等惊险、离奇的敌我斗法,敌弱我强、敌藏我追的情节模式一方面满足了人们的猎奇心理;一方面淡化了新中国成立初西南地区阴云密布的恐怖气氛,配合了1950年代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出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小说也因此获得了在那个历史场域存在的政治合法性。
其次,非但情节模式,小说的英雄人物塑造以及主题思想表征如“十七年”的其它反特小说一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特征。作品中主人公沈兰是作者以公安战线上的史智明、刘同树、林念祖三个人物为原型创造出来的。(15)“史智明是原西南公安部五处一科的科长,后来调到云南任职。这是一个从平原游击队打出来的老革命,侦查经验丰富。刘同树更是二野有名的侦察英雄,浑身上下的每一个伤痕都是一段曲折惊险的故事。而林念祖在解放前是地下党,做过美军的翻译官,后在广东省公安厅侦察处任处长。”(16)小说采取“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创作原则,综合了这三个人物的传奇故事,塑造出了沈兰这样一位机智、多谋、冷静、沉着的公安英雄。
二、手抄本传抄与阅读期待
文学能否产生轰动效应与一定的传播机制密切相关,大量的传播不仅能够使文本的意义得以生成,而且可以使其声誉迅速提升。“文革”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就是通过地下秘密传抄使大量遭受主流意识形态禁止的文学得以广泛传播,尤其手抄本小说无疑构成“文革”期间地下文学社会阅读行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手抄本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一个新的文学类别,用以填充那一段书籍遭禁毁、作家被歧视和冷藏的匪夷所思的文化专制时期,整个一代文化生活需求空白的一种新类型的文学作品。”(17)对于手抄本小说产生的社会效应与文学价值,张宝瑞曾经如是评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百花凋零的悲惨境地,但是富于反抗意识、想象力的中国人不能容忍文化沙漠中长途跋涉的饥渴,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诞生于“文革”时期的“手抄本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对人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18)
虽然此说可能有些抬高手抄本小说的文学价值和思想意义,但是也的确道出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手抄本小说的特殊意义。而周京力则把手抄本的文化价值提得更高,只是他也指出手抄本的负面影响应引起注意:“手抄本是当时中国人文化精神诉求的晴雨表,是文学史中不可或缺的活化石,是重修或完整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补充,其独特的创作流播过程和顽强的表达意识,都使其赋予浓厚激越的悲剧美学色彩,但它作为双刃剑的另一极——文化专制和话语霸权严重带菌者的身份也不容忽视!”(19)从周京力带有浓郁感情色彩的言谈中,我们将会发现:一方面,手抄本在今天已经成为我们考察那个特殊年代的考古遗存。“考古遗存是由人类行为导致的某些结果所构成的,而考古学家的工作就是竭尽所能重新组织这些行为,以重新获得这些行为所表达的意图。”(20)因此,通过对这些正在流失的手抄本进行发掘、打捞,对于考察当时作者创作时的深层次文化心理、读者大众的阅读期待及社会心态无疑具有深远的意义。正如程光炜所言:“小说不仅具有观赏性审美性,也是一种史料。它是对历史的某种留影,可能还是比历史教科书更为忠实的对历史真相的记录。”(21)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当接受者重新组织这些行为,试图从手抄本文学中读出当时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诉求时,需要调动他们多少主观意义上的文化想象。也即是说,这些文学史中的活化石艺术价值如何可以暂且不论,仅仅“其独特的创作流播过程和顽强的表达意识”即可以成为打开读者丰富想象力的一扇窗户。
“文革”期间,许多人冒着危险传播手抄本小说,与当时民间形成的社会氛围、大众文化心理以及读者的“阅读渴望”有直接的关系。“建国后持续有效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规训,已成功构建了阶级斗争的中心政治话语;‘文革’前期的批斗、大串联、大规模武斗,也极大地渲染了全民革命的社会氛围。‘文革’中后期,随着运动高涨期的过去和林彪事件的发生,政治文化秩序进行调整和整顿,国家上层展开了复杂的斗争,社会上出现了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奇异想象,在民间,迷信活动也开始泛滥。”(22)朱大可曾经这样回忆道:“广泛的政治死亡引发出对生命的酷爱。民间养生运动的火焰,竟然在1967年就已被点燃。那是‘文革’最酷烈的时期,国家权力机器全面瘫痪,广场革命席卷整个中国。一些人在自杀的道路上狂奔,而另一些人却在探寻永生的秘密。解放军是养生运动的先锋。军队医生发明或推广了各种疗法,从针刺麻醉,到鸡血疗法。‘老军医’介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他们殚精竭虑,寻求健康长生的道路。他们的事迹开始越出神秘的兵营,成为引导民众生活的伟大指南。”(23)在这样一种因普遍迷惘而导致社会错位的历史氛围中,大肆传抄一些传奇类、娱乐类、社会政治类小说一方面可以填补精神的贫乏,满足大众文化需求:“1976年7月之前,手抄本比较流行。在学校的学生中,初三至高二的学生抄的人最多。当时文学作品非常少,几乎快成了真空状态,我又从小爱听故事,再加上停课闹革命不上课,空闲时间多。”(24)“当时的背景,人的生活很空虚,再说这些东西也不是太离奇,比如像《三条人命案》这些,挺适合咱老百姓的口味儿。”(25)一方面在包括许多知识分子在内的广大民众对当时思想、文化状况极为不满的背景下,既可以借抄阅行为满足一种新的阅读期待,也可以通过传抄、讲述进行新颖的文本创造以弥补因对当时公式化、模式化东西的反感而产生的审美疲劳:“第一个可能就是《绿色的尸体》,看完后心里一震,小说还有这样写的?……心里一高兴,就对自己说抄下来吧。”(26)而且,有时候把这些故事讲给听众听还可以活跃气氛,提高工作效率:“当时作为我来讲很感兴趣,因为对那些模式化、公式化的东西很反感,觉得这些东西还很有意思。我给周围人讲后他们也感到有意思,干起活来就快,干完活儿后又催我接着说。这就证明了当时在民间这些东西还是很有基础的。”(27)另一方面也可以实现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文化想象,引起对政治、人生的思索与探讨:“……它们的更为突出的共同点,乃是对社会政治与人生所作的深入思考,这种意识形态的哲理思考才是作品的核心和灵魂。”(28)同时也可以充分体验到一种“冒险”经历后的英雄情结:“……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抄的时候逞能——我胆大,不怕死人,特别是抄那些恐怖故事的时候。”(29)从这些传抄者形形色色的回忆中,可以想到在传抄、重述这些手抄本的过程中,由于随意的附加,对文本的误读、误传在所难免,而且传抄者投射其中的主观想象成分也将会色彩纷呈。同时,无论他们抱有何种心理,大量传抄手抄本对于其迅速传播无疑会起到推波助澜之效。
综上所述,手抄本小说的传抄者主要以当时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知识青年”和城市里工厂的青年工人为主。这个“传抄共同体”的社会心理,他们的阅读价值观和交流方式以及厌倦了模式化、公式化的文学创作模式的逆反心理形成了疯狂传抄手抄本小说的神话。而且,在“文革”特殊的历史语境里,人们对于阅读的渴望、阅读效率之神速超出了今天的想象。评论家朱大可曾经这样回忆:“当时我们读书非常快,通常是晚上八点左右,书被一个人送达,第二天早晨八点,书就会被另一个人取走。我往往只有十二小时的阅读时间,在15瓦的灯泡光亮下,我总是能够在下半夜之前先把全书浏览一遍,再用剩下的时间细读一些重要的章节。天亮的时刻,当我交出上百万字的大书,就像交出一个被榨空的钱袋。筋疲力尽,但心情很愉快。”(30)朱大可的回忆反映了那个年代特殊的文学传阅方式,如此迅速的阅读,无疑可以加速同一本书的传播速度。同时,可以想象一本上百万字的大书仅用半夜的时间即可浏览一遍,接受者强烈的求知欲望不能不令今天的读者自叹不如。但是,反过来说,读者阅读的精细程度也不能不令人质疑,在如此快速阅读与交流过程中,对书籍的选择更是无从想象。
其实,人们之所以如此赶着阅读很大程度上跟当时文化生活的单调、精神生活的乏味、空虚有关。“远离城市,长期缺乏文化生活,知青们的内心世界像一片久旱的土地,渴望甘露浇灌。”(31)由于“文革”时期的文化专制、政治高压和文艺匮乏,许多人开始转向对民间通俗文艺的关注,因此像《一双绣花鞋》这一类传奇性、娱乐性强的“反特”通俗类小说便较大程度地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和文化想象。“在1969年后,随着绝对权威艺术体系的全面建立,文艺生活变得极端贫乏,人民没有书读,没有文化娱乐,出现了‘八亿人只看八个样板戏’的状况。政治高压、文化专制和文艺匮乏的历史语境,促使和逼迫文学艺术向民间文艺和地下文学发展。全面的高压,促成了艺术多元化分层格局的形成。”(32)尤其是林彪事件的爆发对社会产生地震般的强大震撼,很多人面对这一轰动性的事件似乎无所适从:“这是一个全社会的沉沦时期,林彪事件的震撼使高速挺进的时代列车突然停顿,所有的乘客都不知道何去何从,于是,江湖应运而生。江湖的一大特点就是流浪,由流浪而生的岁月沧桑感,以及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33)由于知青们到处流浪、串联的生活,使得地下传抄文本渐行渐远,足迹遍及全国各地。
三、作品内外之传奇
《一双绣花鞋》的标题就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和阐释余地。上文已经提到,作者况浩文正是由于一双绣花鞋的触动而获得创作灵感的。可是如果仔细阅读文本将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文本中绣花鞋出现的频率并不是太高,而且敌我阶级之间主要是围绕C-3计划而展开斗智斗勇的战斗。所以,如果就小说的题眼或者小说氛围的营构而言,小说标题应该叫《在茫茫的夜色背后》、《C-3计划》或者《雾都茫茫》才最能揭示小说所要表达的文化内涵。其实,《一双绣花鞋》的名字正是由上述标题演化而来。既然取名《一双绣花鞋》,小说中又为何没有凸显绣花鞋的存在价值?是作者身为一名业余作者有意无意的疏忽抑或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场域里作者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这一系列悖论式的疑问无疑都将给受众提供一个百思不得其解的想象领域。
就我国文化传统而言,古代文学中关于绣花鞋的故事并不罕见,如明清及民国小说、戏剧中都有以绣花鞋为题材的通俗文本出现。而在“十七年”左翼话语盛行的历史语境下,“绣花鞋”无疑表征着一种陈旧香艳、美丽妖冶、神秘离奇且带有浓郁女性脂粉气的文化符号。而且,一提起绣花鞋自然会使人联想到女人的足部,众所周知,“女子的足部在中国古代向来被视为身体上最隐私、最性感的部位。”(34)因此,正如《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由于在智取威虎山后偷窥白茹睡觉对白茹小脚的凝视产生的“穆尔维式凝视”的男性狂想一样,在“十七年”、“文革”那个谈性、谈情色变的特殊历史语境中,《一双绣花鞋》这一标题便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受众对于“女体”、“香艳”等符码的都市消费性文化想象。如果说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眼中的这幅‘美人冬睡图’透露的趣味,尤其是‘肉体的底下部位’(巴赫金语)——‘两只净白如棉的细嫩的小脚’在‘少帅’身上引发的不可遏止的‘思欲’显然已超出了‘精神恋爱’的范畴。”(35)《一双绣花鞋》这一题目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它不仅体现出“反特”小说中残留着的未完全被主流意识形态“擦抹”掉的传统因素,而且一定程度上使政治色彩、“反特”主题得以削弱、淡化,相应地使言情色彩得以彰显,从而在“文革”期间革命叙述话语充斥文坛的文学场域中,最大程度地满足了读者的猎奇心理与文化想象。与此同时,它也凸显出“反特”与另一种“民间”——非文人化的乡土、市井文化之间的联系。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说“《一双绣花鞋》是乡土的和怀旧的。”
有意思的是,小说曾借助沈兰略带感伤的深沉回忆设置了许多带有世俗色彩的现代都市场景。如第十八节一开始就为读者营构了一个极具西方现代化情调的生活场景。
灯红酒绿,笑语声喧,男男女女,在刺耳的爵士音乐伴奏下,翩翩起舞,丑态百出。
……舞厅内不时传来黄色歌曲《荡妇心》的音乐声。(41)
这样的场景显然也是有违当时文学的叙事成规,而且爱情的描写更是当时文学表现的禁区。众所周知,新时期以“重放的鲜花”出现的一部分作品如宗璞的《红豆》、陆文夫的《小巷深处》、刘绍棠的《西苑草》等之所以被打成毒草正是由于其对爱情题材的描写。在“十七年”尤其是“文革”时期,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舞厅生活属于腐朽、堕落的具有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活模式,也正是这样的生活环境滋生了林晶沉迷于自我享受的人生态度,并且大胆向沈兰表达爱慕之情。
如果说舞厅场景还带有对于爱情观、人生观的辩论性质,第十九节山城闹市的场景则展示了一个光怪陆离、充满色情想象的历史场域与文化语境:
霓虹灯光闪烁,黄色音乐声喧。
朱玉宛和沈兰在人流中,观看着光怪陆离的闹市。商号打着不顾血本,大减价的巨幅广告,橱窗里摆满了美国克宁奶粉、玻璃丝袜、乳罩、月经带,污七八糟什么都有。……
这里显然是对解放前夜重庆城市堕落、萧条、混乱生活场景的揭露,然而,这样的场景则是有意无意地以“另类”的姿态展示在受众面前。而且,此处列举的许多商品如美国克宁奶粉、玻璃丝袜、乳罩、月经带等等在今天看来无疑是消费文明的现代表征,而在“文革”期间却被作为“毒素”严加禁止。而追求时尚的生活模式,是“文革”期间民间被压抑着的强烈渴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说一方面令读者在充满世俗化的语境中满足了一种对于色情文化的窥视欲;一方面通过对美国商品的罗列勾起了读者想说然而又不便于言说的对于西方时尚生活方式的向往。小说也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了重庆广大市民阶层的生活面影,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意识形态、道德风尚、娱乐需求与文化消费心理。
就文本外部而言,作者况浩文以及小说本身都带有一定的传奇色彩。况浩文创作出《一双绣花鞋》以后,把它寄到重庆出版社,因编辑王文森已经被下放劳改,后来又把小说寄到《重庆日报》,受到著名作家沙汀的肯定与鼓励。沙汀把小说转交给重庆市文联秘书长王觉,当时,无论沙汀还是王觉,都担心原稿中一号人物沈兰的塑造有些违反当时的禁忌。王觉把小说转交给《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征求意见,罗广斌认为很容易修改。小说原稿写沈兰因在嘉陵江救出特务头子林南轩的女儿林晶,沈兰在上级的指示下利用林南轩对他的赏识使用“美男计”打进林府。身为白马王子,沈兰一方面得到林晶的爱恋,一方面因“战友”关系与林家的使女——共产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卧底之间产生感情。后来经罗广斌、王觉、沙汀商议决定帮助作者对原作进行修改,把一号人物沈兰塑造成从爱国主义思想转变成共产主义思想并在特殊战线上立功的典型人物。只是,小说还没有来得及修改成功,“文革”爆发,《一双绣花鞋》被认为是散发资产阶级情调的灰色小说,是“大毒草”,并且由于与“文艺界黑帮黑线”沙汀有过一面之交,况浩文很快被划成“黑线人物”。此时,罗广斌则说他当时看了原稿,就发现作者写了敌我不分的三角关系,而且宣扬了反动的法西斯主义的哲学来源的尼采思想。他还认为,文联的组织路线大成问题,通过沙汀、王觉对况浩文及其作品的重视,可以看出文艺界领导人不突出政治的问题。(36)“文革”期间在小说被禁止后,因传抄《一双绣花鞋》,有被罪的,有被关“牛棚”的,有被“群众管制”的,有被开除团籍的,有被扣罚奖金的……
“文革”结束后,电影文学剧本《一双绣花鞋》在1979年复刊后的《红岩》杂志第一期刊出后,一时间洛阳纸贵,群众争相购买、传阅,杂志一再加印,最后印数高达23万。而且,《一双绣花鞋》被改编成电影、戏剧等在各地上映引起巨大轰动,据珠江电影制片厂在1979年对国内10家报纸做的统计,当时一段时间内国内上演根据小说改编成的剧本《一双绣花鞋》的剧团竟达70多家,剧种接近10个。1980年由况浩文编剧的电影《雾都茫茫》作为当年重点影片向全国发行。随后又拍成电视连续剧《C-3计划》。四川人民艺术剧院将《一双绣花鞋》改为话剧在成都上映后,连映两个多月场场客满,有的观众为了买到戏票,甚至搬了竹躺椅,通宵达旦在剧院门前躺着等待售票。由于《一双绣花鞋》名气非常大,许多商人瞅准商机大肆炒作,于是有了“绣花鞋副食店”、“绣花鞋俱乐部”、“绣花鞋茶楼”等等。不难看出,作为通俗文学,《一双绣花鞋》不仅在“文革”期间引起巨大反响,在新时期依旧产生了轰动效应。同时,不难发现在轰动效应的背后有多少想象、臆测、误读、篡改,利用“绣花鞋”的成分隐藏其中。可以说,《一双绣花鞋》不仅为一代人打开了一扇驳杂、纷呈的现代想象与情感记忆的窗户,而且预示着一个消费文化时代的提前出台。
综上所述,就作者对“镇反”故事的历史重构以及不断被传抄而形成的文本内部而言,小说实际上是在用“工农兵”文学的筐装具有“刺激性”、“神秘性”、“世俗性”效果的“反特”故事与言情故事,用以“党性”与“国家、人民利益”为重的革命文学来演绎通俗文学的核。正是这一点上,《一双绣花鞋》一方面通过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独具一尊的“左翼”文学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对接;一方面满足了普通读者的猎奇心理与文化想象,在“革命文学”与“通俗文学”之间找到了较为宽广的生存空间。同时,根据斯蒂文·托托西的说法,“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37)
通过对《一双绣花鞋》产生轰动效应的爬梳可以发现:其之所以产生如此大的轰动效应并不全部是文学机制运作的结果,而是有许多“非文学”因素参与其中。它与“文革”的爆发、读者的阅读期待、文化想象的驳杂、社会心理的调整、商业的炒作、影视改编等等社会因素纠结在一起,共同形成了小说的轰动效应。
注释:
①④⑤(12)(14)杨敏:《“绣花鞋”背后的“镇反”大批捕》[J],《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第5期。
②赵晓玲:《艰难的言说》[A],见况浩文《一双绣花鞋》(序言)[M],第1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7月。
③马拉:《童年跑过春森路——〈一双绣花鞋〉和我们》[A],见况浩文:《一双绣花鞋》(附录)[M],第335页,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年7月。
⑥周恩来、沈钧儒:《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J],《福建省人民政府公报》,1950年第7期。
⑦⑨高涧平、张子宏、于奎潮:《中国当代公安文学史稿》[M],第106页,第134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9月。
⑧任翔:《文学的另一道风景——侦探小说史论》[M],第189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1月。
⑩汤哲声:《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M],第24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11)解放初,一贯道是最大的会道门组织,据称仅北京就有20万人之众。1951年10月,一贯道被宣布为反动会道门组织,与土匪、特务、恶霸、反动党团骨干一起,成为镇反运动的五方面打击对象之一。点传师在一贯道中位居第五,属于上层。
(13)1950年10月10日,毛泽东亲自主持通过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明确要求:对于这些案件的执行,必须公布判决,在报纸上发布消息(登在显著位置),并采取其它方法,在群众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
(15)(16)参见徐恺:《〈一双绣花鞋〉作者的奇异人生》[J],《晚报文萃》,2004年第4期。
(17)(19)周京力:《长在疮疤上的树——对“文革”手抄本的一次总结与表达》[A],见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M],第16页,第17-19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月。
(18)李彦:《张宝瑞:手抄本是种反抗》[N],《北京青年报》,2004年2月2日。
(20)[英]戈登·柴尔德著,方辉、方堃杨译:《历史的重建——考古材料的阐释》[M],第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7月。
(21)程光炜:《为什么要研究七十年代小说》,未刊。
(22)肖敏:《“文革”地下手抄本小说的话语特质与传播机制——以传奇娱乐类小说为中心》[J],《南都学坛》,2009年第4期。
(23)朱大可:《记忆的红皮书·三1967年的鸡血传奇》[J],《花城》,2006年第3期。
(24)周京力、某木先生:《在坟头上抄手抄本最容易进入情节——与当年手抄本收藏者的对话》[A],见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M],第37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月。
(25)(26)(27)(29)周京力、田先生:《无意中留下了这些手抄本——与当年手抄本收藏者的对话》[A],见白士弘编:《暗流:“文革”手抄本文存》[M],第31页,第37页,第33页,第38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4月。
(28)杨鼎川:《1967:狂乱的文学年代》[M],第131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5月。
(30)《少女之心:70年代“黄色手抄本”的性启蒙》[DB/OL],“搜狐娱乐频道”http://cu.l sohu.com/2008091 5/n259567503,shtml。
(31)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M],第128页,济南:朝华出版社,1993年1月。
(32)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M],第161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
(33)张明策划,廖亦武主编:《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M],第180页,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9年2月。
(34)(35)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M],第20页,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
(36)参考甘犁:《〈一双绣花鞋〉出版前的风波》[J],《龙门阵》,2006年第1期。
(37)[加拿大]斯蒂文·托托西著,马瑞奇译:《文学研究的合法化》[M],第4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8月。
标签:一双绣花鞋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论文; 镇压反革命运动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读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林海雪原论文; 况浩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