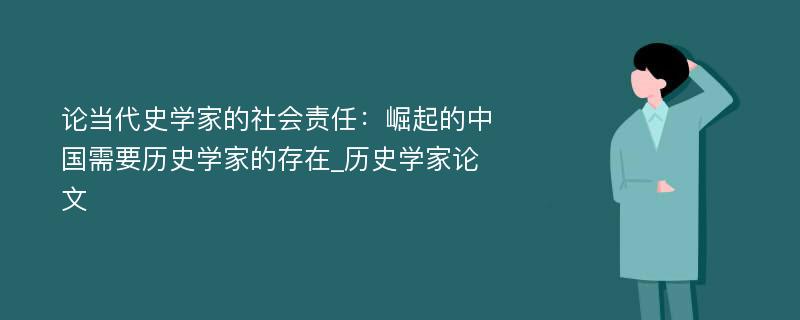
“当代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笔谈——崛起的中国需要历史学家的在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史学论文,历史学家论文,中国论文,工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崛起是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之一。这一崛起与其说是物质财富的暴增,毋宁说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复兴。这一复兴在中国文明史乃至世界文明史上的巨大意义已经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话题,已经跨越学科的边界,几乎成为国内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话语中心。众多人文社会科学,都在通过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和思考,积极参与这一重要的历史进程。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众声喧哗当中,唯有历史学家缺席。无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对中国崛起的讨论如何热闹,史学家们好像都无动于衷。实际上,最不应该成为中国崛起看客的就是史学,因为文明的复兴,仰赖于历史的被唤醒,而史学家担任着现在与过去之间的唯一中介;在中国崛起的进程当中,史学家们最有资格、也最应该成为积极的一员。绝不能因为历史学面对的是静寂的历史,就有理由躲避火热的现实。史学家完全应该也能够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必须明确,在中国文明复兴的挑战中,历史学家肩荷着特殊的重任。这是生活在大时代的史学家的宿命。衡量当今中国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无疑有多重维度,在我们看来,至少有两种责任不可回避:构筑能够解释中国的宏大理论;更紧密地关注现实。
构筑有关历史的宏大理论是崛起的中国对历史学最大的也是最紧迫的要求。宏大理论是一个国家知识体系的压舱石,代表着一个国家理论思考的深度。历史的宏大理论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其自身发展历程的深刻自觉。国家需要历史理论告诉自己从哪里来、长时段社会形态如何演变、何种动力在推动历史发展以及为什么只能这样演变和发展。只有弄清这些问题,才会明了国家和民族到哪里去。一个对这些基本问题处于懵懂状态的国家,无法看清历史大势,因而也就无法找到超越兴乱周期、实现持续繁荣之道。大历史呼唤大理论,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大的社会转型一定会推动历史宏大理论的诞生。西方的宏大历史理论,完全是建立在15世纪以来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之上的。中国现在进行的转型,是在一个有着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十数亿人口的大国中进行,无论在规模上、深度上还是在典范性上,这一转型都绝不亚于西方。因此,中国社会的大转型,也一定能够催生规制恢宏、统摄全局的宏观历史理论。这是历史发展本身对中国历史学发出的律令。
我们必须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有关中国历史的宏大理论建设目前还处于徘徊阶段。1902年新史学诞生之前的中国传统史学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运行其中的是传统的天道观念;1949年后,中国历史为西方话语所笼罩,为西方程序重新编码;改革开放之后,理论建设并未改变“被殖民”的状态,仍然是从西方引进名词、概念、话语体系,毫不犹豫地以它们为准绳,来衡定中国,改造中国,甚至“漠视中华文明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宏大文明独立存在与不断发展所固有的意义和价值,根本不承认或很少考虑在观察传统中国、中国传统及中国路径时,需要建立一种和近代西方文明不完全一样的甚至很不一样的独立的坐标系统”(姜义华:《走出思想上文化上的“被殖民”》,《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所以,自从中国现代史学诞生之后,有关中国历史本身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并没有在高度自觉的前提下得到系统的不受干扰的清理。“五种生产方式”说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口径受到质疑之后,替代概念和理论框架的建构迟迟得不到突破性进展,是中国历史研究最大的无奈。重回中国历史本体的研究,让中国历史的躯体挣脱西方话语的“洋马褂”的捆缚,使中国史重返中国,推动国人在中国史实的基础上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时序与规律,是中国史学的当务之急。
应该看到,微观史学的盛行,客观上削弱了史学界探讨宏大历史问题的兴趣。走向微观研究,是近二三十年来世界史学界的潮流,中国史学也步其后尘,微观史研究大行其道,导致许多人因此生出“史学碎片化”的担心。应当承认,微观史的兴起,是对过去那种不切实际、更多带有意识形态钳制意图的宏大叙事的反叛,但有一点必须牢记,西方微观史学和中国微观史学完全是在两种不同的学术背景下进行的。西方的微观研究以崛起于18世纪、19世纪的宏大叙事为参照,这种对微观史的强调,并不能撼动宏大叙事的框架和价值观,这从后现代史学的迅速退潮可得到证明。在很多方面,微观史是对宏大叙事的调整与补充。但是,中国在知识体系上从来就没经历过一个源自本土的宏大叙事阶段。所以,中国史学并没有放弃宏大叙事的资本。曾经统帅中国历史学几十年的“五种生产方式说”只是对欧洲宏大叙事的拷贝。近年来日渐活跃的微观史学,其深层原因实际在于“五种生产方式说”遭受质疑后,没有一个统摄全局的宏大理论可供依凭。史家各自专注于某一特定历史题材,只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是当前中国史学的基本生态。
西方中国学的兴盛也反衬出国内史学缺乏理论建构的尴尬。上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中国学提出的理论一直在中国史研究中推波助澜,一些有关中国历史的重大命题,多由西方中国学提出。施坚雅的“区域经济理论”、萧公权与周锡瑞等的“士绅社会”理论、罗威廉的“市民社会”理论、黄宗智的“经济过密化”分析、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及乡村基层政权“内卷化”的研究、艾尔曼的“文化资本”解释方法、彭慕兰的“大分流”理论等各领风骚,在在为缺乏理论建构能力的国内史学界所艳羡。西方中国学对中国历史研究的开拓性贡献表明,理论能够给中国史研究带来多大活力,理论建构对于拓展中国史研究的空间是何其重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由于受到“学问家凸显,思想家淡出”风气的影响,太多中国史学工作者斤斤自守于考证之学,以接续民国新考据学统为治学之最高境界。这一点从胡适、傅斯年、陈寅恪等人所受到的追捧就可看出。必须承认,拘泥于考证,无法对中国历史作出宏观性解释。
对许多中国史学工作者来说,对宏大叙事的排斥,已成为矜夸其职业素养的标志。但在西方主流学界,并不存在这种刻意回避宏大叙事的做作。近年来,美国史学家已开始纠正对宏大叙事的疏离,试图重建新的宏大叙事体系(参见程群:《宏大叙事的缺失与复归——当代美国史学的曲折反映》,《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全球史的兴盛,也反映了历史学构筑新的宏大叙事体系的努力。像大卫·克里斯蒂安这样的史学家,已经把研究领域扩展到整个宇宙,时间范围扩展到100亿年到200亿年之间。在他看来,“在历史学科中,像是在任何学科一样,如果想理解细节的含义,理解它们是如何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必须有超越细节的眼光。如果要搞清我们学科任何一个部分的来龙去脉,我们就需要构建大的图景”(大卫·克里斯蒂安:《为“大历史”辩护》,夏继果、杰里·H.本特利主编:《全球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而在历史学界之外,宏大叙事的论述进路仍然倍受重视。弗朗西斯·福山在新近出版的《政治秩序的起源》第1卷中就以罕见的学术雄心展示了宏大叙事的抱负。书中所展现的大视野、大线条、大模式,使得该书甫一面世,就引起世界学术界普遍关注。在该书中,福山从渺远的史前起步,对人类数千年政治制度的历史起源和政治衰颓进行了全程考察,对人类漫长历史进程中现代政治秩序的形成过程进行了全景般的追索。这一学术考察,纵贯数千年,覆盖东西方,几乎古往今来所有重要国家都被纳入研究框架。福山意欲从宏大的历史进程入手,深度透观政治秩序得以形成的深层机制,凸显政治发展的进化规律。这一努力被学者称为“超级宏大叙事”,“绝对是极度推高了的宏大叙事”,“不是一般不关注因果关系与普遍规律的历史学家所可承担”(任剑涛:《为现代政治秩序背书》,《东方早报》2013年1月20日)。因此,必须克服那种人云亦云式的对宏大叙事的嘲笑,从更宏观的角度和层面来透视中国,解释中国。
美国历史协会主席里德曾经说过,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在于为当前解释过去。马克·布洛克也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这不仅是说现实可以帮助历史学家们认识历史,更重要的是,史学家们必须关注和回应现实所涌现与提出的问题。这是当今史学家们所承担的更重要的社会责任。
中国的崛起,并不光是如歌的行板,里面贯穿着一系列颇具张力的冲突和矛盾,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改良、趋新与守旧、危机与转机、压制与反抗、价值与历史、沉沦与救赎等诸种对立因素存在激烈的对抗。改革在今天所遭遇的困境,已经显示出诸多历史负面因素强大的惯性对中国崛起的牵制。这些都逼迫着人们到历史里寻找智慧。现实的需要,决定着哪些历史将被唤醒,哪些沉默不语的文献将重新开口说话。克罗齐对“历史”和“编年史”所作的区分仍然值得史学家警醒。在克罗齐看来,历史是活的历史,编年史是死的历史;历史是当代史,编年史是过去史。一切历史当它不再被思考,而只是用抽象词语记录,就变成了编年史。能否体现现实关怀,决定着你所书写的是“历史”还是“编年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现实的热忱,决定着史学家所提供的历史认识的温度。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重大的理论命题,然后从历史的角度进行探索,是当今史学家无法推脱的使命。福山对中国政治史的研究能够给我们以很好的启示,他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第一卷中用大量篇幅考察了中国政治史,其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提出这样的问题:现代政治制度由强大的国家、法治、负责制组成,中国今天在经济上迅速增长,但三条之中只拥有一条,即强大的国家,这样的情境能否长久?没有法治或负责制,中国能否继续维持经济增长,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增长所引发的社会动员,到底受控于强大的威权国家,还是激起对民主负责制的强烈追求?国家和社会的平衡长期偏向于前者,如此社会能否出现民主?没有西式的产权或人身自由,中国能否拓展科学和技术的前沿?中国能否使用政治权力,以民主法治社会无法学会的方式,继续促进发展(参见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72页)?这些问题关涉重大,每一个问题的回答都关系到中国的现状与走向,而所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探讨都必须从历史出发。
能否针对现实提出重大理论命题,不仅考验史学家的智慧,还决定着史学能否回到学术舞台的中央。当前中国史学家面对的一个尴尬是,除少数史学家外,很少有历史学家参与到今天的舆论议程,一些重大问题,更多是法学家、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在探讨,很少有历史学家参与其中。比如,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一直是热点话题,但参与这一讨论的多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本来,所谓中国模式,其根本是对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总结,历史学家是最有资格探讨这一话题的群体。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对这一模式的型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很少有历史学家从此入手进行讨论。如果说放逐现实、回避问题可以代表1990年代学风的话,历史学界汉学心态的弥漫则可看作其中的典型。为历史而历史成了不少人的追求。史学界很少提出能引发大的学术讨论的话题,甚至引起轩然大波的“告别革命”说这一典型的史学话题,也是由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提出的。面对现实,一些史学家选择了自我放逐。
史学家对现实关注的弱化,当然也与现行学术制度有关。其中,基金和课题对学术的规制尤其突出。出于功利性考虑,基金和课题总是要贯彻集团和组织自身的意志。基金和课题的投放,实质上是对学术的征用。在现行体制下,基金和课题成为学术研究的指挥棒,越来越多的学者围绕基金和课题打转转,于是,猜度和迎合学术研究组织者“圣意”,满足基金和课题的期许、甚至取悦于组织和集团,就发展成为学者的自我约束。学者忙着追逐基金和课题,就无力把眼光从充满诱惑的经费身上转移到现实生活上来,从而也就丧失了真正的创造力和批判力。争取基金和课题,成为学者躲藏在由此带来的实惠背后而回避现实问题最好的借口。基金和课题对学术研究的规制越来越具有体制性,后人究竟如何评价这段由基金和课题主导的学术史,值得人们思考。
据实而论,今天谈论历史学家的社会责任不免有几分难为情。史学在今天中国的影响力,不单单无法与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门类相提并论,即使与哲学、文学等人文学相比也已落下风。哲学已通过理论上的新陈代谢融入国际主流话语,文学则以诺贝尔奖证明了其所取得的进步。唯有史学,特别是历史理论,至今仍处在“文革”造成的巨幅震荡之后的盘整阶段,甚至还滞留在“亚文革状态”。造成中国史学今天窘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社会责任感的弱化是重要原因。古语云:“器大者声必闳,志高者意必远。”史学家的触角应该尽快探出书斋和书院,有力回应社会现实对他的期待,如此,才会改变一段时间以来被边缘化的遭际,重新赢得知识界的尊重。
【作者附记】本文是在郭震旦博士的帮助下草拟而成。震旦不仅提供了文字初稿,而且,文中所提出的微观史在东西方史学界的不同作用、近一段时间来的学术史基本上由基金和课题所宰制,这两个富有学术含量的判断,也属震旦的发现。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