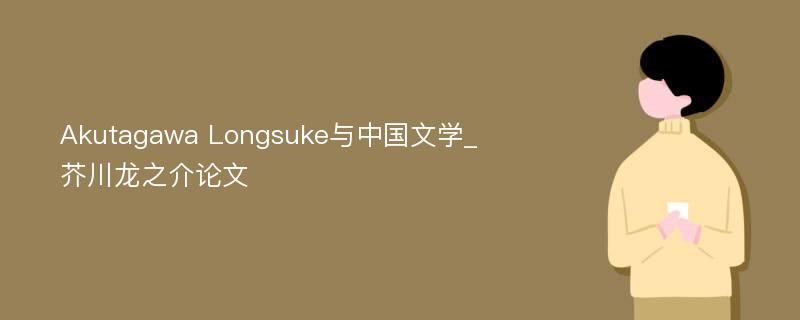
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芥川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研究日本近代作家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课题,芥川龙之介占有重要地位。把握他的创作与中国文学关系必须放在他创作的总体框架中考察。他取材中国古代典籍写作的小说有许多篇章对原作素材作了创造性的改造,充满了现代意识,匠心独具。但是,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文化观主要来自中国古代文化典籍,是理念的,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并没有继续跟踪中国现代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产生一种断裂,与头脑中的中国文化沉积形成一种反差,接触中国现实后自然要产生“误读”,也是一种失落感,因而对于现实中国的认识难免片面。这种现象在其他日本近代作家身上亦有不同程度表现。
研究日本近代作家与中国文学关系这一课题,芥川龙之介(1892—1927)占有重要地位。菊池宽在评论芥川龙之介的创作时说过:“像他那种兼备很高教养和高雅趣味,以及和汉洋的学问的作家,今后将不会有。他从集悠久的和汉传统和趣味,以及欧洲的学问于一身的意义上说,该是过渡期的日本代表性作家,因为在我们下一个时期,将不会有和汉的正统的传统和趣味表现于文艺中。”我们研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一方面可以加深对芥川龙之介的深刻认识,同时也可以从芥川与中国文学关系中探讨经过明治时代日本文学与西方文化的交融之后中国文学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的变化和走向,这对于认识中日现代文学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一
芥川龙之介于明治25年(1892年)3月1日生于东京,是新原敏三的长男。在芥川龙之介出生八个月后由于母亲精神失常,将他寄养于外祖父、母家,养父(母亲的兄长)虽然经营土木业为主,但是这是一个充满文化氛围的家庭,这对芥川以后的文化教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芥川从很小就接触了汉学,他7岁入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 汉学和习字等课程,汉学书籍主要有《日本外史》。他在10岁时就读过《西游记》的日本翻案之作《金毘罗利生记》和帝国文库本的《水浒传》等著作。在中学时代,他学业优秀,特别在汉文方面出类拔萃,对于汉诗也饶有兴趣。在高校进入大学期间,他倾心于中国小说,读过明初的《珠邨谈怪》、《新齐谐》、《金瓶梅》等作品。从这时起他立志成为汉文学家或英文学家。
同时芥川出于夏目漱石门下,他的成长自然受到漱石的深刻影响,正如吉田精一所说:“芥川作为漱石的弟子是受漱石影响很深的一位作家,因此漱石对其影响很大。……芥川、久米等人,在大正四年冬拜识漱石山房,从漱石那里受到的人格影响是很大的。漱石不仅是他英文学方面的前辈,而且在俳句、汉诗、南画方面也是颇有造诣的,芥川在这些方面均具于一身,可以说在漱石门下他是从其师所学最全面的一人。”〔1〕
芥川龙之介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主张抓住现实的片断来解释生活的真实;从生活表面的伟大和美中去发现平凡与丑恶。芥川龙之介作为这一流派的重镇,他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发挥个性特色,作品多选取平凡的琐细生活小事,重视心理和感情的细腻描写,而且十分看重技巧,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我们研究芥川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不能不从这一整体概貌来把握。
在芥川本人的文学观中曾明确论及东西文化交融这一重大问题。他说:“近代的日本文艺横的是模仿西方,纵的则是植根于日本土壤志在表现自己的独立性。”(《僻见》)芥川从事创作的时代已不同于他的前辈夏目漱石和森鸥外,日本文化在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已经历了几十年光景,在芥川龙之介身上体现了对西方文化的比较全面、深刻的理解与消化,较比前人更为成熟。他曾很透辟地谈到“影响”问题:“在艺术上透彻理解之时,模仿几乎是没有的。自他融合之后自然开放的花朵乃是一种创造。如果硬要寻找模仿的痕迹,古今作品不能说有全然皆新之作;但是,寻究其独创性的根基,古今之作又绝非能说成是旧作。”(《僻见》)从这里可以窥见芥川龙之介对于接受域外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融合创新的深刻性。
芥川重视传统,他清醒地意识到任何后来人都不能完全超越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只有在巨人的肩膀上站得更高。他曾在评论《十根针》里这样说:“我们未必就是‘我们’,我们的祖先还在我们身上存活,如果我们不顺从存在于我们之中的祖先,我们就要陷入不幸。佛教上所说的‘过去的业’这句话可以说是对这不幸作的比喻得很好的说明吧。‘发现我们自身’即是发现我们身上的祖先。同时我们也是发现支配于我们的天上的诸神。”
另一方面他具有一种超越西方文化的姿态。芥川是位学者型作家,他对于西方文化是有深刻钻研并有独到见解的。代表西方文化最基本特色的《圣经》,芥川作过刻苦的研读。他在《西方之人》(即指基督—原注)中全面地阐述了一位东方学者对《圣经》及西方文化的认识,在今天看来犹有新意。他敏锐地指出作为东方的日本人在接受基督时是以自己的视角、感受来塑造基督形象的,从接受美学角度来说,不同的接受者具有不同的接受屏幕。“……我只从我的感受的样子来理解‘基督’,最严格的日本的基督教徒对于卖文为生之徒而写的基督的东西恐怕也只好采取宽容的态度吧?”
芥川生活、创作的主要年代是西方各种文艺思潮纷至沓来之时,作为最有文化教养的学者,他接受着方方面面的影响。他曾经这样描绘自己“……我在气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在人生观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固然我们不能以芥川自身所言来判定芥川,但是,在芥川身上反映出的非常现代性的特点是我们理解芥川作品所不可忽视的。芥川在纷彩多呈的艺术潮流中力求独立,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他在《艺术与其他》一文中指出:“为艺术的艺术,一步不慎即堕为艺术游戏说;为人生的艺术,一步不慎即会堕为艺术功利说。”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具有这种眼光不能不认为是有独到见解的。我们今天研究芥川龙之介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对于这种背景是不能无视的。
在芥川龙之介的作品里所涉及到的中国文学(大至文化)的具体篇章是不胜枚举的,他在许多作品、评论中运用自如,这些材料自然可以称作是他与中国文学关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在同一作品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芥川对于西方文学(大至文化)典籍的引用亦不逊色于对中国文学的运用。为此,这部分内容似乎不必硬行剥离开来,它们统统都是芥川文化人格的血肉组成。本文试图通过以下两个方面来看取他与中国文学关系的特色:(一)他以中国文学作品或文化典籍为素材而创作的作品。(二)芥川访华后接触中国现实而写的纪行文字所体现的中国文化观。而且这二者又是他整个创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是把它放在芥川整个生活历程中来考察,使它有可能更切近芥川的实际。
二
芥川龙之介直接取材或直接以中国作为背景而创作的作品是比较多的,在他的整个创作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仙人》写于1915年,取材于《聊斋志异·鼠戏》;《酒虫》写于1916年,取材于《聊斋志异·酒虫》;《掉头的故事》写于1917年,取材于《聊斋志异·诸城某甲》。《女体》,这是一篇虚构的作品,以中国人杨某为主人公,通过他观察虱子在妻子乳房的爬行,实质上谈的是审美的问题,可以说这是篇寓言小说,本文写于1917年。《黄梁梦》创作于1917年10月,取材于《唐代传奇·枕中记》。《英雄器》亦创作于1917年,取材于《两汉通俗演义》。《尾生之信》写于1919年,取材于《庄子·盗跖篇》等。《杜子春》写于1920年,取材于《太平广记·杜子春》。《秋山图》创作于1920年,是以元明清画家轶事为素材而创作的一篇短小的作品。《奇遇》写于1921年,取材于《剪灯新话·渭唐奇遇记》。
芥川的这些取材于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或典籍或设定中国为舞台而写作的小说从广义上来说均可归入历史小说范畴。对于这类作品有的日本研究家指出:“它们只不过借历史的舞台而已,目的并不在于再现‘往昔’。”〔2〕对于这类作品褒贬不一。有人认为是翻案之作, 意义不大,价值不高;有人则认为很有新意,价值很高。如果卒读这组作品,对照所取材的中国文学原作,我们不能否认,在一些作品中芥川是匠心独具的。虽然基本情节与原作相同之处颇多,但是在立意和写作技巧上是芥川所独有的,这种创造主要不是体现在变动的文字的量上,而是在质上。当然,勿庸讳言,有些作品未必说成杰作,价值并不很高。我们不妨以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来剖析一下芥川这组作品的基本特点。
《杜子春》是芥川这类作品中的佼佼者。《杜子春》的素材见于《太平广记》(宋李昉等撰),最早的出处是唐李复言的《续玄怪录》。在原素材里的同名主人公杜子春是周隋间人士。“少落拓不事家产然以志气间旷,纵酒闲游,资产荡尽,投于亲故,皆以不事事见弃。”在他走投无路时遇一仙人,先赠三百万缗钱,荡尽,复赠千万,又挥霍尽致。第三次赠三千万,杜子春以此钱扶贫济孤后约见仙人,仙人引他入华山授以仙法,但戒曰“慎勿语,虽尊神恶鬼夜叉猛兽也地狱及君之亲属所困缚万苦皆非真实,但当不动不语,宜安心莫惧,终无所苦,当一心念吾所言。”但是,杜子春终究破了戒,破戒的原因是他托生为一名美丽的哑女,嫁与卢珪为妻,生一子“仅二岁,聪慧无敌”,但不能语,卢生大怒,持儿两足,以头扑于石上,应手而碎,血溅数步。子春爱生于心,忽忘其约,不觉失声。”原作的结尾是这样写的:“吾子之心喜怒哀惧恶欲皆忘矣,所未臻者爱而已,向使子无意声吾之药成,子亦上仙矣。嗟乎仙才之难得也。吾药可重炼,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勉之哉,遥指路使归。”“子春既归,愧其忘誓,复自效以谢其过,行至云台峰绝无人迹,叹恨而归。”
在这篇小说里似乎是从正面阐述成仙之难,爱心难除,这一方面可以说是肯定了人类之爱,但从杜子春的慨叹又有一种未能成仙的惆怅,从立意上来说又削弱了这一主题。对于这一作品为何出现这种矛盾的品格,我们尚可深入探讨。
芥川龙之介依据这一素材而创作的同名小说可以说是反其意而行之。在芥川作品里反复出现的是对“世间人情之薄”的批判。当杜子春荣华富贵之时则门庭若市,一片阿谀奉承之声。但是,当他千金散尽,沦落之时,则“昔日友人经过门庭前连个招呼都不打”。两度旧戏重演,使他失去了对人类之爱的信心。可以说杜子春陷入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这是杜子春想摆脱尘世欲成仙人的出发点。于是在铁冠子(吕洞宾)的指引下经历了另一个世界的游历与考验。按照铁冠子的戒条,他所必须摒除的是一切人欲。杜子春牢记仙人的指教,甚至在阎罗命令小鬼鞭打变成了马的父母,看见他们“眼里流着血泪,目不忍睹地痛苦地嘶叫”之时也仍然坚持着。但是,“这时在他的耳边,传来几乎听不到的声音:‘你不要为我担心,不管他们怎样我们,只要你能幸福,这就比什么都好。不管阎王说什么,千万不要吱声,保持沉默。’”
“这千真万确是母亲的声音……杜子春终于忘记了老人所告诉的戒律,踉踉跄跄地跑到那一边,两手抱住半死的马的脖颈,眼泪哗哗地流下,叫了一声‘妈妈’。”他终于破了戒,没有成为仙人。
对此杜子春并无悔意。“不管我如何想成为仙人,但是面对在阎罗殿前受鞭打的父母,我是怎么也不能沉默不语的。”而对于这一破戒,仙人是这样回答的:
“假如你真的沉默不语,我想你就会立即失去自己的生命。”
最后杜子春下决心弃绝成仙的念头,“无论如何都想过一种正常人的生活”。在这里与其说是杜子春的选择,莫如说是芥川对现代人哲理的思考。芥川深刻理解现代社会的人类的苦恼,作为人生是酸甜苦辣俱全,如果除去这些,人生就会成为一片空白,并且也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这反映了芥川对现代社会苦难的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超脱。
反映在作品里的另一点是芥川的“恋母情结”。芥川是位没有享受过亲生母亲的母爱的人,这成为他作品里反映出的一种潜在的意识。有的研究家指出:“当杜子春在地狱里抱着的是半死的母亲变成的马的脖颈,而把父亲除外,必须注意到的是母亲发出的几乎听不到的微弱的声音的直接表现,确实是母亲的声音亲切地传到了他的心田。”〔3〕这里突出的是母亲对子女的那种无偿的爱,这不能不与芥川对于生下他八个月后精神失常的母亲的呼唤,“呼唤母亲的声音经常从他心底里涌出。”“作品里呼唤母亲的声音是从芥川心里的声音导出的。”〔4〕这一见解是很中肯的。这种情结在一篇写得很欢快很抒情的小说《桔子》里亦有体现,那是写一个外出当佣女的女孩对于自己弟弟的疼爱的抒情曲。
同时在芥川的《杜子春》的结尾所勾划出的理想境界似乎又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的理想国有着一种关联,这也是原作所不具备的。从上面这种主题的变奏,我们可以说芥川的《杜子春》已是非常现代的作品,它只不过是借用中国典籍的衣衫而已。
我们再比较一下芥川的《酒虫》和《聊斋志异·卷五》的同名作品。乍看去这两篇作品没有大的差异,芥川只是在作品中增设了孙先生、僮仆两个次要人物,这是为了体现小说故事情节的曲折性而设计的。原作讲长山刘氏嗜饮,每独酌辄尽一瓮,一番僧见之,谓其身有异疾,即有酒虫。僧让他在“日中俯卧,挚手足,去首半尺许置良酝一器。”刘氏嗜酒如命,美酒的诱惑使刘氏体中的酒虫终于跃出体外,扑入酒瓮之中。失去了酒虫的刘氏虽然“悲酒如仇”,但是“体渐瘦,家亦日贫,后饮食不能自给。”在本文的“异史氏曰”这样发了议论:“日尽一石,无损其富;不饮一斗,适以益贫。岂饮啄固有数乎哉?或言:‘虫是刘之福,非刘之病,僧愚之以成其术。’然欤否欤?”
这篇寓言小说已涉及到人生的哲理,一些因人而异的嗜好似乎是“固有数”的,以异史氏发问的方式议论“酒虫”是福是病来探讨这一人生哲理。
这篇小说在芥川手里循着这一思考又向前大大地推进了,可以说完全是现代人的哲学思考。试看芥川是如何议论的:“酒虫既非刘之病,亦非刘之福。刘是从过去就嗜酒的,刘的一生如果除去了酒的话,将一无所有。由此观之,刘即酒虫,酒虫即刘。为此将刘的酒虫除去是与杀掉自我一样的。同时,从不能饮酒之日起到刘的自我已不复存在,那么过去健康的身体及家都失去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段话是芥川创意所在不言自明。芥川是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强调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任何戕害人的个性无疑等于杀掉人自身。芥川的这一思想亦体现在他的另一篇有名的寓言小说《鼻》(写于大正5年2月)里,它们可以说是姊妹篇。在《鼻》里那个禅智内供曾为自己的长鼻子而苦恼,“把握自己的能力减弱,始终注意的是自己在他人眼里的形象,使‘自己’不能绝对地生存的内供的姿态,归根结底也是他所看到的人的真实形象。”〔5〕在某种意义上芥川反映的思想和后来的存在主义思想有着一定的共同性,这是非常现代的意识。
另一篇寓言小说《尾生之信》出自《庄子·盗跖》、《国策·燕策》等典籍里。在《庄子·盗跖》中写道:“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在《国策·燕策》有:“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参,三者天下之高也。”显然,尾生之信是古老的中华文化中所推崇的美德之一。为了追求这种信,尾生是甘愿贡献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的。但是,在芥川的《尾生之信》里并不是重复这一主题,在结尾处他作了创造性的改造,使这篇小说另有新意。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
“在这几千年后的今天,尾生之魂已遍历千古,也一定又将其魂寄托于今世人的身上。可以说,在我身上也安放着这一灵魂。因此,我在今世出生以来没有做出一点有意义的事情,但却无昼无夜地打发着生活。可是却好象对于什么必须等待似的,企盼不可思议的东西,这和尾生在薄暮之中在桥下等待永久不会来的恋人不是一样吗?”
芥川在这里是以苦涩的笔调写了人生恰似一种无为的等待,这一思想也和西方20世纪前卫文学的思想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正如有的评论家所说:“写《尾生之信》时,芥川对于为了无为的目标而等待的灵魂,认为确实可以办到什么这一点,他已经不再相信了。”在尾生的身上不是也有古希腊西绪福斯的影子吗?
从以上的三篇取材于中国古代小说(或典籍)而创作的小说决不是简单的译介、演绎,芥川在作品里所反映出的思想是与他整个的创作思想一致的。
另外,从写法上来说芥川龙之介是非常重视现代技巧的作家。他曾在《小说作法十则》中说过:“假如不能使每一句话的美让人心旷神怡的话,我觉得他作为小说家是有缺欠的。”经过芥川改造(或者说依据素材再创造)的作品确实使人感到一种美的享受。“在芥川龙之介那里,这种真实的‘实体’乃是抒情。芥川龙之介在本质上来说是个抒情家的作家。”〔6〕试看《尾生之信》这篇短小的小说中的一段。 在尾生始终痴情地等待他的失约的恋人而不惜被洪水淹死之后,芥川是这样以抒情的笔触来写的:
“夜半,月光溢满一泓芦苇和柳树,河水和微风在悄悄地喁喁交谈,桥下的尾生的尸体被悠然地冲向大海。但是,那尾生之魂,或许对那寂寥的中天的月光会无限的憧憬吧,它悄悄地离开尸体,飘飘然地向明亮的天空飞去,好象水的气味和水藻的气味一样无声地从河上升起,欢快地越升越高……”
这宛然是一首凄楚的抒情诗。
再看《杜子春》写杜子春被引到阎罗殿亲眼目睹小鬼鞭打他变成马的父母时,芥川浓笔重墨,颇有戏剧性地发掘了杜子春的内心世界,也充满了抒情性。
在这里充分显示了芥川龙之介作为新技巧派巨匠的才华。这种改造已经使古老的文化产生了新的生命,它的力量在于通过文字对人心灵的感染。我们可以看到是凡通过芥川改造过的作品都具有这一特点。
三
芥川龙之介曾于1921年(大正十年)3月下旬至7月上旬以大阪每日新闻社海外特别观察员身份到中国,120多天的中国之行, 使他写有《支那游记》等纪行文字,这是研究他与中国文化关系的重要材料。他曾在《支那游记·序》里写道:
“《支那游记》一卷毕竟是天之所惠(或者说使我招来灾祸也未可知)的新闻记者才能的产物。我受大阪每日新闻社之命,于大正10 年3月下旬至同年7月上旬120余天遍历上海、南京、九江、汉口、长沙、洛阳、北京、大同、天津等地,归国之后遂成《上海游记》、《江南游记》,这都是每日必写之作。《长江游记》、《江南游记》虽是之后每日都陆续写出的,但是未完成之作。《北京日记抄》虽不是每日写一次,但我记得是二天左右写一次。《杂信一束》是写在明信片上的文字的收录。但是,我的新闻记者的才能在这些通讯里只是电光一闪,至少象剧院里的灯具之光一闪是确实的。
大正14年(1925)10月”
芥川这次游历其实还经过沈阳,然后从朝鲜回国。芥川与中国文化关系密切的作品还应包括《湖南之扇》和虚构的中国现实题材作品《南京的基督》。
芥川龙之介是对中国文化深有造诣的学者型作家,他所接受的中国文化主要是中国古代文化,他是从书本里、文字中吮吸了中国文化的丰富营养,形成自己的中国文化观和形象。但是,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到他游历中国的本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处于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满目疮痍之时,他亲眼目睹的中国现实与他过去心目中的中国无疑会形成巨大的反差。作为深受中国文化哺育的东方汉文化圈的日本知识分子明显地显示出一种认识中国文化的断裂。他曾在《游记》中写道:
“现在的中国有什么?不是在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上都衰颓了吗?特别是在艺术方面自嘉庆、道光以来没有一件值得骄傲的东西,而且国民不问老少只唱亡国的太平之音。当然,也许在青少年中多少还有其活力,但是他们的声音即使有,在全国国民的胸中恐怕也未引起大的共鸣和强烈的反响这也是事实。我不能爱支那,想爱也爱不起来。目击国民之腐败,如果还能再爱支那的话,只能是颓唐之至的官能主义者,浅薄的支那趣味的憧憬者。如果支那人本身内心还未昏昏然的话,会比我们这些外来的旅客更会嫌恶吧。”
应该说芥川龙之介由于他的阶级地位和中日两国国情的不同,特别是到中国游历是1921年,自然还看不到也认识不到中国未来的曙光和孕育在中国人民之中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力。从政治方面来说,他对于中国人民还是持同情态度的。如在《西湖游记》中他提到了秋瑾女士墓,对秋瑾女士作了正面肯定。
在《支那游记》里芥川采取的是一种新闻记者的记实采访手法,为了探讨芥川与中国文学的关系,我们不妨侧重于他的中国文化观的文字。在《江南游记》里他虽然提到了胡适、康白情的诗,但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学显然所知甚少,而且没有成为他关心的热点问题。
在这次游历中他见到了章太炎、郑孝胥等人。从与章太炎的对话来看,此时的章太炎所论及的中国未来的出路显然是错误的,他以中国人重中庸为根据,认为中国不能走工农革命之路。而郑孝胥更表现为“在政治上,对现代的支那是绝望”的一种态度。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芥川龙之介。
从《支那游记》的文字里很明显地反映出芥川龙之介是以过去从古代中国文化典籍中所获得的文化观来寻找对应物的心态。他在南京看到秦淮河,他脑海里浮现的亦是昔日在中国古代诗词、小说中所描绘的秦淮河。但是,一旦接触实际,作为文字载负的“幻影”就不复存在,芥川所感受到的是一种“误读”之后的文化落差,产生一种失落感。“从桥上眺望,秦淮河不过是一条平平常常的水沟,其宽窄不过与本所的竖川*差不多而已。两岸鳞次栉比的人家据说是小饭店、妓院。在这些房屋上空新树之梢可见,有看不见的画舫三四只,在暮霭中系在那里。古人诗云:‘烟笼秦淮月笼沙’,这般景色已荡然无存,可以说今日的秦淮只不过是充溢粉臭的柳桥而已。”与秦淮河联系到一起的是“桃花扇”中的名妓李香君,芥川来到秦淮河,不能不浮现这一文学作品中的绝色佳人。这种心态可以说是中国文化浸润的结果。但是,这本身也是一种误读。时间虽已流逝,但是芥川心中的文化沉积依然如故,只是眼前的现实与他心中所保存的文化沉积形成一种强烈的反差。他虽然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种反差必然会产生对中国文化认识的一种断裂感。他写道:“爱豪门贵公子侯方域而用鲜血染红桃花扇的李香君,想象她还会出现在二十世纪的秦淮河上确实过于浪漫了。”究其原因恐怕在于日本近代作家的中国文化教养主要是来自中国古典文学、古代文化,他们的中国文化观多是理念的,是从书本中得来的。他们在日本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并没有继续跟踪中国文化,对于中国现实的认识有着一种断裂的势态,因此,当他们一旦接触中国现实,对于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特别是在文化方面都会与过去头脑中的中国文化沉积所形成的中国文化观形成一种分离,这种失落感,自然会使他们产生片面的认识。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芥川龙之介身上,在其他日本近代作家身上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同时,在《支那游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芥川有种猎奇的倾向。芥川的美学倾向中存在追求日本阴翳之美的特质。他曾说过:“人是永远生活于忧愁之中的动物”。有的评论家指出:“芥川龙之介的阴翳之中的美是大家所熟知的。芥川是这一阴翳中的美作家。没有日光但是握有月光。在何处想背过脸处的哀愿中寻找美的韵律,这是芥川晚期作品所充满的情调。”〔7〕也许出于这种原因,他在《支那游记》、 《湖南之扇》中充满了对于丑的事物的特殊注意和猎奇色彩。在《支那游记》中有七处写中国人随地小便。在文字中还有对中国的乞食者与日本的乞食者的比较的文字。在游庐山时,芥川对于中国人倒吊宰杀后的白条猪发表了一通很激烈的感想。“在刚吐嫩叶的树上挂着一头死猪。那是剥了皮的一头猪,后腿高悬倒挂树上。那白条猪充斥肉体的浓重臭气。我看着这白条猪,心想对于这种倒悬白条猪难道有什么有趣吗,吊猪的中国人的低级趣味和被吊的猪看去傻乎乎的,这之间是很少差别的,总之象中国这样低级趣味的国家是各处所没有的。”这种看法显然带有偏见,而且这种偏见似乎对后代日本文人有着很大的影响,笔者曾见过几位当代日本文化人对白条猪产生这种猎奇。这种猎奇之处还有对于“斩首”之兴趣。在《湖南之扇》里,专门写了芥川到长沙之后以昔日东大的学友谭永年为向导,游历长沙的各种记载。
“如果能够看到土匪被处以斩首的场面那倒新鲜哪。”
类似之处不必一一枚举,对这种“猎奇”我们不必一定非得苛责,但是它确实反映了近代日本文人由于长时间的对中国文化、社会现状缺乏直接了解之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很难全面的。即或象芥川这样中国文化沉积很深厚、教养很高的作家,也很难超越这一障碍,这是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在写《支那游记》之前的大正9年(1920年), 他曾写有一篇虚构的以中国现代南京为背景,以中国妓女为题材的小说《南京的基督》,这篇作品所反映出的中国文化观是有代表性的,而且可以放在以上的一系列作品之中来统一把握。
《南京的基督》这篇小说的主人公是虚构的妓女宋金花。她是个暗娼,在卖身的行当里得了严重的性病。她的友人陈山茶告诉她一个迷信的方法:
“你的病必须转移到你接的客人身上才行,你尽快把它转移到谁的身上去吧。如果这样做的话,二、三天你的病一定会好的。”
但是,宋金花不忍心这么作,因为她是个从小接受基督教的虔诚的信徒。在陈山茶走了之后,她跪在墙上悬挂的十字架前,仰望受难的基督,真诚地祈祷,表示对主的虔诚。
最后,一个行骗的外国人骗取宋金花的好感,在宋金花无法自持的情况下终于和她发生性关系,玩弄之后一溜了事。然后宋金花竟奇迹般地治好了病,而这个外国佬却因严重梅毒而发狂致死。宋金花病好认为是基督的灵光保佑了她,她更加虔诚地感激基督。
芥川龙之介在写这篇小说时曾在附笔中记有:“写作本篇拙稿试与谷崎润一郎氏的《秦淮之夜》一比高低。附记于此,表示对谷崎氏感谢之意。”
显而易见,这篇虚构的以中国现代事情为素材的作品与谷崎的作品有着某种相似的东西。但是,芥川的这篇小说从与中国文化关系而论,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一)这篇小说取材于秦淮,这是古代名妓丛生的场所,东方文人的狎妓、与妓女的风流韵事一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题材,这大概也是芥川所抹不去的一种文化沉积吧。(二)作品里表现出古代文化意识与现代西方文化的交融。宋金花已不单单是有东方文化传统的妓女,而是有了基督思想,现代人道主义观念的人物,这也反映出芥川的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心态。(三)写作这篇作品时芥川并未踏过中国国土,内容纯属虚构,这反映出芥川的中国文化观许多方面是从书本上取得,并没有从现实生活中体验、消化,因此显示出一种脱离现实的特点。
* 日本东京的一条小河——芥川原全集注
注释:
〔1〕〔2〕吉田精一:《芥川龙之介》,第41、42页。
〔3〕〔4〕〔5〕〔6〕平冈敏夫:《芥川龙之介》,大修馆书店。
〔7〕山岸外史:《芥川龙之介》,第25~26页。
标签:芥川龙之介论文; 杜子春论文; 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日文字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