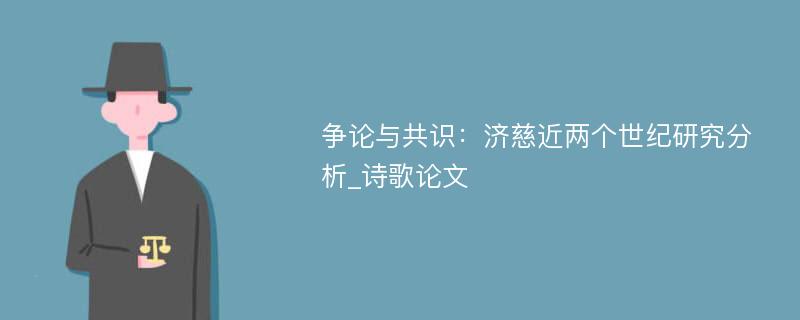
争议与共识:近两个世纪的济慈研究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济慈论文,共识论文,两个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大凡论及英国十九世纪的浪漫派诗歌,都要推举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拜伦、雪莱和济慈为这一派诗人中的杰出代表。这几位旷世奇才,以其才华横溢、富有深刻艺术内涵的作品创造了英国文学史上一个难以企及的辉煌时期,使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的二十几年间成为仅次于莎士比亚时代的一个伟大的时期。在这几位诗人中,以年龄论,济慈出生最晚而又去世最早,在世仅二十六年;以门第论,济慈的家世最为卑微,他的父亲依靠管理马厩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以命运论,济慈可谓最为不幸,八岁丧父,十四岁丧母,二十四时刚刚定婚,便因染上了当时为不治之症的肺痨而被迫与相爱多年的恋人分手,二十六岁时终因痨病不治而客死于罗马;以创作生涯论,济慈从事写作的时间也是最短,一般认为,仅仅有四年;然而以文学创作成就而论,不论是从作品的艺术性还是数量和影响着眼,济慈都可以和其他几位大家相提并论而并不逊色。只是世人差不多花费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才得以客观地认识济慈卓越的文学艺术成就。就此而言,济慈与比他稍晚一些年代的美国诗人惠特曼颇为相似。
追溯历史,便会发现济慈短暂的一生平淡无奇,不象拜轮和雪莱一生充满戏剧性的色彩;虽然他在短短四年的文学写作生涯中创造了奇迹,而他自己在世时对此却几乎没有自信。更遗憾的是,济慈同时代的人乃至后来十九世纪后半叶的读者,要么由于受到偏见的影响,要么由于迟纯的艺术鉴赏力,也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济慈为自己拟定的墓志铭“此处长眠者,声名水上书”,将丰富的思想和感情内涵浓缩于“水”这一意象之中。水是自然、永恒和纯净等天然特性的象征,显然与人类社会复杂的天地是相分离的。济慈认为自己作为诗人的“声名水上书”可以说形象地表现了他对自身的特性及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认识。
济慈自幼身材矮小,不好活动,偏爱独自读书,幼年便开始对文学感兴趣。他在小学期间,八岁便读了斯宾塞的《仙后》,以及当时供成年人参阅的《经典辞典》,从中了解到古希腊和英国的神话传说。这两部作品以其寓言形式、浪漫的故事和清新的意象对济慈产生的影响,在其后来的诗歌创作中不断表现出来。济慈大概在十七岁左右开始尝试写作。当时他仍在学医,私下决定毕业后依靠微薄的遗产谋生,放弃医业,全心致力于文学创作,只是为了避免与监护人发生冲突,才将其抱负隐匿在心里,直至成年不再需要监护。1816年,济慈与当时名声显赫的英国诗人与评论家李·亨特相识,亨特对济慈处于萌动状态的诗才颇为赏识,在其主编的文学刊物《检察者》上陆续发表济慈的诗作,并将济慈引见给一些作家和评论家,其中包括当时很有影响的评论家哈兹里特。亨特的提携使济慈下定决心从事诗歌创作。
济慈创作初期的作品以1817年发表的《诗集》为代表,带有浓厚的模仿色彩,显然是力图师法斯宾塞,然而其中也不乏上乘佳作,例如《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和《睡眠与诗》。1818年,济慈与芳妮·布劳恩相爱并订婚,虽然后因济慈身染肺痨和经济拮据未能成婚,但爱情却将济慈带入创作的成熟时期。在这一年中,济慈创作了《恩底弥翁》,以希腊神话为背景的这一长篇诗体寓言使诗人对美的独特感受力和运用语言的天才初露端倪。他还创作了长篇叙事诗《伊萨贝拉》,显示出他在强调诗作的审美价值的同时,也开始注意表现作品的主题意义。1819年是济慈最为多产的时期,除年初完成了长篇叙事诗《圣爱格尼斯之夜》之外,在春夏之际以颂诗和十四行诗的形式创作了一批传世之作,其中包括历来脍炙人口的四首颂诗,即《夜莺》,《希腊古瓮》,《哀感》和《懒怠》,而且这四首颂诗都是济慈在五月中一挥而就。同年,他还创作了《莱米亚》,这首表现神话的抒情诗再次突出地体现了诗人注重感官享受的创作特征。结构庞大的史诗《许佩里翁》的创作也始于这一年,而无情的疾病却使得济慈无法施展自己的天才来完成这一作品。1820年7月,济慈的诗集《莱米亚,伊萨贝拉,圣爱格尼斯之夜及其他》问世,既使世人再次领略到其诗歌创作成就,也标志着其创作生涯由此告终。赴意大利养病在十九世纪仍为时尚,因为那里阳光充足,气候温和,有助于慢性病患者恢复健康。同年9月,在挚友约瑟夫·塞文的陪伴下,济慈前往意大利养病。此时虽然济慈已经与芳妮分手,但在生病的最后岁月里一直得到芳妮一家人的照料。意大利没有能够使济慈如愿康复。1821年2月23日,济慈在罗马辞世。济慈英年早逝,使一些了解他的天才的人悲痛不已。为了表达对济慈的悼念,雪莱创作了长篇挽诗《阿多尼思》。该诗主题明朗,结构严谨,意象清新,情真意切,读之使人不能不为之感动,素来与弥尔顿的《利西达斯》和丁尼生的《悼念》并称为英国文学中的三大挽诗。
论及济慈的诗歌创作,就必须提及他的书信,因为它们是济慈思想与感情的记录,可以从中追寻其诗学主张与创作演变的轨迹。T.S.艾略特在《诗歌的用途》中,将济慈的书信称为“有史以来由英国诗人撰写的最值得注意和最重要的”书信,因为“济慈对于诗歌的每一论述,几乎都被认为是正确的”。济慈的书信内容涉及广泛,但以谈论诗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为主,其中最重要的当推有关“天然接受力”的观点。依济慈之见,诗人的首要职责是创造美,在创作中一切都必须服从于审美价值。他认为,诗人可以通过想象变成他想要表现的东西,与其内在的生命认同,从而可以从人生与艺术创造的神秘性中解脱出来,实现精神的解放。现在看来,济慈在其书信中表述的许多观点,都对他自己以及后世诗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济慈的书信最早见于R.m.米尔恩斯编著的《约翰·济慈的生平、书信及文化遗产》,该书于1848年出版。1958年出版的两卷本《济慈书信集》,由H.E.罗林斯编辑,迄今仍为济慈书信最完备、最标准的版本。
直至临终时,济慈始终没有做到客观地认识其作品的价值。在1820年写给芳妮的信中,济慈感叹生命的短暂,悔恨自己尚无创作出不朽的作品,并诚恳地说明创作不成功和无法与芳妮结为夫妻是两件令他无法心安的事情。在济慈去世后近两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已经做到客观地认识与评价济慈及其诗歌创作成就,并赋予其英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人们认识到济慈在短暂的一生中对美与永恒的探索是真诚的,没有任何名利的动机,正如他在致友人的信中所言,对于美和永恒的渴望和热爱可以使他彻夜不眠地写作,“即使一夜的创作次日清晨被付之一炬,无人浏览一眼”,也在所不辞。就创作风格而言,济慈效法莎士比亚,追求非个性化的创作模式。因此,济慈的诗虽然富于各种各样的人生体验,结构复杂多变,内涵深刻广泛,但作品的旨趣明朗清澈,毫无稍后唯美主义艺术推崇的怪诞晦涩之气。加之,他的诗语言洗练而富于激情,意象清新隽永,注重音乐性和感官享受,无需了解诗人的身世、创作原则以及所在的时代背景,便可以畅然欣赏与理解其作品。
在当今的批评家和一般读者看来,济慈之所以能够经受时间的鉴别而终于跻身于英国大诗人之列,不仅在于他的作品与时代的主体精神合拍,在形式与内容诸方面卓越地表现出某些共性,还在于其作品由于蕴涵着诗人独特的天才而呈现出不同凡响的特征。在文体方面,济慈在创作初期曾着力借鉴莎士比亚、斯宾塞、弥尔顿和李·亨特等人的文风,但很快便能够化彼为己,形成自已别具一格的诗风。济慈成熟时期的作品注意心理和场景描写并重的原则,长于使用联觉意象,强调遣词造句时兼顾意义和音乐性,大量使用作为形容词的过去分词,以多种艺术效果烘托审美主题。诸如爱情、理想、命运、劳作、抱负和成就等主题是浪漫派诗人所青睐的,济慈自然也不例外,但是他也表现了一些独特的主题,例如有关变形的幻想。在《坐下来重读〈李尔王〉》这首十四行诗中,济慈依据埃及的古老传说,以凤凰为主要意象。相传凤凰每隔五百年便要焚烧香木,然后再自己投身于熊熊燃烧的大火之中,以求一死,最后从其骨灰中脱生出一个新的凤凰。济慈以此暗喻表现自己完全沉浸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之中,犹如凤凰经历焚烧以后而再生,从而自已也具有莎士比亚那样的天才,并取得类似的成就。济慈在未完成的作品《许佩里翁》中也表现了变形的主题,通过描写阿波罗取代许佩里翁成为新的太阳神,主宰诗和光明,宣泄了渴望获得知识与取得史诗般成就的愿望。阿波罗身上寄托了济慈的希望,这自不待言;许佩里翁这一神话人物一般认为是指华兹华斯,济慈视其为杰出诗人的代表。诚然,济慈的诗作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其形式之美,足以使读者沉浸其中,忘却自我,获得愉悦的感受。其内容对美与永恒、人与自然以及社会问题的描写,足以使读者凝神思考,尔后必有所悟,获得效益。
二
近两个世纪来,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评论家对济慈及其诗歌的研究此伏彼起,始终没有停顿。尽管审视的目光越来越敏锐,关注的视野越来越广泛,研究方法与视角也不断变化更新,但始终无法穷尽济慈及其作品的艺术内涵和魅力。十九世纪的济慈研究以毁誉参半的争议为主要特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也有新旧审美观念冲突的作用,情况比较复杂。时至十九世纪末叶和二十世纪初叶,人们对济慈的认识逐渐形成共识,普遍高度评价其诗才,承认其作品超凡的价值,并不断采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深化对这位大诗人及其作品的研究。在英国浪漫派诗人中,济慈的作品最富有现代精神,因而对十九世纪的丁尼生·布朗宁和王尔德等诗人以及二十世纪的意象派诗人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反过来又促使人们欣赏和研究济慈,不断产生新的认识和感受。
济慈在十九世纪的命运颇有戏剧性色彩。济慈在世时以及去世后二十余年间,他的诗作没有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基本上无知名度可言。这主要是十八世纪新古典主义诗学观念的影响延续到十九世纪,济慈同时代的读者仍旧青睐注重节制、讲求法则的诗歌,习惯于四平八稳、精雕细琢的技巧,不求意境高远、气魄雄奇之作,因而济慈富于激情和侧重刺激感官感受的意象的诗歌,自然无法入流。然而在文学批评家的小圈子里,几乎是济慈刚刚投身诗歌创作,或褒或贬的评论便接踵而至,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批评界对济慈的研究始于其创作之初并与其同步发展。最早对济慈予以关注并进行评论的是李·亨特。亨特1816年曾撰文称赞济慈和雪莱,认为他们的诗歌风格别致,感情纯真,意象清新自然,代表了一种新的创作倾向。文中还特别分析的济慈的《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一诗,予以很高的评价。济慈去世以后,亨特于1823年又写了《济慈先生:对其作品的批评》一文,对济慈的创作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研究和一分为二的评论,指出济慈用韵有时失之于雕琢,选择词汇时将其视觉形式特征和音乐性放在首位,其次再考虑其含义。文中还批评当时文坛对济慈的评论有失公允,预言济慈的诗歌在“二三百年后会大受欢迎”。应当说亨特对济慈的评论是客观的,他对济慈历史命运的预言也被事实证明是正确的。然而由于亨特的政治态度倾向于较为自由开明的辉格党,且言论较为激进,所以不断受到保守的托利党党羽的抨击,并曾被捕入狱,度过了两年失去自由的铁窗生涯。济慈在诗歌创作之初本无强烈的政治抱负和倾向,只是由于接近亨特,与以亨特为代表的所谓“伦敦诗派”有一瓜半葛的联系,当然还由于亨特对济慈的诗歌予以好评,因而便被托利党人视为攻击的对象。济慈的作品遭到贬低,人身受到中伤。托利党人出于狭隘政治动机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十九世纪济慈评论中悲剧性的基调。
最早向济慈发难的,是1818年发表的两篇匿名评论。一篇刊载于《布莱克伍德之爱丁堡杂志》,后来证实此文出自英国小说家J.C.洛克哈特的手笔。洛克哈特在文学界以其《司各德传》闻名,在政治上追随托利党,因此便将倾向辉格党的李·亨特及其为首的“伦敦诗派”视为忤逆。政治倾向使洛克哈特将济慈划为亨特的同党,因此文章从头至尾,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于政治异己的敌视态度。洛克哈特宣称济慈的诗歌不够典雅,缺乏上乘的艺术情趣和道德基础;他甚至对济慈的人格进行抨击,称其缺乏良好的教育,因双亲早亡而又疏于教养。另一篇发表在颇有影响的《评论季刊》上,后来得知作者为J.W.克罗克,当时托利党中较为活跃的政客。与洛克哈特的文章相比,克罗克的文章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成见,以较长篇幅详细分析济慈的诗作,一方面承认诗中洋溢着“语言的力量,想象的光辉和天才的光芒”,另一方面又批评诗的品味不高,行文中多有语病,过于追求音乐性和刺激感官的意象,而忽略了叙事逻辑和情节结构。此外,由于济慈在《恩底弥翁》一诗的前言中坦率地承认,因缺乏创作经验,自己早期的某些作品不够成熟,克罗克便借此夸大其事,指摘济慈成名心切,缺乏足够的艺术素养。克罗克对济慈的评论是以济慈1817年的《诗集》和1818年的《恩底弥翁》为基础的,其中涉及诗艺的观点后来证明是客观中肯的,但是在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表此文的《评论季刊》要比刊登洛克哈特那篇文章的杂志影响大得多,加之,文中夹带一些攻击性的词语,所以当时以雪莱为代表的一些人便认为此文给济慈带来了致命性的打击,导致济慈心情郁闷,肺痨加重,英年早逝。
回首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虽然雪莱等人对克罗克的文章所带来的后果的推论,尚无发现确凿的证据,但有一点已经为历史证明得清清楚楚,即:洛克哈特和克罗克的匿名文章,不仅在济慈在世时扼杀了他的声誉,而且在济慈去世后,乃至十九世纪后半叶,仍旧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对其进行研究与评论的走向。从现在掌握的资料来看,济慈与亨特接近的时间是有限的,后来二人的关系也逐渐疏远,而济慈在世时始终没有认识到是由于亨特的缘故,才招致托利党对他的反感、贬低和攻击。
亨特的赞誉和洛克哈特与克罗克的批评攻击,形成济慈研究和评论中的两极对峙。这种局面在济慈去世以后又沿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持批评贬低之见者,大体上都囿于洛克哈特和克罗克的思路,矛头所向并无新意。持欣赏辩护之见者,则努力从不同角度为济慈辩白,阐释其诗歌创作成就。值得提及的是,前者多为政客或者有较强政治倾向的文人,而后者则均为作家和文学评论家以及济慈的朋友。
洛克哈特和克罗克的文章发表后,J.H.雷诺兹旋即在《检察者》上发表署名文章,敏锐地指出他们的批评和攻击完全是缘于政治动机,认为济慈本为一介书生,为艺术是术,刚刚步入诗坛并初展天才,而不负责任的责难有可能扼杀一位天才作家。英国诗人、剧作家和批评家兰姆1920年也在《检察者》上发表文章,以批评家的角度较为详细地分析济慈的重要作品,认为无论是济慈作为诗人的艺术感觉还是其作品的技巧与内涵,都属于上乘。雪莱对济慈的评论主要见之于《阿多尼斯》一诗的序言。雪莱在文中呼应雷诺兹的观点,批评洛克哈特和克罗克对待济慈的态度是不公正的,认为他们的文章最终导致济慈的夭殇。雪莱在《阿多尼斯》一诗及其序言中,通过阿多尼斯这一神话人物的形象表达了对济慈的赞美,而同时又将济慈的形象描写为“悲哀的少女所宠爱的苍白的花朵”。此前,有些评论已将济慈描绘为纯真无邪但多愁善感、才华横溢但性格纤弱的诗人,《阿多尼斯》以及雪莱在序言中的描述与分析显然也是如此。鉴于雪莱的成就,地位、声名和影响,他对济慈的理解和刻画曾经一度在济慈研究中颇有反响。
在济慈同时代的文学评论家中,特别应当提及R·伍德豪斯。1818年《恩底弥翁》面世后,伍德豪斯以评论家的敏感很快注意到这一作品。然而面对李·亨特、洛克哈特和克罗克等人围绕评价济慈所进行的论战,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伍德豪斯没有公开介入,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同年,在写给侄女玛丽·弗罗格利的一封长信中,伍德豪斯对济慈评价之高,为当时所仅见,且为后世所少见。伍德豪斯断言,济慈“这样一位天才,是自莎士比亚和弥尔顿之后至今未曾出现过的”;在将济慈的《恩底弥翁》与莎士比亚值同一年龄时创作的《维纳斯与阿多尼斯》相比较之后,他指出“济慈的诗句含更多的美的东西,更多与更美妙的诗意,较少的奇想和不良情趣,总之,会发现比莎士比亚的作品具有更多的美好希望”。对于济慈的命运,伍德豪斯预言说,济慈在世时路途坎坷,不会得志,惟有去世后才会逐渐受人推崇,进而成为公认的大诗人。令人遗憾的是,伍德豪斯的这封信在整个十九世纪都未曾公诸于世,直到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后,才于1914年发表,使十九世纪论争中的双方都没有机会领略他的见地。即使涉足论争的人之中,也有一些当时很有影响的作家和评论家,象伍德豪斯一样侧重评论济慈的作品的艺术价值。例如F.杰弗里和J.司各特在其评论中就采取了较为客观的、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而且在济慈谢世后撰文表示悼念,为英国失去了一位有才气和希望的诗人感到惋惜。
在济慈去世以后的二三十年里,由于雪莱的挽诗《阿多尼斯》的影响,相当一批欣赏济慈的评论家和读者都将其视为一个唯美是求的诗人,其诗作与思想无涉,长于以可望而不可即的手法表现令人愉悦的感受。这种认识表明对济慈及其作品的理解还处于较为浅表的阶段。真正开始扭转这种局面并将济慈研究引向深入的,是1848年出版的《约翰·济慈的生平、书信及文学遗产》一书。在济慈研究中,公认这部著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作者米尔恩斯为诗人、批评家、散文家和政客,而今天主要以此书的作者闻名。米尔恩斯的主要贡献在于首次公开济慈的书信和诗稿,并对这些第一手资料予以精细的分析,由此在读者面前展现出向来鲜为人知的济慈的内心世界,证明济慈不仅诗艺高超脱俗,而且具有成熟而深邃的思想。米尔恩斯的这部著作产生了明显而久远的导向作用,使人开始同时关注济慈及其作品的艺术内涵和思想内涵。譬如D.马森1860年在《济慈的生平和诗歌》一文中,沿着米尔恩斯的思路,较早提出济慈诗歌创作的特点,是在诗中将注重感受的意象和赋有思想道德内涵的美巧妙地融为一体。
十九世纪后半叶,一些美国作家也开始陆续在报刊和各种著作中评论济慈,说明济慈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于英国。总的说来,美国作家的评论在形式上较为零散,比如惠特曼的评论便只是见于多处的只言片语,大概只有诗人、散文家、批评家兼编辑洛威尔所作的评论较为系统和全面。他在1876年出版的《我阅读的书》一书中,分析了济慈的创作及其作品的特色,认为济慈有捕捉生动意象的天赋,用词兼顾其意义、形式和声音。他还特别强调济慈的诗在给人以美感的同时,也会使人反观自身,思考自我,从而使某种个人感受具有普遍的意义。在洛威尔看来,济慈的作品以感官享受见长的深层意义正在于此。洛威尔的见解代表了与其同时代的美国作家对济慈的态度和认识深度,在向美国读者评介济慈方面很有影响。
大体而言,对济慈的研究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开始逐渐摆脱政治和阶级的偏见,注重文学自身的评论。在这一时期中,对济慈及其作品做出较为全面而深刻评论的人,首推阿诺德。作为维多利亚后期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和批评家之一,阿诺德在1880年出版的《批评文集》中详细剖析了济慈的突出特征:敏锐过人的感受性和洞察力,清澈晓畅而音乐性极强的行文风格,得心应手地运用各种诗歌技巧的能力。不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对于济慈写给芳妮的书信一般都评价很高,而阿诺德则大不以为然,认为无非只显示了诗人感情生活的一面。阿诺德还特别赞赏了济慈“渴望追求美的激情”,强调这种激情中既赋有思想内容也赋有精神内涵。阿诺德的评论结论是济慈足以与莎士比亚“并驾齐驱”。自然,对于阿诺德的结论,也有持异议者。1887年,英国诗人霍普金斯在一封信中论及济慈,认为济慈在1819年春夏之际创作的多首颂诗,标志着其艺术走向成熟,但不同意将济慈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因为济慈带有明显的女性气质。
十九世纪后半叶,济慈研究的另一个明显特征是关注的内容更为丰富,触及到一些未曾注意的方面。1882年,T.H.凯恩在《济慈曾是逐渐成熟》一文中研究了济慈从1818年至去世四年间的文体演变,勾勒出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按照凯恩的分析,济慈的文体不成熟时,主要表现为结构不够完整,作品中思想和艺术方面的诸种成分比例失调;而代表济慈的文体进入炉火纯青时期的作品是其十四行诗,尤其是《致荷马》一诗。D.G.罗塞蒂和W.莫里斯等“先拉斐尔兄弟会”中的艺术家,则刻意赞颂济慈诗中富于形象的描述和生动的意象,并将济慈推为其艺术先驱。A.西蒙斯等人另有发现,认为济慈作品的主导品格是“为艺术而艺术”,固然这种品格是与他们的艺术目标相吻合的。
1882年,英国诗人、戏剧家和批评家A.C斯温伯恩为《不列颠百科全书》所撰写的“济慈”这一条目,内容涉及广泛,叙论结合,承前启后,颇有新见,可以说是对整个十九世纪济慈研究的总结。斯温伯恩指出济慈的诗艺是发展的,而且在短短几年间便达到了完善的程度;他认为1817年的《诗集》就其整体艺术质量而言,是不成功的作品,模仿斯宾塞和华兹华斯的痕迹十分显露,而1820年的《莱米亚,伊萨贝拉,圣爱格尼斯之夜及其他》则表明济慈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他将这部作品集称为英国最佳诗集之一。斯温伯恩还第一次将济慈的颂诗置于其作品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其叙事诗不如颂诗有艺术价值和成就。斯温伯恩继承了阿诺德的观点,强调济慈的作品充盈着与莎士比亚的作品同样的气质,济慈的艺术成就足以与莎士比亚相媲美。至于说到济慈何以在短短几年中迅速而全面地进入诗歌艺术创作的极境,成为旷世难觅的诗人,斯温伯恩将主要原因归于济慈的天赋,认为唯有此说才站得住脚。
三
上文所述十九世纪的济慈研究,为二十世纪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泾渭分明的臧否之争,由逐渐拓展的纯文学批评所取而代之。二十世纪上半叶,济慈研究的特征表现为:在一些新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模式的影响下,开始更多地关注济慈的创作过程、诗风和诗艺的发展以及作品本身更为具体的特征。二十世纪初叶,相当一批著述都集中在研究济慈的创作过程。批评家P E.莫尔与白壁德一道提出了新人文主义,强调道德伦理的价值;受此影响,他在1906年的一篇文章中分析指出,伊丽莎白时期的诗人对济慈有相当重要的影响,主要是促使他将艺术之美与对人生的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同年,塞林考特在为其编辑的《济慈诗集》所写的导言中,详细考证对济慈产生影响的每一位作家,分析每个人对其发生影响的形式和时间及其结果。例如,塞林考特不仅考证出斯宾塞为第一位对济慈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而且还发现济慈最早的诗作是作于1813年,但从未发表过的《模仿斯宾塞》。
随着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问世,对济慈的创作的研究也开始予以借鉴和采用。1909年,著名批评家和莎学专家A.C.布雷德利在《济慈的书信》一文中,虽然并没有采用弗洛伊德的分析方法,但是显然试图从书信中记录的经历窥视济慈的精神世界。布雷德利认为,济慈的书信是理解其作品的形式和意义的线索,也是了解其内在本质的途径。在深入分析济慈的书信之后,布雷德利得出的结论是,济慈自幼备受多方面的压抑,包括恋爱挫折,但他依旧执著于诗歌创作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说明他具有“更开阔的心灵,对人性更多的了解,或者更独特的思想力量”。就此而言,布雷德利认为在济慈同时代的诗人中间,无人可与其相比美;当然济慈也并非象十九世纪有些评论家所描绘的那样,面色苍白,性情柔顺,作为诗人只耽于表现感官感受。此后,类似的研究颇为常见,较为典型的包括批评家和教育家M.H.沙克福德1924年发表的《济慈与逆境》一文。文章考察了济慈短暂的一生中遭遇的诸多不幸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认为济慈的成功主要有赖于其心理基础:他承认人的一生不论长短,都有不可回避的痛苦经历,相信人性的力量并尽力与困难抗争,从而通过超越个人的痛苦感受领悟到事情另一面的积极意义,获得人生中宝贵而伟大的东西。应当说明的是,对济慈进行的较为成熟的心理分析研究,到二十世纪下半叶才出现。
在这一时期,对济慈所作的比较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对济慈研究而言,带有比较特征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早在1817年,J.H.雷诺兹便在一篇专文中以当时刚刚问世的《诗集》为背景,将作者济慈与莎士比亚、弥尔顿和乔叟相比较,为这方面的先行之作。然而当时和后世的评论均认为雷诺兹对尚不成熟的《诗集》评价过高,对济慈也多有过奖过誉之处,对于客观地认识和评价济慈弊大于利。其效果自然也适得其反,且不说招致持不同观点的评论家的反驳,也引起一般读者的反感。然而这一时期的比较研究显然不同于雷诺兹的文章。J.M.默里为当时英国著名批评家,以观点新颖、笔调富有激情而闻名,他在1926年出版的《济慈与莎士比亚》一书中,通过研究济慈与莎士比亚在精神上的相似之处及其在艺术上的借鉴,力图揭示济慈1816年至1820年创作中的“内心生活”。默里还提出了引起争议的观点,认为《许佩里翁》虽未完成,却是济慈在四年间的断断续续之作,与其他一气呵成的作品不同,在多方面显示出诗人的演变,确为其最伟大的作品。该书出版后反响很大,不断扩充再版,1955年易名为《济慈》,包括比较研究济慈与弥尔顿、布莱克、华兹华斯等英国作家的关系。
T.S.艾略特是二十世纪最有影响的诗人和批评家之一,对许多英美作家都曾作过独特而中肯的评论。1933年,他的《诗歌的用途》有一节涉及对济慈、雪莱和华兹华斯三人艺术成就的比较研究。他象布雷德利一样,以济慈的书信为主要研究资料,认为济慈对文学艺术的见解以及对华兹华斯等人的评论,无不体现出天才的智慧,同时代人中能够与其相及者寥寥无几;但是以文学思想的系统性而言,济慈则逊于雪莱和华兹华斯。艾略特的分析比较侧重于文学批评和理论,与其相仿的重要著述,还有S.F.金格理克1932年的《雪莱、济慈和坡作品中美的概念》。金格理克首先分析了三人各自“美”的概念的发展过程,然后再横向比较。依照文中的分析,济慈在创作之初认为美是永恒的,并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所谓“一件美的事物即永恒的欢乐”,后来又将美与真等同起来,所谓“美即真,真即美”。金格理克认为,济慈对美的认识就其实质而言,就是对人生及其意义的认识;而且济慈对美的认识变化,也由其不同年份的作品体现出来。或许正因为如此,金格理克象默里一样,将《许佩里翁》称为济慈最有价值的作品。比较济慈与雪莱之后,金格理克指出二人对美的认识有较大差异。济慈认识美的途径是由吸收对自然环境的感受入手,在此基础上构建美的概念,方法纯朴易行。而雪莱则强调先验的东西,深奥费解,非常人能力所及。雪莱认为美和美的力量都是外在的,而济慈则认定美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其他方面重要的比较研究著作,还包括吉尔曼1939年的《济慈与十四行诗的传统》,以自华埃特和萨里以后英国十四行诗的传统为参照,探讨济慈的十四诗在形式和技巧上的特征。
作为一种文学批评理论,新批评也被引入济慈研究。著名批评家布鲁克斯是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他主张文学批评应当是一种独立存在,主要通过细读文本,分析形象、意象和暗喻来研究作品。在1944年的《没有注释的历史:话说济慈的〈希腊古瓷〉》一文中,布鲁克斯娴熟地运用新批评的方法,几乎是逐行逐节地分析《希腊古瓮》一诗,诠释作为主要艺术成份的暗喻在作品中的作用,兼而讨论诗中表现的美与真的关系。新批评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即诗人与批评家A.塔特,1946年发表了《解读济慈》一文,同样以新批评的方法为手段,通过解析《希腊古瓮》和《夜莺》两首颂诗,说明济慈能够赋予诗中静态图象以运动的创作技巧。新批评的介入,使以往重于宏观评论的济慈研究转变为以微观分析和宏观评论相结合。
二十世纪下半叶,济慈研究无论是在内容、方法与角度,还是在参照对象方面,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各种著述在数量上也可谓空前。此外,上半叶已经呈现出来的一些研究特征也延续下来,并不断在广度和深度方面有所进展。例如就诗歌批评而言,新批评长于研究篇幅较为短小的作品,因而在上半叶济慈的颂诗受到青睐,分析偏重于将作品视为一种自满自足而与其他无关的存在。然而下半叶的一些批评家在研究济慈的颂诗时则明显与新批评派所持的观点不同,从分析济慈的生活经历,尤其是心理状态着手,挖掘济慈及其颂诗之间必然的内在联系,以英国文学批评家K.缪尔1958年的《济慈颂诗的意义》为例,缪尔在对济慈的书信进行透彻的研究后发现济慈在创作颂诗几周之前进入一种矛盾而痛苦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济慈领悟到懒怠也可以具有创造性的作用,于是便希冀自己努力进入一种无牵无挂、自由无为的心理状态,而另一方面,坎坷不幸的生活经历又时时促使他探究人类痛苦的意义,以便以某种方式证明每个人的痛苦都是有价值的。再者,此时他正与芳妮处于热恋之中,如火如荼的恋情也与他试图摆脱抱负与劳作、追求自由无为的心境的心理愿望相矛盾,又使他陷入另一种痛苦之中。正是在这种颇为复杂的心理状态下,济慈开始创作颂诗,而且几首流芳千古的颂诗均在一个月内挥就。明了了这种背景,就会发现《心灵》表现了“轻微的痛苦”,因为诗人在寻找某种可以代替宗教的东西;而在《夜莺》里,诗人则忘情地沉醉于夜莺的欢乐和幸福之中,正如同凡夫俗子总是借助于酩酊大醉摆脱人生的痛苦一样,诗人则凭借“诗的无形的翅膀”扶摇于九天之上,而将人生的牵挂和苦闷统统弃之于大地。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济慈研究表现出更为强劲的势头,取得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果。首先是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批评家之一布卢姆将其“再审视”的理论用于研究济慈及其作品。基于对英语诗歌的分析,布卢姆的理论认为任何诗人都必然要受到前世诗人的影响,要形成自己独特的诗风,就必须努力摆脱这种影响的束缚。在布卢姆看来,克服前人影响唯一有效的方法,是有意识地进行“创造性的再审视”,并将其称之为“误读”。在1961年的《济慈与诗歌传统的困恼》一文中,布卢姆将济慈的“误读”归为以有胆有识的创作自由冲破诗歌传统的约束,并形成自己独特的想象能力。根据对济慈颂诗的研究,布卢姆指出济慈的想象力在英国诗人中是最健全的。读其诗,可以领略到现实与想象中的一切始终保持一种和谐的平衡,人与物即是现实的又是想象的,美与平凡存在于一体,生与死集于一身。总之,济慈在创作中,建立于逻辑现实之上的自由想象,使俗念以为不可能的成为可能。
同年,J.D.博尔格的《济慈的象征主义》探索了长久以来济慈研究中被忽视的一面。博尔格认为济慈真正的艺术成就和贡献,在于依靠自然界中的意象、色彩、景物及其他存在创造一个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世界,尔后再置身于其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描写人类追求美好未来的心理和永恒的梦想,以缓解和宽慰人生中苦涩的感受。以这种观点审视济慈的作品,博尔格认为《希腊古瓮》中创造的艺术世界最为卓越,成功地使浪漫主义艺术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现实。
象博尔格一样,M.霍尔朋别出心裁,研究了济慈创作中的幽默。1966年,霍尔朋发表《济慈与欢笑的精神》,指出自《恩底弥翁》开始,济慈注意在艺术世界中创造一种幽默的品质。济慈力求使这种幽默的品质具有广义的现实性,即在严肃深沉的叙事中杂以可笑的情节,描写喜悦时也表现愁怅,刻画人物的紧张状态时以轻松相衬托,总之,是依靠反差形成幽默。从幽默的角度着眼,霍尔朋提出了一些与他人相左的见解。许多批评家认为济慈删去《哀感》一诗原第一节是明智之举,公认该节文笔欠佳,舍其则使全诗的艺术效果更为理想,而霍尔朋则认为保留该节,有助于诗意的过渡。
在比较研究方面,也有一些著述有较为明显的进展和较为重要的价值,但总体而言,在研究范围和深度方面没有重大突破。比较重要的著作有T.鲍斯莱夫1962年出版的《济慈与华兹华斯的比较研究》,探讨华兹华斯对济慈在文学理论和诗艺等诸多方面的影响,并通过对比两位诗人在使用意象和人物塑造等方面的异同之处分析影响的结果。还包括1973年出版的《浪漫主义再评价:英国诗剧与济慈》,作者H.R.博第将济慈置于十九世纪初叶大的文学背景下,首次注意到济慈和英国戏剧之间的联系,通过较为翔实的考证证实英国戏剧对济慈的艺术发展产生过影响。
在八十年代的济慈研究中,批评界给予一致好评的著作,是美国批评家H.范德勒瑞1983年出版的《济慈的颂诗》一书。范德勒瑞以女性所特有的敏感和缜密,从创作背景、创作心理、文学传统的影响以及诗歌技巧等角度,对济慈的颂诗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自四十年代以来,批评界越来越看重济慈的颂诗,这部著作可以说是对这种研究偏好的一个总结。1984年,范德勒瑞又发表了《济慈与诗歌的用途》一文,再次引起批评界的关注。文章探析了济慈对于诗歌的社会用途的认识,从而揭示出济慈及其作品中尚未发现的某些价值。按照范德勒瑞的研究结论,济慈在早期日记与诗歌中实际上总结概括了历来诗歌的四种社会功用:历史功用,如史诗记载历史;寓言形式的表现功用,如莎士比亚的戏剧;教化功用,如斯宾塞的某些诗作;语言的存留功用。济慈认为,过于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必然注重使诗歌有助于消解人生中的痛苦。而他主张强调诗歌的艺术表现,而同时兼顾其社会功用。依据济慈的观点,实现诗歌的社会功用需要诗人和读者的合作。在诗人一方,必须主要依靠象征的手法,不可直接模仿,通过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使读者有所感悟。文章还通过具体分析一些诗作,展示诗人如何实践其主张。范德勒瑞认为《秋颂》一诗体现了济慈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最后认识,即将自然与文化择为其艺术象征世界的两极,而诗人的职责就在于将自然转化为文化。
九十年代的济慈研究又表现出一些新的动向,其主要特征是内容更新,范围拓宽,视野扩大。开风气之先的,当举1992年出版的《词汇如钟:济慈、音乐与诗人》。作者J.A.米纳汉曾为职业音乐家和音乐教师,长期致力于研究十九与二十世纪文学作品中词汇与音乐的关系。这部著作以考察济慈的书信、诗歌,尤其是其颂诗为基础,总结他对诗与音乐两者关系的认识,并以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海顿和贝多芬等人的观点为辅佐,较为全面地研究音乐对其创作观念的影响,音乐作品结构对其诗歌结构的影响,以及音乐感受的方式对词汇和意象的影响。
1993年,K.奥尔韦斯又将时下流行的女权主义批评引入济慈研究,出版了《变形的想象:济慈诗歌中女性形象的演变》一书。作为女性,奥尔韦斯注意到济慈描写女性形象的特征及其演变,认为济慈在早期诗歌中不惜笔墨地描写阿波罗这一男性形象,反映了他心理对女性的恐惧,并寄希望于阿波罗来消除这种恐惧,但未能奏效。在这种情况下,济慈才开始描写女性形象。对此,奥尔韦斯解释说,从表面上看,济慈笔下的女性形象是男性形象的情人、向导或对手,而实则将其用作象征,来表现诗人想象中的情欲与恐惧,拯救与毁灭,以及力图调合男性与女性的创造力时发现的希望与失望。奥尔韦斯认为,《许佩里翁》中的女神莫妮塔代表了济慈塑造女性形象演变的终极;这一形象融阿波罗式的阳刚之气与女性的柔情为一身,因而更完美,更赋有艺术魅力,奥尔韦斯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开垦了济慈研究中的一块空白地。
1994年,A.贝内特的《济慈,叙述与读者:作品在作家去世后的生命》一书又将济慈研究领入另一个新的领域。晚近,有些研究认为浪漫派诗人中曾一度盛行这样一种观点,即自己在世时作品不会为人所接受,而作古以后作品才会大受欢迎,故创作应当着眼于未来,所谓“作品在作家去世后的生命”。贝内特便是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通过考察诗人、叙述与读者三者的关系审视济慈的创作。贝内特的研究结论是,济慈诗歌已经考虑到读者的阅读及其方式,这种考虑决定了对济慈文本的反应方式,后人的阅读即“作品在作家去世后的生命”。贝内特指出,济慈的作品之所以水平参差不齐,主要在于济慈考虑未来的读者及相应的叙述方式时有不周之处所致;诗人对叙述的选择决定作品未来的读者及其对作品的反应。贝内特的著作并非仅仅限于讨论济慈,还较为广泛地分析了浪漫派诗歌与读者的关系。
除上述学术专著与评论文章之外,传记也是济慈研究中一个重要方面。据不完全统计,自R.M.米尔恩斯1848年出版《约翰·济慈的生平、书信及文学遗产》迄今,以英文出版的有关济慈的传记已经多达二十余部,从不同侧面和角度研究他的生平和创作。其中有鲜明特色并受到好评的传记,以发表年代为序,包括以下几部。《约翰·济慈》出版于1929年,是一部颇有争论的评传,作者为美国女诗人A.洛威尔。洛威尔全面而详尽地记述济慈的生平,从情节、格律、典故、意象、色彩等多重角度评析其主要作品,并称济慈及其作品的真正意义在于代表了现代诗歌精神。C.A.布朗的《约翰·济慈传》1937年出版,被公认为第一部全面描述济慈生平的传记。这部传记初撰于十九世纪,作者为济慈的挚友,主要记载济慈1818─1821年的生活,这期间作者始终与济慈在一起生活。布朗的手稿经后人编辑后才得以出版,其中大部分篇幅资料均用来抨击和咒骂那些对济慈不友善的人。W.J.贝特两卷本的《约翰·济慈》1963年一问世,便受到普遍好评。这部传记文笔优美,叙议客观,内容翔实,充分利用二战后发现的新资料,主要是济慈与朋友间的通信,迄今仍被视为内容最全面、最可信的济慈传记。
标签:诗歌论文; 艺术评论论文; 艺术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十九世纪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约翰·济慈论文; 莎士比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