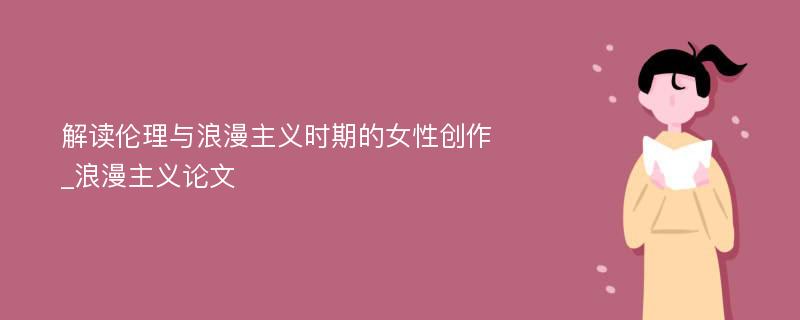
浪漫主义时期的阅读伦理与女性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浪漫主义论文,伦理论文,时期论文,女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阅读之邦的产生
1774年英国下议院通过废除永久版权法的议案,一夜之间使出版界的寡头统治几乎处于“一种崩溃的边缘”①。这个影响英国出版业以后多年的决定,使得更多中低收入者有能力进入阅读之列,并且使文学开始进入教材和普通人的想象空间,最终导致在1780年代文学成了英国学校教材的主要来源。同时,由于“知识税”② 的废除,出版界获得了空前的自由,也开始脱离国家的社会政治利益控制,而被出版界所推崇的“编辑自由”的理念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推广。一个真正阅读之邦的产生已是无可争议的事实,“此时的英国俨然一个书籍之邦,一个出版之邦,一个阅读之邦,一个评论之邦了”③。
1795年迪士累利曾自豪地说:“我们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阅读和批判之国,任何一个温良雅致的作者都会发现欣赏自己的读者开始大量涌现。”④ 两年后针对由广泛阅读所产生的大众评论,戈德温不无抱怨地说:“我们生不逢时,出生在这样一个批判横飞的时代,哪怕是昔日最狂野不羁的作家现在也收敛了许多。”⑤ 出版商莱克星顿回忆道:“目前图书的销售量是前20年的4倍,人不分等级阶层都在阅读。”⑥ 雷恩也慨叹:“举国上下不分等级人们闲暇时间尽用,个个都在阅读,这才真正称得上阅读大众(reading public)啊!”⑦ 19世纪早期英国阅读人数的增长不但是一个蔚为壮观的文化现象,而且对文学创作和欣赏以及现代性的出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此时的阅读已是一种对现代性有特殊意义的现象。与封建时期的释经学(exegesis)和清教时期的类型学不同,这类阅读既不以单一文本为中心也不以单一作品为权威。这是一个阐释的社会,人人都是阅读者。洛克哈特将数以百万计的读者的涌现视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⑧。西丝金也宣称:“写作新技法、出版印刷与默读方式在社会认知和运行方面产生了一场革命。”⑨ 还有评论将浪漫主义时期阅读的兴起与思想意识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当时的出版体制革新与阅读大势变化是同一历史事件中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⑩
浪漫主义阅读伦理的形成
浪漫主义文史家卡莱尔认为:“就一国在特定时期的阅读状况和整体阅读行为所构成的阅读伦理而言,勾勒出一幅比较清晰的画卷还是可能的。”(11)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国成为阅读之邦,阅读范围与题材也随着教育程度的增长而递增。即使是长期以来只阅读英语版《圣经》和其他篇幅短小的通俗读物,并无太多闲钱购置精美多卷典籍的低收入者,也能够得到长篇文学作品。与此同时,教学大纲也将文学选读设为学生阅读的一项基本内容。通过阅读各种印刷文本,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开始逾越已有的非此即彼的狭小空间。此时的阅读已是一种覆盖社会各层面的整体行为。尽管浪漫主义作家面对的读者“具有社会、政治和教育背景上的巨大差异”(12),但是当席卷全国、囊括各类人群的阅读大势到来时,“一场不啻为阅读伦理学上的革命裹挟着读众浸淫印刷文本时所形成的道德评判、接受标准与新的读者—作者关系扑面而来”(13)。阅读之邦的形成既标志着“英国历史上最后一个政府企图通过控制出版业而掌控人们思想时期的结束”(14),也标志着一种全新阅读伦理的到来。这种阅读伦理除了涉及人际关系建立与处理的传统含义之外,主要指的是在全民皆读的特殊时期所形成的读者—作者—作品之间的关系,所以又具有特殊的生成环境、时代特征和特色。在这种强大的阅读伦理形成的过程中,书刊的广泛发行、图书馆的普及和民众尝试写作三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浪漫主义时期报刊的印刷发行鲜有间歇期或淡季,此间发行的文学月刊有近十种之多,(15) 还有《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和《布莱克伍德杂志》(Blackwood's Magazine)等当时最主要的文学评论期刊。(16) 其他各类影响力稍弱的评论也多达19种,此外,还有《观察家》(The Examiner)在内的6种文学报纸。改革派和评论家的论争已经获得了空前的关注,并得到了诸多文学、政治评论杂志的青睐。《戈尔贡》(The Gorgon)杂志就针对当时的状况对自己的办刊方向作了重新定位:“我们推出此刊首为开智,次为巨变作思想准备。”(17) 此时之所以有不同受众的相同阅读伦理的出现,报刊杂志的自由发行与评论观点的激烈交锋功不可没。正如《自由之冠》(The Cap of Liberty)所言:“知识的普及源于自由公正观点的阐发,双向友谊、愿望、自信都是知识普遍传播的结果。”(18) 《改革家登记簿》(Reformists’ Register)明确指出,当时各种不同的时事观念与文学解读交锋的实质是“一场关于知识与权利的论争,而从长远来看知识占上风、阅读伦理得到趋同式发扬”(19)。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读者,各类文学报章不遗余力地与政府、对手甚至与传统阅读习俗进行角力,而塑造对手也构成了浪漫主义时期文学评论的一道独特风景,论战双方所摆出的各种真真假假的证据尤其引起读者的兴趣。
在这股阅读潮中,有一种现象常被忽视:图书馆在新的阅读伦理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阅读与教化目的挂钩以及专业人士对知识分类的提倡,使图书馆的作用得到了空前的提升,这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阅读伦理的变化和文学书籍的流通。以百科全书教化民众、以清晰的分类服务读者,是此时图书馆建立的目的,将文学书籍从科学类图书中分离出来也是当时图书馆的一个初衷。同时,“图书馆聚焦于知识世界,提供的是一种意识模式——社会所知与如何得知”(20)。于是从19世纪初开始,“就有各式私人图书馆、教区图书馆、学校图书馆、咖啡屋图书馆以及付费使用的纯商业图书馆”(21)。在新的阅读伦理的形成上,图书馆的作用并不止于鼓励和刺激文学的传播,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扮演一个开化思想的工具。曾经只为少数精英和权贵所得、所阐释的文学作品,现在终于可以在图书馆里为普通读者所唾手可得了。
尝试写作和加入评论的人数的激增也是促进新阅读伦理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此背景下,文学专业市场与纯粹文学创作领域的空间虽未被彻底打破,但担心与焦虑在浪漫主义作家的心底与日俱增,在如何处理好与出版界和阅读界的关系上,他们也变得更加忐忑。文学书籍的生产和消费的新形式形成了一个对“经典作家”的判断标准:“他到底出了多少书?”拜伦、司各特、罗杰斯、布鲁姆菲尔德、坎贝尔等曾位居畅销书作家之列,而六大经典诗人中的华兹华斯、济慈和雪莱却并不像现在人们想象的那样,个个都是争相抢购的对象。对浪漫主义诗人来说,以量取胜的标准无疑会将他们“跻身英国诗人行列”(22) 的梦想击得粉碎。在这个买方市场里,大众的欣赏口味决定着书籍的定价标准。当朗文公司为《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1800)第二版支付80英镑时,另一家公司却为布鲁姆菲尔德的《农民的儿子》(The Farmer's Boy,1800)支付4,000英镑。六大诗人中写作最快、作品最畅销的拜伦也不是布鲁姆菲尔德的对手,而前者作为经典诗人的地位是后者所无法企及的。
浪漫主义阅读伦理的新特点
“随着文人庇护制的衰落、小说和杂志的兴起以及规模化阅读大众的出现”(23),英国的阅读伦理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新的阅读大众的整体欣赏和评论水平参差不齐,新的阅读伦理中产生了专业与业余评论家的巨大分野。铺天盖地的评论在影响作者声誉的同时还影响读者的判断、作品的销售。若以作品销量为标准,今天所谓的六大经典浪漫主义诗人没有几个能位列“经典”之中。蒙哥马利曾在“宗教浪漫主义”方面著述颇丰、销量可观;布鲁姆菲尔德的《农民的儿子》可能是当时流传最广、出售最多的作品之一;躬耕垄亩的克莱伯的诗歌作品比“湖畔派”的要抢手很多;普洛克的诗歌曾是19世纪再版次数最多的作品之一。这些人的名字现在还有多少人能够记得?销量标准也导致了浪漫主义诗人创作后期的叙事转向,试图与读者大众和解。
其次,大众阅读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个人知识水平、宗教道德标准和满足娱乐需求。大众阅读的首选是具有可读性、好理解的古代历史、虚构小说、宗教与道德类书籍以及诗歌作品。这种单纯的阅读取向影响了新阅读伦理下的读者、作品、乃至整个社会的人文精神。赫兹利特曾高度赞扬出于个人爱好并以道德修养为目的的阅读取向:“我们现在的观点与社会主流话语都是书籍之光照亮的结果,是心灵与心灵交流的结果。书籍与阅读已经将偏见和权利的堡垒摧毁,并势必永远与暴力和邪恶相抗衡。”(24) 新的阅读伦理受众多作家欢迎的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无形的压力。既然如此阅读使万物“无所遁形”,那么大众的评论与出版市场的自我淘汰也是非常严酷和无法控制的。
再者,阅读大众作为一个群体在欣赏作品时几乎不关注作者的身份和性别。在整个浪漫主义时期,除了“《威弗利》的作者”(25) 以外,鲜有读者关注作者的身份。而与此相对的出版创作现象则是,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多是匿名出版。此举之目的在于:匿名出版不仅可以使出版商与印刷商避免诽谤罪或有伤风化罪的起诉,还能使在民间流行的名不见经传的作品获得受众和市场的双重奇效,因为有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的作品常常会被假托出自名家而备受追捧。波里多利的小说《吸血鬼》(The Vampire:A Tale,1819)和霍普的小说《阿纳斯塔西乌斯,或希腊人的回忆录》(Anastasius:or Memoirs of a Greek,1819)都是匿名出版,随后大获成功,因为它们都曾在民间被谣传是拜伦的作品。另外匿名出版可以降低作者可能遇到的风险。出版商的目的是商业利益与个人安全双保险,为了确保自己与作者的安全和经济利益,他们经常会要求作者在出版作品时或隐姓名或用化名。匿名出版的行规还包含出版商对阅读伦理施加的一层影响:将小说或诗歌变成一种具有模式统一可被替代的商品,并使阅读与租借变成一种行为习惯。这种欲盖弥彰之举不仅得到作者的默许,同时也是作者与出版商在新的阅读伦理到来之时所作出的调适策略。1809年初拜伦的《英国诗人和苏格兰批评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的匿名出版就属此类,而“《威弗利》的作者”——并不是瓦尔特·司各特——也一直被出版商使用到了1820年。
最后,新的阅读伦理对女性创作的看法依然未能走出传统道德习俗的窠臼。在阅读大众看来,女作者只能算作一个误入歧途的麻烦制造者、一个私闯他人禁地的冒犯者,“她们的身份总是被定义为男人的亲属、妻子或情人”(26)。在浪漫主义的阅读想象中,女性的创作归属感应该来源于她们对男性的依附关系。阅读伦理中所关注的女性的文化中心性(cultural centrality)被社会伦理中女性的从属地位所禁锢着,并“使女性与象征性国族再现关系和文学生产受到严重影响”(27)。
新阅读伦理下的女性创作
女作家在新阅读伦理中遭受的忽略与敌视并由此而引发的女性创作的“焦虑”、“退避”或“求变”行为,是浪漫主义创作史上的一个典型现象。此时,在女性写作话语中已很难分辨出“接受焦虑”和“自我揶揄”(self-deprecation)意识了。著书立说、直面大众,经常使女作家们处于高度压抑与紧张之中。在视男作家为出版市场、阅读伦理的主角的出版体制下,女作家几乎处于一个无法正视自己的尴尬境地:一方面对社会行为规范心领神会,另一方面却被这些法则排除在外。(28) 女性创作之初就与成名男作家同处一个屋檐下时,她们的焦虑感会更加突出。“英国小说之母”芳妮·伯尼关于父亲对其处女作评价的回忆就是典型的“家族焦虑症”的体现:“我很紧张,羞于和他独处。他说‘我读过你的书,芳妮,你不必为它脸红,它有很多优点,真的棒极了!’我激动地靠在他的肩膀上抽泣起来。”(29) “女儿”面对父亲居高临下的“注视”和“抚慰”现出显而易见的“尴尬”。恭从为人谦卑、做事谨慎之道的芳妮对自己作品面世和声名远播是十分恐惧和焦虑的。
英国女诗人谢立丹曾对浪漫主义时期处在全新阅读伦理下的女作家的处境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和精彩的论述。她认为,作为一种权威话语模式,文学几乎全部归属男性的掌控之下,而女性则是这个领地的应受谴责的“闯入者”。在戏剧《发现》(The Discovery,1763)的前言里,谢立丹讽刺了女作家所遭受的歧视与偏见:
一名女犯出现在你的地盘,
虽然战栗,但希冀满怀。
天大的罪过她愿承担,
简单的越界——不倚不偏。
似逃脱者一般跨越疆界,
野心勃勃进军诗坛。(30)
有评论家曾指出,一百年内,英国文学史上出现过几次阅读伦理革命,文学口味的翻新影响了几乎所有作家的声誉,唯独莎士比亚和简·奥斯丁经久不衰。(31) 即便如此,奥斯丁在浪漫主义时期也并不为阅读大众所知并常被各种权威选集所抛弃,作品匿名出版更在情理之中了。读者从来不去查询“奥斯丁小姐”的作品。《情感与理智》的作者是“一个女士”,《傲慢与偏见》的作者是“《情感与理智》的作者”,《曼斯菲尔德庄园》和《爱玛》的作者是“《傲慢与偏见》的作者”。至于一向看不起女性作家的阅读大众和专业评论家也曾想过它们是否为女性所著,但旋即被“女性不可能写出如此佳作”的思维定式所否定。1816年出版的卷帙浩繁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现存作家自传词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he Living Authors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曾将很多匿名作家以真名公示于众,但却对奥斯丁只字未提。
对于拥有文坛名流父母的玛丽·雪莱来说,新的阅读伦理中所呈现的对女性作家的歧视,又被其特殊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所渲染和加深了。在她未入成年之时,就对阅读的影响和“成名”的压力感受超出常人,嫁给雪莱后,“影响的焦虑”愈加深重。在雪莱去世前后,著作等身的玛丽依然是“雪莱身份的一个隐约的延续”(32)。雪莱去世10年后,玛丽依然拒绝了特利劳尼(John Trelawny)的屡次求婚以及要求她把名字改为“玛丽·雪莱·特利劳尼”的请求。在那场著名的讲鬼故事游戏中,玛丽无疑是个胜利者,但她却始终处在自己的作品和作品改编者的阴影中。小说的匿名出版曾引发猜测无数,“但都认为作者应该是个男性,因为对19世纪的评论家和读者来说年轻的玛丽不可能有那么优秀”(33)。玛丽本人十分反感被作为一个职业作家来对待,对虎视眈眈的读者常存戒备之心。据她的朋友回忆:“玛丽一向抵制把自己当作女作家的任何提议,每次造访都会发现她的书桌上堆满了各种用于誊写、订正整理书籍的物件。这一幕往往使她感到非常紧张而又无所适从,好像是正在做一件有悖社会规范和道德标准之事被逮了个正着似的。”(34) 写作对玛丽来说只是个人爱好而已,而她所写的故事读者明显属于浪漫主义“三类读者”之一——私人读者的范畴。(35) 玛丽曾直言不讳地说:“大名付梓——这是个男人的行当——我只希望被遗忘。”(36) 像著书立说、文坛留名等他人倾力而为之事,玛丽都归结为丈夫施压的结果:“我丈夫极力希望我跻身于名人行列,以不辜负我父母的声誉。他总激励我,要我在文坛上一举成名。……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的故事绝无可能以书的形式奉献给世人。”(37) 在玛丽看来,对女性而言,作品问世犹如婚姻生活的开始,在这当中她们几乎无所获得,但却要丧失姓名和身份。而当代“弗兰肯斯坦”研究领域里所谓的“另一个玛丽·雪莱”(the other Mary Shelley)之说(38),玛丽在有生之年是从未想到过的。
即使在《弗兰肯斯坦》(1818)首版序言中,雪莱为了先发制人特别指出:“不应该从本小说的内容推出某种合乎情理却有损于任何哲学理论的论断。”(39) 但这却丝毫阻止不了来自各方的猛烈攻击。有论曰:“这部小说既无原则,也无主题,更缺乏道德因素。”(40) 更为极端的评论甚至认为:“《弗兰肯斯坦》是当今时代臭气熏天的粪堆上结出的最令人作呕的毒蘑菇。”(41) 保守派评论家克鲁克毫不客气地攻击道:“这个作品所呈现的无稽之谈如此恐怖和恶心。它非常虔诚地献给葛德温,很显然是他那一派的代表作。”(42) 即使在持肯定态度的评论中也不乏揶揄之声,如“《弗兰肯斯坦》虽称得上是一流小说,但它的主题有些冒犯之意,行文也不雅观”,“小说气势雄伟、描绘精美、情感细腻,但是依然缺乏一部佳作所应有的技巧和整体架构,难以被当下的阅读大众接受”(43)。19世纪晚期为争取女性选举权而奔走的宣传家们有意将玛丽树立为成绩卓著的典型,但她们却发现《弗兰肯斯坦》成了一件令人尴尬的事。马绍尔夫人评论道:“现在众人皆知‘现代普罗米修斯’的故事——那个令人震惊而又恐怖可怕的寓言式传奇。”(44) 邱吉尔也谴责雪菜:“怂恿玛丽凭女人气十足的浪漫气质写出了一部行动草率、性情怠惰、结构模糊的小说。”(45)
玛丽在面对新的阅读大众和阅读伦理时,向外界展示的是一个自愿退缩与充满恐惧的弱者形象,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被大众遗忘。而多萝西·华兹华斯在创作伊始面对新的阅读大众和阅读伦理时就轻易缴械了,她不但从未发表过自己的记事,而且终生都只作为哥哥诗歌创作的灵感与素材而存在,作为“一颗灿若星辰的哥哥的卫星而存在”(46)。多萝西一生发表过20首左右的诗歌,但对此却极为揶揄。在写给贝蒙特夫人的一封信中,多萝西表达了她在并不理想的阅读与接受环境里对写作与成名的退避之心:“你一直说我非常胜任写诗。你太抬举我了!请相信我,收到你的来信后我就做了很多尝试,但都绝望地放弃了。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纵使我有语言和数字天赋,我也只是奢想能为我的炉边密友、为少数朋友带来些许好处。”(47) 在一幅幅温馨的炉边诗歌颂读与故事讲解的经典画卷中,女性总是配角,多萝西也不例外。在她眼里,“哥哥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最纯洁美好的事情,他是一个受上帝垂青的人,注定志存高远、行为世范,我自己只不过是他身边的辅佐天使而已。”(48) 伍尔夫曾诘问道:“威廉、自然和多萝西本人,难道不是一个整体吗?他们难道没有构成三位一体吗?”(49) 事实上,在新的阅读伦理中,他们并没有构成稳定的三位一体,因为兄妹间的互动不是双向的,后者的名字在与其创作分离的同时又被捆绑到另一个名下。有学者评论说:“多萝西具有一种‘无性’人格,与自我分离的同时,像一株不孕花蕾紧紧地依附在家族的枝干上。”(50)
在一个阅读泛滥、读者越界的新时期,男性成员为了维护家族的尊严,总是将传统价值观和现行阅读伦理视为水火不容的对立物。家族女性不管是纯粹自娱还是为金钱而作,都会被视为行为不检或有伤妇道之举。多萝西曾将《苏格兰旅行回忆录》(Recollections of a Tour Made in Scotland,1803)从出版商那里撤回来,“主要原因是哥哥身为作者的窘迫和变成公众人物的无奈,对她来说实在是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的暗示,这加重了她的焦虑”(51)。1815年当多萝西的3首诗被收进自己编的诗集中时,华兹华斯也不忘向读者解释说这几首诗是从作者那里强行索取的。华兹华斯的女儿多拉即使匿名发表了她的《葡萄牙数月居住记事》(Journal of a Few Months’ Residence in Portugal,1847),她的作为诗坛魁首的父亲仍不忘向外界解释说,那都是出版商督促与“引诱”的结果。多拉的母亲也曾反复告诫女儿:“此生所求唯婚姻而已,至于著述,千万别越雷池一步。”(52) “家兄”、“乃父”身份在浪漫主义阅读伦理中依然盛行,华兹华斯本人就有一套“只可受命、不可违抗”的人际关系处理原则。(53) 在他身边的那群“侍女”中,多萝西无疑是最不可少又最俯首的一位。至于哥哥彪炳千秋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她的记忆、她的原创和她日记中鲜活的观察”(54),都已是不争的事实。
新阅读伦理对女作家的影响在文学名士罗宾逊的一生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罗宾逊的人格面貌和文学策略常常被解读为与她的文学创作相关联的重要组成部分。评论界对如何看待罗宾逊在经典浪漫主义诗人中的地位尚无定论,不过考察她的多面人生还是能为探讨浪漫主义时期关于阅读伦理与女性创作关系带来启示。罗宾逊17岁出版第一本诗集,并在他人的庇护下开始演艺生涯。作为美女名流,罗宾逊在舞台上下迷倒了众多男士,其中包括年轻的威尔士王子(即后来的乔治四世)。这便开启了报章杂志对罗宾逊耸人听闻的人身攻击。在《回忆录》(Memoirs,1801)里罗宾逊提到:“自己从此便不断地被各种宣传册、小报和讽刺画所攻击。稍一露面,旋即被众人盯视。在都市大街上几乎不敢进任何一家商店,生怕招来巨大的麻烦。有时只好待在马车里数个小时,直到围观的人群散开。”(55)
除此之外,她的逸事更是被虚构成低俗故事而广为流传。在流言蜚语甚嚣尘上之时,罗宾逊却并未终止其文学创作。将自己完全置入公众的注视下,罗宾逊不但很好地利用了她在阅读大众中的“坏名声”,而且将阅读伦理高度关注的女性名流效应发挥到了极致。此时,“女性声名俨然已成一个可闻、可感的实在物,昔日那超凡脱俗的气质、灿若星辰的色泽、恍若风中之曲的美妙,都已荡然无存。它的素材由权威者的关注、匹敌者的敬意、卑微者的嫉妒和同侪们的嫉恨所构成”(56)。有评论称:“罗宾逊的爱情诗非常流行,诗歌中的伤感被她作为一个有凄惨境遇的女人对号入座式的策略给强化了。她怂恿读者对自己真实生活中的人格体现和富有刺激性、为流言蜚语所笼罩的生活方式进行深度探察。”(57) 罗宾逊的这个写作策略甚至对她那些并不引人入胜的作品也产生了奇妙的效果。她的传奇剧《梵森泽》(Vancenza,1792)首版当日就销售一空,连她的女儿也承认说:“这部作品的流行应归功于作者个人的名望以及她的诗歌创作给公众带来的不同凡响的传说。”(58) 罗宾逊还用哀婉动人的语言将个人和社会因素悄然植入文学创作中,她常把自己描述成一个具有浪漫情怀的女主角,书的比喻词语和元叙事性评论都有在撰写小说的痕迹:“我早期生活习性中充满了浪漫和独特的气质,它们是我的意志,我从来没有背叛它们的初衷,在我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或多或少地被急切感性的罪恶所引领过。”(59) 而真实的罗宾逊则隐身于她的戏剧角色之中,“她在有意识地塑造着‘后现代’的主观性,那种视自我为流动不居、富有表演性的概念”(60)。1806年就有一篇名为《已故玛丽·罗宾逊夫人的诗歌作品》(“Poetical Works of the Late Mrs.Mary Robinson”)的文章对罗氏“感性”(sensibility)的诱惑作如下评论:
除了感性之外还有什么是上校、船长和上尉情人们的谈资?当感性化身为一个“可爱”的女人,抱怨着朋友的背信弃义、情人的朝三暮四、浮华享乐背后的虚空时,它就最具媚惑之力。还有谁不为此可人的遭罪者所动容?为此猥琐无情的世道所愤懑?打住!我们何不探究一下这些煽情的哭诉发自何人?为什么是上校、船长和上尉的情人?她们豪奢地出卖世界的良言、朋友的尊重、法律的庇护,而获得的不过是空洞无情的承诺,人类最下贱、最自私和最放荡的部分而已!可怜的罗宾逊夫人就是这样一个人物!(61)
在该评论看来,罗宾逊的感性只是一种显示其“心肠冷漠、趣味庸俗、才气拙劣”的混合物。不管此论的政治意图为何,这里所发出的对引诱(甚至是欺骗)的焦虑,几乎可以与一篇对罗宾逊1791年《诗集》的正面评论对读。该论将精美的印刷、优质的纸张和漂亮的作者插图视为诗集的独特之处,似乎暗示着优质材料、优美诗歌加上漂亮作者不仅是诱使读者购买的动力,而且构成了潜在的商品形式。
在出版体制追求名利双收的情况下,在阅读伦理注重个人消遣和男性作家作品的前提下,在女作家不被认可或不入主流浪漫主义创作的背景下,背负“暗夜啼鸣的天使”之名的女作家不但难入大众读者的阅读名单,就连她们的名号都鲜为人知。在她们中间有很多人的作品已经成了当代英国诗歌研究领域里的热门话题,玛丽·罗宾逊、伊丽莎白·兰顿、夏洛特·史密斯、多萝西·华兹华斯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19世纪中期以后,女诗人在英国的文化版图上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地盘。在回顾过去几十年的女诗人的心路历程、创作与接受轨迹后,雷诺兹指出:“在卷帙浩繁的诗歌出版中,女诗人的作品明显增多,声誉有所提升,女士们在诗歌领域大展身手、收益颇丰。阿波罗已经开始打发那些患意妄为的贴身男仆归隐,而选择主妇们成为他的手下。”(62)
注释:
① M.Rose,Authors and Owners:The Inventive of Copyright,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97.
② 一种向报纸和期刊所征收的税种。
③ William St.Clair,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39.
④ Quoted by Lucy Newlyn,Reading,Writing,and Romanticism:The Anxiety of Recep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
⑤ Quoted by Lucy Newlyn,Reading,Writing,and Romanticism:The Anxiety of Reception,p.5.
⑥ James Lackington,Memoirs of the Forty Five Years of James Lackingt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10,p.329.
⑦ James Raven,Judging New Wealth:Popular Publishing and Responses to Commerce in England,1750—1820,Oxford:Clarendon Press,1992,p.126.
⑧ J.G.Lockhart,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vol.7,Boston:Houghton,1861,P.130.
⑨ Clifford Siskin,The Work of Writing,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p.2.
⑩ See John Brewer,"Publishing," in Iain McCaiman,ed.,An Oxford Company to the Romantic Ag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06.
(11) William St.Clair,The Reading No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p.28.
(12) Andrew Bennett,Keats,Narrative and Audience:The Posthumous Life of Writing,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24.
(13) Jon P.Klancher,The Making of English Reading Audiences,1790—1832,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48.
(14) William St.Clair,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p.15.
(15) 如Monthly Review,Monthly Magazine,Gentleman's Magazine,British Critic,European Magazine,Critical Review,Universal Magazine,English Review,Analytical Review。
(16) 《爱丁堡评论》与《布莱克伍德杂志》在主要观点和评论风格上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二者常被视为文学评论界的对手。《爱丁堡评论》和《评论季刊》在当时已非常流行,甚至在“教化不及、政令难达”的爱尔兰的农民那里都能见到,刊物所登关于司各特、拜伦等流行作家的评论已经成了街谈巷议的主要谈资。
(17) Paul Keen,ed.,The Popular Radical Press in Britain 1817—1821,vol.1,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03,p.xi.
(18) Kevin Gilmartin,Print Politics:The Press and Radical Opposition i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England,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122.
(19) Paul Keen,ed.,The Popular Radical Press in Britain 1817—1821,vol.1,p.11.
(20) Alvin Kernan,Printing Technology,Letters and Samuel Johns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p.246.
(21) Roy M.Wiles,"The Relish for Reading in Provincial England Two Centuries Ago," in Paul J.Korshin,ed.,The Widening Circle:Essays on the Circulation of Literat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Europe,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hiladelphia Press,1976,p.105.
(22) 济慈《济慈书信集》,傅修延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218页。
(23) Andrew Franta,Romanticism and the Rise of Mass Publi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1.
(24) William Hazlitt,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Hazlitt,ed.P.P.Howe,vol.8,London:J.M.Dent and Sons,1934,p.17.
(25) 《威弗利》是司各特在1814年发表的第一部历史小说。由于它非常出名,以至于司各特后来的小说都以“《威弗利》的作者著”来做宣传。司各特的系列创作与《威弗利》具有相同主题的小说被统称为“‘威弗利’小说系列”。
(26) Martin Garrett,Mary Shelley,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9,p.34.
(27) Angela Keane,Women Writers and the English Nation in the 1790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4.
(28) See Mary Poovey,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en Writer,Ideology as Style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Mary shelley,and Jane Austen,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84,p.41.
(29) Elizabeth Kowaleski-Wallacw,Their Fathers' Daughters:Hannah More,Maria Edgeworth and Patriarchal Complic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p.11
(30) Carlo Shiner Wilson and Joel Haefiner,eds.,Re-Visioning Romanticism:British Women Writers,1776—1837.Philadelphi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94,p.277.
(31) See William St.Clair,The Reading Nation in the Romantic Period,p.218.无独有偶,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中也将奥斯丁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指出“奥斯丁的反讽明显地具有莎士比亚的风格”,奥斯丁的人物具有莎士比亚式的内在性。详见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198—199页。
(32) Mary Poovey,The Proper Lady and the Woman Writers:Ideology as Style in the Works of Mary Wollstonecraft,Mary Shelley,and Jane Austen,p.147.
(33) J.Paul Hunter,ed.,Mary Shelley:Frankenstein,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96,p.x.
(34) Eliza Rennie,Traits of Characters,vol.1,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1,p.113.
(35) 浪漫主义诗人将读者分为“私人”、“公共”、“后世”三种。他们为“私人”读者言说,为“后世”读者创作。See Andrew Bennett,Keats,Narrative and Audience:The Posthumous Life of Writing,pp.25—26.
(36) William Wordsworth and Dorothy Wordsworth,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The Middle Years,1806—1811,ed.Ernest de Selincourt,vol.1,Oxford:Clarendon Press,1969,p.25.
(37)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作者自序),刘新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页。
(38) See Betty Bennett and Stuart Curren,Mary Shelley in Her Times,Baltimore: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0; Michael Eberle-Sinatra,Mary Shelley's Fictions:From FRANKENSTEIN to FALKNER,New York:St.Martin's,2000; John Williams,Mary Shelley:A Literary Life,New York:St.Martin's,2000.
(39) 玛丽·雪莱《弗兰肯斯坦》(原序),刘新民译,第5页。
(40) W.H.Lyles,Mary Shelley: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New York:Penguin,1975,p.168.
(41) Steven E.Forry,Hideous Progenies,Dramatizations of Frankenstein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Philadelphia:University Press of Philadelphia,1990,p.9.
(42) J.Paul Hunter,ed.,Frankenstein,p.189.
(43) J.Paul Hunter,ed.,Frankenstein,pp.200—201.
(44) Mrs.Julian Marshall,The Life and Letters of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889,p.139.
(45) Richard Church,Mary Shelle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895,p.52.
(46) Rache Brownstein,"The Private Life:Dorothy Wordsworth's Journals",in 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34.1 (1983),p.48.
(47) William Wordsworth and Dorothy Wordsworth,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The Middle Years,1806—1811,p.25.
(48) Meena Alexander,"Dorothy Wordsworth:the Ground of Writing",in Women's Studies,14.2 (1988),p.196.
(49) Virginia Woolf,The Second Common Reader,New York: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60,p.153.
(50) Robert Gittings and Jo Manton,Dorothy Wordsworth,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8.
(51) William Wordsworth and Dorothy Wordsworth,The Letters of William and Dorothy Wordsworth:The Middle Years,1806—1811,p.66.
(52) Susan M.Levin,Dorothy and Romanticism,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7,p.67.
(53) See Phoebe Pettingell,"Two Cheers for Romanticism",in The New leader,92.1 (2009),p.29.
(54) John Purkis,A Preface to Wordsworth,Beijing:Peking University Press,2005,p.32.
(55) Mary Robinson,Memoirs,ed.J.Fitzgerald Molly,London:Gibbings,1985,p.178.
(56) Maria Jewsbury,The History of an Enthusiat,Boston:Perkings and Marvin,1931,p.107.
(57) Jacqueline Labbe,"Selling One's Sorrows:Charlotte Smith,Mary Robinson,and the Marketing of Poetry," in Wordswoth Circle,25.3 (1994),pp.68—75.
(58) Mary Robinson,Memoirs,p.216.
(59) Mary Robinson,Memoirs,p.8.
(60) Anne Mellor,"Mary Robinson and the Scripts of Female Sexuality," in Partrik Coleman ed.,Representations of the Self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Romantici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253.
(61) Quoted by Robert Darnton,"Readers Respond to Rousseau:The Fabrication of Romantic Sensitivity," in The Great Cat Massacre and Other Episodes in French Cultural History,New York:Vintage Books,1985,pp.388—389.
(62) John H.Reynolds,Selected Prose of John Hamilton Reynolds,ed.,Leonidas M.Jone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6,p.422.
标签:浪漫主义论文; 文学论文; 弗兰肯斯坦论文; 读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图书馆论文; 作家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