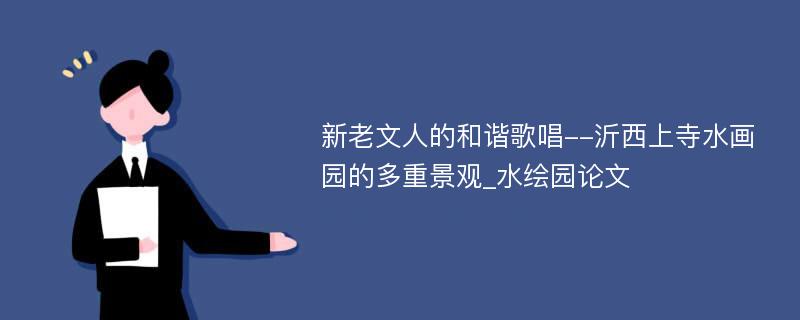
新旧文人的和谐唱和——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的多重风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旧论文,文人论文,和谐论文,风景论文,上巳水绘园修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顺治十七年,王士禛至扬州府任推官,掌管一府刑狱司法,在任扬州推官的五年间,王士禛与明遗民冒襄鸿雁往来不绝,雅聚不断。关于冒、王二人的交游概况,顾启先生在《冒襄王士禛交游考》(《南通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中已作出梳理,本文不再赘述。本文所关注的是冒、王二人共同参与的一次重要文人雅集——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本次雅集无论是“篇什之富、兴趣之豪、主宾之美”①,都足以令未参与之人艳羡不已,而此次雅集中众人所创作的诗歌一反常态地偏离自己原本的创作风格,不约而同地趋近王士禛于扬州期间的诗歌风格。王士禛于此次雅集中的诗作虽只为平平之作,却得到遗民们的交口称赞,这其中的缘故耐人寻味。而和谐唱和的背后,隐藏着的是新旧文人不同的情感需求和利益需求,值得我们去探究。王士禛的“神韵”诗说在扬州期间虽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却已是他诗歌创作的主要风格,这一诗风在此次雅集中表现出极大的实用功能,是该诗风在未来成为文坛主旋律的先兆。
一、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的经过
形成于夏商之际的每年三月巳日于水边嬉游采兰,以驱除不祥的修禊活动,经过长期的演变,与文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文人雅集的重要形式之一。乙巳(康熙四年,1665)仲春,王士禛以书讯冒襄,三月将至水绘园,约为修禊。二月底,王士禛按部下邑至如皋,冒襄喜出望外,出郊迎之,如此郑重其事地郊迎来宾,在冒襄一生中极为罕见,可见冒襄对王士禛来访之重视。
参加修禊的诸子中,陈维崧是冒襄的盟友陈贞慧之子,寄居水绘园读书已有七八年之久,且与王士禛熟稔,是其文友。曾从陆世仪研学“身心性命之学,为人质直而好义,肃毅而温文”②的太仓才子毛师柱因坐奏销案弃举业,经吴梅村之荐,至水绘园读书,也正好赶上参加此次修禊。许嗣隆字山涛,号文穆,乃冒襄之表弟,“神彩疏秀,九龄通五经”③,后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得中进士,官翰林院编修。明遗民邵潜字潜夫,“自号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谐俗,好谩骂人,人多恶之”④。“慕如皋风土而卜居焉,博极群书,工诗精篆隶,持风节不屑下人,贫甚,无妻子童仆,卖文为活”⑤,参与乙巳修禊的时候,邵潜已是八十五岁高龄,带病参与修禊后不久就下世了,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参加文人雅集。冒禾书、丹书为冒襄二子,也名列此次修禊中。参加此次修禊的八个人中,王士禛是仕清新贵,冒襄、邵潜是明遗民,陈维崧⑥、冒禾书、冒丹书乃遗民之后,毛师柱已弃举业,肆力为诗,许嗣隆当时尚未中进士,为后进学子。这些人中,有仕清者,也有忠明者,有带遗民情愫的遗民后代,也有汲汲于文名、功名的新朝学子。这些带着不同政治思想倾向的文人,在水绘园中上演了新旧文人和谐唱和的雅集盛会,吸引着我们去探究其中各种不同情愫的碰撞。
乙巳三月初三日,“天色明霁,桃花未落,春泥已干,风日满美,微云若绡,舒卷天际”⑦,前几日的春雨使得水绘园生意盎然,葱翠可人,园中晴丝飘荡,繁英偶落,台榭掩映于笼翠之间,一水碧波淼淼粼粼,令人心旷神怡。王士禛、冒襄等人先于寒碧堂中品茗,茗罢折入枕烟亭观赏文待诏衡山之《兰亭修禊图记》,后泛舟洗缽池,池上蝶舞蛉绕,水云一色,春风习习,众人陟小三吾后踞月鱼基小酌数巡,复归枕烟亭。胜景美醇引人诗情,王士禛遂提议,“诗不限韵,人不一体”⑧,宾主各踞一景,即兴作诗,共得诗三十八首,含括五言古、七言古、五言律、七言律、五言绝、七言绝六种诗体,冒襄所辑之《同人集》存有“乙巳上巳修禊倡和”诗⑨,陈维崧、杜濬分别为之作《水绘庵乙巳上巳修禊诗序》,冒襄作《水绘庵修禊记》以纪之。修禊当晚,宾主还一起观赏了冒氏家乐演出的《紫玉钗》和《牡丹亭》,但此次观剧,只有冒襄在《水绘庵修禊记》里一语提及,此外再无任何文字记载,故而可以推定,此次水绘园修禊的重心在于诗歌创作,而非戏剧观演。王士禛逗留如皋数日间,六集冒襄水绘园,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可谓文坛盛事,令人企羡。
雅集诗人尽情描绘着明媚的春光和如画的园景,不时回顾千年前的兰亭雅集,歌颂本次雅集的盛况和难得。“此会真难继,吾侪共举杯”⑩,“良朋双绝代,儿辈两盈阶”(11),“人生聚散不可忘,且须痛饮累百觞”(12),“年似永和饶丽景,客同大令自名流”(13),这一幅幅宾主和谐唱和的图景,和雅集诸人的身份、经历之迥异甚不相符,这些新旧文人各有各的愁苦之处,何以此刻能欢愉若此?陈维崧的《洗缽池泛月歌》道出了其中的缘故:
君不见会稽修竹应非昨,王谢清言不复作。伯时丹粉久漫漶,江左巾箱悉零落。人生胜游岂易哉,眼中之人况不恶。酒酣夜阑唤奈何,万事一往如流波。人生有情且作达,忆昨哀乐何其多。(14)
人生苦痛无时不有,与其沉浸于其中,不如将之消解于欢宴胜游中,这是经历了人生起落、世间沧桑,极度感伤后的无奈释然。冒襄早年心怀满腔报国之志,驰骋海内、积极用世,无奈遭遇国变、归隐乡里,却不时遭宵小欺凌,不得安生。在经历了亡国、家变后,陈维崧长期寄人篱下,坎坷的人生境遇及冷酷的现实逐渐磨灭他心中的故国之念及从父辈那继承来的遗民气节,他开始汲汲于仕进,却屡试不售,怀才不遇的落寞感充斥着他的内心。王士禛刚经历了兄长王士禄无端被牵连入狱、论罪落职的沉重打击,使得“本无宦情”(15)的他更加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众人心中的块垒于嘉会雅集中得到暂时的消解,人生苦短多难,于欢乐之时且须尽欢,时代与机遇是自己所无法左右的,只能无奈地逼迫自己淡定地接受现实。
二、杜濬、冒襄对王士禛修禊诗的评价及其原因
由于晚至而没赶上此次修禊的杜濬对王士禛于修禊时所作的诗歌有这样的评价:
吾于七言古颇窃自负,而独意忌王阮亭,今读上巳十首则益有不及之叹矣。或问此诗妙处,余举成句答之,曰“罗袖动香香不已”,曰“挥毫落纸如云烟”,曰“白云欲尽难为容”,曰“近来海内为长句,汝与山东李白好”。也问余七言古自负处何在,余曰:“但觉高歌有鬼神,焉知饿死填沟壑。”如此而已,此诗既经巢民记中品定精详,余特为识在修禊之后,以得避此劲敌,亦属有天幸哉!(16)
王士禛的《池北偶谈》里也存有一段杜濬对自己于此次修禊中所作诗歌的评价:
康熙三年,予与杜于皇(濬)、陈其年(维崧)辈同在如皋,修禊于冒氏水绘园,赋诗。或问杜:“阮亭诗何如?”答曰:“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又问:“君诗何如?”曰:“但觉高歌有鬼神,谁知饿死填沟壑。”(17)
这两段评价其实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杜濬认为,阮亭于水绘园修禊中所作的诗歌放旷不拘、气势宏大、自然天成、毫无凿琢之痕,并举李白《江上吟》“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概之,此一诗句常被用来形容太白之诗的风格,杜濬举于此处,实是以阮亭方之太白。王士禛饶有兴致地把杜濬的评价载入《池北偶谈》中,说明他是很受用于该评价的,他乐于看到别人将之与李白对举,因为这既是对其诗歌艺术造诣的肯定,也是对其文坛地位的认可。然细览王士禛于乙巳上巳修禊所作诗歌,既无太白的旷达之气,也无李诗之自然天授,只是一般的酬唱之作,杜濬之评实乃过誉。王士禛之后的另一大诗人翁方纲在评论这组诗时说:“是坐间立就者,实有兴会而肌理不密。”(18)明确地批评这组诗作乃雅集即兴之作,有偶发之意趣,却言之无物。清人田同之曾云:“诗中篇无累句,句无累字,即古人亦不多觏。惟阮亭先生刻苦于此,每为诗,辄闭门障窗,备极修饰,无一隙可指,然后出以示人,宜称诗家谓其语妙天下也。”(19)可知王士禛之力作,多融合前人精华,苦吟冥想乃成,而挥毫立就之篇,如水绘修禊组诗者,诗思不密,修饰不精,就不一定都能达到不可指摘的艺术水准。再看冒襄《水绘庵修禊记》中对王诗的评价:
先生跂脚坐楼上,隐囊侧帽,望若神仙。摇笔俄顷得七言古十章,一气倾注,首尾无端,大海回风,神龙不测,其兴酣淋漓,几欲乘风而去矣。(20)
王士禛被冒襄形容得气度非凡、宛若谪仙,恭维奉承之意溢于言表。杜濬、冒襄均年长王士禛二十三岁,于明亡后隐逸不仕,尚气节,皆为坚定的遗民,擅长诗文,在文士中享有深望。杜濬多次谢绝富贵者的求诗拜访,于气节有污者如钱谦益之辈,虽亲造其门而不纳,“惟故旧徒步到门,则偶接焉。门内为竹关,关外设坐,约客至,视键闭,则坐而待,不得叩关,虽大府至,亦然”(21)。冒襄自称:“凡我故人有富贵者,余概不先寄书。”(22)以不攀附富贵自居。如此旌尚气节、恃才放旷的二老何以对王士禛这个晚学后生、清廷官员如此推崇备至?
王士禛出身山东新城世代官宦之家,明亡后,伯父与胤自缢殉国,祖父象晋以遗老归隐乡里,故王士禛也算是遗民之后,比一般官员在情感上更接近遗民,也更易得到遗民的接纳。王士禛任扬州推官后,丝毫没有以权压人的官架,他广交布衣,其中不乏遗民逸老,他不仅与遗民酬唱不绝,还从物质、现实中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这使其在遗民中享有很好的声誉及较高的地位。杜濬对王士禛的喜爱应是缘于对其诗的由衷欣赏,杜濬诗学杜甫,诗作“雄浑高确,能直抒其胸臆而涵蓄蕴藉,无卑俚易尽之陋”(23),这与王士禛崇尚盛唐之音,标举“典、远、谐、则”的诗学观点不谋而合。康熙元年(1662),杜濬曾为王士禛的《渔洋山人诗集》作序,不久后与之泛舟红桥,和其《浣溪沙》词,当陈允衡刻王士禛的伯父与胤遗作《陇首集》,并合集于《诗慰》时,杜濬欣然为之作跋。康熙三年(1664)正月初七,王士禛走访杜濬,与之清谈竟日,同年三月,二人共同修禊于红桥,杜濬和王之《冶春诗》,王士禛将修禊所作诗刻为《阮亭甲辰诗》,杜濬再次为之作序。杜濬与王士禛的交往多依托于文学交流,杜对王的情谊是建立在对其文学才华的由衷欣赏之上的。中国文人的恶习之一,仇我者诋之,亲我者誉之,喜从主观情感出发评价事物,所以杜老一得王士禛之修禊诗,便迫不及待为之延誉了。
冒襄之父起宗与王士禛之伯父与胤为同年,故而冒、王之间有故交之情。另外,冒襄也非常欣赏王士禛之诗才。顺治十四年(1657)八月,为送杨通久兄弟归济宁,王士禛与东武丘石常、清源柳焘、益都孙宝侗等诸名士雅集于大明湖畔,举秋柳社。自古文士有悲秋之传统,方其时,大明湖畔丛柳随风轻拂水际,柳叶乍染秋色,微黄欲坠,令王士禛怅然有感,赋《秋柳》诗四章,一时和者就达数十人,此后《秋柳》诗传唱大江南北,和者益众,王士禛的文名也随着《秋柳》诗传遍五湖四海。顺治十七年(1660),王士禛任扬州推官伊始,冒襄就作《和阮亭秋柳诗原韵》四首和之,情韵格调追步阮亭原诗,堪为众多和诗中的上品,并作《秋柳和诗引》阐发关河摇落、台苑凄凉之恨。此外,冒襄在国变后境遇遭际的变化,使得他不得不一改恣肆孤傲的秉性,屈首与权贵之人交游。冒家虽富甲一方,但国变后已无往日的豪势可凭,渐为乡里奸猾欺凌。因此,其结交掌地方刑狱的府推官,未尝没有托庇之意。冒襄在与王士禛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热情超乎寻常,这与冒氏当时的境况有着莫大的关系。冒襄出身官宦世家,鼎革后隐居如皋,广交天下名士,招致无虚日,家道渐衰。“襄既隐居不出,名益盛。督抚以监军荐,御史以人才荐,皆以亲老辞。康熙中,复以山林隐逸及博学鸿词荐,亦不就。”(24)冒襄祖上的功名皆来自故明,其本人为保持遗民气节,自绝仕途,不赴清廷征招。如此,冒氏无论在权势还是家境方面都已大不如前。此外,冒襄曾于辛巳、壬辰两次疏财赈荒,“所全活者不下数十百万”,“然皋俗喜訾警,不乐人为善,其异己者又群为不根之语以惎之”(25)。在冷嘲热讽、恶意中伤的环境下,冒襄始终隐忍着,“匪不能言,匪不敢言,念先人席极盛时,世以靡争忘怨自处,改革后余十七年来,诟唾到门及面未常与人色忤”(26)。甚至连子孙四世守护的逸园放生池被邻人凿塘排水,竭泽而渔,也只能“目惨心摧不敢问”(27)。在这样的情势下,他只有两条途径能改变境遇:其一,子嗣取得功名。王士禛在壬寅冬给冒襄的信中提到:
亟引秦箫传闻近状,知鬼蜮伎俩,无所不至,唾面自干固是一着,然源源而来,殊不可训,宵小之辈起而效尤,此岂可郁郁久居者哉?以弟臆,今惟中翰一席,地望清华,无仕宦之苦,而可为门户之计,计无出此,谷梁、青若有一于此亦足矣。(28)
王士禛推心置腹地提出能有效杜绝宵小欺凌的最好办法就是冒氏子弟能得一功名,其实冒襄早已明白此点,从顺治十一年(1654)始,就携儿应试金陵,后又先后遣两儿游学京师,从龚鼎孳治学,数年不归,以博一第,然终未如愿。其二则是广交权贵,以得庇护。在这一点上,冒襄热衷于与王士禛的交往就是显例。王士禛仕扬期间,冒襄不仅为王士禛画屏障,多次题扇面,亲访寓所,送端午节礼、生日礼,还为王所著的《渔洋山人诗集》、《维扬信谳》作序,将自己所珍藏的董其昌纪游小帖作跋后割爱相赠,为作寿诗,等等,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而冒襄的屈尊下交也得到回报,王士禛不仅为其弟冒褒延誉、为其子丹书多次托友相助(未详何事),从各种渠道帮冒襄了解如皋练饷之事,更重要的是,在冒襄受乡中宵小欺辱的时候,能挺身而出,惩治那些狂妄之徒,冒襄的良苦用心终得回报。在现实利益面前,冒襄对王士禛极尽拉拢之能事,对其诗作自然也是赞不绝口,视为天成。
三、修禊背后新旧文人的情感需求及利益需求
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是冒襄和王士禛等人一起参加的具有代表性的文人雅集。在这次雅集中,新旧文人和谐唱和,丝毫没有因为彼此的身份、政治倾向的不同而产生任何龃龉。清初的知识分子,从政治倾向上划分,可分为忠明的遗民,仕清的新贵,及处于灰色地带的,多数成长于新朝,无明确政治倾向,或具有飘忽不定的政治倾向的一般知识分子。政治局势发展到康熙四年(1665),以明遗民为代表的旧文人内心基本都已别无选择地渐趋平静。回顾乙巳前几年的时政,会有助于我们了解明遗民这份无助的平静。顺治十八年(1661)十二月,清平西王吴三桂率军入缅,缅人惧清之强大兵力,执南明永历帝朱由榔以献。康熙元年(1662),吴三桂在昆明用弓弦绞死南明永历帝,南明最后一个政权就此覆灭。同年,当时抗清最为有力的明将郑成功病逝台湾,其子郑经继承父业。在这一年,鲁王朱以海亦病逝。康熙二年(1663),在荷兰师船的协助下,耿继茂、施琅率师攻郑军,克厦门,取浯屿、金门二岛,郑经退守台湾。康熙三年七月,清廷以施琅为靖海将军,征台湾。同年,另一位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明将张煌言被浙江总督赵廷臣擒获,旋被害。至此,中国大陆已无成规模的抗清势力,清廷逐渐控制了大江南北。清廷为稳定民心,减少因灾荒和赋税过重而造成的流民现象,经常减免各地灾赋,如顺治十八年免直隶、江南、河南、浙江、湖广、陕西各州县被灾额赋有差,康熙元年(1662),免直隶、江南各州县灾赋有差。二年(1663),免直隶、江南、江西、河南、陕西、浙江、湖广、四川、云南、贵州等省二百七十余州县灾赋。三年(1664),免顺治十五年以前逋赋,免直隶、江南、江西、山东、陕西、浙江、福建、湖广、贵州等省一百二十一州县被灾额赋有差。
清政府通过武装镇压和税赋减免等措施,武力和怀柔政策并用,逐渐控制了大江南北的局势,各地民众的抗清情绪渐趋平复,毕竟百姓揭竿而起为的就是过安稳的生活,所谓国家社稷、夷夏大防是食禄者所谋之事,只要皇帝让百姓安安生生地过日子,百姓对于谁做皇帝是无所谓的。中国文人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事准则和理想,维护家国之兴及严守夷夏大防均是传统文人自认为的天职。明清鼎革二十多年后,多数遗民年事已高,甚至到了耄耋之年,虽仍解不开夷夏大防的心结,但在抗清势力已趋殆尽的情势下,遗民们纵然百般不情愿,却也只能别无选择地接受现实,接受新王朝的统治,甚至寻求如何在新王朝下更好地生存。人失望久了,就会变成绝望。在永历皇帝、张煌言被害,鲁王监国、郑成功过世后,遗民们复明的心最终绝望了。“沧海于今已化尘”(29),此时他们的心与其说是死寂,不如说是历经狂风暴雨后的平和。
复明理想的破灭及清政府通过“通海案”、“奏销案”等一系列案件的大肆捕杀打压,使明遗民陷于沉寂,行为上的抗清活动已基本停止。遗民在无望的抗争及血腥的镇压下,逐渐认清并承认明朝已经灭亡这个事实。毕竟满清王朝已用暴力和怀柔政策巩固了自己的政权,成为国家的合法统治者。遗民出于忠孝之念,执意坚持自己对前明的忠贞,不入仕途,不受征召,这是一种坚持遗民气节的姿态,他们所不能接受的是清政权本身。而这些具有儒家传统思想的遗民同样难以舍弃经世济国的理想,固执地坚持学而优则仕,国家社稷乃士人之责任的原则。所谓“夫新旧即移,天地犹吾天地,民犹吾民,物犹吾物,宁有睹其颠沛,漠然无动,复为之喜形于色者耶?”(30)遗民自己出于忠孝的原则不能出仕,而出于济世的原则却鼓励后代求取功名。原本一体的儒家思想原则,在异族鼎革的冲击下,分由两代人去承担和完成。另外,遗民们对清廷和清官员有严格的甄别,在他们看来,清廷是异族的统治核心,代表的是满清贵族的利益,而官员,特别是地方官员,推力田,兴科教,倡民风,净人心,是替民行道,代表的是天下众生的利益。故而,大部分遗民虽抵触清廷,却并不拒绝和清官员往来,这从精神层面上看,与他们坚守的道义并不矛盾,从现实利益的层面上看,他们不仅可以从清官员那里得到有利于后代仕进的人脉资源,还可以在官员的庇护下得到一些自己出于道义而主动放弃的特权及保障,和官员的交往甚至成为他们自矜于世、抬高身价的资本,如冒襄就曾云:
改革初随先宪副投闲,久安耕凿,国初如按台姜公指名荐举,嗣制台蔡公总漕淮上抚军、林公开府海陵,咸垂注下交,襄惟杜门守分。后巡海按部不登宪院,驻节荒园,式庐之后继以旌门。犹忆水槛片席侍蔡、林两公小坐,而提督杨少保亦过访,相与流连永日,下邑至今侈为美谭。即今小儿在都,蔡公与栢乡相国、合肥司马推解卵(笔者注:原文为“卯”)翼有加。(31)
字里行间流露出与清官员交往而倍感自豪的情绪,这就无怪乎其对与王士禛的交往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了。
而仕清的新贵如王士禛者,作为在异族政权下生存的汉族官僚,他们缺乏对满清政权在本原上的认同感,夷夏大防之念世代传承,流淌在汉族知识分子的血液中,披发左衽、称奴于夷与华夏文明的优越感在他们内心深处碰撞、纠结。对汉文化在精神上的依托,使得王士禛身为清朝新贵却依然流露出对前朝若有若无的哀思及对遗民、义士的同情和敬重。在扬州期间,王士禛敢于为乙酉抗清至死的南明弘光政权的扬州知府任民育及殉国的鲁王监国政权的行人司行人杨定国作传。清廷对待甲申、乙酉之变的态度是不同的,崇祯殉国,明乃亡于李自成之手,满清打着为明之君父报仇的旗号入关,故甲申之殉国士大夫是受到清廷的赞颂的。而南明弘光政权则是灭于满清铁骑,乙酉殉国之士皆仇视满清,故清廷对乙酉死节之士的事迹采取避讳的态度。任民育死节之事,于郡志皆避讳不书,王士禛却冒此大不韪为之作传,还自云“予惧其无传也”,担心任民育之抗清壮举,赤胆为明的精神不为后人所知,且称任、杨二人乃“死义”(32),抗清殉明乃死义,言下之意,清之灭南明实乃不义。从为任、杨二人作传一事,可透露出王士禛潜在的民族情感。且在扬州期间,王士禛不拘身份,广交方文、孙枝蔚、彭孙遹、余怀、董以宁、黄永、巩宗子、丁胤、纪映钟、林古度、冒襄、邵潜、归庄等遗民,并与之诗文唱和不绝。
虽然王士禛同情义士、广交遗民,且于诗歌中不时隐晦地流露出对故国若有若无的哀思(33),但并不意味着他具有忠明反清的思想,相反的,他是坚定地站在维护清政权统治的立场上的,这样的政治倾向从他的诗歌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
《润州怀古二首》(其一)
楚云直于大江流,铁瓮城高落木秋。宋帝南徐犹作镇,萧公北顾更名楼。江山胜迹留三国,海道烽烟动五州。见说孙卢西犯日,青燐白浪使人愁。(34)
《频岁》
频岁孙恩乱,帆樯压海头。传烽连戍垒,野哭聚沙洲。司马能清野,天吴渐稳流。江淮非异土,漂泊汝何忧?(35)
这两首诗作于顺治十七年和十八年,隐射顺治十六年郑成功率兵北伐之事,王士禛在诗中把抗清的郑成功比作晋代犯上作乱,残暴嗜杀的海贼孙恩,表明他的立场是站在拥护满清统治上的,他并不希望郑成功北伐成功消灭满清政权,因为他自己连同兄长皆是在清政权下获得功名,跻身统治集团内。王士禛仇视郑成功北伐,除了出于自身的身份而自然生发的情绪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北伐失败后引发的顺治十八年的“通海案”牵连甚广,使王士禛的一些友人也不幸牵涉其中。作为掌管扬州刑狱司法的官员,王士禛不得不参与审理该案件,令他挣扎于职责与民族情感之间。《渔阳山人自撰年谱》中有惠栋的一段注文,让我们能更真切地了解当时的情况:
先是海寇犯江上,宣城、金坛、仪真诸邑有潜谋通贼者。朝命大臣谳其狱,辞所连及,系者甚众。监司以下,承问稍不称旨,皆坐故纵抵罪。山人案狱,乃理其无明验者出之,而坐告讦者。大臣信其诚,不以为忤,全活无算。(36)
王士禛在不违反律例的前提下,对查无实证的受牵连者网开一面,尽力庇护,而这些受牵连者有些也并非被冤枉,当郑成功攻克镇江、瓜州后,大江南北为之震动,遗民们欢欣雀跃,长江流域众多州县望风归附。王士禛既同情、敬重遗民的遭遇和节操,又仇视残明势力的反攻,这是他思想中民族情感和现实利益的冲突,这一冲突来源于王士禛汉族文人与清朝官吏兼具的双重身份。王士禛具有极为理性的自我控制力,能于职务上尽其所能,尽忠职守,公务之余,以其诗歌为媒介,广交遗民,使这两种身份及由此产生的矛盾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调和。
无论是民族情感也罢,现实利益也罢,都是新旧文人生命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对满清政权民族认同感的缺失,促使王士禛乐于结交遗民,也许从与遗民的交往中,可以使他的民族情感得到补偿,心灵得到安慰。而如冒襄这样的遗民,本为传统的汉族知识分子,他们于明末已经习惯了审美的人生态度及优越的生活品质,易代后的乱离和既有权利的丧失,使他们亟须找到新的依靠和保障。于是新旧文人就毫无隔阂地结合在一起,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展现给我们的,正是各取所需的心态下,新旧文人的和谐唱和。
四、水绘园修禊对于“神韵”诗的实践意义及此次雅集的影响
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之所以能实现新旧文人的和谐唱和,除了雅集众人出于各自的立场和现状,有与对方维持一种友好关系的需求外,还在于参与的文人于雅集中选取了恰当可行的诗歌风格。
在参与修禊的诸人中,除王士禛为诗坛圣手外,其他各位也均为骚雅之士。冒襄“富有才情而兼英雄之正骨”(37),所为诗“沉郁顿挫,清新俊逸,无所不有,婉转以附物,惆怅而切情”(38),陈维崧早年学诗于陈子龙、吴梅村,得其风华秀缛之貌,“又益之以风力,极之以含蓄”(39),游于唐、宋、元、明间,极具风秀骨力。毛师柱“夙以文艺振藻于时”(40),所作诗“既清丽以多姿,复闲淡而有味”(41)。原本诗风各异的众人,于此次修禊中却作出风格相当类似的篇章,均为模山范水、批风抹月之作。这些诗歌中,满眼皆是诸如“离墨山中一宵雨,竹鸡白鹇相应啼”(42),“幽禽时一鸣,缄情向春华”(43),“坐来亭榭清于画,何处笙歌细若丝”(44),“柳幕风含春似海,花堤气暖水如云”(45)的诗句,自然悠闲,平缓冲和,诗中有画,却不直露感情色彩,不显见个性特征,放置一处,难辨为何人所作。应该说,众文人于雅集中创作出风格趋同的诗作并非缘于某个人的刻意倡导,而是众人在无意识中做出的最符合实际情境需求的选择。要使包含着不同身份,不同思想倾向的众文人汇聚一处和谐唱和的关键,就在于避开情感矛盾,他们各自不同的情感若放任自由地抒发,只会令场面尴尬,难以收场。既然众人皆有和谐交游之心,在潜意识中就会选择一种能够隐去个人情感的风格来进行创作。细观众人所作之诗,风格一致地趋近王士禛于扬州期间的诗歌风格。王士禛于扬州的五年间,著作颇丰,诗文集就有《过江集》、《白门前后集》、《壬寅集》、《入吴集》、《癸卯诗集》等,此外还举行了多次如红桥唱和、冶春唱和等大型雅集酬唱,其诗歌对于当地文人早已耳熟能详,其创作风格也为众人所熟知。王士禛在当时,虽还没提出成熟的“神韵”说,但其诗已初具神韵诗之风格,善于融情入景,于看似不经意、实则细腻的景物描写中透露出诗人似有似无、若隐若现的情感,以达到超逸、淡远、自然、含蓄的效果。参与此次雅集之诗人不约而同地采用了这种手法创作诗歌,除了对王士禛本人诗歌风格的欣赏与喜好外,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朦胧、隐晦的风格更容易隐藏各自的情感,使得这些不同身份、不同思想倾向、不同风格特征的新旧文人共创出祥和的氛围,和谐唱和,酬唱中时而飘过几缕隐现的情丝,不可捉摸又耐人寻味。这种风格的诗歌为神韵诗的早期形式,由于它对情感的含蓄涵盖,作者能在一定的尺度中既安全又有效地抒发自己情感。嘉庆《如皋县志》载:王士禛“顺治十七年授扬州推官,公正严肃,文藻赡丽,尝按行皋邑,修禊水绘园,赋诗谈讌,于政事无留滞,皋人深被其泽”(46),并于《艺文志》中存录其修禊诗八首。如皋之人深被王士禛之“泽”,除其勤于政事、公正严明外,其修禊水绘园,推广风雅之举,也给如皋人民带去了精神食粮,可以说,王士禛之修禊水绘园,是其神韵诗风在如皋的一次重要传播。
如果将水绘园修禊看成当时文坛的缩影,神韵诗能将情感差异较大的众修禊文人涵盖于其中,其成功实践初步显示出它强大的实用性和可行性,预示着它可能同样适用于情感倾向更为纷繁的文坛。军事上的成功打击、统治力度的加强使清帝国逐渐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发展趋势,扫除军事威胁后的大一统的国家最紧要的任务就是统一人心,而这恰恰是最难办的事,因为这无法用蛮力达到,而是需要有一个既有利于自己统治,又能为大众普遍接受的学说或理论来协助完成。陈维崧评王士禛诗“温而能丽,娴雅而多则,览其义者,冲融懿美,如在成周极盛之时焉”(47)。王士禛的“神韵”说崇尚盛唐山水诗之超逸、淡远,体现出温柔敦厚、平和冲淡的情感,此类模山范水的作品呈现出的太平盛世下文人闲适、从容的心境让统治者感到安心,并予以赞同。而该诗说中含蓄深远、意蕴悠长的一面又让怀有各种丰富情感的文人得以隐晦地抒发情感,让读者在含蓄的诗意中用想象去填补情感的留白空间。可以说,这是统治者与文人间互相妥协的平衡点,而后来王士禛“振兴诗教于上,而变风变雅之音渐以不作”(48),有力地证明了统治者所选中的这个妥协平衡点的强大作用。尚处于发展初期的神韵诗在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中调和矛盾、增进和谐气氛的成功实践,可以说是这一诗歌风格在后来风靡全国,成为上自统治者、下至拥有各种不同情愫的文人普遍接受的文坛主讴之诗风的先兆。
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是王士禛在扬州(当时如皋县隶属扬州府)期间参加的几次大型酬唱雅集之一,由于晚至而不及参与的杜濬深以此为憾,为撰《水绘庵乙巳上巳修禊诗序》,认为此次修禊“篇什之富、兴趣之豪、主宾之美”(49)更甚于兰亭修禊,这虽为溢美之词,但也反映出了没能参与修禊的文人的企羡、向往之情。冒襄在后来的诗文中多次回忆此次雅集,以能够参与其中为人生一大幸事,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居易录》、《香祖笔记》、《渔阳诗话》等书中亦频频提及水绘园修禊,并有诗回顾此次盛会云:“回首上巳日,渌水开名园。临泛泝洲岛,赋诗映潺湲。片月岩际出,流照苍筤根。晨鼓已复鸣,流连别山樊。为乐能几时,信宿还西辕。”(50)可见水绘园景色之美,文人诗酒之娱深印渔洋之心。由于王士禛的政治职位、文坛地位的不断提升,而使得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成为文人心中所企羡的盛会的典范,同时,它作为一次人生经历,在参与者生命中所占有的重要性也相应地得到提升,如嘉庆年间修的《如皋县志》里邵潜的传中写到“邵潜……年八十有五,同济南王司李阮亭修禊于冒辟疆水绘园”(51),在短短的传记中煞有介事地记入此事,可见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已成为世人眼中、邵潜生命中具有代表性的大事。而参与雅集的诗人与王士禛在酬唱中建立的情谊,甚至成为评判他们诗歌优劣的标准。王抒为毛师柱的《端峰诗选》所作的序中称毛诗“诸体皆善,近作尤工,既清丽以多姿,复闲淡而有味,高者固已追踪王、孟,次亦可以嗣响钱、刘,斯诚诗格之最上者已。余两至京师见家阮亭宫詹,必以毛生为问,云司李扬州时,极文酒流连之欢,宫詹为当代作者,苟非有不可忘,何以使之不忘如是。即宫詹之问,可以知亦史之诗矣”(52)。文坛领袖王士禛之询问毛师柱近况,使得毛师柱的诗作成就在世人眼中得以提升,当年的雅集在多年之后对后学之士尚有强大的影响,不可不为之感叹也!
冒襄的私人园林水绘园因王士禛等重要文豪的来访而更加受到世人的关注,和历史上的“金谷”、“玉山”一样,逐渐成为文人雅集盛会的象征符号,吸引着更多文人的向往和来访。而王士禛修禊水绘园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文学以外的影响,那就是冒襄在如皋的地位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证,乡中宵小在修禊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嚣张气焰有所收敛。而贫困潦倒的遗民邵潜因王士禛的亲访其庐,为之赋诗(53),并邀之修禊水绘园而受到邑令的特殊照顾,即日免其徭役(54),这些都是王士禛个人影响力辐射作用的结果。
注释:
①杜濬:《水绘庵乙巳上巳修禊诗序》,冒襄辑:《同人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85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6页。
②毛师柱:《端峰诗选》卷前赵贞序,《四库未收书辑刊》第八辑第22册,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603页。
③杨受廷:嘉庆《如皋县志》卷十六《人物》,第19页。
④王士禛:《池北偶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34页。
⑤杨受廷:嘉庆《如皋县志》卷十七《流寓》,第220页。
⑥陈维崧参加乙巳上巳水绘园修禊时尚未仕清。
⑦⑧冒襄:《巢民文集》卷四《水绘庵修禊记》,《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99-600页。
⑨需要指出的是《同人集》中的“乙巳修禊倡和”并无囊括参与修禊的所有人的作品,有些修禊诗散见于各人的诗集中,如《冒襄诗集》卷三《乙巳上巳王阮亭先生同其年亦史山涛及禾丹两儿修禊水绘庵即席分体限韵》、卷五《同王阮亭使君洗缽池泛月》等。
⑩冒襄:《冒襄诗集》卷三《乙巳上巳王阮亭先生同其年亦史山涛及禾丹两儿修禊水绘庵即席分体限韵》(其三),《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23页。
(11)冒襄:《冒襄诗集》卷三《乙巳上巳王阮亭先生同其年亦史山涛及禾丹两儿修禊水绘庵即席分体限韵》(其四),第523页。
(12)王士禛:《修禊水绘庵即席分体》(其十),《同人集》卷七,第289页。
(13)邵潜:《乙巳上巳修禊倡和》,《同人集》卷七,第289页。
(14)陈维崧:《洗缽池泛月歌》,《同人集》卷七,第291页。《湖海楼诗集》卷二《洗缽池泛月歌》语句稍异,为“男儿有情且作达,往事哀乐何其多”。
(15)王士禛:《与冒襄书》(其五),《同人集》卷四,第170页。
(16)王士禛:《修禊水绘庵即席分体》诗后注,《同人集》卷七,第289页。
(17)王士禛:《池北偶谈》卷十四,第326页。
(18)王士禛:《渔阳精华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86页。
(19)田同之:《西圃诗说》,《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714册,第420页。
(20)冒襄:《巢民文集》卷四《水绘庵修禊记》,第600页。
(21)赵尔巽:《清史稿》卷五○一《遗逸二·杜濬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3859页。
(22)冒襄:《巢民诗集》卷一《五君咏》引,第484页。
(23)杜濬:《变雅堂遗集》卷一《附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第1394册,第168页。
(24)赵尔巽:《清史稿》卷五○一《遗逸二·冒襄传》,第13851页。
(25)陈维崧:《苏孺人传》,《同人集》卷三,第103-104页。
(26)(27)冒襄:《巢民诗集》卷二《逸园放生池歌》引,第495页。
(28)王士禛:《与冒襄书》(其十五),《同人集》卷四,第172页。
(29)冒襄:《巢民诗集》卷四《丁酉中秋后四日陈其年、方田伯、吴子班、刘王孙同两儿雨宿秦淮寓馆,即席限韵》(其二),第535页。
(30)金堡:《徧行堂续集》卷四《李灌溪侍御碧幢集序》,《四库禁毁丛刊》集部128,北京:北京出版社,第394页。
(31)冒襄:《巢民文集》卷三《上甯鹾台书》,第589页。
(32)王士禛:《渔洋山人文略》卷五《任民育杨定国传》,《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227,第60页。
(33)如顺治十八年(1661),王士禛至南京,宿抗清遗老丁胤水阁,并与之泛舟秦淮,酬唱连日,所作《秦淮杂诗二十首》。大概由于深浸金陵城、秦淮河的浓厚历史兴亡感中,而流露出怅惘哀愁之意,然其对故国兴亡的哀思之情的流露控制得恰到好处,总能处于似有似无的临界线,令人不可捉摸。
(34)王士禛:《王渔阳诗集》卷八《润州怀古二首》,上海:锦文堂,1921年,第4页。
(35)王士禛:《王渔阳诗集》卷十二《频岁》,上海:锦文堂,1921年,第5页。
(36)王士禛:《渔洋精华录集释》附录《渔洋山人自撰年谱》,第2017页。
(37)陈继儒:《冒辟疆寒碧孤吟序》,《同人集》卷一,第19页。
(38)倪元璐:《冒辟疆朴巢诗序》,《同人集》卷一,第21页。
(39)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四《与宋尚木论诗书》,《陈迦陵诗文词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0页。
(40)(41)毛师柱:《端峰诗选》卷前赵贞序,第602-603页。
(42)王士禛:《修禊水绘庵即席分体》(其六),《同人集》卷七,第288页。
(43)(44)(45)陈维崧:《乙巳上巳修禊倡和》,《同人集》卷七,第289-290页。
(46)杨受廷:嘉庆《如皋县志》卷十五《名宦》,第19a页。
(47)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一《王阮亭诗集序》,《陈迦陵诗文词全集》,第6页。
(48)陈维崧:《陈迦陵文集》卷一《王阮亭诗集序》,《陈迦陵诗文词全集》,第6页。
(49)杜濬:《水绘庵乙巳上巳修禊诗序》,《同人集》卷一,第36页。
(50)王士禛:《王渔阳诗集续集》卷十六《将发如皋留别辟疆于皇其年诸子》,第1页。
(51)杨受廷:嘉庆《如皋县志》卷十七《流寓》,第221页。
(52)毛师柱:《端峰诗选》卷前王抒序,第602页。
(53)王士禛:《王渔洋诗集》卷十四《如皋访邵潜夫寄庐有赠》:“万历年中古逸民,沧桑阅尽白头新。张苍已老口无齿,杜甫还惊笔有神。偕隐鹿门空往事,五男栗里只单身。行歌带索吟三乐,好与容期共卜邻。”第2页。
(54)蒋寅:《王渔阳事迹征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12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