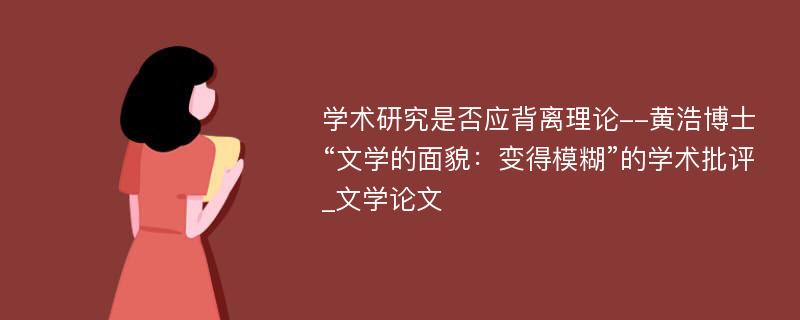
学术研究岂可背离学理——对黄浩博士《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的学术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理论文,学术研究论文,面孔论文,模糊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225(2008)05-0005-06
近若干年,黄浩博士以其“后思路”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文章来探讨文学的历史与未来。笔者在细读时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背离学理的地方。为使讨论更加集中,本文仅对其《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对“后文学时代”文学的历史思索》[1](以下简称《面孔》) 一文进行学术批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文学经典时代”的概念是虚假的
尽管《面孔》直接出现“文学经典时代”这个词只有3次(第5、6、8段),但该文出现了指称同一概念的“文学的经典时代”1次(第7段)、“经典文学时代”5次(第7、9、11、13段和小标题)。可见,“文学经典时代”是《面孔》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应该说,在一篇文章中用不同的名称来指同一概念多少会增加受者阅读上的困难,不过,由于这样做在学理上有时候难以避免[2]20,故无可厚非。
那么,“文学经典时代”指的是什么?《面孔》写道:“是指迄今为止一直被神圣化的文学历史。”(第6段)“在此前的文学年代里(包括整个古典时代和现代,以及社会信息化之前的当代),读者与听者一直是把文学视为‘经典现象’的。人们普遍以神圣的心态去接受文学的各种‘教育’……多次的反复的文本细读,将文本意义和价值反复咀嚼,甚或要配合作家本人或批评家的阅读指导,一部作品的阅读过程才有可能结束……文学的经典时代,就是一个人们用对待经典的虔敬心态去理解文学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们将文学视为经典的时代。”(第7段)从这两段文字中,读者可清楚地了解到黄浩博士的“文学经典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接下来的问题是,像这样的概念所指称的事物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黄浩博士所谓的“文学经典时代”采用的是“规定定义”而非“词典定义”[3] ——其中,“经典”可以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查到,不过,它的外延、内涵与词典中的“经典”的任何一个义项[4] 都差别甚大。具体而言,词典里的“经典”指的是“部分的著作或作品”,而黄浩博士的“经典”指的却是“全部的著作或作品”;词典里的“经典”指的是部分著作具有“典型性”或“权威性”,侧重于客体释义,而黄浩博士的“经典”指的则是所有著作或作品都被视为是“神圣”的,侧重于主体释义。也就是说,黄浩博士的这种“规定定义”是非常之与众不同的,也是很容易让人困惑的。诚然,对于读者的困惑,黄浩博士可轻易地以词典“定义并没有考虑到语境要求”[5] 为由而逃避责难。不过,仍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经典”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术语”[6] ——即是说,其名称与概念的关系是“单参照性”的[2]22,所以,黄浩博士“新造”出来的“概念”在客观上已经是颠覆了惯用的“经典”概念,或者说是抛弃了传统上的“经典”概念。虽然笔者在“颠覆经典”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7],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能指出黄浩博士文章中隐藏着的观点而不能就此展开讨论:
其次,不管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同时存在着喜欢或很喜欢文学和不喜欢或很不喜欢文学两类人,也不管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一样有着认真、深入和马虎、浮浅两种不同的文学接受。对于这样的基本事实,黄浩博士全然不顾,片面地以“社会信息化之前”的“人们用对待经典的虔敬心态去理解文学”来证明那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或许黄浩博士未曾注意到,远在古希腊时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并且有持续影响的探讨诗歌本性”的柏拉图[8] 就对诗歌有诸多的指责[9],那时与柏拉图同属于一条战线的还有色诺芬、赫拉克利特以及诡辩学派哲学家们等[10];而有“第十缪斯”之称的女诗人萨福的许多诗作则因所谓的“伤风败俗”于“1073年在罗马和君士但丁堡被公开焚毁”[11]。这里就不再说古代的文学是如何地多灾多难,只说在所谓的“社会越来越进步”的近一百年里,文学遭受厄运的情况也依旧是屡见不鲜——譬如,1933年,德国法西斯就把海涅的作品付之一炬[12];斯大林时期,苏联“被禁作家的名单”多达3310人[13];中国“文革”时期,许多优秀或不怎么优秀的文学作品被当作“毒草”来铲除,巴金、老舍、曹禺、罗广斌、周立波、赵树理、柳青、杨沫、梁斌、吴强、周而复等一大批作家则受到严厉批评甚或被迫害[14]。
当然,黄浩博士可以辩解说,他所讲的是“普遍性”。但即使这样,它也仍是一种很令人怀疑的说法,因为它无法很好地解释历史上常会出现的下列各类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学现象。第一类是,在同一国度的同一个时期里,有些作家作品会被追捧而有些则不会,前者如巴尔扎克,后者如司汤达[15] ——类似的情况还有朗费罗与惠特曼、斯陀夫人与麦尔维尔[16] 等。第二类是,在同一时空里,某类作品或某一作品在不同人群的眼里是截然相反的。譬如,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通俗文学深受大众喜爱,却遭到了知识分子的蔑视,他们认为这种文学不过是江湖骗子的炫耀和卖弄罢了”[17]。再如,1907年《母亲》刚出版时,各国工人以及社会主义者赞誉不绝,但俄国的知识分子多不喜欢,“觉得它是一个与时代脱节的东西”[18]。又如,20世纪上半叶,英国一些读者对劳伦斯抱赞赏的态度——像拉·阿伯克龙比[19]、摩·爱·福斯特[20] 等,而另一些则反过来——像罗·林德[21]、高尔斯华绥[22]、T·S·艾略特[23]、W·C·皮利[24] 等。第三类是,有些作家在某个时期普遍受冷落(或受欢迎)而到了某一个时期则相反。譬如,《草叶集》刚出现时,除爱默生等少数人给予较高的评价[25] 外,多数反应不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度评价乃至极度赞誉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罗·布坎南[26]、埃·庞德[27]、卡尔·桑德堡[28]、T·S·艾略特[29]、舍·安德森[30]、兰斯顿·休士[31]、巴·聂鲁达[32]、卡夫卡[33] 等。再如,司各特的“作品曾经统治过19世纪20和30年代的书籍市场”,然而,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照勃兰兑斯多少有些夸张的说法:“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只能受到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欢迎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读过但是没有一个已成年的人再会去阅读的作家了。”[34] 第四类是,有些作品历经检验而被保留下来,而有许许多多的作品在出现之后不久便被人遗忘或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譬如,古希腊的悲剧家有许多,但我们今天常常谈起或看到的大致上也只有所谓的“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了,并且这些为我们所见的作品还只是他们创作出来的一小部分。[35] 再如,许多曾广受欢迎的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作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可塞万提斯却完全相反。实际上,即便是像塞万提斯这样的经典意义上的作家,后人首先想到或主要提起的也还是他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尽管其一生“写过不知多少戏剧和中篇”[36]。第五类是,同一位读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对象的态度不一样甚或是截然相反。譬如,对于惠特曼的《草叶集》,亨利·詹姆斯是先抑后扬[37],而阿·查·史文朋则是先扬[38] 后抑[39]。再如,台湾作家陈若曦,先是“很崇拜海明威,不太欣赏福克纳,嫌后者艰深晦涩。仔细读过他的全著后,喜好正好倒过来”[40]。又如,屠格涅夫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是先批评后赞扬[41]。
概括地说,在黄浩博士所谓的“文学经典时代”,远非所有的人“以神圣的心态去接受文学的各种‘教育’”,即便那些总是用“虔敬心态去理解文学”的人,也远非把他所读所听的文学作品都“视为经典”,而是有选择的。进而言之,由于黄浩博士的“文学经典时代”概念歪曲了文学历史的本相,所以是虚假的。
二、“文学经典时代”的因由是可疑的
黄浩博士之所以把“社会信息化之前”称为“文学经典时代”,是因为他断定这个时代“人们将文学视为经典”,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文学资源的短缺”。《面孔》还如此写道:“为了改善由于资源短缺而造成的文学生活的极度贫乏的状态,人们只能选择反复阅读文学文本的‘细读’方式。”(第8段)真的是这样?
的确,今日文学生活资源之丰裕远非古代、近代乃至现代可比。这不仅由于地球人口的增长,加之文化教育的普及,结果包括作家在内的“文学人口”也相应增多,而且还因为文学既有发展又有继承。然而,如果要由此推断出“社会信息化之前”文学生活资源短缺且短缺到“人们只能选择反复阅读文学文本的‘细读’方式”的程度,则太过于牵强。
首先,说说文学生活资源问题。在英国,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仅哈里·布拉迈尔斯的《英国文学简史》所列之重要作品(14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就约有2000部(篇)[42]。在美国,仅二战末到70年代这35年期间,最主要的文学作品就“数以千计”,最主要的作者也有“千余名”[43];80年代仅“原版浪漫小说”的年出版量便达到了上千种[44]。在法国,仅侦探小说的出版,1980年488种,1982年592种,1984年660种,1985年9月至1986年8月695种[45]。在日本,仅1945-1976年期间,被文学史提到的主要作品就约有2000部(篇)[46]。在中国古代,作为文学“正宗”的诗歌作品极其丰富——“唐代三百年,有诗流传至今的人物共有二千二百人,宋代的三百年间更多,接近四千人”,仅陆游的《剑南诗稿》就约有一万首[47]。尽管小说在古代中国的地位低下[48],但仍然是浩如烟海——仅明清时期,值得一提的便有近千部(篇)[49] 之多。在新中国的前30年里,虽然可圈可点的作家作品不多,但数量却不能说少,更不能说“短缺”——1958年的“作家”有“20多万”,当时的“作家协会宣布,中国的专业作家要写出700篇(部)小说、剧本和诗篇”[50]。要言之,以往的文学生活资源并非如黄浩博士所想象的那样“短缺”。
其次,说说阅读方式问题。阅读应有所选择,并应该根据不同的目的以及不同对象的特性和价值来决定是“细读”还是“粗读”,这是古今中外那些有经验的读书人都很注意和强调的,如苏东坡[51]、冯友兰[52]、顾颉刚[53]、培根[54]、王云五[55]、金克木[56]、余光中[57]、爱德华·纽顿[58]、桑名一央[59]、贝蒂娜·苏雷[60]、小泉八云[61]、艾德勒和范多伦[62] 等。进而言之,黄浩博士所谓的“反复阅读”的“细读方式”,远远不是“社会信息化之前”唯一的阅读方式。此外,还应该指出的是,黄浩博士之所言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经不起事理上的推敲。如同奥斯本曾指出过的,有两个原因会导致鉴赏过程的中断:“一是对象不适宜,不能维系审美兴趣,二是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从审美上去感悟那个特定的对象。”[63] 也正像萨特所言:“作品只在与他的能力相应的程度上存在。”[64] 读者会不会或能不能选择“反复阅读文学文本的‘细读’方式”,跟读者自身的条件密切相关。进而言之,黄浩博士所谓的“人们只能选择……‘细读’方式”完全是一种只为了自己的观点而不顾牺牲学理要求的陈述。
三、“经典文学已经死了”的结论是错误的
在《面孔》的后半部分,黄浩博士经由他自己所谓的“文学经典时代”走向“后文学时代”来下结论说“经典文学死了”(第10段)。这是真的吗?非也。
首先,在谈到既存的文学理论时,《面孔》的宣称远多于论证。像第12段就这么说:“经典文学时期所形成并适用的价值体系正趋于‘土崩瓦解’……经典文学价值体系……正在失去‘权威垄断’,失去阐释和评价能力,失去了社会必要的‘文学信任’……”在这里,我们只见结论却不见有效的论证——譬如,“关于文学批评与鉴赏标准的判断”错误在哪?“关于文学本质的判断”有何不妥?“关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判断”何以失效?读者只能看到黄浩博士的罗列,却看不到黄浩博士的任何落实。事实上,只要黄浩博士还抱着一点客观的态度,看看今日中国的文学理论教材(包括由童庆炳、王先霈、董学文、吴中杰等人编写的各种版本)的出版发行情况,就不会匆忙得出“经典文学时期所形成并适用的价值体系正趋于‘土崩瓦解’”的错误结论,尽管它确实是令包括黄浩博士在内的相当一部分人很不满意。
值得一谈的是,“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这一有很长历史的说法,虽然笼统了些,但作为对文学这一艺术的“形象的物质载体”的判断[65] 或“特定的媒介物”的陈述[66] 是妥当的,其作为基本的文学常识,也还是可信的。然而,黄浩博士却因它属于“文学经典时代”的“经典理解”而断定它不适用于“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现象。《面孔》还如此写道:“对于‘后文学时代’而言,由于技术提供了几乎是无限的可能,文学的本质正在被泛化,文学的‘边界’正日益模糊化……”(第12段)从这里,我们知道黄浩博士何以断定“文学是语言艺术”已经是属于过时了的命题的最主要理由。可是,问题并不像黄浩博士所认识的那样。
诚然,今日之艺术形式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各艺术形式乃至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相互渗透也越来越加剧,但这并不等于说各艺术门类已经没有了相对的独立性。从实践的角度看,无论怎样综合渗透,文学仍有它生存发展的“主阵地”——即包括诗歌、小说等在内的不依附于或粘合其它艺术形式的较纯粹的语言艺术领域。实际上,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综合不是今天才有,而是古已有之——如歌曲,就综合了器乐和文学,而戏剧则综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绘画等更多的艺术成分。可是,这并不影响“经典时期”的人把音乐看作是“声音的艺术”或把文学看作是“语言的艺术”的合法性。进而言之,如果说“文学是语言艺术”在所谓的“文学经典时代”还行得通的话,那么,它在所谓的“后文学时代”也仍有存在的价值。从理论的角度讲,“文学与其它艺术形式的区别在哪”是一个不易回避也是不该回避的问题,而“文学是语言艺术”则为此提供了一个也许并非最恰当但肯定是有效的逻辑支点。的确,社会生活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有机体,文学与非文学之间也并非总是泾渭分明,但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放弃理论上予以区分的努力。尽管“非此即彼”式的判断是危险的,可与之相比,“此即彼”式的判断更加危险。我们不能因“人体”含有水分就说“人体是水”,我们也不能因为水存在于人体、蔬菜和各式各样人工食品等越来越多的地方就说“水的本质”“正在被泛化”、“水的边界”“正在日益模糊化”或者说“水已经不是H[,2]O了”。也许说“广告不是文学”或“文学不是广告”的人在今天该受到批评,不过,相比之下,那些说“广告就是文学”或“文学就是广告”的人更难逃责难。
在此,还应该予以特别指出的是,《面孔》中有这么一句让人吃惊的话:“……在这样的文化氛围里,没有人认为文学的边界是模糊的。”(第12段)可以说,凭笔者掌握的有限资料,就能证明黄浩博士说出的这句话“严重失真”——很多年前,指出“难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之间的界限”或“存在着跨越两者之间的例子”的就有包括兹·托多罗夫[67]、保罗·德曼[68]、阿拉斯泰尔·福勒[69]、诺曼·N·霍兰德[70]、加达默尔[71]、浜田正秀[72]、朔贝尔[73]、鲍列夫[74]、苏珊·朗格[75]、韦勒克和沃伦[76] 等在内的许多专家学者。
其次,在论及作家作品与生活的关系时,《面孔》的漏洞很大。概括地说,主要有下列两点。
一是,指鹿为马。譬如,《面孔》这样写道:“经典文学时代……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条件和依据,也是评价作品的‘唯一’标准”。(第13段)仅从这一点便可看出,黄浩博士对于文学理论的历史不甚了然。要求不必太高,一个人只要是认真地学过中国几十年来的文学理论教材就能知道,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命题普遍为“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77],而文学的“条件和依据”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78],至于“评价作品”的标准则普遍为“生活内容、情感内容”和“艺术形式”两个方面[79]——早一点的时候认为应该“把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统一起来”[80],晚一点的时候认为应该坚持“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的统一[81]。
二是,以偏概全。譬如,《面孔》这样写道:“在‘后文学时代’的文学生活看来,文学正在从经典时代的生活虚构而走向虚拟生活……”(第13段)这里暂且不论“生活虚构”与“虚拟生活”是否真的如黄浩博士所辨析的那样,就说黄浩博士的“区别法”是可信的,那也不能证明“生活虚构”在“后文学时代”不重要甚或已经不存在了。而既然它还存在着并将继续存在下去(依黄浩博士的说法:“我不否认……”),还能够与所谓的“虚拟生活”并存,那么,就不宜说文学正在从“生活虚构”走向“虚拟生活”。
最后,在论及读者时,《面孔》存在着严重的臆想倾向。《面孔》写道:“对于‘后文学时代’的文学而言,经典式的读者正在消失,经典式的作家也在消失过程中……这个时代没有了经典的读者,没有了经典的文学环境。”(第14段)这段话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经典式”的读者正在消失,说明此类读者还未完全消失,怎么黄浩博士还要在同一段文字里说“没有了经典的读者”呢?
二是,依照黄浩博士的说法,“经典式的读者”就是“以神圣的心态去接受文学的各种‘教育”’的读者,这样的读者不会“漫不经心”,这样的读者“选择反复阅读文学文本的‘细读’方式”。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地球上有几十亿人口,黄浩博士是如何知道在他所谓的这个“后文学时代”里“没有了经典的读者”的?事实上,这样的读者不但有,而且一些调查还表明有相当的数量——包括中学生[82] 和小学生[83]。此外,从价值的层面看,诚如民连京·卡宁汉所言:“一切好的、真正的阅读都必然是细读;不是细读的阅读无权称为好的、真正的阅读。”[84] 也正像J·希利斯·米勒所说的:“原始语言细读”“甚至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对大学学习和研究也仍然是最基本的”[85]。“后文学时代”存在着“经典式的读者”更不会有什么疑问。至于不“漫不经心”的能够“反复修改”的所谓“经典式的作家”,也同样能够经常看到——如把“30万字的小说先后抄了五遍”的贾平凹[86] 和打算用“一两年时间”“反复修改”一部长篇小说的张抗抗[87] 等。
综上所述,黄浩博士所谓的“后文学时代”与其所谓的“文学经典时代”一样,是虚假的,它严重歪曲了文学生活的本相,其“极端化的排旧立新的决定性因素”“并非真的具有很强的批判力和洞察力”,而只不过像理查德·特迪曼在批判那些诬蔑启蒙运动的人时所说的那样:“与迎合市场经济竞争需求的洗衣皂极为相似,为了占住货架,获取利润,它们也需要革命性。”[88]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也许存在着一个“后文学时代”,但它不是也不可能像黄浩博士在《面孔》中所“描绘”和“规定”的那样。那么,它是何样子的呢?笔者认为,要回答这样一个吃力且不易于讨好的问题,除黄浩博士所特别看重的“理论勇气”和“历史责任感”(第16段)之外,还应该尊重客观事实,依循学理要求,并且有足够的耐心。
收稿日期:2008-07-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