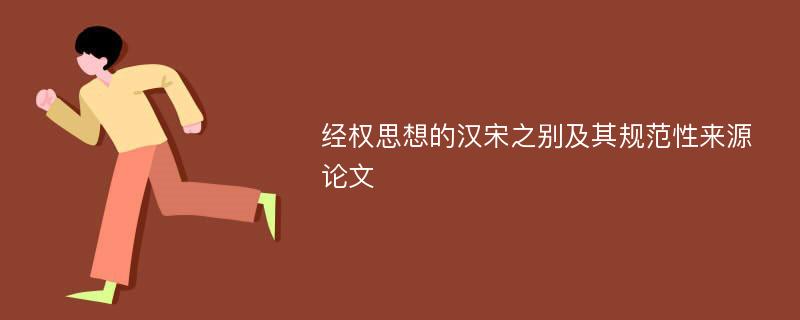
经权思想的汉宋之别及其规范性来源
樊智宁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摘 要] 汉代的经权思想以公羊学为代表,主张“反经有善”。《公羊传》在强调善的结果的同时又在手段上对行权进行限制。董仲舒则以“复正”释权,并且将动机纳入对行权的考量,对行权进行更严苛的规定。宋代的经权思想以程颐与朱熹为代表,主张“权只是经”。程颐将“反经有善”误解为“反经合道”,认为其败坏了经权思想,并以“中庸”“权不拂经”“合宜适变”对经权思想进行重释。朱熹则批判继承了程颐的思想,主张以道统摄经与权,但他并未意识到程颐的问题所在。“实与而文不与”与“理一分殊”是汉宋经权思想区别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 公羊学;经权;程朱;规范性;德性伦理
经权思想是儒家伦理思想体系中重要的内容,亦是儒家指导人们在道德实践中践行道德准则以及将其灵活运用的学说。经者,“织也,从系”(1)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72页。 ,本义是指布帛上纵向的线条,后引申为天地间亘古不变、颠扑不破的道理,在伦理学层面则是指一般的道德准则和规范。权者,“黄华木,从木……一曰反常”(2) 许慎:《说文解字》,第112页。 本义是指黄华木,引申出衡量、变通、权宜等含义,在伦理学层面则是指对道德准则和规范的灵活运用。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对经权思想就有所讨论。《论语·子罕》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首次提出权的概念。《周易·系辞下》亦曰:“巽以行权”,也涉及权的问题。孟子提出“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最先论及礼(经)与权的关系。
然而,后世儒者对经权思想的理解可谓莫衷一是。汉代儒学以经学为盛,其中以公羊学对经权思想的论述最为丰富。(3) 《春秋》三传皆围绕“祭仲行权”讨论问题,《左传》传事不传义,《谷梁传》所言之“权”乃是掌权之义,唯有《公羊传》讨论经权问题。 宋代则以理学为儒学的新形态,其中以程颐和朱熹的经权思想最具代表性。汉儒与宋儒对经权思想的理解存在怎样的差别?二者之所以产生差别的原因何在?这种差别是否具有内在的、同一的规范性来源?这是本文需要讨论的问题。
苏:这种是挑花式图案,有的是较为规则的几何图纹,代表日、月、山、川。还有单钩绣式的植物花草图案,而用得最多的则是羊角花和串枝莲花。围裙是最受我们羌族妇女欢迎的衣物了,也是我们生活必备的服饰之一。它的作用是避免将长衫弄脏,还可以兜东西。以前,我是用自纺自织的纯手工藏青色麻布为底色,用白色棉线或麻线刺绣。围裙上部还会有两个并在一起的方荷包,荷包上也绣着相应的刺绣图案。围裙撩起来,是可以盛放较大物件的。有时跳沙朗舞会用双手撩起围裙的左右角,叫“裙包步”,是一种同手同脚的跳步,而且边跳边唱。我们穿布鞋跳沙朗舞,绣花鞋都是自己绣的,我出门穿有高跟的布鞋。
一、反经有善:公羊学的经权思想
公羊学作为解释《春秋》的三大流派之一,其阐述思想的方式是对《春秋》经文作传或注疏,公羊家对经权思想的阐述亦无出其右。其中,公羊家对经与权关系着墨最多的则是祭仲行权之事。《左传·桓公十一年》交代了祭仲行权的始末:“初,祭封人仲足有宠于庄公,庄公使为卿。为公取邓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郑庄公,曰雍姞,生厉公。雍氏宗,有宠于宋庄公,故诱祭仲而执之,曰:‘不立突,将死。’亦执厉公而求赂焉。祭仲与宋人盟,以厉公归而立之。”郑国执政卿祭仲奉郑庄公遗命立公子忽(郑昭公)为君。宋国支持亲宋的公子突,就设计劫持祭仲,要挟他驱逐郑昭公,改立公子突。祭仲为保全国君的性命和郑国的社稷接受宋国的要求,拥立公子突(郑厉公)为君,于是《春秋》书曰:“宋人执郑祭仲”,公羊学的经权思想主要围绕这句经文得以展开。
(一)善的结果与正当的手段:《公羊传》对经权思想的奠基
在程朱的哲学体系中,“理”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它是事物存在、运行、变化的规律和道理。而在程朱关于“理”的学说中,“理一分殊”是一条重要的命题。“一”是指同一、统一,“殊”是指差异、差别,二者是相对范畴,通常被理学家应用于讨论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之间关系的问题。“理一分殊”首次出现于程颐《答杨时论西铭书》中,其论曰:
朱熹对经权问题的论述大多从二者之间的关系入手,批判继承了程颐的观点。首先,通过上述引文前两句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出朱熹在经权关系的问题上并不满意程颐“权只是经”的论断,他主张在“物事”的层面上区分经与权,即守经和行权是两种不同的行为。对此,朱熹论曰:“以孟子嫂溺援之以手之义推之,则权与经亦当有辨。”(2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116页。 然而,尽管权与经“固是两义”,权依然不能“全离乎经”,这说明朱熹也不赞同公羊学的观点。对此,朱熹亦论曰:“汉儒语亦未十分有病,但他意却是横说,一向不合道理,胡做了……公羊就宋人执祭仲处,说得权又怪异了。”(28)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89页。
国网自动化机房所需要的电能供应是非常大的,电能是自动化机房操作的能源基础,因此,在国网电力调控自动化机房当中,必须要充分保障电能的供应正常,要让供电企业按照国家的标准规定来进行对国网自动化机房的供电,在一定程度上为了能够让自动化机房设备2条以上的电源点,这样的设置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最大化地保证供电的正常运行,若是其中一条供电电源出现问题,那么还有另一条线可以供电,这样能够保证其正常运行,从而去实现机房自动化的运行稳定,若是在某种情况下所有的电路都出现了问题,那么其还有临时供电设备,这样做才能够保证国网自动化机房的正常运行,从而保证其安全性。
在这段传文中,《公羊传》一方面对权做出定义,另一方面亦对行权的条件做出一系列规定,现对这段传文进行分析。“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何休注曰:“古人,谓伊尹也。汤孙大甲骄蹇乱德,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宫,令自思过,三年而复成汤之道。前虽有逐君之负,后有安天下之功,犹祭仲逐君存郑之权是也。”(4) 《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标点本,第98页。 商汤的孙子太甲即位之初耽于享乐,四方诸侯怨声载道。伊尹为保全成汤社稷而流放太甲于桐宫思过,三年之后还政于太甲,太甲成为一代贤君,成汤社稷也得以存续。何休将伊尹与祭仲类比,由此可见,《公羊传》对祭仲能知权是持褒扬态度的。
暗笑了半晌的钱总倒是从王祥身上看到了商机。他起初还在隔岸观火,不亦乐乎。不过看王祥年轻气盛,这次虽然被骗得挺惨,但是打架都是从挨打学起,有了这次被骗的经历,王祥也算是从老道那里出师了。于是就想收下王祥当自己手下:
权与经,不可谓是一件物事。毕竟权自是权,经自是经。(2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87页。
那么《公羊传》是否认为在任何的情况下都可以行权?答案是否定的。这就是“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关于这句传文,何休注曰:“设,施也。舍,置也。如置死亡之事不得施。”(6) 《春秋公羊传注疏》,第98页。 《公羊传》对可以行权的情况要求极为严苛,若非遇到“死亡”则不能行权。这里的“死亡”是指“君必死,国必亡”的结果。具体到祭仲身上,即如果他不答应宋国人的要求,不仅郑国江山社稷不保,郑昭公亦会被宋国人杀害。因此,在这种极端的情况下祭仲才可以行权。
此外,《公羊传》对行权的手段和动机亦有所规定,即“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更为具体的描述则是“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何休对这两句传文并未有过多的发挥,然而徐彦作疏解曰:“生者,乃所以生忽存郑,非苟杀忽以自生,亡郑以自存。”(7) 《春秋公羊传注疏》,第98页。 祭仲承受逐君之罪名,属于自我贬损的行为,他并未以损害他人的方式来行权。并且,从祭仲行权的动机上来看亦是以他人为目的的,他是为了“生忽存郑”,而非“亡人自存”。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公羊传》的经权思想做出如下总结。首先,《公羊传》在权的定义上包含两点,同时这也是其对经与权关系的理解。其一,就行为的内容而言,权必须要与经相反。如果权与经在内容上不加区分或是相似,那么权的说法亦无存在的必要。其二,就行为的结果而言,权的后果也必须是良善的。如果当权的后果不能尽善,那么则必须选择能够造成相对良善的结果的行为。其次,《公羊传》对行权还有三点规定,这些规定反应出《公羊传》经权思想中谨慎的态度。其一,就行权的具体情境而言,行为人必须在遭遇极端的情况下才能行权。其二,就行权的手段而言,行为人在行权的同时不得将他人当作手段,但是行为人可以将自身作为手段。其三,行为人除了不得将他人当作手段之外,还必须将他人作为目的。总而言之,《公羊传》的经权思想在于“反经有善”,其对经权思想的理解和行权的规定也为整个公羊学的经权思想确立基调。
(二)“复正”与善的动机:董仲舒对经权思想的拓展
两汉公羊学的大家当推董仲舒与何休。何休的注解对《公羊传》义理有诸多发明,然而在经权思想上并无太多新意,只是对传文详加解释。相比之下,董仲舒对公羊学的经权思想则有更多新意。他在《春秋繁露》中解“宋人执郑祭仲”经文曰:
祭仲之出忽立突,此执权存国,行正世之义,守惓惓之心,《春秋》嘉其义焉,故见之,复正之谓也。……祭仲措其君于人所甚贵,以生其君,故《春秋》以为知权而贤之。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虽不能成,《春秋》善之,祭仲是也。(8) 重泽俊郎:《春秋董氏传》,《周汉思想研究》,东京:弘文堂书房,1943年,第326页。
董仲舒的这段解经文字由两部分组成,它们分别出于《王道》和《竹林》,日本汉学家重泽俊郎出于这两部分文字皆是对“宋人执郑祭仲”的解释,于是将其合成为一段传文。这两部分文字亦分别在两个方面体现董仲舒对公羊学经权思想的拓展。
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经权思想在儒学史上亦是不容忽视的。朱熹讨论经权问题的文字甚多,仅《朱子语类》“可与共学章”就有二十八条。因此,将其所有文字一一列出、逐条分析实无必要,以下仅选取五条即可对朱熹的经权思想略作管窥。
其二,将善的动机纳入行权的考量之中,即“故凡人之有为也,前枉而后义者,谓之中权”。祭仲虽然做到“存国”与“生君”,但毕竟造成“逐君”的结果。因此董仲舒的这句话有为祭仲辩护的目的。苏與注解此段就援引虞舜放象与周公摄政的例子,并论曰:“事关宗社,心无所利,势有所穷,卒底奠安,醇然见义,非夫凡庶之所能拟也。”(10) 苏與:《春秋繁露义证》,第58页。 祭仲行权从动机上来看与虞舜、周公相似,皆是在遭遇关乎宗庙社稷的大事之时,迫于形势而不得不行权。尽管行为所造成的后果未必尽善尽美,然而他们的动机亦皆是良善的、无一毫私利之心的,故而“《春秋》善之”。可以看到,董仲舒的思想使得权在道德行为的衡量中存在着善的动机和善的后果之间的张力,这也使得公羊学经权思想中道义论的特点更加凸显。
此外,董仲舒还有其他关于权的论述。他在《春秋繁露·玉英》还提到:“权之端焉,不可不察也。夫权虽反经,亦必在可以然之域。不在可以然之域,故虽死亡,终弗为也。”这段话同样有两方面内容。一方面,董仲舒认为“权虽反经”依旧承认权是与经相对的不同事物。另一方面,董仲舒还认为行权有其“可以然之域”和“不可以然之域”。《玉英》的这段话与《王道》《竹林》的内容存在着矛盾。在对行权的定义方面,《玉英》继承《公羊传》的原意,《王道》《竹林》则取返回、归还意。在对行权的规定方面,《玉英》比《公羊传》更为严苛,认为行为人在“不可以然之域”即使是“君死国灭”亦不得行权。相反,《王道》《竹林》将善的动机纳入行权的考量,实际上弱化了对行权的规定。
综上所述,董仲舒对公羊学经权思想的创见在于强调反经之“反”有返回、归还的意思以及行权人的善良动机。表面上看,董仲舒的观点不仅与《公羊传》的经权思想矛盾,甚至在他自身的经权思想体系中也是矛盾的。对于上述的矛盾,我们需要从不同的层面上理解。将反经之“反”理解为相对、相反,这是基于行为表现的层面而言的。将“反”理解为返回、归还,这是基于行为目的层面而言的。质言之,在道德实践中经与权在行为表现层面必然不相同,但是在行为目的层面则都是相同的,经与权所追求的皆是良善结果。相似的,行权的规定无论是否需要考量行权人的动机,其目的亦皆是以高度谨慎的态度将行权规定在“可以然之域”。不可否认,公羊学以反经释权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使得行权沦为权诈阴谋之术。董仲舒显然预见到了这种可能性,因此他才将返回、归还的意思引入权的释义中,同时也将行为人的动机纳入行权考量的范围。
(三)公羊学经权思想与“实与而文不与”
蒋庆认为,由于关注对象的不同,儒学的性质也有不同,公羊学在性质上属于“区别于心性儒学的政治儒学”(11) 蒋庆:《公羊学引论——儒家的政治智慧与历史信仰》,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8页。 。蒋庆的论断恐未尽然,将公羊学简单归类于政治儒学的观点是值得推敲的。但是,公羊学蕴含丰富的政治哲学内容,这是不可否认的。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有云:“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其实皆以为善,为之不知其义,被之空言而不敢辞。”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司马迁意识到不论是君父还是臣子都必须深刻地理解《春秋》之义,其中就涉及经与权的辩证关系问题。就臣子而言,不明经与权的关系则会陷入自以为“善”却不知其“义”的窘境。因此,立足于解释《春秋》的公羊学在经权思想上必然具有浓厚的政治哲学色彩。公羊学对经权问题的讨论亦往往结合具体的政治事件进行,如董仲舒在《春秋繁露·玉英》中即以史事论之曰:
故诸侯父子兄弟,不宜立而立者,春秋视其国,与宜立之君无以异也,此皆在可以然之域也;至于鄫取乎莒,以之为同居,目曰莒人灭鄫,此在不可以然之域也。故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也者,谓之大德,大德无逾闲者,谓正经。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谓之小德,小德出入可也。权谲也,尚归之以奉钜经耳。故春秋之道,博而要,详而反一也。公子目夷复其君,终不与国,祭仲已与,后改之,晋荀息死而不听,卫曼姑拒而弗内,此四臣事异而同心,其义一也。目夷之弗与,重宗庙;祭仲与之,亦重宗庙;荀息死之,贵先君之命;曼姑拒之,亦贵先君之命也。事虽相反,所为同,俱为重宗庙,贵先帝之命耳。
程颐的这段文字目的在于向杨时解释张载《西铭》的“万物一体”与墨子的“兼爱”的区别。其中的详细内容这里暂且不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其中的“仁”与“义”都属于伦理道德的范畴。“理一分殊”在其提出伊始就涉及普遍的道德准则与具体的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
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封也。诸侯之义不得专封,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相灭亡者,力能救之,则救之可也。
曷为不与?实与而文不与。文曷为不与?诸侯之义不得专讨也。诸侯之义不得专讨,则其曰实与之何?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天下诸侯有为无道者,臣弑君,子弑父,力能讨之,则讨之可也。
本研究发现ESRD行透析治疗患者肿瘤坏死因子样弱凋亡诱导剂(sTWEAK)水平较健康对照组明显降低。sTWEAK水平随肾功能逐渐下降而降低,sTWEAK及FMD均随eGFR的减退而下降。随着肾脏损害程度的增加,患者血清sTWEAK浓度相应降低,治疗后浓度较治疗前提高。
根据周代礼制,只有周天子享有专封与专讨之权。一方面,《白虎通·封公侯》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数邑居山川至五十里,名山大泽不以封者,与百姓共之,不使一国独专也。”又曰:“王者即位,先封贤者,忧人之急也。故列土为疆非为诸侯,张官设府非为卿大夫,皆为民也。”前者意图说明天子分封公侯是与百姓万民共享有天下之意,后者意图说明王者即位先册封贤能之士亦是为民。尽管《白虎通·封公侯》这两句话的真实含义都在于表明天子(王者)不专有天下,但同时也表明了只有天子(王者)才有权力施行专封之权。另一方面,《白虎通·诛伐》云:“诸侯之义,非天子之命,不得动众起兵诛不义者,所以强干弱枝,尊天子,卑诸侯。”又曰:“世无圣贤方伯,诸侯有相灭者,力能救者可也。”质言之,前者强调天子在征伐权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诸侯亦只有获天子诏命方能兴兵伐不义。然而后者又进一步提出因时制宜的权变学说,即在没有圣贤方伯主持公义之时,有能力的诸侯兴兵伐不义是被允许的。这亦是《论语·季氏》中孔子“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此言之意。
在公羊家看来,齐桓公与楚庄王身为诸侯,亦未被册命为方伯,他们未得天子之命而僭越天子、方伯之权,故《春秋》书齐桓公为“诸侯”,贬楚庄王为“楚人”以彰显“文不与”。然而,时值春秋乱世,“上无天子,下无方伯”,齐桓公与楚庄王扶危定难、主持公义,他们的行为有利于当时的社会稳定,也有助于儒家礼乐文明的重建,因此《春秋》对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持赞赏态度的,这就是“实与”。
再结合齐桓公与楚庄王的具体事迹,可以对公羊学“实与而文不与”书法中的经权思想有更详尽的了解。“诸侯城缘陵”事件之本源见于《公羊传·僖公十四年》,其曰:“孰城之?城杞也。曷为城杞?灭也。孰灭之?盖徐、莒胁之。曷为不言徐、莒胁之?为桓公讳也。”此时的杞国已然受到徐国与莒国之威胁而灭国,齐桓公在缘陵修筑城墙,协助杞国复国。而《春秋》不言徐国与莒国之威胁,亦是为齐桓公避讳。诸侯相互攻伐以至于灭国,周天子本该及时出面主持公道。但是周天子置若罔闻,于是齐桓公协助杞国存继社稷,相当于重新分封了杞国。“楚人杀陈夏征舒”事件之本源见于《左传·宣公十年》,其曰:“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饮酒于夏氏,公谓行父曰:‘征舒似女。’对曰:‘亦似君。’征舒病之。公出,自其厩射而殺之。二子奔楚。”陈灵公、孔宁、仪行父荒淫无道,皆与夏姬有染,还当着夏姬之子夏征舒之面开极其下作的玩笑。夏征舒发难,弑杀了陈灵公,驱逐了孔宁与仪行父。于是,夏征舒身获弑君之罪,陈国亦陷入动乱。次年冬,“楚子为陈夏氏乱,伐陈。……遂入陈,杀夏征舒,轘诸栗门。”夏征舒弑君而无人讨之,陈国内乱亦无人可平定,楚庄王则在此时出面诛杀了弑君之罪人,这相当于天子出兵为诸侯戡乱护国。(12) 对于楚庄王伐陈的动机,《左传》认为其并非出于道义,而是欲将陈国纳入楚国的版图,后经申叔之劝谏才复建陈国。然而本文主要以《公羊传》的观点为讨论核心,《左传》的记载仅在史料方面对《公羊传》进行补充。
由此可见,按照公羊学的经权思想,齐桓公与楚庄王不得僭越天子与方伯的职权专擅兴废征伐,这是守经。但是他们在周天子无力维护天下秩序之时挺身而出并且取得良善的结果,这是行权。此外,齐桓公城缘陵、楚庄王杀夏征舒与祭仲出忽立突皆是具体的政治事件,公羊学正是借助这些政治事件阐述经权思想。因此,公羊学的经权思想自然也就带有政治哲学的特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公羊学的经权思想仅局限于讨论政治伦理规范,它对个人层面的道德实践同样具有指导作用。国家是大写的个人,它由每一个个人组成,政治生活与个人的道德生活不仅息息相关,即便是隐遁避世的人,只要他还与其他人交往,他的生活亦会有政治因素的存在。总而言之,公羊学经权思想的特点是政治性,这脱胎于公羊学整体的治学方式。因此,公羊学经权思想的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反经有善”。
二、权只是经:程朱的经权思想
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汉宋之争可谓是长期委决不下的话题,汉学与宋学这两种学术形态在各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经权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亦呈现出两种模式,吴震即认为,儒家经权问题“主要以两条线索展开:一是孟子的‘嫂溺援之以手,权也’,一是《公羊传》‘权者反于经’”(13) 吴震:《从儒家经权观的演变看孔子“未可与权”说的意义》,《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 。如前文所述,《公羊传》的思想基本代表汉儒的观点,而孟子的这一条线索则被程颐与朱熹继承发扬。程颐与朱熹的经权思想与汉儒大相径庭,一方面,他们主张回到孔子与孟子,依据“可与立,未可与权”和“嫂溺援之以手”来讨论经权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对汉儒,尤其是公羊学的经权思想颇有微词。程颐反对公羊学以反经释权,他认为“汉儒以反经合道为权,故有权变权术之论,皆非也。权只是经也。自汉以下,无人识权字。”(1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16页。 程颐以“权只是经”取代汉儒“反经合道”,自此以后“诸家论权,皆祖程子之说”(15) 《论语或问》卷10,《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6册,第776页。 。
(一)中庸、权不拂经与合宜适变:程颐对经权思想的重释
程颐对经权问题的讨论散见于他的著作与问答之中,虽然条目不多、文句支离,但是他毕竟开创宋儒对经权思想新形态之先河。程颐的经权思想最集中的体现则如下文所述:
古今多错用权字,才说权,便是变诈或权术。不知权只是经所不及者,权量轻重,使之合义,才合义,便是经也。今人说权不是经,便是经也。权只是称锤,称量轻重。孔子曰:“可与立,未可与权。”(16) 《河南程氏遗书》卷18,《二程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34页。
前期准备工作通过企业财务处或会计师事务所实地调研,根据最新会计准则制定详细的实施方案,通过校内外专家讨论和可行性论证、修改方案,编制实践能力培养指导手册。
诚然,除这段话以外,程颐还有其他讨论经权问题的语录,但是皆不如这段话全面。程颐的这段话分别讨论了权的定义、行权的规定和行权的境界三个问题,现依次对这三个问题进行分析,辅之以其他的语录作为佐证。
接头处剪切强度值最大为1.31 MPa,最小为1.08 MPa。接头处剪切强度与接合面粗糙程度、表面骨料形态等有关,沥青砂浆过渡层与沥青接合效果较好。
首先是权的定义,程颐认为自孔子与孟子之后的儒者对权的概念存在误读和错用。尤其是汉儒,他们以反经释权造成了行权沦为“变诈或权术”的严重后果。因此,程颐重新对权下定义,他提出权的含义“只是称锤”,其作用在于“称量轻重”。显然,程颐的定义回到权最原始的含义,将权视为衡量事物的尺度,而非与经相对的事物。此外,程颐又说“欲知《中庸》,无如权,须是时而为中……何物为权?义也。然也只是说得到义,义以上更难说,在人自看如何。”(17) 《河南程氏遗书》卷15,《二程集》第1册,第164页。 这句话程颐就说得更加具体,权作为尺度就是义。至于何为义?需要结合每个行为人的具体情况而言。质言之,在程颐看来权实际上就是中庸之道。
其次是行权的规定问题,程颐认为行权必须符合两方面的规定。一方面是“经所不及者”,这是在行权范围上的规定。从表述上看,“经所不及者”与董仲舒划分可以然与不可以然领域的说法相似,但二者的内涵则相去甚远。在董仲舒看来,“可以然之域”是行权的范围,“不可以然之域”是守经的范围,权与经的地位是相同的。但是,将行权的范围限制于“经所不及者”,这就使得权与经不可等量齐观,行权成为守经的辅助手段。另一方面是“使之合义”,这是在行权内容上的规定。程颐曰:“夫临事之际,权轻重而处之以合于义,是之谓权,岂拂经之道哉?”(18) 《河南程氏粹言》卷1,《二程集》第4册,第1176页。 行权要求行为人只能在遇见道德两难境地的时候以合乎道义的方式解决问题。此外,由于行权在内容上必须合乎道义,那么权也并非“拂经”,从这个意义上看,权就是变通之经。
最后是行权的境界问题,这是程颐对孔子“可与立,未可与权”的解读。在《论语·子罕》的原文中,共学、适道、立、权四个概念是递进式的关系,权的境界高于前三者。如果权是与经相反的权术、权谋,那么就意味着最高的境界是权诈阴谋之术,孔子俨然是一位阴谋家的形象,这是程颐不可能接受的。因此,程颐认为“若夫随时而动,合宜适变,不可以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几可与权者,不能与也。”(19) 《河南程氏粹言》卷1,《二程集》第4册,第1204页。 权的境界之所以最高关键在于“随时而动,合宜适变”。《中庸》曰:“义者宜也”,宜与义的含义相同,是应当、合适的意思。换言之,行为人达到权的境界就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灵活运用规范,同时他的行为也必然是合乎道义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权的定义问题、行权的规定问题还是权的境界问题,程颐皆立足于批判公羊学以“反经合道”释权的立场。然而,程颐的立足点存在很大的问题,即公羊学的经权思想并非“反经合道”,而是“反经有善”。这两种说法看似相差无几,有学者对此就有“若以其行为结果为‘善’(‘然后有善者也’)便断其行为合乎道义”(20) 吴震:《从儒家经权观的演变看孔子“未可与权”说的意义》,《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 的论断。亦有学者认为程颐出于对公羊学“只问功利不问道义的担忧”(21) 刘增光:《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 ,故而在对行权的规定上更为严苛,此语实有未安。实际上,这两种说法差别很大。“反经有善”强调的是后果,对于行为来说,其所造成的后果是可经验的或是可预见的,无论后果善或是不善皆如日昭彰。“反经合道”强调的是动机,而行为的动机恰恰具有主观性和私密性,其善或不善难以捉摸。从这个层面上看,只强调道义而忽视后果反而更容易使得行权沦为“变诈或权术”。程颐正是由于误解公羊学的经权思想,将“反经有善”与“反经合道”相混淆,故而才有“权只是经”的偏颇观点。
(二)道贯乎经权:朱熹对程颐经权思想的批判继承
其一,以“复正”解释行权。何谓“复正”?苏與注曰:“复正犹言反之正。”(9) 苏與:《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14页。 在董仲舒看来,《春秋》褒扬祭仲在于他能够“复正”,换言之,在道德实践中行权就是“复正”。按照董仲舒的理解,公羊学对权的定义就产生了新的内容。《公羊传》认为权是“反于经,然后有善者”,其中的“反”原本是相反、相对的意思。然而董仲舒以“复正”来解释行权,这就使得“反”又带有返回、归还的意思。
《公羊传》为何要褒扬祭仲能知权?这就涉及到权的含义问题。在《公羊传》看来,所谓权,乃是“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这也是整个公羊学经权思想的核心所在。虽然何休未对这句传文作出注解,然而何休在《公羊传》此段文字之前论“何贤乎祭仲?以为知权也”时则注曰:“权者,称也。所以别轻重,喻祭仲知国重君轻。君子以存国,除逐君之罪,虽不能防其难,罪不足而功有余,故得为贤。”(5) 《春秋公羊传注疏》,第97页。 祭仲在面临“存国”和“逐君”的两难问题中需要综合考量二者的轻重。而在《公羊传》看来,前者的重要性要大于后者。换言之,祭仲驱逐郑昭公是违背君臣之义的反经,但是他的目的则是为了达成保全郑国社稷这一良善的结果。
权与经固是两义,然论权而全离乎经,则不是。(2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91页。
所谓权者,于精微曲折处尽其宜,以济经之所不及耳。(2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92页。
所谓经,众人与学者皆能循之;至于权,则非圣贤不能行也。(2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89页。
随着国家“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健康管理已经上升到非常重要的高度。对于从事健康管理的人员而言,如何正确认识健康管理的核心内涵及在实践中成功的实施至关重要。这就需要我们深入地思考健康管理的合理化模式,并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修正。
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2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89页。
古人之有权者,祭仲之权是也。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权之所设,舍死亡无所设。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杀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为也。
其次,通过上述引文第三句与第四句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出朱熹在对行权的规定上对程颐的观点既有继承也有补充。就行权的范围而言,朱熹主张行权“于敬畏曲折处尽其宜”和“济经之所不及”实际上就是程颐认为的行权“使之合义”与“经所不及者”,这是朱熹对程颐观点的继承。就行权的主体而言,朱熹则区分众人、学者、圣贤,这是朱熹对程颐观点的补充。朱熹认为,行权人必须是圣贤,而众人与学者只能依经行事,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权是时中,不中,则无以为权矣”(29)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89页。 。何为“时中”?《中庸》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换言之,权即是中庸,这是儒家的至高境界,非圣贤不能至之,故而朱熹认为行权是圣人的专利。
再次,通过上述引文最后一句的内容,我们能够看出朱熹将经与权皆归摄于道,这是其经权思想的核心所在。朱熹认为道是“统体”,它既统摄经与权,亦贯通经与权之中,经与权是道的一体两面,即“道之常”与“道之变”,这显然是针对“反经合道”的说法而言的。同时,朱熹亦曰:“不知经自是义,权亦是义,‘义’字兼经权而用之。”(30)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95页。 经与权亦是义的一体两面。因此,在朱熹将经与权归摄于道,其实是将二者归摄于义,“反经合道”意味着“反经合义”,这与程颐“何物为权?义也”的说法是相同的。
综上所述,朱熹的经权思想在表面上显得暧昧不清,实际上立场坚定。他尽管批判程颐“权只是经”,然而又多次为其辩护,其曰:“程先生‘权即经’之说,其意盖恐人离了经,然一滚来滚去,则经与权都鹘突没理会了。”(31)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88页。 又曰:“伊川见汉儒只管言反经是权,恐后世无所忌惮者皆得权以自饰,因此有此论耳。”(32)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89页。 质言之,在朱熹看来,程颐是由于纠正公羊学经权思想的流弊才有此矫枉过正的言论。诚然,朱熹亦有调和程颐与公羊学观点的意图,认为“公羊以‘反经合道’为权,伊川以为非。若平看,反经亦未不是。”(33)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3册,第990页。 但是,从朱熹仍然将公羊学的经权思想理解为“反经合道”来看,他显然未意识到程颐观点的问题所在。
2019年博览会的最新亮点是4月2日举办的工业先锋峰会,它将汇集各领域的思想领袖和创新者,共同探讨未来工业、商业和社会的战略和方案。
(三)程朱的经权思想与“理一分殊”
《公羊传》是公羊学思想的根本经典,同时也是公羊学家发明新意的基础文本。因此,公羊学经权思想最直接的体现就在《公羊传》对《春秋》经文的解释之中。《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解释“宋人执郑祭仲”的传文曰:
《西铭》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则二本而无分。(原注:老幼及人,理一也。爱无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弊,私胜而失仁;无分之罪,兼爱而无义。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胜之流,仁之方也;无别而迷兼爱,至于无父之极,义之贼也。(34) 《河南程氏文集》卷9,《二程集》第2册,第609页。
有时候我也想,这个谢瑞天是不是真的对我动了感情。没错,世界上有钱的男人大把,但世上漂亮迷人的女人更是不计其数。他为什么要在我身上作这么大手笔的投资呢?
可以看到,董仲舒提到的公子目夷、祭仲、荀息以及卫曼姑四人的事迹,皆是关涉宗庙社稷的大事。而董仲舒的“可以然之域”“不可以然之域”“大德”“小德”“正经”“权谲”等一系列有关经权思想的概念、范畴和问题都与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有密切的关联。换言之,公羊学的经权思想必须以政治事件作为质料阐明道理,其具体的运用以“实与而文不与”的书法尤为明显。“实与”是《春秋》对乱世中的某些政治行为给予实际的肯定,“文不与”则是由于这些政治行为违背礼制,《春秋》给予其文辞上的否定。这里以《公羊传·僖公十四年》解释“诸侯城缘陵”与《宣公十一年》解释“楚人杀陈夏征舒”为例。
朱熹继承了程颐在伦理道德领域的应用“理一分殊”的思想,并且还有更为详实、细致的讨论。朱熹对“理”的理解极为宽泛,他认为“理”不仅包含伦理道德的规范,还囊括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规律。朱熹关于“理一分殊”的论述亦内容丰富、不一而足,以下仅选取两例与道德规范相关的论述。
如果电动机选用变频调速方案,Tt和Tr都取常数,在电动机启动时,Tt可取电动机的额定转矩倍数为1.7[5]。建模分析中,取弹性轴的弹性系数k=10N,然后分以下几种情况讨论。
理一也,以其实有,故谓之诚。以其体言,则有仁、义、礼、智之实;以其用言,则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实。故曰:“五常百行非诚,非也。”盖无其实矣,又安得有是名乎!(35)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1册,第104页。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物物各异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36)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2册,第398页。
将这两段论述与“经者,道之常也;权者,道之变也。道是个统体,贯乎经与权”这句话综合考察,可以看出,朱熹的理与道皆是最高的道德准则,其内容含摄仁、义、礼、智等儒家最基本的德性规范,又由于“所居之位不同”,这些德性规范在具体实践中发用亦各不相同,如仁、义、礼、智发用为“四端”,君、臣、子、父亦由于其位次身份而流行为各自所要求的规范。质言之,在朱熹的经权思想中,道即“理一”,经与权即“分殊”。至于仁、义、礼、智等种种德性,君仁、臣敬、子孝、父慈等种种规范,皆属于“分殊”中经的范畴。然而,在道德实践的过程中,经的运用难免会遭遇一些困境,于是异于经所要求的权就因此应运而生。以“孝道”与“孝行”为例,对子女而言经的规范就是要求子女应当孝敬父母,不得违背父母之命。可是,当父母之命威胁到子女的人身安全的时候,就需要改变经所要求的规范来排解其中的矛盾,这就属于“分殊”中权的范畴。
对人防地下室和楼梯等部位进行安全照明软件分析,根据规范要求,并通过灯种类的选择、灯步距的设置或改变灯的瓦数来进行优化,选择既满足安全照明,又可以降低能耗的布置方式,地下室软件照明分析伪色如图6所示。
结合“理一分殊”审视程颐与朱熹的经权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他们何以主张“权只是经”的缘由。经与权皆是道的一体两面,道是“理一”,是最高的、普遍的道德准则,同时它也包含儒家所提倡的各种德性。经与权是“分殊”,是道在不同位次与不同情境中的变化流行,前者表现为不同身份的个体所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与所应当具备的德性,后者表现为在不同情境中的个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改变常规的行为准则。总而言之,从“分殊”的层面上看,经与权有明确的界限,守经和行权亦不可混为一谈。从“理一”的层面上看,经与权都具有相同的本原,守经和行权皆是道在道德实践中为追求至善的表现,程颐与朱熹是在这一层面得出“权只是经”的论断。
三、内在与德性:经权思想的规范性及其来源
伦理思想的作用是指导人们做出正确行为,因此,一切伦理思想都应当具有规范性。换言之,规范性是伦理思想的本质特征。(37) 麦金太尔认为规范性仅存在于规范伦理学之中。但是,科尔斯戈德则认为德性伦理学规范的是人的品德,元伦理学则研究规范性本身的问题,实际上都关注规范性,具体内容本文不赘述。 儒家的经权思想亦不例外,不论是经还是权,它们皆具备某种强制性,这种强制性要求人们的行为符合它们的准则,这就是规范性。因此,探究经权思想的规范性及其来源是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任务。
与此同时,当前中产阶级的崛起亦是俄罗斯的政治稳定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一群体对于执政者的权力垄断愈发表现出政治多元化要求和更多的民主诉求。一如福山所言:“赢得政治自由,不是国家权力受到挟制时,而是强大国家遇上同样强大社会的制衡时。”〔4〕对更民主的参政制度和更开放的政治环境提出诉求的现象随着这一社会群体力量的提升,不可避免。
规范性的来源形式分为内在与外在两种。内在规范性的来源是行为人的自身,它根植于行为人自身的情感或理性,外在规范性的来源则是行为人之外的主体,如社会的风俗、宗教的律令、国家的权威。依照这两种形式,我们可以对经权思想的规范性来源做出一番考察。对于权来说,无论是公羊学的“反经有善”还是程朱的“权只是经”,皆强调行为人在行权的时候要结合具体情况,综合考量行为的后果、动机甚至手段。在这些思维活动中,行为人自身的情感与理性皆是其行权规范性的来源。但是,对于经来说,问题则显得更为复杂。经强调在一定的关系中,居于某个位次的人需要遵循相应的规范。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儒家针对这些规范制定相应的礼,以便于指导人们的实践。换言之,守经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守礼,礼所包含的等级秩序、纲常节目成为守经行为规范性的外在来源。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经权思想的规范性在来源上存在矛盾。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体系中,礼亦来源于行为人的自身。在《论语·阳货》中,孔子有言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在《八佾》中,孔子亦曰:“人而不仁如礼何?”其表明儒家的礼不仅是外在的行为规范,它是源自于行为人的德性。孟子更进一步,他在《孟子·告子上》中认为催生礼的德性是“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更加确证经与礼的来源是内在的。因此,在来源形式上而言,经权思想的规范性属于内在规范性。
经权思想在规范性的来源形式上是内在的,那么其具体来源是什么?这是接下来需要讨论的问题。按照孔子与孟子的理论,经所要求的规范源自于行为人的德性,这一点不难理解,问题在于权是否亦源自于行为人的德性。譬如公羊学的经权思想,它不仅在权的定义上强调其必须带来善的后果,在对行权的规定上亦强调“不害人以行权”的手段正当性。此外,在程颐的经权思想中亦有强调权是“中庸”,行权需要合乎道义的内容。因此,行权似乎兼具后果主义与道义论的特点,权所要求的规范更多是源自于理性的反思,亦或是自身意志的某些法则。换言之,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经权思想是属于德性伦理还是属于规范伦理。
对于这个问题,朱熹通过“理一分殊”将其解决。道是“理一”,经与权皆是其“分殊”。道是人天生的纯然之心,经与权是人在道德实践中根据不同情况所呈现出的规范,经与权甚至一切道德准则都是人心中道的发用流行。道的发用流行并非是纯粹的,这是经权思想与西方近代的规范伦理学不同之处。道所呈现出的规范是绝对不能够脱离行为人的具体位次与现实情况的,它一定涉及行为人的情感,而非纯粹的出于剥离感性杂多的自由意志与理性算计。事实上,经权思想所能体现的重视个人理性与情感的交融是中西方古典伦理思想中皆存在的特色,换言之,在西方表现为理性对欲望、激情的控制,在中国则表现为道心与人心的斗争,具体到经权思想中就是道“贯乎经与权”。
总而言之,经权思想的规范性是内在的规范性,它的具体来源是行为人的德性,它对行为人的德性具有很高的要求。如果行为人的德性不足,其守经尚且无碍,至于行权则难免流于“变诈或权术”。因此,公羊学与程颐的经权思想中对行权都抱有极其谨慎的态度,并且皆对其作出许多严苛的规定,甚至在朱熹看来只有圣人与君子才能行权。
四、结 论
综上所述,自孔子与孟子以降,儒家对经权问题的讨论以汉儒与宋儒为盛,其中汉儒以公羊学为代表,主张“反经有善”的经权思想。并且,公羊学的经权思想往往结合具体政治事件得以阐发,因此具有较为浓厚的政治哲学色彩。然而,以程颐与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将公羊学的“反经有善”误解为“反经合道”(38) 首次提出“反经合道”的是曹魏的王弼,其注“巽以行权”时有“权,反经而合道”之语。吴震认为王弼基本上承接汉儒思想,亦可认为是汉儒的观点,此语恐非。参见吴震:《从儒家经权观的演变看孔子“未可与权”说的意义》,《学术月刊》2016年第2期。刘增光持相反观点,认为程颐的确误解汉儒之论。参见刘增光:《汉宋经权观比较析论——兼谈朱陈之辩》,《孔子研究》2011年第3期。 ,认为正是以“反经合道”为权才导致奸邪之徒以权自饰。因此,程颐与朱熹力图以“权只是经”来矫正“反经合道”所带来的弊病。但是,“权只是经”的说法又使得经与权之间成为了分析命题,权被消解于经之中。
随着人口老龄化到来,加之长久以来的医护比例失调,目前我国护士的缺口非常大,因此护理专业被列为国家紧缺人才专业。培养高素质、技能型护理人才是提高国民健康水平的重要举措,而基础护理学实训教学质量也将严重影响我国护理事业的发展。由此可见,突破传统教学思想,开展多种教学方法已经成为当代护理教育改革的主题[4]。
诚然,程颐与朱熹经权思想的立足点是基于对公羊学的误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经权问题的讨论没有意义。相反,朱熹以道统摄经与权,以“理一分殊”处理经与权的关系,使得儒家经权思想上升到形而上学的层面,解释了经权思想的规范性及其来源,这是公羊学所未能言及的领域。就形式而言,经权思想属于内在规范性理论,就具体来源而言,经权思想规范性根植于人的德性。换言之,儒家的经权思想是重视个人的品格与德性的培养,行权也只有在德性高尚的人那里方能运用自如。而对于常人而言,行权则必须慎之又慎。
The Differences of Scripture and Tact Thoughts in Han and Song Dynasties and Its Normative Source
FAN Zhi-ni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China )
Abstract : The ideas of scripture and tact in Han dynasty, represented by the Gongyangxue, advocated “fanjing youshan”(反经有善). While emphasizing the good result, Gongyangzhuan also restricted the exercise of tact in means. Dong Zhongshu interpreted tact by “fuzheng”(复正) on exercise and took motive into the consideration of tact to define it in a more stringent manner. Cheng Yi and Zhu Xi we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scripture and tact thoughts in Han and Song Dynasty, advocating “quan zhishijing” (权只是经). Cheng Yi misunderstood “fanjing youshan” as “fanjing hedao”(反经合道), and thought that it corrupted the idea of scripture and tact, and reinterpreted the idea of scripture and tact with “the mean”(中庸), “quan bufujing”(权不拂经) and “heyi shibian”(合宜适变). Zhu Xi inherited Cheng Yi’s thoughts critically and advocated ruling scripture and tact thoughts by “Tao”.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Han and Song’s ideas of scripture and tact are“shiyu er wenbuyu”(实与而文不与)and “liyi fenshu”(理一分殊).
Key words : Gongyangxue; scripture and tact; Cheng-Zhu; normalization; virtue ethics
[收稿日期] 2019-06-01
[作者简介] 樊智宁(1992- ),男,福建南平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伦理学。
[中图分类号] B 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194(2019)06-0013-11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 DOI] 10.13951/ j.cnki.issn1002-3194.2019.06.002
[责任编辑:刘春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