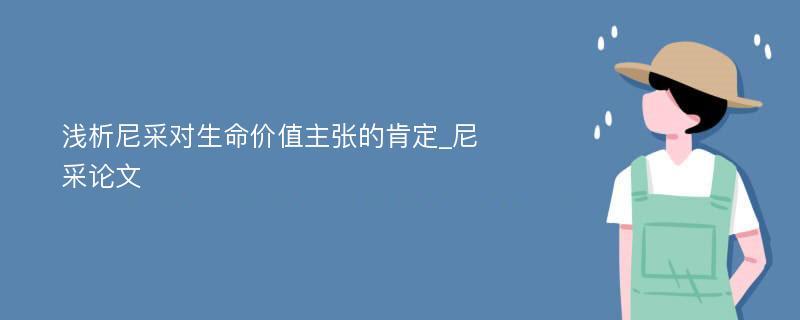
浅析尼采肯定生命的价值倡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尼采论文,价值论文,生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987(2007)01-0067-05
尼采对柏拉图—基督教及其现代性道德进行了彻底的颠覆性批判,其目的就是为了把人们导向“升华生命的道德”[1] (p63)。这种新道德反对从臆想的抽象善恶准则出发来裁定人们鲜活生命的柏拉图主义道德教条,坚持以生命的保持和提升为维度来设立和创造价值对象,维护并发展人的生存的个性化创新。由于“肯定生命”是这种道德价值观的基础和核心的内容,因而真切地把握“肯定生命”这一价值倡导的实质和主要内容,对于准确理解尼采创造性的价值诉求也就有着关键意义。
尼采在价值观上终生所肯定、辩护的首要的东西就是人的生命,是人的生命对于道德乃至于人的一切创造物的优先和基础地位①。尼采所肯定、辩护的人的生命是指以身体形态存在的富有支配、创造意志的有机体,它有三个基本特性:其一是整全性,它意指生命是各种因素的偶合体,是“一种意义的多样体”[2] (P31),生命不能为任何抽象准则所涵盖、统摄;其二是能动创造性,它是指人的生命不是被动的,而是趋于保持或提升自身的富有活力的存在;真实的生命总是“永远憧憬未来,被他过剩的精力胁迫着,找不到片刻的安宁”[3] (P98)。其三是独特性,这一特性是说人的身体生命是某种“全新和创新的东西”[4] (P696),他既相互区别又自身分化和变易。鉴于尼采对生命的这种理解,我们可以认为尼采所倡导的“肯定生命”就是肯定整全且具活力的个性化的创新生命。对于这一思想人们最大的疑惑就是:既然活着的每个人无事不在生存、无时不在执着的生命,为什么尼采还要殚精竭虑地向人们呼吁“肯定生命”呢?这主要是因为在尼采看来,人们生存着并不一定意味着善待生命,人们在生活中常常会用自己的创造物来残害自己鲜活而富有潜能的生命。这种残害生命的创造物,最根本的就是由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启经基督教完善化的柏拉图主义的道德;多少年来人们在这种道德的支配下追求着一种否定整全且富活力生命的虚无化生存。
尼采认为柏拉图主义道德之所以走向“否定生命”,就是因为他将某个抽象的理想原则至上化和实在化,让具体而生动的生命成为某种抽象理想的手段和批判的对象:
“‘否定生命’”竟成了生命的目的、发展的目的!生命竟然成了天大的蠢事!这样荒唐的解释只不过是用意识的要素(快乐和痛苦,善和恶等)来测定生命的怪物而已。”[4] (P378)
“他们信仰道德‘真理’,他们在这里发现了最高价值——他们对生命理解愈多,就愈要否定生命。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事好干呢?……因为生命是非道德的……以非道德为前提,一切道德都要否定生命——”[4] (P490)
在尼采看来,怨恨和否定人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哪怕是一个片段或环节,人们就会虚构出一个和整全生命对立的超感性抽象理想,如古希腊的“中庸之道”、基督教的“上帝恩典”、现代社会的“绝对平等”来遏制现实人的生活激情,束缚人的生命创新,使人的鲜活生命趋于萎缩和暗淡。“否定生命”的实质就是站在生命颓废的立场上抽象地肢解生命,让有着无限情调的整全而富活力的生命在对超感性理想的崇拜中日趋虚无。尼采申言:“当人们凭空捏造了一个理想世界的时候,也就相应剥夺了现实性的价值、意义和真实性。”[5] (P5)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现实世界是连锁和互相制约的”,若你对整全生命充满着怨恨和报复精神,只要其一,不要其二——只要光明,不要黑暗;只要快乐,不要痛苦;只要存在,不要变易——那只能使你走向非理性的疯狂和虚无!
如何把人从怨恨和报复生命的抽象片面的道德疯狂中拯救出来?尼采开出一个基本的、也是最具创造性的药方,即肯定整体且富活力的生命:不仅肯定现在,而是肯定曾在和将在;不仅肯定存在,而且肯定毁灭,和生成;不仅肯定意图,而且肯定超意图的身体机能;不仅肯定快感,而且肯定痛感和苦难。尼采认为惟有这样的肯定才能够赢得整全且富活力的生命,才能实现生命的个性化创新和超越。尼采抨击传统的超感性抽象道德理想是毒害良知、性爱和天然性的谎言,是对传统道德的抽象片面性和生命整全性形成的对抗以及由此造成的对生命的摧残的批判。在尼采看来,“肯定生命”的价值取向是“一个来自充盈和超充盈的、天生的、最高级的肯定公式,一种无保留的肯定,对痛苦本身的肯定,对生命本身一切疑问和陌生东西的肯定……”[5] (P52)。这种肯定式的生存选择就是“热爱命运!”它是“超人”的选择。在尼采那里,人是否伟大就在于能否担当命运、肯定生命:“我衡量伟大的公式是热爱命运:你们不要想变更什么,将来不要,过去不要,永远也不要。”[5] (P40)尼采的理想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的基本品格就是肯定生命:“查拉图斯特拉明确地确定了自己的使命——也就是我的使命——,可不要误解了它的意义:查拉图斯特拉就是肯定,甚至为一切既往辩护,甚至超度这一切。”[5] (P40)在《善恶的彼岸》一书中,尼采称肯定生命是最纵情的最有生气和创新之人的理想精神,他说:“有这种理想的人不仅学会了顺应和相容曾存在和现存在的东西,而且希望拥有它——像曾存在和现存在那样——永恒地,不知足地喊着从头再来(da capo)。”[6] (P194)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清晰地看到,尼采肯定生命的价值倡导是对崇尚超感性抽象理想的柏拉图主义道德的一种争辩和抗争,其目的是想引导人们从自身独特具体、能动开放的身心出发尽其所能的发挥自身潜能以实现生命形态的不断转型和超越。尼采认为人们只有忠实自身生命的丰富矛盾、尊重生命的深层欲求、善待生命的激情才能保持自身价值追求的现实性,进而使自身生活富有原本的生命活力和美好享受,使自身的创造物总是显示和确证自身生命的力量、生长和美,最终使人的思考和生存、道德和生命有机地结合、共同地发展起来。
行文至此,有人也许会问,传统的柏拉图主义道德也是一种生命现象,尼采不是也持着一种激烈的批判和否定的态度吗?尼采在这里难道不是犯了自相矛盾的错误吗?产生这样错误理解的原因在于没有弄清楚尼采对传统的柏拉图主义道德的“否定”不是和尼采“肯定生命”中的“肯定”直接对立的术语,这里的“否定”指的是一种批评和对抗:批评的是它保护颓废者的性质,对抗的是它对个性化创新生命意志的主宰。尼采尽管竭力批评、否定传统道德,但并不指望让其彻底消失。尼采深知,传统道德是衰竭者自我肯定的形式,而衰竭者是力的博弈、生产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现象;这一现象虽然让人心生不快,但尼采是位战士,他欢喜在这种批评和对抗中生活。而和“肯定生命”中的“肯定”直接相对立的“否定生命”中的“否定”,指的是怨恨生命中必然要存在的现象并致力于彻底消灭它,这种出于怨恨的彻底否定精神在尼采那里并不具有。因而我们说尼采“肯定生命”的价值倡导和他批判、否定传统道德并不自相矛盾。
尼采肯定生命主要是向对生命的复仇感和怨恨感宣战;由于对生命的怨恨主要是针对苦难、身体和过去,因而尼采反对这种复仇和怨恨的“肯定生命”的主张主要就有这样三项内容:肯定包含苦难的苦乐生命;肯定包含无意识机能的身体生命;肯定包含过去的过程生命。以下简要分析之。
第一,肯定包含苦难的苦乐生命。尼采认为传统的柏拉图主义颓废道德形成的直接原因乃是衰竭之人怨恨生命世界的苦难而产生出的逃避苦难的愿望;因此,新道德作为生命力充盈旺盛之人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当然要肯定包含苦难的生命世界,以引导人们积极勇敢地面对和参与包含苦难的人生。追求生命力提升和个性充盈的英雄式生存就是原创性权力意志的体现,它必然伴随着痛苦和快乐;因为痛苦乃是权力意志的障碍,因此是正常的事实;而快乐则是障碍的消除,是权力感的享有。在尼采看来,个性化创新式的生命从来都是由障碍与征服、痛苦与欢乐等对立因素交织起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舍弃任何一方面都会危及真实生命及其提升。尼采曾就此申言:“(平庸者)认为理想是丝毫无害、无恶、无危险、无疑问、无毁灭性的东西。我们的认识正好相反,即认为,随着人的每一步的增长,其反面也同步增长;我们认为最高等的人——假如可以提出这样一种概念的话——就应该是这样的人,他把生命的对立特征明确地表述为生命的光环和辩护词……”[4] (P327)。
尼采所理解的健康快乐的人性生活不但无法回避痛苦,而且需要痛苦,人是通过痛苦赢得快乐并茁壮成长起来的:“请相信我的话吧:获取生活中最丰富的果实和最大享受的秘密在于冒险犯难的生活!”[7] (P218)尼采批判叔本华主要是因为他想逃避痛苦、由于痛苦而怨恨意志和生命:“我认为,教诲人们否定意志的这些乃是祸害和诽谤……我是按照意志对反抗、痛苦和折磨的忍受程度来评价意志力的;我不把生命的恶劣和痛苦的特征作为谴责生命的借口,而是希望生命有一天会变得比过去更加恶劣和痛苦……”[4] (P325)
尼采所申述的上述道理,中国传统文化也曾经验式地触及过。中国人常说的一些谚语和格言如“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祸福相依”、“无内忧外患者恒亡”就明显地包含着这个道理。但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苦难生存价值的思考并没有被系统化和理论化,因而也就不能上升到人生观的高度作为一种基本的价值原则来审视、鉴别与此对立的文化现象。于是中国虽有肯定苦难价值的经验性智慧,但在其旁边更有着追求无忧无虑、十全十美的安全、逍遥的哲学。因此,“乐感”、“隐忍”、“出世”的文化异常发达。这种文化已经深深积淀到当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别表现在青少年的家庭教育之中。许多父母远离了对孩子的风险、苦难和挫折的教育,以至于使得孩子在舒适的环境中远离了生命的力量、存在的丰盈和伟大的个性。
我们有必要像尼采那样把痛苦作为生命的基本环节肯定下来,莫要因生命的苦难而怨恨、遗弃鲜活的生命而制造莫须有的浪漫化的没有任何对抗和苦难的田园牧歌式的未来;更不应当站在一个抽象“应当”的立场上一味地批判生命中的苦难、逃避生命中的对抗,那样只会使自己日趋软弱和疲惫。因为苦难是生命的本质现象,它渗透在人类生活及其发展的每一个基本环节;只有欣然、乐观地接受、参与包含苦难的生命才能享有美丽而丰富的人生。这需要来自力量的勇敢,而人是能够勇敢的。这种勇敢也只能在面对苦难时不为它所吓倒并且参与到苦难之中去培养。人的精神中可以失去或没有很多东西,但最不应该缺乏的就是直面苦难的生存勇气,因为那样你就会失去一切!包括快乐!
当然,尼采这一观念也有美化苦难价值的倾向。世上并不是所有具体欢乐的产生都必须以痛苦作为前提,而且有些苦难的确可以并且应该减少并消除掉。人们想望少些苦难的生活并不一定就必然走向颓废。超过人的极限承受力的长久苦难给予人的伤害足以让人失去生命的活力而趋于毁灭,有效的规避是十分有价值的。对于苦难,像尼采那样一味地强调“酒神精神”而纵情欢呼,这一态度,从根本上说,既不真诚,而且也是对自身生命的一种不负责任的浪费和伤害。
第二,肯定包含无意识机能的身体生命。尼采创造性地将道德发展史描述为由“前道德时期”到“道德时期”再到“超道德时期”的演进模式[6] (P127)。在他所肯定和张扬的“超道德时期”,人们将价值重心放在非意图的无意识机能上,而在“道德时期”被封为至尊的“意图”、“道德理想”则被降低到手段及其相对性的位置上。尼采说:“今天,至少我们不道德者浮动着这样的怀疑:一个行为的决定性的价值恰恰在于非意图的东西中,而且,它的一切意图性的东西,一切在它之中可以被看到、被‘意识’到的东西,还属于它的表面和皮毛,——像任何的皮毛一样,这皮毛有所显露,但还更多地是掩盖。”[6] (P172)因此,肯定身体生命的非意图感性机能存在的合理性及其价值,是尼采道德观的基本价值取向。尼采如此描述自己的德行观:“如果我们应该有德行的话,我们将大概只有这样的德行:它们与我们的最秘密和最衷心的嗜好,与我们的最强烈的需要,学会最好地相容。”[6] (P273)在尼采那里,“超道德意图”的身体是一种富有创造活力的能动存在,有其无意识特性,对此尼采曾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说道:
“我的兄弟,在你思想与感情之后,立着一个强大的主宰,未被认识的哲人,——那就是‘自己’,它住在你的肉体里,它即是你的肉体。”[2] (P32)
“这创造性的‘自己’,为自己创造了尊敬与轻蔑,欢乐与痛苦,创造性的肉体为自己创造了精神,作为权力意志之手。”[2] (P32)
尼采认为,超意图的身体才是生命中主导的东西,是真正的原因,是大理智,而道德意识、精神只不过是它的工具和手段;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身体机能,而是最不为人知和最隐蔽身体的无意识机能决定人们的意识和道德。一切有着明确意图的价值估计都不过是身体生命实现自身权力意志的表现方式和变态,亦即结果。传统道德理论倒果为因,认为人的行为总是意图决定的,一个行为的价值在于它意图的价值中;于是,人们努力让意图成为君临天下的尺度,这样便成就了否定身体首要性和基础性的道德上的柏拉图主义。为这种道德所束缚的人们把抽象理想设定为标准、生命的最高价值状态,彻底遮蔽和否定了人的生命的无意识机能对既得精神状态的突破和超越。这就是尼采所说的虚无主义的“精神错乱”:“人构想了一个世界,目的是诽谤和玷辱它。其实,人每次都向虚无伸出了双手,并且把虚无解释为‘上帝’、‘真理’,尤其是这个存在的法官和判官。”[4] (P493)尼采为拒斥这种虚无化的生存而吁求人们“郑重对待一切生命的必需品,并且蔑视一切‘美丽的灵魂’,视其为轻薄和无聊。”[4] (P548)
这是一种新的道德呼唤:肯定包含无意识机能的身体生命!尼采说:“根本问题:要以肉体为出发点,并以肉体为线索。肉体是更丰富的现象。”[4] (P178);“信仰肉体比信仰精神具有根本意义”,“要以肉体为准绳”[4] (P152)。在尼采的视域中,属于身体的欲望、冲动和激情没有了往日的罪性,得到的歌颂和称许;因为它们是原创性权力意志最直接的表现形态,是实现个性化生命创新和超越的直接动力和表现。
尼采肯定无意识机能的根本旨意在于呼唤人们通过参与生动而整全的生命世界来超越既定的意识成果对鲜活生命的绝对宰制,而不是鼓吹非理性放纵。全面考察尼采的文本,我们可以发现尼采并不完全否认意识、思想、灵魂在生活中的价值。他反复强调艺术、认识、道德都是保持和提高生命的手段,是权力意志的支配物,是身体这一“大理智”的工具,就已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人的精神性存在也是创造活动的一个环节。只是尼采所热爱的生命是个性化的创新生命,这样他就只能够肯定和维护包含无意识机能的身体生命,因为只有通过身体无意识机能的发动才能把人带入新的意识整合和创新境界;而不能像传统的理性主义道德那样只维护精神而贬低身体,使意识因为缺乏身体的源泉而贫乏,使身体离开意识的合理调适而残缺。
尼采肯定包含无意识机能的身体生命,其意义首先在于有力地消解了浸淫欧洲两千年之久的柏拉图主义超感性的抽象道德对人们生命创新的压抑,因为尼采所强调的身体生命是独特、具体和富有活力的,肯定和维护它必然有利于人们对既得意识状态的超越和自身生命的创新。其次,尼采这一思想由于深刻地认识到了身体的基础性、道德行为的非意图性,从而也从以下两个方面深化了对道德现象的认识:其一是人的身体机能对道德行为的制约性。无论如何,道德意图、理智不是我们研究道德的出发点,尼采虽没有达到马克思那样的深度,从人的工具性生产实践追寻道德的起源和变革,但他从个体生存的视角出发研究道德的依赖性,认为个体先有生存,即先在世界中,然后才有意识与道德;道德意识是生命的工具而不是相反。这种思想是合乎实际的。一种道德观幻想凌驾于生命之上,成为绝对至尊,只能说明这种停滞了的精神在反映着停滞了的生命,亦即日趋毁灭的生命。尼采这一深刻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海德格尔对“此在”的生存本质的极具创意的分析。其二是身体无意识机能对道德生活的影响。尼采强调了生命的一些非理性因素如冲动、激情、渴望在道德价值生活中的具有积极作用,这一思想也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美好的创造性人格的塑造除了道德理性的作用以外,还应该有来自生命体内的冲动和激情。这些冲动、激情不仅积淀着理性的道德,更带着血肉之躯的旺盛的活力。借鉴尼采这一识见,我们就应该不仅关心我们的道德认知的合理性,还应该关怀我们身体生命的健康、关怀我们生命的知、情、意等方面的和谐发展。
尼采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分析的表面性以及价值倡导的某种不确定性。尼采说的对,人不是精神是身体,但人的身体还是可以再作分析的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的五官感觉、人的身体生命是全部世界史的产物,最主要的是劳动的产物;由此出发,合理的生存价值论就不应该停留在一般的肯定身体生命,而要重点肯定对人的生命有积极影响的生产方式,致力于从人的“自由个性”的实现和提升的基本途径的维度上来设定和追求自己的价值理想。尼采盲目于这一点,不能指出身体生命力的生成和提升的基本根源在于人的工具性生产方式,只是毫无确定性的呼吁人们听从和尊重身体的要求,最终陷入唯意志论的盲目性和软弱性;它对人们的健康品格及其社会的合理秩序的成功建构有着消极的影响。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中克服这一理论的局限性。
第三,肯定包含过去的过程生命。尼采肯定生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过去、曾在、既往进行认同、辩护甚至是欢欣,这一思想的实质就是对生命的过程性、时间性进行价值肯定,以否定传统的柏拉图主义道德因为生命的易逝性的痛苦而敌视流动变易的生命,以批判他们把真实的生命理解为永恒的惩罚、把无时间性的超生命理想的实现视之为永恒的幸福。尼采的这一深刻的思想集中表现在《查拉斯图拉如是说》一书中的“赎救”篇中,在这一重要但却相对晦涩难解的章节中,尼采精辟地阐述了这一道理:
“拯救过去的人们,而改变‘已如是’为‘我曾要它如是’:这才是我所谓赎救!
已如是,这便是意志之切齿的愤怒与最寂寞的痛苦。意志对于一切已成的,无力改变:所以,它对于过去的一切,是一个恶意的看客。
这才是报复:意志对时间与时间‘已如是’的厌恶。
一切‘已如是’都是断片与谜与可怕的机缘,——除非创造性的意志补说:‘但是我要它如是!我将要它如是!’”[2] (P167-169)
传统的柏拉图主义道德在价值上否定感性生成的过程性生命世界,而企望一个超越时间掌控的永恒的“幸福王国”;形成这种错误的一个根本的原因,在尼采看来,就是意志不能欣然地接受“过去”,不能接受“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的感性变易的生命世界而是不断地怨恨自己为什么不能停止流动变易的时间性生命于一种幸福状态。中国人经常感叹的“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就隐含了这一情结。正是因为人们总是生存在一个连自由意志都不能改变其变易的过程性的世界中,才使得生命力衰竭之人产生对充满变易的时间性生命世界的厌恶、对虚构的无变易性的“真实世界”的向往。他们通过设想一个理想的尽善尽美的道德主体生活在“永恒的幸福”、“神仙般的极乐”的世界来否定过程性生命世界的短暂性和有限性,进而陷入敌视生命的超感性理想的幻觉之中。
尼采要否定这一系列的反思,让人的精神从无时间变易性的“永恒”的幻觉中清醒过来,以找回人对其生命易失性、生成性亦即过程性的深沉自觉。这里最关键的是消解人们对“已如是”,亦即对过去生存的怨恨,因为这种怨恨使意志远离变易的、生成的过程性的生命。尼采的方案是建立在对世界远景式的整体透视基础上的意志决断:我永恒地要它如是!这一思想告诉人们:
(1)过去的,以及通过延伸包括现在和未来的时间性的生命世界不是人的有限的理性所能裁定和审判的。
(2)时间性的过程生命值得我们向往、追求并努力经验。
(3)生命的问题和责任是由生命者自己担当的,不怨天,不尤人!
听从这种决断的意志就不再轻视并且痛恨自己对时间变化的软弱无力,不再沉陷于痛苦的遗憾之中而不能自拔,不再作虚无主义的努力去追求一个无时间性的超感性理想,不再因生命有缺陷而使人变为罪责者、使莫须有的无缺陷性的上帝成为惩罚者。
尼采上述的价值倡导,在本质上不能称之为非理性,因为其中渗透着尼采对世界及人生的整体性概览。在尼采看来,世界是力的博弈、游戏的巨大舞台;人的生命也是权利意志,并且属于全,在全之外尽是虚无,没有上帝!立足于这个全体世界上的个体的人如何能判定某一过去的现象、某一过去的选择一定是错误的,是不应该存在的呢?!如何能由此走向对生命的过程性、时间性的怨恨和敌视呢?!这种怨恨和敌视难道不是一种对富有活力的健康生命的浪费和破坏吗?!最合理的态度难道不是从真实的、变易的过程生命出发,忠实于这个实际,热爱命运并勇敢担当吗?!是的,包含过去的过程生命中有泥泞、冷箭、中伤;也有苦难、紧张和遗憾,但何处是净土?埋怨“已如是”的“纯粹意志”对永恒“理想王国”的浪漫向往不是一种恶劣的梦幻又是什么呢?!
当然,尼采为了拒斥超感性理想而轻视理性反思、走向对感性世界的一味的推崇,也有其深刻的片面性。生活在相互联系的整体世界之中的人毕竟不能离开和舍弃理性反思,虽然这种思维因为人的有限性而常犯错误,但相互交往的、不断传承的历史性的人还是能够借助自身的发展了的思维克服错误、继往开来。尼采反对通过理性思考形成无时间性的超感性观念有其重要的道理,因为人终究不能臻于“十全十美”;但像尼采那样完全拒斥对既成事物的反思性的批评、检讨、褒贬则是一种因噎废食的做法。因为,人的生产性和历史性的本质决定了有所“领会”、“反思”的生存既是人生存的一种“必然”,又是人生存的一种“当然”;惟其如此,人才有可能能动地超越过去,实现个性化的生命创新。
尼采“肯定生命”的价值倡导,用整全且富活力的个性化生命否定抽象片面的道德理性,虽然没有达到像马克思那样从社会生产出发现实地理解人这样的一种理论深度,但他坚持人的生命在价值创造中的首要和基础地位,呼唤人们尊重和善待整全生命的潜能和活力,还是从微观个体的视角维护了生命的个性化创新和超越的价值和意义。尼采正是通过这一倡导,才真正实现对柏拉图主义超感性道德的批判性超越;它有力地开启了后尼采时代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人的生存、生命的持续而热烈的关注。我们只有深切地把握尼采这一思想的真实底蕴,才能从根本上了解尼采颠覆性道德理论的价值旨归和思想史上的转折意义。
注释:
①尼采曾借查拉斯图拉之口向世人申言:“我,查拉斯图拉,是生命的辩护者、苦难的辩护者、循环的辩护者”。这一断语确切地表明了生命在尼采价值取向中的首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