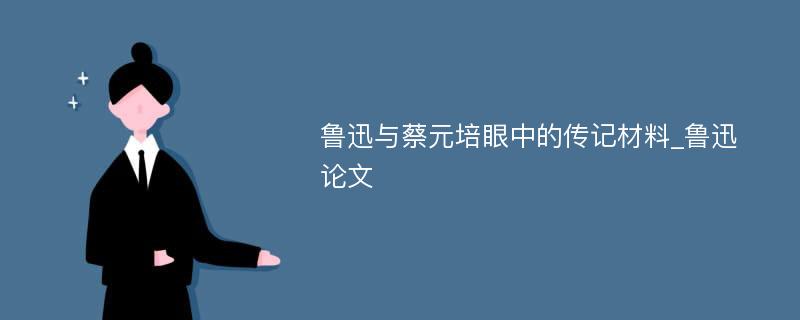
蔡元培眼中的鲁迅与传记材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传记论文,眼中论文,蔡元培论文,材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概括鲁迅其人与文学,蔡元培写在《鲁迅全集》卷头的序言①是最为出色的。蔡元培是鲁迅的同乡也是其学长。他是最早正确掌握作为修养的德意志观念论的人。在思想史方面,由于他的理想主义晚于由严复倡导传入本土的英国经验论,因此在清末并未引起广泛的影响。但是,在辛亥革命之后,身为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他所导入教育界的人格主义的影响力是巨大的。那成了孕育新精神之母胎。在对容闳——胡适所倡导的美国学制的输入形式中,他赋予其充实的内容。文学革命是他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在他的直接带领庇护下兴起的。对于文学革命他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场,允许自由思想的存在,为了护卫思想自由而身先士卒地进行公平的战斗,最终新思想取得了胜利。鲁迅是他成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后被邀入教育部的,并随着政府的北移而一同迁至北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他的庇护之下。对他的正义观念、自尊心和奋斗努力,鲁迅表现出由衷的敬佩之情,这也毫无疑问地激励着鲁迅身上天生的气质。而且,由于鲁迅给予了文学革命以实质性的内容,所以我想作为前辈的蔡元培也是深感欣慰的。
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的蔡元培,虽然最终没能完全彻底地接受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他并不妨碍他的后辈们超越他的思想,而且在那种新思想的主张之外,在动摇强权方面,他也常常以拥护自由的立场坚决地予以支持。这种充满骨气的气度也是和鲁迅所共通的。蔡元培的人格受到大多数人的尊敬,所以,他屡屡被政界所召做调停工作。他为人淡泊名利、责任感强、笃好学问。在这一点上也与鲁迅相通。作为教育家的他的战斗的人道主义观念,最终被作为人生教师的鲁迅所深深继承。
鲁迅死后,在由全文化界自发地组织起来的“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上,蔡元培被选为主席。他的确是最合适的人选,由此而组成的委员会,更加强调与鲁迅一致的人民的意愿。(副主席是宋庆龄。这位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者,也在与反动势力斗争的经历方面屡屡与鲁迅相同。)
蔡元培的演说或文章,始终贯彻着独特的文明史观,其中气势磅礴、风格激扬的作品占多数,其格调的整饬在当代是无与伦比的。那种风格是无法移译的。下面,为了能够概括性地了解鲁迅的业绩,代之传其大意:
“行山阴道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令人应接不暇;”有这种环境,所以历代有著名的文学家美术家,其中如王逸少的书、陆放翁的诗,尤为永久流行的作品。最近时期,为旧文学殿军的,有李越缦先生,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所以他杂集会稽郡故书、校《嵇康集》,辑谢承《后汉书》,编汉碑帖,六朝墓志目录,六朝造像目录等,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例如科学小说的翻译,《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抄》,《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又金石学为自宋以来较发展之学,而未有注意于汉碑之图案者,鲁迅先生独注意于此项材料之搜罗;推而至于《引玉集》,《木刻纪程》,《北平笺谱》等等,均为旧时代的考据家赏鉴家所未曾著手。
先生阅世既深,有种种不忍见不忍闻的事实,而自己又有一种理想的世界,蕴积既久,非一吐不快。但彼既博览而又虚衷,对于世界文学家之作品,有所见略同者,尽量的移译。理论的有卢那卡尔斯基,蒲力汗诺夫之《艺术论》等;写实的有阿尔志跋绥夫之《工人绥惠略夫》,果戈里之《死魂灵》等;描写理想的有爱罗先珂及其他作者之童话等,占全集之半,真是谦而勤了。
“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虽也痛快,但人心不同如其面,环境的触发,时间的经过,必有种种蕴积的思想,不能得到一种相当的译本,可以发舒的,于是有创作。鲁迅先生的创作,除《坟》,《呐喊》,《野草》数种外,均成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三六年中,其文体除小说三种,散文诗一种,书信一种外,均为杂文与短评,以十二年光阴成此多许的作品,他的感想之丰富,观察之深刻,意境之隽永,字句之正确,他人所苦思力索而不易得当的,他就很自然的写出来,这是何等天才!又是何等学力!
综观鲁迅先生全集,虽亦有几种工作,与越缦先生相类似的;但方面较多,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然欤否欤,质诸读者。②
如果把鲁迅当作学者划分体系,并且将他的学问成就作为旧学的发展,从旧学的角度来加以观察,那么从蔡元培自身的学问立场出发并不奇怪。而且,即使从那一方向看大致也可以解决,也能够看出鲁迅所具有的问题的复杂性。新时代的批评家们,当然对蔡元培的理解不满意。但是,他们的方法,也不过是用与蔡元培所持的不同的方法来衡量鲁迅而已。鲁迅内在的新精神形成的运动法则,就像蔡元培不了解鲁迅一样,还没有人能清楚地了解。
传记材料
鲁迅传记的研究虽然还算不上开始,但起码也可以说是已经开始了。鲁迅精神的继承是伴随着全国一致抗战的文化界的各种势力联盟的共同话语而呼吁起来的,并且成功地贯穿了整个抗战。尽管如此,话语也只是作为话语流传。战争导致了物质条件的困难,人们可以感受到埋头于传记研究的精神的宽裕被剥夺了。战争结束后,人们恢复了日常性的生活,时值各势力间的协调关系再度失衡的今天,为了新文化的建设,正在出现围绕鲁迅遗产而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鲁迅作为今日文学的问题,再次引起公众注目。写作鲁迅的传记,对于今天的文化而言,就会成为某种决心的显示,我以为这猜想一般人会予以认同的。
国内外有很多想写鲁迅传记的人、能写鲁迅传记的人和必须写鲁迅传记的人。他们各自或者共同着手开始工作。他们的条件大体上是相同的。而要出成果,则须假以时日。
鲁迅的传记时至今日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以说,作为现代的文学家而言,也有非常好的。主要的著作有几种。他们都各有特色,比如像李长之的《鲁迅批判》,他在中学时代就有过亲身经验:“‘鲁迅’这两个字,我一见了,便觉得好像血液在倒流。”③在有这种体验环境中走出来的人的作品里,即使在今天也有可利用的价值。然而,就其可利用的东西而言,那本身还不具备古典文学那样独立的价值体系。我想现在的研究者,也还必须从原始资料出发吧。
不言而喻,文学家(假如确定鲁迅为文学家)传记的第一手材料就是作品。鲁迅的作品今日几乎被完全集中出版。其完整性大概将来也不会发生什么大的变化。初期的翻译和创作虽然被埋没了,但由于被杨霁云发掘出来,连同那些没有出版的原稿和对旧书的校刊及考证,也经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在全集出版之际变成了铅字。甚至连编集后记和广告之类的琐碎文字也都被收集起来。经过杨霁云、许广平他们的努力,《鲁迅全集》尽管是在战乱中得以编辑出版,但还是相当完整。尽管多少还有遗漏的文章,后来在鲁迅死后十周年的1946年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至此,全集终于成了更加完整的作品。今后即使再发现一些佚文,其量也不会多吧,不会从根本上影响对鲁迅的评价。另外,除了关于初期考证的未整理的未定稿外,如果仅限于作品,似乎没有未发表的以及和所印文本相异的原稿。(上述两方面都依据许广平对苏联研究者提问的回答。)当然,文章在报纸和杂志上发表和收集到单行本中时,有时会不同。他晚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被剥夺了执笔写作的自由。从那个时代开始用笔名(鲁迅的笔名有八十个以上)写作。即使用笔名写作,也经常有被删改或者完全不予发表的时候。后来将那些文章整理出版的时候,他把当时曾经用过的笔名和被删削的地方明记下来,在争论的地方附上对方的文章发表。(那时他的著作几乎都是自费出版,或者是近于自费出版的形式。)所以,由于言论压迫的缘故,不必担心出现不同的版本。并且,在他所发表的文章中,即使是发现了事实上的错误,他也决不订正改写。如果有那样的情况,就加写或者重新写作。他好像认为创作出来的文章一经写出后独立,就连创作者也必须尊重其独立性。因此,从这一点考虑,也就不会产生不同的版本。单行本也好、全集也好,我们至今所拥有的他的著作,都是定本,没有重大的疏漏。
鲁迅传记的研究者,只要是和作品有关的资料,都给予了充分的材料印证。因此,他写什么、如何写就都为大家所知。而与之相反,他没写过什么,以及为何没写,人们就不十分了解了。一般来说文章有这样一种关系:即写文章要排除不能写的东西,而未能写的东西也排除所写的文章。其排除方法因人、因时代的不同而不同。但我想,在鲁迅的场合,知道写文章应该排除什么是极为重要的。他经常说我“写不出圆满的文章来的”④。由于表现的和应该表现的之间不一致,导致他一生苦恼。他文章的欲言又止、踌躇不爽、身心疲惫,让读者感觉到他文章中未能表现出其内心思想的深度。不用说,把文章作为一种目标追求,吃透文章并走出文章是可能而且应该可能的,但无论怎么说,如果把那样的方法作为方法,就不是万全之策。所以,我想要找到跳出文章从外部角度解析文章的线索。可是,能成为那样材料的,是作品必须完整,而这一点还远没有达到。
那种材料之中有怎样的内容呢?第一,有许寿裳编写的年谱。虽然是极其简单的东西,但是作为年谱却是唯一的,而且许寿裳是鲁迅的同乡同辈,所以他记载的是可以确信的。那些材料取舍本身都具有意味,都是经过严密考虑而选取的,却也因此变得过于简单。
第二,有近亲的记录和回忆。有从少年时代开始到留学时期的周作人的回忆,还有须藤医生的病况记录也是重要的文献。除此之外,还有许广平、萧军和内山完造等人所写的各种各样的资料。还有许多的人写成的印象记和会见录。但是,能够作为参考的材料实在很少。特别是他的有关亲戚,由于近亲者似有所隐,致使缺少发掘它的研究者,实在遗憾。这方面的材料,今后应该更加增多,也会增多吧!
第三种材料,是鲁迅的信和日记。鲁迅写过的信,特别是回信的数量看起来非常多。在其著作当中,有用问卷调查的形式阐述意见的文章,即使是在私人信件的情况下,也肯定回信一一解答对方的提问,这是他的习惯。一般性的信件具有作品的性质,但也有不具备的。把信件集中起来的计划,在全集出版的时候,就当时来看条件不备,没能进行。区别于全集,许广平编辑出版了一册《鲁迅书简》,收集了69封信件。它由鲁迅与许广平的往返书信,和在鲁迅生前就出版的一册《两地书》组成。还有用日语写给日本人的书信,收集至《大鲁迅全集》当中。之外,还有收到鲁迅信的人,用各种形式发表的作品也有一些。只有这些是公开出版的全部内容。可是,1946年,用和作为鲁迅去世十周年纪念出版发行的全集相同的形式出版发行的《鲁迅书简》一书,收集了给八十多人的865封书信。即使是从传记研究方面来说,这也确实是巨大的收获。但是,未被刊登的书信肯定还有很多。
其次还有日记,这是记录他从作为教育部职员赴北京任职之日时开始记载,直至他去世前(1912.5.5-1936.10.17)“从未间断”的原稿,除了在战争中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队逮捕之时遗失的1922年间的部分,其余的部分,都经由当时在上海的许广平之手妥善保管。那些日记都是以人事往来、书信往复和钱财支出等为主,有备忘的形式。除了极少部分被发表之外,其他还没有公开发行。传记材料的重大来源还有些欠缺。
如上所述,作品之外的材料实在匮乏,但那匮乏程度是可以对照丰富的作品而加以弥补的,反过来看,被参照的作品,则因此而使有价值的次序一下子转变成传记性的次序,如果巧妙地加以使用,就能够获得相当好的效果。
(本文译自《竹内好全集》第一卷,筑摩书房1981年版)
注释:
①②蔡元培:《鲁迅先生全集序》,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鲁迅全集》第1卷,上海复社1938版。
③李长之的《鲁迅批判》,193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在1945年的三版《后记》中,李长之谈到1925年1月25日他写过的一片散文《猫》中的一段话,其中有这样的记述:“‘鲁迅’这两字,我一见了,我便觉得是滚圆的活跃的血似的长虫所盘绕的躯体,也就仿佛热沸的温泉所奔腾着的路径。”竹内好大概是根据这段文字意译为“好像血在倒流”。
④《我要骗人》,《且介亭杂文末编》,《鲁迅全集》第6卷48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