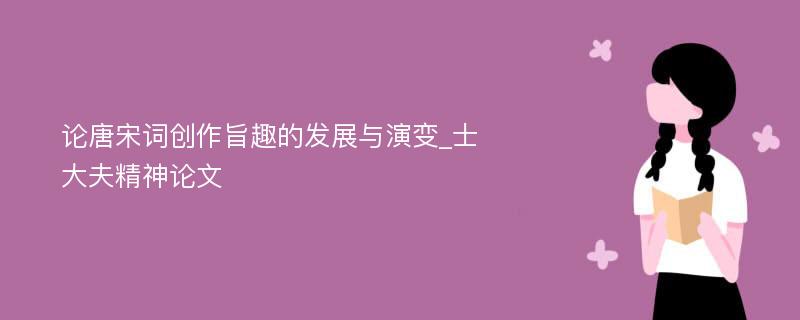
论唐宋词创作旨趣的发展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旨趣论文,唐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词学理论中,向来有“以诗为词”“以赋为词”“以文为词”“以论为词”等说法。与这种从题材、风格及表现手法的角度来划分词之类型的方法不同,本文提出一套“以色为词”“以趣为词”“以韵为词”“以气为词”的分类概念,其目的是为了对唐宋词之创作旨趣之发展演变过程勾画出一个简要的轮廓,并通过这种文学现象的揭示,探讨唐宋文人在对词进行雅化的过程中,其审美理想是如何形成、发展与确立起来的。为此,在本文的开头,有必要将上述分类概念的内涵大致确立下来,以便对史实进行观照、辨认,对问题进行分析论证。我们认为,所谓“以色为词”者,其创作旨趣主要在于表现色情性感;所谓“以趣为词”者,其创作旨趣主要在于表现俳谐幽默;所谓“以韵为词”者,其创作旨趣主要在于表现风神韵致;所谓“以气为词”者,其创作旨趣主要在于抒发感慨意气。当然,随着唐宋词的流变,这些概念的内涵也会有所丰富与发展,而本文正是通过对这一过程的辨析,来阐释唐宋词创作旨趣之发展与演变的。
关于词的缘起,文学史上有多种说法。相对来说,得到公认的有源于六朝说与源于隋唐说。如明人王世贞说:“六朝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弇州山人词评》胡应麟说:“陈隋始之,盖齐、梁月露之体,矜华角丽,固已肇端。”(《庄岳委谭》)朱弁《曲洧旧闻》说得更具体,他认为词于“六朝已滥觞矣。梁武帝有《江南弄》,陈后主有《玉树后庭花》,隋炀帝有《夜饮朝眠曲》”。综合上述说法,考诸史实,今人刘大杰先生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认为,词主要源于齐梁小乐府与唐人之律绝,这基本上是不错的。今存最早的初唐人词如虞世南的《织锦曲》、长孙无忌的《新曲二首》等,与齐梁宫体诗的写作旨趣就大略相同。所谓“芙蓉绮帐还开掩,翡翠珠被烂齐光,长愿今宵侍颜色,不爱吹箫逐凤凰”(长孙无忌《新曲》其二)与梁武帝《江南弄》“美人绵眇在高堂,雕金缕竹眠玉床,婉爱寥亮绕红梁。绕红梁,流月台,驻狂风,郁徘徊”都是写色情性感,亦即是“以色为词”的。之所以如此,当然是为了筵前席上佐欢助兴的需要。而一些由唐人律绝改编而成的词,则只取其声情摇曳之美感,旨趣广泛,主色者甚少。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词中有一类俳谐之作,即是本文所谓“以趣为词”者,如初唐时人杨廷玉《回波词》“回波尔时廷玉,打獠取钱未足,阿姑婆见作天子,傍人不得枨触”,以及李景伯、沈佺期等人所作的《回波乐》等。这一类,据今人王昆吾先生《唐人酒令艺术》考证,则多是唐人酒筵互相调谑之作,其表现手法多采用夸张、比拟、双关、隐喻等。谐谑嘲讽是隋唐时广为流行的语言艺术,今《全唐诗》专门收有“谐谑”诗4卷, 《唐五代词》也有不少谐谑之作, 《太平广记》还专门编撰了“嘲谑”逸事5卷,可见时风。总之, “以色为词”“以趣为词”在早期词源起的过程中曾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写作旨趣,词之所以受到世人欢迎并得到兴盛发达,也当与这种旨趣能“以资笑乐”有关。
中唐以后,文人始有意识地写作词曲,相对那些“胡夷里巷”之曲,“色”的成分明显减少,但还是袭用了男欢女爱的传统内容,然其创作旨趣已从性感描写转为情意的抒发。白居易的《长相思》《忆江南》、刘禹锡的《潇湘神》、皇甫松的《梦江南》等就特别注重风神韵致。如《长相思》采取以景寓情的手法写少妇思念丈夫,便于淡远中显出深致。此期文人之作中仍有不少“以趣为词”者,如元稹、李绅、范尧佐等人的《一七令》,分别赋竹、赋书、赋茶、赋月,而采用拆字、双关、谐音等表现手法,多方形容,以示风雅多趣。这些词作都明显具有酒令性质,与后来托物言志的咏物词旨趣是不同的,它们并不用来表现作者的性情意趣,志向怀抱,而只是将一些与物有关的情事、典故搜括、罗列出来,通过巧妙的构思措置,敷衍成篇,以达到佐欢助兴的目的。而王建、戴叔伦、韦庄等人的《调笑令》《三台令》等也是赋物之作,其原初的写作旨趣也是在于谐谑,今人不察,以为其写胡马、写团扇、写边草皆寄寓了作者的情思感慨,其实不然。即从这些酒筵令词的常用辞式也可看出,其语句或重复、或颠倒,在一种类似绕口令的句式中施展才情,以达到有趣的艺术效果,这才是词人们的目的。总之,白居易等中唐文人词虽然开始回避色情旨趣,注重韵致抒发,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而“以趣为词”则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风尚。文人们还只注意到词的“佐欢助兴”作用,而没有产生以词言志抒情的想法。
晚唐温庭筠是文人中第一位写词的专业作家。词的特质便是由这位号称“鼻祖”者确立的。温庭筠虽然“能逐弦吹之曲,为侧艳之词”(《旧唐书·本传》),但毕竟还是保留了较多的士大夫文人气质。他的词虽大多是为青楼妓馆“应歌”而写,其内容必须“艳”“媚”,但总的来看,在表达方面还是比较含蓄的。如《菩萨蛮》15首,《更漏子》6首,《南歌子》7首均是其代表作,其中并没有很露骨的色情描写,所谓“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新添声杨柳枝》就是他《金荃集》中“侧艳”已极之作了。后世文人指责其词“淫艳猥亵”,却实在举不出比此更猥亵的句子来。飞卿在晚唐文坛上也是以善诗善骈文著称的,其诗情味萧瑟,并不与《香奁》同体,其骈文也极重修饰,有唯美倾向。这就影响到其词创作虽以女性为题材,但旨趣却并不在色情性感。他写女性之美貌,多比喻;写女性之情思,多隐曲。如写独处之愁闷以“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的场景暗示;写娇美之容色以“藕丝秋色浅,人胜参差剪”的服饰描写替代;写女子之动作则以“绣衫遮笑靥,烟草粘飞蝶”之神情意态来点染,这些确实都是文人写女性之词的很精到之笔。唐圭璋先生《唐宋词简释》评“小山重叠金明灭”一首说:“此首写闺怨,章法极密,层次极清。……末句,言更换新绣之罗衣,忽睹衣上有鹧鸪双双,遂兴孤独之感与膏沫谁容之感。有此收束,振起全篇,上文所以懒画眉、迟梳洗者,皆因有此一段怨情蕴藉于中也。”要之,使温词具有含蓄蕴藉之美感特征的原因正是由于作者有着对“韵致”而非色情的自觉追求。温庭筠这位文人词的“鼻祖”也正是通过“韵外之致”的表现将俗词引向雅化之路的。而“韵”在温词中的表现则主要是含蓄优雅。含蓄已如前所述,优雅则体现在其辞采精工华美、浓丽而不失秀婉。尤其在以优美辞采暗示柔情蜜意方面获得了很大成功,取得了韵味无穷的效果。俞平伯先生《词曲同异浅说》认为“词虽出于北里,早入文人之手,其貌犹袭倡风,其衷已杂诗心”,也是看出了词在转入文人手中时,其题材虽然没有改换,其创作旨趣却已发生变化了。事实确是如此,就温庭筠而言,他不仅对词的声律、体制作了大量的整理工作,而且也引导词的内容脱俗为雅,正是这种雅化的意图,使词确立了以“韵”为主的特质。
五代时,词坛两大重镇是西蜀与南唐。西蜀以花间词为代表,承袭了温词的秾艳华丽,“以韵为词”者不少,“以色为词”也颇多。如“娇羞不肯入罗衾,兰膏光里两情深”(和凝《临江仙》)等就显然是在追求“淫媟”的旨趣,这除了反映小朝廷君臣醉生梦死、寻欢作乐的现实和生活在此种环境氛围中的文人心态之外,也表现出早期文人词“雅化”意识还不够自觉。南唐在以李璟、李煜与冯延巳为代表的词作中,除了李煜前期尚有“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等写幽会偷情之作外,其余绝大部分是“以韵为词”的。相对温词,他们更脱去了秾华浮艳,更注重士大夫文人的高雅情致,所谓“南朝李氏君臣尚文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李清照《词论》)。李璟的两首《摊破浣溪沙》,于深婉清丽的笔调中隐约透出一种难言的惆怅,思致宛然,决无浅薄率意之病。冯延巳词则以“其旨隐,其辞微”“闳深美约”“思深韵逸”受到后世词人的激赏,而后主词被看成“宋人一代开山”,其原因即是“盖温韦虽藻丽,而气颇伤促,意不胜辞。至此君方为当行作家,清雅宛转,词家王孟”(胡应麟《诗薮·杂编》)。要之,南唐词中之“韵”已从一般的优雅含蓄发展到清雅宛转,其士大夫文人尚“清”尚“雅”,注重旨隐辞微之逸韵的审美理想在他们那里已经初步形成。而后主后期因为身世变故所写的那些抒发人生感慨的“主气”之作,对宋代士大夫作词之主体意识的确立也有开启作用。鉴于此,后世词家对南唐词评价历来很高,正表明了文人们对词应具有高雅不俗之士大夫情趣这一文学观念的普遍认同。
五代结束以后,进入北宋,起初五十年的词坛是颇为沉寂的,最早打破这种沉寂的名家是柳永。若论柳词写作旨趣,“以色”“以趣”“以韵”“以气”者皆有,然以“以色为词”最受市民阶层欢迎,影响最大,也最具作家特色。所谓“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叶梦得《避暑录话》),使其成为风靡一时之流行歌曲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其语言俚俗,但与其宣扬色情的浓厚世俗情味也是大有关系的。柳永与温庭筠身世相似,都是仕途失意者,但他更具有不愿以“浅斟低唱”去换取浮名的自觉意识,而甘心作一个“偎红倚翠”的才子词人。他明白地宣称自己的兴趣乃在“烟花巷陌”的意中人身上,因此用自己的词笔尽情描写“似恁偎香倚暖, 抱着日高犹睡”(《慢卷》)的床第之乐与鱼水之欢,其写作旨趣显然在于表现色情性感。然而正是这种“淫艳猥亵不可闻之语”,产生了“四方传唱,敏若风雨,人人歆羡咀味于朋游尊俎间, 以是为相乐”(鲖 阳居士《复雅歌词序》)的轰动效应。面对这股代表市民文化思潮的“柳词热”,处于社会上层的正统士大夫文人深为不满,他们很忌讳“俗艳”而推崇“雅致”,尽管他们也并非不好色,在其作品中也免不了要描写色情以自我欣赏,但他们在理论上却是反对“以色为词”而赞许“以韵为词”的。与柳永同时及稍后的晏殊、张先、欧阳修等即是这样一批词人。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载晁补之语云:“张子野与柳耆卿齐名,而时以子野不及耆卿,然子野韵高,是耆卿所乏处。”正是看出了张先胜过柳永处在韵致高雅。然而在张先词中犹有“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千秋岁》)那样的直白之作,而不如晏殊词的温雅有致。李之仪在《跋吴思道小词》中论道:“(词)至柳耆卿,始铺叙展衍,备足无余……韵终不胜,由是知其为难能也。张子野独矫拂而振起之,虽刻意追逐,要是才不足而情有余。良可佳者,晏元献、欧阳文忠、宋景文,则以其余力游戏,而风流闲雅,超出意表,又非其类也。……语尽而意不尽,意尽而辞不尽,岂平平可得仿佛哉!”王灼《碧鸡漫志》也认为“晏元献公、欧阳文忠公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风流闲雅”“风流蕴藉”“温润秀洁”正是晏词创作旨趣之所在,也是晏词中“韵”的审美内涵。晏殊虽然也是抒发传统的婉约情思,但他已很少代妇人立言,在他的词中,士大夫文人的闲情逸致已基本代替了男欢女爱的风月之情,较之南唐词,措辞更文雅,格调更高雅,风格意境也更为淡雅而具有深远悠长的韵味。之所以如此,正是与他追求一种富贵闲雅的平和气象与温文高雅的书卷气质分不开的。这种美学追求在承平时代生活优裕的上层士大夫文人中很有代表性,那些“云破月来花弄影”(张先《天仙子》)“绿酒初尝人易醉”(晏殊《清平乐》)“水面风来酒面醒”(欧阳修《采桑子》)等流连花月、诗酒逍遥的词作都体现了富贵闲雅的生活情趣,在后世文人看来的确韵味无穷,故极为他们赞赏歆羡。
如果说,晏殊一派是从“以韵为词”角度对词进行雅化,那么,苏轼一派则是从“以气为词”角度来对词进行雅化的。从胸襟气度上来说,苏轼已不是一般的文人雅士,而是旷世难有其俦的“逸怀浩气之士”,他无意精研小词之道,而只是将词作为抒发人生意气的“陶写之具”,故“满心而发,肆口而成”“雄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三引晁补之语)。元好问说:“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新轩乐府引》)近人蒋兆兰《词洁》亦云:“自东坡以浩瀚之气行之,遂开豪放一派。”在苏轼以前,李煜、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等人也曾以词抒发意气,但无自觉意识,或只偶一为之。而东坡则于词中以旷放恣肆的笔调尽情抒发胸中的愤气、狂气、浩气、逸气,以致不顾“以诗为词”“句读不葺之诗”“不知音律”等非议诟病,唯求一泻磊落之气而为快(注:何薳《春渚纪闻》卷六载东坡尝自言“某平生无快意事,唯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东坡《思堂记》亦云:“余天下无思虑者,遇事辄发,不遐思也。”清人许昂霄《词综偶评》亦谓“东坡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唯词亦然”。此数语,皆可窥见东坡“以气为词”写作旨趣。)。过去往往有人以为东坡要在“婉约”词派外另建“豪放”一派,但事实上真正够得上“豪放”风格的苏词在其集中只占有十分之一不到的比例,倒是抒发人生意气之作几乎占了三分之一的份量,这是在他以前的词人中从未有过的现象。而苏轼也正是在以词畅快淋漓地抒发人生意气方面与李、范、王、欧等写“士大夫之词”者一脉相承而与那些写女性、女色题材,风格婉媚柔曼的“伶工之词”迥然有异的。进而言之,李、范、王、欧那些曾被人视为“豪放”之作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剔银灯·昨夜因看蜀志》《朝中措·平山堂》等其实也只是抒发了衰飒悲凉的人生感慨,很少带有“豪放”成分,故将其目为豪放词是不妥的。然而这一点虽已有学者指出,却未能将其与传统词作风格大不相同的原因找出来。只有王国维《人间词话》“词至李后主,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似能触及问题根本。盖士大夫之词必须体现士大夫的胸怀理想、思想意识与精神世界。而最能体现士大夫生命精神与生命意识的就是那些直抒感慨、直诉怀抱的意气之作。至于那些表现缠绵旖旎之风神韵致的作品则只善于传达幽微的思致意绪,显示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由此可见,这种从“以气为词”角度对词体进行的改造,是比“以韵为词”更为彻底的。这已经不是一般的优雅、文雅、高雅所能概括的了。相比之下,通过含蓄蕴藉的情趣对词进行雅化还不能让词脱离婉约柔媚的“小道”性质,而只有“以气为词”才是对士大夫志气怀抱的发扬,才是对士大夫气格人品的尊重。陈洵《海绡说词》说:“东坡独尊气格,箴规柳秦,词体之尊,自东坡始。”便是对苏轼“以气为词”从“气格”上对词进行雅化之作用的肯定。苏词的这一意义也被当时人看到了,王灼说:“(苏词)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碧鸡漫志》卷二)胡寅说:“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酒边词序》)王、胡二说固然有些以偏概全,但却能敏锐地感受到苏词中出现的新质及其所产生的作用。在苏词影响下,一时间,黄庭坚、晁补之、贺铸等人皆写了不少抒发人生意气的词作。尤以晁补之《摸鱼儿·买陂塘》诸作最具“坦易之怀,磊落之气”,故“堂庑颇大”(《艺概·词曲概》语)。然而,“以韵为词”却已是词坛大趋势,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定型,似已成为填词者必须遵守之游戏规则,故“以气为词”虽对此有所突破,却不能与之分庭抗礼。不但黄、贺,就是东坡本人也颇多表现韵致的作品。当然,“以气为词”与“以韵为词”在本质上也并不相妨,而不像“以韵为词”与“以色为词”有着雅俗性质上的区别。在坚持“雅化”这一共同审美理想的原则下,“以韵为词”与“以气为词”对“以色为词”都表现出强烈不满。晏殊讽刺柳永“彩线慵拈伴伊坐”写男女旖旎情事,苏轼不满秦观“销魂、当此际”的柳味狎昵词,都可看出此中消息。但尽管如此,其他文人还是难以完全放弃“以色为词”,在黄庭坚、贺铸甚至秦观词中都有一些“亵狎”之作,黄作中尤多。不过总的来看,他们还是有着崇尚“雅韵”的自觉意识,秦观即是在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的人物。冯煦说他的词“闲雅有情致,酒边花下,一往情深,而怨悱不乱,悄乎得小雅之遗”(《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周济则称赞其“和婉醇正”“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笔”(《宋四家词选序论》)。而贺铸“工语言,深婉丽密,如次组绣”(《宋史·文苑传》),其写作旨趣可以想见。与此同时,“以趣为词”在文人间也颇流行,苏轼的《南歌子·师唱谁家曲》、陈慥的《无愁可解》、黄庭坚的《渔家傲·踏破草鞋参到了》都是著名的调笑之作。与早期谐谑词不同,苏黄趣词多“借禅以为诙”,即通过幽默、轻松的笔调,以反讽自嘲的方式表示自己对世相人生的悟解。
随着慢词长调的成熟,“以韵为词”更朝着缠绵沉郁、回环往复方面发展,“韵”的内涵也更加丰富。周邦彦便是一位集大成者。周是一位才华富赡、极深于情又极温厚和平的江南才子。他一生屡遭摧挫,心态长期压抑。故其词“无处不郁,令人不能遽窥其旨”,“遥遥挽合,妙在才欲说破,便自咽住,其味正自无穷”(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而他正是以这种沉郁顿挫、凄咽缠绵的方式来倾诉自己那一腔幽怨难言的情愫与思绪的。清真多慢词,又妙解音律,精研词法,能自创长调,其妙处在反复勾勒,所谓“层层脱换,笔笔往复”(周济《宋四家词选评》),然虽一往情深、哀怨至极而又终未有一语道破,所谓“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无一点市井气”(沈义父《乐府指迷》),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浑厚和雅”(张炎《词源》)的艺术特色,而“浑厚和雅”也正是周词“韵”之内涵,它被后世“以韵为词”者推为词体艺术的极至。周邦彦也因此获得了“词坛巨擘”“冠冕词林”的最高评价。冯煦在《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中说:“毛氏先舒曰:‘北宋词之盛也,其妙处不在豪放而在高健,不在艳冶而在幽咽。豪放可以气取,艳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则关乎神理,难可强也。’又曰:‘言欲层深,语欲浑成’,诸家所论,未尝专属一人,而求之两宋,唯片玉、梅溪,足以备之。周之胜史,则又在‘浑’一字,词至于‘浑’而无可复进矣。”
“词至于浑而无可复进矣”,浑者,浑厚而不纤弱也,浑化而无痕迹也。从周邦彦这位集大成者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以韵为词”中“韵”的内涵从唐到北宋的发展演变轨迹,即从温庭筠的“含蓄优雅”发展到南唐词的“清雅宛转”,再发展到晏殊的“闲雅温婉”,进而发展到周邦彦的“浑厚和雅”,是为尽善尽美矣。荆浩《画有六要》曾对“气”“韵”的概念作过辨析,他说:“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即由于胸中意气充溢,气度恢宏,故运笔取象,随心所欲。“韵者,隐迹立形,备仪不俗”,即不仅要具有高雅不俗的形象,而且意味深藏,不可显露痕迹。故韵者,常指雅韵、韵外之致也。宋代范温《潜溪诗眼》说:“有余味谓之韵。”故韵必须含蓄蕴藉,婉曲有致,余味深长。人们常以神韵、远韵、清韵、雅韵、余韵、幽韵来言“韵”,与“气”相比,“韵”的最大特点即性质上属于一种幽深微妙的意绪而非强烈深重的感慨,表现上则是冲淡、含蓄而非发露的。如前所述,“韵”之所以成为词的特质乃是雅化的需要,正是由于雅化才使词从“主色”“主趣”向“主韵”转化,也是由于雅化才使词中之“韵”的内涵越来越趋于精致、完善、丰富,从而使词摆脱了早期的俗艳、浮靡,而越来越朝着优雅、婉曲、幽深、蕴藉、缠绵、隐约、隽永方向发展。
两宋之交,词坛上一方面是士大夫文人越来越注重词的和雅浑成,倡导雍容典重的大家气质(如李清照《词论》所论),另一方面却是在下层浅薄少年中又掀起一股柳永热。此时一位号称“滑稽无赖之魁”的词人曹组也极受欢迎,据王灼《碧鸡漫志》记载,“今之少年妄谓东坡移诗律作长短句,十之八九不学柳耆卿则学曹元宠”。以曹组、张山人、王彦龄为代表的词人都是“善作滑稽无赖语”者,他们的作品“嫚戏污贱,古所未有”(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而“闻者绝倒”“脍炙人口”,可见“以色为词”与“以趣为词”在此时仍有市场。“只是由于为周邦彦的雅词所压倒,后又为南宋爱国词所压倒,才没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刘庆云《词话十论》第229页,岳麓书社1990 年版)。
南渡之后,因着时代的原因,文人们的愤气、浩气被激发起来,词也再不能含蓄缠绵下去了。所谓“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与苏轼时代以词抒发个人意气不同,此期词之中气乃是由国家、民族灾难所激起的群体悲愤,所以由苏轼开创的“以气为词”至此才成气候。这首先是岳飞、李纲、胡铨等爱国名臣和张元干、张孝祥等人“忠愤气填膺”的慷慨之作,另外像朱敦儒、向子諲等人也常以词抒发悲怆激越之爱国情怀。“以色为词”“以趣为词”因着人们心情与时代气氛已再无复前时之热。在大动乱过后,周、秦的流风余韵又在词坛泛起,尽管在清丽婉约之中多少寄寓着时代忧患之感,但总的来说,是在体验一种心灵意绪而非抒发强烈深重的意气。
“以气为词”的集大成者是辛弃疾。其门人范开说他“意不在作词,而其气之所充,蓄之所发,词自不能不尔也”(《稼轩词序》)。黄梨庄《借荆堂词话》也说他“一腔忠愤,无处发泄”,“故其悲歌慷慨,抑郁无聊之气,一寄之于词”。然稼轩因其所处的特定时代,本人与历代词人完全不同的独特生活经历等缘故,其胸中意气不惟激越强烈,而且特别沉雄厚重。较之苏词中常见的“逸怀浩气”,辛词中的“气”显然更多酸楚悲愤、抑郁怨怒的成分。因此,他虽“不平之鸣,随处辄发”(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但那种壮志难酬、报国无门而屡遭摧挫的情感更多地是借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出来。夏承焘先生认为辛词在“一层隐约含蓄的外衣之内,有一颗火热的心在跳动”,因此具有“肝肠似火,色貌如花”的美学特征,刘扬忠先生认为“具有某种集大成性质的稼轩体,不但在思想特质上堪为南宋时期民族正气与时代精神的代表,而且在艺术上也全面继承了词体文学的优秀传统,完成了南北词风、刚柔之美的融合”(《南宋中后期的文化环境与词派的衍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7年第6期)。 这些都是对辛词艺术十分准确的把握。正因为以抒发意气为主要旨趣的辛词能采取“以韵为词”者常用的回环往复、比兴寄意的表现手法,所以才会时时呈现出蕴藉、缠绵、宛曲的艺术特点而又使人感到“姿态飞动”“有力如虎”(陈廷焯《白雨斋词话》),才能“于雄莽中别饶韵味”(同上),“于豪迈中见精致”(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这是在“主气”基础上“气”“韵”最佳的结合,它既不违背词的艺术特质,又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胸中的意气。这种所谓“摧刚为柔”“寄劲于婉”的创作方法得到了词人们的普遍承认,“以气为词”也只有到了辛弃疾这里才既保持“本色”,又多姿多彩,艺术上也更加完美成熟。在辛词的带动下,陈亮、刘过、黄机、刘克庄等人皆能于词中寄以磊落之气,其中尤以陈亮“不作一妖语、媚语”(毛晋《龙川词跋》),其抒发意气时“精警奇肆,几于握拳透爪”(《白雨斋词话》)。今人吴熊和先生认为他“吐气如虹,比辛词更豪放横肆”(《唐宋词通论》第249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年版)。而辛本人则与苏轼一样,虽是“以气为词”的集大成者,其旨趣却不局限于此,除不写色情词外,也有不少纯粹“主韵”“主趣”之作。由于他腹笥颇丰,那些“主趣”之作不但生动幽默,而且极显学问,比前时苏黄之作更有发展。
与辛弃疾同时的姜夔是一位出身孤寒而布衣终老的词人,他一方面具有“翰墨人品,皆似魏晋之雅士”(周密《齐东野语》载范成大评语)的清高气质,另一方面为了生计,又不得不长期寄食公卿,作豪门清客。现实与人品之间的矛盾,使姜夔的人格意识十分强烈,而怀才不遇、困顿落魄的身世遭遇也时时使他充满悲怨难平的感慨。但姜词中并无多少直抒意气之作,因为他写词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表现高雅不俗而又思致深微的风神韵致(注:关于白石词主韵,张惠民先生《宋代词学审美理想》第十二章《清空高远的审美理想》一节有极为详尽透辟的论析,可参看。《宋代词学审美理想》,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之所以如此,当然与他始终只是一位清客词人,其意气远不如苏辛二张等忠愤之士强烈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有不少词作即是写在达官贵人府中,甚至就是在陪同主人宴赏游玩时的“应制”“奉和”之作(如代表作《暗香》《疏影》《齐天乐》等),这当然就不便直抒意气了。他只是通过揣摩物态神理和精研辞句,表达出一种幽微清妙的韵致,以供他的读者细细品味,赏玩不已。然而姜词毕竟不全都是娱人之作,况且他的读者与温词、柳词甚至周词的读者也有本质的不同。如杨万里、范成大、萧德藻、张鉴等在当时皆是学养极深的名公巨儒。因此姜夔作词必须特别讲究雅正,讲究气骨,才能使他们在赏识其辞章的同时也敬重其人品。与温、李、晏、周等“以韵为词”者相比,姜词中不但无半点“俗艳”,而且也没有一丝柔媚软弱之气。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说:“白石脱胎稼轩,变雄健为清刚,变驰骋为疏宕。”但与稼轩“摧刚为柔”“寄劲于婉”相反,白石则是“以健笔写柔情”,这是在“主韵”基础上的“气”“韵”结合。他无论写景状物,皆能于冷色幽香中表现出萧瑟苍凉的韵致,而词人清刚孤傲之人品气骨即于此种“古雅峭拔”(张炎《词源》评姜语)的韵致中隐隐传出。因此,白石词虽未直接抒发意气,但其意气却隐含于其词的气骨之中。可以说,若无怀才不遇的意气便无自尊自傲的气骨,而气骨也正是姜词中意气与韵致得以结合的中介。唯其“气”“韵”结合,才能“以健笔写柔情”,唯其“气”“韵”结合,才形成了姜词所特有的“清空骚雅”“古雅峭拔”之艺术特色。
南宋末年的词坛,除刘克庄、刘辰翁等少数作家尚有慷慨悲歌的“主气”之作外,基本上是“主韵”一派的世界。史达祖、吴文英、王沂孙、张炎、周密等都被后世视为姜派词人。他们一般都具有或依人作幕或落魄终老的凄凉身世,其创作旨趣也大都在于表达幽清哀怨的心境意绪。然而,与姜夔相比,他们再难有清刚的气骨,而只能沉潜于典丽的辞藻与精审的音律章法之中。他们的雅化意识比在此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作家都更自觉、更明确。所谓“音律欲其协,不协则成为长短之诗;下字欲其雅,不雅则近乎缠令之体;用字不可太露,露则直突而无深长之味;发意不可太高,高则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沈义父《乐府指迷》)便是他们对词法的总结。他们近学姜夔,远绍周邦彦,协音律、崇雅正、主深致、尚柔婉既是其词中“韵”之内涵,也是其所追求的词体艺术之审美理想。这种由他们确立下来的词体审美理想,在元明清数代几成定论,很少有人提出异议。词发展到宋末这批文人,真可以说是雅化得无以复加。“主气”与“主趣”之作在他们那里已经销声匿迹,“以气为词”也因有直突发露之嫌而屡为其非议。但这种“雅词”由于过分讲究语辞的雕绘,典故的堆垛与表现的深隐复杂,其内容常常令人费解,其韵味也不易为人感受。因着时代的关系,在南宋灭亡、国难当头之际,爱国英豪还是要以词抒发胸中悲慨,下层人民也时常将“趣词”用作讽刺权奸当道、朝政昏庸的武器。至于“以色为词”,则本是唐宋以来因城市经济发达,为着适应市民阶层娱乐需要而产生的,只要生存的环境仍然存在,就不可能完全消失。在宋末士大夫文人将词完全雅化之后,“主色”与“主趣”的写作旨趣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走入了元曲之中,在新一代的文人那里获得了新生。
上面我们对于唐宋词创作旨趣之发展演变过程作了一番简要的勾勒,限于篇幅,许多问题都未能进行深究。我们认为,本文的主要意义是在于提供了一种对唐宋词研究的新视角。相对于“以诗为词”“以文为词”等仅从表现形式与文体风格特征来论述作品的方法,“以韵为词”“以气为词”等概念从创作旨趣角度来观照唐宋词作家作品,无疑更贴近于词体艺术本质,也更适合于揭示创作主体审美追求的自觉性,便于反映词作中审美意蕴之内涵的复杂性与流变性,从而对唐宋词发展规律的考察起着一定的拓展思路之作用,对那种只根据古代原始词学理论进行阐释的单一狭窄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有所突破。我们认为,作家的创作旨趣,既受到时代与社会的影响,受到文学源流继承发展等因素的影响,更与其个人人格理想、性情怀抱、身世遭际有直接的关连。而士大夫文人作为一个与市民相对的阶层,在其审美理想、创作旨趣等方面自有共性存在。过去我们的词学理论往往只重视作品表现手法的运用与艺术风格的形成,近年来加强了对作家及流派的审美理想与创作实践关系的研究,但对创作旨趣在审美理想与表现手法及艺术风格之间的中介作用缺乏必要的注意。其实相对审美理想来说,创作旨趣更直接影响到表现手法的运用,并直接作用于作品风格体貌的形成。因此,笔者不揣浅陋专撰此文对其进行论证,也是希望引起词学界的重视,起到抛砖引玉之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