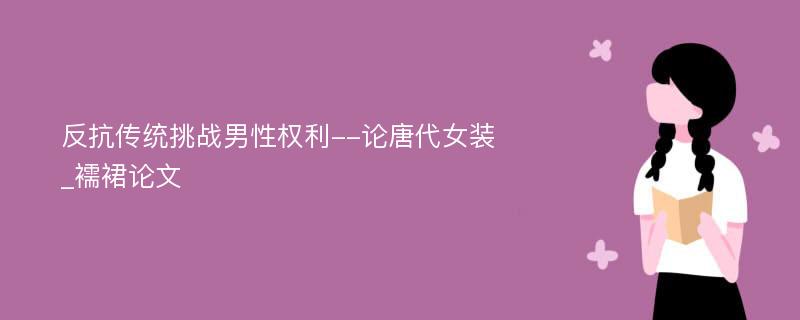
反叛传统 挑战男权——试论唐代妇女服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男权论文,唐代论文,试论论文,妇女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4)03-0046-05
就像唐代妇女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代妇女的服装在中国服装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唐代妇女的服装除了是封建社会中一朵昂首怒放、光彩无比的瑰丽之花,最重要的则是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奏响了一曲“反叛传统”,“挑战男权”的强音,至今仍余音袅袅。
唐代妇女的服装主要分为襦裙、男装、胡服三种。袒露颈部、胸部的襦裙(有人也称之为袒胸装),是对《礼记》“短毋见肤,长毋被土”传统服装制度的反叛,而女子着男装则是对《礼记》“男女不通衣裳”的挑战了。其内含前者是“女性崇拜”之遗风在服装上的表现,后者则是在此“女性崇拜”的基础上,对男权的公然挑战,是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服装体现。下面,试分别论述:
一、襦裙
襦裙服主要为上着短襦服,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足登凤头丝履或精编草履。上襦很短,襦的领口常有变化,但是不管是圆领、方领、斜领、鸡心领,领口都开得很大,一般可见到女性胸前乳沟,这是中国服饰演变中比较少见的服式和穿着方法。在永泰公主墓壁画中,宫廷女官们上衣衣领都低至胸部,丰腴的颈项与乳房上部都露在外面。陕西唐代李重润墓中石椁上的宫装女子像,身穿宽领短衫,领口开敞,并且刻画了外露的乳峰形状。周芳的《簪花仕女图》描绘的也是这种袒胸的服饰。唐代懿德太子墓石椁浅雕和众多的陶俑上都显示了这种领型。方干的“粉胸半掩疑暗雪”(《赠美人》);欧阳询的“二八花钿,胸前如雪脸如花”(《南乡子》);周芳的“慢束罗裙半露胸”(《逢邻女》)……就是对这种服饰的形象描绘。这种服装被宋代以下的道学先生称为“淫佚之行”,没有能够续存下去,成为封建社会中的一段千古绝唱。
服装说到底是一种文化现象。《说文》曰:“衣,依也。”《白虎通》曰:“衣者,隐也。裳也,鄣也,所以隐形自鄣也。”《释名》曰:“衣者,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通典·礼志》曰:“上古穴处,衣毛,未有制度。后代以麻易之,先知为上,以制其衣;后知为下,复制其裳,衣裳始备。”从这些经典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衣裳最初的功能就是御寒遮羞的,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具有了社会性。据“周公制礼”的说法,在西周时期,中国的服装制度就已经非常完备了,这也使得中国人从上古时期就处在一种严密的思想束缚之中。《旧唐书·舆服志》曰:“昔黄帝造车服,为之屏蔽,上古简俭,未立等威。而三五之君,不相沿习,乃改正朔,易服色,车有舆辂之别,服有裘冕之差,文之以染缋,饰之以絺绣,华虫象物,龙火分形,于是典章兴矣。”服装除了有严密的等级制度外,对其式样、尺寸也有严格的限制。也就是说,古代的中国服装一直是在如何严密地遮掩身体上面做文章,而不是去研究如何突出人体的曲线美和健康美。在服装式样的选择上,道德标准时时压倒审美标准,礼仪要求常常克制实用目的。[1](P63)
有唐一代,崇尚道教。而道教在其孕育和形成的过程中,始终体现着一种女性崇拜。构成其理论内核的老子学说就是以女性崇拜为其学说的特征。拙文《〈太平广记〉山洞意象文化分析》考证,“山洞”是女性崇拜的遗存,是整个社会“回归母体”情结的表现。也就是说“女性崇拜”是有唐一代社会的潜意识表现。吕思勉先生认为:“《老子》全书之义,女权皆优于男权,与后世贵男贱女迥别。”[2]程伟礼认为:“《老子》一书存在着生殖崇拜的遗迹,老子大量地吸取中国女性的智慧,对女性的处世经验加以概括,并作为一些基本命题融合进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老子甚至还把回归母亲子宫当做一种终极追求。”[3]老子生于父权制文明之世,但是却顽强地坚持为父权制文明的正统意识形态所不容的远古女神宗教的思想遗产。他让“可以为天下母”的混沌充任宇宙发生神话的主角,这样便有效地排斥了男性中心文化所推崇的男性创世主的观念。宇宙万物是原始母神“生”的结果,而不是男神凭借其至高无上的意志和权威“造”的结果。[4](P183)也许正是老子的“女性崇拜”的思想暗合了有唐一代“女主”的环境,老子才被推崇为大圣高上大道金阙元元皇帝。
在原始社会中,最重要的不外是生存和生育两件事。在这两件事上,女性占有最重要的力量,成为维持民族生存的决定性力量。女性崇拜成为历史最悠久的性别崇拜,女性成为历史最早,人数最多的崇拜偶像。马克思说:“在一切蒙昧人中,在一切处于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中级阶段,部分地也处于高级阶段的野蛮人中,妇女不仅居于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当时刚刚灭亡的母权制,还有一个残余,这就是在罗马人看来几乎是不可理解的,德意志人对女性的尊敬。他们认为妇女是一种神圣的和先知的东西;他们也在是最重要的事情上听取妇女的意见。”[5](P60)
《朱子语类·历代类序》:“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统治阶级氏族及其升降》一文中也指出:“若以母系母统言之,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独孤氏,太宗之母窦氏,即纥豆陵氏,高宗之母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故李唐皇室之女系母统杂有胡族血胤世所共知。”由此可见,从李唐王朝皇室母族的血缘渊源看,其血统不是汉族,而是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族的后裔。李渊家族世为北魏武川镇军官,李渊祖父李虎随宇泰开创关中政权,是两魏、北周之际有名的八柱国之一,其父李炳也是柱国大将军。可知李渊父族亦为鲜卑化汉族。所以,在李唐王朝开国初期的几位帝王身上,自然不可避免地渗透北方草原民族的精神气质,自然不可避免地保存着母系氏族女性崇拜的痕迹。正是由于这块基石作为潜在的社会心理基础,一代英杰武则天以女性的资质登上了那一直由男子垄断的皇帝宝座,而且“内辅国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当时称为‘二圣’。”后来“加尊号曰圣神皇帝,降皇帝为皇嗣。”[6](《则天皇后本纪》)
以露为美的襦裙,虽然远不及则天称帝那样波澜壮阔,影响深远,但是,这一令后代儒学先生们瞠目的服饰现象,不仅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大唐帝国的宫廷内院,而且还引发了诗人、画匠们的创作灵感,被名正言顺地载入了史册,这不能不说与“女性崇拜”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
女性崇拜最主要的是女性生殖崇拜。新石器晚期红山文化的孕妇裸像,原始艺术家夸大了女性身体的曲线,突出了她肥硕的乳房和臀部,还有圆鼓的腹部,充分表现出对女性生殖功能的赞美和崇拜。[7](P52)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四壩文化(公元前2000年)彩陶人形壶,亦为裸胸女子。[8](P15)旧石器时代大母神石像——所谓委兰朵的维纳斯,那完全缺乏线条韵躯体明显地体现了雌性本质:永远怀孕的大肚子,水囊似的巨乳。原始的生育崇拜者神化了雌性本质,在物质贫乏的处境中,他们把自己对丰饶的贪求,都寄予雌性躯体的神秘力量。[9](P42)这位大女神,作为一个整体,是创造新生命的象征,而她身体的各部分也并非肉体器官,而是生命领域神圣的象征中心。因此,大女神的自我表现,她对乳房、腹部,甚至全裸的驱体展示,都是显圣的形式。所以,在克里特文化圈内,乳房的裸露是一种适应于祭典的圣事行为。女神和与她同一的女祭司们展示她们丰满的乳房,滋养的生命之乳的象征。[10](P127)乳房,它赋予女人以营养施与者的典型特征,依据希腊的传统,第一只酒杯是以海伦的乳房为模型而仿制的。[10](P124)
总之,母腹、子宫、牝器、乳房等等都是人类和大地的生殖力、生命力的象征。向往、歌颂、回归它乃是农业民族追求丰盛和安谧的心理从深层结构里情不自禁的外化或物化。[4](P819)那么,唐代的妇女们穿上这种坦胸露乳的襦裙,本身也是“显圣”的再现,另外也是“女性崇拜”服装化的表现。然而中国隶属在典型的表意(内向)系礼教服饰文化圈内。[11](P86)
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遥远的法国竟然上演了一幕与我国唐代妇女同出一辙的服装剧——乳裸运动。这场运动是与妇女解放运动同时出现的。这是一个裸乳开始的时代,如果不这样做,就会枉费一生,勇敢地投身于这种冒险的女人们,揭开了解开胸罩扣链的序幕。[12](P37)这是一种回归自然的行为,自然,女性自然,母亲自然。[12](P57)这是向原始舒适感觉的回归,向作为文明对立面的自然状态的回归。[12](P75)而法国的这场裸乳运动与唐代的袒胸襦裙装的盛行相比,迟了1300余年。不管是唐代的袒胸襦裙,还是法国的裸乳运动,都与妇女本身的个性自由,思想解放有极大关系。前者诞生于“女性崇拜”之风盛烈的唐代,而后者孕育子女权色彩颇浓的妇女解放运动。难怪高罗佩不无叹息地说:“可是在宋代和宋以后,(妇女)胸部和颈部都先是用衣衫的上缘遮盖起来,后来用内衣高而紧的领子遮盖起来。直到今天,高领仍是中国女装的一个显著特点。”[13](P245)
自由的乳房尚停留在观念的层面上。大概只有到了那一天,当大多数女人把身体的舒适看得比美观重要,当乳罩毫无用处,当乳房已同脖子或脚一样失去性感,被同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看待,女人才有可能挺起自由的乳房走向人群。[9](P51)唐代妇女已经先知地潇洒走一回了。由女人大大方方展示自己身体之日,正是历史还女人自由平等的权力之时。
与袒胸的襦裙配套而穿的是半臂和披帛。半臂是一种短袖上衣,由汉魏时期的演变而来。一般多为对襟,长及腰部,两袖宽大平直,长不过肘。《新唐书·舆服志》:半袖裙襦者,东宫女史常供奉之服也。“披帛”,《中华古今注》卷中记载:“女人披帛,古无期制,开元中,诏令二十七世妇及宝林、御女、良人等,寻常宴参侍令,披画披帛,至今然矣。”半臂和披帛既不能御寒,也不能遮体,它们完全是唐代那求新求美的社会文化心理在服饰上的形象体现,是服饰由实用向审美的又一次飞跃。
与袒胸的襦裙一样,反映唐代妇女反叛传统,追求自由的性格是唐代妇女对羃羅的抛弃。羃羅是一种遮面之巾,巾幅宽大,不仅可以遮住脸面,还可以用以遮蔽身体。与《礼记·内则》:“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相一致。《旧唐书·舆服志》曰:“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羅。……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渐为浅露。……则天之后,帷帽大行,羃羅渐息。……开元初,徒驾宫人骑马者,皆著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遮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俄又露髻驰骋,或有著大夫衣服靴衫,而尊内外,斯一贯矣。”我们可以从敦煌莫高窟第323窟初唐《迎佛图》,217、103窟《法华经·化化城喻品》中骑马出行的妇女身上,看到遮盖不同的羃羅形象。[14](P725)
综上所述:袒胸的襦裙的盛行的渐息以至绝不行用,使我们得知唐代妇女女性意识的觉醒,以及她们对传统的反叛。
二、男装
如果说袒胸的襦裙是女性在“女性崇拜”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反叛,那么男装则是女性对男权文化的挑战了。
中国礼教的特点之一,就是提出社会地位上的男女有别,而且明确强调“男尊女卑”(拙文《女子是如何生成的》中有详细论述)。由于儒家强调禁欲,所以也不主张男女之间的沟通。在《礼记·坊记》中,孔子说:“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故男女授受不亲。”这些礼教精神自然反映到服饰上来。《礼记·内则》曰:“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这些礼教思想,长期桎梏着中国妇女的行动乃至思想,只有到了唐代,才出现了女着男装的着装时尚。
《新唐书·五行志》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新唐书·李石传》:“吾国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旧唐书·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大唐新语》:“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唐六典·内官尚服》注:“皇后太子妃青袜,加金饰,开元时著丈夫衣靴。”《新唐书·舆服志》:“中宗时,后宫戴胡帽,穿丈夫衣靴。”形象资料可见于唐代仕女画家张萱的《虢国夫人游春图》与《挥扇仕女图》等古代画迹。据学者统计,从公元643年的长乐公主墓到公元745年的苏思墓共有29处墓地的壁画中都有女着男装的形象。这种女扮男装形象,前后变化不大,一般头戴幞头,或扎布条,或露髻,身穿圆领或翻领长袍,腰束带,下身着紧口条纹裤,脚蹬线鞋或翘头靴,双手或隐于袖中,或捧包袱等物。这种形象初看起来很容易被认作男性,但从其服装艳丽的颜色发髻或幞头下的发丝,长袍下露出的花裤和女式线鞋,人物面部的柳眉细眼,小嘴红唇,面施薄粉,以及身姿、动作、持物等情形,可以判定出其女性的特征。[14](P734)
究其深刻内含则是女性想从“边缘”走向“中心”的服装表现。“女孩从一出生就面临着劣势。这肯定会强化她的男性情结,使她妒羡拥有她所缺少的所有权力的男性角色。”[15](P34)唐代女性不同于以往的女性,她们身上过多地带有母系氏族女性崇拜的痕迹,正因如此,她们才不会满足于男尊女卑的现状,她们想要重新走上政治、经济的舞台。据现存史料,唐代皇后只行过八次先蚕礼,其中武则天就占了四次。目的即要昭示臣民,她是一位政治领导者,一个公共人物,而不只是宫闱中的母妻。[16](P662)高宗龙朔二年(662)二月,朝廷更改了绝大多数中央政府机关与职位的名称,甚至连皇帝嫔妃的名号也一并更改了(皇后不包括在内)。这项措施的重点在改变这些妇女的身份性质。至少在名目中,她们由皇帝的妻妾变成内廷的官僚。旧名衔的字义几乎都是私人性的,而且都是沿袭过往宫廷组织的旧称,新名衔则是前无所承地创造这些称号试图将宫中的嫔妃定义为两类人:一是对皇帝统治有贡献的辅臣,一是皇帝的侍女,譬如“夫人”变成“赞德”——以增进皇帝的道德素质为职责的人,“九嫔”改为“宣仪”——宣示皇帝的威仪,“美人”改为“承旨”——承受皇帝的命令,龙朔二年的嫔妃名衔更改似乎强烈暗示,就像政府中的男人一样,宫廷中的女性也有重要的政治或实务上的功能。[16](P664)中宗继位不久,“最小偏怜”的幼女安乐公主就自请为皇太女,她曾说:“阿母子(或作阿武子)尚自为天子,况儿是公主,作皇太女,有何不可!”(《资治通鉴》卷二零八)这几乎可说是石破天惊的要求。她的行为无异于公开宣称,妇女在原则上可以当皇帝。[16](P681)
中唐诗人吕温曾写有一首关于上官婉儿的长诗——《上官昭容书楼歌》:“汉家婕妤唐昭容,工诗能赋千载同。自言才艺是天真,不服丈夫胜妇人。”全诗虽不及政治,但对婉儿“不服丈夫胜妇人”的志气颇致嘉许。唐代著名的宋若昭五姐妹,“皆性素洁,鄙薰泽靓,(化妆脂膏)不愿归人,欲以学名家。”……“德宗召入禁中。试文章,并问经史大谊,帝咨美。……又高其风操,不以妾侍命之,呼学士”……“穆宗以若昭尤通练、拜尚宫。”……“历宪、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与诸王、主率以师礼见。宝历初卒,赠梁国夫人以卤薄葬。”卤薄即帝王诸侯仪仗队。唐制四品以上官员皆有。[6](卷七十七列传第二)从中可看出她们强烈的女性意识。
如前文所引的霍妮,她把自我分成了三类:一是真实自我,二是理想自我,三是现实自我。自我的理想化,不会仅仅停留在内在的过程,而且会透入到实际的生活中,因此,一个人会企求去身体力行他的理想自我。那么,自我的理想化必定会产生一种广泛的驱力。这种驱力可分为:一是完美的驱力,二是雄心的驱力,三是极报复的驱力。[15](P141)以此来分析唐代的女着男装,我们可看出,像男人那样建功立业是“理想自我”,可是现实生活给予女性的机会少之又少,可以说是为了完美,也可以说是为雄心,甚至可以说为了报复,女子们先从服装上和男子一致,以满足自己理想自我的要求。唐代中后期,传世的图像和考古资料都再也见不到女扮男装的妇女形象了。女诗人鱼玄机只能“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康正果在《魅力的构成及其颓废》一文中指出:在雅典娜全副披挂的塑像身上,非女性化的倾向更为增强,除了她那男孩型的女相,她的衣裙上还套了甲胄,开了双性气质性角色易装互扮的先河。[19](P21)此外,她头盔上的怪兽和盾牌上的巨蛇,均显示了日神式美学中地母、灵怪之类雌性阴魂的残留。以此来观照唐代女着男装的壁画、雕像,我们难道没看出来母系氏族女性崇拜的残留吗?唐代妇女身着男装走下了历史舞台,但是比起《晏子春秋》中“妇子而男子饰者,裂其衣,断其带”的结局要好得多。毕竟在中国这充满男权蠂篱的舞台上,唐代的女子们真正地按自己的意志风光了一次,走了一回。
总而言之,唐代妇女服装是在既定的传统形式中吹嘘进新鲜的生命;在旧有的形态中融入了多样丰厚的感受。它自是历史的积淀与波衍。身着襦裙的唐代妇女,身着男装的唐代妇女都已经离开我们很久远了,但是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索:为什么在唐代会出现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袒胸的襦裙和潇洒男装?
收稿日期:2004-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