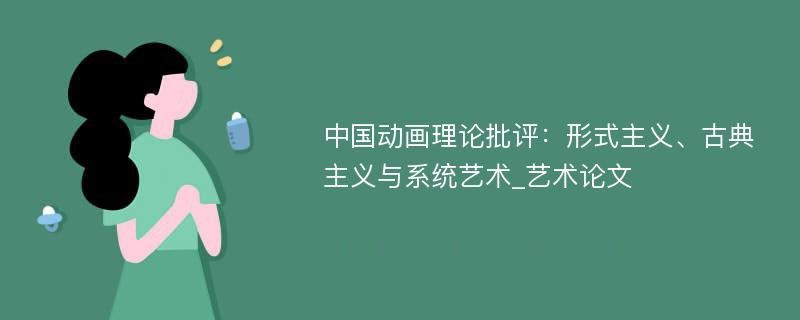
中国动画理论批判:形式主义、古典主义与体制艺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典主义论文,形式主义论文,中国论文,体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9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13)06-0109-(09)
研究中国动画,绕不开20世纪60年代—80年代曾在世界动画界独树一帜的“中国动画学派”。这对当下中国动画落寞现状而言,着实是个无法回避的尴尬。原因有二:一是后辈“不肖”,不仅在世界动画节上颗粒无收,未能再现万籁鸣等前辈艺术家昔日的荣光,而且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动画学派”退潮后,将国内动画市场几乎丧失殆尽,情况至今没有多大改观;二是“中国动画学派”所代表的“民族化”美学传统,与当下美、日动画所代表的“现代化”美学模式大相径庭,造成了当下中国动画理论界的严重分歧——“复古派”觉得重走当年的“民族化”美学道路才是立足世界的不二法门,段佳《中国动画向何处去》的长篇忧思堪称代表;[1]“洋务派”坚信借鉴当下美、日动画风行全球名利双收的现代商业模式,才是起死回生的强心剂。激进者直接质疑“中国动画学派”之称的由来。薛燕平说,“这一名词是国人自己发明的,电影史上并未明确出现过这一概念”。[2](P164)殷福军指出:“中国动画学派”一说来自国外的说法缺乏根据,因为找不到国外的原始出处。①其实两派均言之成理,但都只看到了问题的某一侧面。
“中国动画学派”当年屡获国际大奖,艺术成就与地位影响颇高。然而同为“中国动画学派”的代表作,何以《大闹天宫》辉煌无比,《金猴降妖》却在安纳西国际动画节铩羽而归?“中国动画学派”何以在短短几年内骤然衰落?这与“民族化”动画美学的自身缺憾有关,单纯“招魂”无从解决当下中国动画的生存困境。只有彻底厘清“中国动画学派”的成功关键与陨落根源,中国动画才能拥有真正的明天。只有站在艺术、历史与社会交汇的理论高度,反思既往中国动画的理念、形态与发展轨迹时,才能详尽深入地剖析当年的“中国动画学派”及其“民族化”美学道路的优劣得失。
一、美学特征:“形式主义”的惊艳与单薄
“中国动画学派”当年的成功,可称为“形式主义”的胜利。此说并无贬意。“形式”在西方美学史上地位极高,很早就“被定位为美和艺术的本体存在”,[3](P192)形式主义理论可追溯至赫尔巴特、康德甚至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20世纪初,克莱夫·贝尔和罗杰·弗莱倡导的“形式主义美学”直接推动了结构主义和符号美学产生。贝尔坚信“有意味的形式”,“就是所有视觉艺术作品所具有的那种共性”;[4](P4)弗莱认为“艺术作品的形式是其最基本的性质”,[5](P500)强调再现性内容引起的感情会很快消失,形式引起的愉快感受则永远不会消失和减弱。
“中国动画学派”没有如此系统深入的理论认知,但建国初民族意识空前激昂,与思想探索相比,民族艺术形式探索的前途显然更为光明。1955年上海美影厂厂长特伟提出“敲喜剧风格之门,探民族形式之路”,[6](P330)动画家集中精力于改编各种民间艺术、拓展新的动画片类型,以民族艺术形式取胜的整体风格逐渐形成,无意间暗合了“形式主义美学”,“中国动画学派”由此而生。
单凭“形式”特别便可名扬海外吗?一般不能,可“中国动画学派”适逢其会:一来,中西方历来多战争、贸易而少艺术交流,集中展现中国民族艺术的“中国动画学派”自然令西方人眼前一亮。当年“中国动画学派”在国际上的巨大成功,大半来自这种“少见多怪”的惊艳感。此类成功,要求不断花样翻新。故而“中国动画学派”从京剧、木偶戏、剪纸、年画、皮影、敦煌壁画等民间艺术中寻找素材与灵感。②这种“轻内容开掘、重形式改编”的创作模式,胜在短期内易于成功,但过于依赖改编并非长久之计,对原创动画的发展不利。二来“中国动画学派”中集中展现的民族艺术形式本身水准极高,往往是千百年来中国绘画、图案的精华所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命名本身就表明:新中国动画家视动画为“动起来”的“美术”,他们努力将中国画写意性、抒情性的艺术传统与境界融入动画创作之中。这与沃尔特·迪斯尼等人的“再现性”动画及其“写实性”绘画传统完全不同,却契合了形式主义美学大力揄扬“写意/表现性”绘画而批判“再现/写实性”绘画的艺术思想——“再现常常是一位艺术家的缺点的标记。一个低能的画家如果无力创作出哪怕能唤起稍许审美情感的形式,他将会通过暗示生活中的情感来弥补这一点,而为了唤起生活中的情感,他必须运用再现的手法”。[4](P15)简言之,西方人当初之所以被“中国动画学派”震撼,是因为透过“中国动画学派”看到的,不仅是一些风格独特的形式艺术动画,还有一种崭新的动画美学与美学路向。
然而,“惊艳”难以持久,到头来动画还是靠艺术水准说话。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动画改编,必须找到它与动画的完美结合点。这需要相当漫长繁琐的摸索实践。“中国动画学派”的成功之作,都是深入研究京剧、水墨画等艺术形式后的创造性转换,故能在动画中凸显原艺术形式的神韵精髓。据当时的动画设计严定宪回忆,在创作京剧动画《骄傲的将军》之前,“特伟为了探索民族形式,组织大家看了很多经典京剧……还带着我们一起去京剧学馆看演员练功,从中体会京剧表演艺术中的一些精华”。[7](P103)如此“改编”,难度之大、所耗时间资金之多、对主创人员要求之高,尤在一般原创动画之上。当年上海美影厂有国家的全力支持,聚集了国内最出色的艺术家,且动画年产量要求不高,③才有那段辉煌。
只是当年上海美影厂过于忽视理论建构,流传至今的动画遗产中,多形而下的方法技巧,却严重缺乏系统专业的动画理论。这种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方式,脆弱性可想而知。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动画在国外动画倾销与自负盈亏的双重打击下,艺术传统遽然中断。前些年中国动画重获政府支持时,业内人士兴奋之余竟不知所措,不知原创动画从何做起!为什么?因为很多人缺乏基本的动画理论常识,他们以为:当年“中国动画学派”也无非改编借鉴;同为借鉴改编,效仿陌生老土的“中国学派”,何如借鉴时下流行的美日动画?没有严格系统的动画理论指导,一味泛泛地批评,根本不足以扭转这种困境。
其实昔日中国动画的“形式主义”并不简单,没有足够的民族艺术造诣极难成功。时下中国动画改编受挫的根源,在于情节叙述与所改编的民族艺术形式相互割裂,没有当年“中国动画学派”的圆熟之感。这不是否认“民族化美学”动画道路的现时可能性,倘若有“十年磨一剑”的决心与毅力,万事皆有可能。只是动画艺术发展并非华山一条路,当代动画是包含绘画、文学、音乐、戏剧在内的综合艺术。
昔日“中国动画学派”纯以民族艺术“形式”取胜,在“内容为王”的今天看来过于单薄狭窄,并非动画艺术发展的最佳路向。美国的《花木兰》、日本的《十二国记》都是借鉴“中国风”的名作,可它们成功的关键乃是内容与形式的双赢。何况在人才交流频仍、资讯高度发达的当下,民族艺术形式早已不是国内艺术家的独门绝技,国外动画想披一件“中国风”的外衣并不困难,艺术造诣高超的西方动画家大师潜心研究后,完全可以模仿。迪斯尼动画大片《花木兰》的总美术设计师汉斯·巴彻,只花几周时间便触及中国画写意、白描等艺术精髓:“我看了一些原版的中国连环画……一种绘制树木、山峰和村落的独特方式。人物角色、动物以及道具的绘制更是巧妙绝伦……我注意到,在大多数单幅历经百年的水彩画中,有某种事物使其非常具有典型特征……那就是缺少透视和精细的细节内容,这使水彩画看起来非常平。”[8](P105,P109)他的仿作精妙绝伦,以至于赢得了动画界最高荣誉安妮奖的“动画长片制片设计杰出个人成就奖”。
当下中国动画的最大危机,不在于“民族形式/中国元素”的有无多少,而是理论认知与路向选择的问题。昔日前辈们以纯粹的“民族形式”取胜的经验无从复制,只有多管齐下,在动画剧本的深思熟虑、人物形象的精雕细琢的同时,融入深层民族文化心理,才是民族动画美学的康庄大道。
二、创作理念:“古典主义”的崇高与迂阔
形式主义美学在20世纪初颇具先锋意味,客观上以之成名的“中国动画学派”却极少给人“前卫/现代”之感。因为在更深的“内容”层面,从故事叙述到情感表达,它们实际遵循的是古典主义理念。
16世纪以来,关于“古典主义”争议不少,但“美、理性、健康和传统”等核心理念不变,多数学者认可高乃依阐发的创作原则:“模仿古代作家,以政治作为重要主题之一;对善与恶的朴素(也即是自然的)描写,以‘愉快宜人的方式’给予人们以道德教益;将鲜明主题置于古代背景,以确保逼真”。[9](P55,P56)“中国动画学派”与之颇为相似,“文以载道”“寓教于乐”“尊崇古典”等理念曾在中国动画形成阶段发挥重要作用,但也严重束缚了民族动画的拓展空间。
首先,“文以载道”被等同于“为政治服务”,不利于长远发展。动画艺术最初诞生时的社会语境,对其理念形成影响极大:西方动画出现于商业气息浓厚的美国,以娱乐大众为主要目的;中国动画“文以载道”的核心理念,早在民国时期便已定下基调。当时国难当头,万籁鸣等渴望“以动画片为政治现实服务,作为警钟来唤醒国人”,[10](P70,71)因此“我国的动画片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供人玩赏和娱乐的消遣品,它从一产生就跟当时的斗争现实紧密配合,紧紧地为政治服务”。[10](P70)动画家们将强烈的“政治激情”巧妙融于崇高优美的“图像叙事”之中,在当时可谓艺术与现实积极互动的必需:《铁扇公主》中唐僧师徒四人为过火焰山与牛魔王夫妇斗智斗勇的故事,改编为鼓动全民团结抗击强敌、克服困难的社会寓言;《大闹天宫》中天生地长的自由精灵孙悟空与戒律森严的天庭的冲突,演化成底层勇者反抗上层人物封建统治的革命;《哪吒闹海》里不谙世事的少年哪吒与四海龙王的私人恩怨,化作小英雄大义凛然、痛击祸害百姓的反动集团的正义斗争……热切激昂的早期中国动画与“崇拜至高无上的理性”④的古典主义可谓珠联璧合。
然而过犹不及。战乱时期成型的动画创作理念,在战后中国延续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宫崎骏等人还批评中国动画“政治倾向过于强烈”。⑤倘若中国动画能像华特·迪斯尼那样清醒睿智,只在二战期间积极配合美国军方拍征兵广告之类的宣传片,战争结束后便及时调整,恢复商业娱乐动画的本色,中国动画史理应更加辉煌。但建国之后,所有艺术创作都被扭曲为政治宣传工具,根本没有动画家们创作调整的可能。此后成型的“中国动画学派”,格外偏重对政治理念、现实政策的图解表达,完全忽略受众心理、艺术个性等其他因素与特点,乃是特殊形势下的历史必然。新时期以后,中国政府在给予动画创作空前自由的同时,几乎取消所有经费支持。中国动画陷入了新的尴尬境地,如履薄冰般行走于政治意蕴、艺术个性、经济收益与受众认可度之间。如此复杂艰巨的创作转型,单凭动画艺术家自身难以完成,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大力支持必不可少。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中国动画要走的路还很长。
其次,“寓教于乐”的实质是重道德教化,轻思想、趣味。从动画史的角度看,早期中国动画并未滞留在“少儿文艺(样式)”的层次故步自封:民国时期呼吁国民团结抗日的《铁扇公主》,新中国成立后《牧童》《山水情》等艺术短片,其实都是“成人动画”的佳作。这种创作风格何以后来湮没无闻?这与建国后动画艺术的思想性被人为淡化有关。
从受众研究的角度看,早期中国动画“文以载道”,是面向全体受众的启蒙感召;新中国成立后“寓教于乐”,则只服务于少儿。“根据当时有关部门指示要求,美术片主要是以少年儿童为服务对象,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他们,因而动画片多选取童话、寓言和民间故事为题材,主要表达品德教育方面的内容……”[11](P50)作品定位于低幼化后,题材内容、思想深度严重受限。几十年来除《牧童》等少数专为获奖而拍的实验短片外,其他作品只能在政治宣传、道德教益的小圈子内团团打转。当年“中国动画学派”一味讲求形式主义,不为无因。《小蝌蚪找妈妈》“寓”科普内容于精妙绝伦的国画艺术,无疑是一大创举,但色调过于单调暗淡,内容太过单薄……根本不符合儿童的审美特点;水墨动画这一艺术奇葩,居然以“低幼化”内容与“成人化”形式结合的情形问世,可谓明珠暗投。反倒是美国《花木兰》《功夫熊猫》等作品,做出了赏心悦目的水墨动画的艺术效果。中国至今仍无同等佳作产生,固然有资金、技术等外部原因,但“寓教于乐”造成的思想禁锢亦不可小觑。
“寓教于乐”之说,出自贺拉斯的《诗艺》。杨周翰几十年前的译文是:“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12](P141)仿佛贺拉斯主张文艺创作中“教诲”“趣味”缺一不可。其实考诸原文语境,艾晓明的新译文更符合诗人本意——“诗人应该给人教诲或愉悦,或者寓教诲于愉悦之中”。[9](P90)即便以道德说教闻名的西方古典主义名家,也并非时时处处为道德教益聒噪不休。多米尼克·塞克里坦曾以蒲柏为例,强调“不应夸大法国古典主义作家的道德意向”,事实上“蒲柏的机敏胜过技巧”,“他比他同时代人中任何一个都更善于以文字自娱。”[9](P60,P77)
动画领域更应如此。动画原本就是为愉悦大众而诞生的艺术类型,“趣味”乃是促其发展的第一推动力。首位动画大师迪斯尼创立的动画帝国以“趣味”立足世界影坛,绝非偶然。同样,如果不是从小被动画“趣味”吸引,万氏兄弟怎会在民国时倾家荡产地探索动画片奥秘?道德“教益”,至多是搭便车的乘客。抗战救亡的政治使命感,或许促进了《铁扇公主》的拍摄,但没提高其艺术水准,给人印象最深的还是其中的幽默叙事。万籁鸣虽说,“当时国难家仇,我也无闲情逸致搞娱乐性的动画片”,[10](P71)但《铁扇公主》实际上相当幽默,猪八戒变作牛魔王骗得芭蕉扇后,一路得意洋洋唱的那个桥段让人忍俊不禁,“牛大嫂太风骚,众小妖都俊俏,老猪真有点受不了”,诙谐滑稽而颇具性格喜剧色彩。有成人动画的倾向而无低俗情色弊病,此类幽默元素在中国动画史上极其匮乏。只是万氏兄弟当时没意识到“趣味”乃是“教益”存在的前提,后来更是为政治热情而压抑了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有的电影公司向我提出要仿照美国动画片,搞一些荒诞不经、低级趣味的胡闹玩意儿以获得暴利。我和弟弟们表示坚决不干,我们坚持要配合当时的形式和斗争……”[10](P72)创作理念的迂阔死板,直接造成了作品数量稀少,客观上削弱了动画艺术的社会影响力。因此,虽然万氏兄弟1933年就已解决声、光、画合成的技术难题,但始终筹不到资金拍摄动画长片。1941年才因迪斯尼《白雪公主》的巨大成功得到投资,拍成《铁扇公主》,《大闹天宫》的宏大构想则拖到60年代才夙愿得偿。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动画学派”是另一极端,伴随国家资金支持而来的是政治理念的强力控制。《骄傲的将军》《牧童》确是阳春白雪,但《铁扇公主》那种生机勃勃的成人化趣味、轻喜剧倾向却已消失殆尽。随后几十年内,中国动画的情感基调日趋严肃低沉:新中国成立前《铁扇公主》慷慨陈词外,仍以喜剧风格为主;新中国成立初《大闹天宫》庄重严谨,是悲喜交融的正剧风格;“文革”后《哪吒闹海》中,愤懑无言以致与亲人划清界线等情节的悲剧意味十足,十年浩劫间国人的幽愤展露无遗。
这与以闹剧般嬉戏欢娱为卖点的迪斯尼等早期西方动画明显不同。在动画艺术的诸种美学品格中,“趣味”的重要程度尚待商榷,但它无疑是动画艺术产生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之一,将其一笔抹煞至少是片面的。中国动画一开始就肩负着启蒙救亡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后出于政治思虑而险些将艺术性、趣味性抛诸脑后,时过境迁后自然行之不远。理论缺陷导致实践片面,实践落后反过来又导致理论底气不足……要想走出这个恶性循环,中国动画必须从正本清源的理论建设开始,“趣味”回归理应作为找回观众的第一步。
再次,“尊崇古典”的改编方式缺乏时代感与灵活性。古典主义推崇古希腊罗马艺术传统、喜欢模仿古典名著,但不是复古主义。多米尼克·塞克里坦有言:“古典的首先意味着秩序井然和高度控制”,“‘古典的’(classic,它的主要义项是“最优秀的”——译注)……意味着典型的、模范的(确实可靠的事例)”,“‘古典主义’(classicism)是一种写作或绘画的方式,它标志着宁静的美、高雅、严谨、整饬和明晰。”[9](P2,P3)《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则认为:“根据已确定的规则(即根据对古代作品的研究),所有组成部分都达到和谐与协调,最后形成一个不能再作丝毫增减和改动、否则就会遭到损坏的整体……在绘画方面,J·I·大卫则又重新确立了拉斐尔和奥古斯都罗马时期的形式标准,把古典主义变成了为新的劝人为善和歌功颂德题材服务的工具。”⑥
两者相互印证可知,西方古典主义思潮至少包括三重意蕴:1.秩序井然与高度控制;2.通过古代“典范”来劝人向善与歌功颂德;3.主要表现宁静、明晰、严谨之美的创作方式。
“中国动画学派”的三大特点中:“文以载道”与为满足政治意识形态“秩序与控制”的需要相符;“寓教于乐”与宣扬革命价值观导致说教口吻压垮娱乐色彩的叙事风格相符;“尊崇古典”则与中国动画多数作品忠实取材、改编自民族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谚语遥相呼应。
其实“中国动画学派”也有《草原英雄小姐妹》《没头脑和不高兴》等少数现实题材的作品,但后者的质量、数量与影响都不成气候,以致少人提及。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动画学派”几与古典题材动画同义,批评中国动画缺乏时代感的意见不绝于耳。这或许与中国古代绘画素以宁静高雅、含蓄蕴藉的“古典意境”取胜,不善表达动感繁复、色彩绚烂的“现代内容”有关。但从动画史的角度看,《大闹天宫》等万氏兄弟早期作品不乏现实题材商业短片,竭力效仿的“典范”并非诗意静美的古典中国画,而是活泼跳跃的西方迪斯尼——被引为民族动画经典的《铁扇公主》中,迪斯尼式的闹剧噱头与形象设计比比皆是。早期中国动画秉承的是兼容并蓄的拿来主义,而非义和团式的民族主义。建国后“中国动画学派”之所以完全致力于“民族化”创作道路,显然另有原因。只有从政治、文化、艺术等多元交错的社会场域来看,才能体会到“民族主义”对中国动画道路选择的巨大影响:艺术水准难分轩轾的《乌鸦为什么是黑的》《骄傲的将军》,只因分别借鉴外国(俄罗斯)动画与国粹京剧,前者被口诛笔伐至今,后者却被誉为民族动画的旗帜。当时的古今中外之辩,几乎相当于自力更生或崇洋媚外的政治标签。“中国动画学派”除了高度聚焦于民族化、古典性,已别无选择。万籁鸣等大师因此丧失了创作自由度,中国动画则错过了将中国古代绘画传统现代化的历史机遇。简单指摘前辈动画家缺乏现实性、时代感的说法是不公平的,他们根本没有这个机会。
古典主义不等于抱残守缺。艺术家无法选择时代,亦不应随波逐流。中庸的精髓在于尺度把握,“一个作家所采用的形式是其必然成为他之所感与所说的折衷物的某种形式”。[9](P110)不知变通者难成大器,艺术家不是超凡脱俗的隐者高士,理应懂得如何在现实阻碍中保全艺术,戴着意识形态的镣铐跳出最富个性的舞蹈。“蒲柏仍是最重要的奥古斯都古典作家,就因为他不纯粹是古典派”。[9](P77)
在改编中国古典名著方面,日本动画家表现出色。他们对经典的“尊崇”,不是原样照搬式的忠实,而是表现为对其情节框架、人物形象的熟稔热爱与信手拈来。日本动画也有横山光辉《三国志》等高度忠于原著的佳作,但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从中国名著中借用一鳞半爪后恣意放纵想像随意点染的作品。同一部如《西游记》,被不同日本动画家改编后,艺术风格与个性意蕴大相径庭:手冢治虫几十年前的《我是孙悟空》,就让孙悟空玩起了滑板车;鸟山明《七龙珠》只用了孙悟空恣意奔放的猴形超能英雄的艺术形象;《最游记》中师徒四人抽烟玩枪、飙车耍酷,一副现代嬉皮士派头,只保留了一路西行取经降妖除魔的情节框架……《乱马1/2》《圣斗士星矢》等作品的中国元素更少,但都娴熟而恰到好处,完全具备“陌生化”般新意迭出的艺术效果。
同为借鉴古典文化遗产,较之于“中国动画学派”尊崇原作的古典正统,显然热衷于融入个体经验情感的日本动画,更为思维活跃的现代人所青睐。
三、发展模式:“体制艺术”的精彩与坎坷
不过即便弊病明显,昔日“中国动画学派”亦非时下中国动画可比。昔日辉煌的终结与现实处境的困窘,已是目前动画界最重要的理论研究起点。“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80年代初”是中国动画最后一个黄金时代。[13](P30)80年代中期,中国动画急剧滑坡,偶尔还有《山水情》等一两部短片在国际获奖,但整体颓势毕现;90年代后,则不仅在国际动画节上再无建树,国内市场也大幅缩减,几乎沦为美日动画的倾销市场。几十年的艺术积淀,短短数年后便化为乌有。中国动画的溃败何以如此快而彻底?这一直是最令中国动画人愤懑困惑的斯芬克斯之谜。
试图回答困惑、改变尴尬现状的努力不在少数:有人反思“中国动画学派”的失败教训,认为它缺乏现代感难以吸引观众是主要原因;有人借鉴美日动画产业的成功经验,认定完整的产业链才是成功关键……政府似乎也有采纳意见的决心。然而一晃十余年过去,政府出台了若干扶持政策,国内动画行业的确热闹了许多,可真正优秀的原创作品依然不多,中国动画的再度辉煌还是遥遥无期。可见上述建言并未切中肯綮,或者说有意无意回避了制约中国动画发展的根本问题。
中国动画的核心症结,在于它始终是一门“体制艺术”:受社会体制影响过大,既未形成系统深入而切合实际的动画理论,艺术传承较弱;又没形成独立自主的生产模式,难以经受社会动荡的考验。
首先强调动画理论的重要性,是因为动画必须建立与社会体制灵活互动。任何艺术要长久流传,都需具备在社会剧变中自我保全的能力。与文学等传统艺术相比,动画的资金投入、回报周期的要求高得多。因此优秀的动画理论在深入阐释形而上的艺术特性之外,还应包涵形而下但必不可少的现实性,以便后来者懂得利用现实条件创作优秀作品的必要性。动画人必须有意识地锻炼自己以动画立足社会的各项能力。这对动画艺术传承至关重要。
然而,中国动画诞生于战火纷飞的民国时期,第一代中国动画家对动画艺术充满热爱,但当时创作实践举步维艰,深入系统的理论建设无从谈起。中国最早最重要的动画理论文献,应是1936年万氏兄弟的《闲话卡通》一文。[14]文章历数美国动画的娱乐效率、德国动画的艺术品质,以及苏联动画的教育功能,对各国动画艺术特点与创作模式的概括比较颇为精要到位,而且已初步触及“商业”(美国动画)、“艺术”(德国动画)、“教育”(苏联动画)、“政治”(中国动画)等左右动画发展的重要因素。然而,文章随后将中国动画的未来路向确定为革命色彩浓重的“寓教于乐”与“民族风格”,格外强调“政治”因素的重要性。这一理念的社会意义非凡,但将社会责任担当置于对动画艺术规律的探寻之上,既没有官方认可,又难以吸引民间资金支持,险些导致中国动画中道夭折。
万氏兄弟出身贫寒,上述理论不过是个人的社会理想,并非有意为后世中国动画“立法”。不过世事难料,民国的“金钱社会”很快被“政治社会”取代,万氏兄弟这种明显轻视艺术特质与规律的理念,因与“政治宣传”为主的文艺政策相契,居然被改造为新中国动画创作的方针。中国动画理论就此画地为牢,由此产生的“中国动画学派”虽然风格独特,但对动漫艺术规律的探索足足停滞了几十年。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动画失去国家经费支持后,在国外动画的强势冲击下瞬间土崩瓦解,便是因为本国动画理论、创作模式被体制束缚了几十年,早已丧失了基本的应变能力。
其次,中国动画因社会体制剧变屡次中断,缺乏高屋建瓴的长远规划,没找到合适的生产模式。在这方面,中国动画不及美日动画远甚:美国动画是好莱坞电影产业的重要部分,有成熟完善的市场机制与法律保障;日本动画不仅有强大的商业链与政府支持,而且已彻底融入日本文化……国外动画已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不会因战乱等社会变动而中断。而中国动画,至今仍是个迷失在自家深宅大院里,不知昂首看天的孩子。
其实“体制艺术”并非毫无优点,动画艺术的发展对体制要求并不高,只要社会不处于“文革”般反智反文化的极端暴虐状态,动画艺术在任何社会意识形态中都有一定的发展空间。动画犹如刚刚破土的种子,生长的潜力巨大,在不同体制的社会中因遇到的阻碍不同而形成不同的发展模式,最终的生长路线、表现形态自然不尽相同:美国动画是市场经济体制孕育出的庞然大物,日本动画是在美军占领下苦心经营的文化产业神话,“中国动画学派”与南斯拉夫的“萨格勒布学派”同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倔强成长的艺术奇葩……没有新中国的鼎力支持,万氏兄弟酝酿30年之久的《大闹天宫》多半无从问世。前南斯拉夫动画大师波尔多则坦承只要避开与执政党、政府态度背道而驰的想法,“我们……制作电影不会受到公司或者政府的任何限制”。[2](P168)
同为社会主义体制语境中的“体制艺术”,前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学派”更为辉煌,有赖于社会秩序的长期稳定。中国动画的不幸在于所遭遇的体制剧变太过频繁,以致屡次被迫改弦易辙、无所适从:民国时期,动画不过是“走马灯”一类小把戏,政府无暇也不屑政治干预,影响动画发展的是“商业/经济”因素。“动漫是一个投入巨大、回报周期长的资金密集型产业”,[15](P47)动画艺术家们无论政治觉悟、艺术理想如何,在创作中都需要有适当的商业妥协,否则无法生存。即便民国时期唯一的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万氏兄弟也融入了大量商业因素,真正的“抗日”台词不过寥寥几句,而且颇为含蓄。有人看到《铁扇公主》票房回报十分可观,有意投资拍摄《大闹天宫》,后因物价飞涨中途作罢。倘若当时社会稳定,中国动画行业很可能形成美式动画的商业模式。然而随后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变动剧烈频仍,动画拍摄很快由取决于“经济”投资变成取悦于“政治”风向:新中国成立初还算有得有失,在动画理论严重受限的同时,却因政府资金支持得到了创作丰收。“文革”期间,险些沦为标语口号的视频载体;80年代,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以上海美影厂“被抛”为标志,中国动画同时遭遇“政治”“经济”的两面夹击。
“从1957年到20世纪80年代,……上美厂每年得到一定的维持生产的资金,保证完成每年300分钟~400分钟的产量计划……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改变,……随着政府对上美厂控制和支持的减少,上美厂除制作教育性、艺术性动画片外,必须分出力量来生产商业动画以维持自身生存”,“1993年……政府……保证了厂里职工的基本工资和大约总支出的70%……1998年的报告显示……只有30%的收入来自国家财政。”[13](P22,P23)
作为中国动画艺术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上海美影厂被抛入市场自生自灭,是否应该?如果被视作一般企业,为何1995年国家主席致信上海美影厂时强调:“要不断推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动画艺术精品”?[13](P23)为何上海美影厂还会煞费苦心地拍摄那些成本极高而无利可图的“教育性、艺术性动画片”?[13](P23)片面指责上海美影厂没能及时转型、缺乏商业意识,是不公平的:20世纪80年代末,上海美影厂就开始了电视动画等商业尝试。只是当时恰逢国门重新开放,外国动漫为抢占中国市场而低价大肆倾销的当口。日本甚至由政府出资购买动画,在东亚诸国免费播放……以企业化待遇履行公益性、事业化使命义务与责任承担,上海美影厂与中国动画内外交困而日趋没落实属必然。“今天,上美厂似乎仍是中国唯一一家能够生产出有资格参加国际动画节作品的动画公司,但是,由于国家财政支持逐年降低……在过去的三年中,上海美影厂仅创作了这样水平的动画片三部,而1988年一年就创作了十部。”[13](P25)虽然90年代后各级政府出台了许多扶持政策,但缺乏全盘规划、过于急功近利,注定了那些投机性质的动漫频道、动漫基地、动漫公司,只能韭菜般一茬茬被收割了事。
这不是主张中国动画重走以前老路。池塘里养不出大鱼,中国动画要发展壮大,迟早要放归大海。但在此之前,是否该像野生动物放生一样,先在适当保护下锻炼一番生存技能?上海美影厂在短短数年缓冲后,就被迫单独面对美、日等国在国际市场称霸数十年的动画大鳄,不被吃得尸骨无存才怪。“上海美影厂许多有才华的动画人为了高收入放弃原来的工作,进入外国设立在中国沿海城市的动画公司。”[13](P22)80年代时有过“下海”经历的动画导演邹勤感慨说:“我为《鹿与牛》工作了一整年,仅比平时多收入800元人民币,而我为太平洋动画工作,仅做一些不动脑筋的简单活,一个月5000元。”[13](P25)薪金如此悬殊,甘愿为艺术牺牲个人利益的理想主义者能有多少?中国动画的专业人才,多数在外资动画公司从事最基础的描线、上色等体力活,无从接触核心技术环节,很难提高自身水准,指望他们取经回头支撑中国原创动画是不太现实的。
当然,上海美影厂“被抛”不等于中国动画完全成为“体制弃儿”。同一时期“央视动画部”,吸收了大笔政府资金后招纳了不少原上海美影厂的优秀人才,开始逆势崛起。上海美影厂的导演并不缺商业头脑,80年代中后期的《黑猫警长》《葫芦兄弟》等电视动画社会反响颇佳,成本控制、周边推广、产业链运作等方面也颇为成功,只是条件困难无以为继。相形之下,坐拥种种便利的“央视动画部”则顺风顺水,实际接过了中国动画事业的接力棒。“央视的第一部电视动画片就是美影厂老导演和我们这些新人一起制作的。”[1]1996年,著名动画导演、原上海美影厂副厂长方润南调入中央电视台主持大型电视动画《西游记》的拍摄。“这部历时六年完成的动画片,从文学剧本定稿、美术设计定型、样片制作到中后期制作,由中国十五家动画公司参与,制作人员近两千人……耗纸30吨,斥资3000万元”,堪称“首部由中国制作的全数字化动画片,在中国动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16](P241)如此强大的制作阵容与资金投入,远非上海美影厂“一集创作费用七万元”的《葫芦兄弟》可比,[16](P222)但论社会反响与艺术水准,显然还是后者令人印象深刻。
中国动画如此盛事,为何不交给公认的行业龙头与艺术中坚——上海美影厂,却费尽周折将上海美影厂的导演调到央视来做?曾在央视动画部当过十年动画编导的段佳,也曾发问:为何“大量的动画资金又投进央视动画部,却把‘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这个世界知名的品牌,交给了至今尚未成熟的市场,任其自生自灭”?[1]“央视动画部”到底是选编播放的媒体平台,还是从制作到播放一条龙服务的特殊机构?……这些具体问题背后隐藏着更大的疑问:在社会体制改革这盘大棋中,有无对中国动画的全盘考虑?有的话,是否专家负责,制定依据何在,执行力度如何?
作为严格意义上的“体制艺术”,中国动画连自身在社会体制中的位置、分量都难以确定,如何准确制定长远、有效的发展规划?政府主导的产业模式往往不合动画自身规律,有时甚至适得其反:比如各地方政府的动漫产业扶持政策,一是只知锦上添花,对在电视台播放的本地动画进行现金奖励,不知雪中送炭,在拍摄前提供资金支持;二是奖励普遍以播放平台的行政等级为标准——在国家、省、市等不同级别的电视台播放,奖励金额相去甚远。因为前期投入巨大、资金回报周期较长,为防资金链断裂,动画公司很多时候不得不廉价出售成本高昂的作品。据上海美影厂资深导演曲建方介绍,“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影集团收购他们动画片的价格是一分钟一万元人民币……进入21世纪后的市场经济时期,电视台收购动画片的价格竟然降到了每分钟三块钱!”[2](P170)这不仅造成了动画公司在市场上的弱势地位,而且助长了投机分子以劣质动画搞公关套取政府奖励的不良风气。这让以“烧钱”著称的动画行业如何生存?即便不计代价得失最终登上央视,也不等于万事大吉——因为还有严格的节目审查机制。2007年“收视率首次超过境外动漫,被誉为卡通版《七剑下天山》”的《虹猫蓝兔七侠传》,[17]曾因武侠作品难以避免的些许粗口暴力,一度被央视少儿频道以“正常节目调整”的名义停播,后因民众、媒体强烈批评才得以重播。
“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⑦近百年来,中国动画连起码的艺术理论与发展模式都未形成,罪魁祸首便是社会体制频繁剧变造成的蹭蹬坎坷。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当下中国动画最需要的,不是出台多少扶持政策,而是从“体制”的桎梏中挣脱出来。
中国动画欲求真正长足的进步,必须虚实相生、远近结合:作为社会产业,要有切实可行务实而科学独立的长远发展规划;作为现代艺术,应在保证现实收益的同时,追求对人类世界与社会历史的超越情怀与哲理思考。
收稿日期:2013-10-20
注释:
①“动画电影:文化、美学与产业”研讨会:2012年6月28日,由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详见郑欢欢:《为国产动画电影转型升级提供启示——“动画电影:文化、美学与产业”研讨会综述》,载《当代电影》2012年第8期。
②即便在“中国动画学派”彻底没落之后,上海美影厂仍有坚守这条创作道路的动画家,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邹勤的《鹿与牛》是用竹子做的形象”,见约翰·A·兰特主编:《亚太动画》,张慧临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③“从1957年到20世纪80年代……上美厂每年得到一定的维持生产的资金,保证完成每年300分钟~400分钟的产量计划,产品由中国电影公司以一定的价格收购。”见约翰·A·兰特主编:《亚太动画》,张慧临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页。
④勒内·布雷语。见多米尼克·塞克里坦:《古典主义》,艾晓明译,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⑤引自1989年“上海美影厂”特伟等人应日本动画协会之邀,到日本举办“中国美术电影展览”,与大冢康生、宫崎骏、高田勋、古川肇郁等人的谈话。参见张松林,贡建英:《谁创造了〈小蝌蚪找妈妈〉:特伟和中国动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5页。
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词条“Classicism and Neoclassicism”的扼要介绍。详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著:《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4)》,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不列颠百科全书编辑部编译,中国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⑦《孟子·告子上》。
标签:艺术论文; 动画的发展论文; 动画论文; 形式主义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花木兰论文; 美术论文; 牧童论文; 新古典主义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