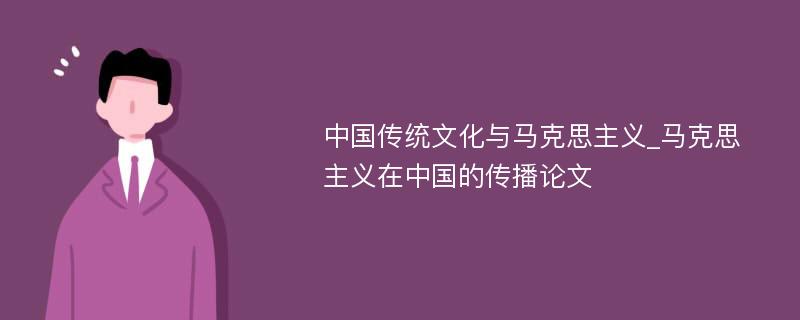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末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引起中国新知识界的关注,并获得迅速、广泛的传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马克思主义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中国历史也揭开了新的一页。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的欧洲,之后即在西方迅速传播,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即便是相对落后、地处东方的俄国,也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近代中国知识界大肆崇尚西学,竞相学习、模仿西方的时代潮流中,人们不可能不对在西方兴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有所耳闻,但为什么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中国的知识界才开始引进、传播马克思主义?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探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考察。正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背景,造就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殊文化环境。同时,这一文化传统也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发展历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首推经学。经学是传统意识形态的载体,其功能即在于为现实政治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经学的地位因当政者的需要“法定”而成。经典作为权威性文献,涉及的是上古的政事经验,它必须在被提取为抽象的原则、赋予新的义理的条件下,才能应用于新的政治实践,体现出为现实政治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功能。这样,经学就作为意识形态的资源而存在,所有活动都需要从中取得依据和支持。因此,经学不在于理解而在于解释;不在于复其原貌而在于创新。否定了创新的解释,也就否定了经学的经世功能。当政者为了自身的政治需要,在给予经学“法定”地位的同时,也不得不赋予其神圣的形象,从而使其具备了普遍的约束力。每当当政者需要从经学中获得依据和支持时,就不得不在解经方面下工夫。所以,解经就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文化活动,而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某种政治行为,经学的发展也就成为意识形态嬗变的标志。这样,学术活动便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经学文化也就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而存在。虽然从根本上说,所有社会意识形态都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但是经学的政治功能更直接、更突出。
明清以降,传统政治秩序似大厦将倾,为其提供合法性依据的经学也遭到危机,经学作为意识形态资源的潜力已近枯竭。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传统经学也发生了某种转变,从宋明时期以心性伦理的思辨为主的理学形态,转向以文献的考订、字义的训释为重要内容的考据形态,学风由虚入实。乾嘉时期,经学一度复兴,“不仅有朝廷提倡的讲义理的宋学,也有学者特别用功的汉学。汉学中不但古文派兴盛,今文派崛起也有力。但正是这走马灯般的形态更替,表明经学作为意识形态资源的潜力已近枯竭,因为经学史上出现过的几种形态都重复一遍了”(注:陈少明等:《被解释的传统》,中山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33页。)。然而, 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放弃从经学中为现存社会秩序找到合法性依据的企望。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与对峙中屡遭败绩,迫使国人放弃盲目自大的心理,重新审视西方文化,援西入中成为潮流。但是,西学的兴盛并不是独立于传统经学文化,而是被经学当作了意识形态资源的补充。科学的治学方法融于经学研究,科学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自身的价值。中国的知识界期望从融入了科学的治学方法的经学中寻求现存社会秩序的合法性依据,凡不符合这一需要的东西自然不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之列。另一方面,当时研究西学仅限于科学技术方面,后来虽达到政治制度的层面,但都未及精神文化的层次。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没有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注意实为必然。然而实践上,“洋务运动”并没有最终成功,戊戌维新也很快失败,合法性的援引依然挽救不了虚弱性的痼疾。相反,从魏源的“师夷长技”到康有为的旧经新解,反倒是加速了经学的终结,导致经学最后失去合法性,失却其意识形态的地位;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帝制,从政治上终结了经学的合法性;五四新文化运动使经学在文化领域遭到彻底的打击,经学的经世功能最终瓦解。经学的终结,使从其中寻求合法性依据变得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传播的重要前提。
在近代中国同西方的交流中,国人首先看到的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接着是模仿这些物质现象背后的政治体制,到了“五四”时期,才进入到精神文化层面的内容。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传播的重要条件。“五四”时期,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广为流行,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口号深入人心,传统经学彻底瓦解。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崇尚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的潮流,从西方寻找符合这一潮流的价值观念,为摆脱社会危机寻求出路,便是中国新知识界的必然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由于其理论的和逻辑的力量引起中国新知识阶层的关注。特别是唯物史观在解释社会历史时的巨大科学价值,与新文化运动中科学主义、怀疑主义风行,以理性向权威挑战相适应,这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的魅力不仅在于对传统的科学和理性的批判精神,而且在于指明了社会运动的方向;不仅是对传统心性伦理的反叛,更在于使新道德获得了历史理性基础。十月革命的胜利,进一步从实践上增强了马克思主义的说服力和吸引力。布尔什维主义能在封建势力十分强大的俄国取得胜利,这对一直深受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双重压力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种希望和寄托。“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注:《李大钊文集》(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3页。)。 这句话十分典型地表达了中国新知识界对俄国革命的热情和厚望,同时也表明了他们热情洋溢地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二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在“五四”前后的迅速传播与传统文化的衰落所造就的独特的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但是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并不是就此消失,相反却一直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传播与发展的全过程,而最终在中国取得领导地位的也正是这种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的影响像一把双刃剑,既造就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又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带来负面的影响。
传统经学的终结,标志着经学作为意识形态资源为现实活动提供合法性依据的功能的瓦解。但是,从既定意识形态中为解释现实寻求合法性依据的思维方式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这一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时人们对它的理论思想的取舍。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李大钊还是陈独秀,他们所看重的不是一门实证科学——当然马克思主义首先是一门科学,而是一种指导实践的方法,是一种可以作为信仰和生活动力的社会意识形态。这一现象也体现在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上。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两三年,中国共产党便宣告成立,这使得马克思主义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这种情况的长处是,在现实的政治力量的扶持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较为迅速,与中国革命实践的联系也更加紧密,从而有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其短处在于缺乏充分的理论准备,实践过程中容易出现偏差和失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这种情况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使它成为经学失去意识形态功能后的替代品。经学的经世功能瓦解后,从既定的意识形态解释说明社会、寻找合法性支持的思维方式必然急于寻找某种具“法定”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其速度之快甚至远远超过西方,这种现象与上述文化心理不无关系。而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地位一旦确立,传统思维方式的负面影响也就凸现出来: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不是从具体的实践出发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来套用于现实,解释现实,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演化为一种新的“解经术”。于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就只剩下阐释和论证现行政策的合理性,为之在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寻找理论依据,这成为在实践中导致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的根源。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左”倾错误,很大程度上就源于这种传统文化思维方式的根深蒂固的影响。
诚然,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离不开对它的科学理解与解释。但是,仅仅解释以便从中寻找合法性依据是远远不够的,即使做到了结合具体实际给予创新性的解释也不够,必须在实践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基础上突破原有的某些观点、结论甚至是非根本性的原则。例如,“一国两制”理论就是对原先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国家原则的突破。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在于对其根本立场、原则、方法的继承和发展,在于继往开来,而不能停留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现实。作者无意鄙薄解释的作用,但是在改革的进程中,解释的运思方式往往成为改革的阻力。因为实践是具体的,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也是多种多样的,“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页。)。硬是事事都要从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找到依据,最终必然导致对现实实践的否定而阻碍改革的进程。所以,“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91页。)。
近代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变革和社会文化的发展走向问题。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经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社会理论纷纷登场,但这一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中国社会历史迫切需要得到解释、说明,而实践中却又一次次失败,中国太需要实践上成功的证明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这种迫切需要,使得中国的新知识分子对于刚刚成功地指导了苏联十月革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抱有强烈的热情。“哲学家从来都只是用不同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实践性完全适应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一开始就与中国的社会实践结合得非常紧密,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强烈的需要,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与发展带上了浓厚的实用色彩。一旦中国社会的现实得到科学的理论解释和说明,在实践上就企望尽快获得如俄国那样的成功,这种心态无疑是“左”的思想滋生的温床。强烈的实用心态容易导致急躁情绪,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这种现象一直存在着。表现为在实践中急于求成,对于好的实践方式喜欢一哄而上;当实践进程出现曲折时,与“本本主义”解释的运思方式相联系,又容易转向另一面,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似乎马克思主义不再适合中国社会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无疑应具备现实的应用性,但是要注意避免实用心态的负面影响,避免流于庸俗的实用主义。
三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便必然地遇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从建设性的观点看,这种关系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首先即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程,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便是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其次,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还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比如传统精神价值。缺少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便受到限制,甚至步入歧途而陷于困境。马克思主义只有获得特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在该民族文化的氛围中生根开花,传播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一个基本方向,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性的基础上融入传统文化的价值理性。作为深层次的民族心理价值观念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血缘关系、文化气质、宗教信仰、政治经济发展等交互因素在本民族心理上的积淀和反映。它一旦形成就会给本民族以巨大影响,形成一整套观念和习俗,是民族认同和发展的一个内在依据。民族心理价值观念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源,它存在于民族的兴旺之中,更表现在民族的危难之时,而且往往是危难之时更能激起强烈的民族价值认同,进而民族的凝聚力也更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首先要取得民族心理价值观念的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能否顺利深化,一定程度上要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和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的影响。“社会群体鉴别一个政治制度是否合法的依据,是看它的价值取向如何和它们相吻合”(注: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32页。)。不可否认, 民族文化的价值取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前提下,其主要途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对传统文化进行发掘、研究,弃糟粕、存精华,赋予传统文化以时代特色,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成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传统文化有其巨大的稳定性和历史惯性。它曾造就了领先于世界的东方文明,也包含有僵化、保守的因素。无论在“五四”时期,还是在80—90年代市场经济的建构过程中,中国民众经历的文化心态的困惑和中外文化观念的冲突,实际上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传统文化模式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无法成为现代人活动的依据和意义的源泉。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历史理性的基础上,革故鼎新,彻底清除传统文化中僵化、保守乃至反动的东西,传统文化才能被置于崭新的基础上,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根本的相通性和互融性,这是双方统一的基础。但是作为两种异质文化,我们绝不能忽视其对立的一面。所以,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实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转化与更新;同时,又要以这种经过辩证转换的新文化去阐释马克思主义,使其符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并具备为中国人所熟悉的民族形式。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能简单地依据传统文化和传统思维方式去牵强附会地理解、解释马克思主义。
标签: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经学论文; 政治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