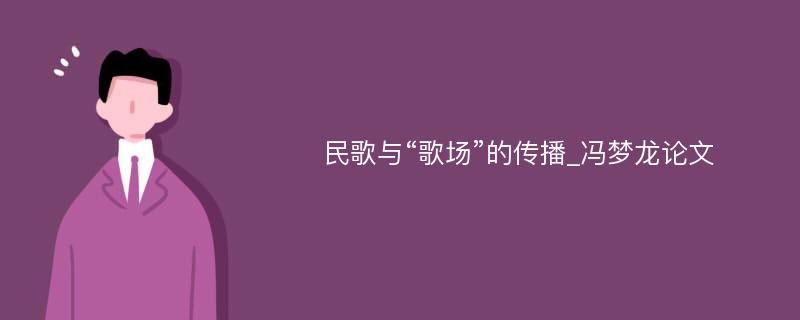
民歌与“歌场”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间歌谣是活在大众口头上的文学,它在文学史上的效应,不仅是口头的诗歌创作,还有口头的文学传播,本文着重分析其特殊的传播形态——“歌场”传播。 原生野味、永葆鲜活的文学传播形态——“歌场”面貌部分还原 “新歌旧曲遍州乡,未闻典籍入歌场。”①这是唐代敦煌歌辞《皇帝感》中所唱的“歌场”。宋代范成大在《南塘寒食书事》诗中写“歌场”:“酒侣晨相命,歌场夜不空。土风并节物,不与故乡同。”②清代杨伦《杜诗镜铨》注解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诗时引《风土记》云:“荆湖民俗祷祠多击鼓,令男女踏歌,谓之歌场。”③此处所说的“歌场”,指民歌传唱的场所。因为当时不可能留下录像的现场,如今再现当时“歌场”的情景颇有难度,但我们还是可以借助于有关记载而加以部分地还原,如《陶庵梦忆》和《扬州画舫录》分别记载: 虎丘八月半,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鼎沸,呼叫不闻。更定,鼓铙渐歇,丝管繁兴,杂以歌唱,皆“锦帆开澄湖万顷”同场大曲,蹲踏和锣丝竹肉声,不辨拍煞。更深,人渐散去,士夫眷属皆下船水嬉,席席征歌,人人献技,南北杂之,管弦迭奏,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二鼓人静,悉屏管弦,洞箫一缕,哀涩清绵,与肉相引,尚存三四,迭更为之。三鼓,月孤气肃,人皆寂阒,不杂蚊虻,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串度抑扬,一字一刻,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然此时雁比而坐者,犹存百十人焉。④ 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钮丝》、《四大景》、《倒扳浆》、《剪靛花》、《吉祥草》、《倒花蓝》诸调,以《劈破玉》为最佳。有于苏州虎丘唱是调者,苏人奇之,听者数百人。明日来听者益多。唱者改唱大曲,群一噱而散。又有黎殿臣者,善为新声,至今效之,谓之《黎调》,亦名《跌落金钱》。二十年前尚哀泣之声,谓之《到春来》,又谓之《木兰花》。后以下河土腔唱《剪靛花》,谓之《网调》。近来群尚《满江红》、《湘江浪》,皆本调也。其《京舵子》、《起字调》、《码头调》、《南京调》之类,传自四方,间亦效之,而鲁斤燕削,迁地不能为良矣。于小曲中加引子、尾声,如《王大娘》、《乡里亲家母》诸曲;又有以传奇中《牡丹亭》、《占花魁》之类谱为小曲者,皆土音之善者也。⑤ 以上《陶庵梦忆》中是写苏州虎丘中秋节“席席征歌”、“杂以歌唱”,再与下面所引的《扬州画舫录》中所说“有于苏州虎邱唱是调(指《劈破玉》)者”等相互印证,可见这两段均是与传唱《劈破玉》等民歌的“歌场”有关。从以上的描述中,可见歌谣传唱环境的原生态:“自生公台、千人石、鹤涧、剑池、申文定祠,下至试剑石、一二山门,皆铺毡席地坐,登高望之,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其实,早在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⑥“歌场”遍布于乡间田野、市井里巷,在乡间田野传唱的往往称之为“秧歌”、“山歌”:“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⑦还有青年男女晚间在山野对歌:“瑶峒月夜,男女隔岭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犹存歌仙之遗风,一字千回百折,哀厉而长,俗称‘山歌’。”⑧还有渔歌与山歌此起彼伏:“渔唱田歌,夹重湖之表里。”⑨也有将山歌、秧歌传唱一道描述的:“此田畯红女作劳之歌,长年樵青,山泽相和,入城市间,愧汗塞吻矣。”⑩至于“入城市间”的歌谣传唱,李开先在《时调》中录下了一个生动的细节:“有学诗文于李崆峒(李梦阳)者,自旁郡而之汴省。崆峒教以:‘若似得传唱《锁南枝》,则诗文无以加矣。’请问其详。崆峒告以:‘不能悉记也,只在街市上间行,必有唱之者。’越数日,果闻之,喜跃如获重宝。”(11)值得注意的是,遍布于乡间田野、市井里巷的“歌场”中往往有赛歌会的兴起与歌乡的形成,例如江南苏州一带的“接韦陀”、“抬猛将”赛歌会,常州的“唱春”与“盘春锣”等,常熟的白茆歌乡,吴县的芦墟歌乡,张家港的河阳歌乡等闻名四方。还有遍布于乡间田野、雪山草原等的许多少数民族的歌节,如瑶族的“歌堂”、苗族的“坡会”、壮族的“歌圩”、侗族的“赶歌场”、布依族的“歌白节”、白族的“三月街”、傣族的“泼水节”、哈萨族的“阿肯弹唱会”、维吾尔族的“麦西来甫”、藏族的“雪顿节”、西北的“花儿会”等。有一首《一路上“花儿”唱不断》如此唱道:“河州城人叫它小江南,青枝(吧)绿叶的牡丹;大夏河弯弯地绕城边,‘花儿’声响遍了两川。”(12)对于这些遍布于乡间田野、市井里巷的民歌传唱,明代中期的李梦阳借用王叔武的话评说:“夫诗者,天地自然之音也。今途咢巷讴,劳呻而康吟,一唱而群和者,其真也,斯谓之风也。”(13)所谓“途咢巷讴”即遍布于乡间田野、市井里巷的民歌传唱是“天地自然之音”,最接近自然,最富有野性,也最接地气。 从《虎丘中秋节》《扬州画舫录》的描述中,可见歌谣传唱主角最能接地气,最为大众化:“土著流寓、士夫眷属、女乐声伎、曲中名妓戏婆、民间少妇好女、崽子娈童及游冶恶少、清客帮闲、傒僮走空之辈,无不鳞集。”商贾有时也参与民歌的传唱活动:“芦人楚语时相问,估客巴歌也自传。”(14)可见,农夫商贾、童稚妇孺、市井细民、俳优歌伎、道士禅僧等都参与了歌谣的创作或传播活动。这与以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及书会才人、女乐歌伎等为主体的诗词曲等传唱不同,民歌的传唱以“无闻无识”(15)的农夫山民、童稚妇孺、市井细民为主体,因而,明代中期何景明在评论传唱《锁南枝》等民歌时调时说:“时调中状元也!如十五《国风》,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觚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者,以其真也。”(16)晚清黄遵宪也指出:“十五《国风》妙绝古今,正以妇人女子矢口而成,使学士大夫操笔为之,反不能尔。以为人籁易为,天籁难学也。”(17)将“妇女女子矢口而成”与“学士大夫操笔为之”相比较,强调其“天籁”与“人籁”之别,强调农夫山民、童稚妇孺、市井细民传唱民歌之“真”,这是因为民间歌谣活跃在农夫山民、童稚妇孺、市井细民的口头之上,活跃在最广大的底层民众之中;“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18),有无比强大、无比鲜活的“人气”。正是这无比强大、无比鲜活的“人气”,将“下里巴人”的民歌时调推上“尊体”的地位,称为“我明一绝”(19),与唐诗、宋词、元曲等均为时代“一绝”。 从《虎丘中秋节》《扬州画舫录》的描述中,可见歌谣传唱的氛围很有“气场”,颇具轰动效应:“小唱以琵琶、弦子、月琴、檀板合动而歌。最先有《银钮丝》《四大景》《倒扳浆》《剪靛花》《吉祥草》《倒花蓝》诸调,以《劈破玉》为最佳。有于苏州虎丘唱是调者,苏人奇之,听者数百人。明日来听者益多”;“天暝月上,鼓吹百十处,大吹大擂,十番铙钹,渔阳掺挝,动地翻天,雷轰沸,呼叫不闻。”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运石民工的歌谣唱道:“运石井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20)这首民谣又作:“运石渭南岭,渭水为不流。千人一唱,万人一歌。”(21)唐代往往有千家万户传唱歌谣的景象:“二月仲春色光辉,万户歌谣总展眉”(22);“万户歌谣满路,千门谷麦盈仓。”(23)明代后期袁宏道《迎春歌和江进》写歌谣传唱时的“气场”:“铙吹拍拍走烟尘,炫服靓粧千万人。……采莲舟上玉作幢,歌童毛女白双双。……观者如山锦相属,杂沓谁分丝与肉。”(24)现当代也往往是“撑船唱歌歌满河,砍柴唱歌歌满坡。男女老少都会唱,村村屋屋都是歌”(25)。民间歌谣的传唱不仅有一时的轰动效应,而且有历久弥新的活力和吸引力。对于这种活力和吸引力,晚明宋懋澄在《听吴歌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吴歌自古绝唱,其歌至今未亡。余少时颇闻其概,会历年奔走四方,乙未孟夏,返道姑胥,苍头七八辈皆善吴歌,因以酒诱之,迭唱五六百首。其叙事陈情,寓言布景,摘天地之短长,测风月之浅深,状鸟奋而议鱼潜,惜草明而商花吐。梦寐不能拟幻,鬼神无所伸灵。令帝王失尊于谈笑,古今立息于须臾。皆文人骚士所啮指断须不得者,乃女红田畯以无心得之于口吻之间。岂非天地之元声,匹夫匹妇所能者乎?”(26)《听吴歌记》中说的“乙未”是指万历二十三年(1595),宋懋澄(1570-1622)从“少时颇闻其概”到“会历年奔走四方”的青壮年,在听吴歌“迭唱五六百首”时,仍被深深地吸引。应该说,民歌传唱最具鲜活性和吸引力的是男女传唱情歌,因为爱情是民歌中永恒的主题,所谓“瑶峒月夜,男女隔岭唱和,兴往情来,余音袅娜”(27)。又有广西南部民间情歌唱道:“兄在岭顶唱支歌,妹在深房织绫罗;妹在深房听到了,手脚停下没丢梭”;“恋情言语在歌音,不比读书道理深;知妹本是聪明女,听闻就识你兄心。”(28)对此传唱情歌的吸引力,清代中期的赵翼在《土歌》中写道: 春三二月墟场好,蛮女红妆趁墟嬲。长裙阔袖结束新,不赌弓鞋三寸小。谁家年少来唱歌,不必与侬是中表。但看郎面似桃花,郎唱侬酬歌不了。一声声带柔情流,轻如游丝向空袅。有时被风忽吹断,曳过前山又嫋嫋。可怜歌阕脸波横,与郎相约月华皎。曲调多言红豆思,风光罕赋青梅摽。世间真有无碍禅,似入华胥梦缥缈。始知礼法本后起,怀葛之民固未晓。君不见双双粉蝶作对飞,也无媒妁订萝茑。(29) 显然,与诗词曲唱和的场所歌舞楼台、都门帐外、花间酒边不同,与杂剧、南戏演唱的勾栏瓦肆也不同,民间歌谣的传唱遍布于乡间田野,天地最为广阔,最接近自然,最富有野性,也最接地气;与以文人雅士、达官贵人及书会才人、女乐歌伎等为主体的诗词、散曲等传唱不同,民间歌谣的传唱以“无闻无识”的农夫山民、童稚妇孺、市井细民为主体,歌谣传唱主角最具人气,最为大众化;与诗词曲即兴唱和、杂剧和南戏舞台演出不同,民间歌谣传唱的氛围很有“气场”,颇有轰动效应以及历久弥新的活力和吸引力。总之,民间歌谣的传唱是原生野味、永葆鲜活的文学传播形态。 推动“歌场”流转、民歌传播的典型 在“歌场”流转、民歌传播之中,不断出现一些典型人物。其中,大多是民间的无名士,如粤地民歌传唱中的“歌伯”: 粤俗好歌。凡有吉庆,必唱歌为欢乐,以不露题中一字,语多双关,而中有挂折者为善。挂折者,挂一人名于中,字相连而意不相连者也。其歌也,辞不必全雅,平仄不必全叶,以俚言土音衬贴之,唱一句或延半刻,曼节长声,自回自复,不肯一往而尽。辞必极取艳,情必极其至,使人喜悦悲酸而不能已已,此其为善之大端也。故尝有歌试,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赏,号为歌伯。(30) 粤俗的“歌试”,既是热热闹闹的“歌场”,又是民歌中一场“科举考试”——“以第高下,高者受上赏,号为歌伯”。“歌伯”,为大家推崇的民歌传唱的表率,堪称民歌“状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歌伯”与其说是民间“歌试”中考出来的,还不如说是从民歌群体传唱的“歌场”中脱颖而出的。 粤地民歌传唱中还有十分活跃的女子群体——“天姬队”: 东西两粤皆尚歌,而西粤土司中尤盛。邝露云:峒女于春秋时,布花果笙箫于山中,以五丝作同心结,及百纽鸳鸯囊带之,以其少好者,结为天姬队。天姬者,峒官之女也。余则三五采芳于山椒水湄,歌唱为乐,男子相与蹋歌赴之,相得则唱酬终日,解衣结襟带相遗以去。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赵龙文云:傜俗最尚歌,男女杂遝,一唱百和。(31) “男女杂遝,一唱百和”,可见“歌场”颇有气势。而且这种颇有气势的“歌场”在特定的时节常常出现朵朵欢乐的浪花:“春歌正月初一、三月初三,秋歌八月十五。其三月之歌曰浪花歌。”在这随时随地流动的“歌场”中,活跃着一支“天姬队”,这是来自民间又活跃于民间的民歌传播的典型群体。 民歌传唱中的典型人物,既有群体,也有个体,个体中最有名的是民间女歌手刘三妹: 新兴女子有刘三妹者,相传为始造歌之人。生唐中宗年间,年十二,淹通经史,善为歌。千里内闻歌名而来者,或一日,或二三日,卒不能酬和而去。三妹解音律,游戏得道。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唱和,某种人奉之为式。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徭、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七日夜歌声不绝,俱化为石。土人因祀之于阳春锦石岩。岩高三十丈,林木丛蔚,老樟千章蔽其半,岩口有石磴,苔花绣蚀,若鸟迹书。一石状如曲几,可容卧一人,黑润有光,三妹之遗迹也。月夕,辄闻笙鹤之音。岁丰熟,则仿佛有人登岩顶而歌。三妹,今称“歌仙”。(32) 刘三妹之所以被称为“歌仙”,一是她为相传中民歌的始祖——“相传为始造歌之人”;二是歌声超群,“淹通经史,善为歌”,“解音律,游戏得道”;三是很有听众缘与亲和力,唱和者众,传播面广,“尝往来两粤溪峒间,诸蛮种类最繁,所过之处,咸解其言语。遇某种人,即依某种声音作歌与之唱和,某种人奉之为式。尝与白鹤乡一少年登山而歌,粤民及徭、僮诸种人围而观之,男女数十百层,咸以为仙”。不分民族,不限语种,处处唱和,人人推崇,常常有“男女数十百层”的气场。显然,刘三妹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民间“歌仙”,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似乎可与文人“诗仙”李白相媲美。20世纪60年代根据广西僮族民间传说改编拍摄的电影《刘三姐》,其中就有“刘三妹”的影子,深受亿万观众的欢迎,是民歌在当代成功传播的一个典范。 应该说,推动“歌场”流转、民歌传播的典型中,不仅有民间无名士,还有著名的文人,比如唐代的刘禹锡,他早在贬官郎州时期,就发现“甿谣俚音,可俪《风》什”(33)。特别是在夔州刺史任上,他对当地的民歌《竹枝词》向文人诗坛的流转做了较大的努力,如他在《竹枝词》引中指出: 四方之歌,异音而同乐。岁正月,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雎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伫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到于今,荆楚鼓舞之。故余亦作《竹枝词》九篇,俾善歌者扬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歈,知变风之自焉。(34) 在“里中儿联歌《竹枝》”等群体性歌唱的“歌场”之中,又以“以曲多为贤”一句点出了“歌场”中无名士的典型人物;文中既有善学民歌的先贤——屈原,也有刘禹锡借鉴民歌创作《竹枝词》的目的——“俾善歌者扬之”。“扬之”,传播也。这是民间“歌场”向文人诗坛“流转”的一个缩影。正是在建平(今四川巫山)特定“歌场”的氛围中,刘禹锡师法先秦时代的受民间歌谣影响而创作《九歌》的屈原,借鉴民歌创作《竹枝词》九首,其中有的歌唱风土人情和劳动生活,有的借民歌鞭挞官场与世俗的阴暗面,也有的歌唱男女爱情的欢乐与悲哀:“山桃红花满上头,蜀江春水拍山流。花红易衰似郎意,水流无限似侬愁。”(35)又如《竹枝词二首》其一云:“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36)既保持了纯朴的民歌风味,又将民歌的雅化与文人诗的通俗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堪称文人传播民歌的典范。 在明代乃至中国历代传播民歌的文人群体中,冯梦龙是成就和影响最大的一个,他是推动“歌场”流转、民歌传播的一个典型人物。冯梦龙生活在吴歌流行的江南地区。《乐府诗集》卷四四中《吴声歌曲》题解引《晋书·乐志》:“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稍有增广”,“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弦。”(37)并指出:“盖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吴声歌曲起于此也。”(38)到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百姓无犬吠之惊,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渌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39)。正是江南民间群体文化的繁盛带动了江南“歌场”的兴盛,到明代达到高潮,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时尚小调》中说,当时两淮与江南对于《打枣杆》《挂枝儿》等小调,“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40)。冯梦龙所编的《挂枝儿》《山歌》,主要收录明初至万历年间的吴歌。《挂枝儿》十卷,分题为《私部》《欢部》《想部》《别部》《隙部》《怨部》《感部》《咏部》《部》《杂部》,收入民歌(其中有部分是文人创作的拟民歌)计419首,加上评注中说明是经过改订的16首原作,共计435首。《山歌》共计十卷,卷一至卷九为《山歌》,卷十为《桐城时兴歌》。卷一至卷十实录民歌380首,加上评注中说明有异文的3首,应为383首。冯梦龙之所以极力鼓吹、整理、刊刻、传播民歌,是因为他对民歌有独特的认识,他在《叙山歌》中指出: 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41) 在此,冯梦龙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编辑《挂枝儿》《山歌》等民歌专集的用意——“藉以存真”、“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他将“不屑”与诗文“争名”的民歌,看作是“男女真情”的流露,如冯梦龙编撰的《挂枝儿》中有一首《调情》:“俊亲亲奴爱你风情俏,动我心遂我意才与你相交,谁知你胆大就是活强盗。不管好和歹,进门就搂抱着。撞见个人来也,亲亲,教我怎么好。”对此,冯梦龙评论说:“亦真。以上二篇,毫无奇思,然婉如口语,却是天地间自然之文,何必胭脂涂牡丹也。”(42)他就是要“借男女之真情”,作为“发名教之伪药”。在这个思想指导下,冯梦龙给后世留下了《挂枝儿》《山歌》《夹竹桃》(《夹竹桃》实质上是拟民歌)、《黄莺儿》等民歌选集。这些民歌“发名教之伪药”的效用,在当时具有反对封建礼教的积极意义。此外,冯梦龙在辑录、流布民歌的过程中,坚持“存真”的原则,力求保持来自于乡间田野、市井里巷的民歌纯真俚俗的野性,他在《山歌》开卷第一首《笑》后的附记中,冯梦龙针对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凡‘生’字,‘声’字,‘争’字,俱从俗谈,叶入江阳韵。此类甚多,不能备载。吴人歌吴,譬诸打瓦抛钱,一方之戏,正不必如钦降文规,须行天下也。”(43)“藉以存真”、“俱从俗谈”是冯梦龙在编辑《挂枝儿》《山歌》时的理性认识,也付之于他搜集整理民歌俗曲的实践,以力求“存真”和“从俗”态度编辑《挂枝儿》《山歌》两本民歌专集,成为中国文人传播民歌的一个典型。正是由于冯梦龙在搜集整理民歌俗曲的实践中力求“存真”、“从俗”,努力接民间“地气”,使民间与文人两支队伍在民歌传播中的汇合,推动了浑朴质实、清新自然的“真”文学的发展,推动了冲击封建礼教和拟古文风的文学解放思潮的发展。 ①《皇帝感》其一,任半塘编著《敦煌歌辞总编》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34页。 ②范成大:《南塘寒食书事》,《范石湖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5页。 ③杜甫著,杨伦笺注:《杜诗镜铨》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31页。 ④张岱:《虎丘中秋节》,《陶庵梦忆》卷五,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64~65页。 ⑤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一一,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257页。 ⑥(39)李延寿:《南史》卷七○《循吏传》,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697、1697页。 ⑦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一二《诗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1页。 ⑧(27)黄遵宪著,钱仲联笺注:《人境庐诗草笺注》卷一《山歌》注引张元济《岭南诗存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5、55页。 ⑨汤显祖:《豫章揽秀楼赋并序》,《汤显祖诗文集》卷二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83页。 ⑩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七,《艺苑卮言校注》,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363页。 (11)(16)李开先:《时调》,《李开先全集》中册《词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52页。 (12)《中国歌谣集成》(甘肃卷),中国ISBN中心2000年版,第13~14页。 (13)李梦阳:《诗集自序》,《空同子集》,明万历三十年邓云霄刻本。 (14)李孝光:《送国侍者》,顾嗣立编《元诗选》二集《五峰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21页。 (15)袁宏道:《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17)黄遵宪:《山歌题记》,载钱仲联《人境庐诗草笺注》之《前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页。 (18)《南史》卷七○《循吏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96页。 (19)陈宏绪:《寒夜录》卷上引卓珂月语,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1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700页。 (20)《甘泉歌》,杜文澜辑《古谣谚》卷六九,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81页。 (21)《渊鉴类函》卷一八五《乐部》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22)《二月仲春色光辉》,张锡厚主编《全敦煌诗》卷八七,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2~3753页。 (23)《儿郎伟》(驱傩),《全敦煌诗》卷一五四,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2页。 (24)袁宏道:《迎春歌和江进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25)《撑船唱歌歌满河》,《中国歌谣集成》江西卷,中国ISBN中心2003年版,第7页。 (26)宋懋澄:《听吴歌记》,《九籥集》前集卷一,明万历刻本。 (28)王祥珩:《广西南部民间情歌》,北京大学《歌谣》周刊第二卷第三十八期,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三月十三日。 (29)赵翼:《土歌》,《瓯北诗钞》“七言古二”,《赵翼全集》第四册,凤凰出版社2009年版,第120页。 (30)(31)(32)屈大均:《广东新语》,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58、362、261页。 (32)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八《刘三妹》,第261页。 (33)刘禹锡:《上淮南李相公启》,《刘禹锡集》卷一八,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13页。 (34)(35)刘禹锡:《竹枝词九首并引》,《刘禹锡集》卷二七,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58~359、359页。 (36)刘禹锡:《竹枝词二首》,《刘禹锡集》卷二七,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364页。 (37)房玄龄等:《晋书》卷二二《乐志下》,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716~717页。 (38)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四,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639~640页。 (40)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47页。 (41)冯梦龙:《叙山歌》,冯梦龙编纂《山歌》卷首,《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69页。 (42)冯梦龙:《挂枝儿》,刘瑞明注解《民歌集三种注解》(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8页。 (43)冯梦龙:《山歌》卷《笑》附评,《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71页。标签:冯梦龙论文; 民谣论文; 扬州画舫录论文; 竹枝词论文; 山歌论文; 陶庵梦忆论文; 广东新语论文; 劈破玉论文; 诗歌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