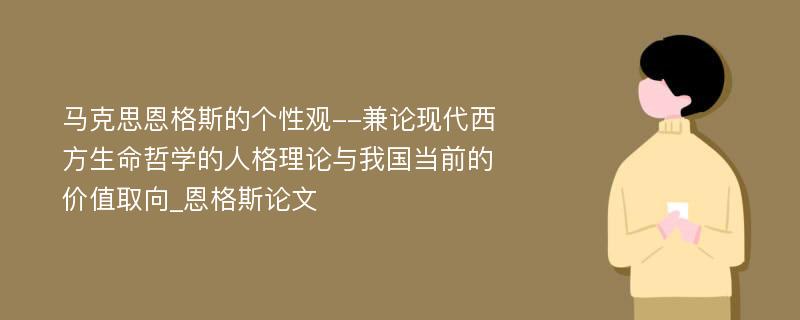
马克思恩格斯的个性观——兼评现代西方人生哲学的个性理论和我国当前的价值导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个性论文,人生哲学论文,导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又是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合写《德意志意识形态》150周年。在纪念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个五十年”的这两个重要事件的时候,重温恩格斯临终前对新世纪基本特征的预言,从新的视角开掘《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人们忽视了的有关个性及其形成发展的理论观点,对于我们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个性观,科学地确定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导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恩格斯的选择:自由个性是新世纪的箴言
恩格斯逝世的前一年,1894年1月3日,意大利律师、社会党人朱泽培·卡内帕给他写来了一封信,请他为将于当年3月起在日内瓦出版的周刊《新时代》找一段题辞,用简短的语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特征,以区别于曾被佛罗伦萨大诗人但丁称之为“一些人统治,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
恩格斯没有把这一请求当作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他看来,第一,“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个诗人,也是近代的第一个诗人”,因而新纪元的题辞必须出自一个同样占有划时代地位的人物之手;第二,“要用不多几个字来表述未来新时代的思想,同时既不堕入空想社会主义又不流于空泛词藻,这个任务几乎是难以完成的。”经过再三考虑,他于1884年1月9日从伦敦回信道:
“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恩格斯的这一选择,以最清晰的语言宣布:人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是新时代的根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追求的最终目标!
指出这一点,肯定会使一些人感到莫名的惊诧。因为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也不管是好心还是恶意,他们总是把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本位主义”,而既然是以“社会”为本位,那就肯定要强调“社会”高于“人”、“整体”高于“个人”,只能主张人的“合群性”和依赖性,而不能主张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只能把社会和集体看成人和个人存在发展的前提,而不能反过来把人和个人看成社会和集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那么,是不是恩格斯选择错了,抑或是我们把恩格斯的观点理解错了呢?
恰恰相反。把社会由自然和历史从外部强加给人们的“结合体”变为人们自己自觉联合而成的“自由人联合体”,使“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成为一切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是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贯目标。
马克思在驳斥施蒂纳关于“人们丝毫没有发展自身的意图,他们总是想建立一个社会”的说法时,强调:“人们丝毫没有建立一个社会的意图,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使社会发展起来,因为他们总是想作为孤独的人发展自身,因此他们也就只有在社会中并通过社会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发展。”②“只有我们的桑乔这种类型的圣者才会想到把‘人们’的发展与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发展分割开来,然后在这种幻想的基础上继续幻想下去。”③“圣麦克斯认为共产主义者要‘为社会’‘牺牲’,其实他们只是想牺牲现存的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引者)”。④
在集体与个人的关系上,马克思也不仅肯定:“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而且区分了“过去的虚假的集体”和“未来的真实的集体”,认为:“从前各个人所结成的那种虚假的集体,总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而使自己的联合下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⑤这就是说,真实的集体不是处于个人的“结合”,而是以“自由个性”为前提的“联合”,“在这个集体中个人作为个人参加的。”⑥
这就是说,承认人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并不是资产阶级和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的“专利”。马克思主义与现代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区别,不在于是否承认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而在于如何看待个性自由,如何达到自我实现。
其实,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是整个现代历史和人生哲学以及一般社会思潮共同关注的中心问题,是现时代的共同呼声。只要简要地回顾一下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史,就可以明白无误地发现这一点。
古代对人的理解是狭隘的。这种狭隘表现在内外两个方面,就外部来说,人们只限于把本民族、本部落、本部落联盟等等看作主体,没有把人看作是普遍的。这不仅意味着“非我族者,其心必异”,而且简直可以说是“非我族者,其类必异”。就内部来说,人们只限于从有机整体的角度看诗人,没有把个体看作独立的个性。“血族复仇”的观念就是明证。两方面综合起来说,就是当时只有狭隘的“人群”的观念,而不存在普遍的“人类”和独立的“个人”观念。这种状况,在一定意义上一直延续到整个中世纪。在西方,它表现为“希腊人”和“野蛮人”、“基督徒”和“异教徒”的对立;在中国,则表现为“华夏族”和周边的“夷狄”、“犬戎”、“苗黎”等的对立。
从这个最初的观念出发,人的自我意识沿着两个方向发展起来。一条途径可以称之为“我是人”的方向,即向着承认人的普遍性的方向发展,由“人群”逐渐扩展到“人类”的观念。就西方来说,它萌发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人性”或“人道”(直译是“人的”)概念,古罗马时期的喜剧作家普卡利乌斯·泰伦斯在其剧作《自我折磨者》中的一句台词“我是人,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就是代表这一趋势的千古名句。另一途径则可以称之为“人是我”的方向,即向着承认个人的独立性的方向发展,由“人群”逐渐深化到“个人”的观念。在西方,它同样萌发于古希腊时期。普罗塔哥拉的名句“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包含着对作为感知主体的个体特异性的承认。
从文艺复兴运动开始,人的自我意识冲破了古代的狭隘眼界,把上述两个向度的理解都大大向前推进了,并由此形成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在英国经验主义及受其影响的法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中,人被理解为自然的、经验的个体,人类的存在不过是这些真实存在的个体的集合,“人类”的观念不过是从个体性归纳出来的抽象共同点。而在大陆理性主义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及与其密切联系着的浪漫主义文艺运动中,人则被理解为伦理的、理性的族类(人“类”),个体的存在不过是体现这一真正本质的人类的单个“标本”,“个人”的观念不过是从族类性中演绎出来的虚假个别性。前一种观点主要以英国休谟和法国的爱尔维修为代表,后一种观念则主要以文学家席勒和哲学家黑格尔为代表。
但是,直到近代为止,在“我是人”和“人是我”这两个向度中,“我是人”一直是主导的,这不仅因为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日益转向自然科学和实证的社会科学,近代对人的问题的关心主要是在德国古典哲学范围内发展起来的,而且因为即使在涉及到人的问题时,所持的“人是我”也是不彻底的。他们尽管把人理解为个体性的存在,但仍然把这种个体性归结为抽象的共同人性—每个人都固有的同样的自然本性。因此并没有使“人是我”彻底摆脱“我是人”的束缚,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在他们那里,“经验的个别性”恰恰同时是“抽象的普遍性”,“自然唯物主义”恰恰在人的问题上变成了“抽象唯心主义”。即使就近代哲学的终结者费尔巴哈和施蒂纳来说,也表明了“我是人”和“人是我”这两种向度尚未彻底分裂。费尔巴哈是从“我是人”出发的,他主张人的“类本质”,但这种“类本质”又被归结为单个个人的自然的、情欲的存在;施蒂纳是从“人是我”出发的,他强调人是“唯一者”,却仍然把“唯一者”看成是人类普遍本质的理想的、伦理的化身。
只是从现代人生哲学开始,“人是我”才完全摆脱了“我是人”的影响,人类个体才被看作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克尔凯郭尔公开宣布:“没有人,只有你、我、他。”如果说近代哲学主要是在泰伦斯“我是人”的影响下研究人的话,那么现代人生哲学则完全是以“人是我”为自己的旗帜的。正是在这面旗帜下,现代人生哲学一步一步地清除着“自我”中的人类共同性。叔本华抛弃了人的共同的理性本质,尼采抛弃了人的普遍的伦理规范,弗洛伊德则把人的一切文明成果都看作是作为“超我”压抑人的“本我”的东西,海德格尔进一步否定了人的本性,但还保留着对人的先验生存状态的承认,萨特却干脆连这一点也抛弃了,使个人的一切都变成了自我的“创造”。
必须承认,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对人的这种理解确实是片面的,它们同样曲解了人的个性。把“人是我”同“我是人”绝对对立起来,实际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与人关系的对抗性质。但是,正象资本主义社会本身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一样,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对人的这种片面理解也是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重要侧面。从古代的狭隘“人群”观,经过近代的抽象“人类”观(以及经验“个体”观),再到现代的纯粹“个人”观,本身曲折地反映了人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和个性意识的成熟,曲折地表达了人类自身解放和个性自由发展的要求。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对个性问题的解决方式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但它们提出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这一问题本身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它们对个性问题的回答从总体上说是错误的,但它们对某些具体问题的研究却可以给我们以不少启示;甚至它们的失足之处,对我们都有重要的警诫意义,正所谓“前车之覆,后者之鉴”。因此,那些企图通过否定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来维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纯洁性”的人,实际和同克雷洛夫寓言《隐士和熊》中所讲述的那样,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熊的服务”。他们所捍卫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并不是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而是类似于早期的不成熟的“粗陋平均的共产主义”、甚至巴枯宁“兵营式的共产主义”的东西;他们所坚持的对人的理解,实际上仍然停留在古代狭隘的、“自然共同体”意义上的“人群”观上,这种观念远低于他们所“批判”的现代人本主义。从这种观念出发,不仅不可能从本来的意义上抛弃现代人本主义,甚至不可能正确把握其真实的含意,无法与之进行真正的“对话”。借用马克思的说法,他们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不过是企图倒转历史车轮的行为,因为他们不是高于“私有财产”,而是压根儿“尚未达到私有财产的水产”!
(二)自由个性:“个人行为和独创发展”的统一
要找到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的途径,我们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要搞清:“个性”是什么?“自我”是什么?
通常人们认为,所谓“个性”,就是个人不同于他人的特征,即每个个人都不可避免地具有的人类个体的特异性。
其实,这并不正确。一方面,“个性”不等于“个体特异性”。固然,前者必须以后者为基础,但个性特异性却可以用来单纯标志其自然(生理)的特异性,而个性却是“社会个人”的特异性,另一方面,个性固然总是个人的特性,但个人并不一定具有个性,马克思就认为存在着两种个人:“无个性的个人”和“有个性的个人”。
马克思认为,个体、个人、个性是三个既有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范畴,个性不等于“个体性”或“个人性”,它只能被“了解为独创发展和个人行为”的统一。⑦马克思的这一个性观,主要是在批判施蒂纳关于个性即是“唯一者”的“独立性”的过程中展开的。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个性是一种社会性。它是指个人存在的独立性和个人“人性”的具体性。人们常常把“社会性”仅仅理解为“群体性”和“依赖性”,其实这是片面的。马克思所讲的“社会性”本身是独立性和依赖性、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统一。人不能以孤立的个体形式存在,但是人的群体性又根本不象蚂蚁、蜜蜂“社会”那样,是由遗传机制所造成、由生理上完全特化了的个体所构成的有机群体,人类个体总有某种独立性。因此,一窝蚂蚁实质上只是一只蚂蚁,“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⑧。而人之所以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却正在于它“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⑨正因为如此,人的个性绝不是单纯的“个人的直接本性”即自然属性的特异性,而是“社会个人”的独立性和具体性。
施蒂纳不懂得这一点。他的所谓“唯一者”的“独立性”,只是指人作为自然个体的“个体特异性”。这样一来,他就抹煞了人的个性与一般存在物的个体性之间的质的区别。按照施蒂纳的这一逻辑,既然人的自然个体性可以称之为“个性”,那么任何动物、植物以至无机物都应该具有“个性”了。事实正是如此,施蒂纳“十分庄严肃穆而又洋洋得意地说,他不会因为日本天皇吃东西而感到饱,因为他的胃和日本天皇的胃都是‘唯一的’、‘无比的胃’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同一的胃。”⑩马克思认为,这实际上不过是莱布尼茨如下“旧原理”的翻版: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因为自然界中永远不会有两个完全相一致的东西”。对此,马克思讽刺道:“在这里,桑乔的唯一性降低为他同任何虱子和任何沙粒所同有的性质。”(11)从这种观点来看的人的“个性”,“归根到底就是警察所确定的个人与自身的同一,即一个个人不是另一个个人了。这样,这位想冲击世界的英雄桑乔就一落千丈而降为签证局的一个文书了。”(12)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的个性不包含人的自然个体性。正象人的社会性必须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并以扬弃的形式包含着后者一样,人的个性也以人的自然个体性为基础并包含它于自然之内。人的社会性不能离开其自然性属性而孤立存在,它本身是一种“社会化了的自然”。所谓人的个性是一种社会性,只是说人的自然个体性不再是独立于人的社会性之外的自然,而是作为“人化了的自然”受个性的社会结构所制约。
其次,个性还是一种主体性。它是指个人行为的自主性和个人“人格”的独立性。人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存在物,而且是一种有意识的、能动的存在物,活动是人的存在的根本方式。“社会个人”的独立性和具体性,也集中地表现为个人活动或个人行为的独立性和具体性。因此,马克思特别强调对人的个性必须同“个人行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就是说,人的个性必须以“人格”为前提,以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为前提。所谓“人格”,正是指“赋有意志和意识的”行为主体。(13)他能够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行为,并对这种行为产生的后果负责。只有具有自己独立“人格”的人,对自己的行为具有自主性的个人,才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人”。那种尚未具有行为自主权的人(如幼儿),自愿放弃行为自主权的人(如奴才),或被强制剥夺了行为自主权的人(如囚犯和奴隶等),都不可能具有独立人格,不可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人”。
在马克思看来,离开个人行为的自主性,去谈论人的“个性”,只能是种可怜的自我欺骗。施蒂纳正是如此。他把个性仅仅归结为“自我的唯一性”,胡说什么农奴和奴隶即使在被拷打、被剥夺了自主权时仍是充分享有“个性”的。因为“主人的皮鞭落在我身上”,“我的骨头因拷打而吱吱发响,我的肌肉因鞭笞而颤抖证明:我还是属于我自己的,我还是自己的我。”(14)马克思讽刺地说:“如果不用唯一的自然科学语言而用病理学的语言,这些通过贾法尼电流在他的那具刚从绞架上取下来的尸体上,甚至在一个死青蛙的身上也可以发现的象‘骨头’吱吱发响、肌肉颤抖等等现象,在这里却被他用来证明他‘整个地’‘无论外部响、肌肉颤抖等等现象,在这里却被他用来证明他‘整个地’‘无论外部或内心’还是他自己所有的,他还支配着自己。”(15)其实,这些所证明的恰恰是奴隶或农奴的人格被践踏,个性被剥夺,证明的只是“奴隶主的权力和独立性”,而不是农奴或奴隶的“独立性”。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下由于“物的人格化”和“人格的物化”,只有金钱和资本才具有“个性”,而人特别是劳动者则被剥夺了个性。
当然,与尚未形成或自愿放弃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不同,被剥夺者的行为自主性是不可能完全丧失的。因此,奴隶、农奴或雇佣工人的人格和个性并没有完全被剥夺。但是,这绝不是象施蒂纳硬要人们相信的那样,是因为被拷打的是“我的”自身,呻吟和颤抖是“我的”痛苦。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内心’没有妄自菲薄,即在‘外部’也表现为没有自暴自弃”,他们“嘲弄那些折磨他们的人。讥笑这些人的软弱,讥笑奴隶主们不能强迫他们俯首听命,只要他们还忍得住肉体上痛苦,他们不作任何的‘呻吟’,不作任何的哀诉。”就是说,他们不是由于逆来顺受、放弃自己的“人格”而表现出自己的个性,而是由于反抗才显示出自己的个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他们仅仅由于“超脱所谓奴隶身份就是他自己的‘独自性’的这种思想”,并以实际行动去争取“从这个‘独自性’中解放出来”,才保持或进一步获得了自己的个性。(16)
最后,个性更是一种独创性。人不仅是一种社会的存在,也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行为主体,人还是自由的存在。同样,个性也不仅表现为社会个人的个体特异性、独立人的行为自主性,更重要的是体现为“个人的独创发展”。只有个人的独创发展,才真正配得上“自由个性”的美名。
马克思认为,个人的独创发展离不开“比较”,而“比较”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外在比较。个人活动的“唯一性”或“无比性”,是说个人在某一活动中的不可替代性或无可超越性。他说,这种“独创性意义上的‘唯一性’,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前提的,即无比的个人在一定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不同于其他的个人在同一范围内所进行的活动”。(17)通俗地说,就是个人给他所进行的活动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使这种活动及其产物成为他的个性的对象化。例如某一位歌唱家的演唱是个性化的、无可替代和不可超越的,因为换了一个人即使唱的是同样的歌,也不具有这一位歌唱家独特的音色、激情和魁力。其二,更重要的是要把外在比较转变为内在比较。个性在于个人发展的自律性。人们不应当再拿某种不以个人为转移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而比较应当转变成他们的自身区别,即转变成他们个性的自由发展。(18)一个人如果自身没有追求、没有内在价值标准,或者不以自身发展为尺度,只知道迎合世俗观念、附合他人,或者单纯追求外在目的(如仅仅追求物质财富的占有和社会权势的攫取),那么,他就绝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有个性的人”。
不过,这里必须强调的是,马克思肯定个性的真正本质在于个人活动的“唯一性”和个人生存的“自律性”,并不是从脱离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这一意义上讲的,他坚决反对那种把个性的“唯一性”歪曲成个人的孤立性,把个性的“自律性”歪曲成个人的封闭性的观点。他说:“倍尔西阿尼(当时意大利的著名女歌唱家——引者)所以是一位无比的歌唱家,正因为她是一位歌唱家而且人们把她同其他歌唱家相比较;人们根据他们的耳朵的正常组织和音乐修养做了评比,所以他们能够认识倍尔西阿尼的无比性。”(19)同样,个人生存的自律性也离不开外部尺度,必须把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辩证地统一起来;而且这种“自律性”的尺度本身也是随人的发展而变化的,即“比较应当转变成他们的自身区别”。这就是说,马克思所理解的“唯一性”(无比性)是以社会性、普遍性(可比较性)为基础的,“自律性”(自身同一性)是以历史性、发展性(自身区别)为基础的。两方面合起来,表明马克思所讲的人的个性,即“独创发展和个人行为”的统一,不仅是“联系中的独立性”和“发展中的同一性”,而且是同整个人类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的。
施蒂纳则不然,他把“唯一性”理解为:“作为一个唯一者的你,与其他的个人再没有丝毫共同之点,所以也没有任何使你和其他的个人区分开来或者对立起来的东西”。(20)马克思指出,这种把个性看作是孤立的个别性的观点,恰恰会导致相反的把人看作抽象普遍性的另一极端。“两极相通”,否定个人之间存在着人类的共性,正好同时否定了人的个体的个性。因为,“倍尔西阿尼的歌唱不能与青蛙的鸣叫相比,虽然这里也可以有比较,但只是人与一般青蛙之间的比较,而不是倍尔西阿尼与某只唯一青蛙之间的比较。只有在第一种情况下(即以共性为前提的“歌唱家之间的比较”——引者)才谈得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比较,在第二种情况下(即从孤立的两个“唯一者”出发的“倍尔西阿尼与某只唯一的青蛙的比较——引者),只是他们的种特性和类特性的比较。”(21)施蒂纳对个性“自律性”的理解也同样是错误的,他实际上是沿袭了“费希特派的哲学家的说法”(“我就是我”),把“自律性”变成了个人与自身的绝对等同。这样一来,所谓为“自我”就成了一种“固定观念”、一种永恒不变的尺度。马克思指出,人们真正的个人“自律”,恰恰只有“通过他们把‘固定观念’从头脑中挤出去的办法来实现。”(22)
马克思上述三个方面的分析,深刻地提示了人的个性所包含的“个体特性——独立人格—独创发展”这一内在结构,说明了人的个性是一个由“个体特异性”,经过“行为自主性”,发展到“活动独创性”的过程。马克思的这一个情况,不仅与古代和近代对个性问题的理解彻底划清了界限,而且为我们正确评价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在个性问题上的得失提供了科学的标准。
现代西方人生哲学对“自我”和个性的理解,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弗洛伊德主义和人格主义的理解。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是在其早期提出的“无意识——前意识——意识”的心理结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的。他认为,个体的人格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构成。其中,“本我”是个体与生俱来、先天存在的各种本能、欲望的总和。它象一只沸腾的大锅,是个体本能和欲望的贮藏库,是自我和超我的动力源泉。本我没有统一意志,不受伦理道德束缚,不顾及客观条件,只遵循“快乐”原则。“超我”是儿童早期在父母、教师和社会的影响下形成的“自我理想”和“自我良心”,它是社会的法律、伦理规范的“内化”,它以潜意识罪恶感的形式压抑着“本我”。“自我”则是从本我中分化出来的,它以服务于本我、满足本我、保护本我为宗旨,以协调“本我”与“超我”、现实之间的关系为职责。因此尽管弗洛伊德看作个体有组织的、现实的个性的代表,但实际上他的“人格”是分裂的,他的“自我”归根结底不过是“本我”的表现。他的“个性”实质上是一种本能愿望。
人格主义者则把“自我”归结为一种精神性的道德主体。其创始人美国哲学家鲍恩说:“我们有思想、情感和意志,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还有一种自我控制或自己支配自己的力量。所以在经验中我们有‘自我’和相对的‘自主’。这就造成我们的真正的人格。说得更确切一些,这就是‘人格’的意义。”人格主义者认为,每个人的人格是各自独立的、完全自由的,但又是有限的。有限的个人人格是无限的、最高的“人格”—上帝创造的。因此,个人人格作为一种“自制力”归根到底来自上帝的意志,各个有限人格之间的道德和谐归根结底来自上帝先定的道德秩序。
弗洛伊德和人格主义对个性的上述理解,尽管涉及到了作为行为主体的个人,但实际上都把个人行为的决定者引向个人之外,归结为个人的自然本性(“本我”)或抽象的伦理实体(上帝)。因而他们对个性的理解就其实质来说,并没有摆脱自然的“个体特异性”或抽象“人类普遍性”的局限,他们仍然停留在对个性理解的最初阶段,尚未上升到真正的“行为自主性”的水平。
第二种类型是存在主义者特别是“无神论存在主义”者对个性的理解。他们反对把“自我”归结为个体自然的本能欲望或抽象的伦理本质,强调个性是一种最本己的、个别化了的情感或意志。海德格尔的“我死故我在”便是他的个性观的核心。他认为,存在的个体化只有在“畏死”中才能真正体验到,真正“有个性的个人”便是达到“畏死”情态的人。因为只有体验到真正有自我个性的个人是达到“畏死”情态的人。因为只有体验到“谁也不能代替我死”,才能真正领悟到“谁也不能代替我生”,死是“自己的死”,生也只能是“自己的生”。“畏死”的体验把每个自我彻底个别化,使其摆脱对自然、社会、他人的依赖,孤独无依、无所救助,于是个人只能依自我,返回自我,成为个性化的人。萨特则强调人的个性就在于行为的自主性,他认为“自我”是一种绝对自主的、对自己的行为具有绝对自决权、并对之负有绝对责任的存在。他的名言是:“存在先于本质”。个人最初是空无所有的,首先只是存在、露面、出场,然后才按照自己的意愿造成他自身。“人不外是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
与弗洛伊德主义和人格主义相比,存在主义对个性的理解大大前进了一步,上升到了个人人格的独立性和个人行为的自主性。但是,由于存在主义者实际上把个性看成是每个人直接具有的或者本来应有的,因而也不可能真正把握个性的实质。实际上,个性只是人们的存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把个性说成是每个人直接具有或本来应有的,这并不是真正高扬个性的价值,而是把个性贬低为一般“个别性”。萨特就曾经批评海德格尔,说他用“我死故我在”来论证人的个性,是一种“循环论证”。确实,所谓“谁也不能代替我死”,同“谁也不能代替我吃饭”即施蒂纳所谓“我不会因为日本天皇吃东西而感到饱”一样,只是说明“我的”死是“个性化”的死。海德格尔之所以能用“我死”来论证个性化的“我在”,是因为他已经把“死”事先规定为“个性化”的死。说穿了,他本意是用“我死”证明“我在”,结果却是从“我死”推出“我在”。这当然是一种循环论证。如果排除掉这种逻辑错误,海德格尔的“畏死”“丝毫不涉及战胜日常平庸的个性”(萨特语)。不过,萨特自己也并不高明:他的“绝对自由”观同样不能把“有个性的个人”与“无个性的个人”区分开来。既然“我们的英雄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他能够成为的那个人,每一个所做的都是他能够做的事”,(23)那么一切个人都已经是“个性化”的、“自我实现”的了,又何必要你萨特出来饶舌呢?!不仅如此,既然现存世界能使每个人都达到“个性化”和“自我实现”,它就已经是“尽善尽美”的了。这样一来,萨特也就正象马克思批判鲍威尔时所说的那样,他的“震撼世界”的词句、他的“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成了“最保守的哲学”。(24)当然,这不是萨特的本意,但却实实在在是其逻辑之必然!
接近于攀上马克思个性观第三层阶梯的是马斯洛和弗罗姆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这可以说是现代人生哲学个性观的第三种类型。马斯洛从其关于人的需要结构的“五层宝塔”出发,把人格看成是发展的,认为健康的人格和真正的个性在于“自我实现”的需要,而这种高级需要必须在较低级需要至少得到基本满足的基础上才能发挥其行为动机作用。弗罗姆则强调了人对自己的对象可以有两种态度:“占有”和“存在”。单纯的“占有”是一种异化,只有使对象对象化的过程成为自己本质的确证过程,才算得上“存在”型的生活方式。
但是,即使马斯洛和弗罗姆也没有真正懂得马克思关于真正的个性在于“独创发展”的精神实质。第一,他们不是把高级需要和高级享受首先看作是自由的活动,而是仅仅归纳为一种高级体验或高级心理。第二,他们仍然没有摆脱人的先验本性的纠缠。马洛斯把人的高级需要归结为人的先天本能(尽管他称之为“似本能”即区别于动物本能的人类本能),弗罗姆则把人的高级享受(即活动本就是享受)说成是人在未被异化之前就已经具有的潜在本性,并企图把这一“人的本性”的范畴强加给马克思。这样一来,他们观点中所包含的“个性是人的需要及其满足方式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结果”这一思想就完全落空了;他们实际上回到黑格尔的“种子哲学”。既然人的高级需要和高级享受是一种类似本能的东西或潜在的本性,象“橡籽”尽管不等于“橡树”却包含了一切长成“像树”的内在根据一样,那么,这里存在的就不再是真正的发展,至多不过是个体的“发育”,不过是“展开”、“显现”而已!
(三)自我实现:条件和途径
只有马克思的个性观,才真正为人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指明了条件和途径。
首先,既然个性是一种社会性,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的独立性和以普遍的人类性为基础的具体性,那么人们就不应当在社会之外和人类普遍性之外去追求个性自由,而应当把自我实现过程看作社会化和个性化相统一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错误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人生来就是个体的,因而个性是无需追求的,需要追求的是人的社会性”,所以他们把社会化称为“个人的一条必由之路”。另一种观点则与之相反,认为“人总是准确无误地降生在社会之中,因而社会性是无需人去追求的”,所以他们认为只有个性化才是“个人不可逃避的生存使命”。
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是片面的。马克思说:“在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唯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但是他们相互间不是作为纯粹的我,而是作为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个人而发生交往的,同时由于这种交往又决定着生产和需要,所以正是个人相互间的这种和人的个人的关系、他们作为个人的相互关系,创立了——并且每天都在重新创立着——现存的关系。”(25)这就是说,把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是完全错误的,人的个性化和社会化实质上是人的自我实现这个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就人的自我意识来说,个人既必须在社会关系中认识和把握自身,又是从个人独立主体和自身需要的角度去认识和把握社会的;就人的自我设计来说,个人生存目标的确定必须同社会发展的客观状况和客观趋势相适应,但社会历史条件又不能直接决定个人生活道路的选择,它是个人自己筹划的结果;就自我实现的过程本身来说,人既必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活动,但这种社会关系和历史条件又是个人活动本身造成并不断加以改革着的。
因此,那种借口“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能存在,只有在集体中才能获得个人自由”,来否定人的个性和自我实现的观点,完全抹煞了人的生存方式的自觉能动性,实质上把人的生存变成了动物式的消极适应外部环境的本能活动。马克思当年批判德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时所说的,“我们的作者不是把社会、‘总和的生命’看作它赖以构成的‘单个的生命’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只是把它看作还同这些‘单个的生命’发生特殊相互作用的一种特殊的存在。”(26)持有这种观点的人口口声声强调人的“社会性”,其实他们本身却把人类社会变成了类似蚂蚁、蜜峰“社会”那样的生物群体,与其称这种观点为“历史唯物主义”,倒不如称之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生物学”更适合。
存在主义者特别是萨特在自我实现问题上的错误,并不在于他们强调了“自我设计”、“自我创造”,也不在于他们强调了要成为“有个性的个人”必须不把自己混同于外物或他人,而在于他们片面夸大了个人与情境、他人和社会的对立,仅仅把情境、他人和社会看作个人自由和自我实现的障碍,因而导致了对客观社会条件和人类普遍本质的绝对否定。所谓“个人只有在反对他人时才是自由的”、“他人就是地狱”、“社会就是陷阱”等等说法,就是这种观点的极端表现。这种观点表面上看似乎突出了个人存在的独立性和具体性,实际上恰恰否定了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客观条件和社会内容,从而架空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本身。
与存在主义的观点相类似,我国也有某些“人才学家”提出,真正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就应该让人才“象野草拼命地长,野花拼命地开,野兔拼命地跑”,“象一匹野马一样自由自在地驰骋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在他们看来,社会总是束缚人的个性的、总是压抑人的自由的,只有在自然状态中人才是不受限制的。这同样是错误的。马克思早在批判施蒂纳等人时就指出:“并不是‘不自由的野人之子’而正是‘文明人’才‘认为’野人比文明人更为自由。弗·哈尔在舞台上塑造的‘野人之子’并不知道文明人的那些限制,因为他不能体验到它们,如同只从剧院中去认识‘野人之子’的‘文明的’柏林小市民,也丝毫不知道野人的那些限制,这是一样很明显的。”(27)“假如我们自由的历史只能到森林中去找。那么我们的自由历史和野猪的自由历史又有什么区别呢?”(28)其实,在自然状态中存在的绝不是什么完全的“自由”和真正的“个性”,那儿有的只是严酷的自然必然性和本来意义上的生物个体性!
马克思主义在自我实现问题上的第二个基本观点,就是坚持人格形成和自我实现、自由和责任、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
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的个性又是一种主体性,它突出地表现在个人的行为自主性和人格独立性上,那么人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就不仅是一个单纯的“自我”外化的过程,而且同时是一个“自我”形成的过程;就不仅是一个争得自己行为自主权的过程,而且同时是一个履行个人生存职责和义务的过程。
在这个问题上同样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思想理论界一直为此而争论不休。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个人对自己的冷淡”。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援引弗罗姆《自我的追索》中所说的“我们的道德问题,是个人对自己的冷淡”,认为“这话对于我们正好切中要害,因为我国有两千多年忽视个人的传统,而且个人的发现至今仍在阵痛之中,个人的正当地位至今尚未得到确认。”另一种观点则与之针锋相对,认为中国的道德问题不是什么“个人对自己的冷淡”,而是“个人对社会、集体的冷淡”。他们直接诉诸中国历史现实状况的经验证据,指出费孝通先生早在数十年前就在《乡土中国》中深刻揭露过中国人的“私的毛病”。苏州人家后门常通一条河,听起来再美丽没有了,文人笔墨里称之为中国的威尼斯,天底下再没有比苏州城里的水道更脏的了,人们什么东西都往河里倒,明知别人家在河里洗菜洗衣服,也将河当厕所。为什么呢?因为这条小河是公家的。“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说大家可以占一点便宜的意思,有权利而没有义务了。”
毫无疑问,上述两种观点所援引的证据都是确凿的,但是他们由此引出的结论却都是片面的。实际上,问题的症结在后一种观点所援引的费先生的最后一句话中已经点明了,那就是必须从“权利”和“义务”的辩证统一来看问题。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是以“权利和义务相统一”为前提的。马克思一再指出,所谓个人行为的“自主性”并不仅仅是一种纯粹的权利,它还意味着一种“责任”、“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29)离开义务讲权利,就必然会把自由变成一种个人任性的为所欲为,把个性自由变为一种“不开化的利已主义”;反之,离开权利讲义务,就会根本抹煞人的个性自由,成为封建专制主义、宗教禁欲主义或者巴枯宁“兵营式共产主义”的辩扩士。在马克思看来,这两种畸形的东西尽管表面上绝对对立,实际上却是互为补充的。真正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本身正是在反对上述两种片面性的过程中才发展起来的。
因此,中国道德问题的解决,当务之急在于确立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性,而不是鼓吹绝对的“个人权利”或进行抽象的“普遍义务”的说教。离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无论是“对自已的冷淡”还是“对集体的冷淡”都不可能得到解决。
最后,马克思主义在自我实现问题上的第三个基本观点,在于强调自我实现与自我发展、个性自由与人类解放的辩证统一。
自我实现问题上的第三种“二律背反”就是:究竟它是“每个人无可逃避的生存使命”还是“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的生存境界”?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每个人都是“从自己出发的”,他们的活动及其产物当然都是他们的“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因而每个人都是自我实现的,差别只在于各自“自我实现”的具体方式不同而已。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大多数个人“沉沦”于日常在世状态,孜孜以求名,孜孜以求利,终日为生活琐事所“操心”、“烦”,因而只能混迹于外物和他人之中,只有少数超出了日常烦忙状态的人才能真正达到自我实现的高度。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同样是一种抽象的对立。初看起来,似乎前者是“民主”的、“人道主义”的,后者则带有“贵族式”的烙印,因为他们似乎主张自我实现只是少数人的“特权”。其实,前者对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权利的普遍承认,是以降低“自我实现”本身的标准为代价的,任何生存状态都被他们看作“自我实现”,这种“自我实现”实际上不过是生存的“自身同一”。如果把这种逻辑贯彻到底,可以说连动物、植物甚至一切无机物都是“自我实现”的,因为它们的存在都是它们“自己的存在而不是别的东西的存在”。后一种观点坚持了自我实现的标准,但同样陷入了形而上学的静止观点,没有看到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存境界在历史上是发展的、不断上升的,今天“少数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明天会变成多数人甚至一切人“不可逃避的使命”。
马克思从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扬弃了上述“二律背反”。他关于人的个性所包含的“个体特异性—行为自主性—活动独创性”的内在结构和历史发展的思想,为人类通向真正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指明了方向。
一方面,马克思没有廉价地将“自我实现”的权利“赐予”一切人。他认为,自我实现并不是个人与生俱来的本性,而是个人生存状态和生存境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人们的生理活动和必要劳动范围内,个人并未超出“自然个体性”的存在。在谋生活动特别是剩余劳动领域内,个人才超出了自然个体性局限,获得了“行为自主性”。但是,即使在这里,个人也未上升到“有个性的个人”的境界,他们仍然只是由一定的社会分工所造成的特定的“社会角色”,只是一定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的“人格化”、类型化。只有在“自由活动”中,人才真正进入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殿堂。在这里,个人才能在自己的产品上打上自己独特的印证,活动才会真正成为个性的对象化的确证,每个个人才会真正成为不可替代、无可超越的“唯一者”。要了解这一点,并不需要高深的知识或素养,只要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一个茶杯(仅仅作为茶杯而不是作为艺术品)是可以替代的,而一幅名画则是无可替代的,茶杯的制造者是一种“无个性的个人”,而名画的创作者则是一种“有个性的个人”。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采取鄙视人民大众的“贵族老爷式”态度。第一,他的个性结构思想表明,有个性的个人活动必须建立在无个性的大众活动的基础上,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说,正是后者构成了个性自由和自我现实的基础,推动着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的发展,“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第二,在大多数人仍然处于“无个性的个人”状态时,少数“有个性的个人”的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也不可能是完备的;并且他们也是只有使自己的活动有助于推动前者向更高的生存状态上升,才可能成为“有个性的个人”。第三,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在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人们能够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改变整个人类的生存状态,造成每个人都能做到使自己的个性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新世界,这就是人类的共产主义时代。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念相反,马克思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正是个性空前繁荣的时代,他要消灭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把人类变成无差别的个体集合,恰恰相反,是要使人们之间的个性差别成为唯一的差别,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开辟最广阔的天地。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这一体制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基本要求,是确立独立的人格和行为自主,也是人们自我实现的更高个性追求创造了一定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我国尚有相当多的人口尚未超出最低生存追求的层次。因此,现阶段正确的价值导向只能是:以人格独立化和行为自主权为中轴线,同时鼓励人们把进一步提高个人主体生存境界的追求同改善全民族的客观生存状况的努力结合起来。在这里马克思中学时代就写下的话语:“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30)仍然应成为一切有志于追求真正个性自由和自我实现的人的座右铭!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9页。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5页。“桑乔”是《唐·吉诃德》中同名主人公的仆人,这是马克思借用来讽刺地指称施蒂纳。
④同上书,第235页。“圣麦克斯”即施蒂纳。
⑤⑥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85页、第516页。
⑧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95、21页。
⑩(11)(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0页、第520、第519-520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4页。
(14)(15)(16)(17)(18)(19)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49页、第350页、第351页、第517页、第518页、第517页。
(20)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2页。
(21)(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17-518页、第518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8页。
(23)(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64页;第2卷,第244页。
(25)(26)(27)(28)(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5页、第562页、第343-344页、第3页、第137页。
(3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