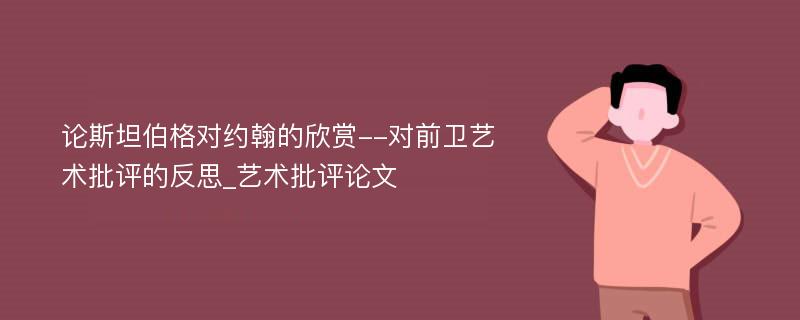
论施坦伯格的“约翰斯赏析”———个关于前卫艺术批评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约翰论文,前卫论文,伯格论文,批评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卫艺术①批评在多大程度上是可靠的?这一发问和一般人在赏画这件事情上常有的一个困惑有关:那些看上去极其普通甚至常人似乎都能画出来的作品(比如波洛克的滴洒画、弗兰克·斯特拉的不规则多边形画、莫里斯·路易斯的条纹画等),却在批评家的眼里充满了那么多不同寻常的意义;那么,究竟是我们的鉴赏水平不够,还是批评家们在过度阐释?对于一般人来说,审美素养不够从来都是一个事实,其程度因人因地因时代而异,而批评总是引发太多的争议而难以服众,则似乎是自前卫艺术的诞生以来才特别引人注目的现象。这种现象的产生,与艺术批评变化了的语境有关。与弹药充足、武器完备因而总是充满了自信的传统艺术批评家不同,前卫艺术批评家一开始都是一些很苦恼的人,他们所遭遇的困惑对于他们的前辈来说基本上不会遇到,而对于他们作为批评家的身份来说却是很伤自尊的,那就是——竟然有他们看不懂的作品!在这里,看不懂的意思是:艺术可以这么搞吗?甚至,这是艺术吗?至于其品质的好坏,那就更让他们无从判断了。那么,弃之不顾吗?然而,现代艺术史一次又一次地将离经叛道者们的作品合法化甚至经典化的事实却让他们心有不甘,生怕又一次错过了见证伟大艺术诞生的良机,如此患得患失的焦虑可谓让他们痛不欲生。而往往是在经历如此反复的阵痛之后,他们的“阐释”终于分娩了,并因此而成为命名艺术史事件、引领未来艺术方向的批评经典。一方面,这些批评的独创性的确令人耳目一新,但另一方面也让人对其作为一种阐释的可靠性疑窦丛生:究竟是那些他们所命名的艺术真有他们说的那么不同寻常乃至伟大,还是他们作为批评家的自尊促使他们说出了一些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欺人之语?这就是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本文是以在我看来可以作为典型案例的美国当代艺术批评家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1920-2011)的“约翰斯赏析”为例所做的一个窥豹一斑的考察,所思有限,意在引起学界对这一现象的重视和研究,并由此反思前卫艺术批评的困境及出路所在。 一、作为形式主义批判者的施坦伯格 施坦伯格是著名的文艺复兴艺术专家,但其巨大影响却主要源于他作为一个前卫艺术批评家的身份,其贡献在于打破了以格林伯格为代表的形式主义理论一手遮天的批评格局,确立了一种据称是将形式分析、情感内容与历史语境熔为一炉的批评模式。“因此,目前国际艺术史界公认,是施坦伯格领导了拒斥格林伯格/弗雷德版本的现代主义运动”(施坦伯格475)。其长达40年的艺术批评成果汇集于《另类标准:直面20世纪艺术》(Other Criteria:Confrontations with Twentieth Century Ar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7)一书,收入其中的《另类准则》一文被人视为其批评思想的纲领,也是一篇讨伐形式主义理论的“檄文”。针对格林伯格认为传统绘画倾向于掩饰而现代绘画却故意突出绘画媒介特征的观点,即“在欣赏古典派大师的作品时,看到的首先是画的内容,其次才是一幅画面;而在欣赏现代派作品时,看到的首先是一幅画”(弗兰契娜哈里森5-6)。施坦伯格以对伦勃朗的《读书的女人》的精彩分析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格林伯格的这个说法其实是偏颇不公、无法成立的,进而针对格林伯格认为现代绘画以追求摆脱错觉的平面性为其目标这一核心论断尖锐地指出:“格林伯格想将所有老大师与现代主义画家的差异还原为一个单一的标准,而这个准则要有多机械就有多机械——要么错觉,要么平面。然而,如此简单的艺术还有什么意义可言?”(96)。更为关键的是,施坦伯格有力地证明了这种机械的二分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其实格林伯格在提出现代绘画以追求纯粹的平面性为其目标之后,似乎也意识到了其理论可能面对的质疑,即在有的人看来,不管你怎么画,画面上的(三度空间)错觉总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如果承认这一点,格氏理论关于错觉和平面性的区分似乎立刻就会瓦解,但格林伯格认为他强调的其实是纯粹的视觉经验:“现在这是一种严格属于绘画和视觉的三维空间。在古典派大师创造的空间幻觉中,人们可以想象身临其境,在画中行走,现代派画家创造的幻觉只能看,只能用眼睛遨游”(弗兰契娜哈里森8-9)。可以想象,当年格林伯格写下这段话的时候该是多么得意——有惊无险啊!卖个破绽,再杀你一个回马枪!然而,真能这么说吗?让我们看看施坦伯格是怎么讲的: 在什么样的绘制空间里,你可以让自己漫游其中?格林伯格显然能够想象自己步履蹒跚地行走在伦勃朗式的幽暗空间里,但他却无法想象穿行在奥列茨基的图画空间里会是什么状态。在一个太空旅行的时代,我们还需要被提醒,一种类似大气层外的虚空的图画,对想象中的穿梭来说是极为诱人的,不正如类似不断后退的风景的图画,对一个步行的人来说同样是有吸引力的吗?我们如今是在康德时代的交通概念的衬托下来界定现代主义绘画的吗?(92) 看了这段话,我们还能那么理直气壮地坚持格林伯格那种关于空间错觉的不同类型的区分吗?施坦伯格就是在这些几乎不容辩驳的技术分析的基础上,对于现代艺术批评中的形式主义倾向进行了近乎毁灭性的调侃和打击: 今天占主流地位的形式主义批评家总是将现代绘画处理成一种进化技术,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有某种特殊的任务需要解决——这是为艺术家们设置的任务,就像在大公司里为研究职员所设置的问题一样。只要他能提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那么作为工程师与技术研究人员的艺术家就变得非常重要。对那个问题的选择如何与个人的冲动、心理结构或社会理想相吻合,却无所谓;只有解决办法才是重要的,因为它回答了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技术专家们提出的问题。(100) 这是迄今为止我所能看到的对形式主义理论的最为形象也最为辛辣的批判。②在我看来,施坦伯格在这件事情上所扮演的角色,完全可以媲美那个说皇帝其实什么也没穿的孩子,在形式主义理论统治批评界长达半个世纪而近于僵化的历史时刻,其批判质疑可谓应运而生,功莫大焉。而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度的怀疑精神、极其敏锐的批判意识的人,在面临与当年形式主义者们所遭遇的类似的批评困惑时,最终似乎也未能免俗,没有经受住“理论”的诱惑而营造出他的可疑的“另类标准”。这一点在他对美国当代艺术家贾斯帕·约翰斯(Jasper Johns,1930-)的批评阐释即他所谓的“约翰斯赏析”(40)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二、疑点重重的“约翰斯赏析” 在前述施坦伯格批评文集《另类标准:直面20世纪艺术》中,收录了施坦伯格论及美国当代著名艺术家贾斯帕·约翰斯的两篇文章,即发表于1962年的《当代艺术及其公众的困境》以及同年发表但后来稍做修订和扩展的《贾斯帕·约翰斯:最初7年的艺术》。在我看来,这两篇文章提供了一个反映前卫艺术对于前卫艺术批评家的困扰以及由这种困扰所产生的批评效应的经典案例,所以值得对其深入剖析,以期对于前卫艺术批评的深层机制有所揭示。 贾斯帕·约翰斯被认为是一个界于抽象表现主义和波普艺术之间的艺术家,有时也被定义为新达达主义艺术家,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崭露头角,其作品充斥着旗帜、靶子、地图、数字、字母等一类平淡无奇的图像或物品(因为有些形象是直接挪用或做出来的,所以称其为物品而非图像),对于一般人而言,它们看起来是如此无趣,甚至让人怀疑它们怎么可能是艺术,即便是批评界,在约翰斯首次个展后围绕其作品的激烈争论也持续了好几年时间(Erdopohl 53)。但令人惊叹的是,他却因为这些作品而获得巨大的成功,成为油画卖得最贵的在世画家。③《纽约时报》的艺术批评家甚至称他为“自杰克·波洛克以来最伟大的美国艺术家”(Reily and Charles 20)。这一巨大的反差不仅让一般公众困惑不已,就连像施坦伯格这样的批评家也曾为之伤透脑筋:“这些画,特别是它们的主题,既激起观众巨大的热情,也使他们惊慌失措。这些主题前所未有地‘陈腐’,过去似乎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单调乏味的东西。他何以要选择如此不讨人喜欢的主题来作画?”(35)。施坦伯格也诚实地向我们透露了1958年他在纽约第一次观看贾斯帕·约翰斯的首个个展时的反应: 我本人的第一反应也很常见。我不喜欢这个展览,泰然自若地认为它令人厌烦。但是它使我感到沮丧,却不知道原因何在。接着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有一个门外汉在面对现代艺术时的典型症状。我对艺术家感到愤怒,就好像他请我去吃饭,却让我吃一些根本不能吃的东西,便如亚麻布和石蜡。我对某些朋友装出一副很受用的样子感到生气——不过带着一丝不安,也许他们真的喜欢?因此我对自己如此麻木,在整个参观过程中出尽洋相,感到更加不快。 与此同时,这些画一直萦绕在我脑海里——使我不安,令我沮丧。每念及此,我都感到强烈的失落感或被剥夺感。(27) 这段文字在我看来称得上是反映前卫艺术批评心态的金子般的文献。其中的“门外汉”一词是关键,因为正是这个自己居然是个“门外汉”的意识严重地伤害了施坦伯格作为一个艺术批评家的自尊,所以他要么阐明它确实不是艺术,或至少不是好的艺术,要么阐明它不仅是艺术,而且还是意义重大的前卫艺术。施坦伯格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对于约翰斯作品的阐释,施坦伯格是从对其主题的疑惑切入的:“我想不断地质疑这些主题的普通性,看一看它们是如何在他的绘画中发挥作用的”(44)。他列举了约翰斯绘画主题的八个特点,并一一对其进行了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施坦伯格是怎样一点点地发现约翰斯作品之“不同寻常”的意义,从而一点点地克服其“强烈的失落感或被剥夺感”的。而我们要做的,就是紧随其后以探讨这些分析是否言之成理。 1.“不管是物体还是符号,它们都是人造物”(施坦伯格44)。 施坦伯格认为,约翰斯之所以选择人造物,其目的是与模仿艺术彻底地分道扬鏣,因为“街道与天空——它们只能被模仿(simulated);但是一面旗帜、一个靶子、一个数字5——这些却可以被制造(made)出来,而创作出来的画所再现的,不过是其物体本身罢了。因为没有一个5的拟像或图像是可以画出来的,只有5这个数字本身才可以画出来”(45)。在我看来,这个论断对于数字或字母一类的图像来说是成立的,甚至对于约翰斯作品中的靶子来说也是成立的,因为它本身的确就是一个可用的靶子,但却不适用于以旗帜为主题的那些作品,因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它们仍然不过是对现实之旗的某种模仿,而非自身就是旗帜,不然的话就太奇怪了。而施坦伯格进一步得出的结论则更不能成立:“20世纪艺术的一个关键问题——如何使绘画成为一种直接的现实——在主题从自然转向文化时得到了解决”(45)。如此理解绘画的现实性完全是一种误解,因为绘画的现实性并非提供一个非模仿的对象,而是绘画性本身的呈现。就拿约翰斯这里所说的数字5来说,只要我们首先看到和意识到的是数字5而不是这个5的绘画构成,那它作为绘画的现实性就是失败的。 2.“所有主题都是我们周围的普通物品”(施坦伯格44)。 首先,施坦伯格认为这些普通物品“属于不偏不倚的、没有等级的、普遍的东西”(5)。然后评论道: 在仔细打量这些标准化了的事物时,我们会对其存在的正常等级感到一种陌生的减速感[……] 所有这一切都慢了下来。由于它们不是工业化流水线上大规模生产出来的物品,因此它们不再屈从于人类使用者的机械状态[……]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改变态度的可能性[……]出于一个奇怪的悖论,这些人造的、独一无二地制作的普通事物,从人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了。 如果说他的作品总是扰人心绪,那或许是因为它们暗示了我们的缺席,不是从一个浪漫主义的荒原上缺席,也不是从一个抽象能量的宇宙中缺席,而是从我们自身所在的位置缺席了。(46-47) 对于这个评价,我要提出的异议是:第一,约翰斯作品中的旗帜不是普通物品,至少相对于其作品中的抽屉和自制晾衣架来说,它给人的感觉具有更多的象征意味,所以即便是在约翰斯自己使用的这些物品之间,等级的不同事实上仍是存在的;此外,如果确如施坦伯格所说,约翰斯总是选择那些日常普通的东西而非像泰姬陵那样不寻常的事物入画,那也正好体现了他在主题选择上的等级意识。第二,说这些普通物品在约翰斯作品中的呈现可能会让我们产生一种态度上的改变,这自然有其道理,但是,即便是艺术家给我们呈现一个非手工的物品,因为观看语境的缘故,我们同样可能产生一种态度上的转变;另外,在传统绘画中,多如牛毛的静物写生画,同样可以让我们产生类似的反应。所以,施坦伯格的做法并不独特。第三,说这些普通物品“从人类的阴影中摆脱出来了”,这一说法在我看来颇为费解;因为正如施坦伯格所说,约翰斯这些普通物品的特征在于可制造性,约翰斯的作品体现了“从自然向文化的转折”,那又何谈“从人类的阴影中摆脱”? 3.“所有主题都拥有一种常见的形状,这一点不会改变”(施坦伯格44)。 通过这一点,施坦伯格想要说的是约翰斯在其作品中所使用的物品都是现成品,没有对它们进行任何变形或设计的处理,也就是说,拿来就用,顺其自然: 在贾斯帕·约翰斯的画里,常规的意义从来没有被嘲弄。也没有用愤怒、反讽或唯美主义的态度来改变他所转录的形状。没有任何东西令人想起大多数富有原创性的达达主义作品那种反复无常、故意离题或杂乱无章的东西。在他的所有主题里,约翰斯都承认一种前结构的形式,就像一个艺术家正式接受人体解剖那样。(48) 施坦伯格因此而称约翰斯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不明白这种拿来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在此意味着什么。是不是一成不变地挪用现成品就是现实主义?是不是这种挪用就是一种完全摆脱了主观任意的客观?很不幸的是,正如施坦伯格本人所讲,约翰斯告诉他说“之所以喜欢这些模板,是因为他们不怎么像艺术”(50)。这难道不仍然是一种偏好吗?而且,执意地要在艺术与非艺术之间进行区分,这不就是关于物品的等级意识吗?所以,事实情形是,约翰斯选择了这样的“现实”而非那样的“现实”,那么,怎么能说他的方式是“最实在的现实主义”呢?而更为关键的是,强调所谓的现实主义在这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施坦伯格仍然纠缠于我们在第一个主题探讨里指出的那个误解,即把绘画的现实性视为非模仿的现实物而非绘画性的呈现。 4.“它们要么是整体的现实,要么是完整的系统”(施坦伯格44)。 施坦伯格的意思是说,约翰斯的作品所呈现的东西,要么是一个单一的东西(例如一个数字,一个靶子或是一块遮阳板),要么是一个可能性的完整的集(例如美国国旗、地图)。对此,施氏是这样理解的:“由于他的对象不是从特殊的视点观察到的,因此这里不存在一种有意义的碎片得以孤立出来的思想立场。没有党派性。他的系统或现实的完整性暗示着艺术拒绝推广他主观的立场。”这段话里的逻辑是相当奇怪的,因为它的意思是,只要一个艺术家呈现了单一或完整的事物,那么他就是没有立场的。而这一点其实也马上就被施坦伯格所提到的两件“例外”作品(《有四张人脸的靶子》和《带石膏模型的靶子》)所反驳。这两件作品都有非完整的人体部件,按照施坦伯格本人的理解,“主题仍然是完整的靶心,那些解剖碎片只是为其提供强调性的衬托而已”(52)。既如此,又怎么能说约翰斯是没有立场的呢? 5.“它们倾向于限定画作的形状和向度”(施坦伯格44)。 对此施坦伯格是这样解释的:“在约翰斯的作品里,‘内在框架’具有绝对的驾驭能力,无论被刻画的图像是旗帜、靶子、字母、书籍、画布或是遮阳板”(55)。施坦伯格认为,由于选择这些被制作的实物进入画面,画作的外框大小就由这些实物所自然构成而不随画家的主观所左右。在我看来,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这些所谓被制作的实物,如果是现成品(如书籍、遮阳板),大小虽固定,但仍然有赖于艺术家的选择和使用;如果是被制作的(如旗帜、靶子或字母),它们的大小就是由艺术家来决定的。所以,不存在作品的大小由这些所谓实物的“内在框架”来决定这回事情。以约翰斯的作品《坦尼森》为例,施坦伯格的解读就难以让人认同。第一,施坦伯格认为画面底边组成坦尼森名字的罗马字母确立了画的宽度。但我们完全可以认为约翰斯是在完成了作品的主要部分之后,才以底边长为限来安排这几个字母的,至少在我看来,这更有说服力。事实上,该作品的宽度是由约翰斯选择用来拼成作品其余部分的两副独立的担架面板所决定的,而这种选择在我看来,仍是一种主观的外部决定。第二,施坦伯格居然在这部作品里读出了这样的意味:“由于某种原因,我觉得,人们还能感觉到这些简单做法的步骤;缓慢、庄重的姿势,就像在一个不知名的葬礼仪式上,床单略微倾斜的两侧产生了一种高大墓碑的感觉”(56)。我们无权要求施坦伯格不能产生这样的感受,但毫无疑问,期待别人也有同感恐怕没有什么道理。 6.“它们是扁平的”(施坦伯格44)。 施坦伯格就此想要强调的是约翰斯的作品不再转化为一种媒介的特点:“油彩就是油彩,数字就是数字,但其中的每一个都只是它自身。你还可拥有各种涂了油彩的物品,但是你无法拥有一片涂上了色彩的风景,因为其中风景成为伪造的东西,而油彩则成了掩饰物。(59)”在另一处,施坦伯格以《有四张人脸的靶子》为例评价道:“在约翰斯的画里,人们感到了错觉的终结。油彩的处理不再被当作一种转化的媒介[……]平面便是平面,坚实性则是三维的,这就是本案的事实,不管它是不是艺术。不再有变形(metamorphosis),也不再有媒介的魔术。在我看来,这是绘画的死亡、突然断裂、道路终绝”(28)。而在我看来,这既不符合我们观看约翰斯某些作品的直观感受(如《地图》),也不符合施坦伯格本人对约翰斯作品的解读,因为他总能从这些他称之为非媒介的作品里读出那么多的意味——以他对《遮阳板》的解读为例:“遮阳板与基底的画布一起,散布着油彩本身,这些油彩难得地富有大气的氛围,而且可以产生深度错觉。这成了一个夜晚的空间,闪烁着从未知的源头射出的白光,就像升空而后落下的烟火在半空形成的烟雾”(63)。 7.“它们通常是无等级的,这允许约翰斯维持一个均等质量的画面区域,而不需要强调或突出什么”(施坦伯格44)。 施坦伯格评论道:“在约翰斯的图画世界里,所有的成员都处于民主平等的状态。没有任何一个部位会以另一个部位为代价突现出来。图像的每一个部分都趋向于画面,就像所有的河流都归于大海一样。油彩有时候会有波痕,有时候也有意外之笔,但都像水平面那样公平;人们可以设想,任何一部分都可以在任何一点上取代另一部分”(63-64)。这个论断是无法让人认同的,尤其是最后一句话;因为事实上很简单,如果可以用画面上的任何一部分取代任何另一部分的话,我们完全可以据此得到完全不同的画,而我们能说,这幅完全不同的画还和原来的画是一样的吗?施坦伯格还进一步说:“换言之,没有一个人可以指出一样特殊的东西,或许正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场”(64)。很可惜,这些强制命名式的话语既没有逻辑支撑,也没有可诉诸他人共鸣的直观体验。 8.“它们可以与隐忍而不是与行动联系在一起”(施坦伯格44)。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就这个主题特点而言,施氏所谈的居然是约翰斯作品的象征意味!其表述则像一位善感的诗人: 约翰斯的象征主义也许不那么明显,但是忽略他图像中的象征意味的变量,要么是疏忽,要么是教条主义。因为他所选择的物品显示了一种独特的偏好:让事物发生。除了认知意义外,一面旗帜什么也不是。一个靶子是用来瞄准的;一本书是为了被打开的,字母与数字则是用来被打乱的,遮阳板是拉下的,抽屉填满了东西却关闭着。(65) 施坦伯格进而总结道:“他的主题是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画家所拥有的意图的敏感载体”(65)。既然如此,他此前怎么能说约翰斯的作品是非媒介化的呢?对约翰斯作品的这种象征意味的解读在以下这个总结性的陈述里更加煽情: 我发现约翰斯早期的所有绘画,在其主题的被动性及穿越时光之隙的缓慢绵延中,都暗示着一种永恒的等待——就像面朝墙壁的图画等待着被翻过来,或是那个空荡荡的衣架等待着有人来晾衣服一样。不过,这是一种无所期待的期待,因为这些物品,如约翰斯所呈现的那样,并不认可任何生命的在场;它们只是人类缺席于人造环境的符号而已。(72) 特别注意这段话中的“符号”一词!因为既是符号,就不可能是非媒介化的。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一下施坦伯格对约翰斯作品的八个主题特点的分析了。在我看来,可以归结为三点:(1)绘画的现实性。这是第1和第6个主题特点分析想要强调的东西,但前者强调的是绘画对于一个非模仿物的呈现,后者强调的是绘画非媒介化的真实。而据我们的分析,前者是一种对于绘画现实性的误解,后者又被施坦伯格本身的分析所否定(参第6和第8个主题特征的分析)。(2)约翰斯作品主题呈现的无主观色彩的客观(第2、3、4、7个主题特点的分析),而据我们的分析,这个论断并不成立。(3)实际上奠基于第2、3、4、7个主题分析之上的约翰斯作品主题的所谓被动性的意义,即施坦伯格所谓“人类缺席于人造环境”。而这一点,除了视其为施坦伯格个人的善感性领悟,我们还能说它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关于施坦伯格的“约翰斯赏析”的结论,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施坦伯格因为约翰斯作品而产生的焦虑而分娩出的批评阐释不仅漏洞百出、自相矛盾,而且充斥着善感性的过度表达?有意思的是,施坦伯格本人似乎早就料到了我们的这番质疑,并且备好了“自我拆台”的答辞: 我所说的——是可以从他的画作中看到的,还是人们赋予它们的?它与画家的意图吻合吗?它与其他人的经验相符吗?我的感觉正常吗?我不知道。我明白这些画作看上去并不必然像是艺术,因为艺术向来被认为解决了远为困难的问题。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不是艺术,是否伟大或优秀,会不会升值。无论过去我拥有什么样的看画经验,这种经验似乎都有可能既是一种障碍,也是一种帮助。我被迫评判,比方说,塞进一张画布里的抽屉的审美价值。但是我曾经看到过的事物中没有任何东西教会我该如何作出评判。在可行标准缺席的情况下,我孤军奋战,得自行评判这些画。我用于这些画的评判的价值,将考验我个人的勇气。在这里,我能够发现自己是否有能力来经受一种崭新经验的冲突。我是在通过过度分析来逃避这种经验吗?我偷听过别人的谈话吗?试图在这类艺术中看出某种意义来——这只是表明我自己身上的某种东西,还是一种本真的经验?”(31) 这段话的真诚令人刮目相看,而且,它似乎让那些试图批判施坦伯格的人感到无趣——人家都不打自招了,你还能说什么呢?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掏心窝子”的表白并不能为施坦伯格起到挡箭牌的作用,因为无论如何,一个人的表述总不能自相矛盾,就拿上面提到的他关于约翰斯作品所谓“不再有媒介的魔术”这个说法,就与他本人在约翰斯作品中读出来的那么多文学或哲学内涵的表述前后不一。事实上,这个说法也与施坦伯格的祖师爷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的路子相悖,因为图像学的最终诉求是图像的意义及其背景,这就决定了在某种意义上图像必须是“媒介的魔术”。 当然,施坦伯格还有更为高明的辩护,当再次提到自塞尚以来的艺术对于批评的挑战时,他这样写道: 与戈尔凯郭尔(Kierkegaard)的上帝一样,这样的作品以其扰人心绪的荒谬扰乱我们,贾斯帕·约翰斯几年前呈现在我面前的也是如此。它要求作出决定,从中你能发现自己的某种品质;而这一决定,用戈尔凯郭尔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信念的飞跃”。与戈尔凯郭尔的上帝一样,他要求阿伯拉罕在对每一个道德标准的背离中都必须做出牺牲;与戈尔凯郭尔的上帝一样,这些画作似乎是任性的、残忍的、非理性的,要求你无条件的信仰,却不允诺任何回报。换言之,将自己呈现为一种厄运,正是原创的当代艺术的本质所在。而我们这些公众,包括艺术家在内,应该为自己身处这样的困境而感到骄傲,因为没有别的东西像它那样真实;艺术毕竟被认为是生活的镜子。(31) 最后一句显得有点莫名其妙,它不像出自一个现代艺术批评家之口,但这不是关键,因为跃然纸上的语调的“悲壮”感才是这段话想要表达的东西:“要求你无条件的信仰,却不允诺任何回报。”这就是克尔凯郭尔笔下的信仰骑士亚伯拉罕所面临的处境。这非常有意思,施坦伯格作为一个前卫艺术批评家的悲壮感在与信仰骑士亚伯拉罕的想象性比拟中达到了巅峰。在《恐惧与颤栗》中,克尔凯郭尔饱含激情地颂扬了那个从小就让他迷恋不已的信仰骑士亚伯拉罕,通过一系列繁复的论证他要为之辩护的是,亚伯拉罕遵从指令向上帝献祭亲子的行为不仅没有伤天害理,而且还是一种比伦理更高的伟大的信仰激情的表现。然而,除了不断地重复这一断言外,克尔凯郭尔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说辞,倒是以下这些句子所勾画的图景却令不少人为之动容: 当一个人走上了悲剧英雄那艰难曲折的道路,这里会有许多人可以给他忠告;可是对于走了信仰的羊肠小道的人,却无人能够给予忠告,因为无人理解他。(克尔凯郭尔43) 就当我们在狂欢节的群宴上以嚣声来骚扰天堂,并以为这就走上了与信仰的骑士同一条道的时候,那信仰的骑士却在寂无人声的旷世间,肩负着可怕的责任独自前行。(克尔凯郭尔55) 在我看来,这两段话中以“羊肠小道”和“寂无人声的旷世”作为背景所呈现的信仰骑士的孤绝超卓的悲怆形象,是克尔凯郭尔为亚伯拉罕所做的最有效果的辩护,但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看到,克尔凯郭尔所诉求的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感染力罢了,也就是说,他所采用的竟然是一种美学的手段。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施坦伯格在对贾斯帕·约翰斯进行阐释之前对于自己作为一个开路先锋充满了自觉意识的一段话: 1958至1961年这四年间的形势揭示了艺术的某种本质特征。一件艺术品终于不再像一张小小的明信片那样上面盖着标示其价值的邮戳。尽管有其物性的一面,艺术品的价值却更多地被认为是对想象生活的一种挑战,而“正确”地思考或感知艺术品的方式,则完全没有。除了困惑或憎恨,人们如果还想感知到别的东西,他们的思想与感受的既定习惯就必须被清空。长期以来艺术界洪流的流向一直不明,要么被拦蓄起来,要么泛滥而出,直到经过一些冒险的批评家多次试切(trial cuts),某些河道才得以成形。最后,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约翰斯赏析”的宽阔河道——尽管它仍然弯来弯去——终于可以航行了。(40) 很明显,我们可以看到施坦伯格为其作为一个前卫艺术批评家的辩护竞与克氏所为如出一辙,其效果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施坦伯格批评的症结及可能性出路 以上分析探讨几近繁琐,但却是本文刻意为之,其目的在于通过对一个批评样本的详尽解剖,以获得对于前卫艺术批评之操作机制的近距离感知。现在,我们再回顾一下施坦伯格的“约翰斯赏析”所呈现给我们的东西:被误解的绘画现实性观念、个人化的诗性感悟以及批评姿态的悲壮感。然后我们看到,抛开属于施坦伯格的个性呈现但无助于艺术批评之有效阐释的后两个因素,构成施坦伯格批评之技术支撑的第一个因素其实仍然完全处于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理论的阴影之下。 这种主要由机械的形式主义分析加上主观随意性的感悟表述的批评方法,对于施坦伯格来说并不是偶然的,其实在《另类标准:直面20世纪艺术》中的另一篇重磅级论文《〈阿尔及利亚女人〉与一般意义上的毕加索》里也有运用。毕加索创作的一系列有关阿尔及利亚女人的绘画也曾让施坦伯格感到困惑,因为他想不明白毕加索何以对这个题材情有独钟,恋恋不舍。最终,用了100多页的篇幅,在对毕加索的十五幅阿尔及利亚女人画进行了对于读者来说堪称精神折磨的极其繁琐的技术分析之后,施坦伯格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毕加索最终想要实现的乃是全方位地(即从正面、侧面、反面同时)再现人体这一目标,而对于这一目标的追求,不仅是西方艺术,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艺术的再现传统的现代延续,而且也和毕加索个人的色情冲动相关。如此一来,这个分析就达到了所谓主题分析和形式分析的有机融合。在我看来,这个结论的技术部分给人的感觉恰像那句“高射炮打蚊子”的俗语,而以毕加索的色情冲动来解释这个技术结论,则近乎一个理论的玩笑。 这一批评方法还在其名篇《另类标准》一文中用于阐述其所谓的“平台式画面”理论。施坦伯格认为,有一条贯穿传统绘画,甚至直到立体派和抽象表现主义的中心线:“绘画再现一个世界的观念,这是某种世界空间(worldplace),它可以从画面上读出与人类的直立姿势相一致的东西。画作的上部对应于我们头部所在的空间;而其底边则对应于我们的双脚所站的地方”(105-07)。而在1950年前后,以罗伯特·劳申伯格和杜布菲的作品为代表,“绘画发生了某种新变化[……]这些画不再模拟垂直区域,而是神秘的平台水平面。”这一画面“从垂直向水平方向的倾斜”则被施坦伯格视为“艺术主题中最激进的转移,即从自然向文化的转移”(107-08)。这就是施坦伯格的“平台式画面”理论!以严肃的艺术史家眼光对于绘画主题之历史演变所做的严肃的学术论断!然而在我看来,它完全经不起推敲:第一,我们可以从传统绘画中找到大量的非直立姿势视线所形构的画面;第二,说对垂直区域的模拟就是自然,而对于平台水平面的模拟就是文化,这一区分毫无道理(因为按照这套荒谬的理论,直立姿势的视角及所看到的世界是自然的,而躬身或低头的视角及所看到的世界就是文化的);第三,1950年以后的绘画,也仍然可以找到大量的所谓模拟垂直区域的绘画,至少在量上不会出现施坦伯格仅在几个艺术家的身上所发现的那种绘画主题的演化趋势。其实,这几条质疑的理由,以施坦伯格的智力来说,难道会想不到吗?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或许,在理论场上也会出现“利令智昏”的现象?不然,该怎么解释呢?这些话可能过于尖刻,但是前卫艺术批评中这种理论建构上的粗糙和随意确实令人不敢恭维,也让人对前卫艺术批评的学术品格感到沮丧和忧虑。 施坦伯格之所以无法走出批评的怪圈,其根本原因在我看来是因为他仍然像他所批判的格林伯格一样,也未在根本意义上理解现代绘画之自我确证的含义,这就决定了他对于格林伯格形式主义理论的批判仅仅属于技术层次的批判,而非观念层次上的根本动摇,也决定了他在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理论背景下提供的批评阐释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至于究竟如何理解现代绘画的自我确证,国内艺术批评家吴兴明先生的洞见似乎终于捅破了那层挡住了格林伯格视野的窗户纸:“在康德、黑格尔,所有现代事物的自我确证归根到底都是主体性原则的产物,是主体性的自我确证或自我确证的对象化,因此门类艺术的现代性自我确证归根到底是人的自我确证。”因此,“在现代语境中,艺术归根到底是人的感性合法性的自我证明(审美现代性)。这是‘人义论’的必然要求。与理性以反思为根据的自我确证不同,感性的自我确证要求感性价值的独立自足及其实践性的肯定和创造。因此,开创新时代的感性形式,清除、抵制理性、意义、宗教、象征对感性的抽空、异化和统治,抵抗体制、惯例对感性的藩篱与强制,不断保持感性的新锐度、活力度,抵制物感的惯习化、僵硬化、空洞化——简言之,对不断生长着的活生生的现代感性之永无止境的创造和推进,就形成了现代艺术包括现代美学自我确证背后的真正价值诉求”(7-8)。很可惜,无论是提出现代绘画之自我确证的格林伯格本人还是批判格林伯格的施坦伯格,都没有理解到这个层次,从而导致他们未能对吴兴明先生所说的印象派以来的西方艺术中的“物性凸显”(即现代性感性的自我确证)有所感知和发现。就拿贾斯帕·约翰斯的作品来说,其重点并不在于施坦伯格所误解的那种绘画现实性(即遮阳板一类现成品的挪用、靶子一类的制作物或像数字、字母一类非模仿物的呈现),更不是他所谓“人类缺席于人造环境”的荒凉感的表达,而是基于新型画法基础上的物感设计。以《旗》为例,“虽然画中之旗确有美国国旗的形状和颜色,然而它是一幅画;不是随便什么样的画:而是以蜡画法画成——多种质地的亮蜡叠加,但薄到可以看见作为底衬的报纸。旗所显露的是作为一幅画的紧密的物质呈现”(Bass 45)。或许这样理解才是正确的方向,也才能说明为什么贾斯帕·约翰斯的作品直到今天仍受追捧。 《另类标准》一书的译者沈语冰先生曾在译后记中语重心长地说道:“我以为,缺乏形式分析和图像的训练,是我国美术批评这个学科始终上不去的根本原因。”而“奇怪的是,国内的美术学院(尽管有批评专业或策展专业)似乎从来不教如何做批评”(转引自施坦伯格501)。忧切之情令人感动,其译介之功也堪可称道,但我也有一种担忧,就是我们在接受西方的这些理论时大多亦步亦趋而无起码的质疑和反思,邯郸学步,反倒忘了自己的东西。所谓争论才是最好的学习,这篇看似不敬的批判文章,就算是一个我们学习和研究施坦伯格的起兴吧,如果能够引发更多更有价值的探讨则是本文的期冀所在。 ①本文所谓的前卫艺术,主要是指二战以后抽象表现主义以来的西方现代艺术。 ②为求辩证,读者也可参看国内批评家、自称“不折不扣的格林伯格的辩护者”的王南溟先生的著作:《现代艺术与前卫——克莱门特·格林伯格批评理论的接口》(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③其作品《错误的开始》(False Start)于2006年拍出了8000万美元的高价。参见: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June 25,2014.Wikimedia,June 29,2014〈http://en.wikipedia.org/wiki/Jasper_Joh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