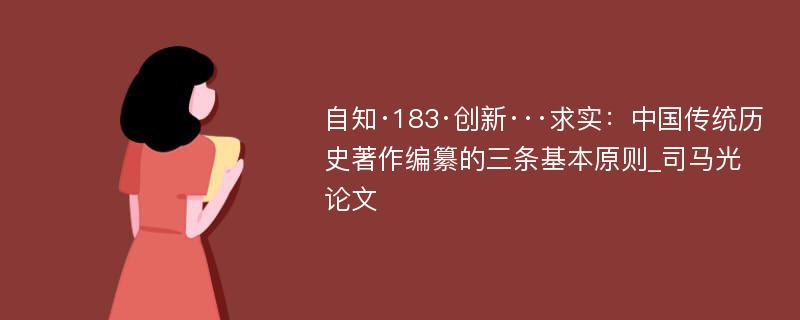
资治#183;创新#183;求真——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三项基本原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项论文,中国传统论文,基本原则论文,资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320(2001)04-0025-05
中国传统史著何以连绵不断,汗牛充栋,内容繁富,形式多样,社会功能巨大?就是因为编纂史著坚持了资治、创新、求真的三项基本原则。资治原则是编纂传统史著的灵魂,创新原则是编纂传统史著的生命,求真原则是编纂传统史著的骨骼,三项基本原则互相依赖,共同促进了传统史著的编纂,使传统史著为封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对封建社会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本文试图探讨一下中国传统史著编纂的三项基本原则及其相互关系,以期为现代史学论著的编纂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资治原则:传统史著编纂的灵魂
资治原则就是编纂史著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也就是要通过历史著作的编纂为政治提供服务。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史学著作没有灵魂就没有生命。因此资治原则对中国传统史著的编纂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国最早的史学著作就是从服务于政治的文字中编纂出来的,诚如柳诒徵先生在《国史要义·史源》中所说:“由赞治而有官书,由官书而有国史。”唐太宗李世民在诏书中说:“大矣哉!盖史籍之为用也。”[1](卷81《修晋书诏》)资治原则在编纂史著中主要表现在借鉴和教化两个方面。
一是借鉴。从历史的治乱兴衰中,总结经验教训,寻找治国方略,以资治道和推测未来,为统治者的决策提供依据。《诗·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氏。”就是说商代要以夏代的兴衰成败为借鉴。班彪在续《太史公书》(《史记》)而作《后传》时,曾“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他认为“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以观前,圣人之耳目也”,把历史文献作为圣人治国的耳目来编纂。司马迁编纂《史记》是为了“述往事,思来者”,以“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2](卷18《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稽其成败兴衰之理”,都是为政治提供借鉴。东汉荀悦在编纂《汉纪》《目录》时说,编纂史著要“综往昭来”,记载“明主贤臣,规模法则,得失之轨”,“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让统治者从中得到借鉴。班固编纂《汉书》时,注重“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还通过篇后的“赞曰”,论是非寓褒贬,以使皇帝“明鉴戒”,从而明显地体现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唐代李渊在命萧踽等人修六代史诏中明确地提出了为政治提供借鉴的编纂原则:“考证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1](卷81)杜佑在《通典·自序》中提出编纂的原则是:据“往昔是非,可为来今之龟镜”,“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详古今之要,酌时宜可行”,就是史著要“经邦”“治国”,为政治提供服务。北宋司马光主持编纂的《资治通鉴》则一语破的,道出了编纂的政治原则,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得很清楚:“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害非,是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要“穷探治乱之际,上助圣明之鉴”。元朝《进金史表》说:“国可灭史不可灭,善吾师恶亦吾师。”《进宋史表》说:“鉴于有夏,鉴于有殷,乃臣子告君之道。”明朝《进元史表》中说:“因已往之废行,用作将来之法戒。”这都是把政治借鉴作为编纂史著的原则。明清之际,王夫之等人提出了“经世致用”的编纂史著原则,引古筹今,鉴往训今,把历史著作的编纂与政治借鉴原则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
二是教化。通过历史著作的编纂,褒奖真善美,贬抑假恶丑,“兴孝悌而正风俗”,用礼仪或封建伦理原则评判历史事件和人物,为人们提供伦理道德规范,使史著蕴含中华民族的精神底蕴和众多历史人物的人格魅力,教化人民,赞助政治。《春秋》用道义发挥政治教化的功能,司马迁认为:“春秋者,礼仪之大宗也。”[2](《太史公自序》)《春秋》编纂的原则是:“崇善而抑恶”,“昭明德而废幽昏”。《汉书》的编纂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评价历史,一味地用历史去论证和阐释宗法等级制度和君主制的合法性与永久性,用班固自己的话说就是:“旁贯《五经》,上下洽通”,“纬六经,缀道纲”。使《汉书》成为明天道、正人伦的儒家伦理教科书。东晋袁宏编撰《后汉纪》就是要阐扬“名教之本”,以“弘敷王道”,“通古今而笃名教”,把名教的宣扬作为编纂的根本原则。范晔在编纂《后汉书》时,也是以阐扬礼教伦理,序定专制人伦为原则的。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1说,《后汉书》“贵德义,抑势利,进处士,黜奸雄,论儒学则深美康成,褒党锢则推崇李杜,宰相多无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见采,而唯尊独行”。范晔极力表彰党人不畏强暴,蹈仁赴义的精神,盛赞杨震“抗直方以临权枉,先公道而后身名”[3](卷54《杨震传》),批评才华平庸的胡广“饰情恭貌”“据正或桡”,却官越升越快[3](卷44《胡广传》)。唐太宗御撰《晋书》一味用历史阐释君臣纲伦,特别推崇孝道,反映在编纂内容上就是不厌其烦地罗列所谓“孝悌名流”,编为《孝友传》,搜集所谓的“贞烈守节”,编为《列女传》,又特辟孝父忠君的《忠义传》。在杜佑编纂的《通典》中最能体现“教化”精神的“礼”,篇幅几为全书的1/3,而对食货、选举、职官、兵、乐、刑等的论述也无不围绕着“礼”展开。宋代编纂史学著作也以立德为先。欧阳修编纂《五代史记》(《新五代史》),就是以史解经,用史实弘扬三纲五常,他立志效法《春秋》,“一本于道德”,试图通过五代史的编纂,重建“人伦之本”,“臣子大节”。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也完全以儒家伦理道德评价历史事件和人物,凡君相之举措,有足以厚风俗、成教化者,必然深嘉之;其坏礼制、背经术者,则深惜之。元、明、清各朝编纂史著“以表彰道学为宗”,直言不讳地宣称要“先理致而后文辞,崇道德而黜功利,书法以之而矜持,彝伦敕是以匡扶”[4](《进宋史表》)。把表彰道学,崇尚道德作为史著编纂的最高原则,“余事皆不堪措意”[5](卷46)。《道学传》、《忠义传》、《奸臣传》、《逆臣传》连篇累牍,正史、别史尽是鼓吹六经、羽冀名教之作,历史著作完全成了伦理道德的说教。
二、创新原则:传统史著编纂的生命
没有创新就没有生命力。中国传统史著编纂坚持创新原则,根据时代的特色和社会的需要,不断求异创新,另辟蹊径,或创造新的编纂方法,或补充新的内容,或提出新的历史见解,极大地丰富了史书编纂的形式和内容,扩大了历史著作论述的范围,促进了人们对历史面貌的整体性认识,更加全面地、客观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使传统史著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充分发挥了史学著作的政治教化和启迪智慧的功能。创新原则在传统史著编纂中表现在编纂方法、编纂内容、历史观点三个方面。
(一)编纂方法的创新
传统史著编纂方法主要从史体和史例两方面创新。史体是史著内容的外部表现形式,史例是史著内容的内部结构形式。通过形式的创新,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历史内容,更好地总结封建政治的成败规律。
中国最早的史著体裁为编年体,孔子《春秋》发凡起例,它按照年、时、月、日时间顺序记事。《左传》以《春秋》为纲,记事丰赡,不仅有精彩的记言,而且有记一件事的始末原委的,如僖公二十三年记晋公子重耳流亡19年的经历。《春秋》首创“属辞比事”,即规定一些义例来约其文辞和编排史事,这就是后人说的“春秋笔法”,用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到汉代编年体史著又推陈出新,荀悦的《汉纪》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的方法,以人为本去编排史事,记载了许多历史人物和重要事件,突破了时间界限,根据需要有时补叙前因,有时备述后果,或兼及同类人和事,建立了编年断代体的规模。宋代司马光“因丘明编年之体,仿荀悦简要之文”,编纂了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资治通鉴》,主要采用“编年附传”的方法,人物首出交待籍贯世系,死时交待生平事迹和道德人品,增强人物的整体性。还采用追叙方法、并叙方法、预叙法,保持历史事件的完整性。扩大了编年纪事的范围,弥补了编年体事以隔年的短处,使之成为最有代表性的编年体史著。
纪传体是继编年体之后的重要史书体裁,它以人物为中心,分为本纪、列传、世家、书、表,各自为用,交织配合,是有意识创作的一个完整的编纂体系。正如刘知几在《史通·二体》中所说:“‘纪’以包举大端,‘传’以委曲细事,‘表’以谱列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此其所以长也。”《史记》编纂的义例有“类别区分”,即类叙法,首创“互见法”,就是以参错互见来组织材料,详此则略彼,使有限的笔墨能容纳丰富的内容。班固易纪传体通史为纪传体断代史,把《史记》创建的纪、传、表、志体进一步完备,特别是断代为史,更突出了一代帝王为中心的封建史观,被历史统治者奉为正史,“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6](卷1)。纪传体把事件、制度、人物和历史进程的记载融为一体,扩大了历史著作记述的范围。
典制体是唐中期杜佑开创的新的史著编纂形式,它从会通和分门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纪传体史书的书志部分,写出了第一部典制体通史——《通典》,从而突破了编年、纪传二体的格局。每事分门别类,举其始末,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废置,从而探讨典章制度对为政得失、民族关系、社会进步、历史进程的影响,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郑樵编纂的《通志》“经纬异制,自有成法”,把《史记》、《汉书》等书的“合传”、“附传”改为以朝代为纲,按先后次序编排的“分传”形式,其中的《二十略》贯彻了“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的原则。马端临编纂的《文献通考》首创文、献、注的撰述方法,“详博综贯,尤便于用”[7]。
宋代袁枢编纂的《通鉴纪事本末》,首创纪事本末的史著体裁,它分门别类,每事各详其起讫,自立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使“前后始末,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所未见也”[5](《通鉴纪事本末》)。
传统史著编纂方法的创新,还有学案、表、图、史论、史评等体。各种体裁不断发展创新,相互融合,共同铸造了中国传统史著多姿多彩的表现形式,至今仍有鲜活的生命力。
(二)编纂内容的创新
首先,我们看二十四史内容的创新。《史记》所载内容在先秦史籍《尚书》、《竹书纪年》、《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的基础上补充了大量的新资料,司马迁首创了学术史、民族史、经济史、工商史等的编纂。班固《汉书》的《艺文志》、《五行志》、《刑法志》、《地理志》、《百官公卿表》、《古今人物表》、《外戚恩泽侯表》,范晔《后汉书》的《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等传,司马彪《续汉书》中的《百官志》、《舆服志》,《晋书》的《载记》、《忠义传》、《孝友传》、《叛逆传》,《宋书》的《恩倖传》,《梁书》的《诸夷传》,《魏书》的《官氏志》、《释老志》,《隋书》的《诚节传》,《五代史志》的《经籍志》,《新唐书》的《卓行传》、《奸臣传》、《叛臣传》、《逆臣传》,薛居正《旧五代史》的《选举志》,欧阳修《新五代史》的《杂传》、《死节传》、《死事传》、《一行传》、《唐久臣传》、《义儿传》、《伶官传》、《司天考》、《职方考》,《宋史》的《道学传》,《新元史》的《序纪》、《博尔忽传》、《赤老温传》、《韩林儿传》,《明史》的《七卿年表》、《阉党》、《流赋》、《土司》等,《清史稿》的《交通志》、《邦交志》、《大学士表》、《军机大臣表》、《部院大臣表》、《疆臣年表》、《交聘表》等,都是根据时代特色补充的新的史著编纂内容。
其次,典制体内容的创新。《通典》的内容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门,而《通志》除沿袭其内容外,新增《六书》、《七音》、《校雠》、《图谱》、《金石》、《氏族》、《都邑》、《谥》、《昆虫草木》等略。《文献通考》内容的二十四考,其中十九考参照《通典》而作,《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考为《通典》所无。《清朝文献通考》新增了《外交》、《邮传》、《实业》、《宪政》和《四裔》等考。
最后,我们看编年体内容的创新。《左传》有196800多字,篇幅为《春秋》的10倍,《春秋》犹如事目编年,而《左传》丰腴,补充了大量新的资料,记述了不少生动的历史过程和人物活动。荀悦的《汉纪》虽取材于《汉书》,但也有新资料补充,如,对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领袖铜马的事迹记载就远比《汉书》详细。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虽然取材于正史,但唐五代时期补充了大量资料,远比《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丰富得多。
由上可知,史著编纂内容的创新,不仅有各种类型的人物传记,详尽的历史事件,而且对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制度、民族关系、邻国交往等都有记载,全面地总结了历史智慧。
(三)历史见解的创新
历史著作的编纂必然反映当代人的思想,人类对历史的认知判断和价值判断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思想的变化而不断深入和有新的变化。传统史著从历史的发展中不断总结出可资现实借鉴的新的历史见解,为社会需要提供服务。
先秦的史著认为,凡王朝的兴亡、世间的治乱以及人们的福祸寿夭都是天命决定的。而《左传》对此提出质疑,记载了周内史叔的话“吉凶由人”,而不由天。汉唐期间,天人感应等封建的天命迷信思想充满史著,《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桓谭传》、《张衡传》、《扬雄传》等中对谶纬迷信思想提出了批评。唐代杜佑编纂《通典》,取消了自《汉书》以下正史中宣传迷信的《五行志》。他一改过去史著中轻视经济的观点,以食货为首,认为“教化之本在乎衣食”,主张轻徭薄赋。他还对儒学在治国中的作用提出怀疑,儒学虽然是“要道”、“宏纲”,但“每念懵学,莫探政经”,或缺“匡正之方”[8](卷147《杜佑传》)。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客观地分析五行灾异学说,他不同意过去所谓国家兴亡天降祯祥或妖孽的天人感应说,而认为这是事物的反常现象,因此,“不曰妖,不曰祥,而总名之曰《物异》”。历代史家都宣扬张良“从赤松子游”、“学辟谷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断言其非,他说:“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因未超然而独存者矣。”[9](卷11)他明确指出,神仙之术乃“虚诡”之学,“子房托于神仙,是功成身退,明哲保身之术,其智可知也”。对于西汉文景时期,连年减轻租税甚至免缴租税,班固以后史家在史著中都当作惠政歌颂,而荀悦在《汉纪·孝文皇帝》下评论说:“官收百一之税,民收太半之赋,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苛于亡秦,是上惠不周,威福分于豪强也。今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这是荀悦针对豪强横征暴敛逾于国家租税的现实作出的客观评价,可谓至理名言。这些新的历史见解都是根据时代的需要提出的,更符合历史的实际,借鉴价值也更大。
三、求真原则:传统史著编纂的骨骼
传统史著编纂坚持求真原则,用实事求是的态度,采取科学的方法,广泛搜集史料,精审考证和选择史料,保证史料的科学性。秉笔直书,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使史著编纂的内容既确凿可靠,又合乎情理,真实全面地反映历史面貌。求真原则为史著编纂的政治原则和创新原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没有求真原则,资治和创新两个原则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求真原则在传统史著编纂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对资料搜集广泛,考证精审
司马迁的《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取材广泛而博杂,据张大可在《〈史记〉研究》中说,单以《史记》本书考校,司马迁所见古书达102种,还有采用材料而未记其名的。他对史料进行认真的考辨和选择,并在游途中亲自采访和实地考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择其言尤雅者”,“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使《史记》记载翔实,言之有据,成为“信史”,如关于《殷本纪》记载的商代世系经过近几十年来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证明完全可信。班固编纂《汉书》,除了《史记》重复部分外,“自太初以后,又杂引刘氏《新序》、《说苑》、《七略》之词”。《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杜佑《通典》说:“博其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有裨得失进,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这说明杜佑搜集资料是十分广泛的,而且杜佑对资料的考证取舍也相当认真。如:《史记·河渠书》载,“西门豹引漳水溉邺”,而《汉书·沟洫志》说,“史起为邺令,遂引漳水溉邺”。《通典》卷二采用《汉书》记载,明言《史记》记载有误,资料研究表明杜佑采用《汉书》记载是正确的。据张熙侯先生在《通鉴学》中统计,司马光《资治通鉴》引用资料共301种,陈光棠先生在《中国史学家评传》中,在张先生考证的基础上,考证出《资治通鉴》共参考359种书。司马光选择可靠的资料编入,他比前人更进一步的是把各种不同资料的说法和自己选择的理由和盘托出,逐条说明,做了《通鉴考异》30卷。足见司马光对资料选择的审慎态度。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说:“凡叙事,则本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疑传疑者不录”。“论事,则先取当时医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记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史传之非者,则采而录之”。“其载诸史传记录而可疑,稽诸先儒之论辨而未当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则窃著己意,附期后焉”。由此可见,马端临对文献资料采用不仅广泛,而且认真甄别选择,从而得出恰当的历史结论。
(二)秉笔直书,探求真理
传统史著编纂尊重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地记载历史,科学地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编纂史著应“仗气直书,不避强御”,必须“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称赞司马迁《史记》说:“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司马迁热情洋溢地歌颂秦末陈胜吴广农民大起义,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腐败,把陈胜、吴广列入《世家》,比之于“桀纣失其道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作,秦失其道而陈涉发迹”,充分肯定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伟大作用。班固在《汉书·匡张孔马传赞》中对汉武帝以后,公孙弘、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马宫等人以儒宗居宰相位置评价说:“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际见绳,乌能胜其任乎!”这个评论不失实、不偏激,体现了实录精神。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如实记载历史事实,对统治者的丑行不隐讳,如《晋纪》中写贾后的淫荡;《唐纪》中写唐玄宗晚年的奢糜等。他对唐末黄巢农民大起义记载颇详,搜集大量唐书中所未载的资料,歌颂农民军纪律严明,不掳掠百姓,“所过不掳掠,唯取丁壮以益兵”,占领洛阳后“劳问而已,闾里晏然”等。这充分体现了司马光秉笔直录的精神。
传统史著的编纂从历史真实的客观记述中,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为统治者提供科学的借鉴内容。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不迷信天命,不崇拜宗教,重视人事的作用。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中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就是说神也要依人的意志而行,弃民者终为民所唾弃。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评价项羽说:“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他指出了项羽灭亡,不是天意而是用兵之过。范晔在《后汉书·张衡传》中全文引用《驳图谶疏》,对谶纬迷信的虚伪性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具有破除迷信的作用。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说:“未通人理于万一,而遽从事于天,是犹未操舟而欲涉海,不陷溺者,其几矣。”他认为:“为治之要,莫先乎用人。”[9](卷72《明帝景初三年》)他对范缜《神灭论》和韩愈的《谏迎佛骨表》全文存录,具有批判灵魂不灭论和佛教的作用。在卷11中他还指出道教的虚妄:“其讹甚矣”。杜佑在《通典》中认为,唐中叶社会动荡不安的原因:“盖因人事,岂唯天时。”国家的兴衰在于法律制度的得失和政治的优劣。“天下兴衰系于用人”、“天下兴衰在于政治是否清明”、“天下兴衰在于法律制度是否健全和贯彻执行”,这些历史规律的探讨,具有科学的思想价值,为资治原则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综上所述,我们部分地考察了传统史著编纂坚持三项基本原则的具体表现,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史著的编纂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根据不同时代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特点,采用多种编纂形式,记载真实、丰富、具体的历史内容,客观地总结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阐发人生哲理和启迪人们的智慧,使各阶层人都能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和教益,提高人们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生产、人际交往和应付各种事变的能力,增加成功的机会和少走弯路,充分发挥了史著的社会功能。这给我们当代史著的编纂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编纂史著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根据时代的需要,不断创造新方法,发现新材料,提出新的历史见解,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反映时代的要求,探讨历史发展规律,编纂出既具科学价值,又能经世致用的历史著作,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思想文化保证和智力支持。
收稿日期:2001-05-06
标签:司马光论文; 汉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资治通鉴论文; 宋朝论文; 史记论文; 汉纪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历史学家论文; 通典论文; 西汉论文; 左传论文; 东汉论文; 历史学论文; 清朝历史论文; 明朝历史论文; 元史论文; 后汉书论文; 离骚论文; 汉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