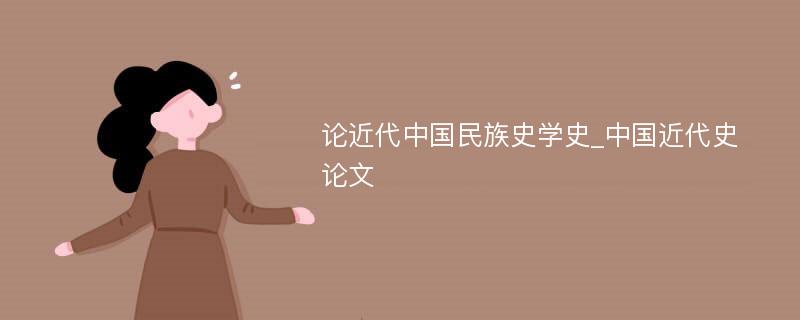
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史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中国论文,近现代论文,民族论文,史学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6)01-0153-07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拉开了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这一时期,面对列强的分裂活动,学术界对边疆民族问题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形成了新的民族史观、民族史撰述方式,中国民族史学也体现了新的功能。从整体上看,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史作为中国民族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民族史学史的基础上,步入了新的发展轨迹,形成新时期的特点。① 一、中国民族史观的变迁 自鸦片战争爆发至民国,政治动荡及外来文化的冲击,促使士大夫群体的民族史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一时期,传统的华夷观逐渐解体,新的民族观、国家观及世界观开始形成并迅速传播。 1.传统华夷观的解体 在历代中原王朝所纂正史及其他史籍中,修史者都从华夏或中国的角度来记述各民族历史,“中国”与“四夷”往往是相对而言的。至晚清,“中国”的内涵发生转变。在接触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强国过程中,士大夫群体开始以新的国家观来看待“中国”。“中国”逐渐成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名称,在地理范围上是指清朝管辖之下的疆域,清廷在外交场合下也认可了“中国”这一称谓。士大夫群体开始从“中国”的角度来撰述民族史,过去与“中国”相对的“四夷”,开始成为“中国”之内的民族。同时,以“中国”为单位叙述历史及民族史的著作不断涌现。 晚清,较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学者开始质疑传统的华夷观,认为华夷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二者可以互相转换。如王韬《华夷辨》云:“自世有内华外夷之说,人遂谓中国为华,而中国以外统谓之夷,此大谬不然者也。《禹贡》画九州,而九州之中诸夷错处,周制设九服,而夷居其半。《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夷狄虽大曰子。固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地之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大,厚己以薄人哉!”②这是王韬在接触西方先进文化后形成的认识。郭嵩焘甚至更坦率地指出,三代之际,中国礼乐教化发达,“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而今西方国家的富强文明程度远超中国,“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③。 晚清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籍大量出版,这些著作的编纂理念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传统的“四夷”观念,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外国史略》《坤舆万国全图》《全地万国纪略》《万国通鉴》等。这些书籍的传播,促使人们在观念上打破了以中央王朝为中心的华夷史观,人们逐渐认识到西方还有很多国家,这些国家具有发达的文明,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蛮夷之国。 2.新民族史观的确立 在传统的历史记述中,修史者对民族意义上的人群称为“民”“族”“种”“部”“类”,或称为“族类”“族部”“部落”“四夷”“外国”“藩部”“属国”等,这些表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民族观念。晚清时期,“民族”一词通过梁启超等学者由日本译介而来,开始在学术著作中出现并逐渐普及。④“民族”一词与当时中国特定的反清、反帝等社会形势联系在一起,并深化了其内涵。经过学界的论辩与探讨,历史上的区别不同人群的表述开始统一到“民族”这一词语上,并出现了“民族史”这一史学的门类。 晚清,新史学开始孕育,其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连续发表了多种关于中国民族史的论述,主要有《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国历史上民族之分类》《中华民族之研究》等。在这些著作中,梁启超开始明确地把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区分了民族与种族、民族与国民等概念,强调了“民族意识”在民族形成和归属中的重要作用。以“诸夏”为例,梁启超论证了中华族自始是多元结合的观点:“吾族自名曰‘诸夏’,以示别于夷狄,‘夏’而冠以‘诸’抑亦多元结合之一种暗示也。”⑤梁启超认为:“我中华族,本以由无数支族混成,其血统与外来诸族杂糅者亦不少。”⑥尽管他对民族同化的观点和分析并不准确,如他认为:“先秦以前,中国本土除华族以外,还有八族,即苗族、蛮族、蜀族、巴族、氐族、徐淮族、吴越族、百濮族。最后除苗、濮二族外,其余六族皆已同化于中华民族。”⑦但他的论述起到了为新的民族史学奠基的作用。 民国建立后,“民族”不再是历代的四夷或清代的藩部,开始作为平等的政治单元参与国家政治活动。“五族共和”、民族平等观念在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中得到倡导和落实。同时,西方“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和影响,也促使当时的学术界从构建“民族历史”的角度来增强中国凝聚力,以防止国家的分裂。如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一书中表述了自己的民族进化史观,他说:“中国者,合六大族组织而成,中国之历史,实六大族相竞争相融合之历史也。”⑧林惠祥在其所著《中国民族史》中说:“中国诸民族之主干实为华夏系。”“华夏系不特为今汉族之主干且亦为全中国民族之主干。”⑨ 3.马克思主义民族史观的形成与发展 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和共产党人,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到史学研究之中,这也影响了当时中国民族史的撰述与研究。如李大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具体的民族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先后在《甲寅》上发表了《新中华民族主义》《大亚细亚主义》等文章。⑩ 经过官方与学界的共同推动,中华民族观念逐渐深入人心,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符号。在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地论证自身在中华民族解放中的作用,1943年7月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为中国二十二周年纪念而作》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既非‘外来的’,也不是几个人凭空制造出来的。它的所以发生,所以发展,所以没有人能把它取消得掉,那是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这样一个政党,犹之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要求有一个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党一样。谁要想取消共产党,就如同谁要想取消革命的国民党一样,都是违反历史发展的笑话奇谈。” 在当时的陕甘宁边区生活着回、蒙古等民族,这些民族对边区的政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注重探讨处理民族问题的策略。1938年底,西北工作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少数民族问题研究室,下设蒙古问题研究组和回回问题研究组。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并以之为指导开展了回族、蒙古族的研究。1940年,研究室编写了民族问题丛书,包括《回回民族问题》《蒙古民族问题》和《蒙古社会经济》等。1941年,《回回民族问题》在延安出版,该书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将回回作为一个民族整体看待,考察了回族的来源、回族长期被压迫和斗争的历史,分析了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批判了各种有关回族问题的谬论,对民族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47年,吕振羽著《中国民族简史》(大连大众书店,1947),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考察民族史的专著。(11)吕振羽在书中表明其为解决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问题而研究民族问题,严厉地批判了国内资产阶级的大汉族主义,主张各民族平等。该书着重撰述了汉族、满族、蒙族、回族、藏族,以及维吾尔族、罗罗族、唐古特族、苗族、僰族、黎族、鄂伦春族等民族的发展史。 二、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立与发展 在传统史学中,有关民族历史的记述是作为“四夷传”附于史书中的,民族历史的编纂是主要出于统治集团资政的需要。晚清至民国,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也出于对现实民族问题的回应,中国民族史开始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而发展起来。 1.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立 晚清学者在译介“民族”概念的同时,也有意识地深入探讨其内涵。梁启超认为“民族”有八个特征:“其始也,同居于一地,其始也,同一血缘,同其支体形状,同其语言,同其文字,同其宗教,同其风俗,同其生计。”(12)梁启超对“民族”概念的阐述迅速传播开来,为当时学界所认同,而后,民族主义等理论也大量译介,改变了人们认识民族历史及现实政治的方式,也影响了民族史学的发展,促使近代民族史学科的产生。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史学》一文,他指出:“叙述数千年来各种族盛衰兴亡之迹者,是历史之性质也;叙述数千年各种族所以盛衰兴亡之故者,是历史之精神也。”(13)1906年,梁启超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提出:“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吾中国言民族者,常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为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为何?合本部属部之诸族对于国外之诸族是也。”晚清,随着新史学的产生及发展,中国民族史逐渐成为史学的研究热点,学术界明确了民族史研究的地位及意义。 民国建立后,中国民族史开始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学术界开始重视探讨中国民族史学科本身的性质及研究方法。林惠祥所著《中国民族史》中明确指出:“中国民族史为叙述中国各民族古今沿革之历史,详言之即就各族而讨论其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并及各族相互间之接触混合等问题。”(14)林惠祥认为,民族史学科的性质包括两方面,一方面“为通史之补助,民族史固亦为历史之一种,然为专门史而与普通史不同。其与普通史之别在乎范围较狭,专论民族一项,与普通史之范围广阔门类繁多者不同。民族为历史现象之要素,故普通史亦必述及之,然以限于体裁,东鳞西爪,言之不详,故须有民族史以补足之”,另一方面“为人类学之一部,人类学中有一部分叙述人类各种族之状况者,民族史即此一部分也”。林惠祥还将民族史的功能概述为四项,他说:“民族史之性质,亦即效用,盖有下述四项:(1)为通史之辅助,(2)为人类学之一部分,(3)为实际、政策上之参考,(4)为民族主义及大同主义之宣传。”(15) 民国时期成立了一些与民族史有关的学术机构。1934年初,顾颉刚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禹贡学会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1935年3月1日,《禹贡学会简章》对学会宗旨进行了修改,扩大至“以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及民族演进史为目的”(16)。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也有专门的学者从事民族史研究。此外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还先后成立了中国民族学会、中国边疆学会、蒙藏委员会学术研究会等与中国民族史研究相关的学术团体。 民国时期的中国民族史学者多从业于研究机构及高校,他们以专业知识分子的身份来从事研究,改变了清及以前由官方机构或官员撰述民族史的传统。民族史的研究更加具有专业性,学术研究的旨趣也由传统的经世致用转为学术上的求真求实,中国民族史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 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史的人才培养机制逐渐形成。一些大学的历史系开设了中国民族史的相关课程,如中央大学历史系的选修课就包括中国民族史、风俗史、历史地理、蒙古史、西藏史等。(17)此外,中央大学、西北大学还设立边政系,开设了民族语言及回教史、康藏史、蒙古史等课程。(18)民族史研究人员的培养逐渐走向正规化、专业化,民族史知识也开始通过课堂讲授来传播。 2.中国民族史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探讨 晚清以后,一些掌握了西方史学方法的学者,开始尝试将这些方法与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结合起来,注重发掘新的材料,产生了一大批考证成果。有关民族史的考证成果也次第出现,主要涉及古代民族的族源、族称、族属、族系等问题,其中,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的民族史考证较有典范意义。 民国时期,王国维撰述了大量的民族史考证论著,如《鬼方昆夷玁狁考》《黑车子室韦考》《胡服考》(1915年)、《西胡考》及《西胡续考》(1919年)、《匈奴相邦印跋》(1922年)、《月氏未西徙大厦时故地考》(1925年)等。还有学者精通多种民族文字,能利用民族文字史料对民族史问题进行考证,比较有代表性的学者为陈寅恪。1930年,陈寅恪发表《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号,1930年5月)一文,该文由《蒙古源流》入手,引用藏、蒙、满文等文献及拉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订出吐蕃彝泰赞普的名号与年代。 当时,中国民族史学界除对既有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系统考证外,还深入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各民族的民间文献、口述史料等。民族史学研究积极借鉴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由此产生了一大批基于实地考察的民族史(志)论著,如颜复礼与商承祖著《广西凌云瑶人调查报告》(1929年)、杨成志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1930年)、林惠祥著《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1930)、凌纯声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甲种单刊,1934)、庞新民著《两广瑶山调查》(上海中华书局,1935)等。 同时,受民族学理论的影响,中国民族史研究突出了族称、族源、族属、族系等问题,学术界重新构建了现代的中国民族史知识体系,先后出版了十几部中国民族通史著作,这些著作确立了新的民族史叙述框架。民国时期,随着民族观念的深入理解与民族识别的初步开展,学术界积极发掘新的文献,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对各民族史研究展开深入研究,研究的重点为当时基本识别的民族,包括汉族史、满族史、蒙古族史、藏族史、维吾尔族史、苗族史、彝族史等,关于这些民族都有相关著作问世。 三、中国民族史撰述方式的演变 晚清新史学兴起后,新的史学编纂体例不断出现,同时,旧史学的撰述方法仍在继续。因此,这一时期的民族史撰述方式更加丰富多彩。 1.传统的民族史编纂 晚清,蒙元史的研究与撰述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的学术成果有魏源撰《元史新编》、屠寄撰《蒙兀儿史记》、柯劭忞撰《新元史》等,这些著作以传统的史学体例对蒙古及其他民族历史进行记述。 民国时期,《清史稿》修纂完成,该书基本延续了传统的历史编纂方式,该书卷五百十二至卷五百二十九依次为《土司传》《藩部传》《属国传》,并专设《邦交志》记述中外关系。在民族历史的记述体例与内容上,《清史稿》较之于乾隆时期所修《清朝文献通考·四裔考》有了根本的变化。 晚清方志对民族历史的记述出现了变化。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清朝颁布了《乡土志例目》,令各级衙门按照例目撰写乡土志和志书,这对地方志中的民族史撰述是一个促进。晚清许多边远地区也修纂了方志,对当地的民族情况记述更为详细,增设以前方志没有的内容,同时,纂修者受到西学的影响,地方志在记述民族时出现了新的门类,如谱系、语言、礼俗等方面。 光绪年间,内蒙古的基层行政设置由盟旗改为州县。相应的,这些州县编纂了方志,如《蒙古志》(3卷,姚明辉辑,光绪三十三年刊本)、《土默特志》(10卷,高赓恩纂)、《绥远志》(10卷,高赓恩纂)、《归绥道志》(47卷,高赓恩纂)、《归绥识略》(36卷,张曾纂修),这些方志都对本地区的蒙古族情况予以记述。光绪年间编撰的《肃州新志》涉及民族史的内容较多,如密兴复本末、哈密古迹山川风俗土产、巴里坤古迹山川风俗土产、吐鲁番火州鲁陈、车师高昌考、高昌王麴嘉传、西州回鹘、准噶尔传、西域诸部、准噶尔灭亡纪略、阿木尔萨拉叛亡纪略、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纪略、乌什叛乱纪略。 光绪三十二年(1906),新疆巡抚袁大化下令设立通志局,袁大化任总裁,王树枏、王学曾任总纂,开始纂修《新疆图志》。《新疆图志》特设了《藩部志》和《礼俗志》,记述了境内各民族的源流及风物人情等。 2.新的民族史撰述方式 晚清时期,学术界开始以全新的民族史观为指导,采用新的体例及历史分期方法重新叙述中国民族史。1905年,梁启超发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就其叙述体例及内容而言,实际上是一部中国民族发展简史,文中提出了“现今之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数民族混合而成”(19)的观点,这是对传统华夷观念的超越。 1905年,刘师培撰成《中国民族志》一书,在该书序言中,刘师培说明了写作此书的宗旨:“吾观欧洲当十九世纪之时,为民族主义时代。希腊离土而建邦,意人排奥而立国,即爱尔兰之属英者,今且起而争自治之权矣。吾汉族之民,其亦知之否耶?作民族志。”该书超越了传统的民族史撰述方式,以新的民族观念为指导,采用新的体例叙述中国民族史,在近现代民族史学上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民国建立后,“五族共和”观念开始广泛传播,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与撰述逐渐摆脱了华夷之辨之下的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开始注意阐述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发展历程,构建民族国家的统一发展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开始按新的体例编纂中国民族史,专门的中国民族史著作不断涌现,以“中国民族史”为题的论著就有多种,如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北平文化学社,1928)、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世界书局,1934)、宋文炳著《中国民族史》(中华书局,1935)、缪凤林著《中国民族史》(中央大学,1935)、刘掞藜著《中国民族史》(四川大学,1935)、柳贻徵著《中国民族史》(上海世界书局,1935)、林惠祥著《中国民族史》(商务印书馆,1936)等。至于不冠以“中国民族史”名称的论著则更多,如梁启超著《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1922)、李济著《中国民族的形成》(1923)、张其昀著《中国民族志》(商务印书馆,1933)、吕思勉著《中国民族演进史》(上海亚细亚书局,1935)等。此外,一些中国史论著也都以较大篇幅对中国民族史予以探讨和研究,如童书业《中国疆域沿革略·四裔民族》(开明书店,1946)等。由于受时代的限制,这些著述对中国民族问题的认识具有很多可商榷之处,但都称得上是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奠基之作。 民国时期的学术界也注重探讨中国民族史的编纂宗旨、体例、方法等问题,如林惠祥说:“以能阐明上述各项即种族起源名称沿革支派区别势力涨落文化变迁及各族相互间之接触混合等事者为准。凡通史所不详,而于民族之沿革上有重要意义者,咸在采取之列;至于通史所常述之材料则只略提而不复详述,以免重赘而省篇幅,如汉族之史实,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统治中国后之事迹,皆从简略,而只以一小段概括之。”(20)民国时期出版的中国民族史著作,大致有两种编纂体例:第一种以王桐龄著《中国民族史》为代表,以历史分期为章节,在各历史时期分述各民族的类别、演变及族际交往的历史;第二种以吕思勉著《中国民族史》为代表,全书统按各民族分章节,每一章综合叙述某一民族的起源、演变及消亡,并讨论其各个支系的变迁。 民国时期,还先后出现了几部叙述中华民族史的著作,如常乃惠著《中华民族小史》(爱文书局,1928)、曹松叶著《中华人民史》(商务印书馆,1933)、郭维屏著《中华民族发展史》(成都,1936)、李广平著《中华民族发展史》(正义出版社,1941)、张旭光著《中华民族发展史纲》(桂林文化供应社,1942)、俞剑华著《中华民族史》(国民出版社,1944)等。 四、中国民族史学功能的转化 中国民族史学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受到时代变革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其功能也随时代而变化。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更加突出维护祖国统一、加强中华民族认同的作用。 1.维护祖国的统一 在朝廷腐败日甚、列强侵华日深的政治形势下,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史学界逐渐凸现出救亡图存的强烈倾向。帝国主义侵略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方面诸列强侵略中国,使中国各民族饱受丧权辱国之痛;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在对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经济掠夺、文化渗透的同时,还对这些地区直接进行蚕食,甚至分裂活动。在这种边疆危机日深、民族危亡的时期,不少史学家开始重视边疆史地研究,考证民族地区的地理、攻防、治策等蔚为风气,其中较有影响的著作有张穆撰《蒙古游牧记》、何秋涛撰《朔方备乘》、姚莹撰《康輶纪行》等,这些著作对边疆民族史都有深湛的考证。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伪满洲国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筹建及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严峻形势下,学术界展开了关于“中华民族”问题的讨论。国家危亡的形势促使了民族精神的凝聚,这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明治初年至1945年,日本史学界热衷于为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服务,积极研究我国东北边疆民族历史,提出了一系列违背史实的主张和观点,妄图否定历史上东北地区的民族是中国的古代民族,进而否定东北是中国的领土。针对这些荒谬观点,中国学者也致力研究东北民族史,运用事实驳斥了日本人的无稽之谈,代表性的著作有傅斯年著《东北史纲》、金毓黼著《东北通史》。又如,在日本的怂恿下,20世纪30年代,暹罗政府开始宣扬大泰族主义,1939年6月暹罗改称为泰国,并派人到我国云南境内傣族地区活动,并声称要收复失地。这些活动引起了中国政府及学术界的注意。中国学者从族源、族属角度予以反驳,如凌纯声在《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一文中指出“创立南诏的蒙氏是乌蛮,属于今之藏缅族”,而“非摆夷民族”。(21)1944年,岑家梧发表《由仲家来源驳斥泰族主义的错误》一文,他认为“仲家原为中原汉人,后来因为犯罪流徙或奉调戍边,日久便与土著通婚而土著化了”,“目下仲家语系虽与泰语相通……其与汉语的关系则极为密切……仲家与汉人在血统上的关系,已有极悠久的历史”。(22) 此外,学术界还对西北、西藏地区的民族进行研究,以反击国内外利用民族历史的分裂言论,主要著作有白眉初著《西藏始末纪要》(北平建设图书馆,1930)、洪涤尘著《新疆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5)、曾问吾著《中国经营西域史》(商务印书馆,1936)、洪涤尘编《西藏史地大纲》(正中书局,1936)、任乃强著《康藏史地大纲》(雅安建康日报社,1942)、贺岳僧著《西北史纲》(文信书局,1943)等。 2.加强中华民族认同 晚清,为推翻清朝统治,革命派提出了“排满”的口号。1894年,兴中会盟书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23)1906年,中国同盟会宣言称:“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24)革命派为鼓动革命精神,注重发掘先秦典籍中“黄帝”的相关记载,将黄帝奉为汉族的“始祖”,以之作为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同时,革命派也注重撰述汉族与其他民族的斗争史,如黄节撰《黄史》、柳亚子撰《中国兴灭小史》、陶成章撰《中国民族权力消长史》、宋教仁撰《汉族侵略史》等。民国建立后,革命派改变了“排满”的口号和做法,转而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上的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及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团结。 晚清,较早使用“中华民族”一词的是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多次使用“中国民族”一词,有时用来指汉族,有时用来作为有史以来各民族的总称,在后一种用法中,已初步具有了各民族从古至今凝成某种统一整体的含义。在1905年发表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中,梁启超同时使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民族”的概念。在晚清至民国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中华民族”的概念为学界所接受,为了加强民族认同,学界也致力于宣传“中华民族”一体的观念。 1939年2月13日,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发表《中华民族是一个》一文,顾先生开篇即提出:“凡是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在今以后大家应当留神使用这‘民族’二字。”他强调:“中华民族不组织在血统上……中华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现在汉人的文化,大家说来,似乎还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实也不对,它早因各种各族的混合而渐渐舍短取长成为一种混合的文化了。”1944年,罗香林发表《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一文,提出中华民族“是构成中国这国家的主体,它是中国所有人民的总称,所以凡住在中国领土以内而取得中国国籍的人民,都是中华民族的细胞,他们的合就是中华民族的内蕴”。(25)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版了几部中华民族史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都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整体,通过对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和历史发展的叙述,以唤起中国人共同的民族意识,凝聚团结抗战的力量。在当时出现的几部中华民族史著作中,以郭维屏著《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俞剑华著《中华民族史》具有代表性。郭维屏著《中华民族发展史》一书叙述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发展历程及其盛衰的变迁。俞剑华著《中华民族史》认为中华民族是“由小宗族合而为较大的宗族,由较大的宗族合而为更大的宗族”,汉、满、蒙、回、藏等族就是中华民族的宗支,它们经过长期的交往与战争,最终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 晚清至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巨变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传统的华夷观受到了强烈冲击,并逐步解体。在民族史观上,传统的“华夷之别”观念开始向“中华一体”观念过渡,民族史的研究与撰述也围绕这一时代主题而展开。中国民族史逐渐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出现了研究民族史的学者群体,并形成了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在民族史撰述的体例上新旧杂陈,新的撰述体例逐渐确立并取得了初步的发展。中国民族史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不同的社会群体都基于自身的需要而撰述民族史,民族史学的功能出现了多元化的态势,但主要的方面是加强了中华民族认同。中国近现代民族史学形成了自身的理论框架,涉及了民族史学的基本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当代民族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注释: ①关于中国民族史学史的任务和意义、发展的几个阶段及其特点,参见史金波:《中国民族史学史刍议》,见《云南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 ②王韬:《韬园文录外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45页。 ③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册,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439页。 ④关于“民族”一词,在中国古文献中就已出现,《南齐书》中的“民族”与当前我们使用的民族的含义几乎相同,南北朝时期在区别不同民族时,已运用以文化本位为基础的“华夷之辨”的认同标准,证明了“民族”一词是中国古文献中固有的词。见邸永君《“民族”一词见于〈南齐书〉》,《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 ⑤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页。 ⑥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6页。 ⑦梁启超:《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二,第13页。 ⑧王桐龄:《中国民族史》,北平:北平文化学社,1934年,第1页。 ⑨林惠祥:《中国民族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页。 ⑩参见《李大钊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 (11)朱政惠:《吕振羽〈中国民族简史〉的史学思想》,《历史教学问题》1989年第3期。 (12)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13)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第12页。 (14)林惠样:《中国民族史》,第2页。 (15)林惠样:《中国民族史》,第1页。 (16)《禹贡学会简章》,《禹贡》第4卷第3期。 (17)《国立中央大学文学院史学系课程规则说明书》,《史学》1934年第1期。 (18)杜肇敏:《中央大学的边政学系》,《西北通讯》1948年第3卷第3期;习之:《西北大学的边政系》,《西北通讯》1947年第6期。 (19)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四十一,第4页。 (20)林惠样:《中国民族史》,第3页。 (21)凌纯声:《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第1期。 (22)岑家梧:《由仲家来源斥泰族主义的错误》,《边政公论》1944年第3卷第12期。 (2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0页。 (2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7页。 (25)罗香林:《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三民主义半月刊》1944年第4卷第6期。标签:中国近代史论文; 民族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史学史论文; 梁启超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