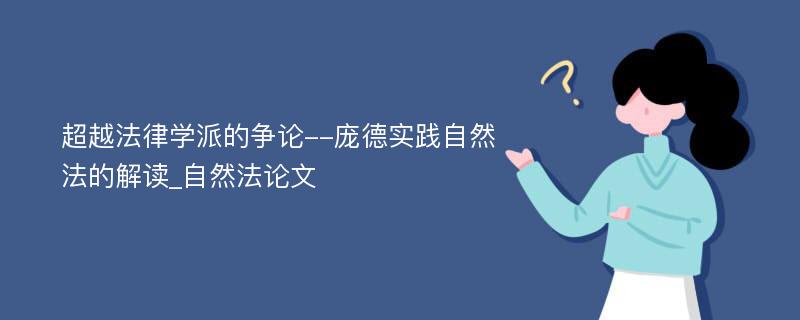
超越法学流派之争——解读庞德的实用自然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庞德论文,自然法论文,流派论文,之争论文,法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然法思想在西方哲学史上渊源甚久,最早可以上溯至人类文明的开端时期,它伴随着自然法学派的兴盛、衰落和复兴而传承至今。在自然法学派的演进过程中,历史法学派、规范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等流派先后出现,它们质疑自然法思想的绝对价值,挑战自然法学派的主流地位。庞德的实用自然法正是在深刻反思自然法价值的背景之下提出来的,这种自然法符合特定时空下的特定文明,具有内容可变和不断生长的特性。具体说来,实用自然法就是庞德对特定文明所预设的有关正义和权利的基本观念,台湾学者马汉宝先生将其翻译为法律基理,邓正来先生则称其为法律先决条件,它虽然不是法律,却是法律应当符合或者说是不能违背的信条。然而对于庞德提出实用自然法的意图何在,或者说实用自然法在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中扮演何种角色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审视,是我们系统把握和整体领悟庞德法律思想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近些年国内学者对庞德法律思想的研究往往侧重于透过著作本身挖掘其背后的理论资源并进行深刻解读,指出庞德社会学法理学的可能代价和限度。①虽然这些研究也是从某个具体的问题点比如社会整合、知识增量出发力图展现庞德理论的深度以及可能限度,但是他们所选取的立足点仍是一种外部视角,是站在庞德的法律思想之外对其理论进行“客观和中立”的描述和评价。在笔者看来,这种外部视角容易将庞德的某些观点和思想做工具化的利用以契合自己的“问题意识”,最终将有可能导致对于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缺乏内在的体认,进而引起诸多误解。本文将选取实用自然法这一内在的视角,揭示实用自然法背后的各种学派资源,进而论证这一概念在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中所扮演的地位。 一、为何从法学流派出发 目前国内几乎出版了庞德的所有法学著作,其中以邓正来先生译介的五卷本《法理学》最为巨大,这一系列书籍是庞德晚年的集大成之作,囊括了庞德之前的全部法律思想,包括绝大部分论文和专著。除此之外,有沈宗灵先生翻译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邓正来先生翻译的《法律史解释》,陈林林翻译的《法律与道德》和唐前宏等翻译的《普通法的精神》。仔细分析这些著作的内容和结构,将会发现一些共同之处。在《法律史解释》一书中庞德试图勾勒出一幅法律哲学和法律思想发展的一般性图谱,在他看来,历史进程中的法律发展都是在处理和协调稳定和变化之间的关系,在法理学中表现为规则与自由裁量之间的调适。②对此,庞德认为之前的法律思想试图用唯一因素来解释法律历史的发展,它们分别是伦理和宗教解释、政治解释、人种学和生物学解释、经济学解释等。在这些解释中,我们明显可以感觉到庞德对各种法学流派的分门别类,比如伦理解释几乎可以对应自然法学派的许多观点,政治解释很大程度上是以哲理法学派和历史法学派为参照的,经济学解释更是可以直接与法经济学派对号入座。民国学者吴经熊先生就指出,“庞德是个彻头彻尾的工具主义者,无论唯心主义的法律史解释还是唯物主义的法律史解释,均有其功用。在他的体系中,都有恰当的位置,执行着恰当的功能”。③比如他从目的论视角来审视法学上的唯心主义,伦理学解释成了重点强调权利观念的价值,政治学解释背后是个人的自我做主和自由的价值;从机械学角度来看法学上的唯物主义,人种学和生物学的解释讲的是地理环境和种族心理对法律发展的影响,经济学解释则是对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这种现象在《法律与道德》一书中也非常明显,庞德在分析法律与道德的问题时也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即从历史、分析和哲学等三个视角来透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自然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等流派纷纷上阵,在庞德的熟练驾驭之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通过三维视角完全地呈现在这些法学流派各自的理论之中。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之中,庞德虽然没有直接给出自己对法的定义,但他认为法应当有三个维度上的意义分别代表法令成分、技术成分和理想成分,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对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成果的归纳。即使在《普通法的精神》一书里,也无时不透露着庞德对各种法学流派的批判性吸收和借鉴,庞德在分析促成美国普通法精神成型的七大主要因素之中有一个就是关于19世纪法哲学的论述,在他看来,这一时期的五大法学流派从不同的出发点都指向了相同的法理学立场,即注重“将个人判断和良心作为令人满意的理论基础,自然权利原则和自然法概念中的个人良心成为服从义务的最终判准”。④由此可见,庞德的主要著作始终贯穿着对各大法学流派的理解和重新认识,通过对这些流派背后的代表性人物观点的分析和批判,庞德开创了社会学法理学,进而形成自己的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其中就包括本文所要论述的实用自然法。 纵观庞德一生,从学者和教师到法学院院长,他几乎是整个法学领域最博学的人,能够通晓所有法律部门。据说,庞德即使在做院长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缺过学生的课,甚至当有的教员生病了,他直接接过这门课程而不管它是什么内容。⑤庞德渊博的学识与独特的才能是分不开的,有两大才能不仅使他迅速和准确地捕捉到别人的思想和观点,也使他能在吸收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独特理论。首先,他是一个他人作品的出色阅读者和综合者,他经常能够比学者们自身更好地理解这些学者们所说的话;其次是他能辨明智识趋向的重要性,不管是法律的还是超法律的,并且将它们融合进自己对法律的看法之中。⑥正是因为庞德这种非凡的能力,他的著作中无处不显示出对运用他人理论观点的驾轻就熟,不同法学流派的演进和争论构成了庞德许多论著的实质内容和相关主题,同时在庞德重新组合和精心布置之下也预示了社会学法理学的某些端倪。实用自然法即是庞德这两大才能的结晶,在庞德看来,自然法学派代表了人类对美好价值的连续性追求,他的理论不能弃绝理想走向虚无主义或“放弃哲学”,因此,社会学法理学仍然要保持价值之维,这就需要从自然法学派的学术丛林之中汲取自己所需的理论资源;同时,庞德绝不是想重新回到托马斯意义上的传统自然法,他需要从与自然法学派对立的流派中挖掘智识养分,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实证主义法学派。 二、实用自然法的保守倾向 自然法理论总是试图提供一幅普适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理想图景,它并不否认现实中法的存在,只不过它认为实际中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需受到更高级规范的约束,这一约束力可能来自上帝、道德或习俗。然而,自然法理论一旦形成并占据主流就容易变得僵化,它的忠实信徒可能会不顾社会情势的变迁而依然固守原有的自然法信条,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正是看到这一点,庞德毅然否定18世纪那种抽象人性推演的普遍自然法和19世纪形而上学僵化的自然法,转而关注17、18世纪那部分创造性自然法的复兴。对于当时的美国法理学者来说,他们对自然法有着持久的兴趣,许多人越来越感觉到需要用一些最终的原则来阻止当时美国现实主义的继续蔓延,同时他们又深知传统自然法的弊害而不愿重回托马斯时代。于是,许多人开始用哲学和自然法的一些观点填补实证法中存在的缺漏,或者说是为现已存在的法律提供一个评判的基底(post factum)。⑦庞德即是其中的一例。庞德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自然的自然法和实在的自然法(natural natural law and positive natural law)的文章,试图从自然法的源流中建构起自己的自然法概念。 (一)庞德对自然法保守一面的发觉及误解 庞德认为他的自然法概念至少能够在三处找到学理依据:亚里斯多德的保守主义的自然法、充满活力的自然法理论包括古罗马法学家和17、18世纪的法学理论、中世纪的保守主义自然法。⑧在他看来,亚里斯多德对法律中实证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区分其实就隐含了法是由陈旧的习惯部分和新近的制定部分两部分组成的意思,也就是说,自然的公正能够用习俗或传统来证明,这在庞德对法律实际上是如何处理价值问题的看法中有清楚的表述,即经验、理性和传统三种方法,⑨其中经验是理性指导之下的经验,理性是经过经验考验的理性,而传统则包含了经验和理性。同时,古罗马时期的罗马法学家们对法律问题做出的解答其实是运用公平正义等充满活力的概念对当时的罗马制定法进行弥补,这种情况同样也发生在17和18世纪的衡平法裁判当中,自然法理论中自身就具有适用社会发展的变化性因素,没有完全一成不变的理论信条。最后,庞德总结出中世纪自然法思想的三个主要特征,即威权主义、神学基础和永恒性,在庞德看来,这一时期的自然法站在了个人的对立面,完全忽视个体的道德权利;由此,他得出任何一种社会秩序包括服务于个体成员的需要和社会自身的生存发展两种功能的结论,也即道德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区分。后来庞德将利益划分为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并且庞德对这些利益的划分并非绝对,因为“相互冲突的利益可以从同一观点加以比较,而将其都视为社会利益,然后加以比较最为方便”,⑩对于庞德来说,所有不同的利益都可以化约为社会利益。 然而,庞德对不同时期的自然法的理解其实存在着很大的误解,很大程度上犯了对一些概念理解不深和不完整的错误;换句话说,实用自然法能够从自然法顺利推演主要建立在庞德本人对自然法的片面理解之上,带有用自己的观点和理论设想来附会自然法理论的明显倾向。 第一,庞德没有看到能够标示自然法学派学说和主张的一个根本性特征即自然或本质观念的不变性(immutability)。庞德是个价值相对主义者,他不相信存在一种具有普遍性和连续不变的永恒性价值,通过对自然法历史发展的具体考察,他认为某些时期的自然法学家似乎表露出自然法概念能够反映社会需要及时做出调整的可能性。实际上,虽然亚里斯多德的某些观点具有相对保守的成分,但庞德却对亚里斯多德本质概念中的不变性因素视而不见,其隐含的意图其实是想“抹杀亚里斯多德自然(本质)概念中的不变性而仅仅留下那个理念的特征(the character of ideal)”。(11) 第二,他对中世纪自然法的重新发现有意遗漏了集体观念或共同的善背后的个人主义。庞德认为,中世纪时期教会的权力蔓延到世俗社会,当时的自然法笼罩着浓厚的神学色彩,神权或教权紧紧地将个人束缚在教会和国家这样的集体之中。然而,如果说中世纪的自然法理论不是个人主义的和伦理的,那么这种自然法理论可能什么都不是。并且,个人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教会的法规的确是为了致力于共同的善,但个人的善本来离不开这种应服从当局而带来的共同的善。 第三,特定时期具体做法的易变性不能否定自然法价值的绝对性和不变性。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自然法作为理念太过于抽象和一般化,因此在成为具体的实在法条文之前,必须经历一个特殊化的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立法者和司法者的能动作用得以彰显。因此,实在法中特殊条款的变化或司法裁判的具体变迁其实都是在自然法提供的轮廓之中进行的继续充实和完善。在自然法看来,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来自于不变的自然法,变化是其永恒内容的一部分。正如托马斯本人所说,“自然法包含特定的持续存在的普遍条款,而人类法则包含特定的随情况而变的特殊条款”。(12) (二)没有绝对价值的自然法 不可否认的是,实用自然法的确能够在自然法之中找到一些“家族相似”之处,因为实用自然法的主要目的即在于提供一幅理想图景,根据庞德的设想,这些法律基理能够起到自然法的作用却没有自然法可能具有的弊害,在“上帝已死”和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它能充当自然法曾经扮演过的角色从而指引实际存在的法。庞德非常认同科勒的文明观,认为人类虽然没有永恒不变的价值却存在一个最高的目标即维护和发展文明,对于不同社会来说,这个目标过于抽象不能直接加以运用,因此,庞德提出特定时空文明下的法律基理以提供更为具体的理想图景。不同文明和社会具有不同的法律基理,这有赖于这一社会中的立法者和法学家加以提炼和概括。对此,庞德最得意的弟子斯通教授提出了七点有说服力的批判意见。(13)后来许多学者对庞德的法律基理的认识和批判就是建立在斯通的批判之上,这些质疑的声音很多都出自对特定时空文明的责难。 庞德认为法律自身不能实现正当化,必须借助于文明,只有在法律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之中才能确定法律的价值,然而,从法律基理中自然会引出这样的疑问,当代或特定社会在何种程度上能够成为一个理想图景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与现代社会的实际需求相一致?从庞德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归纳的几点法律基理来看,强调自我保存等个人主义的思想始终隐现其中,而当时的美国正快速步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现代社会,对社会立法的呼吁和行政规制的加强逐渐显露出来。对于这些美国社会正在发生或将会发生的变化,庞德的法律基理并没有将其考虑进来,法学家依理性和经验所发现的特定社会的理想图景只是指涉现在甚至还有过去的。尽管庞德口口声声地说自己希望看到的是17、18世纪那部分创造性自然法的复兴,可是“17、18世纪的理想价值是崭新的和向前看的,而庞德的理想图景却是过去的和向后看的”。(14)体现在实用自然法中的保守倾向同样出现在庞德对美国法律程序体系的批判之中,在指出缺陷之后,他为美国联邦民事程序规则描述了一些具体的原则,这有助于使程序和实体相结合以服务于公共利益。然而,非常明显的是,“一股纯粹的保守冲动正致力于对普遍性本质的反对”。(15)不难想见,庞德提出实用自然法的意图在于超越自然法永恒价值的严格性,其背后是一种价值相对主义在作祟,在庞德的构想中,我们可以根据当前的社会非常自由地提出新的价值主张,这些价值主张不受某个最高规范的约束,它建立在任何我们当前适用和继续实施的标准之上。 然而,问题是我们如何能够确定当前的社会或现存的文明就一定存在理想化的价值序列?实用自然法所主张的文明基理难道一定能够保持客观中立吗?更深层次的追问是,所有利益是否真能化约为社会利益?应当由谁来确定我们这个社会的社会利益?经过选择和确认的社会利益是否真的就“比个人自我实现更重要”?果真如此,那么社会利益“一旦成为法律承认和保障的对象并且成为衡量法律之功效的判准,即使不会即刻扼杀个人自由,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为某些个人或群体以各种‘社会利益’之名侵损真正的个人利益开启‘合法’之门”。(16)由此,自然法所宣称的不变的权利,在庞德的实用自然法之中就被置换成了特定时空下的社会利益。实用自然法中再也没有自然法因素,有的只是文明与法律的关系。 三、实用自然法的实证品格 在面对邪恶立法的情况下,自然法学派基本上主张“恶法非法”,违背人类良知和基本道德观念的法律不再具有约束力,甚至不能算作是法律;而实证法学派大多数认为“恶法亦法”,因为“法的存在是一回事。而法的优劣,则又是另外一回事”。(17)除了在法律与道德的基本关系上自然法学派与实证法学派存在明显的对立之外,在对法的定义及性质等问题上它们之间也存在许多明显不同之处。从表面上看,庞德的实用自然法似乎是自然法在社会学法理学中的翻版和具体运用,其实不然,它直接取消了对自然法中绝对性价值的讨论和对个人主义的持续关注,剩下的只有自然法的躯壳。相反,经过一番细致剖析,实用自然法这一概念对实证法学派的某些观点和思想却可能存在非常明显的套用之处。(18) (一)作为一种框架的理论与实用自然法 单就概念本身而言,实用自然法这一提法很有可能是来自于自然法,然而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实用自然法的建构更大可能是受到了凯尔森所作的框架理论的影响。凯尔森的规范法学意图彻底解决实然和应然纠缠不清的症结,它在事实和价值之外创设了第三个领域即规范。规范成为沟通事实因素和价值因素的桥梁,但自身并不是事实也不是价值。在凯尔森看来,传统的解释方法包括推理论证和类推适用等并不能解决这种规范不确定的实践难题,一方面,这些传统的方法没有提供一条客观可信的途径用以解决“意志”与“表达”、“目的”和“文本”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它们没有为论证推理以及类推适用等方法找到客观的基础,“因为这些方法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并且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用来判断我们什么时候该选择这个而不是那个”。(19)于是,受到休谟定律的启发,凯尔森开始回到规则本身,从规范及其有效性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在他看来,规范的效力并不取决于规范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取决于该规范的上一级规范并且一直可以追溯到基础规范,由此形成一个链条式的规范等级结构。由此,规范的确定性可以完全依靠整个规范系统的形式有效性而得到保证,无需纠结于解释或理解对规范内容的确定。 因而,凯尔森提供的框架理论卸下了“实质内容”的重负,规范可以为法律实施提供具备多种可能性的认知。与凯尔森的框架理论类似,庞德也没有提出一些非常明确的司法规范,我们所能找到的只是“不同公民的利益”和“一些没有决定性内容的规则和自由”,只有那些运用到每一个人身上的主观性价值才是一个规范,虽然庞德也将个人自由作为整个社会工程的规则并看作是伦理原则的具体运用,但是庞德的意涵“并非是简单的个人自由而是绝对受制于主观性价值的自由”。(20)也就是说,个人自由并非自然法意义上的绝对价值,并没有永恒不变的实质内容,而是会随着不同个体和不同社会而改变。实际上,实用自然法对绝对价值的拒斥就决定了它只能采用一些主观性的价值,也即随着特定时空和不同文明社会而改变的法律基理。如同凯尔森的规范一样,实用自然法并没有实质性内容,它能够适用于具有明显不同的事实和价值环境的社会,因为它的效力来自于庞德的文明概念,并且这个庞德所说的最高目标其实也是没有实质内容的,实用自然法完全是在形式合理性和形式有效性保证下的规范假设。 (二)强力支撑下的规范与理念的混合体 庞德对法的性质和本质特征的认识暴露了他与分析法学派的明显承继关系。边沁、奥斯丁开创的分析法学将法律的范围严格限定在实际存在的法之内,通过对法的定义、性质和特征等概念的清晰界定,分析法学家意图达到标准明确和容易适用的规则体系。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对自然法的许多概念抱着一种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的态度,它更多地“不是去了解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是真正好的东西,什么是真正坏的东西”,他的实用自然法关注的是“人们会认为什么是好的东西”,因此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技术或方法”。(21)因此,在法的研究对象上,庞德可能会更倾向于分析法学派的概念分析,搁置对法律理想成分的虚无缥缈的争论,转而将目光放在人们对实际存在的法所达成的规则共识之上。 具体说来,庞德在什么是法的问题上主要得益于奥斯丁的理论。在奥斯丁看来,法理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实际存在的由人制定的法,是政治优势者对政治劣势者制定的法。而法就是主权者的命令,命令、义务和制裁这三个术语中的每一个都在说明同样的含义。庞德在《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一书中曾分别从法律秩序、法律规则和司法程序等三个方面谈到过法律的定义,即使庞德特别强调法律的价值一面,他仍然是“一个新奥斯丁主义者”,因其如同所有分析法学家一样,“将暴力认为是法律中的基本因素”。在比较自然的自然法和实在的自然法那篇文章中,庞德将前者界定为“一类独立于任何实际存在的法的理想条款集合体的理念法,后者则是特定时空下的实证法”。(22)庞德认为,许多学者的著作混淆了这两者的区别,有些学者将实证法表述为具有宗教的、伦理的或理性的基础,另一些学者看到的却是实证法仅仅是那些特定政治组织下对权力的运用。庞德试图在这两种说法中找到平衡,他眼中的法是按照使正当条款达到正当结果的目的进行操作的权力体系。从这里很快就可以看出,庞德已经为实用自然法的出场拉开了序幕。在承认法律以权力和制裁为后盾的同时,庞德没有忘记给权力套上目的论的“紧箍咒”,就如法律不能依靠指涉自身实现正当化一样,权力也不能通过不受任何限制的运用和行使而实现自身的正当化。权利的行使是为了达到法律的目的,只不过这里的“正当结果”不是自然法意义上的“绝对价值”而是法律与文明之间的直接关联,在这一点上,庞德的实用自然法又超越了分析法学派。 除了在法律与文明之间的关系上看到法的目的之外,实用自然法对法的概念的认识很大程度上还是实证的。庞德当时所处的美国社会现实主义运动对传统法学观念的挑战日益明显,善于把握学术动向的庞德不可能对这一现象熟视无睹,其实,社会学法理学与法律现实主义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简单说来,庞德就是凭借着将“伦理道德性或预设理念和分析法学有机融合”,从而与卢埃林等现实主义者划清界限,因为在卢埃林看来,法律仅仅是意味着“对客观可证明的事实及其之间的关系的发现”,这些才是法律科学的特征,像庞德那样“把‘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作为一项整体的事业来研究完全是一种错误”。(23)法律现实主义通过关注法官如何做出判决来展现实际社会中运行的法律,它其实并没有一种内在的法律哲学支撑。卢埃林曾经把现实主义分为三类,其中第三类最令人感兴趣也最有建设性意义,卢埃林称其为“部分现实主义者(realists-in-part-of their work)”,这一概念被用来指代那种任何人都能使用而不管他的法律哲学或政治立场背景的现实主义。(24)按照这种分类法,庞德显然也可以归为广义上的现实主义,因为庞德对法的看法走的是研究实际存在中的法的分析路径。受到现实主义的影响,庞德也曾经将法律粗略地分为“书本上的法”和“行动中的法”,这一划分非常接近于埃利希提出的“活法”概念。庞德从目的论出发认为法律应该解决社会问题,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等带来的社会变化使得法律出现了“真空地带”,这时候急需规则加以填补。不同的是,埃利希认为存在许多不同种类的法,法律仅仅是社会进步和社会变化的自然结果而非干预的工具,“活法”背后是各种交流、关系、协议等等。(25)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庞德的“书本上的法”还是“行动中的法”其实都是被用来指向法律制定者和法律实施者的,它们都可以包含在与“活法”相对的“做出决定的规范”之中,也就是说,庞德在做出这类区分之前已经形成了对“什么是法”的先入之见,即法代表了一类在政治组织社会中由国家制定的规范。 (三)超越法与道德之争 在法与道德的关系方面,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的学者长期以来就争执不下,因而这也成了理解法的本质的核心问题之一。奥斯丁等分析法学派的观点是明确的,“法律是什么”不能与“法律应该如何”相混淆,后者是立法科学需要解决的问题,属于伦理或道义科学的范畴,而前者才是真正的法理学所应当关注的。虽然近些年实证主义内部对法律与道德的看法有了新的争论,法律实证主义阵营中的主流观点仍然是坚持法律与道德相分离,于是,“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之争,主要表现为分离命题和必然联系命题”。(26)庞德对道德概念的认识是建立在特定文明时空“所已经接受的价值理念之上的”,他对任何绝对价值标准的拒绝“事实上就导致了法律与道德的分离”。(27)但是,庞德的实用自然法并没有像凯尔森和奥斯丁那样简单地处理法律与道德的分离过程。道德虽然不能直接成为判断法律效力的合法性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立法者可以制定具有任何内容的法律,相反,某一社会的法律应当符合由所属文明决定的法律基理,应当具备最基本的道德观念和公平正义。 在前人的基础上,哈特认为自然法应当具有最低限度内容,因为“(法律和道德)没有这些特定内容,人类正如他们现在这样,将没有任何理由自愿遵守任何规则;如果因他们自身利益的缘故自愿去服从和维护规则的人之间没有最低限度的相互合作,强制那些不愿服从法律的人去按照法律行事,将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28)其实,这也就是法律实证主义内部对“内在必然联系命题”得出的基本主张。进一步说,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外在分离命题与内在联系命题其实是相互融贯的,前者仅就合法性标准而言是成立的,而后者则占据着更加基础性的地位,并为前者提供合理性说明。比较实用自然法中的法律基理与哈特提出的自然法最低限度内容,两者具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法律应当符合的平等和正义观念,但这些内容自身又并非法律,而是对法律提供一种指引或合理解释。如果说“外在必然分离命题”和“内在必然分离命题”的区分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化解了自然法与法律实证主义之争,那么庞德的实用自然法其实也就同时超越了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 四、超越如何可能 不可否认的是,实用自然法在对法的本质及其性质的认识上更趋近于国家论的法律实证主义,然而,这却并不能使我们得出结论说,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是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延伸发展。一方面是因为实用自然法并没有放弃对“法律应当怎样”的追问,每个特定社会都应当按照当时的法律基理指导法律的制定,立法者应当制定正当的条款以达到正当的社会效果。更重要的一方面是实用自然法有着完全不同的哲学基础,即实用主义。 (一)实用主义主导一切 实用主义经由詹姆斯的发展而成为美国社会主流的一种法律哲学,庞德开创的社会学法理学为其赢得“所有致力于法律事业的人的尊重和爱戴”,同时也使其成为“实用主义的领袖”。(29)詹姆斯的这种实用主义从一种纯粹或彻底的经验主义出发反对古典的理智主义,认为“凡是为人所经验的,才是实在的”。(30)在他看来,检验真理的最终标准是真理可能会产生的实际结果,因为拥有真理本身并非目的,而是我们用来实现某些非常重要的需求的初步手段。善的实质是满足人的需要,在不同人群相互冲突的要求之中应当追求最大多数需求的满足和最低限度的损害。 同时在耶林的利益学说影响之下,庞德认为,众人对要求法律保障的不同需求实际上是一种利益主张,法律的任务就是发现这些利益,进而加以确认和维护,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新的需要和利益诉求又将出现,法律对利益的承认和保护的工作又将继续进行下去。但是与詹姆斯不同的地方在于,庞德将这种需求和利益统摄在他的实用自然法之下,因为并不是任何实际的社会需求都会得到法律的认可进而加以保护,如果“一些需求与大多数人的愿望相悖就不能得到认可”,放在实用自然法的语境之中,法律对利益的承认其“前提是符合特定文明的法律基理”。(31)通过实用自然法的“筛选”,我们发现詹姆斯对实用主义的利用其实是中立的,每种需求在他那里都是一种善,都应该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然而,庞德需要在实用主义的体系之外寻找可以做出价值判断的依据以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要求,他需要“一些切实有形的指导以便做出决定”,因此,有学者认为庞德的实用自然法是“实用主义与黑格尔主义的联姻,甚至可以说是对两者一个错误的折中”。(32)这种说法与其以新黑格尔主义对庞德可能产生的影响为切入点展现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密不可分,单纯就实用自然法不可避免地需要做出价值判断来看,庞德确实是一个新黑格尔主义者。不容忽视的是,庞德对法律历史和思想学说始终抱着一种功能主义的态度,他不仅会研究某一时期的法律有哪些渊源和学说背景,更会关注这些渊源和理论是如何运用的,对社会实践产生了哪些效果。所以,他那庞大的社会学法理学体系其实“综合了许多不同的甚至经常是针锋相对的法哲学家们的理论精华”。(33)如此看来,实用自然法对黑格尔的理念学说的运用并不能被简单地贴上黑格尔主义者的标签,充其量只能说这一学说能够对实用自然法顺利完成价值判断的任务“发挥作用”,而“根据实用主义原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如果上帝的假设令人满意地发挥作用,它就是真实的”。(34)因此,无论是对自然法学术概念的“抄袭”,还是对法律实证主义的借鉴,甚至是对新黑格尔主义的某些观点的运用,对于庞德来说,都是建构和完善实用自然法的工具和手段,他的哲学基调和伦理基础始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的观念是庞德分析和选取有用资源的思维预设。 (二)从社会视角来看法律 庞德认为法律发展历史的演进依次经历了原始法阶段、严格法阶段、衡平法和自然法阶段以及成熟法阶段,最后到达他所说的法律的社会化阶段。法律开始成为实现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法律的任务是通过对各种社会利益的确认和限定以实现对人的内在本性的最大控制。在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看来,法律史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法学流派都试图确立单一的因素来解释法律的发展,不能全面反映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我们应该对法律进行一种社会工程的审视,更多地研究实际社会中的法律秩序而不是将目光仅仅停留在法律的性质上。 简而言之,至少在庞德看来,在他之前的法学流派几乎都是从内部来研究法律,而现在他要开始从外部来研究法律,“他试图将方法论的运用和规范的进路相混合以创造一个新的理论”,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社会学法理学将会“更关注法律与社会的联系导致的法律的发展,而不是传统法学研究普遍的对法规和案例的分析和解释”。(35)法律的目的在法律与社会控制之间架起了桥梁,对社会利益和社会效果的关注取代了对法律本身的研究,庞德的社会学法理学真正做到了“以社会为本位”,之前的法学流派除了极端的概念法学之外都会或多或少同时关注法律的应然和实然问题,大体上都还是“以法律为本位”的。可是,庞德完全倒置了他的研究视角,社会成了他研究其他问题和现象的立足点,法律如同道德、习俗和宗教一样,都只是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研究法律本身并不是目的,它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利益同时造成最小的损害和浪费。 既然社会才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中心,法学也没有必要过分强调自身的独特性和逻辑自洽性,不同社会科学之间不仅能够更应当相互合作和协力配合,“除非准备好接受各个学科之间持续而深入的相互重叠,否则连学科的核心部分都无法得以理解,更不用说核心之外的争议领域了”。(36)从实用自然法为特定文明时空下的社会提供更为具体的理想图景来看,实用自然法在庞德构建的社会学法理学中将不仅会超越法学流派之争,也会超越作为一门学科的法学和作为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的法律自身。接下来的问题是,法律难道真的就像庞德所说的那样,只有实现社会控制这一唯一功能而没有其他价值吗?近些年诉讼程序理论的发展彰显出与实体正义相对的程序正义的重要性,尊重法律、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本来就具有一种形式合理性的价值。并且,我们是否还应当反思,社会控制究竟是法的一种功能,还是法律得以执行和贯彻后产生的结果?是否存在“读者或作者用事后推理的方式来假定出现的结果是法律造成的原因”这样一种可能性?同时,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像纳粹德国这样的法西斯政权制定的法律,这时,法律并不必然是具有“为个人需要提供持久基础的功能”,还可以像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性主义者所主张的那样作为剥削和压迫一部分人甚至是大多数人的工具。(37)另外,“以社会为本位”的超越做法,在某种程度上也就宣告了法律自足性和独立性的破产,法律将有可能彻底沦为一种工具,那些今天对社会利益做出确认和规定的人,或许明天就会毫无顾忌地撤销这一认可,作为工具的法律背后将是一张威权主义的狰狞面孔。 (三)法律与文明的可能张力 法律实现社会控制还不是最终的目标,至少在逻辑上不是,社会控制是为了维持和促进文明。按照庞德的说法,文明使人类得以持续不断的发展,也是人类目前能够控制外界自然和内部人性的能力。(38)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大概可以看到文明的发展取决于对自然和人性的控制,人类本性如果不加以控制就将会像原始的自然界一样显露出野蛮的一面。因此,社会科学家应该像自然科学家有效利用自然一样充分发挥各种社会控制工具的作用以产生相应的社会效果,谋求对人性的全面控制,尽量减少与实现社会控制的目标相悖的人性可能。因此,在庞德预想的文明进步观念里,本来就应该对那些可能与文明不符的人性进行最大限度的控制,尤其是在这个社会化进程加快的现代社会,更需要在社会利益的集体目标之下抑制甚至消灭那些总是不能化约为社会利益的个人主张。结果,实用自然法下的社会利益将在文明进步和人力发展的合理化说明之下逐渐吞噬个人主义所能立足的最后一片净土。正像后来学者所总结的,庞德在学术事业上取得了令人无法企及的巨大成就,但是他的主要缺陷是在将人作为人来看待(see men as human beings)这一方面能力有限。这可能与他一生之中很少遇到亲密友谊有关,虽然他有许许多多的朋友,也许正是这一个人性格原因使得他缺乏建立一种私人的与他人亲密无间的关系的能力。(39) 反观实用自然法对法学流派的超越,庞德在潜意识里已经预设了只有实用自然法才能直接实现文明进步的价值判断。对法律及其运作的研究只有建立在“以社会为本位”的基础上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的社会控制功能,相比之下,诸如自然法学派、实证法学派等流派对于社会控制和文明进步的认识很大可能是停留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因为在这些学派的论述中很少提到法律与文明的直接关系甚至根本就不加关注,法律对文明的促进作用只是潜移默化的自然演进过程,无需刻意强调。但在庞德看来,这种“放任”的态度是不能容忍的,如同自然科学家缺乏对自然物之效用的认识一般,这将使我们在现有的基础上裹足不前,进而在人类何去何从的终极问题上迷失方向。然而,立足法律自身的研究,将实现法治同样作为一种善,难道就不能促进社会进步和文明进步吗?对于这样的疑问,恐怕庞德是无法回答的。 非常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中肯意见。 注释: ①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关于庞德的《法律史解释》和《法理学》第一卷的书评,尤其以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的三篇论文为代表,分别是邹立君:《从知识增量的角度解读罗斯科·庞德〈法理学〉第一卷》,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3期;刘小平:《传承与演进:法律哲学发展的历史——解读罗斯科·庞德的〈法律史解释〉》,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第3期;孙国东:《社会学法理学的可能代价和限度——从社会整合看〈法理学〉第1卷》,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9期。另有两篇论文也都是从著作本身入手得出庞德法律思想的独特之处,具体参见程乃胜:《何谓法理学——读庞德〈法理学〉(第一卷)》,载《河北法学》2006年第12期;姬小康:《法律史解释:一种理解法律哲学历史发展的方式——读罗斯科·庞德〈法律史解释〉》,载《河北法学》2007年第9期。 ②[美]庞德:《法律史解释》,邓正来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③吴经熊:《法律哲学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④Roscoe Pound,The Spirit of Common Law (Boston:Marshall Jones Company,1921),p.146. ⑤Erwin N.Griswold,“ROSCOE POUND—1870-1964”,78 Harvard Law Review(1964-1965),4-5. ⑥N.E.H.Null,“Reconstructing the Origin of Realistic Jurisprudence:A Prequel to the Llewellyn-Pound Exchange Over Legal Realism”,Duke Law Journal(1989),1308. ⑦Linus J.Mcmanaman,O.S.B.,“The Legal Philosophy of Roscoe Pound”,13 Cath.Law.(1967),98. ⑧Karl Kreilkamp,“Dean Pound and the Immutable Natural Law”,18 Fordham Law Review(1949),175. ⑨[美]罗斯科·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沈宗灵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58~63页。 ⑩马汉宝:《法律思想与社会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8页。 (11)Karl Kreilkamp,supra note⑧,180. (12)St.Thomas Aquinas,Summa Theologica,volume1-2,translated by English Dominican Fathers,1923,p.97. (13)这些质疑大致包括倒退文明的问题、价值判断不可避免、特定文明时空难以存在同质性、转型时期的文明问题以及人才问题等,具体参见Stone,“A Critique of Pound’s Theory of Justice”,20Iowa Law Review(1953),531-544.马汉宝先生也曾专门论述过庞德的法律基理所面临的问题,其中的质疑很大程度上就借鉴了斯通的看法,请参见注⑩,马汉宝书,第169~174页。 (14)James A.Gardner,“The 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 of Roscoe Pound”(part two),7Villanova Law Review(1962),188. (15)Jay Tidmarsh,“Pound's Century,And Ours”,81 Notre Dame Law Review(2005-2006),590. (16)邓正来:《社会学法理学中的“社会神”:庞德法律理论的研究与批判》,载《中外法学》2003年第3期。 (17)John Austin,The Province of Jurisprudence Determined (London:John Murray,1832),p.157. (18)颜厥安先生曾对法实证主义做过系统的归类,鉴于文章篇幅限制,这里将只关注狭义之法实证主义的代表性人物。具体请参见颜厥安:《法与实践理性》,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19)See Stanley L.Paulson,“Formalism,‘Free Law’,and the ‘Cognition’Quandary:Hans Kelsen's Approaches to Legal Interpretation”,27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Law Journal(2008),21. (20)Linus J.Mcmanaman,supra note⑦,128. (21)Karl Kreilkamp,supra note⑧,203.庞德其实在许多方面误用了自然法的学术概念,因其很大程度上是用黑格尔的理念来思考一些自然法的问题,这使得他的理论更像是一种技术,从而也显得比他自己所可能认为的更接近于分析法学。More concrete statements,please see,Rev.Dr.Francis J.Powers,C.S.V.,“Some Reflections On Pound’s Jurisprudence of Interests”,3 Catholic University Law Review(1953),22. (22)Arthur L.Goodhart,“Roscoe Pound”,78 Harvard Law Review(1964-1965),31. (23)N.E.H.Null,supra note⑥,1314. (24)N.E.H.Null,“Some Realism about the Llewellyn-Pound Exchange over Legal Realism:the Newly Uncovered Private Correspondence,1927-1933”,Wisconsin Law Review(1987),959. (25)David Nelken,“Law in Action or Living Law? Back to the Beginning of the Sociology of Law”,4 LegalStudies(1984),161. (26)范立波:《分离命题与法律实证主义》,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27)Rev.Dr.Francis J.Powers,C.S.V.,supra note(21),20-21. (28)H.L.A.Hart,The Concept of Law(seco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193. (29)Beau James Brock,“Modern American Supreme Court Judicial Methodology and Its Origins: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Legal Thought of Roscoe Pound”,35 Journal of Legal Profession(2010-2011),199. (30)[美]梯利:《西方哲学史》(增补修订版),[美]伍德增补,葛力译,商务印书馆,第619页。 (31)Henry W.Mcgee,Jr.,“Roscoe Pound's Legacy:Engineering Liberty and Order”,16Howard Law journal(1970-1971),24. (32)James A.Gardner,supra note(14),172,174. (33)Linus J.Mcmanaman,supra note⑦,106. (34)同注(30),梯利书,第618页。 (35)Elise Nalbandian,“Sociological Jurisprudence:Roscoe Pound's Discussion on Legal Interests and Jural Postulates”,5 Mizan Law Review(2011),142. (36)[美]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3页。 (37)Elise Nalbandian,supra note(35),148. (38)Roscoe Pound,Social Control through Law(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42),p.16. (39)Arthur L.Goodhart,supra note(22),37.另有一位学者也同样看到了庞德这方面性格的“缺陷”,他认为庞德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的不足其实可以追溯到他对人之本性(各个方面)理解的失败,特别是在人的本性及目的和法的目标及追求之间。Please see,Francis J.Powers,supra note(21),19.标签:自然法论文; 自然法学派论文; 法理学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理想社会论文; 法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