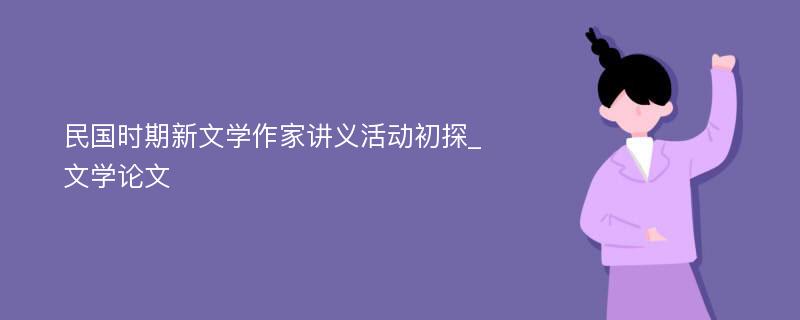
民国时期新文学作家大学讲义编写活动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讲义论文,民国时期论文,作家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国时期,鲁迅、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等众多著名新文学作家都有民国大学任教的经历。民国大学,教员授课多需先编写讲义,这些讲义多数为大学出版部印制的非正式出版物,数量庞大,有相当部分留存至今,但多数未作集中整理,散见于各大学图书馆、档案馆,国家图书馆、各省市图书馆亦有少量存藏。①也有一部分讲义正式出版,以专著或教科书形式留存至今。②整理现存讲义文献,在此基础上考察民国时期新文学作家的讲义编写活动,不仅可以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认识作家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同时还有助于探讨新文学与高等教育、新文学学科化进程等带有跨学科性质的问题。 一 民国时期新文学作家大学任教概况 众多新文学作家进入新式大学任教,主观上受大学丰厚待遇和优越环境的吸引,客观上,与民国新式大学在教师招聘时看重国外留学经历,而新文学作家恰恰大部分有海外留学经历有关。据统计,“在现代文学史上较为重要的300余位现代作家中,具有留学背景的竟有150位之多”③。 新文学作家进入大学,作家身份及其所从事的新文学创作无疑要让位于教员身份及其担负的专业教育职责,作家也要被大学教育重新分类:第一类仅讲授新文学及相关创作类课程,第二类讲授国文系其他课程,第三类则是在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同时也开设其他课程。 有些新文学作家虽在多所大学开课,但始终只讲授新文学及创作类课程。虽然数量不大,但作为执着坚守新文学创作、研究的一批作家,他们的教学活动流露出最初的现代文学学科意识。例如杨晦,先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孔德学院、青岛大学、西北大学等多所大学任教,一直只开设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艺批评两门课程;方令孺,先后在青岛大学、复旦大学任教,开设写作课,讲授诗歌、散文创作理论;汪静之,先后在安徽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任教,专授现代小说创作理论;白薇,在中山大学只授新文学赏析与创作;路翎,1948年起在中央大学任教,只开设小说写作课程。 也有一些作家执教于国文系,但是从未开设过新文学及创作类课程。虽然不排除这与个人的知识构成有一定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其间有可能渗透着他们对国文系专业教育的认知和思考。例如,鲁迅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任教,只开设中国文学史和小说史两门课程;刘半农、钱玄同任教北京大学国文系,只开设语言学类课程;郑振铎,先后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暨南大学任教,开设中国小说史、中国戏曲史、比较文学等课程;赵景深先后任教于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开设民间文学、童话研究、戏曲研究、小说研究、曲艺研究等课程;李劼人任教成都大学,开设文学概论、中国文学史等课程。 与前两种情况相比,更多的作家选择在讲授新文学课程的同时开设其他课程。从中既可以看出新文学作家为适应大学教育环境所作出的积极调整,也可折射出由于新文学课程所处的边缘地位,多数作家必须不断学习积累,开出主干课程以适应职业需要。 新文学作家在国文系比较集中开设的课程有三门。首先是文学概论。这门课在民国大学国文系基本都有设置,但讲授内容差异很大,涉及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艺思潮等。宽泛而富于弹性的讲授内容更便于作家开设。老舍、杨振声、李广田、李长之、张资平、吴文祺、许杰等都开设过文学概论。其次是中国文学史。作为国文系的主干课程,它的重要性自然对作家们具有吸引力。同时,文学史是西方舶来的课程形态,对于很多有海外留学经历或崇尚西方文学教育理念的作家来说,比较容易产生兴趣。文学史类著作的不断出版也为开课提供了丰富的参考资料。杨振声、刘大白、朱自清、台静农、刘大杰、苏雪林、林庚、张长弓等都曾开设过中国文学史课程。第三,外国文学课程。这类课程虽然当时在国文系并非最重要的一类,但在外文系处于核心位置,因而可同时供两系学生选修。得天独厚的留学经历和良好的外语能力,为作家们开设这类课程提供了便利。胡适、周作人、许地山、穆木天、陈瘦竹、老舍、沈雁冰等都曾开设过此类课程。 从新文学作家任教国文系的情况看,仅有少数人执守新文学课程,多数则开设新课另谋出路。从中可以体会现代文学学科化初期的艰难。新文学课程的边缘性以及生存的危机感自是“另谋出路”的原因之一,但对于敏感的作家们来说,来自国文系内部的轻视和由此带来的对新文学发展的困惑迷茫或许对其影响更大。西南联大遭受日军轰炸,刘文典大骂沈从文“你跑做什么!我跑,因为我炸死了,就不再有人讲《庄子》”④;苏雪林武汉大学讲授新文学研究遭遇学生“若不点名,谁也不愿意来上课了”⑤等轶事,正是新文学及其讲授者在国文系内部处境的缩影。朱自清则是基于对社会发展和国文系使命的思考,将特定内涵的“国学”教育视作自己的职业重心,而将新文学课程放在娱乐的位置。⑥1931年他在撰写《中国文学系概况》时,还将“创造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学”作为国文系最重要的教学目的之一,到了1934年再次撰写概况,则对新文学只字未提。⑦其间的变化清晰地标识出新文学课程初入国文系的处境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文学作家任教心态的变化。 二 形态各异的新文学作家课程讲义 为考察新文学作家的讲义编写活动,笔者选取了49位有明确大学国文系任教经历的作家,通过资料整理,将作家、任教学校与时间、所授课程、讲义名称、讲义形态与出版存藏等信息对应起来,进而得出相对完备的讲义线索。经整理,共集得49位作家的授课信息117条,其中有明确讲义编写活动的作家31位,集得讲义62部。这些讲义几乎涵盖彼时国文系全部课程,其中以文学史讲义数量最多。 出自新文学作家之手的上述讲义,形态上可大致分为简括型和专题型两类。 简括型是指多数作家所编讲义与其他教员的讲义相比,整体偏于简要、概括。“史略”、“简编”、“纲要”、“要略”,被新文学作家较多地用于各类文学史和新文学课程讲义的命名。从篇幅上看,这些讲义以“略”、“简”、“要”称之可谓名副其实。以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讲义为例,鲁迅在厦门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略》,闻一多在中法大学的讲义《中国文学史稿》,陆侃如、冯沅君在多校使用的讲义《中国文学史简编》,与非作家任教者(如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讲稿》、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等)的讲义相比,篇幅明显偏短,内容也更简略。 论简括,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从早期在清华大学讲授诗经,到西南联大时期开设唐诗、神话研究等课程,再到在中法大学讲中国文学史和神话,其课程讲义都非常简略。闻一多的课程讲义以两种方式保存至今:一种是作为未刊稿收入全集。包括在中法大学任教时编写的《神话与诗》和《中国文学史稿》,分别收入《闻一多全集》未刊稿和《中国文学史稿》第十卷《诗经》编;两部讲义均为提纲式,只简略列出章节名称、各级标题、主要观点和重点概念。另一种是根据学生课堂笔记保存下来并整理出版。此类有在清华大学任教时的《闻一多诗经讲义稿》⑧、西南联大时期的《闻一多先生说唐诗》⑨。两部课堂笔记的篇幅十分有限。对此汪曾祺回忆中有关课堂细节可为佐证。⑩一是闻一多的讲义本很大,字是写在特制的毛边稿纸上的,且专门收集使用别人用过的废毛笔,字是篆楷。这样的书写工具,决定了讲义不可能长篇大论。一是闻一多授课图文并茂,非常生动。以神话课为例,他用整张毛边纸画出伏羲、女娲的画像,口讲指画,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灵活多样的讲授方式,极强的语言组织和现场表达能力,决定了过于详细的讲义会成为束缚,因此提纲式是一种更适合闻一多授课的讲义形式。不仅闻一多,很多新文学作家的课堂讲授都非常精彩,胡适、鲁迅、俞平伯、老舍、沈从文等同样以此著称,留下了不少讲课“叫座”的校园轶事和教育佳话。 编写讲义是民国大学教育对教员的要求,大学也通过出版部不断对讲义进行规范(11),但从根本上说,讲义是辅助性教学工具,其内容和形式以满足教员教学需要为第一原则。一般来说,新文学作家往往思维比较活跃,乐于阐发个人观点,加之很多作家在演讲方面不乏社会实践,具有较强的临场语言组织能力,因而,简要概括的讲义在为他们的教学提供基本脉络和知识点的同时,也留下了可供发挥的空间,有利于体现课堂教学个性,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与简括型类似,专题型讲义在新文学作家讲义中也占很高比例。俞平伯在燕京大学“小说史”课程的讲义《谈中国小说》,孙俍工在上海劳动大学“中国劳动文艺史”课程的讲义《唐代的劳动文艺》,沈从文在上海公学、武汉大学“新文学研究”课程的讲义《新文学研究——新诗发展》,汪静之在暨南大学“小说通论”课程的讲义《作家的条件》,赵景深在复旦大学“中国小说研究”课程的讲义《小说闲话》,废名在北京大学“现代文艺”课程的讲义《新诗讲义》,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各体文习作”课程的讲义《习作举例》,苏雪林在武汉大学“新文学研究”课程的讲义《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许杰在暨南大学“小说戏剧选读”课程的讲义《现代小说过眼录》等,都是典型的专题型讲义。 专题型讲义一般围绕一个或几个与课程相关的主题编写,各讲内容独立完整,相互并列平行,深浅度没有差别,也没有先行后续的逻辑关系,教师可根据需要随机安排讲授顺序。专题型讲义的应用与新文学作家从事文学评论有一定关系。首先从讲义内容看,各讲都是对某一问题或问题某一方面做较完整的阐发,既是完整的一讲,也是一篇有重点、有例证、有层次的独立文章,这与评论文章类似;其次从讲义的结构看,相对松散的章节设计给了教员很大自由度,新文学作家可以结合最新的文学作品、研究动态和个人思考,安排和调整授课内容,使课程的时效性和个性凸显。这种展开方式与评论写作存在一定的契合,很多此类讲义也正是以评论文章的形式见诸报端。 尽管简括型、专题型的编写形态并非新文学作家讲义所独有,但他们的编写实践不约而同趋于这两种类型亦非偶然。简括型讲义多为作家开设文学史、文学概论课所编,其基本结构与其他教员所编讲义并无明显差异,但在具体内容安排上则常带有一定的个性化色彩。专题讲义多为作家开设选修课所编,与其他教员的专题讲义相比,章节的独立性更强,更接近于报刊文章。在大学教育知识化、体系化起步的时代,讲义编写当力求系统、全面、整饬,这已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从教者的共识,而作家为选修课所编讲义的形态显然与之不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家身份与教员身份之间的冲突,自由、发散、纵情挥洒的创作状态与客观、明晰、准确、系统的讲义编写要求相互抵触。担任教职的作家一方面需要有所调整,积极适应新身份的要求,另一方面在具体教学活动中又难免受到固有思维的影响,这样的特殊状态很自然地在讲义中有所投射。 三 新文学研究、写作类课程的讲义编写 在笔者重点考察的49位有国文系任教经历的作家中,开设新文学研究和写作类课程者鲜有完整讲义留存至今。这一现象并非偶然。 首先看新文学课程。在大学任教的作家中,开设过真正意义上的新文学课程的有十余位,所开课程总计近30门。但笔者搜集到的讲义线索仅16条,若除去系列讲座、暑期学校和实际开设在1949年后的,则仅有10部左右。这之中由大学出版部正式印发过的,仅有朱自清、沈从文、林庚、废名等人的五六部。稀少的讲义数量,至少反映出民国大学国文系内部新文学教育的两方面情况: 其一,国文系整体教研氛围的保守影响了新文学课程讲义编写。抗战爆发前,各大学国文系仍旧以文字、音韵、训诂、古典文学文献等为主要教学内容,创新主要体现于研究方法而非教学内容的拓展。学科基础越深厚,这一倾向表现得就越明显。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抗战前就都未开设过专门的新文学研究性课程。(12)即使较早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学校,教师也会感受到来自传统的压力。例如,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授“新文学研究”课程仅两年即不再开设,甚至放弃了“创造新文学”的教育理想;苏雪林回忆自己在武汉大学讲授“新文学研究”时谈道,“大凡邃于国学者,思想总不免倾向保守。武大中文系几位老先生都可说是保守份子”(13)。在压力下她不得不传统与新文学并重,自嘲为“只知写写白话文,国学没有根柢的人”(14)。这样的氛围无疑对教师编写新文学课程讲义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即使编写完毕,也容易受到其他课程的挤压而难以保证印发。 其二,对新文学课程的内容缺乏共识,影响讲义编写。新文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复杂的存在,不同的思想观念、政治姿态和美学趣味等在创作中并存,时或发生种种争鸣和交锋。这种状态对新文学引起社会关注、逐步发展为文坛主潮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时间距离尚未充分拉开的情况下,当需要基于一定的文学观和学理性确定高校课堂教学的内容时,就会面临困难。这些作家身份的教员虽然有着新文学创作实践,但此时尚未形成深入、系统、具有共识性的有关如何看待和评价新文学创作的观点和标准,倒是新文学建设参与者的主观因素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带入课程。于是,既有部分比较了解学科教育特点的作家尽量回避争议与分歧,也有一部分作家将课堂作为宣传个人文学观点的途径和文艺论争的战场。这加重了课堂讲授的随机性,更难以形成系统完备的授课讲义。 学科教育体系中的边缘化处境,教师讲授的随机性,客观上影响了新文学课程讲义的编写,同时也促使作家另辟蹊径为讲义寻求独特的传播形式——报刊发表;而课堂讲授的相对灵活,使新文学课一定程度上成为作家创作活动的延伸,内容比较适合成文。事实上,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废名的《新诗讲义》、许杰的《现代小说过眼录》,都是一边讲授一边在报刊发表,最终虽未形成系统化的课程讲义,却成为了颇有影响的报刊连载文章。 再来看与新文学教育关系密切的写作类课程。“各体文习作”是民国各大学国文系普遍开设的课程,40年代还被教育部列为国文系必修课。当时的知名大学多聘请著名作家讲授。但这门由作家开设的写作类必修课留下的讲义非常有限。笔者收集到的仅有:孙俍工1928年至1931年在复旦大学讲授诗歌习作的讲义《诗的原理》,沈从文1929年至1931年在上海公学和武汉大学讲授小说习作的讲义《中国小说史》,俞平伯1930年在清华大学讲授高级作文(词的写作部分)的讲义《词课示例》,孙席珍1930年代在中国大学讲授文艺习作的讲义《诗歌论》,沈从文在西南联大讲授各体文习作(白话文部分)的讲义《习作举例》,许杰抗战时期在广东文理学院、暨南大学讲授小说习作的讲义《鲁迅小说讲话》。完整讲义的稀少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彼时写作教育面临的两方面问题: 一是写作的经验性积累难以转化为系统性知识用于课堂讲授。刘文典曾在西南联大短暂讲授习作课程,“他告诉学生,其实写好文章并不是什么难事,只要大家记住‘观世音菩萨’这几个字就行了。……‘观就是要多观察;世就是要懂得人情世故;音就是要讲求音韵;菩萨就是要有救苦救难的胸怀。’”(15)这番话虽有调侃的成分,但很好地揭示出写作的基本条件,习惯、经验、技巧和情怀,这之中可以由课堂习得的只有技巧。不可言说的情怀在师生交流中尚可传递,而需要个人积累揣摩的习惯和经验要作为一种知识搬上课堂,并编写出系统完善、条理清晰的讲义,其难度可想而知。虽也有像路翎一样不顾教学要求,将写作课堂搬至操场、郊野者(16),但多数新文学作家还是顺应趋势,在认识到写作经验性与大学课堂知识性讲授之间矛盾的前提下,选择回避个人创作经验以提高写作课内容的客观性和知识性。这在讲义上有较为直观的体现。孙俍工授“诗歌习作”以荻原朔太郎理论著作《诗的原理》译本为讲义,沈从文与孙俍工授“小说习作”用小说史课讲义,沈从文授“各体文习作”以评析徐志摩等多位作家写作风格为主要内容……或翻译外国理论著作,或以文学史代之,或分析其他作家的作品,绝不涉及个人写作体会和经验,这反映出多数新文学作家讲授习作课的特定心理和做法。 二是习作课的开设方式也不利于完整讲义的生成。民国大学国文系的习作课有两种开设方式颇为常见,一是按语体分为白话文习作和文言文习作;一是按文体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习作。第一种方式在20年代至30年代初比较流行,北京大学国文系就是将文言文习作与新文学习作分别开设。随着白话文占据主导,第二种开设方式逐渐增加,清华大学、青岛大学、武汉大学在30年代均依据文体分别开设习作课。无论是按语体分还是按文体分,都是将习作课作了拆分,教师随之有所分工,往往只需要承担其中某一部分的教学,无形中削弱了课程的系统性,增加了讲授内容的随机性,同时也影响了完整讲义的生成。独特的开设方式便于发挥新文学作家在某一领域的优势,但不利于写作课程教学体系的形成和完善,也不利于在教学实践中产生具有系统性的、比较成熟的讲义和教材。 讲义编写是授课的先决条件,作家在他们所擅长的新文学研究和写作课的讲义编写中遭遇困难,且困难主要来自国文系教学实际和课程内容本身。在此情况下,多数作家自然更乐于将较多的精力用于准备那些对个人教职更有裨益的课程,与之相关的讲义编写活动随之呈现出另一番景象。 四 作家/教员身份与讲义编写 新文学作家讲授新文学研究或写作课顺理成章,但要开设国文系其他课程则要经一番努力,下一番工夫。多数作家在讲义编写上用功最多。首先,编写讲义是多数大学对教员的要求,相对完备、与课程相适应的讲义是开课的先决条件;其次,民国时期,各学科课程体系尚不完备,课程种类少课时多,教员编写讲义要付出较多的时间和精力;第三,民国大学同时承担“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17)和从事学术研究两方面职责,站在中文学科发展史角度回看,民国时期的很多重要著作或脱胎于课程讲义,或与著者所授课程相关,可见彼时课程讲义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教员编写势必投入更多。 很多任教大学的新文学作家都在日记、书信中或多或少地提及编写讲义的艰辛。鲁迅在北京大学开设小说史课数轮,学术积累、任教经验不可谓不丰富,但1926年下半年赴厦门大学国文系任教后,仍会流露出讲义编写的艰辛感。鲁迅任教厦门大学期间开设小说史和中国文学史两门课程,其中中国文学史课程需一边讲授一边编写讲义。鲁迅从一开始就对中国文学史讲义抱有较高期许。初到厦门大学,他在写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文学史,须编讲义。看看这里久存的讲义,则我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我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18)稍后信中又说:“我想不管旧有的讲义,而自己好好的来编一编,功罪在所不计。”(19)针对鲁迅强调讲义的学术性,许广平曾从教学角度做过提醒,“对于程度较低的学生,倘使用了过于深邃充实的材料,有时反而使他们难于吸收,更加不能了解”(20),但鲁迅对此似未作回应。中国文学史讲义每周需编写四五千字,鲁迅从9月27日起正式开始编写,每章(一讲)需要两天的时间。(21)如果从数量上看,编写压力似乎并不太大,但就是这看起来不甚困难的工作,着实让鲁迅倍感疲劳。他在9月30日的信中说:“只有两小时须编讲义,然而颇费事,因为文学史的范围太大了。”(22)10月28日的信中又说:“倘连编三四点钟讲义,便觉影响于睡眠,所以我讲义也编得很慢。”(23)从鲁迅自己的描述看,编写讲义的辛苦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对讲授内容的筛选甄别,一是难以适应连续编写的工作强度。 周作人任教北大期间的讲义编写也很典型。周作人于1917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讲授希腊文学史和近世欧洲文学史。两门课程均为每周两小时。由于是首次开课,故需一边编写讲义一边授课,讲义必须按时完成,否则将影响授课。这种讲义编写方式本身就会带来很大压力,而实际的讲义编写过程也确实占去了周作人大量时间和精力。翻阅周作人日记,考察其编写希腊文学史、近世文学史课程讲义的情况,可见其讲义编写分两步,第一步是草拟,第二步是抄录,然后交北京大学出版部刻印发放。从日记记载看,为准备两门课程,周作人每两到三天就要抽出至少半天或者一个晚上的时间编写讲义。(24) 由于对讲义有较高的学术期许,周作人虽感疲惫,但仍努力保证讲义具有较高的水准,这一点从其授课期间借阅和购买书籍的情况可见一斑。周作人1917年7月至12月借阅、购买与希腊文学、近世欧洲文学相关的图书资料情况如下:借《希罗文学史讲义》二册、阅《露国(俄国)现代文学》、阅《希腊民俗与古宗教》、阅《英国少年义勇团的组织》、购阅《民俗研究》、购阅《童话研究》、阅《心理研究》、借《希腊文学》、借《罗马文学史》、阅《文艺复兴》、购《古代艺术与仪式》、阅《莎士比亚》、借《人类研究》、购阅《文艺思潮论》、借《古代希腊哲学》、购阅《西班牙文学史》、购阅《希腊诗选》、阅《希腊悲剧论》、购《现代独逸(德国)诗选》、购《法兰西文学史》、购《爱兰文艺复兴》、购《法国六诗人》、购《近世德国文学之精神》。(25)在讲授希腊文学史和近世欧洲文学史前后,与两门课程相关的书籍占据了周作人借阅、购买图书的大部分。 讲义编写过程中,时间、精力的投入和较高的学术期待带来的艰辛感并非新文学作家独有,多数大学教员很可能都有类似体会。但作家思维向教员思维转换遇到的问题,则是新文学作家讲义编写活动中所独有的。鲁迅就曾谈道:“我今后的路还当选择:研究而教书呢,还是仍作流民而创作?倘须兼顾,即两皆没有好成绩。或者研究一两年,将文学史编好,伺候教书无须预备,则有余暇,再从事创作之类也可以。”(26)随着大学教育的发展和教员的职业化进程,大学教师成为令人向往的职业,“研究而教书”与“流民而创作”的对比,见出新文学作家在自由创作与大学教职之间的纠结。鲁迅、周作人这样学养深厚的作家在教学工作中尚能感受到大学任教在思维、身份转换上的困难以及编写工作的艰辛,其他作家的情况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时期,许杰曾在广东文理学院、暨南大学等高校开设“小说概论”、“小说研究”等课程。后来,讲义以“鲁迅小说讲话”为题出版。许杰在自序中称:“我为了要凑足作为一个专任教授的教学时数,须得开出几门课程,因而也就不得不把‘小说概论’和‘小说作法’之类的都凑上了。何况在那时以前,我也曾经写过几篇短篇小说,也曾经在报刊杂志上刊载过一些文章,无形之中,似乎也给我虚张了一番声势,证明我有此能耐似的。究其实际,却是可怜得很,我自己又何尝懂得什么小说理论,当然也没有学过什么小说作法的了。这些,我自己是心中有数的。但是,为了吃饭,也就不得不装出这一副样子来。后来我想,既然把课程开出来了,自然得找找当时所能找到的一些参考书籍。我事先备起课来,东抄西凑,横直总比学生先走一步,于是,走上讲台,照搬照卖,似乎还没有使学生听得打瞌睡,也就给我敷衍过来了。”(27) 鲁迅任教厦门大学期间与同事罗常培说过的一段话,很好地概括了作家任教过程中遭遇的思维转化难题:“研究需要沉下心去搜集材料处理材料,人的才智沉下去了就浮不上来,浮上来就不容易沉下去,所以研究同创作就不能同时兼顾。”(28)讲义编写的劳作之苦,与工作量密切相关,加之作家通常富于激情和才华,往往更为敏感而有个性,这与讲义编写所需要的客观、规范、体系性强等不无矛盾。在讲义编写活动中思维方式的调整对新文学作家来说并非轻而易举,由此也加重了他们的压力。 ①近年来,笔者以国文系为中心对课程讲义作了集中搜集,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东南大学等20所高校,共得到讲义线索403条,其中获讲义原稿151种,讲义出版物288种(部分讲义同时获得原稿和相关出版物)。 ②详见李瑞山、金鑫《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讲义集中出版现象概说——以中文学科为中心》,《出版科学》2015年第4期。 ③郑春:《留学背景与现代中国文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④张中行:《刘叔雅》,《柴门清话》,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6页。 ⑤《苏雪林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7页。 ⑥徐德明、李真:《朱自清传》,团结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⑦《清华周刊》1931年第11—12期以及1934年第13—14期的《中国文学系概况》。 ⑧刘晶瑶:《闻一多诗经讲义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⑨郑临川:《闻一多先生说唐诗》,《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4、5期,1980年第1期。 ⑩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见《人间草木》,汪曾祺著、傅光明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222页。 (11)详见金鑫《民国时期北京大学的书刊经售和“准出版”》,《出版史料》2013年第1辑。 (12)北京大学曾在1931年9月至1932年6月开设“新文艺习作”课程(《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课程表》,见《北京大学日刊》1931年9月14日),为便于论述这里将其视为写作类课程。 (13)(14)苏雪林:《我们中文系主任刘博平》,《走近武大》,龙泉明、徐正榜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15)章玉政:《狂人刘文典:远去的国学大师及其时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3页。 (16)朱珩青:《路翎:未完成的天才》,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17)《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2年10月24日部令第17号)第一条,见《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673页。 (18)(19)(21)(22)(23)(26)《两地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7、123~124、123、133、136、138、231页。 (20)《许广平文集》第3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38页。 (24)(25)《周作人日记》上册,1917年9月—12月,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 (27)许杰:《鲁迅小说讲话》自序,泥土出版社1951年版。 (28)罗常培:《蜀道难》自序,《苍洱之间》,黄山书社2009年版。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作家论文; 大学课程论文; 艺术论文; 周作人论文; 读书论文; 沈从文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