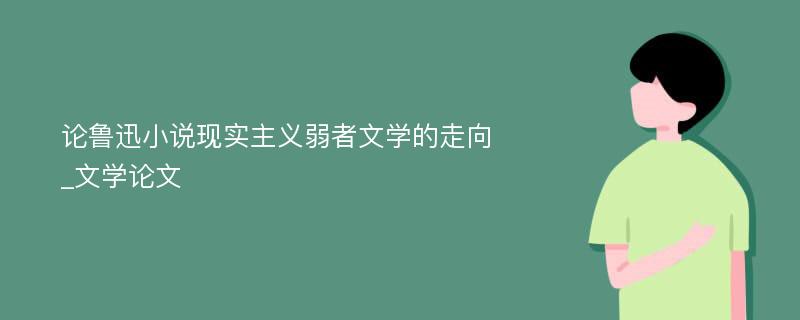
弱者的文学如何前行——论路内小说中的现实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弱者论文,文学论文,小说论文,论路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觉得,年轻根本就不是优点,而是……是一种残疾。”这是青年作家路内在他的代表作《追随她的旅程》里满腹牢骚中的一句。在人物接下来的解释中,一种深深的绝望感打动了许多年轻读者的心,作者写道:“年轻的时候老是被人欺负,跟残疾人一样,别人抽你一个耳光,你只好哭着回家,没劲。不过老了也没劲,也被人欺负。你说,到底怎么样才能不像个残疾人呢?”将年轻视作一种残疾,这不仅是在抒发年轻时遇到的委屈和不公,更是在刻画今天年轻人无力反抗的生存现实,压迫无处不在,希望却从来不遇,路内的作品充满着由深刻的生存绝望而带来的黑色幽默。你很容易在熟悉的文学谱系中找到这种黑色幽默的脉络,比如颓废的美国式的青春小说,或者王朔式的自我调侃的痞子文学,但细细体会,路内的故事又显然与这些青春故事不同。路内讲述的是一群特殊的年轻人的成长故事,《追随她的旅程》是路内追随三部曲系列之二,发表于2008年,同期发表的还有另一长篇小说《少年巴比伦》。和许多初涉文坛的作家一样,路内的创作多取材于他青春时期的真实经历,主要讲述的是一群技校生和技术青工的生活与情感状态。在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下,这类青年被统称为“三校生”(职业技术学校、中专、大专),其构成虽比较复杂,但他们共同的命运就是高考的失败者,或者根本无缘高考。在一个已经经由现代教育实现了区隔和规训的社会里,这群年轻人暗淡的前途在路内的笔下被渲染成一种远不止颓废、空虚、无聊的灰暗背景,他们身上有一种彻骨的失败感,但却没有失败的美感,有一种被抛弃的痛感,但却没有逆来顺受的伤感,有些许挣扎与反抗的火花,但最终却没有演变成革命的庄严,偶尔阶级的记忆与历史会灵光一闪,但却总会被无处安放的现实的沉重粉碎。当我尝试将路内的创作放在当代文学史的脉络中理解的时候,所有这些矛盾看来是之前许多问题的延续,路内的特殊性不仅是由他个人和他笔下主人公特殊的成长背景造成的,某种程度上,这些特殊的问题有更为普遍的接近当代中国青年与中国文学的意义。
一 成长为何不再可能
在《追随他的旅程》中,路内让一本残破的《西游记》成为他笔下主人公“路小路”的青春读本。关于这本书,作者这样理解:“四个有缺陷的人,结伴去寻找完美,当他们找到之后,世界因此改变。《西游记》的奥妙在于,在此寻找过程中,乃至到达天路之终,作者从未试图改变这四个人的人生观。他们就这样带着缺陷成为了圣徒,他们和《天路历程》不同,和《神曲》不同。我十八岁那年读罢此书,就觉得,像这样成为圣徒,真不知应该高兴呢还是忧伤。”我觉得,对《西游记》主题的这种理解,可以看作是路内为自己创作所做的一个注解。《西游记》和西方经典之间的差别是路内的成长故事与现代青年经典的成长故事之间的差别,理解这种差别对理解路内至关重要。
自19世纪初以来的中国现当代文学,青春叙事中最核心的内容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个核心内容就是成长。成长意味着个人经历一系列现实以及精神的危机,最终找到自己在世界当中的地位。当然,对中国特殊的革命历史而言,青春成长叙事同时也是特定历史年代的产物,它尤其特别“描摹了建国初期中国社会的青春风貌,也反映了这一时代赋予作家的诸种青春心态”。①显然,当代中国青年的青春故事是有时代性的,这个时代是以新中国政权的建立为标志,新的政权与青年人的人生姿态之间一直存在着相互借喻的关系。确实,我们从王蒙、茹志鹃、周立波等人的创作中,能够感觉出新鲜的极具中国特色的青春气息。但很快,对青春的压抑和规训,即教育的力量,开始出现在了这个建设不久的政权内部。一方面,出身论和成分论将一大批青年划归到了社会政治的边缘,这差不多划分了一个另类的青春时代。另一方面,“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又透露出新政权对红色接班人的担忧,青年成长的话题开始具有了严肃的政治使命色彩。重要的是,这类有着强烈政治“整体性”支撑的青春成长小说,不论是自下而上的个体改变,还是自上而下的集体规训,矛盾的最终和解是它们被一再讲述的最重要的原因。从《青春之歌》里有着典型小资产阶级性格的“林道静”,到《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中的极富社会主义事业心的新政权的建设者“林震”,以及《千万不要忘记》里的受教育对象“丁少纯”,当代文学中的成长故事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信念和阶级自觉。这种趋势发展到最后,体现个体成长的焦虑与痛苦的内容被不断压缩,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塑造的起点越来越“去问题化”,“高大全”的新青年形象在文学、美术、摄影、音像等载体中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最重要的审美符号。这类形象到了新时期以后,自然有了各式各样的蜕变,蜕变之一,便是以“伤痕”文学为代表的“问题青年”的出现。在之前的文学史叙述中,出于把握时代政治变革的考虑,“伤痕”文学所体现的问题多被直接地当作现实政治的反映来处理,但如果我们抛开这些看,究竟什么是新时期青年们成长中的核心问题?近几年,随着研究的推进,许多论者开始将问题集中在为什么社会主义历史没有生产出社会主义主体这样的根本性的追问中,在他们看来,中国当代青年从“潘晓”开始再度成为思想问题的核心,个人的成长,人生的意义,人生观的选择这些在毛时代不成问题的问题重新面临时代的挑战。只是这次,历史没有简单地重复,尽管问题相似,但时代不再是“五四”。经济主义大潮带来了全新的对“人”的定义,“人生的路啊为什么越走越窄了”——这一潘晓式的困惑和提问题的方式,从此成为改革开放后的一道斯芬克斯之谜,而路内式的“《西游记》青年”正是这道谜题苦求无解之后的青年人最新的自我认识。当路内说“到达天路之终,从未试图改变这四个人的人生观”的时候,成长的核心内容已经悄然发生了改变。路内用另外的一套话语逻辑阐释了自己对于新的成长故事的理解,成长不再是个体经历各种矛盾和磨难后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而仅仅意味着一个个破碎的个体注定要去经历的一段漫长的时间过程,“九九八十一难”,无尽的考验成了无聊的重复,“成为圣徒”背后的真理意义和终极价值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二 教育及其问题
事实上,对路内而言,没有生产出社会主义主体的那段社会主义历史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恰恰相反,他的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正是深刻而真实的社会主义印记。这些印记留存在作品的各个角落,也留存在人物生活的方方面面。首先,“职业技术学校”本身就是前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宝贵财富,在传统工人作家笔下——比如胡万春的作品——进技校进修,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是一个工人值得骄傲的经历。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至少到了“路小路”们成长的年代,技校变成了另外一番面貌。在《少年巴比伦》中,作者这样介绍了自己的学校:
戴城的化工系统有一所独立的职业大学,称为戴城化工职大,戴城化工系统的职工到那里去读书,就能拿到一张文凭。读这所大学不用参加高考,而是各厂推荐优秀职工进去读书,学杂费一律由厂里报销,读书期间还有基本工资可拿。这就是所谓“脱产”,脱产是所有工人的梦想。②
割裂地来看,“脱产”和脱产的梦想,似乎并不在中国工人文学的谱系中存在,“劳动最光荣”,产业工人、一线工人最高贵,这些思想一直是传统“车间文学”以及工业题材的现实主义文学想要突出的核心。在这些文学中,“脱产”是教条主义官僚主义滋生的温床,一定要批判。然而时过境迁,在路内笔下,第二代工人的生存内容应时代政治的变迁而变化,职业技术学校作为作者和他笔下的主人公最主要的活动场所,已经差不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消失,它存在的最后功能就是尽可能多地透支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福利,对这类教育资源的争夺差不多是路内的父辈们,上一代工人所能利用到的最后的社会资源。因此,在路内笔下此类学校多沦为腐败的暗角,普通职工的子女能进职大是非常困难的。另外,职高(职大)的教育状况非常糟糕,师资薄弱,教育目的含混,学生难以管理。但路内并不局限于传统的职业教育,他顺势将社会上其他各种名目的职业教育来了个大清洗,在他的描述中,这些职业教育根本就是以教育为名的赚钱机构,他们培养的“厨师根本不会炒菜,园丁根本不会养花,技工根本不懂技术,画漫画的根本不会画画”。这样的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不仅毫无理想可言,更毫无能力可言。曾经作为改变个人命运的教育制度,在路内们的眼里,像是个可有可无的必须完成的作业。进一步地,路内说,进入“重点中学的学生非常骄傲,你很容易就能把他们从人群中辨认出来”。③但这种闪光的身份并不持久,因为青年们很快发现,正规大学甚至名牌大学教育同样非常糟糕,《追随她的旅程》里也塑造了一些考上大学的青年形象,比如“杨一”,总之,所有社会提供给年轻人的教育与年轻人的成长之间是非常有距离的,这种距离是如何产生的,路内并没有深究,在路内的不做深究里,我们反而更能体会出一种深刻的悲观。尽管类似对教育的不信任在新锐的青年文学中非常普遍,从80年代初的刘索拉、徐星们,到90年代的韩东、朱文们,“文革”后的中国青年仿佛一直处在这种对主流教育体制的反抗中。但路内所展现出来的悲观却另有一种引人注目之处。众所周知,自改革开放以来,底层青年个人奋斗的正途就被规定为参加高考,接受正规教育,改变命运,正因如此,当代文坛才收获了像“高家林”这样经典的青年形象。所谓“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说的就是这一代青年在新的教育理念和价值观念之下的成长之路。就内容而言,路内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从社会主义传统教育体制的剩余出发,反观整个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体制的变革,在所谓市场化、专业化的导向之下,中国劳动力教育的断裂和残破之处清晰可见。由高考而带来的教育等级化更将职业教育学校逐渐挤压在社会最底层。80年代初上“中专”和考“中技”还是农村和小城镇青年的梦想之一。但是到90年代,路内和他笔下的人物很清楚,教育早已不是改变个人命运的途径,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无法从刻板而落后的学校教育中习得,因此,路内笔下青年的颓废叛逆,已经不仅仅是先锋文学式的对教育制度的简单嘲讽和不信任。先锋文学的颓废背后是个体的笃定和信念,那是一种非常“前卫”的精英的感觉,“它意味着敏锐,意味着独特,意味着对平庸的厌恶,对流行风气的超越,对现成秩序的反叛,甚至是对新的精神生活的投入……”④即使是对朱文系列作品中的主角“小丁”来说,颓废对他仍然有不容忽视的美学内容,那与一个现代哪怕是后现代的主体精神的确立密切相关。但“小路”们却别无选择:“我不是叛逆青年。我做工人就是这个样子,迟到早退,翻墙骂人,诸如此类的坏事,每个工人都可以去干。假如我去写诗,那我才是工人之中的叛逆青年。我还说到我堂哥,那个收保护费的,他也不是叛逆,他们黑社会里面的规矩比厂里大多了,谁敢不服?假如他去考大学,那他就是黑社会之中的叛逆青年。这种叛逆很少的,它不会被人扁,只会被人嘲笑。我一直认为,被扁的理想是值得坚持的,被嘲笑的理想就很难说了。”⑤类似的话经常在路内的作品中出现,这里作者是在用一种我们都很熟悉的风格来说一种我们其实都不敢直接面对的现实。“小路”的颓废没有了艺术的先锋色彩,却获得了真实生活的重量。在内容的滑动中,青春叙事的核心问题已经发生了改变。具体而言,以文学为“叛逆”,这差不多是上一代文艺青年们最重要的生活形式。这类形式是以个体突围为主,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抒情风格见长。比如余华的青春叙事,尽管路内声称自己受到余华的影响很深,但余华的冷酷和路内的冷漠是两回事。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现实对“我”的冲击带有非常强烈的主观体验性,这种心理体验一定程度上是先锋的个体用以确立起主体地位,宣布其长大成人的重要环节。当然,路内显然借鉴了,或曰沿袭了先锋文学所开创的个人主义风格。但路内们注定无法实现个人主义,这其中的原因我们需要继续探究下去。
余华之前,成长小说纠缠的总是个人与外部世界的二元对立,但经由先锋的“向内转”,某种可以称之为“自我成长”的东西开始占据青春文学的主导。那个在“我”十八岁的一天拍了拍“我”的屁股送我出门远行的“父亲”形象模糊而清晰,很好地象征着新一代青年成长的故事原型。理论上,我们可以说,这是由于占据真理位置的话语分崩离析了,主体需要重新确立自己的叙事风格。但只要文学的背后是一个现代主义的个人孜孜以求的主体性,那么这类文学就不出传统资产阶级文学的脉络。而与先锋小说不同的是,路内的小说明显无法塑造某一个特别突出的主人公,“我”成了他非常难以把握的形象。事实上,如前所述,路内非常善于描写“群像”,而且这些“群像”还是参差对照的,不是单一的。比如前面提到的各级各类中学的学生形象,另外比如工厂中各类青年形象,各类社会青年(无业或者自由职业)形象,包括接下来我将会提到的各种老工人形象。当颓废无法成为个体挑战社会的先锋形式,其现实指向和它所代表的群体便不能仅仅在文学史的脉络中来理解。路内无意间逼迫他的读者重新思考生活与风格之间、生活方式与审美方式之间更重要的联系。
三 经验如何传承
到此为止,路内式的成长小说有一个主题开始突出,那就是在一个没有真理性的时代,在一个缺少引路人的时代,如何完成青年的“教育”或者学习,或者“自我教育”、“自我学习”。事实上,在许多现代后现代的理论家那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哈贝马斯和利奥塔最深刻的分歧就在于现代神话是一项仍可以继续修补完善的工程,还是一个早就该彻底改造重头再来的新命题。当8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试图接续中国的现代性叙事时,他们并没有过多地怀疑这种接续的可能性。但是潘晓讨论其实已经在发问:西方经典意义上的现代性道路有深刻的问题,带着问题前行是可以的吗?我觉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认识和阅读路内式的成长小说的中国谱系才显得更为重要。
成长小说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往往首先体现在个人与家庭尤其是父与子的冲突中,这一冲突模式在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中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叙事-象征地位。在启蒙话语之下,代表新生、新知与未来的“子”辈们通过对父辈的反抗而成功地将现代性话语编织进中国的革命进程中;建国之后,父子冲突更多地在阶级对立中突出新的党—国话语对个人—家庭叙事的绝对领导,如此,“父”的形象逐渐被党的形象所取代;当然在“十七年”的小说中,也不乏“落后的父亲”形象,如《比能走那一条路》中的宋老定,在这些形象为了完成对儿子一辈——这一社会主义新人的叙事支撑:社会主义农村新人的世界观正是为了克服和超越传统的小生产者的价值观念而不是延续。新时期以来,这一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尤其到了90年代,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连接被市场经济的整体性彻底粉碎,父与子的象征性意义便不再具有不言自明的现实指向,尽管在文学中,它的表现表面上仍然是非常清楚的,比如王朔、余华,冲突逐渐去除历史语境而抽象为人性的矛盾,或者像更为年青的韩东、朱文一代,父亲形象很多时候就是落后的代名词,父子冲突更多地被通俗表现为代际冲突,革命和阶级的政治意味悄悄退场,文化矛盾,或者所谓人生观世界观的差异被突出出来。父亲成了这些年轻人调侃、嘲讽甚至教训的对象。在90年代这些表面简单的故事背后,其实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从社会主义历史中走过来的“父亲”的正面形象,为什么没有在新的历史时代下继续其“合法性”,他们的“落后”和不合时宜,他们的滑稽可笑,为什么那么真实——之所以深究这一问题,是因为在路内的小说中,一些重要的差异开始出现。
在路内们的成长道路上,除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工厂教育同样非常重要。在这些教育中,教育者——或者传统教育小说中“引路人”的形象——主要由爸爸、师傅、前辈、老师等组成。可想而知,路内对这些“引路人”的态度同样很不恭敬。而这些“引路人”也并没有承担起传统教育者的职能,他们最大的缺陷在于作为“引路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路在何方。小说《少年巴比伦》有一节专门写父亲带着儿子去拜访一位当了一辈子钳工的亲戚,作为一个基层技术工人,这位亲戚的出场被路内写得非常糟糕:
我堂叔家住在戴城的西区,此地从乾隆皇帝那一代起就是贫民窟,两百年过去了,差不多还是老样子,放眼望去,全是用毛竹和油毡布搭起来的棚子。这种棚子点火就着,小风一吹能烧出二十里地。我堂叔就住在这个地方。那天我爸爸带着我穿过贫民区狭窄的道路,绕过几条小巷,经过了一个淌着黄水的公共厕所,在一间黑擦擦的房间里找到了我堂叔。他们家简直就是一个钳工窝棚:椅子是钳工班里焊成的铁椅子;桌子是钳工班里厚重的工作台;电风扇是工厂里的老货,只有风翼、没有罩子的台扇,随时都能把手给削掉的那种。唯独那张床,是一种红木雕花大床,古朴苍凉,看起来像是我们家清朝的祖宗传下来的。⑥
如此困窘的生活状态显然无法显示任何榜样的力量。堂叔的生活也许就将是“我”未来的样子,这无疑加深了“我”的绝望感。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传统是重视榜样的力量的,但榜样的力量很少才从物质生活方面得到体现。从改革开放开始,是不是富裕,日子过得好还是不好,成为社会衡量一个人或一种生活观念是否值当的重要指标。时过境迁,当新一代工人要成长的时候,如何在最根本的生活层面把工人最骄傲的资本展示出来,这同样也是叛逆青年路内想要做到的。“堂叔”看起来确实有技术,但他这样教育年轻人:“做钳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捞点小外快,下班以后坐在弄堂口,摆一个修自行车的小摊,一个月差不多可以挣五百元。”以及,“做钳工还能收徒弟,徒弟得孝敬师傅,送上香烟白酒,否则什么都学不会,永远停留在二级钳工的水平上,永远拧螺丝的干活。”⑦这些“经验”如果从风格的角度看,倒也可以说这个堂叔很可爱。但如果我们从整个工人叙事的立场来看,堂叔的这些话丝毫体现不出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工厂的老工人身上有任何“社会主义”的特征。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对路内笔下这些本来应该体现出社会主义传统的形象特别关切。我发现,路内式的“引路人”们毫无例外地都在向青年传授底层工人生存的技巧。比如“我爸爸”曾说:“营业员一辈子都得站着上班,工人干活干累了可以找个地方坐着,或者蹲着,或者躺着,这就是工人的优越性。”⑧他还说,“在工厂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当然也要学会保护自己,遇到爆炸千万别去管什么国家财产,顶着风撒丫子就跑,跑到自己腿抽筋。”⑨这些话,在路内的语境中是真正的生活教材,是无比宝贵的财富,相比于书本知识,它们更直接,也更实用,甚至成了工人子弟相比于农民工们引以为傲的资本。在这种背景下,路内并没有简单地按照先锋文学的样子处理“父子冲突”,尽管父辈们的生活没有光环,但却是和青年人一样需要应对生活中的各种磨难。
显然,路内式的父亲在传递一种“经验”,一种生存经验,而传递经验本应该是前现代的父子叙事、成长故事中的核心内容。我走的路比你过的桥多,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或者用本雅明的话“借助年龄的权威”,用谚语、唠叨、故事,讲给儿孙辈们听。由经验构成的父辈们的故事,没有任何政治阶级革命的痕迹,仿佛是任何一个时代的手艺人们都会讲的故事,这些经验无法成为路小路们讽刺调侃的对象,因为他们注定要在这些经验中生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路内的创作并非经典意义上的成长小说,它缺少现代叙事中必不可少的矛盾项。或者说,在去历史化,去革命化的时代,父辈们已无“经验”可传递,“不是工人远离了政治,而是那时候的政治赶走了工人”。⑩他把许多矛盾都平移了,人物被放在了同一个水平面上,缺少了时间的指向。这使得路内的文字在风格上有了散文化的倾向,成长的历险性和故事性不再明显。这就像他自己说的:“十八岁真是无处可去,如果想去到更远的地方就要花很大的力气,而且很冒险。我并不怕冒险,我连冒险的机会都没有。”(11)这种特点对于成长小说而言可能是陌生的,但对于今天的文学接受而言,却非常熟悉。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所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摆脱缠绕在小说世界里的宏大叙事,故事性和带有生活气息的抒情性相互借重,逐渐形成了主流的审美趣味。人们对任何生活的经验都产生了兴趣,当然这其中最重要的经验是西方的、现代的生活经验。他们吃什么穿什么,跳什么舞步,唱什么歌曲,怎么谈情说爱,怎么打官司……这些内容不仅是文学的核心,也是中国人生活的核心。在这一轮的向西方学习中,日常生活的经验性获得了绝对的领导权。对文学而言,我更愿意将此变化视为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的背面。成长故事中有了社会秩序之外的经验的传承,有了教育和训导之外的可交流性,这为我们在今天的语境下重新思考文学的位置和意义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四 模仿与创造:弱者的文学如何前行
新世纪以来,一种被称为“底层”书写的文学潮流开始引起各方面关注。在这些关注中,写作者自身的身份——打工者、工人、底层人——是非常关键的,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了这些文学所涉及的内容,比如王十月与深圳作家群的创作;另外一类文学就是职业作家中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复活,比如曹征路、肖克凡等的创作。他们引发关注的地方反而是作品的内容,关注底层,关心普通劳动者成为他们成功的关键。路内与这两类写作相互关联,但又有一定的不同,进一步说,正是在所有这些文学的相互关联中,才引发了我对路内创作的关注,今天,一种关乎写作者主体生存痛痒的朴素的文学创作是否和如何可能?
古人云,人不平则鸣。这看似是件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办到的事情,然而当现实真正的不平迎面而来的时候,年轻人往往发现发出声音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事情。在路内的创作中,我们首先能够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熟悉感,这种熟悉感来自于由先锋文学和通俗文学所共同构筑的90年代风格:无聊、颓废、冷漠、伤感、温情,熟悉文学史的读者可能很容易在历史的沿革中放置该类文学的位置,称其为“第二个王朔”,或“青年余华”,或“中国的《在路上》”……然而风格上的接近或发展,并不意味着文学的真正创新。在底层写作中,我们往往会为作家们极其相似的风格所迷惑,孤独的个人、异化的心灵、陌生化的形式……写作对打工作家而言,一旦受到主流文学的裹挟,便不可避免地首先要将自己变成一个现代主义的个人。但诚如路内作品中所揭示的,先锋文学式的个人在今天是不可能存在的,一个有着严肃写作态度的作家,不会给这样的文学青年再次成长的机会。于是,深刻的分化出现了。在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史上,如何评价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艺术,以及如何建设革命的现实主义艺术之间,本雅明、阿多诺、布鲁诺、卢卡奇、比格尔、詹姆逊等等,都给出了或鲜明或调和的思想。然而就中国语境而言,这一问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众所周知,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一直被“纯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之间的斗争包裹着,在这种斗争中,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过时的”、“低等的”、“丑恶的”理论被纯文学逐渐取代。尽管不断有作家宣称自己的创作是现实主义的,但事实上这个概念所能激发起来的能量与想象并不多。在我看来,今天,以现代主义技巧突围的纯文学已经成功取得了合法地位。这种合法地位不仅体现在文学创作上,更体现在文学接受上。更为严峻的现实是,纯文学所代表的艺术自律的观念越来与成为这个社会的“肯定的文化”(马尔库塞),它越来越走向其最初革命性的反面。比如在王十月的创作中,尽管其内容多涉及普通工人的跳楼、讨薪、反抗,但因为刻意的内心化追求,这类作品首先让读者想到的是孤独、罪恶、丑陋以及更为重要的,对这些情绪情感的感同身受与适当调整。
综上所述,对今天的中国年轻作家而言,不论将严肃的写作态度命名为什么,文学写作的困境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生活世界的碎片化,生活意义的多元化,传统现实主义赖以生存的严肃性和史诗性消失,写“自己的生活”是否只是为文学世界提供一种不一样的资源,个人如何在这样的写作中为“自我”和“世界”找到合适的关联。路内的写作体现了一种彻底丧失意义世界的中国青年的悲苦,他的失败感,推而广之,正是中国式的现实主义所遭遇到的最大难题。第二,90年代以来一种被称作“后现代主义”的情感结构借由市场经济被生产出来,世俗生活的幸福感总是被不安定感、无聊感、空虚感摧毁。青年写作在内容和情感上由此变得琐碎而平庸,文学的合法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质疑。而借由路内的创作,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情感结构从之前刘索拉等的先锋知识分子到朱文等的新锐文艺青年,一路走来,发展成了一种普遍的中国青年的生活态度和情绪。因此,从审美上,文学是否依然能够创造出足以抵制这些情感的美学形式,是其能否继续下去的关键。第三,在一个阶层分化和贫富差距不断持续的社会,如果没有革命和斗争作为整合阶级的理论资源,后果会是什么?文学在今天必须承担他更为深刻的历史命运。如果把路内的创作与当下的底层写作,打工者文学及其他工人(白领或者职场)文学结合起来看,他们似乎面临共同的问题,写作应该不仅是他们改变个人命运的工具,更应该成为他们深刻认识社会人生的工具,成为他们参与社会斗争的武器。
注释:
①董之林:《论青春体小说——50年代小说艺术类型之一》,《文学评论》,1998年第2期。
②路内:《少年巴比伦》,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6页。
③路内:《追随她的旅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④王晓明:《在无聊的逼视下》,《视界》,2000年5月第1辑。
⑤路内:《少年巴比伦》,第128页。
⑥同上,第29页。
⑦同上,第30页。
⑧同上,第14页。
⑨同上,第25页。
⑩蔡翔《七十年代》,北岛、李陀编《七十年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31页。
(11)路内:《少年巴比伦》,第123页。
标签: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青年生活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西游记论文; 少年巴比伦论文; 追随她的旅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