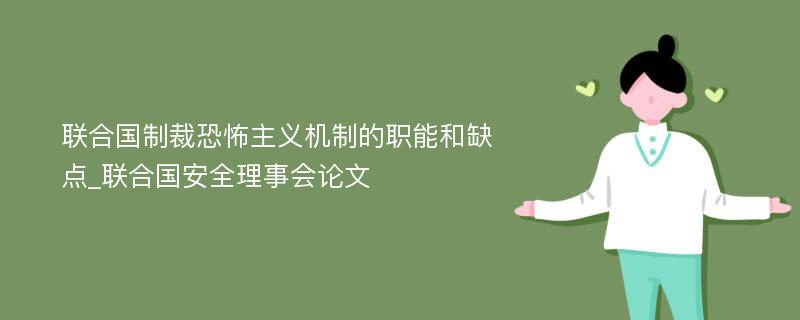
联合国制裁恐怖主义机制的功能和不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联合国论文,恐怖主义论文,机制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冲突与合作是国际政治研究者的经久话题。现实主义理论家关注冲突问题,探讨国际权力分配与国际冲突的关系。自由主义理论家关注合作问题,偏重国际制度对国际合作的意义。治理恐怖主义则是一个涵盖了冲突与合作的课题。“9·11”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充分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巨大危害,并致力于打击各类恐怖主义活动。在这些努力中,美国的单边主义方式占据主导地位。它强调利用强权打击恐怖主义,反映出国家与国家、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冲突的一面。考虑到单边主义政策无法解决恐怖主义的跨国流动问题,即使在其单边主义影响最盛的时期,美国也采取了多边主义的政策以争取其他国家的合作,这体现了治理恐怖主义对制度的需求。联合国制裁恐怖主义机制(下文简称制裁机制)正是这种需求的产物。当前,国内外研究美国单边主义反恐政策的成果很多,但系统分析制裁机制与国际反恐合作的成果仍然有限。
国内外的国际法和国际政治学者都对制裁恐怖主义机制进行了研究。国际法学者关注它的程序和价值缺陷,认为机制缺乏正当的列名和除名程序,并违背了人权原则。①国际政治学者则侧重于探讨该机制所处的困境、机制运作所依赖的动力和缺陷。加拿大学者卡尔娅妮·莫莎妮(Kalyani Munshani)指出,联合国反恐清单机制的运作由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推动,这些冲突使综合清单具有一种静态性质,因而不能满足国际反恐的需要。②美国圣母大学法学院的吉米·古诺(Jimmy Gurulé)教授探讨了制裁机制在冻结资产方面的困境,并认为这种困境的原因在于成员国的不合作。他建议,主要国家应当发挥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作用。对于那些不服从制裁制度的国家和地区,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将其列入不合作的名单(the FATF list of non-cooperative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NCCT])并予以公布。③显然,他希望美国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并进一步施加压力以迫使他国合作。该建议的前提是,不触动美国的制度霸权。国际法学者要求反恐不能违背人权,这有其合理性。相比之下,西方国际政治学者的建议则更多地着眼于为西方的外交政策服务,在忽视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和利益的情况下,一味强调反恐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以及他国制裁恐怖主义的义务。虽然相关的学者注意到了机制在推动国际合作方面的不足,却没有深入探究成员国不合作的根本原因。而且,他们也没有客观地评价制裁机制对于国际合作的贡献和不足。本文尝试对此作出分析。
联合国制裁恐怖主义机制是联合国制裁塔利班、基地组织及与其相关的个人和团体的规则、机构包括决策程序的总称。“9·11”事件后不久,安理会推动了这一机制的形成,它的前身是制裁国家的机制。1999年,联合国设立了制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1267委员会。由于该机制不能有效解决恐怖主义的问题,联合国又通过1333号决议(2000年),将制裁对象扩大到基地组织,并增设了监测机构。由此,制裁恐怖主义机制初步形成。2002年阿富汗战争后,随着塔利班下台,安理会出台1390号决议(2002年),进一步扩大了制裁对象,将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相关的个人和集团也包括在内。到2004年,安理会改组和强化了监测机构,设立了分析性支助和制裁监测工作小组(下文简称监测组)。至此,联合国制裁恐怖主义机制正式形成。它由决议形成的规则(设立综合名单、冻结资产和武器禁运等举措)和机构(1267委员会和监测机构)组成。制裁机制对国际反恐合作有哪些贡献?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国际合作?哪些缺陷限制了它发挥作用?为回答这些问题,下文将首先评估该机制的功能和不足,然后探讨这些不足的根源,最后加以对策分析。
一 制裁机制的功能
国际机制的功能,一般指机制所带来的行为模式的后果。④在罗伯特·基欧汉看来,国际机制有两大功能:一是惩罚功能。对故意违反机制的国家行为,机制具有惩罚作用;二是服务功能。机制为成员国提供高质量的信息,减少信息不确定性。⑤在国内学者门洪华看来,国际机制的功能还应该包括示范作用、规范作用和约束作用。⑥综上,对于国际合作而言,国际机制具有五大功能。不过,由于制裁恐怖主义机制应对的目标是非国家行为体,它的功能设计有别于处理国家间问题的机制,主要体现于该机制的惩罚作用。制裁机制在联合国里运作的方式只对成员国产生一种隐性的惩罚功能。如监测机构会把国家的不作为或不合作行为记录在案,甚至写进监测机构的报告。一旦这些报告成为联合国的正式文件,就会被永久记录,而有损相关成员国的名声。虽然如此,由于联合国有关制裁机制的一系列决议都没有明确规定对违规国家的惩罚。因而,国家间机制意义上的惩罚作用不适用于制裁恐怖主义机制。因此,制裁机制的功能主要体现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示范作用
示范作用,指机制给国际政治行为体带来新的主观认知与互动关系。⑦而且,在新认知的基础上,国际机制会促进国家形成模式化的新行为和对他国如此行为的预期。制裁机制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为成员国带来了新的认知与互动关系。
(1)综合清单。综合清单列有涉嫌恐怖主义活动的个人与实体的名字。2010年7月底,综合清单列有488个个人和实体。⑧在国际社会尚未就恐怖主义定义达成共识的情况下,综合清单为大部分国家指明了反恐的方向。在综合清单的示范作用下,一些国家或国际组织也仿照联合国制定了自己的反恐清单。它们是美国、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印度、欧盟和上海合作组织等。可以说,制裁机制有效地推动了新的认知与互动关系的扩散。
(2)成员国的报告制度。安理会的1390号和1455号(2003年)等决议,要求成员国向制裁委员会提交本国实施制裁措施的报告。2003年,安理会为此专门规定了成员国报告的指导准则。这些准则包括七大类26个问题,⑨体现了不同于应对传统安全问题的新思路。在机制运作之初,这种方式并没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有70个国家提交了报告。⑩在安理会、1267委员会和监测机构的推动下,有更多成员国接受了这种合作反恐的理念,并递交了大量有关国内反恐措施的报告。到2004年,88个国家根据1390号决议提交了报告。截至2009年12月4日,大部分国家根据1455号决议提交了报告,还剩32个会员国没有提交。(11)在联合国的制裁机制中,有如此数量的国家提交反恐报告,史无前例。
(3)制裁机构官员访问成员国的制度。为推动成员国重视制裁机制和评估成员国的制裁情况,1455号决议和1526号决议(2004年)分别授予1267委员会主席和(或)成员及监测机构成员访问选定国家的权力。由此,委员会和监测机构的成员开始亲临成员国的边防、海关前线以了解执行制裁的情况。这展示了一种新的互动关系,是联合国下属机构合法介入成员国国内事务的一种新的尝试。截至2011年2月,监测机构已经完成了对90个会员国的访问,有的是多次访问。(12)通过这种方式,成员国增加了对制裁机制的了解和重视程度。而且,访问制度带来了成员国对国家利益的新认识。如此众多的国家愿意接受制裁机构的访问,表明成员国意识到,遵循访问制度的要求符合本国的国家利益。
以上可见,综合清单解决了制裁对象的问题;报告制度和访问制度带来了新的制裁理念和互动方式。而制裁机构又进一步推动了这些理念和互动方式的扩散。它们在成员国中产生了一种示范效应。可以说,示范作用为制裁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提供了理念基础和合作路径。
(二)规范作用
规范作用,指国际机制使世界政治行为体的行为模式化和规范化。联合国制裁机制从两个方面规范了国际行为体。
(1)规范国家和国际组织与制裁机构的互动关系。1390号决议、1455号决议和1526号决议都要求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必须与制裁机构充分合作。对于成员国,制裁机制的规范作用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除了前文所述的成员国提交制裁报告,还通过《1267委员会工作准则》规范了成员提交新恐怖主义分子名单和从名单中除名的程序;(13)第二,机制规定了被列名者所在国或国籍国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的义务;(14)第三,机制还规范了制裁国的行为。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机制要求成员国给予被列名者以制裁方面的人道主义例外和豁免。(15)制裁机制也规范了与国际组织合作的方式。在安理会的推动下,制裁机构与联合国反恐委员会、1540委员会建立起协作关系。到2009年,监测机构已经联合1540委员会专家对成员国进行了12次访问。联合国还和空运协会、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刑警组织建立了新的合作关系,互相支持对方的反恐任务。2006年,监测组同国际民航组织和空运协会启动了打击非法空运武器和弹药方面的合作进程。(16)安理会还与国际刑警组织合作并定期发出通缉恐怖主义者的海报(或通知)。截至2008年11月,两个机构所发布的针对个人和实体的通知分别有308份和20份。到2010年9月底,该数据进一步增加,总计达到361份。(17)这些合作加强了制裁恐怖主义的国际力量。
(2)规范国家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关系。在一些地区,尤其是穆斯林社会,没有管理慈善机构或人道主义基金会的传统。这为恐怖分子滥用这类组织提供了机会。因此,安理会的1526号决议规定,为切断“基地”组织、奥萨马·本·拉登和塔利班等恐怖主义者与相关资金、金融资产及经济资源的联系,防止他们滥用非营利组织。(18)为此,制裁机构推动了成员国对国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到2003年,海湾国家已关闭了大约50个慈善机构,有40多个慈善机构处于官方监管之下。其中,沙特阿拉伯审计了245个国内慈善机构、冻结了它们的驻外办事处、关闭了12个慈善机构并禁止在商店和清真寺设置捐赠箱。(19)到2005年,成员国又进一步采取了管理非政府组织的措施。(20)
以上可见,规范作用解决了制裁合作的依靠力量(国家和国际组织)和手段(通过非政府组织的管理)问题。可以说,规范作用促使国际组织间的反恐合作和成员国对国内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成为一种模式化的行为。
(三)约束作用
约束作用,指机制对世界政治行为体的预期和行为的限制性作用。在确立自己的利益时,这些行为体必须把国际机制考虑在内,在机制约束的范围内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相关的行为体也会借此预期他者的行为。(21)制裁机制规定了国家制裁恐怖主义的两项义务:(1)将恐怖主义定罪。1390号决议规定,对那些属于制裁对象的本国国民和在本国领土内活动的相关个人或实体,所有国家必须采取立法或行政措施,完善国内法律或规章,保证采取有力措施将他们定罪或给予惩罚;(2)执行三大制裁措施:对清单中的个人和团体实施资产冻结、旅行禁令和武器禁运。在冻结资产方面,“9·11”事件后,约166个国家和司法部门针对恐怖分子/组织发布了冻结资产的命令,中止了相关的金融和其他经济交易,冻结了大量资产。(22)到2007年年底,36个成员国依据制裁制度冻结了约8500万美元的资产。(23)在军火禁运和旅行禁令方面,大部分国家声明已实行国内管制制度,没有发现违令者。可以认为,制裁机制在这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
由上可见,约束作用规定了国际制裁合作的内容。由于制裁机制的存在,成员国在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时,需要顾及这两方面的义务。只有在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不资助恐怖分子,不向恐怖分子提供庇护地,不向他们提供武器及训练的情况下,成员国才能合法追求自己的利益。这些义务阻止了一些成员国对恐怖主义的资助,也形成了他国不资助恐怖主义的预期。
(四)服务作用
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中,由于没有最高的权威,信息的不确定性使国家间互动的成本极为高昂。而国际机制可以向国际行为体提供可靠的信息和信息交流的渠道,加快信息流通,降低信息不确定性。(24)所谓服务功能,就是指国际机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采取的努力,它为制裁合作提供了外部条件。例如,1267制裁委员会和监测机构的活动宗旨即是为成员国服务,为他们提供可靠信息,如国际反恐的现状和制裁对象的准确资料等。
首先,制裁机构的报告为成员国提供了国际反恐现状的信息。安理会要求1267委员会和监测组定期汇报现有制裁措施的执行情况,评估其存在的问题。自2004年后,制裁委员会主席多次向安理会口头汇报各国实行制裁的情况和制裁机构的工作。在分析和评估成员国报告的基础上,监测机构向安理会提交了近二十份书面报告。这些报告减少了成员国获得国际反恐的现状和信息的交易成本。
其次,提供制裁对象的准确资料。为了向成员国提供可靠的恐怖主义名单,安理会要求1267委员会定期更新综合清单。更新的内容主要是补充识别信息。所需的识别信息包括制裁对象的全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国籍、地址和居住国等内容。在初期,综合清单上的人员缺乏足够的识别信息。如2003年,清单上的34位人员仅提供了姓名。因此,在执行过程中成员国经常遇到重名问题。据监测组的报告,葡萄牙曾经发生过一个金融机构数据库内大约有50人与联合国清单上个人姓名相同的情况。一些国家也表示,由于缺乏最起码的识别要素,无法将联合国清单上的某些人员列入国防管制程序。为改变这种情况,安理会的1455号决议(2003年)在要求成员国提交新名单的同时,规定会员国必须竭尽所能向1267委员会提供被列名者的识别资料,以便在综合清单上增加更详细的信息。(25)为此,监测机构也多次向成员国索取清单所列个人的资料。最后,结合成员国和国际刑警组织所提供的数据,1267委员会多次修订名单,不仅增加了综合清单中的识别信息还优化了名单格式。仅2007年一年,制裁机构就对名单上的现有条目进行了324次修改。2010年,制裁机构又对名单作了465项修订,涉及391个现有条目。(26)这些措施有效地减少了成员国实施制裁的困难。
第三,提供与清单所列实体相关的机构的资料。在冻结资产时,如何处理一些跨国的非政府组织,如慈善组织,成为制裁方的一个难题。它们遍布世界各地的办公室或者分支机构,为恐怖主义资金转移提供了便利。要查清楚这些办公室和分支机构绝非易事。而制裁机构正是从成员国的报告中获得了大量有关这些非营利组织的分支机构和办公室的信息。如与基地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国际仁爱基金会有20个分支机构,全球救济基金会有22个分支机构。(27)通过制裁机构对成员国报告的汇总,那些分支机构和办公室的信息陆续被更多国家所掌握。
制裁合作所需的理念基础、合作路径、依靠力量和手段、制裁的内外条件一一具备后,在国际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制裁恐怖主义的国际联盟。这个联盟既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国际组织等成员。由此可见,机制增强了制裁恐怖主义的国际力量,也提升了冻结资产、军火禁运和旅行禁令的效力。对于那些受恐怖主义危害的国家,制裁机制成为一种有益的公共产品。它防止了成员国公然资助恐怖主义,明确了国际反恐的对象,并推动越来越多的国家采取制裁措施。可以说,制裁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那些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的恐怖主义者的力量,并形成了一种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新模式。
二 制裁机制功能的不足
从理论上来说,制裁机制对所有的联合国会员国都具有约束力,无论是超级大国还是中小国家。因为设立该机制的决议注明,安理会依据宪章第七章采取制裁行动。而《联合国宪章》第25条规定:“联合国会员国同意依宪章之规定接受并履行安理会之决议”。但事实上,并非所有成员国都遵从机制的规则。考察了成员国的遵约情况后,我们发现制裁机制存在以下不足:约束功能较弱;示范作用范围较窄;规范作用的效用有限和服务功能的质量不高。
(一)约束作用较弱
约束作用的不足体现于两个方面:首先,机制对制裁行为的约束能力较弱。按照监测机构的报告,综合清单涉及89个国家。其中,58个国家是综合清单中的国籍国、居住国或注册地国。(28)按照机制的约束功能,本该有58个制裁国。但事实上,实施冻结资产的制裁国家只有36个。按地区来划分,欧洲、欧亚地区和北美约占70%;南亚约占8%;近东占21%(主要在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东亚地区和非洲所占比例不到1%。(29)而且,在所冻结资产总价值中,95%以上由其中九个国家执行。与此类似,按照监测机构的说法,旅行禁令和武器禁运的措施也没有受到成员国足够重视。(30)可以说,制裁国具有数量少和地区不平衡的特征;其次,按要求提交新恐怖主义者名单的国家较少。在2004年和2005年,提交名单的成员国较多,分别为21个和18个。目前,名单的提交国不超过50个。提名国的数量少,并不代表成员所掌握的恐怖分子少,一些国家的情况恰好相反。在2003年,埃及、约旦、科威特、黎巴嫩、摩洛哥、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也门均报告逮捕了据称属于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个人,(31)但这些国家不愿提供名字。制裁国和提名国较少,表明制裁机制的约束功能仍然较弱。
(二)示范作用范围较窄
正如上文所述,制裁机构访问了90多个国家。虽然,访问制度的实施较为顺利,但报告效果并不理想。从数量来看,有32个国家仍未提交报告,这远逊于1373号决议机制下成员国全部提交报告的情况。而且,虽然大部分成员国汇报了国内的反恐情况,但正如监测组指出的,大多数报告是描述性的,既未具体陈述该国为实施制裁制度而采取的行动,也未提供其他有益信息来回答提问,纯粹是走过场。(32)很明显,大部分国家只是为了履行义务而报告,不是为了反恐。从报告的质量看,愿意受机制约束的国家较少。可以说,报告制度的实际普及范围仅限于那些在反恐问题上利益攸关的国家。此外,也不能高估综合清单的示范作用。仅有上文提及的几个地区或国家设立了自己的反恐清单,示范作用的影响范围仍然较窄。
(三)规范作用效用有限
在规范国际组织和成员国管理非政府组织方面,我们同样不能高估制裁机制的功能。一方面,从国际组织来看,现有机制主要规范了制裁机构与国际刑警组织、民航组织和国际空运协会及联合国系统内的反恐机构的互动关系。而对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类与制裁密切相关的组织,制裁机制并没有发挥重要作用。正是这一点限制了制裁机制的规范效用,而其作用的有限性难免会削弱制裁机制的声誉。另一方面,在制裁机制推动成员国管理本国的非政府组织方面,规范作用仍然有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要有效管理非政府组织,尤其是那些具有跨国活动能力的非政府组织,不仅需要国家层面的努力,还需要国际层面的应对。从管理非政府组织的实际后果来看,相关国家不愿将违规的非政府组织列入制裁清单。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无法获得这类非政府组织的相关信息并从国际层面进行治理。以上两方面显示,制裁机制规范作用的效用有限。
(四)服务功能质量不高
机制的服务功能本应为成员国提供更全面和准确的有关恐怖主义者的信息。但有资料显示,“9·11”事件后,102个国家逮捕了超过4000名与基地组织有关的恐怖分子。(33)而制裁机制产生以来,综合清单的人名总数仅有500个左右。这表明,制裁机制的服务质量远不能满足国际社会的反恐需求。何况,有效的制裁依赖于高质量的综合清单。只有在综合清单提供了详细的识别信息的情况下,成员国才能定位制裁对象,进而采取制裁措施。尽管制裁机构对综合清单作了多次修改和补充,但事实上,缺乏足够的识别信息一直是综合清单的硬伤。如,2008年5月的综合清单有482个人名,其中的57个未列出全名和出生日期;另外5个名单仅仅有全名和出生日期;其他的26个条目列出了名字、出生日期和出生地点,但却没有诸如国籍、地址或居住国等任何其他识别资料。(34)可以说,只有392个名单具有准确性。在完善识别信息方面,制裁机构的服务质量同样不高。
综上可见,虽然制裁机制对国际反恐合作具有积极意义,但也不能无视其功能的局限性。正是这些局限性限制了制裁恐怖主义的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对其原因,制裁机构归之于成员国的能力不足和不配合。(35)的确,在执行制裁时,有一些国家缺乏相应的能力,某些小国甚至缺乏制裁所需的人才和设施。但这样的小国毕竟是少数。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缺乏能力不是他们不配合联合国制裁机构的主要原因,在其身后有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因素。
三 制裁功能不足的根源
宏观层面的因素主要是权力分配和相互依赖。微观层面的因素来自制度本身,即制度的健全度和透明性。宏观和微观层次的因素相互作用,影响了成员国的反恐合作意愿。
(一)权力分配
奥兰·杨指出,在构成要素(in material sense)上,国际机制参与者之间的权力分配严重失衡限制了机制的有效性。(36)权力分配的失衡同样也会限制制裁机制的功能。联合国制裁机构在权力分配上的严重失衡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首先,核心规则由美国、英国和俄罗斯等国主导制定;其次,在联合国制裁恐怖主义机构中,西方国家的官员占主导地位。(37)可以说,制裁机制具有浓厚的西方色彩,机制中的权力分配不利于非西方国家的作为。虽然这种严重的权利不对称便利了制裁机制的建立,但弱小无权者往往成为不合理机制的受害者。因此,在本国没有决策权的情况下,一些非安理会的成员国不愿采取合作态度。另一方面,制裁机制的西方色彩进一步加强了这类被列名团体的敌对态度。早在阿富汗战争后不久,本·拉登就指责联合国对穆斯林犯下了罪行,指责那些自称是阿拉伯领导人而同时与联合国合作的人是异教徒。(38)2004年5月,本·拉登悬赏刺杀联合国秘书长安南。(39)这种威胁性的姿态更坚定了一些成员国的不合作态度。例如,20多个列入综合清单的个人据调查为突尼斯国民或居民,但突尼斯的报告却没有提供详情,(40)那些抓到相关人员的国家也不愿提交名单。
(二)相互依赖
成员国的合作意愿还与国际政治中的相互依存度有关。恐怖主义袭击使得这种相互依存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恐怖主义势力所针对的目标主要是西方国家。为从全球层次上打击恐怖主义,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的依存度提升。这改变了非西方国家对西方的单方面依赖局面。在反恐方面,非西方国家的对外依存度较低。另一方面,跨国恐怖主义的发源地大部分处于非西方世界。如果这些国家配合联合国的制裁机制,有可能引发国家内部矛盾上升的危险。(41)因此,尽管西方国家对非西方国家有反恐合作的需求,但非西方国家只能在确保国内安全和稳定的情况下提供反恐合作。这也是综合清单所涉及的国籍国与居住国虽多,实际参与制裁的国家却较少的原因。
(三)机制的健全度
国际机制的健全度是指它在程序方面的完善程度。在健全度方面,制裁机制的不完善体现在综合清单的运作程序和缺乏对违规国家的惩罚性规定。其中,综合清单的运作程序缺陷在于列名和除名程序的规则。1267委员会的列名和除名规则不同于安理会的议事规则。在安理会,程序性事项的表决需要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对于非程序事项或称实质性事项的决议表决,要求包括全体常任理事国在内的9张赞成票。而1267委员的表决需要安理会全体理事国的同意。也就是说,安理会的任何成员都拥有否决权。这项规则使除名过程耗时冗长。麦瑟·阿登(Messrs Aden)和阿里(Ali)的案例就表明了这一点。他们的居住国瑞典政府曾两次请求1267委员会将其除名,但都遭到拒绝。(42)第二次申请时,制裁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同意解除对他们的制裁,但由于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反对而未能达成一致。后经瑞典和美国多次协商,并向美国提供两人与基地组织没有任何联系的证据,安理会才解除了对他们的制裁。截至2007年,经制裁机构除名的仅有5人。一名来自英国,其他4人分别来自瑞士、瑞典和德国,后三个国家通过长时段的外交游说才达到目的。这方面的缺陷限制了成员国提交更多名单的意愿。一些国家直言,因为制裁机制缺乏健全的除名机制,自己在向综合清单提名时犹豫不决。(43)另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述,制裁机制没有惩罚违规国的规定。不设立惩罚性规定不仅削弱了了安理会成员国自身的约束,而且导致一些国家的不作为。监察机构的报告指出,如果不进一步提醒,一些会员国甚至会忘记1390号决议所规定的提交报告的义务。(44)可以说,制裁机制本身的缺陷,限制了机制进一步推动国际合作的功能。
(四)机制的透明度
国际机制的透明性指机制的设立、规范的建立、组织的创设和机制的运作程序具有公开的特征。联合国制裁机制的不透明体现于它的运作程序,即综合清单的列名和除名程序实行了闭门会议。机制不透明带来了两种后果:一是闭门会议导致15个理事国对列名和除名权的垄断,也使非理事国得不到与理事国同等的信息。在决策权不平等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很难出现更多国家提交新名单的情况;二是闭门会议极易引起误列名的现象。误列名现象的直接受害者是被列名者,而间接受害者是与列名者相关的国家。而第三国误列名单的行为,可能会使相关的国家陷于反恐不力的窘境,并因此蒙羞并有损于相关国家的双边关系。上述后果已经引发了成员国对机制不透明的不满。2006年,50多个会员国对该机制的透明度提出质疑。(45)2010年,不结盟运动也吁请安全理事会制裁委员会精简其列名和除名程序,以确保正当程序和透明度。(46)显然,机制不透明降低了一些国家参与制裁的热情和意愿。
联合国设立国际制裁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国际合作来治理恐怖主义。与其他国际机制类似,只有机制使成员国获得相对收益,才能顺利运行。毋庸置疑,制裁机制的实施给深受恐怖主义危害的国家带来了收益,反过来也进一步推动了机制的发展。如果没有制裁机制,很难吸引这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入制裁的行列。如果没有监测机构,未必会有如此众多的国家汇报本国的制裁情况,成员国也难以及时获得最新的全球反恐信息。不可否认,制裁机制对国际反恐作出了重要贡献。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罗斯玛丽·迪卡洛(Rosemary DiCarlo)指出,过去11年来,制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制度一直是联合国最有效的反恐工具之一,也是世界各国一致应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威胁的象征。(47)正是由于制裁机制的贡献,美国国内对联合国的支持度迅速上升。根据2009年的一项民意调查,在备选的八项反恐措施中,联合国反恐制裁机制获得了84%的美国人支持。(48)这改变了克林顿时期美国国内强势的反对联合国的声音。
与此同时,也不能夸大制裁机制的功能。在促进国际反恐合作方面,制裁机制还存在一些缺陷:制裁国和提交相关名单的国家数量较少,成员国的报告质量差,无法规范强势的国际组织,综合清单质量低等。事实上,它仅仅获得了部分国家的支持,它的实际功能远未达到它的初始目标,即在全球范围内制裁恐怖主义。机制不能得到广泛支持的原因在于成员国的不配合。其背后更为深层的原因在于权力分配不对称和相互依赖的变化以及制裁机制本身的不健全和缺乏透明性。十年来,尽管国际社会治理恐怖主义的事业已经取得了进展,但正如沈丁立教授所言,基地与美国一百年不会言和。(49)因而,治理恐怖主义仍然是世界各主要国家的重要事务,制裁恐怖主义机制也会长期存在。要进一步提升治理恐怖主义的效力,就需要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的反恐合作。这需要联合国制裁机制自身的完善,需要改变机制中的权力分配不对称和相关国家在相互依赖中的困境。
要完善制裁机制,一方面,安理会应当改革综合清单的列名和除名程序,采取安理会的表决规则,而非一致同意原则。另一方面,为增强成员国的国际义务的意识,制裁机制应该增加惩罚性规定。与一味强调金融行动工作组作用不同的是,笔者认为,在平衡权力分配和努力根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的同时,制裁委员会可以借鉴反洗钱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的做法,设立类似的自有名单。依据这个名单,联合国的发展援助机构对相关国家提供不同待遇。这既可以产生激励作用也能成为一种变相惩罚的手段。此外,制裁委员会还需要提高其运作的透明性。虽然闭门会议的行事方式便利了理事国内部的协调,但闭门会议并不能阻止外界了解安理会内的斗争。(50)既然反恐是正义事业,制裁委员会不妨改变闭门会议的行事方式。
在权力分配方面,主要大国应当意识到反恐问题的复杂性和对外依赖性。尤其对于西方国家而言,要成功治理恐怖主义,非西方世界的合作必不可少。大国需要改变制裁机构的西方色彩,提升非西方国家在制裁机构和监测机构中的人员配额。由于制裁涉及89个成员国,西方国家可以在保留其人员配额的情况下,扩大制裁委员会和监测机构的成员。既可以提升非西方国家的地位,也能增强其国际责任的意识。对于相互依赖因素所造成的困境,并非是制裁机制范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制裁是治理恐怖主义的不可缺少的手段,但它终归不能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要提升一些国家的合作意愿,就需要结合其他手段,如发展援助,减少非西方国家内部的困境,逐渐消除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使相关国家在反恐合作方面无后顾之忧。
注释:
①Larissa Van Den Herik,"The Security Council's Targeted Sanctions Regimes:In Need of Better Protection of the Individual",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0,2007,pp.797-807; Peter Gutherie,"Security Council Sanctions and the Protection of Individual Rights",New York University Annual Survey of American Law,Vol.60,2004,pp.491-541; Andrew Hudson,"Not a Great Asset:The UN Security Council's Counter-Terrorism Regime Violating Human Rights",Berkele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25,No.2,2007,pp.203-227;王孔祥:“强行法与公正审判权的冲突—联合国安理会1267号决议评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33-37页。
②Kalyani Munshani,"The U.N.Consolidated List:Effect of Committee Dynamics on Creation and Compliance",Cardozo Law Review,de·novo,2009,pp.284-310.
③Jimmy Gurulé,"The Demise of The U.N.Economic Sanctions Regime to Deprive Terrorists of Funding",Case Western Reserv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Vol.41,Issue 1,2009.
④Robert O.Keohane,"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6,No.2,1982,p.333.
⑤Robert O.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pp.80-83,92-93.
⑥在门洪华的分析框架里,国际机制的另一个功能是惯性作用。由于惯性作用更多的与机制的变迁相关,与国际合作缺乏直接的联系,笔者在此省略了这一功能分析。参见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6页。
⑦Peter M.Haas,"Do Regimes Matter?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Mediterranean Pollution Control",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3,No.3,1989,pp.401-402.
⑧联合国文件,S/2010/497,摘要,第1段。
⑨Http://www.un.org/Docs/sc/committees/1267/guidanc_en.pdf.
⑩截至2002年8月12日的数据。参见联合国文件:S/2002/1050,第103段。
(11)联合国文件,S/2004/1037,第12段;S/2011/245,第77段。
(12)联合国文件,S/2011/245,第72段。
(13)Http://www.un.org/chinese/sc/committees/1267/committee_guidelines.pdf.
(14)联合国决议,S/RES/1617(2005),第5段。
(15)联合国决议,S/RES/1452(2002)。
(16)联合国文件,S/2006/750,第112段。
(17)联合国文件,S/AC.37/2008,第20段;S/2010/497,第67段。
(18)联合国决议,S/RES/1526(2004),第4段。
(19)这些估计数字由著名的反恐专家阿米尔·塔赫里汇编;参见2003年5月12日《纽约邮报》,阿米尔·塔赫里的文章“恐怖的秋天”。另见沙特阿拉伯发言人阿德尔·朱拜尔的讲话,刊登于2003年5月18日《福克斯星期日新闻》,后来由驻华盛顿特区的沙特阿拉伯王国大使馆公布。转引自《监测组关于对基地组织、塔利班以及有关的个人和实体实行制裁的第二次报告》,S/2003/1070,第38段,http://www.un.org/chinese/sc/committees/1267/experts.shtml.
(20)这些措施包括:(1)向其他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改进慈善部门的法人管理和监管。英国通过英格兰和威尔士慈善委员会,向中东、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一些国家提供技术援助。这些援助帮助接受国采用英国的制度作为模式,加强慈善部门的治理;(2)阿联酋要求海外慈善组织以实物形式(如货物和服务)而非资金形式提供援助,以减少挪用捐款的危险;(3)沙特阿拉伯设立机构,以监管所有海外慈善活动。沙特在通知捐款接受国的同时,还采取逐个批准海外捐款的政策;(4)美国则对其管辖范围内的慈善机构,发布了关于理事结构、财务透明性和责任制以及防止资助恐怖主义的程序诸方面的指导意见。联合国文件,S/2005/572,第88段。
(21)门洪华:《和平的纬度: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研究》,第103-104页。
(22)关于基地组织的资产有不同的观点。有反恐专家指出,基地组织有3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来自本·拉登的私人财富和其他资金来源。但“9·11”调查委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1994年沙特剥夺了拉登的国籍,强迫其家庭卖掉拉登在家庭公司中的股份。1996年本·拉登离开苏丹时,没带走一分钱,财产被苏丹接管。基地组织的经费有多种筹资渠道,而不是所谓的3亿。笔者支持后一观点。参见http://www.people.com.cn/GB/guoji/14549/2792843.html.
(23)联合国文件,S/2007/677,第57段。
(24)[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苏长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5页。
(25)联合国决议,S/RES/1455(2003)。
(26)联合国文件,S/2008/324,第27段;S/2010/497,第43段。
(27)联合国清单中的国际仁爱基金会机构,除美国外,还包括其设在阿富汗、阿塞拜疆、孟加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加拿大、车臣、克罗地亚、格鲁吉亚、荷兰、巴基斯坦、俄罗斯联邦、沙特阿拉伯、苏丹、塔吉克斯坦、也门,以及达吉斯坦、加沙地带和印古什。《分析性支助和制裁监察组第二次报告》,第54页;《分析性支助和制裁监察组第七次报告》,第17页,http://www.un.org/chinese/sc/committees/1267/experts.shtml.
(28)联合国文件,S/2008/324,第1段。
(29)这是2003年的数据,但后来该数据变化不大。联合国文件,S/2003/669,第37段。
(30)联合国文件,S/2007/677,第100段;S/2003/1070,第93段。
(31)联合国文件,S/2003/1070,第19段。
(32)联合国文件,S/2004/679,第82段。
(33)Michael Chandler and Rohan Gunaratna,Countering Terrorism:Can We Meet The Threat of Global Violence? Reaktion Books Ltd,2007,p.85; Rohan Gunaratna,"The New A1 Qaida:Developments in the Post-9/11 Evolution of al-Qaida",in Boaz Ganor ed.,Post-Modern Terrorism:Trends,Scenarios,and Future Threats,Interdisciplinary Center(Hertseliyah,Israel),2006,p.47;“联合国官员谴责部分成员国不合作致制裁基地失败”,2003年11月4日,http://www.chinanews.com.cn/n/2003-11-14/26/368668.html.
(34)联合国文件,S/2008/324,第24段。
(35)联合国文件,S/2002/1338,第33段;S/2007/677,第26、60段。
(36)Oran Young,"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Hard Cases And Critical Variables",in James N.Rosenau and Ernst Otto Czempiel,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185.
(37)李金祥:“联合国制裁恐怖主义制度的构成及其本质”,《和平与发展》2011年第3期,第25页。
(38)“本·拉登再次发表录像声明,对联合国横加指责”,《中国日报》,2001年11月5日。
(39)新华网,2004年5月7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4-05/14/content_1467232.htm.
(40)联合国文件,S/2003/1070,第34段。
(41)Oran Young,"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Hard Cases And Critical Variables",p.189.
(42)Case T-306/01R,Aden v.Council,2002 E.C.R.Ⅱ-2387,90.
(43)联合国文件,S/2005/572,第54段。
(44)联合国文件,S/2004/1037,第12段。
(45)联合国文件,S/2006/154,第40段。
(46)联合国文件,A/C.6/65/SR.2,第22段。
(47)联合国文件,S/PV.6424(2010)。
(48)"U.S.Opinion on Transnational Threats:Terrorism",November 2009,p.2,http://www.cfr.org.
(49)沈丁立:“基地与美国,一百年不会言和”,《环球时报》2011年9月9日。
(50)Kalyani Munshani,"The U.N.Consolidated List:Effect of Committee Dynamics on Creation and Compliance",p.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