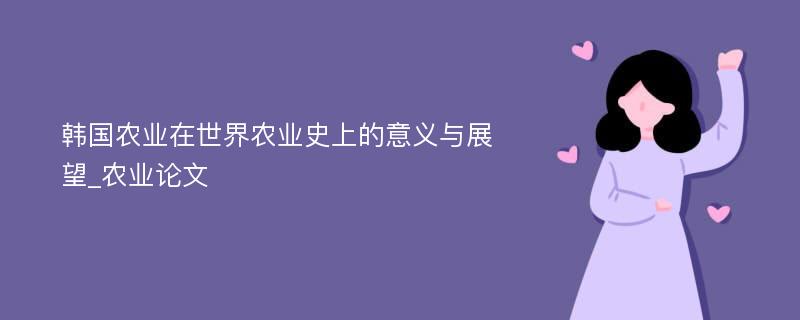
韩国农业在世界农业史上的意义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业论文,韩国论文,史上论文,意义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312.34;S-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04)02-0108-08
一、绪论
众所周知,韩国的农业危机是由“乌拉圭回合”这一国际性的协商所导致的。现在,让我们认真回顾加入WTO十年以来的农业历程,去认真思考一个问题——韩国农业究竟是什么?为此,我们在研究韩国农业及其发展史的时候,都要用世界史的视角去认识和评价。在来势迅猛的农业开放热潮中,对农业的传统性质的期待已日益淡化。然而,在这期间,大多数的国民不顾粮食自给率低下的事实,无视农业存在的意义,而且,就连农业具有的无限的公益性也逐渐地被国民所忘却。其结果是:除了开放的步伐有所放慢的“大米”还有点儿剩余之外,麦子、大豆之类就要依靠进口了。抛弃复合耕种,片面地追求单作化和专业化导致了土质衰退,除草剂、杀虫剂的滥用威胁着国民的健康。因此,探索解决世界粮食危机的对策并加强对生态农业的研究,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那么,乌拉圭回合协商,真的像他们所打出的“同等竞技条件”的招牌那样自由平等吗?倒是WTO所提倡的“无一例外的关税化”,“对农家补助的生产—价格不连接原则”等,才是以“经济相对优势”这把尺子来衡量农业价值的司空见惯的做法。进而,今年开始的New round协商更是令人失望。因为它忽视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其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全球化对世界经济所做出的贡献。可是为什么会在世界各地广泛出现对全球化的抵触?是因为少数富裕国家所拨出的巨额补助金导致的慢性的过剩生产,使全世界的农产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促使贫穷国家的小农们被驱逐出农村?为此,对包括农业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追求自由贸易的WTO的全球化进程,我们有必要进行再检讨。
另一方面,由李比希(Liebig,1803-1873)倡导的克服化学农业的副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界的全新的生态农业思想已成为世界的趋势。即将来临的石油资源的枯竭也证实,以廉价的石油资源为基础的大规模的机械化和化学农业所面临的限度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放眼发达国家粮食资本家的粮食问题的现状,建立生态农业来保护生态环境和国民的健康已迫在眉睫。那么,保护生态环境,旨在恢复人性的这一全新的农业哲学应该如何去实现呢?(注:Shridath Ramphal:Our Country,The Planet-Forging a Partnership for Survival,Island Press,1992.)笔者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向不应该从外部引进,而是应该从恢复韩国农业的本质的过程中寻求答案。
从这样的观点出发,笔者想重点阐明韩国农业在世界农业当中的特性。自古以来,韩国农业一直保持着适宜于风土的复合耕种,而这就是生态农业的本质要求。韩国农业是韩国所处自然环境的产物,而且只有适宜环境的农业才能生存下去。因此,未来的农业发展方向也应该从我国农业的传统中去寻找。只有将韩国农业所走过的历程与世界农业进行比较,才能真正地展望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韩国农业的前景。
二、韩国农业的起源
一个民族的农业发展过程,其实是生态环境和与此相对应的农耕文化互相结合的结果。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再经过青铜时代发展到初期的铁器时代;农业的发展过程,就是围绕人类、社会组织和农业所进行的连续的技术革新过程。在韩国,按考古学划分的时代,一般为旧石器时期(10000年前),新石器时期(5000~1500BC),青铜器时期(1500~300BC),初期铁器时代(300BC~0AD),原三国时期(0~300AD),三国时期(300~668AD)。
在韩国,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初期出现的,而且只局限在个别地区。农业的最初出现可能是在公元前5000~4000年的时候,在咸镜北道现罗津先锋市屈浦里的新石器遗迹中,发现了最初磨粮食用的磨石和多种类型的镐。
最新发现了大约公元前3000年栽培的炭化谷物,而且还出土了锄(Homi)、锹、耜(犁头,Boseop)、镰刀等农具,和用于磨农具的磨石等各种农用工具(注:崔梦龙:《韩国先史时代的饮食文化》,《韩国饮食文化研究院论丛》第一集,1988年。)。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西北地区(黄海道智塔里、弓山里)的遗址中发现的镐锤锄(用来打碎土块的农具)之类的工具。它是与磨石之类的农具一同被发现的。这样的事实证明,韩国的最初的农业是以“镐锤锄”挖翻肥沃的冲积土,种植谷子和稗子等杂粮的方式展开来的。由初期的锄头农耕法进而发展成较为先进的耜农耕法,到了初期铁器时代,原三国时期发展成为基于灌溉的犁农耕法。
在韩国初期的农耕文化中最为令人瞩目的是,起初以谷、稗子等杂粮作为主要农作物,之后逐渐变得丰富多样,包括了稻子、大豆、红豆、高粱等。金浦、一山等地的事例告诉我们,稻作农业的大范围普及大约是在BC3000~2500年的时候。在该地区除稻子之外还种植有其它农作物。约在BC1300年的时候,平壤南京遗址中也发现了多种类型的炭化谷物。除此之外,初期的稻作农业的遗址还有数十处。在此不仅有被炭化的米,土器表面的稻种印痕等直接的证据,也有象半月形石刀、有沟石斧等间接的资料。这样的稻作农业沿着西海岸,一直传播到南方。从单粒型(Japonica type)稻种的分布来看,当时还传到了日本。其理由是韩国的稻作农业的起源比日本要早,日本和韩国种植的稻子也是同一种类的。另外还有当时人口流动的路径,也能说明这一点(注:李镐澈:《朝鲜前期的农业经济史》,1986年。)。
另一方面,韩国的青铜时代的上限,最近又提前到BC15世纪(注:崔梦龙,推测青铜时代的上限是BC15世纪。),其证据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欣岩里的遗址。当时的农业已经采用了多种多样的方法,如土碳层周边地带的农业、沙质冲积地带的旱田农业、丘陵下面地带的水田和旱田农业等等。当时的稻子品种也是多样的(注:引用“日山”发现结果,“出土了非japonica,也非indica的古代米(许文会,1996),可见,只能是‘韩国稻’了”)。在骊州欣岩里遗址出土了米、麦、谷子、高粱等,还有旱田稻。把全国范围内的事例汇总起来看,当时的作物还有米、麦、黍子、芝麻、荏胡麻、麻等(注:在南江水库,除谷物以外,还发现了1300余球根类植物(许文会,1997),推测当时为便于纺织,还特别种植了麻。)。
如上所述,韩国在新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以杂粮为中心的火田式的锄农法。这意味着最初的定居农业的出现。这样的锄农法一直延续至稻作农业较为普及的青铜时代,接着又发展成耜农法。而到了铁器时代的初期和原三国时代,开始了利用灌溉设施和使用耕牛的犁农法。另一方面,我国的农业起源与世界的发展轨迹是一致的。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和稻米为中心发展的。毋庸置疑,这是我国国土所处的自然环境使然。
三、世界上的农业地区及其发展过程
(一)世界上的农业地区
与其它任何产业相比,农业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最大的一个产业。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利用自然的能力无论如何巧妙,也不能改变自然本身。对农业影响最大的自然环境因素是气温、降雨量和湿度,这些也是决定一个地区的农业类型和其发展方向的最重要的因素。法国的气候学家德马而顿(De Martonne,Emmanuel),于1926年提出了“干燥指数”概念,将其成功的解释为一个算式。他提出的公式为I=P/(T+10)。其中P为一定期间内的降水量的合计(用mm表示),T为相同期间内的平均气温(用摄氏度来表示)。
利用该公式计算得出的年平均干燥指数大于20为湿润地带,小于20为干旱地带,而小于10则为天然降水无法满足农业生产的沙漠地带。但有些地区又有点特殊,例如地中海沿岸的降水几乎全部都集中在冬季,而夏季几乎没有降水,为此又计算了夏季(6月~8月)的干燥指数,即夏指数。夏指数为5以下的地区为降水集中在冬季的冬雨地带。这样的地带,夏季进行农业生产是非常困难的。用一年的干燥指数20和夏指数5为基准的“饭沼二郎”方法论,可将世界农业分成四大类(注:饭沼二郎:《日本农业的再发现》,NHK Books 226,1980年,第25-29页。)。
首先,世界农业的第一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小于20,夏指数小于5的西南亚地区和地中海的南岸地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东地区,该地区的年降水量不足400mm,而且降水又都集中在冬季,是非常特殊的干燥地带。该地区若要进行农业生产,必须采用轮作保水法来防止土地中水分的蒸发。在该地区,一般在10月份播种麦子,用冬季的雨水栽培的两季式(休闲+麦)农法较普遍,而此外的沙漠地区是无法进行农业生产的。
其次,第二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大于20,夏指数小于5的冬雨地带,即地中海北岸地区和苏联的南部地区。包括内陆地区在内,这个地带形成了先种植大麦后再进行放羊等畜牧业的“二季式”农业。而在希腊至西班牙的南欧低丘陵地区则种植葡萄、橄榄等;畜牧业以放羊为主。另外,在南欧地区,城市的近郊或能进行河川灌溉的地区,形成了发达的灌溉农业。
再次,第三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小于20,夏指数大于5的特殊地带,例如印度的旁遮普(Punjab)地区和中国的华北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属于年降雨量不到300mm的干旱地带,但是年降水的三分之二又集中在夏季。该地区的夏季农作物是杂粮,冬季农作物是大麦等。这些地区为了防止土壤中水分的流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耕保水的农作方法。而一方面,中国的华北地区一年二熟结束之后,将犁完的土壤覆盖起来,以免土壤中的水分流失。这些地区的农业具有共同之处,即都以保水为目的,选择了中耕农业。
最后,第四个地带为年干燥指数大于20,夏指数大于5的夏雨地带,也就是湿润地带。北欧地区和东亚地区为其典型。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北欧地区利用夏季的降水,一直保持着“三圃式”农业。该地区原来与南欧地区不同,是以夏季农业为主,但由于土质差和冬季寒冷,种植期间内的除草是没有意义的。但是,种植过的土地必须闲置二年后再进行除草的“三圃式”农法定位在该地区。而在韩国、中国南部和日本等高温高湿度的东亚地区,如果不积极除草,就很难有收获了。东亚的这种“中耕除草”技术传播到北欧“三圃式”农业地带,使该地区的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提高。这就是著名的英国农业革命。总之,东亚的农业特征可以概括为中耕除草,并且清除杂草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
我们用干燥指数所观察到的世界农业的差异,产生于各地区为了克服各自所处的独特的农业环境所采取的不同的方法,这一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些环境因素可以将农业分为“干旱地带的农业”和“湿润地带的农业”二大类,从其农业特点来看,若将前者称为“保水农业”,后者则应为“除草农业”了。而世界农业的发展可以概括为由“干旱地带的保水农业”发展成为“湿润地带的除草农业”。
另一方面,以地力的恢复和除草为目的的闲置土地的“休闲农业”,逐渐发展成为无休闲的“中耕农业”。尤其是一直保持着“三圃式”农业传统的北欧地区的农业革命,就是反映这种发展变化的典型事例了。这种世界性农业发展过程在各国的农业环境和历史中表现得更为具体。为了克服各自所处地区的制约条件,虽然都做出了不断的努力,但是各个国家的农业仍然还是处于固有的环境之中。
举一个事例,在美国萨克拉曼多(Sacramento)地区,灌溉干旱的土地进行的水稻栽培,虽然因受到自由贸易的恩惠不断地扩大其种植面积,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摆脱水源不足和污染问题。借助于科学的力量可以克服多种制约扩大种植面积,但是其昂贵的生产费只能分摊给那些进口粮食的国家了。在韩国,为了普及产量高却不适宜风土环境的新品种(统一稻),付出了很大努力,也获得过一时的成功,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韩国的经验也在提醒我们环境的重要性。旨在“中耕农业”和“除草农业”的世界农业的发展,都只有在各自所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发挥自己的优越性。因为农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比其它任何产业都大。其实“可持续发展农业”这一新的农业目标,说白了也就是反省以科学技术为先导、无视农业环境的过去农业,用适宜于环境的农业取而代之。从这一点来看,一方面留意于世界发展的趋势,同时去寻求最适合自我环境的、最富有个性的发展道路,世界农业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四、西方农业和亚洲农业
在全球多种多样的农业当中,韩国的传统农业究竟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韩国农业也能像西方农业那样实行规模扩大化,并且获得成功吗?这样的疑问只有在认真理解世界农业发展过程的基础上,才能找出答案。为此,让我们先去粗略地了解一下西方农业的发展过程吧。大约在一万年前,以西南亚为发祥地的西方农业的出发点是以大麦农业为主的“二圃式”农业。这种初期的干旱地农作法在罗马时代传播到北欧地区,发展成“三圃式”农业。这种制度后来成为西方农业长期以来的传统。闲置期的土地用来放牧牲畜,牲畜的粪便又成为极佳的肥料。但是,原来的以除草为目的而闲置的土地逐渐用于牧草地,遇到了产业革命引发的农产品需求的爆发性增长,终于实现了完全脱离休闲的农业方法。像这样,在闲置期的土地上,种植饲料作物来进行牧业的诺福克(Norfolk)农业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而且,圈地运动又把原来为放牧牲畜而划分成小规模的土地结合起来,使大规模耕种的出现变得可能。这一系列的变化就促成了“农业革命”。
此后,以“休闲”和“除草”为特征的西方农业,克服了其制约条件,将大麦农业和畜牧业结合在一起,以实现规模扩大化为发展方向。能最好地反映这种发展趋势的就是南北战争以后的美国农业。他们以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为先导,成功地实现了规模的扩大化,并在此基础上,用强大的劳动力作为武器,使美国成为操纵全世界的强国。从西南亚干旱地区发源的西方农业的近代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克服休闲,通过机械化实现的大量生产上。更具特点的是,在干燥地区以麦为主要农作物的西方农业,主要靠机械化手段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不是用提高单位面积生产量的方式发展起来的。这种规模扩大化的趋势,通过单作化,进一步得到强化;为此,大量使用了石油化学的产物——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等化学农药。凭借强大的生产力,1846年试图开放农产品市场的英国的第一次尝试(注:李镐澈:《产业化与农业经济》,韩吉社,1991年。),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最近又被美国的“乌拉圭Round”协商,强行地实行起来了。
另外,亚洲农业的源头在中国的古代农业。中国华北地区以杂粮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干旱地带农业,本来就具有“中耕保水”的特征。这种农业传到较湿润的东亚地区时,形成了复杂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复合耕种。贯穿这种多样的东亚农业的共同因素就是稻作农业,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如同用于干旱地带的中国的犁,传到东亚湿润地带一样,华北的中耕农业传统也发展成中耕除草农业了。东亚地区的农业发展方向是:用集约型劳动投入来耕种极其有限的土地,提高单位面积的生产量。也就是说扎根于劳动集约型的亚洲农业的发展方向从根本上与西方农业是不同的。不同的原因有:高温多湿的气候一开始就要求那里的人们必须战胜杂草,才能获得收获的,这使扩大规模变得十分困难。并且,东亚的主要农作物稻子,其单位面积的人口抚养能力,大大超过西方农业的主作物——麦。
但是不少美国人或在美国学过农学的人们常常对此没有正确的认识。他们认为东亚地区集约型劳动是因为耕地面积小、农业规模小。但事实上并不是因为规模小才集约投入劳动力,而是用那特殊的集约型劳动才能守住农业本身,所以无法把规模扩大到一公顷以上。现行的WTO政策正处于用西方农业的观点来认识亚洲农业的矛盾状态。被那些每户拥有180公项的超大规模的美国的生产力所威慑的东亚政府,认为生产力低,是由于耕种规模小。因此,一味地强制要求农民们扩大规模,为了规模化、机械化和单作化,政府投入了巨额的农业补助金。如此一来,原来的复合耕种模式就完全被打破了。
由此浮出一个问题是:湿润地区原来以中耕除草为起点的亚洲农业,从此也要走像西方那样的机械化和规模化的道路吗?为了对应WTO的农产品自由贸易主义政策,亚洲各国所采取的农业政策又如何呢?不幸的是“耕地规模扩大化”,“专业农业人员的培养”,“食品消费结构的转换”等政策,只能反映那些想推进农业发展的人们心中所藏的面对西方农业的刻骨铭心的自卑感。而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只有在客观认识历史的发展和自己所处的坐标时,才能得以提高。忽视原来的环境和出发点的不一致性,无条件地要求进行规模经济的“憧憬西方政策”,才是其误区所在。从这一点来看,从生态农业的角度,找回韩国农业的真面目并非是件轻松的事。
五、韩国农业的传统及其发展方向
韩国农业是东亚农业的一条支流,属于世界农业地带当中的第四地带。尤其是韩国处于中国华北(长江以北)和气候湿润的日本的中间位置,使它的气候具有中国华北般的春旱和超出日本的夏涝的特征。这样的半干旱(Semi-dry)固有的环境条件,就赋予韩国农业带有保水农业传统的中耕除草农业的性质。因此,韩国农业从古代开始就形成了劳动集约型的复合耕种,又直接发展成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相协调的水旱轮换的农作法。这样做是为了清除高温多湿的环境导致的茂盛的杂草和防止土壤有机物质的流失。
韩国的农业拥有七千年的悠久历史,并且由于向南北方向细长延伸的国土形状,和其他国家相比,生产出了多种多样的土特产品。因此稻子所占的种植面积并不大,例如1919年,稻田只占全部耕地面积的36%。当然,农作物当中最多的还是稻子,其经济地位也到了几乎能代替货币的程度了。实际上,韩国农业是以杂粮、大豆和稻米为主作物发展起来的。
在三国初期,农业从锄头农业发展成犁耕农业,而到了四世纪,又发展成灌溉农业了。那时的稻作农业只能采取休闲的方法,因为,高温多湿的气候下,既要防止杂草,又要防止土质下降。休闲制一直延续至新罗统一时代,其记录有全罗南道潭阳的“开仙寺石灯记”和高丽末期的“高城三日浦埋香碑(1309)”。但是这种休闲制到高丽后期就逐渐发展成每年耕作的连作制了。
现在,利用韩国最古老的农书《农事直说》,来观察一下十五世纪韩国农业的整个面目(注:李镐澈:《朝鲜前期的农业经济史》,1986年。)。这个时代种植最为广泛的是黄米、小米、大豆和稻子;其次是麦类和人参等农作物。并且朝鲜前期的农业以作物的多样性为中心发展起来,但只能是少数人口耕作大面积土地的粗放型农业。到了朝鲜后期,稻作农业有了很大的变化。移秧法的出现使稻作农业广泛地普及起来,水田的轮作体系也起了很大变化。在开垦壬辰倭乱造成的荒废的国土过程当中,地主制作为重要的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到了十八世纪,移秧法不仅扩大到天水水田(只能靠雨水浇灌的稻田),而且还利用在水田和旱田农业上了。同时,原来的水稻的直播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
从韩国农业的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韩国农业克服休闲制,以发达的中耕除草技术为基础,向高级的轮作体系和连作体系发展的整个发展趋势。同时也不难看出,由人少地广时的粗放型农业向以集约型耕种来提高土地生产力的生产模式转变的发展趋势。加强劳动集约,深化水田农业和旱田农业的复合化,成功地解决了土质的保护和杂草害虫的治理问题。如今水田和旱田的二熟制已广泛普及,将不充足的水资源轮流灌溉水田和旱田这种“轮水田法”也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且,到梅雨季节为止,将水稻种植在旱田里栽培的“干田法”在韩半岛西北地区盛行。韩国农业的发展可以用“集约化的道路”一词来形容,它同时也促进了韩国传统农业水旱轮换农法和复合耕种的发展。复合耕种与当时盛行的货币经济结合起来,使许多商品农作物的种植变得可能,甚至使得原产地为美洲的农作物也轻而易举地变为己物。
到了十七、十八世纪,人口平均增长率高达3%,人口的增加进而产生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土地的劳动集约型农业。这种变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直接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而且,推翻传统的身份制度,从根本上推翻了封建社会。
十八世纪以后,我国的农业发展导致了100人/平方千米的极高的人口密度,它的根基主要是农业技术所实现的高水准的集约型农业。但是,与西方不同的是,这种结果的原因,并不是土地和资本的大量投入造成的,而是农业劳动质和量和农业技术的革新带来的必然结果。虽然,还有多种富农经济,但是,在每户平均耕种规模不断减少的当时,农业发展的原动力仍然在于无数小农们从事的商业性农业的发展。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选择集约化道路的韩国农业的发展,直接成为韩国社会迈向近代社会的推动力,并且克服肥料资源紧缺的困难,最大限度地利用农作物多样的特性,进而形成优秀的轮作体系,韩国农业传统中发达的农业技术和复合耕种,就是未来生态农业的一个突破口。但是由不均等成长论下的开发政策所带来的近代化的成果并没有滋润农民。加入WTO以后的韩国农业,在国内方面,为了提高农业国际竞争力,培养专业农业人员来代替小农,并实施“结构调整政策”来扩大规模;在国际方面正准备着2004年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根本”这一点来看,他们的要求必将带来农民被驱出农业和农村,甚至农业被抛弃的结果。这意味着韩国农业传统的彻底改变。为此,巨额的农业补助金投入到了农村,传统的复合耕种完全被中断。其结果是土质在下降,杂草和害虫泛滥,进而导致杀虫剂、杀菌剂、化肥的大量使用和日益增加的农业公害;大米的大幅度增产和杂粮大豆的大幅度减产,又导致了大米的减产政策和杂粮大豆的大量进口,促使粮食自给率逐年大幅度下降。
最近的农业危机是由于忘却了韩国农业的本质,将农业转化成单一稻作所带来的结果。或许他们认为进口美国廉价农产品更为有利。但是如何面对预计在21世纪发生的世界性的粮食危机呢?更令人吃惊的是,竟有一些人认为现在的危机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依从WTO的要求所导致的。这场悲剧,是由于他们疏忽了东亚的提高劳动的质和量的发展模式与西方的资本积累的发展模式之间的不同。因此,我们必须对加入WTO以后的十年来的农业轨迹进行再检讨,并且摸索出恢复韩国传统的道路,再次向多种农作物的复合耕种转化。
六、结论
韩国农业拥有着七千年的悠久历史。它不仅对韩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且还渗透到韩国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里。尤其是大米,它曾经承担过仅次于货币的经济职能,而稻草犹如“韩国稻草屋顶”所象征的那样,成为了韩国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韩国农业是韩国特有环境的产物,它与以近代化的名义进入我国的西方的化学农业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人们现在常说的“身土不二”就说明传统的复合耕种是既安全又十分必要的产业,因为它能给我国国民提供粮食、健康和洁净的环境。
最近的农业危机的象征就是将在2004年实施的“大米市场的开放”。但是,可以说当我国农业的传统被人们所遗忘的时候,它就已经暗示了我国农业的危机。完全无视和抛弃我国农业一直以来依循着的历史特性和环境特性,无条件地模仿西方农业的错误认识,其实就是招来当今的惨败的原因。不难想象,农业问题不能只归结于农民。抛弃农业往往就是对国土环境和国民健康以及民族文化的抛弃;从农业的环境特性来看,农业衰落往往会影响未来的生存环境。
以水田和旱田相协调为基础的复合耕种被WTO以后的农业政策完全抹杀掉了。东亚长期以来的传统已被打破,土质下降了,杂草和害虫多了起来,化肥和农药用量增多了;结果是大米过剩,大豆、大麦全部需要进口了;一方面要对过剩的大米实施减产政策,另一方面农药、麦粉和转基因大豆(GMO)问题困扰着人们。粮食自给率也在大大降低,但令人惊讶的是,那些开放主义者们所期待的结果却恰恰没有出现。
韩国农业果真要抛弃自己的传统,按照WTO的要求,选择与西方相同的道路吗?对于韩国农业十年来的发展过程,我们应给以什么样的评价呢?我们只有在客观地认识自己所处的具体情况时,才能提高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竞争力”。掩盖现有环境与过去的历史之间的差异,一味地坚持西方或欧洲的做法,难道真的可取吗?然而从今年开始的新一轮回合(New Round)协商正处在矛盾之中。忽视地域性、多样性以及一片土地所形成的独特的传统文化等所有本质性的价值,而是用“贸易收支”这一量化的数据来衡量和评价农业,显然与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大相径庭。
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用生态农业的视角去寻回韩国农业的真正面貌,而这个担子并非轻松。就像以麦为主的西方农业和以大米为主的东亚农业有区别一样,各个国家在各自的风土历史中形成的多样的农业文化,应作为人类的无形资产去尊重。事到如今,我们应该去思考一个问题:全球化究竟对农业价值的维护做了何种帮助,它能否与农业的多样性和安全性共存呢?我们必须坚持农业的全球化,但同时对各个国家农业的特殊性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带来的多样性和持续性给以关怀,它们应该是并存的。二十一世纪的韩国农业,不能被商业性或政治性的理解所左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