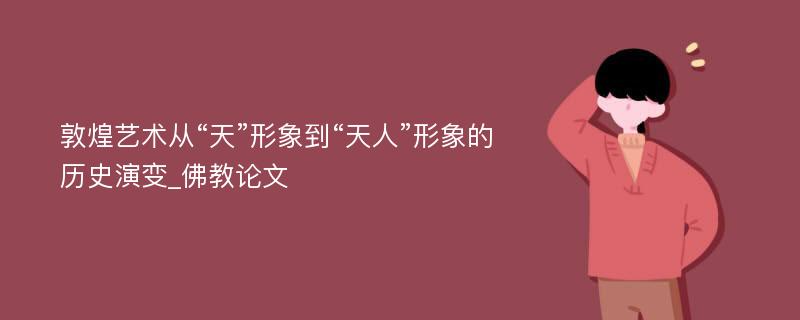
敦煌艺术中“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历史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形象论文,天人论文,艺术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主要结合“思想的旅行:从文本到图像、从图像到文本”这一论题,讨论学习敦煌石窟艺术的一点想法:一千多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图像,逐步发生了由具有印度西方古典特点的佛教艺术到中国东方特点的佛教艺术的转变,具体说来就是由“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转变。 对于这种转变,西方美学与文学理论有关图像的理论中几乎没有涉及。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总结西方“艺术批评诸坐标”的作品、世界、艺术家与欣赏者四要素说,包括强调“世界”的模仿说、强调“艺术家”的表现说、强调“欣赏者”的接受说或阐释说,以及强调“作品”的符号论,可谓概括了西方古代至现代文学理论的各个方面,也适用于对文学艺术图像的理解,但惟独没有解释敦煌佛教艺术何以发生这种历史嬗变的原因。而索绪尔的语言学也只着重从共时性的角度探索语言(符号)的结构,否弃了语言(符号)的历时性演变,因此借用符号学理论也无法阐释敦煌壁画的千年演变。 站在敦煌这一丝绸之路的要冲之地,西望阳关之西的漫漫古西域,向东回顾绵延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两个词汇跳入我的脑海:“传播”与“本土”。印度佛教与佛教艺术在传播过程中经过了“本土化”的过程,这也是佛教艺术形象历史嬗变的原因。这倒有点符合德里达有关“延异”与“撒播”的理论。因为德里达的“解构”理论必然反对结构主义的“中心”与“稳定”,而力主能指在时间中的滑动,以及意义的充满能量的向四面八方“撒播”。①中国古代文论将这种现象称为“通变”。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篇中有言“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②将文之通变提到“无穷之路,不竭之源”的高度。所谓“通”即为继承,而“变”则为变革。认为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必经继承与变革的“通变”之路,这样才能“必酌新声”。而印度佛教经丝绸之路的传播到达敦煌,经过中华文化熏陶与改造的“本土化”过程而成为中国佛教,佛教艺术也随之发生了历史的嬗变。所以,中国古代的“通变”以及敦煌艺术表现出来的“传播”与“本土”,应该成为美学与文学理论之图像理论的必然组成部分,这就是本文的要旨。 二、嬗变的动因:由印度佛教到中国佛教 首先,我们要从图像学的角度研究这种嬗变的原因。众所周知,由佛教经文到壁画是一种图文互换。图文互换有三种表征:能指互换,所指共同;能指互换,所指增损;能指互换,所指迥异。③敦煌壁画的千年嬗变几乎囊括了以上三种情形,但其基本原因还是“所指”的变异,即佛教东传后由印度佛教转变为中国佛教,其教义也逐步汉化。这一“所指”的变化是导致敦煌壁画历史嬗变的根本原因。 佛教传入中国始于西汉后期明帝之时遣使天竺求取佛经,使者于公元67年到达洛阳白马寺,为中原佛教之始。佛教传入后经过起起伏伏,终于在经过“本土化”的过程后立住了脚。这种本土化首先是吸收中国本土文化,逐步做到儒释道的统一,主要是逐步将佛教教义与佛经逐步“汉化”。吸收了儒家的孝道思想,也主张不孝要遭报应,出家行道是根本的孝道等;吸收了道家更多的概念与思想,将道家“无”的概念与佛教的“空”对接,将道家的“清静无为”、“守一”吸收入佛经,以解释“禅定”等等。就艺术而言,敦煌石窟艺术中还吸收了道教的“羽人”形象,使其与飞天相衔接。佛教还与中国民间俗文化结合,突出“救苦救难”的内涵,在佛教中强化了沟通神人的菩萨特别是观音的地位等,从而被广大民众所接受。诚如蒲松龄所言,“佛道中惟观自在,仙道中惟纯阳子(吕洞宾),神道中惟伏魔帝(关公),此三圣愿力宏大,欲普度三千世界,拔尽一切苦恼,以是故视差云宝马,常杂处人间,与人最近”。④ 经过这样的佛教与儒道统一及其俗化过程,印度佛教逐步改变成中国佛教,其代表即为禅宗。印度佛教完全是一种出世的教派,其教义很复杂,简单地概括,就是苦集灭道四圣谛。谛,意为真理或实在。四谛即:(1)苦谛:指人经历三界六道生死轮回,充满痛苦、烦恼。(2)集谛:集是集合、积聚、感招之意。集谛,指众生痛苦的根源。谓一切众生,由于贪、瞋、痴等造成种种业因,从而招致未来的生死烦恼之苦果。从根本上说,众生痛苦的根源在于无明,即对于佛法真理、宇宙人生真相的无知;正因为无明,众生才处于贪、瞋、痴、慢、疑、恶等烦恼之中,由此造下种种恶业;正因为造下种种恶业,又使得众生未来要遭受种种业报。这样反复自作自受,轮回不休。(3)灭谛:指痛苦的寂灭。灭尽三界烦恼业因以及生死轮回果报,到达涅槃寂灭的境界,称为灭。(4)道谛:指通向寂灭的道路。佛教认为,依照佛法去修行,就能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到达涅槃寂灭的境界。这里包含丢弃尘缘、因果报应、生死轮回、普度众生、禁欲苦修等内容。 总之,印度佛教是一种出世的宗教,但传播到中国后,经过“本土化”的改造,成为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禅宗创始于南北朝时来中国的僧人菩提达摩。他在佛教释迦牟尼所言“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人皆有佛性,通过各自修行,即可获启发而成佛”;后另一僧人道生再进一步提出“顿悟成佛”。禅宗主张修道不见得要读经,也无须出家,世俗活动照样可以正常进行。禅宗认为,禅并非思想,也非哲学,而是一种超越思想与哲学的灵性世界。认为语言文字会约束思想,故不立文字。认为要真正达到“悟道”,唯有隔绝语言文字,或透过与语言文字的冲突,避开任何抽象性的论证,凭个体自己亲身感受去体会。禅宗为加强“悟心”,创造许多新禅法,诸如云游等,这一切方法在于使人心有立即足以悟道的敏感性。禅宗的顿悟是指超越了一切时空、因果、过去、未来,进而获得了从一切世事和所有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自由感,从而“超凡入圣”,不再拘泥于世俗的事物,却依然进行正常的日常生活。禅宗不要求特别的修行环境,而是随着某种机缘,偶然得道,获得身处尘世之中,而心在尘世之外的“无念”境界。“无念”境界要求的不是“超凡入圣”,而是要“超圣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与常人无异,只是精神生活不同,在与日常事物接触时,心境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换言之,凡人与佛只在一念之差。可见,禅宗所包含的人皆能成佛,无须苦修禁欲,读经行善即可顿悟成佛等观念解决了佛教的平民化、神秘化问题,使之成为一种人间佛教,包含着儒家的仁爱和人皆可为尧舜的思想、道家的离形去智之“心斋”思想等,是一种中国化的佛教。 在这种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佛教使其教义由出世发展到出世与入世的结合,从而使佛教壁画的“所指”发生了根本变化。这是导致壁画形象(能指)变化的根本原因。加之,画师也由原来的希腊画师凭借希腊画法到敦煌时期当地画师渗透进中国画法,在能指上逐步发展与变化。这正是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所指与能指的双重变化,导致由“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历史嬗变的原因所在。 三、印度佛教图像的东传及其变异:由“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 印度佛教最初是无偶像崇拜的,后来发展到偶像崇拜。它主要运用古希腊雕塑艺术手法,通过雕塑与彩绘刻画佛陀的形象及其修炼成佛、济世救人的事迹,主要保留在犍陀罗地区的石窟中,即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白沙瓦及周边地区,以及与阿富汗东北部接壤的喀布尔河中下游及印度河的上游地区,俗称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佛教艺术主要是一种西方古希腊式的宗教艺术,一种对于“佛”即“天”的歌颂,一种“天”的形象。美国学者杜兰在《印度的艺术》一书中指出,由于亚历山大的东征使得古希腊艺术与印度艺术相融合,也使佛教艺术具有了古希腊艺术的特点。如其所言:“在希腊教师的指导下,印度的雕塑一时具有了一种平滑的希腊外表。佛陀变成了阿波罗的样子,也变作一个想到奥林匹克山的神;在印度的神和圣者的身上开始有波纹状的披布,式样好像菲迪亚斯的人形墙;而虔诚的Bodnis-attvas则和兴高采烈的醉酒‘森林之神’混在一起,佛陀与弟子们的理想化而且几乎是女性化的像和希腊腐败的现实主义的可怕实例成为对照,像在Labore忍受饥饿的佛陀,便是每根肋条与筋腱毕露,而有着女性的面孔与发式及男性的胡须。”⑤事实情况是公元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率军侵入印度西北部地区,使希腊文化在印度迅速扩大。公元1世纪后,大月氏人建立中亚、西亚和南亚的贵霜帝国,印度的佛教信仰与亚历山大东征所开辟的希腊化潮流相结合,并使大乘佛教对于佛的神化与希腊画像技艺相结合,这就是著名的犍陀罗佛教壁画艺术。从此佛教壁画艺术在印度西北部兴起并逐步流转各地。⑥ 总之,随着佛教传入中国,犍陀罗佛教艺术也传入中国。西汉末年在新疆地区已有犍陀罗佛教艺术,之后进一步传入敦煌,建成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莫高窟佛教艺术。莫高窟始建于前秦建元二年即公元366年,至今仍保存完整的洞窟有492个,里面珍藏着佛教壁画45000多平方米,彩塑2400多身,还有唐宋木结构建筑五座。莫高窟的艺术是融建筑、彩塑、壁画为一体的综合艺术,是我国也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宝库。初期仍是印度的犍陀罗艺术风格,后来逐步本土化,发生重大转型。转折点是公元642年即贞观16年,此时适逢盛唐时期,也成为其艺术的巅峰时期。公元1524年明朝正式关闭嘉峪关,并于1529年放弃哈密,敦煌佛教艺术逐步走向衰落。后来的一些整修活动也只是局部的维持,改变不了其艺术终结的历史。敦煌石窟艺术前后持续达1000多年,不仅见证了中西文化艺术的传播与对话,而且是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一座宝库。 佛教雕塑与彩绘又称“变相”,即将佛教教义呈现于图像。饶宗颐指出:“过去有人说‘变’是‘变相’的简称,这恰倒因为果,应该先有‘变’之名,后来增益相或图,成为并列复词,称为‘变相’或‘图变’。演衍讲说这种‘变’的故事之文字,谓之‘变文’。专绘‘本生经’或其他佛经中故事的,谓之‘经变’。”⑦这里讲的“变”只是文体的变化,由佛经改编成通俗故事的称为“变文”,改变成雕塑或壁画的称为“变相”。其实,“变”即改变、变异之意,当然也包含两种文化艺术在交流对话的历史长河中的融合与变异,1000多年的敦煌石窟艺术,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印度佛教艺术传播交流过程中由西方文化到中国文化的重大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经济社会与哲学观、审美观的重大变化,佛教艺术(犍陀罗艺术)产生在古代印度的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之下,古代印度是一种严酷的种姓制社会,其宗教哲学观是一种一神教崇拜哲学观,佛陀即“天”处于至高无尚的地位,艺术观是古代希腊的“高贵的单纯与静穆的伟大”的雕塑之美。而中国则是一种典型的农业社会,儒道互补、以儒为主、亲亲仁爱的社会,哲学观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审美观则是一种“天人合一”根基上的气本论生命美学观,宗白华以“气韵生动”概括其特点,并将之阐释为“有节奏的生命”。在佛教本土化的过程中必然要在保留某些适合中国本土印度佛教文化元素的情况下,以中国的文化艺术观念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改变。这种改变集中地体现在佛教图像之上。 第一,由“乐死”到“乐生”的变异。 印度佛教是一种对于现实人生绝望的宗教,将现实人生完全看作“苦难”,唯有行善成佛才是人生最好的结果。涅槃是人生修行的最好结果,是对于人生烦恼的解脱,是一种最好的结局。所以,印度佛教是一种“乐死”的观念,将涅槃在雕塑与绘画中表现为人死后之象。而敦煌石窟艺术则从中国古代哲学“生生之为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出发,将涅槃描绘成一种生的状态。如敦煌158窟之涅槃佛,天庭饱满、身体丰腴、表情安详,完全是一种睡着的状态,似乎是随时等待醒来普度众生,积德行善。诚如穆纪光所言“佛的涅槃被艺术化为‘佛还活着’,是中国人把佛世的‘阴’转化为‘阳’的心愿的曲折表现;‘佛还活着’所铺展的语境,能为我们解读敦煌艺术的整体,建构一套相关的话语体系”。因此,158窟的涅槃佛被称为“睡佛”。⑧相反,印度犍陀罗艺术中的佛的涅槃是一种肌肉干瘪的死亡状态。我们从这幅公元2~3世纪的犍陀罗佛陀涅槃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德国学者吴黎熙对这幅图进行了描绘:“这一幅用灰色片岩制作而成的浮雕所表现的是佛陀去世和进入涅槃时的情景,佛陀身后并没有背光,他是按戒律要求僧人的姿势而侧卧着的。他左面的一位和尚大概是阿难陀,正保持着祈祷的姿势。背景上所刻画的人物沉浸在深深的悲哀之中。”⑨这两幅图清楚地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体现了从“乐死”到“乐生”的转变。 第二,由“天堂”到“天堂与人间共存”的变异。 印度犍陀罗艺术主要是表现佛的活动,是一种天堂的图像,敦煌石窟艺术则逐步增加了人间的活动画面,而且愈来愈多,成为天堂与人间的共存,充分表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的观念。 首先是人间容貌的描绘。佛教艺术是一种宗教艺术,主要表现佛界的神秘崇高、遥不可及。但敦煌石窟艺术却给佛界带来了人间气息,菩萨也有了人间形象。例如45窟中的菩萨阿难完全是充满童稚之气的现实生活中的少女。其次是人神相等。敦煌石窟艺术的开始是完全对神的歌颂,即便有人,例如供养人也只占极少空间。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的图像开始凸显,甚至达到与神相等的地步。如130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绘于盛唐时期,是唐代供养人画像中规模最大的一种,共12人,第一人身形高大,体姿丰满,是一种杨贵妃型的人物。再次是神权下降、皇权上升。随着历史的发展在敦煌石窟艺术中对于皇权的表现开始凸显,例如修于晚唐925年的220窟,里面对于帝王就非常突出,表明神权的下降与皇权的上升。复次是世俗生活的表现。敦煌石窟艺术一开始基本是宗教生活的描绘,到后来世俗生活逐渐增多,几乎描绘了中国古代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耕获、婚嫁、狩猎、医病、相扑、游泳等等。又次是人佛交流。敦煌石窟艺术由于佛的形体高大,但需要体现人与佛的交流,于是在雕塑时有意调整佛的角度,使之前倾,使之与礼拜的佛教徒在跪拜时正好视线相接,充分体现了佛的人间关怀。如45、46与113窟。 第三,由佛的歌颂到菩萨歌颂以及东方女神塑造的变异。 在印度佛教艺术中,犍陀罗艺术主要是对佛陀的歌颂,其他菩萨都是辅助性的,但敦煌石窟则逐步突出了对于菩萨的歌颂。其原因在中国“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看来,佛陀是崇高的,甚至是高不可及的,但菩萨却是佛陀与人之间的中介与桥梁,起到沟通神人的作用,因此对菩萨的歌颂在敦煌石窟艺术中占据的位置愈来愈突出与重要。《翻译名义集》引僧肇释“用诸佛道,成就众生故,名菩提萨垂”,说明菩萨为佛与人之间的中介。诚如易存国所言:“其中尤以观世音为代表,以其为中心形成的菩萨信仰成为中国佛教的一大特色。”⑩敦煌石窟艺术受中国天人观影响突出了菩萨,创作了文殊、普贤、观音等形象生动的菩萨雕塑与壁画。特别是观音成为救苦救难的救星,也是东方的女神。观音菩萨衣着华贵,丰腴饱满,婀娜多姿,足踏莲花,一手持净瓶,一手持柳枝,随时准备以瓶中的圣水拯救苦难中的人们。敦煌石窟创造了各种观音图像,有千手观音、水月观音、如意轮观音、金刚杵观音等等,仅唐代观音的图像就多达130余窟。而且,在犍陀罗佛教艺术中观音是没有明显性别的,甚至是男性,有胡子,但在敦煌石窟中观音变成了女性,温柔和蔼,大慈大悲,成为人们心中的女神,以至于专门有了供奉观音的殿堂。观音集中体现了中国佛教“护生”的特殊内涵,成为中国佛教艺术的特点与亮点。 第四,由块的、画的艺术到线的、节奏的舞乐艺术的变异。 印度佛教深受古希腊艺术的影响,因而是一种“块”的艺术,以雕塑性著称,如南亚婆罗浮屠的佛像重在表现佛陀的静穆和谐、高贵的体态。但敦煌石窟却受中国传统艺术通过流动的线以体现节奏为主的乐舞艺术特点的影响,出现了以生命节奏为主的线的艺术塑造。主要是飞天的塑造。而且飞天由起初身体的飞舞发展到后来飘带的飞舞,这种线的艺术呈S型,充分反映出身体的生命活力,而飞天对地面的挣脱和对天的向往,成为生命自由的象征,非常具有东方特有的美感。与此同时,敦煌石窟艺术对于乐舞的图像的表现非常突出,有胡旋舞、反弹琵琶、组舞、舞乐图。诚如宗白华所说,“敦煌艺术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特点与价值,是在它的对象以人物为中心,在这方面与希腊相似。但希腊的人体的境界和这里有一个显著的分别。希腊的人像着重在‘体’,一个由皮肤轮廓所包的体积。所以表现得静穆稳重。而敦煌人像,全是在飞舞的舞姿中(连立像,坐像的躯体也是在扭曲的舞姿中),人像的着重点不在体积而在那克服了地心吸力的飞动旋律”。(11) 第五,几点体会。 首先,从敦煌石窟艺术由“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历史嬗变,说明这一现象呈现的“传播”与“本土化”对于形象所带来的变异,可以补充进当代形象(图像)理论的建设之中。因为传播是一种图像的历时性“延异”,在这种“延异”过程中诚如德里达所言,可以造成所指与能指的滑动,好像植物之“撒播”,意义与图像均可发生极大的变异。这就突破了传统的结构主义图像理论仅从共时性考察所指与能指关系的局限。而德里达于20世纪60年代讨论的论题在1000多年前的中国敦煌已经被艺术实践所证明。在这里,“本土化”说明经济、社会、文化是文学艺术图像及其变异的根本原因,这也正是马克思有关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这说明当代图像理论建设除了关注文学艺术的内部因素,还要关注外部经济社会文化的因素。而对形象(图像)直接发生影响的还是一个哲学观与审美观,例如印度佛教艺术东传中的变异,主要是审美观由西方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观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哲学观的转变,以及由西方块的雕塑艺术观到中国古代线的生命论乐舞艺术观的转变。同时也证明了中国古代从刘勰《文心雕龙》之“通变”到敦煌石窟艺术之“变相”,都是中国古代宝贵的有关形象(图像)学理论,应该很好地总结与发扬。所谓“变”有改变、变革之意。刘勰在“通变”中讲到了时代变迁给文学带来的变化,同时也讲到“通变”给文学带来的活力,所谓“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12)而敦煌石窟艺术反映出来的艺术(图像)之变包含极为丰富的内涵:有时间因素、地域因素、文化因素、民族因素、宗教因素、观念因素与技法因素等,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 其次,敦煌壁画1000多年的历史嬗变,充分反映了佛教壁画演变过程中所经历的极为复杂的彼岸(信仰)与此岸(现世),以及西方形式美艺术与中国生命美艺术十分有趣的交流对话与吸收融合。这其实是一种东西两种文化与美学形态的二律背反。这种二律背反的结果是两种趋势:一是两者融汇为中西合璧的具有更强的张力与魅力的中国本土艺术,如前已提到的丝带飞天与美神观音等;二是形成两种元素的分庭抗礼,双方的消解,最后走向式微;或是神或天的力量的恢复,各种“天”的崇拜的佛殿纷纷建立;或是人在夹缝中偶露真容,宋元以后所建佛寺中各种世俗罗汉(如挑水罗汉)的出现等。这种对话与交融所导致的敦煌石窟艺术,由西方“天”的艺术到中国“天人”艺术之变,反映了审美观念的巨大变化,由西方模仿的与表现的艺术到中国的生命艺术的转换。中国生命艺术是一种特殊的遵循“一阴一阳之为道”的审美规律的艺术,是在天人的阴阳对比中表现出中国佛教普度众生的特有的“护生”内涵,在观音女神婀娜多姿的身姿与飞天的飘逸线条中,通过天人与线条本身的阴阳对比,表现出一呼一吸之生命的力量。而且,敦煌佛教壁画还告诉我们,这种由“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嬗变,实际上是从佛教的角度为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生命美学增添了新的内涵。那就是此岸与彼岸、块与线的二律背反所形成的张力,为“保合太和乃利贞”的“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志同”的泰和之美增添了彼岸的关怀,佛陀与观音以其无边的佛法与普度众生的圣水,给信众带来美好的年成与安定的生活,在壁画中佛教进一步走向人生。这是对于佛教艺术的中国式的改造,也是对于佛教彼岸性的某种意义的消解,从某种角度成为蔡元培所言“以艺术代宗教”的历史根据。说明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一神论信仰,是一种对于笼统的“天”的崇拜,以“天人合一”为信仰准则,以“礼乐教化”中的审美境界为信仰追求。这就是长期以来冯友兰与李泽厚所提出的中国古代儒家“天地境界”对于宗教的替代作用。而在佛教壁画艺术东传中这种彼岸与此岸的二律背反与块与线的张力,所形成的敦煌壁画图像艺术,是世界上仅有的,19世纪中期以后被西方后现代美术所吸收,价值重大。这种佛教艺术传入的汉化过程,也给中国艺术以重大影响。引进了飞天、观音、反弹琵琶与睡佛、立佛等具有空前魅力的形象,对于中国传统绘画写实技法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包括工笔画的出现。对色彩的运用也有重要影响,使中国艺术更加色彩绚丽。 最后,这种敦煌佛教艺术东传中的变化,实际上是中国文化艺术史上的第一次西学东渐,其结果是在中西文化艺术碰撞中产生了一种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壁画形态,由此说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具有强大的吸收和消化能力,也说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和实相生”、“气韵生动”等文化艺术理念的强大生命力与真理性,为我们今天发展艺术文化事业指明了方向,增添了信心。 本文为作者在2013年10月19日在“思想的旅行:从文本到图像,从图像到文本”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①赵教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40页。 ②刘勰:《文心雕龙注·通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30页。 ③赵宪章、顾华明主编:《文学与图像》(第二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80页。 ④转引自易存国:《敦煌艺术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3页。 ⑤[美]杜兰:《印度的艺术》,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47~248页。 ⑥李利安:《阿旃陀石窟》,《光明日报》2013年10月30日。 ⑦饶宗颐:《饶宗颐东方学论集》,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3页。 ⑧穆纪光:《敦煌艺术哲学》,北京:商务出版社,2007年,第103页。 ⑨[德]吴黎熙著,李雪涛译:《佛像解说》,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⑩转引自易存国:《敦煌艺术美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9页。 (11)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0页。 (12)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通变》,第331页。标签:佛教论文; 艺术论文; 释迦牟尼论文; 敦煌石窟论文; 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观音菩萨像论文; 文学论文; 希腊历史论文; 观音论文; 壁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