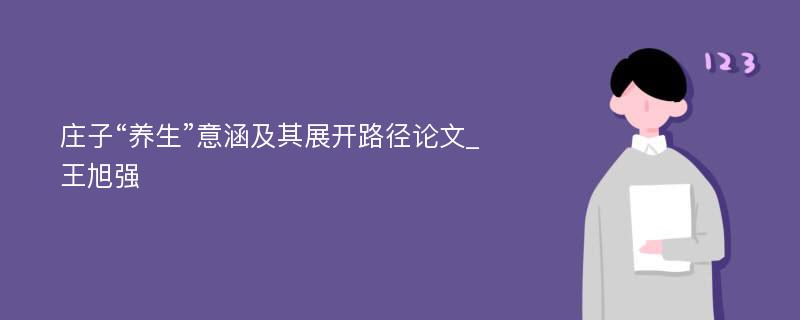
王旭强
(兰州大学大学哲学社会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庄子所谓“养生”,实际是指“养心”,但不局限于此一维度,也不排斥“养身”的可能性。“生”,即“身”与“心”两个面相,此二者共同构成庄子意域之“生”。本文旨在通过历代注家对《养生主》此一篇之“缘督以为经”一节注疏之分析,联系内篇,对此一论点进行尽可能有效之论证,以图为庄子所谓“养生”意涵提供更优解。
关键词:养心;督脉;庖丁解牛;薪尽火传
《庄子内篇》中多处出现一些样貌奇特之人,如:右师,支离疏,王跆,申徒嘉,叔山无趾,哀跆它。这类人的特点就是:形残神全,即畸于人而眸有天。在庄子看来,身与心相比,心更加重要,但这并不构成对于身的排斥,所以无法推出庄子反对形貌整全的结论。心灵与形体相比,心灵是第一位的,形体是第二位的,但第二位的并不意味着可有可无。庄子所专注的核心是:心灵,“其所保者与众人异”。(《庄子·人间世》)人宁可“形残神全”,而不可“形全神残”,尽善尽美的状态就是“形美神全”,如“姑射神人”,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一、缘督以为经
庄子之世,战国中期左右,这是一个激烈变革的时期,百川沸腾,山冢崒崩。自周平王迁都洛邑开启东周至于此时,承担守护秩序重任的周王室对其自身所处的内外交困的境地所作出调整和回应未曾产生有效的改变,现有的社会体系濒临崩溃。古老的政治架构和权力分配模式由于内部力量的紊乱此时开始呈现出一种灾难性的后果,宗法制遭到破坏,王室与诸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原有的礼乐文明所建构起的社会秩序,开始分崩瓦解。
孟子和庄子对于生活的态度以及社会诉求有很大不同,但对于此时社会现实的揭露却如出一辙。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文明衰落的时代,其国如此,其君如此。人们在其生命的开端时,就降临于黑暗之中,在其生命将处于终结之时,还是处于黑暗之中而不自知,并且总是如此般走向死亡,从黑暗中而来,在黑暗中而去。这对于生命而言,无疑是一重浓黑的悲凉。庄子试图打破这种无明的压迫,而为生命寻找到另一种全新的可能,他想叫醒那些闭着眼睛,行走在大地之上,过着影子般生活的人。
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生,可以全身,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庄子·养生主》)
有人以为,“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是指做好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坏事不要遭受刑剹之害。此解法似有不妥。将“为善无近名”解为做好事不要有功名心,看似合理,实则无关乎本篇之要。若以“为恶无近刑”为做坏事不受罚,则流于荒诞。本篇旨在论述养生之道,而做事之好坏与养生之间亦有何关联,着实难以推敲。窃以为文中所谓“为善”不是指做好事,而是指善于养生,所养者,为一完整的生命。“为恶”亦不是指做坏事,而是指:即使不善于养生,也不要让自己的生命受到像刑罚一样的伤害。而此一句“缘督以为经”,则为庄子“养生”之要旨,其“养生”之核心意涵尽在于此。但对此一句之注解,名家注疏颇为不同,大约可分为如下几类:
取“中”之解:在郭象[1]和成玄英[2]看来,所谓“缘督”即为顺中,所谓“经”即是指“常”。取“督脉”解:王夫之[3]以为,“督”为人身后之中脉,不偏不倚,有脉位而无形质,使得清妙之气可以流通于人身上下。取“至善”解:朱文熊[4]认为,“督”即是《大学》中所言至善,《中庸》中所谓指隐至微之独。取“真君”解:胡文英以为,“督”即为《齐物论》中所谓“真君”。取“中间”解:陆树芝、林云铭以为,“督”是指“衣缝当背之中”,可以引申为“中间”,亦指出“缘督”与导引之法无关,“缘”为顺,“经”为常。
名家注疏似为繁杂,然逐条分析,可以看出:注疏家们大都取“中”之意以解此句,而取“督”之本意者极少,亦明确指出此与内丹修炼之道无关。以“中”解“督”,其意甚为明显,养生之道,在于得中,得中则通,通则天地灵气往来。这是一种直觉体悟,关乎心灵之扩大,心神之保养,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我无伤于物,物亦无伤于我,物我无伤,回归精神的故乡,游于无物之初,游于无何有之乡。在身得以保全的同时,心灵亦获得一份洒落与逍遥,以此为“养生”之核心,亦合乎《庄》学之旨。
但注疏家们为何一致不愿取“督”之本意解?也可从上述注疏中窥见一丝端倪:“或云导引之法以督脉为经,亦缪”,若取其本意解,则与“摄形养生”之术法为一,若如此则违《庄》之大旨。庄子要求“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庄子·德充符》)、“不刻意而高”、“不导引而寿”(《庄子·外篇·刻意》),他的确反对“摄形养生”、“炉火修炼”之事。但就实而论,取“督”之本意与“炉火修炼”确为二事,取“督脉”解有可能会导向“炉火修炼”,但不必然如此,所以,以此二者相等同,似为不妥。此外,庄子并不没有反对“身体形貌”的意图,他要求“循自然之理而不伤身”,不有身,则何以有其生。况且形神合则生,形神离则死,若无形体,心神何以居之。循自然之理,以养护形体,而无关于“内丹修炼”,以心神灵魂的提升为目的,而心神的壮大又可以反哺于形体,形体与心神相互加强,可以进于姑射神人之境: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以“督”为人身体中的督脉,督脉连通人体上下,使生命上下贯通,而无阻碍,成一整体。所以取其本意解亦可,而不违《庄》之旨。
二、庖丁之刀:以刀喻心
若以“缘督以为经”为提纲挈领,在“庖丁解牛”一节庄子则给出一条具体的“养生”之道。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庄子·养生主》)
对此一段,误解甚多,故有必要一一厘清。
常识以为“庖丁解牛”指通过不断的实践,经验的积累逐渐丰厚,最后达至“道”境。可以看出,此种解释,将解牛所达到的极致境界归结为一种实际的操练功夫,认为从“始解牛之时”、“三年之后”至于“方今之时”为一技艺不断娴熟的过程,持之以恒,则学艺日久,技能越精。不断地练习,臻至熟练,可以肢体协调,举手投足可以“合于《桑林》之舞、中《经首》之会”。就此一点,已偏离庄子本意远矣。
窃以为,此节是在阐述“养生”之操作路径,而非技艺如何娴熟。技艺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遮蔽;既是一种手段,也是一重隔膜,它使得人与世界相分离。常识化的理解之所以有偏差,其核心在于对“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一句理解有误,“进”亦非进入之意。郭象注:“直寄道理于技耳,所好者非技也”。[8]成玄英疏:“进,过也。所好者,养生之道,过于解牛之技耳”。[9]陆树芝、林云铭释:“出乎技之上”。[10]注疏家们皆取“过”之意,“过”即为超越。至此,此句涵意已为明显:所好者为超越于技艺之上的道。所以,此句非指由技入道。在此之技道关系非是由技向道的历时日久的攀爬,而应当是由道对技的向下赋予,只有基于此一要点,庖丁之技方可以呈现为极致的表演,其节奏亦可以合于雅乐。
此节行文,皆述“解牛”之事,何以窥得“养生”之操作路径?
纵观此节,可以窥见,有一“刀”或“刃”字自始至终,出现达十余次。该字有何要紧之处,以至于多次浮现,其和“养生”之道亦有何关联?此一点值得推敲。庖丁最后一句:善刀而藏之。郭象注:“以刀可养,故知生亦可养”。[11]陆树芝释:“力不劳,而神亦大适,用刀一如未用,故曰:善刀而藏。以上皆言所好之道,在于养刀”。朱文熊释:“文人水到渠成,弹丸脱手,囊笔而出,四顾天地皆仄,确有此种神理,此缘督之逍遥自适也”。
注家以为,“养刀”和“养生”之间具有某种关联,但并未对此间关系作更进一步说明。为何庖丁“善刀而藏之”之后,文惠君说:“闻庖丁之言,吾得养生焉”,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某种跨越。或许在庄子的语境下这种跨越是不言自明的,但对于研究者而言则是需要推敲进而明晰此间关系的。庄子在此节行文中反复提到“刀”,最后文惠君得养生之道,故而在此可以明确:“养刀”和“养生”之间是有关联的。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养刀”即是“养生”,这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而“养生”的重点则在于“养心”,所以“养刀”即是“养心”。如此,则“养刀”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可以明确,基于此种解释,庖丁“善刀而藏之”与文惠君得养生之道之间的跳跃则可以被有效链接。换言之,“刀”对于“心”而言,是一重隐喻,刀可养,心亦可养。以刀为心,则可对“庖丁解牛”一节有如下新解读,似乎是契合《庄子》主旨的:在此之“刀”隐喻人之心灵,以刀解牛,意指人以心与世界相互交涉,庖丁“善刀而藏之,所谓“善刀”,即是养刀,以刀可养,意指心灵之可养。庖丁之刀,十九年而如新,在于其对刀之爱护,旨在强调内在心灵的保养,那份最初所禀受的性灵可以一如,不随时间的消退而磨损,可以若“新发于硎”一般。“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凡人在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因其心中有太多的偏私,所以失去了那份天然,以至于将其心灵伤害至千疮百孔之境地,而不可复归于其初,不亦悲乎!人生于世间,固然有诸多不得已,但也不可因此而伤害那份可以使人自我成就的灵性。人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而有别于万物,需要意识到:什么样的生命才是真正值得拥有的,是汲汲于外在的名利还是保养内在的心神灵魂,对此不可不慎重。庖丁四顾,踌躇满志,在空间中,他透过时间长廊,看到了自己的突破。人在其生命的践履中总会遇到艰难险阻,他曾经也遇到过很多困难,“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但他最终都成功做到了。他感到开心,也很安心。庖丁之技,有道贯通于其中,而技亦为道之展现。道、心、技三者贯通于一体,皆得以加强。而身亦为心之延生,身心一体,亦皆得以长养,此所谓“养生”之道。亦有注疏家持此论:
只一庖丁解牛之事,则尽养生主之妙,以此乃一大譬喻耳。
大名之所在,大刑之所婴,大善大恶之争,大险大阻存焉,皆大大軱也。
三、右师与泽雉:养生之范
庄子在明言“养生”之路径后,又给出了两个特殊的典范:右师与泽雉。若以为文轩公与右师的对答所呈现出的意涵是显明的,则泽雉所表达的意义似乎是潜藏的。此泽雉并非山野之中自在游走之泽雉,在更深的程度上,它是对人的一重隐喻。以雉喻人,泽雉获得了更加深刻的意涵。泽雉的选择意味着人对其自身存在境遇的选择,对泽雉的关注更是对人自身存在境遇的关注。
文公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是以知其天也,非人也。”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蓄乎藩中。神虽王,不善也。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庄子·养生主》)
文公轩与右师之对答虽短,但实为难解,注疏家之注释亦颇为繁杂。有注家以为,右师一足,是其命如此,成玄英、朱文熊持此论;另有注家以为,右师如此是天使之然,林云铭、释德清、王夫之持此论;亦有注家将此归结为“知”之不足所导致。然结合内篇之旨,联系注家之注疏,对此亦可窥得一二。若以右师之介为天生使之然,则可从王夫之解,天生如此,有介,有舆。若以右师之介为“犯于王憲”所致,何以言“天也,非人也”?有注家以为是“天使其仕禄,故取刖”。但“仕禄”与“取刖”有何关联?“仕禄”不必然导致“取刖”的刑罚,而“取刖”的刑罚亦不必然由“仕禄”所导致,所以二者并无必然之因果。所以,此解有疑。有解以为是“不知进退,自取天罚”所致。但右师“不知进退”之论又从何导出,纵观《养生主》全文,未有一处表明右师“不知进退”,所以此点亦不明确。窃以为此段右师之论有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之意,人于世间,“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物为接,日以心斗,”有许多不得已,有许多不可把控之处,所以导致形体的残缺亦有可能,此为“人智”之缺。虽身有所缺,但“神”却得以保全,而迷惘之人则与此相反,身虽无缺,而心“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也”。此二类人构成鲜明对比,更近一步突显庄子所谓“养生”之要。
右师入仕,而泽雉“不蕲蓄乎藩中”,似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反自然”,摆脱层层桎梏,破除种种机心与成见,于天地之间,快然自足,放飞心神,尽养生之妙义,亦自得一片逍遥与洒脱。“夫俯仰天地之间,逍遥乎自得之场,固养生之妙处也。又何求入笼而服养哉!”“夫泽中之雉,任于野性,饮啄自在,放旷逍遥,岂欲入樊笼而求服养!譬养生之人,萧然嘉遁,唯适情于林籁,岂企羡于荣华!”如若落入尘网之中,则性情受束,如倒悬之人,而不可得解。相较于外在之荣华与名利,自我内在之性灵洒落则显得更为重要,于此不可不慎。“夫始乎适而未尝不适者,忘适也。雉心神长王,志气盈豫,而自放于清旷之地,忽然不觉善为之善也。”“雉居山泽,饮啄自在,心神长王,志气盈豫。当此时也,忽然不觉善之为善。既遭樊笼,性情不适,方思昔日甚为清畅。鸟既如此,人亦宜然。欲明至适忘适,至善忘善。”泽雉倘若入于藩中,失去的是自由,不仅身体受束,而心灵亦被縛上一层枷锁,人亦如此。自由为生命的核心,生命如果没有自由,那剩下的便只是一场虚妄。所以要自作主宰,而无求于外,若有真宰,与之沉浮,真实的去体验生命,不宰制,不分别。
四、老聃之死:安时处顺
庄子于“养生”之典范后对于生死,这一终极存在境遇给出了一重全新的考量。在此所呈现出的问题是:作为一个有限的必死者,应当如何面对这一遭遇?普通的个体在这一时刻所表现出的大多只是“不蕲之言”、“不蕲之哭。在庄子看来这是不当的,亦或是不必要的。生,是时运之使然;死,亦可以坦然顺之。对于生死,安时处顺即可,这既是自然的方式,也是对生死的更好的一重关照。
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悬解。”(《庄子·养生主》)
此一段中,“遁天倍情”指何事,“忘其所受”所忘记的又是何物,“所谓之遁天之刑”又是遭受的何种刑法?
注家以“遁”为“逃”、为“违”、为“去”,其意皆同,指逃离。于“倍”之一字,有注家以“加”释,亦有注家以“背”、“悖”释。此二解看似相距甚远,实则殊途同归,细究可知:若取“加”之意,其所加者为“人之情”、“流俗之情”;若取“背”之意,其所背者为“性命之情”。二者皆以“真情”为旨归,只不过最初的指向不同而已,所以此二解皆可。“倍情”者,增益了流俗,而背离了生命的真实,也忘记了其所禀受于天的那份天然,那份纯真,被后天的种种所支离,变得破碎,距离那最初的如一原来越远,这也是“遁天”,违逆“养生”之道所要承受的罚,在一个虚假的世界里,无处可逃。情,可以深,不可以陷溺于其中而不得拔。陷溺,是一重偏执,早已失却了“情”之真。真情,是一种心意,是体贴,是关照,只有用“心”才可以洞察到,而不是通过外在的表现及行为。即使是假,若以一颗真心去做,那假也就成了真;即使是真,若以一颗虚假之心去做,那真也就成了假。所以,关键在于真心真情。真情源于真实“自我”之最深处,可以自我生发,自我完成,自我实现,而不假借他者。庄学并不反对“真情”,其所反对的是虚妄的“人情”,庄子向来“大有径庭,不近人情。”
惠子谓庄子曰:“人固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天选子之形,子以坚白鸣!”(《庄子·德充符》)
在庄子看来,惠子汲汲于外,劳心劳神,心灵为世俗尘垢所染,故而不赞同于他。因为他失去了“天情”而坠落到了“人情”。有“人情”就有倾向,有倾向,就有偏爱,而偏爱则会导致不必要的伤害。
五、薪尽火传:大化流行
此节最后提到“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一句,意味深长。
由名家注疏可看出,注家们大多以“薪”喻“形”,以“火”喻“神”,此解亦合庄子意。所谓“养生主”之“主”者,实为心神,亦即内在自我之性灵。在庄子看来“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无论得与不得,其存在之真实不会有丝毫之减损。以“薪”视“形”,则虽“薪尽”,而“火”不必随“薪”之尽而尽,可传于另外一“薪”,“薪”有尽而“火”无尽,故而构成“生”的形躯可以腐朽,可以消亡,但作为“生”之核心的“神”则不必然随“形”之消亡而消亡,亦有可能如“火”传于他“薪”一般,另有一安顿之所,即形有涯而神无涯。至于其安顿之所在何处,对于此一点,则不可知。诚如前“薪”已尽,传“火”于后“薪”,此后“薪”非前“薪”所能知。人生于世间,皆知有一死亡,死亡为生命之必然,天地之间,无处可逃。但人于其死亡时,对于其生死是不能自知的。虽然死亡为生命的不可避免的归宿,但对此并不需要怀有极大的忧虑与恐惧,悦生而恶死,在庄子看来是完全不必要的。在庄子眼中,悦生恶死者与此骊姬实无二致,“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庄子·齐物论》)但这也不是在说死在价值上就高于生,亦或是死后有一精神的天国或极乐世界,庄子没有此种意图,对于生死,他只是强调“无变于己”。但在此能否依据“薪尽火传”一句就得出庄子主张灵魂不朽的结论?需要做出区分,主张“不朽”和主张“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导向,切不可混为一谈。倘若主张“不朽”,认为有一无限终极世界存在,则与此相对而言,就会有一“有朽”,即认为有一有限幻灭世界。在此,世界被完全二分,此主张是否能合《庄》学之旨?
窃以为,庄子所强调的是生命与世界的生生化化,所谓生,即是创造,即师法于自然,但这并不意味着是对于自然的机械模仿,也不是要获得关于自然的影像,而是开发人的内在的、源源不断的创造精神,合于大化。《易》言曰:生生之谓易。观万物之生意,裁成辅相,参赞化育。所谓化,即大化如流,与物同化,上下四方,往古来今,不断生化与流动,世界周流,变动不居。生命为世界中一生命,世界亦因生灵万有而成就其鲜活,生命与世界共为一体。在此之中,无所谓有限,亦无所谓无限;无所谓终极,亦无所谓幻灭;无所谓有,亦无所谓无。因为这是一个整全的大世界,超越了终极与幻灭、有限与无限、有与无一类的对立,凡对立,都是一种成见,都是一重迷惘,而这个大世界,是本然纯真而没有成见的。所谓“人”,即形神合一者,神在人,寓于形而为神;不寓于形,则化于天,归于道。道即大全,万有内蕴于道中,道亦内蕴于万有之中。大即大化,万有即小化,小化为大化中一小化而非独立之一小化。以道观之,无论是为庄周,还是为蝴蝶,亦或是其他之生灵,都是等值的,都是一样的,故而皆可以欣欣然。所谓“生死”,亦只是大化中之两种状态,故而无所谓“悦生”,亦无所谓“恶死”。世间万物,彼此之间,并不是相互阻隔而各行其是,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另一个生命的延续,只不过是转化了另一种形式。因而,物类之间应该打破凡人的界限而彼此相互流转。因此,整个造化世界就是一个源源不断、生生不息的生命传承,此即“火传”之火,亦“养生”之生。
参考文献
[1][2][8][9][11]郭象注 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顺中以为常也。缘,顺也。督,中也。经,常也。”[M].北京:中华书局,1998:67
[3][15]王夫之著.《庄子解》:“身前之中脉曰任,身后之中脉曰督。督者,居静而不倚于左右。有脉之位而无形质者也。”[M].北京:中华书局,1964:31
[4][13]朱文熊撰.《庄子新义》:“缘督之督,即《大学》之至善,《中庸》至隐至微之独。”
[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28
[5]胡文英撰.《庄子独见》:“督如家督长子之督,即《齐物论》中所谓一身之真君也。”[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19
[6][10][12]陆树芝撰.《庄子雪》:“缘,循也。督,中也。”[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2011:35
[7]林云铭撰.《庄子因》:“缘,循也。经,常也,循此以应物之常,不必复随无涯为知矣。”[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30
[14]释德清撰.《庄子内篇注》[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65
[16]郭象注 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右师,官名也。介,刖也,公文见右师刖足,故
惊问所由,何于犯忤而致此残刖于足者也。”[M].北京:中华书局,1998:70;朱文熊撰.《庄
子新义》:[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31林云铭撰.《庄子因》:[M].上海:华东师
大出版社,2011:32;释德清撰.《庄子内篇注》[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1:67;王夫
之著.《庄子解》:“天命使之一足。”[M].北京:中华书局,1964:32
[17]郭象注 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知之所无奈何,天也;犯其所知,人也。……偏刖曰独。夫师一家之知而不能存其两足,则是知之无所无奈何。若以右师之知而必求两全,则心神内困而形骸外弊矣,岂直偏刖而已哉。”[M].北京:中华书局,1998:70
[20][21][22]郭象注 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8:70
作者简介:王旭强 (1993年—),男,汉族,宁夏西吉人,单位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论文作者:王旭强
论文发表刊物:《知识-力量》2018年2月下
论文发表时间:2018/5/8
标签:庄子论文; 注疏论文; 庖丁论文; 生命论文; 心神论文; 在此论文; 有一论文; 《知识-力量》2018年2月下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