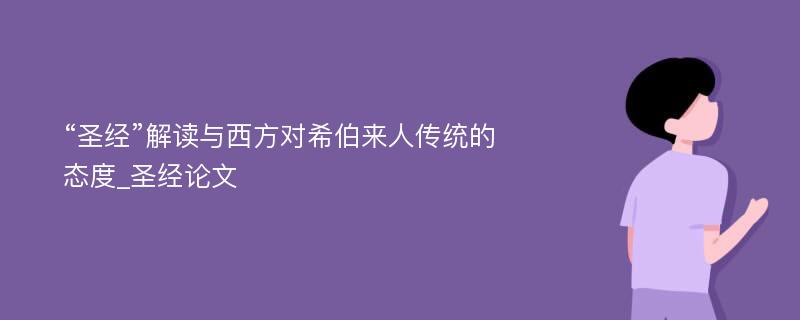
《圣经》的阐释与西方对待希伯来传统的态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希伯来论文,圣经论文,态度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上个世纪中期奥尔巴赫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模仿》,此后西方把《圣经》文本明确 地作为一部文学名著的研究便逐渐兴起,到了80年代可谓进入了一个高潮。至今这个研 究方向的势头仍很猛烈,吸引了无数对西方历史、文化、文学和政治思想理论有兴趣的 学者。
艾里克·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注:艾里克这个名字有两种拼法:Erich和Eric ,此处取用了《模仿》一书标写的名字。)是个犹太学者,二战期间,他为了躲避希特 勒迫害逃到土耳其,在那里写出了《模仿:西方文学中对现实的表现》(Mimesis: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这部重要的著作。(注:这篇文 章中的人名、书名大多是笔者自己的译法。引文如没有注出译者,也是笔者自译的。) 虽然在书中他只用了第一章“奥德修斯的伤疤”来讨论《圣经》的文体,但他已经成功 地揭示了《圣经》不仅是一部宗教和历史文献,它也是与荷马的《奥德赛》并驾齐驱的 伟大史诗。(注:关于奥尔巴赫在这一章里的分析,本文作者在另一篇名为《<圣经·旧 约>的叙事特点、解读的戏剧性和意识形态影响》的文章里已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该 文已收入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的论文丛书《欧洲文学与宗教》,任光宣主编,即 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在他之后,对《圣经》特别是《旧约》的文体、叙事特点 、人物塑造、整体结构、修辞手段、隐喻和象征含义等进行深入探究、取得了丰硕成果 并有独到见地的学者人众,其中最突出的是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罗伯特 ·艾尔特(Robert Alter)、梅厄·斯腾伯格(Meir Sternberg)、加布利尔·约斯泊维齐 (Gabriel Josipovici)、帕特里克·格兰特(Patrick Grant)、弗兰克·克尔莫德(Frank Kermode)、约翰·H·哥特森特(John H.Gottcent)、威斯理·A·科尔特(Wesley A.Kort)、约翰·B·加布尔(John B.Gabel)和查尔斯·B·维勒(Charles B.Wheeler)等。而后现代的文论家们也不甘寂寞地加入了阐释《圣经》的行列,比如米柯 ·巴尔(Mieke Bal)对《旧约·士师卷》作了相当深刻的女权主义批评,而米哈伊尔· 巴赫金(Mikhai Bahktin)、保尔·利科(Paul Ricoeur)和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等也纷纷撰写了文章,用各自创建的理论来展示《圣经》的文学特色。
原加拿大渥太华大学知名教授大卫·拉依尔·杰弗里(David Lyle Jeffrey,现任教于 美国德克萨斯州贝伊勒大学)曾于1990年发表过文章《20世纪80年代<圣经>作为文学的 研究状况评介》,综述了20世纪80年代西方在《圣经》文学的研究领域内取得的主要成 就和存在的问题。(注:David L.Jeffrey,“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Vol.59:No.4,Summer,1990,pp.570-580,p.570,pp.577-580,pp.570-571,p.575.)他指出20世 纪80年代伴随着西方的文学教授和学者们对《圣经》复兴的极大兴趣,出现了一个研究 高潮,大约出版了讨论《圣经》的几十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这个《圣经》研究的热潮 之所以产生有许多原因,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学者们都共同认识到,如果在后现代的今 天还想让西方经典文学被读者们接受、读懂并欣赏的话,了解和熟悉《圣经》已是当务 之急。(注:David L.Jeffrey,“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Vol.59:No.4,Summer,1990,pp.570-580,p.570,pp.577-580,pp.570-571,p.575.)西方几乎所有英语国 家的大学在80年代都纷纷开设了《圣经》文学课程,因为教员和学生都意识到,对《圣 经》普遍的无知影响了学生理解从乔叟到乔伊斯的所有文学作品,一批导读的手册也应 运而生。(注:在他的文章里,杰弗里列举了四五个流行的手册。见第570页。)80年代 的这些《圣经》著作的作者大多并非专门的神学家或宗教界人士,而是刚刚转入这方面 研究的教授和文学评论家,他们采用的理论或方法几乎全部植根于后现代,他们用结构 主义、形式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或其它阐释学方向的 理论来进行高层次的《圣经》解读。杰弗里的文章一共评介了约15个作者的20篇作品, (注:虽然视角不大相同,笔者在《<圣经·旧约>的叙事特点、解读的戏剧性和意识形 态影响》一文中已经比较详尽地评介过杰弗里在他这篇文章中提到的两三位主要评论家 的著作和贡献,他们很有代表性。愿意进一步深入了解这方面内容的读者可以参考拙文 。)除了讨论这些著作或文章是否只是把《圣经》当作纯文学作品研究以及对《圣经》 了解得是否深透之外,他的文章还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后现代文学理论名流们介入《圣经 》文学批评的目的。比如罗兰·巴特同别人联合出版了《结构分析和圣经阐释:解读文 集》(Structural Analysis and Biblical Exegesis:Interprtational Essays),然而 他的主要兴趣是在《圣经》阐释里尝试使用结构主义理论的消解边界的功能。因此,像 巴特和利科这类理论家来评论《圣经》的作品就不同于大学师生对《圣经》的研讨。理 论家们并不真正关心文本,更多的不是为了促进对《圣经》的了解,而是为了拿《圣经 》来检验自己的理论,因为《圣经》恐怕是目前世界上尚存的、仍旧能够抵制被任何一 种理论任意摆布的惟一文本了。(注:David L.Jeffrey,“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Vol.59:No.4,Summer,1990,pp.570-580,p.570,pp.577-580,pp.570-571,p.5 75.)
但是杰弗里文章提出的最值得继续思考的问题乃是西方文明中希伯来传统和希腊传统 的关系,以及在这次《圣经》的文学批评运动中西方学者们对希伯来传统所表现的不同 态度。一提及这个问题我们自然首先就会想到19世纪的著名文人、学者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实际上,阿诺德的名字与今天的《圣经》文学阐释密切相连。作为 一个牛津大学的诗歌教授,他在这方面的影响一直延伸到今天。阿诺德十分关心对《圣 经》的正确认识,努力要“把《圣经》从‘非利士人’的影响下解救出来”,使其回到 大学课程的经典书目之中,成为一部人文教育的基本文献。(注:David L.Jeffrey,“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Vol.59:No.4,Summer,1990,pp.570-580,p.570,pp .577-580,pp.570-571,p.575.)
谈到阿诺德与希伯来传统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提及的是他的重要论著《文化与无政府 状态》(Culture and Anarchy)。随着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暴露,以 阿诺德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精英们纷纷就社会现状、原因和解决办法发表己见。众所周知 ,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中阿诺德把英国的三大社会阶层:贵族、中产阶级和劳 工群众分别喻称为野蛮人、非利士人和群氓,并对他们各自的问题进行了剖析。阿诺德 认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推崇实干、实效,把工具手段置于一切之上,而忽略了“理智的光 照”,没有“完美的文化”。他指出,各行其是的无政府状态是这样一个只强调行为自 由而没有“理智光照”的社会的必然结果。(注:阿诺德在书中多次阐明这些观点,比 如在第2章“随心所欲,各行其是”中,他写道:“我们崇拜自由本身、为自由而自由 ,我们迷信工具手段,无政府倾向正在显化。因为我们盲目信仰工具,因为我们缺乏足 够的理智光照,于是情形愈演愈烈……。”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 书店,2002年,第45页。)在进一步查看和追溯无政府现象的根源时,阿诺德对比了“ 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这西方两大文化思想传统。他大力肯定了以《圣经》,特 别是《旧约》为代表的希伯来传统在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约束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 同时又指出,“希腊精神”才是令人善于思考、追求知识的传统,才能给予社会“理智 的光照”,因此也是当时英国社会更加迫切需求的精神。(注: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 》,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45页,见第4章“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中的 有关叙述。比如:“希腊精神要求人所做的一切事都必须令思想满意,显然,这样的要 求很适宜用来推动我们的民族向前走,使我们在许多方面的能力和活动都能达到完美。 ”第139页。)他特别批判了基督教和代表基督教思想的《圣经》中强调的克制和奉献自 我、追随上帝而不加思考的那种绝对服从。阿诺德最反对清教和不从国教等教派把希伯 来文化中已经占有很大分量的人类罪孽感又进一步推至极致,他认为这是阻止人们实现 完美的巨大障碍。(注: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韩敏中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1 16页。阿诺德这部书有其论战背景,他的批评,包括对宗教界人士和非利士人的批评大 多都是具体有所指的。除去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里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具体所指。在 大卫·杰弗里的文章《20世纪80年代<圣经>作为文学的研究状况评介》里也明确地指出 了阿诺德所针对的是哪些人。可以查看该文第570-571页。)在他眼里,基督教和希伯来 传统只讲道德行为和道德感情的做法与中产阶级的实干和实际精神形成了互动,并一拍 即合,助长了推崇工具理论的英国现实,只求在物质层面解决问题。因此,阿诺德要提 倡希腊精神的思想自由和快乐,提倡文艺复兴的思想解放,但他也看到了文艺复兴的另 一面,并以它的负面为例警告天下,即太多的思想自由、无拘束地满足欲望就会带来社 会道德败坏的危险。(注: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第120-121页:“如果说伟大的基 督教运动是希伯来精神和道德冲动的胜利,那么被称作‘文艺复兴’的那场伟大运动就 是智性冲动和希腊精神的再度崛起和复位。……但如同古代多神教世界的希腊风气一样 ,文艺复兴在道德上也是孱弱的,道德品格松垮,道德情感冷漠……”)
那么,如何能把“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正确地结合起来,如何能获取两者的 有利因素以达到纠正和造福社会的目的呢?阿诺德的一个药方就是加强人文教育,纠正 教育中的实用和功利成分。他首先提出了要在学校设置《圣经》阐释课程,不是宗教意 义上的读经,而是文化和文学的阐释研究。在他1873年发表的研究《圣经》阐释的《文 学与教条》(Literature and Dogma)中,阿诺德对解读《圣经》的方法做了具体建议, 后来他又在《上帝和圣经》(God and the Bible,1875)里再次强调正确理解和阅读《圣 经》的重要性。在《评论文集》(Essays in Criticism,First Series in 1865)中,他 申明他的批评,即用希腊主义(Hellenism)来替代保守的、宗教的无政府的圣经主义(biblicism),(注:“圣经主义”是我按照biblicism的-ism字尾所选择的暂时译法。) 是一种进行文化改革的现代工具。他提倡当时德国的教育体制和他们的“科学”研究方 法,一种“圣经考证学”(higher criticism)。(注:见《文化与无政府状态》第93页 的论述。实际上,是阿诺德第一个使用了“the Bible as Literature”这个说法。)按 他的想法,人类堕落和需要救赎的状况应该是古代的事情,不应该在现代过分强调。他 希望通过科学地读《圣经》来帮助建立一个能起到正面影响的、宽容的宗教文化,而那 令人尴尬和窒息的人类犯罪及负罪的问题就可以被现代批评的理性手术刀切除掉。(注 :见《20世纪80年代<圣经>作为文学的研究状况评介》,第570-572页。)阿诺德对希伯 来传统的批评,对思想自由和智性的强调,有趣地呼应了人类父母亚当和夏娃不甘愿盲 从而偷食知识之果的违禁行为。自然,他也就不会认同原罪和赎罪那一套思想和心灵的 桎梏。开设《圣经》课的提议就是阿诺德的改革理想的一部分,是为了建立“全国民的 正确理性”(national right reason)而进行的人文教育运动的组成部分。它一方面显 示出阿诺德对基督教影响的重视,但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企图在保留希伯来传统对西方( 具体就是英国)的道德约束的同时,摈弃它原来的狭隘、森严,从而给英国人留下接受 希腊思想自由传统的余地,把他的国民从盲目行动、追求实干效果和物质利益的状态中 解救出来。他的建议提出后有一阵子也得到了呼应,比如1896年牛津大学诗歌教授(后 任芝加哥大学英语教授)理查德·G·默尔敦(Richard G.Moulton)就编写了《圣经文学 研究》(The Literary Study of the Bible)来支持阿诺德,试图在大学课堂里用圣经 考证学教授《圣经》;科特内(W.L.Courtney)也编写了加注释的《圣经》故事选读本《 文学读者的圣经》(The Literary Man's Bible,1907)。(注:这两例来自杰弗里上述这 篇文章。)但是直到20世纪中期,阿诺德关于《圣经》进入课堂,特别是把它作为经典 列入各高校课程的建议并没有如他所愿地得以实现。
自奥尔巴赫到20世纪80年代的《圣经》文学研究高潮及其成果既延续了阿诺德的思想 ,也出现了与阿诺德对立的观点。弗莱就是阿诺德的拥戴者,在他的著作里,我们见到 了阿诺德始于《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的事业的延续。像阿诺德一样,弗莱原来也是 个诗歌教授,在多年的教学中他深感《圣经》与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密切关系,以至经常 觉得自己的诗歌课像是一门《圣经》的注释课。于是他决心改变被动局面,从正面来讲 授和研究《圣经》,便专门撰写了讨论《圣经》的《圣经与文学》(包括上下两册专著 《伟大的代码》和《语言的力量》),从而进入了20世纪后半叶《圣经》作为文学话题 的研讨行列。(注:关于他专门研究《圣经》的原因和过程,请参看《伟大的代码》(The Great Code:Bible and Literature)的“前言”,(London,Melbourne & Henley:Routledge & Kegan Paul,1982),第xi-xxiii页。)这两部著作集弗莱一生研究之大成 ,探讨了《圣经》作为文学的身份、特点和地位,以及它对西方文学的影响。他撇开了 神学和史料研究,把《圣经》当作一个神话原型体系,从语言、隐喻和类型等方面来查 看和分析,显示了《圣经》文本的丰富内涵。因此,如阿诺德希望的那样,希伯来传统 得以在宗教束缚之外的世俗意义上突现其文学、文化与历史特点,在现代社会中继续发 挥其影响。但不同于弗莱,也有当代学者在自己著作中表示了与阿诺德某些方面不同的 意见,比如艾尔特和克尔莫德合作出版的《圣经的文学导读》(The Literary Guide to the Bible)。这部书以阿诺德的研讨方法和目的的对立面姿态出现,编者在前言里声 称由阿诺德起始一直控制了《圣经》批评的“圣经考证学”和“科学”批评所追求的文 学和文化目的现在都已破产。19世纪这种“科学”批评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削弱了 《圣经》文本的文学性。(注:David L.Jeffrey,“The Bible as Literature in the 1980s: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Toronto: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Vol.59:No.4,Summer,1990,pp.570-580,p.570,pp.577-580,pp.570-571,p.5 75.)他们和阿诺德的分歧不在于对《圣经》本身价值的评估,而在于是否要强调《圣经 》研讨的社会、道德和政治方面的意义。另外,在20世纪后半叶的研究高潮中,阿诺德 的“科学”或“圣经考证”批评并没有引起学者多大的兴趣,相反这种方法常被看作是 理解《圣经》文本丰富内涵的障碍。
对阿诺德提出批评的罗伯特·艾尔特当时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希伯来文和比 较文学教授。他是《圣经》纯文学研究的主要代表。他的两本著作《圣经的叙事艺术》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1981)和《圣经的诗歌艺术》(The Art of Biblical Poetry,1985)扎扎实实地从希伯来原文去查看了《圣经》,特别是《旧约》的叙事特 点和修辞手段,十分有说服力地显示了《圣经》文学性的高超,从而推翻了自奥古斯丁 《忏悔录》开始的认为《圣经》毫无艺术性可谈的定论。他受到奥尔巴赫的影响,但他 更主要的是用了犹太教士读经的方法(the midrash method),那是一种读者中心的多元 细读方法。艾尔特主要的贡献在于证明了《圣经》文本并非杂乱无章,它是个统一体, 结构上前后呼应,也有十分细致的人物刻画。艾尔特把《圣经》文本带出了宗教和神学 的藩篱。在《圣经》的诗歌艺术方面,他成功地归纳出希伯来诗歌的格律、模式和技巧 ,展现了它不亚于用任何其他语言创作的诗歌的成熟和精湛。
艾尔特和以他为代表的纯文学研究虽然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圣经》这个文本却不是 文学评论可以垄断得了的,把它完全置于文学批评之下引起了不少人担心,提出强烈异 议的代表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比较文学和诗学教授梅厄·斯腾伯格。斯腾伯格在其 代表著《圣经的叙事诗学:意识形态文学与解读的戏剧性》(The Poetics of Biblical Narrative: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1987)的前言里批评 了《圣经》纯文学研究。他指出《圣经》的确是文学作品,但它是意识形态很强烈的文 学作品,因此不能把它当成纯文学对待。斯腾伯格申言自己不是在搞历史研究,也不是 要进行政治和道德说教,他称自己的研究为“historiographical”,即在讨论《圣经 》诗学的时候紧密联系它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目的,从历史编纂学的视角来审视《圣经》 的叙事特点,以纠正纯文学讨论可能陷入的不负责任的文字游戏倾向。(注:Meir Sternberg,The Poetics of the Biblical Narrative:Ideological Literature and the Drama of Reading,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Chap.1,pp.1-40.)尽管斯腾 伯格在具体解读中也难免艾尔特等人有时出现的牵强附会,但是他的意识形态着重点确 实把《圣经》研讨又带回了阿诺德的初衷,把《圣经》置于宗教控制之外的世俗教育之 中,把它当作西方文学、文化和思想意识的经典来读,从而达到扬弃希伯来传统、正确 承袭希伯来传统的目的。
然而,进一步揭示希伯来传统在现当代巨大影响和意义的是杰弗里文章没有提到,但 也属于20世纪80年代的另一部著作,这就是马里兰大学教授苏珊·汉德尔曼(Susan Handelman)于1982年发表的《杀死摩西的人:现代文学理论中出现的拉比解读影响》(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该书追溯了希腊哲学的主要内容和精神,并把希腊传统与希伯来传 统,特别是与犹太教的拉比们阐释经文的做法进行了比较。她指出后现代的文论多元现 象实质是犹太传统对希腊哲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抽象思维的判逆行为。她的著作全面 地评介了希伯来宗教思想对当代文学批评的不容置疑的重大影响,显示了从弗洛伊德到 拉康和德里达,还有哈罗德·布鲁姆等人的文学理论如何体现和延续了希伯来的认知传 统。
汉德尔曼指出,文学解读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和理论有两个发端:一个是《圣经》的 阐释学,另一个则是希腊哲学中有关认知、阐释和解读的观点。她认为阿诺德提出的希 腊和希伯来的对立构成了西方文明在根本上的对立统一。这是雅典和耶路撒冷的对立, 是哲学和教会的对立,也是基督教徒和犹太人的主要分歧所在。(注:Susan Handelman ,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2,p.3,p.4-15,p.137,p.xviii.)在书中,汉德尔曼从希腊哲学的根本点谈起,即从古代希腊哲学家对语 言的功能及它与真理的关系入手来展示在认识论上它与希伯来传统的重大区别。她首先 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对语言(word)这个字的不同看法谈起。在希腊文里相当于word的字 是onoma,它与“名字”(name)同义。这说明,希腊人不认为语言等于存在,它只是存 在的事物的名称而已。名称是个比喻,有相当的随意性,由此希腊哲学认为语言和用语 言所表达的文学只是对现实的模仿,它自然不能与现实相提并论,它次于真(存在)和善 (行为),属于第三位的美(艺术/文学)的范畴。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希腊哲学的中心思想 就是逻各斯主义,强调本体(或终极存在)的重要性,并要超越语言去够及本体。
与希腊情况相反,在希伯来文中相当于word的字是davar,它与“事物/东西”(thing) 同义。因此,在希伯来传统,特别是犹太教传统中,语言和存在相当,两者一样重要, 一样可信,也就是说上帝的话/经文就等于上帝。结果是,在希伯来的读经传统中没有 对文字和语言的任何怀疑和保留态度,犹太教士个个从实际需要和自己的理解来细读经 文,并视各种解读行为都合理合法,而各种解读的内容都是对上帝指示的认识,不强调 对错之分。由于存在对经文是否等于上帝和真理的这个看法上的分歧,当基督教在希腊 影响下从犹太教衍生出来成为整个西方的宗教时,它的一大根本变化就是把原犹太教中 无形的、只靠语言代表的耶和华上帝具体化为肉身的耶稣。耶稣即是上帝的有形的代表 ,是个本体存在,而非虚无不定、变化多端的话语。这样,道成肉身则成为基督教与犹 太教的一大区别,也带来了《新约》与《旧约》的不同,它可以说是希腊哲学传统渗入 和影响了犹太教的结果。
接着,汉德尔曼回顾了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希腊哲学观,(注:Susan Handelman,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2,p.3,p.4-15,p.137,p.xviii.)然后分析当代多元文论现象,如德里达、利科、拉康等人如何强调语言 功能并否定有任何语言之外存在的思想这种与希腊哲学对立的观念。(注:Susan Handelman,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2,第15-2 5页。汉德尔曼在其后的章节里详细地剖析了拉比的读经传统背后的哲学思想以及后现 代文论代表们与这个传统的密切关系。)她还有趣地提到现当代的许多伟大思想家和科 学家都是犹太人(如马克思、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德里达、奥尔巴赫、布鲁姆等),以 此进一步说明现当代的多元思想、多元文化和文学理论现象确实与希伯来传统这一背景 有关。然而,汉德尔曼最后还是回到了希腊哲学的立场,她指出,虽然这些多元文论的 出现受了希伯来传统的影响,而且其目的是对希腊哲学理论的解构和挑战,但是这些文 论家们并没有能够完全追随摩西,回到犹太传统中去。以弗洛伊德为例,他曾经公开宣 称要解构整个西方本体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注:Susan Handelman,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2,p.3,p.4-15,p.137,p.xviii.)但 他因为受了希腊传统的教育和同化,挣扎在两种文化之间。他提出的心理分析理论实际 是力图把拉比的读经传统与德国的科学批评传统结合在一起,以达到用他的心理分析的 “福音”来取代摩西。
总结归纳汉德尔曼的剖析,我们可否认为现当代的多元文论现象是对阿诺德当初意图 的一个反动。阿诺德提倡思想自由,但反对无“理性光照”的无政府状态,即应该用完 美的理性(逻各斯)来支配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现当代的多元解读赞许的却是相对真理 ,这样不但杀死了摩西,也杀死了上帝,最后也必然杀死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 否可以认为现当代多元文论是用希伯来传统来助长了在阿诺德眼里比行为无政府状态更 严峻的思想无政府状态。其实,汉德尔曼在书里也点到了类似的意思,她引用杰弗里· 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的话指出:文论家们已经把世俗的分析理论变成了另一个宗 教,造成了混乱。(注:Susan Handelman,The Slayers of Moses:The Emergence of Rabbinic Interpretation in Modern Literary Theory,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2,p.3,p.4-15,p.137,p.xviii.)多元文化和解读使文学研究陷入 了没有积淀、没有定论、没有标准的混乱之中,否定你的前人,你自己不久又变成了下 一个解读所否定的对象,正如阿诺德所说:“对批评来说,是有一片能够看到的应许福 地,但是那块地方我们进不去,我们将死在荒漠里。”(注:见阿诺德的文章《当前批 评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转引自苏珊· 汉德尔曼著《杀死摩西的人》,第222页。)西方文明和文学批评最终是否将会如阿诺德 担心的那样成为一片荒漠呢?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不少学者的关注,他们纷纷撰文申张了 阿诺德传统,批评了后现代的多元文论的无政府状态。大卫·杰弗里在他的另一篇文章 “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灵性传统”(“Logocentrism and Scriptural Tradition”)(注: 这个译名是该文译者李毅先生的,其中的“scriptural”一字好像指的是圣经传统。) 中对哈罗德·布鲁姆和希利斯·米勒提出了批评,进一步指出了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文论 造成的认知无政府状态。杰弗里指出按西方哲学和神学传统,从奥利金(Origen)的新柏 拉图主义讽喻说到奥古斯丁在此基础上发展的象征说,都认为语言首先是表达意图的工 具,“而意义并不是寓于语汇之中,而是寓于作者之中。”(注:见杰弗里文章《逻各 斯中心主义与灵性传统》(“Logocentrism and Scriptural Tradition”),李毅译, 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2000年第4辑,第89-90 页。)类似希腊哲学的认知理论,奥古斯丁的基督教认知体系把语言作为一种“指代” ,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注:见杰弗里文章《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灵性传统》(“Logocentrism and Scriptural Tradition”),李毅译,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2000年第4辑,第92页及该页注1。)意义寓于被指代 的事物,而终极意义则寓于天地的创造这一事实及其先决条件——上帝,上帝是“置于 一切事物之上的事物。”(注:见杰弗里文章《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灵性传统》(“Logocentrism and Scriptural Tradition”),李毅译,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 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2000年第4辑,及该页注2。)奥古斯丁和他之后的基 督教理论家都认为符号和事物本身的混淆是一种偶像崇拜,是把语言强调到了不适当的 地位。上帝的道(God’s Word)和男人女人们的话显然是不同的:我们讲话用语言,上 帝讲话用事物、人物和事实,这在道成肉身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人的语言绝不可能超越 上帝话语之上,人的语言总是“对谈体”的,人不可能具有任何“绝对的话语”。(注 :见杰弗里文章《逻各斯中心主义与灵性传统》(“Logocentrism and Scriptural Tradition”),李毅译,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文化研究所主编《基督教文化学刊》 ,2000年第4辑,第93页及该页注1。)按照这种思路,语言虽然是多义的,但是在世俗 的解读和阐释中,它的多义应当围绕一个统一的中介体。这个中介体可以是文本的整体 结构或者是众所接受的阐释意见,而它同解读的关系在本质上是限制性的。因此,虽然 每个阐释者对文本的解读不会是惟一义,虽然每个看法的表述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它也 是片面的,决不是终极的真理。也就是说文本阅读是需要负责任的一种道德行为,应当 以一种有道德回应的方式进行。只有具备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文本研究和解读才有意义 。很多西方作家,如T.S.爱略特,也持这种观点。
然而,解构主义恰恰抹杀了文本理论中的道德准则。这方面的一个有力例证就是沃纳 和伊格尔顿围绕理查逊名著《克拉丽莎》的一场解读争论。1979年耶鲁结构主义学者威 廉·B·沃纳(William B.Warner)发表了《读<克拉丽莎>:阐释之争》(Reading Clarissa:The Struggles of Interpretation),在书中他大讲每个读者的阅读行为都 可以是对文本的强奸,而对克拉丽莎这样一个完美得令人乏味和讨厌的女人,最好的办 法就是穿透她、强奸她。沃纳置作者理查逊的意图于不顾,从文本里割裂出克拉丽莎如 何身着撕破的雪白衣裙跪求拉夫雷斯饶了她的这类例子,从而证明克拉丽莎一直在下意 识地引诱拉夫雷斯。其结论就变成克拉丽莎是自找的强奸,强奸犯拉夫雷斯不但没有错 ,而且他干得好,让读者都感到痛快。(注:William B.Warner,Reading Clarissa:The Struggles of Interpretation,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9 .参见pp.30-39,pp.42-49,p.80,p.268。)沃纳的解读是地地道道的不要作者的“自由” 解读,是不折不扣的不道德的阅读。沃纳的这部书激怒了马克思主义文论家特里·伊格 尔顿(Terry Eagleton),于是他撰写了《克拉丽莎之奸:塞缪尔·理查逊小说中的写作 、性欲和阶级斗争》(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il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来回应沃纳。(注:Terry Eagleton,The Rape of Clarissa:Writing,Sexuality and Class Struggle in Samuel Richards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2。参见pp.65-67。)书名中的“克拉丽莎之奸” 既指伊格尔顿要讨论的是拉夫雷斯强奸克拉丽莎这个议题,又一语双关地批评了沃纳的 解读强奸了《克拉丽莎》这本小说。在书中,伊格尔顿对解构主义黑白不分、毫无道德 准则的阐释的气愤溢于言表。
综上所述,近200年来西方知识界,特别是文化精英们,对始自阿诺德的对“希伯来精 神”和“希腊精神”在西方文明中地位的关注显然一直没有中断。事实上,这两种认知 方式和行为方式一直在互动中影响着西方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也成为当代多元化政治现 状以及多元文化和文学理论的重要认知背景。上个世纪盛行的解构主义等文论的逐渐衰 落似乎再次印证了阿诺德反对文化无政府状态的呼吁对当代仍具有指导意义。虽然社会 在发展,人类的认知也在发展,但我们完全可以肯定先进的科学科技和高度丰富的物质 资源都无法取代或否弃深置于西方文明中的“希腊精神”和“希伯来精神”的作用,它 们还将继续影响今后的西方文化和思想发展。也许它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强势、弱 势之区别,但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看来西方社会的终极理想、它的最佳状态只能 在这两种对立的认知体系彼此的抑制和互动中逐步实现。
